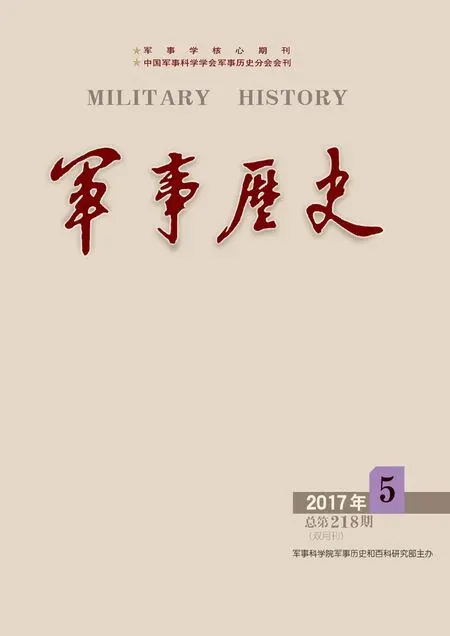高语罕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
2017-01-03★
★
高语罕(1887年8月1日~1947年4月23日),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中共早期建党建团的参与者,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辛亥革命前后积极投身推翻清王朝和北洋政府统治的革命斗争。大革命期间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等职,积极开展反蒋介石、汪精卫等右派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与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一起参加“小划子会议”,起义后起草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并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工作,抗战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对战争和政治的上的人心向背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担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主张暴力革命
1907年7月,高语罕在安庆陆军测绘学堂毕业前夕,亲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毕业后,到安徽督练公所测绘科工作。11月,炮营队官熊成基率炮、马二营发动起义。因为预定为内应的步营队官薛哲犹豫不决,未能及时打开城门接应,“马炮营起义”宣告失败。高语罕目睹了起义的全过程,从中得出教训:革命不是口说的,而是要用武力的,并且需要很有组织的革命武力。
起义失败后,高语罕的同事韩衍成为当时革命的实际领导人。高语罕和韩衍、陈独秀等经常聚会,筹划安徽革命。*李宗邺:《回忆高语罕》,转引自中共寿县党史办公室编:《寿县革命回忆录》,2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安徽也宣布独立。1912年1月2日,孙毓筠就任安徽省都督,正式成立皖省军政府,招韩衍襄助政务。韩衍遂发起成立“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在军事上,集合以陆军小学学生为中心的青年学生,组织了保卫省城治安的武装——青年军。青年军分三个大队,每队各设一个大队长和军监。在三个大队之上,设总队长与总军监各一。总队长由韩衍推荐的廖少斋担任,总军监则由韩衍自任,高语罕任青年军秘书长。
在韩衍遇刺身亡后,高语罕冒死为他掩尸,并对韩衍的《青年军讲义》做了详细疏证,取名《青年军讲义疏解》。书中,高语罕坚决反对革命党人和北洋派势力妥协,认为既然组织了革命的武装,必然地要承认暴力的必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今日但有弹丸政治”。这个“弹丸政治”并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单独行动,而是有组织的群众行动。“弹丸者所以资我造时事之器”,这就是承认暴力的催生的作用,并且认为暴力的实际目的乃是“经济的利益”。*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见韩衍《蓍伯遗著》,12页,安徽省图书馆藏。
随后,高语罕留学日本,与李大钊相识。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等人在江西湖口起义,宣布独立,发起“二次革命”。7月17日,安徽也宣布独立,陈独秀回到安庆,再次出任都督府秘书长。高语罕也从日本回国,同陈独秀等商讨对策。*王世平主编:《中国共产党芜湖历史》,第1卷,34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同时对革命阵营中许多人的颓废和消沉提出了批判。据高语罕回忆,“曾记得民国二年以后,革命党人多失意流落沪上,以我所知,多数人皆颓废不堪,天天等着革命到来,弹冠走马,绝不晓得潜心研究学术,做进一步准备工夫,更不知分析已往革命的失败,计划将来的进攻。”袁世凯病死后,上海的革命党人都喜极欲狂,高语罕却清醒地认为:“且慢高兴!袁世凯不过是北洋军阀的代表,他之帝制自为,并不是个人行动,只是封建的地主贵族的社会制度的产物。”“现在袁世凯虽死,而产生袁世凯的社会制度并未消除,将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袁世凯继之而起,以至于生生不已。”*张其柯:《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27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张其柯是高语罕笔名。
二、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提出打倒蒋介石的主张
1916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之初,高语罕即发表了《青年之敌》、《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岛茹痛记》等多篇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高语罕受陈独秀委托,参与建党建团的筹备工作。*张申府:《所忆》,1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1922年8月,高语罕赴德国留学,1925年8月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工作,并在上海大学任教。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高语罕与汪精卫、邵力子共同起草大会宣言,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里惟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他频频抨击国民党右派主张:“一个革命党员就是一个战士,他的行动完全要受党的指挥,尤其是参加政治的同志,如加入议会,加入内阁等等,要绝对的服从党的命令,否则即应以叛党论,立予除名,这才是真正有纪律的革命党。”“‘如何森严纪律?’‘如何严密组织?’‘如何改良宣传方法?’‘如何划一党军的教育?’‘如何专重党代表的职权?’‘如何使军队中长官诚心与党代表合作?’如何使军队长官诚心接受政治部的宣传不致过于阻挠?’‘如何应付时局?’‘如何规定保障工农利益的政策和纪律?’‘如何消释党中摇惑份子之疑虑?’等等,皆为本党现在及将来的生死问题。”*高语罕:《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1926(4)。
国民党二大后,高语罕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兼任毛泽东任所长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1926年3月20日,高语罕和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四人亲历“中山舰事件”,而被蒋介石称作“黄埔四凶”,高语罕被迫辞去政治主任教官职务。随后在一次演讲大会上,高语罕提出,要打倒产生北洋军阀的社会制度,“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蒋介石听说后,遂下令驱逐高语罕出广州。
1927年初,高语罕担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宣传委员会委员,旋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即连续发表14篇社论,严厉抨击蒋介石,被誉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之一。3月27日,高语罕以《‘反对’与‘打倒’》为题发表社论,列举了蒋介石制造南昌、九江、安庆惨案罪行:“自从本党发生提高党权运动以来,大家同志对于蒋介石同志一年以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三月二十)的行动,都表示不满。”“若果介石同志执迷不悟,不肯公开地在全党的最高机关,在全国民众面前,承认自己的过失,在行动上表现自己为革命而奋斗的决心,势必将党的纪律、党的主义、党的政策破坏无余,民众将离开本党,党的生命与国民革命的成功,都将变成幻想。那时,我们便不能姑息蒋介石同志个人,一定要群起攻之,便是‘打倒蒋介石’!”*高语罕:《“反对”与“打倒”》,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03-27。
1927年4月18日,武汉政府任命刘伯承为暂编第15军军长,高语罕为第20军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20军党代表本为朱德,此时朱德应老同学朱培德邀请,去南昌任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因时局变化,高语罕赴20军途中折回武汉。
三、任第2方面军秘书长,参加“小划子会议”
1927年6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张发奎为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高语罕与张发奎关系较近,特被聘为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同时为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决定把中共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的第2方面军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再由九江、湖口向安庆进发。表面上,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较好,并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共回粤的意向,中共中央也有利用“东征讨蒋”、“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7月11日,叶挺率第11军24师为“东征讨蒋”的前锋,向九江开拔。随后,黄琪翔的第4军、贺龙的第20军也陆续向九江地区集结。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在武汉公开“分共”。高语罕随同第4军在半秘密状态下赴九江。第4军军部设在庐山脚下甘棠湖心烟水亭中,这里相传是三国时东吴周瑜的水军都督府。高语罕同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就相识,他俩每天傍晚在湖中划船消遣。
此时,中共中央还没有明确打算在南昌起义,仍是依张回粤徐图发展,只是强调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7月20日,在九江的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五人,在九江租界海关召开谈话会。认为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反对武汉政府。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南昌起义问题。7月21日,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向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了九江谈话关于集合叶、贺部队在南昌起义问题,得到赞同。7月22日,瞿秋白、邓中夏把“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带回武汉,请中央即速决定。22日,鲍罗廷、李立三、张太雷与聂荣臻、林伯渠继续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张太雷把研究意见带回武汉。
此时,南昌起义能不能举行,除了等待中央指示外,还要看贺龙的态度,如果20军不参加,起义也不能举行。7月23日,贺龙到达九江,至此,贺龙的20军全部集结九江。高语罕一面等待中共中央的批复,一面积极争取尚未入党的贺龙参加起义。据1932年《上海周报》杨甫的《高语罕在上海》一文介绍,贺龙之加入共产党,也受了高语罕一定的影响。
7月24日,汪精卫准备召集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是要在第2方面军中“分共”。江西省政府主席、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第4军军长黄琪翔邀请第20军军长贺龙、第11军副军长叶挺到庐山开会,准备夺他们的兵权。7月25日,高语罕与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以游湖为名,在甘棠湖一只小船上召开紧急会议。当时议定:叶挺、贺龙不参加次日由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会议;叶挺、贺龙不按照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命令去德安集中,而是依次把自己的部队开往南昌,贺龙部队先给叶挺部队让路。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极端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晚年多次谈到“小划子会议”。一次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个人,有叶剑英、叶挺、贺龙、高语罕,还有一位不肯定。另一次告诉萧克说:“是廖乾吾。我、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叶剑英:《南昌起义二三事》,见沈谦芳主编:《亲历南昌起义》,108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7月27日晨,张国焘来到九江,召集高语罕、贺昌、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开会,传达头天中共中央常委研究的暂缓发动南昌起义的决议。他说,他来的任务是看看地形,与大家讨论南昌起义的事情。高语罕等坚决反对推迟起义时间,并说再无讨论的余地。此时,由中共九江市委直接领导、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名义主办的九江《国民新闻》向高语罕约稿,揭批汪精卫。高语罕就发表了给汪精卫的一封公开信,说他只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一碰到实际政治的紧要关头,便要动摇。
汪精卫从报上看到声讨他的文章以后,对《国民新闻》恨之入骨。7月29日晨,汪精卫和孙科、张发奎、唐生智等从武汉坐船抵达九江,他一到九江码头就下令,立即停止出版《国民新闻》。
7月30日,汪精卫等在牯岭开庐山会议,决定在第2方面军实行 “分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叶剑英参加了庐山会议,散会时已近黄昏。他派人星夜下山,到烟水亭向高语罕报警。
高语罕接到叶剑英密报,已是7月31日凌晨两点,立即搬至南浔路对面的大东旅馆,清晨即乘车赴南昌。到了南昌,高语罕立即给叶挺打电话,叶挺让他马上到司令部。高语罕到司令部时,已是7月31日深夜。
四、起草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起义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
1927年8月1日上午,参加南昌起义的7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韩麟符以及38名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当日,南昌《民国日报》以显著版面刊登了高语罕起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是由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的15名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联合署名的。宣言严厉地揭露并斥责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反革命面目,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的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与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高语罕:《中央委员宣言》,载南昌《民国日报》,1927-08-01。
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三次北伐。高语罕一路上生病,开始在叶挺军部,后来又转到贺龙军部。这是一次长途行军,高语罕随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9月23日、24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9月30日早晨,起义部队撤离汕头,抛弃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达了挂红旗的决定。此时,周恩来找到高语罕,安排他到香港,去与张发奎、黄琪翔接洽联络。
高语罕到香港与张发奎联系未果,经军委同意,先到澳门杨匏安家里暂住。高语罕和杨匏安都是中共五大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澳门小住时,高语罕认真反思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教训,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原因。
“(A)政治上的。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纲在民众中宣传,而且头上还戴着倒霉的国民党左派的帽子,其实国民党何尝有左派,只有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左派这个名词,一到时局紧张,便出了空虚。所以做政治工作的,一路之上,只有吃饭睡觉,闹得不但民众不晓得我们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军中的士兵,也大半不明瞭。还有说这是叶挺、贺龙想做军长、总指挥罢了。而且我们国民革命直到社会革命的中心问题,只是‘土地革命’。但是,在路上就没有听见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在民众中切实宣传过,更谈不到实行。当时大家都抱着秋毫无犯,王者之师的梦想(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得不到民众的帮助,这是‘八一’事件政治上的失败。”
“(B)军事上的。我们同志负责军事责任的,很少对于战略上战术上能以担得起指挥大部队作战的(刘伯承同志还好,但广东地形情势不熟悉),比如当时名义上四个军长:十一军叶挺、二十军贺龙、十五军刘伯承、九军朱德,大致除了刘伯承同志之外,都犯了一个毛病——轻敌——疏忽。至于不取道筠门岭直捣敌人的中路,以摇撼广州,而乘其未备,这是军事上的失败。”
“(C)组织上的。我们在军中对于小组会议,没十分注意,这是大的缺点(这是我就亲历者说话,因为我没有参加小组会议,便说不注意,也许是有),弄得军部C.P.与非C.P.的同志不能发生十分的联系。”
高语罕也表示了自己对于中央的最近政策的意见:“对于中央最近的政策完全信任,必须这样才可以战胜党内的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等危险的倾向。现在革命已到了极其严重时期,如果党没有绝对的威权和积极的适当的政策,是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的。”*高语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见沈谦芳主编:《亲历南昌起义》,82~84页。
五、翻译、传播马列主义,关注政治、军事上的人心向背
大革命失败后,高语罕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政治信念,抱定为真理而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勇敢精神,编译了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唯物论史》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康德的辩证法》《费希特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等著作;撰写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白话书信》《白话书信二集》《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怀念牺牲战友的《百花亭畔》《九死一生记》、宣传抗战的《烽火归来》《一日一谈》《入蜀前后》等著作;撰写了《青年书信》《读者顾问集》《国文作法》《红楼梦宝藏》等著作,引导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个人前途和社会问题、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为中国未来撒播革命火种。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救亡运动弥漫全国,高语罕没有袖手站在救亡运动的圈子之外,“眼底战场应有我,哪堪憔悴作诗人!”2月7日,高语罕和丁玲、王亚南、施存统、陈望道等成立著作者抗日会,发表宣言,要求全民抗战,反对政府之不抵抗主义,拥护第19路军。随后,高语罕和久居上海的程演生、李季、王独清等人,发起整理《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高语罕在《明亡述略》中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指出:“人民大众的心理向背是决定民族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权谁属的唯一因素,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以拉拢这一因素为己助,而取得政权,后来也就以欺骗这一因素,失去他的拥护而毁灭,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法则’。”*王灵皋辑录:《崇祯长编》,序言,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王灵皋是高语罕笔名。
1937年8月初,淞沪会战爆发,高语罕给张治中发了一个电报:“抗战既起,举国兴奋。弟十年伏处,偷生海隅,际兹时会,已不愿再事苟活,决计回国驱驰军前,觅一死所。”*高语罕:《烽火归来》,7页,上海,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1939。高语罕又给张发奎发去一封信:“内战把我们离隔了十多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却又把我们打成了一片。中国人老话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西方革命家也说‘革命须待反革命的鞭策’,都可说明我们这次抗战是翻开伟大历史新页的一个破题儿。先生适在这个战场上任了一员开路的先锋,我们这些以前的战友,自然都很引以为荣幸!并对抗战前途增加了不少的信任。”*高语罕:《烽火归来》,110页。高语罕先后到张治中、张发奎的部队前线观察,因战事发展又回到南京。
这时,黄埔军校老同事陈立夫约高语罕谈话,高语罕告诉他,从观察到的现象看,这次战争只是单纯的军队在和日本动员了全国的军队作战。“但是为什么北伐时的中国农民那样热烈的参加反军阀的内战,而现在对于对外抗战,却反倒这样冷淡和旁观呢?”“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之下,经过国民党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宣言与适合工农大众之政治的经济的要求的政纲。全国工农大众都相信这个政纲是于他们有利的,并且是马上可以实行的,所以他们拼死命地来拥护国民革命的北伐。”“但十余年来,演成自相残杀之局,农民对国家只感到痛苦和憎恶,无以聊生;就是日本人来了,也不过是无以聊生。假使前方战事失利,军警特务队失却镇压的力量,公务员一逃,政府动摇,汉奸伙着流氓便出来统治南京,这是多么危险啊!”陈立夫邀请高语罕出来工作,高语罕拒绝了,表示“愿以平民的资格,用某一点一滴的力量,在社会方面参加抗战的活动。自然,我的政治信仰,并没有改变,而数年以来,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此后一切言行,都集中于抗战。”*高语罕:《烽火归来》,87~98页。
1938年初,经胡宗南介绍,高语罕到重庆为抗战做事,拟了一个抗战纲领,指出:抗日战争为革命战争,新时代之革命战争,必有新的革命军队,新的革命干部,始足完成此伟大之使命;中央对于全国军队,应不分畛域,待遇平等;全国军官士兵之生活,宜尽可能使之相差到极小限度。*高语罕:《入蜀前后》(2),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2)。
在《前线的安徽》创刊号上,高语罕发表了《民众总动员问题》,提出三个具体的主张:“第一,必须平素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人,才能完成总动员;第二,必须为民众而奋斗的团体,即民众自身自动组织的职业团体,如职工会、农会、商会等才能以动员民众;第三,必须顾虑到民众的生活,方能动员民众,才能完成民众的总动员。”*高语罕:《入蜀前后》(2),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2)。
1942年的《读书通讯》自51期至55期,曾连载高语罕长文《管子的战争哲学》。高语罕强调管子的战争哲学的特点,最重要的是战争须先得民心。“政之所兴,在得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心向背是政治的基础,是国家兴衰的关键。要发动战争,必先得到人民的拥护,要得到人民的死力,必使其在实际生活经验中,深切感受到战争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发动。
高语罕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日本的必败丝毫未尝置疑,在1945年7月11日的《罕庐座谈》便断定:“日本的士气必然摧毁。”*高语罕:《入蜀前后(11)》,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12)。9月30日,高语罕为《新民报》作《日本的政治前途》社论,指出战败的不是日本国民,而是日本的天皇政治。*高语罕:《九死一生记(3)》,载成都《新民报》日刊,1945-08-18(4)。高语罕还对抗战胜利后国内战争形势进行了预判。10月24日,他在《新民报》社论中提出:“吾人对于团结问题固具有极迫切和极热烈的愿望,但就政治经验与历史常识而论,此一谈判固必成功,惟吾人对于此一谈判之结果万不可过存奢望,过于幻想,否则,必将陷于不可宽恕的错误。因为讨论国家的政治问题,丝毫不应当从什么‘忍让’、‘诚意’、‘容忍’等等道德观念出发,应该完全从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实际利害出发。”*高语罕:《入蜀前后(12)》,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13)。稍后,高语罕在另一篇社论《政治与战略》中指出:“盖一个国家之中,有两个政治信仰不同,而利害冲突至巨的军队,绝不能同时并存,绝不能和平相处,此证之古今中外之历史而莫或例外者也。”“吾人敢正告国人曰:‘团结谈判希望不大,内战似难避免。即勉强妥协,其为时也亦必至暂。斯言虽苦,却将成为历史真理!’”*高语罕:《入蜀前后(12)》,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13)。
1947年4月23日,高语罕病逝于南京中央医院。时人感叹:“博学能文又健谈,江淮革命著先鞭。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