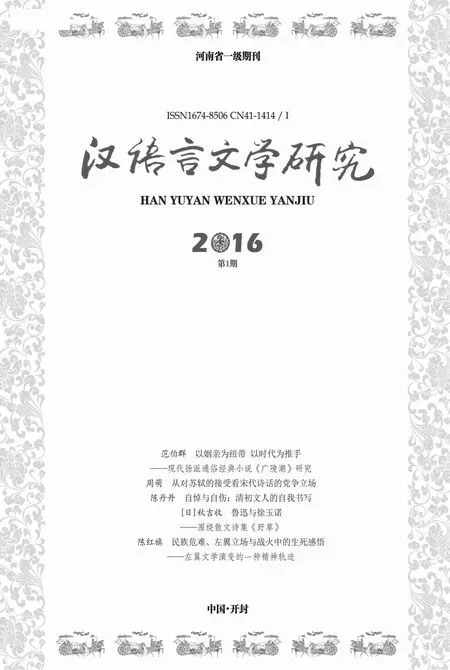浅谈“铅字时代的中国小说”
2016-12-28马正锋
马正锋
浅谈“铅字时代的中国小说”
马正锋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和分析了“铅字时代的中国小说”这一提法可能引发的思考。文章从中国的近代印刷出版业切入,对“铅字时代”做了界定,认为中国小说在此时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整体上讲是读者、出版社、作者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三者的此消彼长,影响了小说的方方面面。“文字改革”对于小说写作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中国的“文字改革”在时间上又几乎始终伴随着“铅字时代”,本文也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作了考察与梳理。
关键词:铅字时代;小说;近现代出版业;文字改革
一、中国的铅字时代与近现代出版业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铅字代表了具有较高权威和信誉的文化和知识。“希望早日看到您的文章变成铅字”,即使在今天,读书人仍会用这句话来表达相互间的恭维。当然,一般情况下,铅字本身当然不能算是文化或者知识,它之所以与后二者产生如此密切的关联,是因为它是后二者的载体——“书籍”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铅字”一词的广泛使用,应在西方近世印刷术传入和发展之后;它为读书人所认可,继而成为某种文化的载体或者象征,则要晚至清末最后几年。
在近代铅合金活字传入之前,中国已有铅活字印刷。明朝的陆深在《金台纪闻》中说:“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版印尤巧便。”①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李兴才审订:《中华印刷通史》,台湾: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2005年修订版,第426页。清人魏松《壹是纪始》记载:“活版始于宋……金又用铜、铅为活字。”②同上。中国活字印刷术较为简陋,其相较于雕版印刷并无明显优势。木刻活字印刷尚且没有成为印刷之主流,更遑论铅活字印刷了。
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石蜡③或译“郭士力”“郭石猎”。(Karl Gutzlaff)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戈公振称“此报发刊于中国境内,故我国言现代报纸者,或推此为第一种,因前三种(按:指《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特选撮要》与《天下新闻》)皆发刊于南洋也。”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湖南: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0页。郭石蜡不但编报,还制作了中文字模,用于浇铸铅字。在他之前,马礼逊、戴尔也一直在研制中文铅活字。在他之后,又有美国教会、法国人葛兰德、法国皇家印刷局等单位或个人,也为铅活字铸造技术的完善做出了贡献。1842年,鸦片战争以大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戈公振称:“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香港以鸦片战争之结果,割于英。英华书院即由马六甲迁至香港。斯时教士之所从欧美来者渐众,所制中国铅字亦渐完备,于是出版事业日兴。”⑤同上。1859年,姜别利(William Gamble)在宁波创制电镀字模,从而有效减少了刻字工时,显著提高了铅活字的质量和数量。他还仿造西方活字规格,将汉字活字分为七种型号。1869年,日本人在姜别利技术的基础上,美化了七种活字的大小和规格。此后,这种铅活字及其确立的汉字活字规格,为中日两国长期使用。
现代报业与铅字印刷关系紧密,中外概莫能外。近代报业在中国崛起,是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国内维新运动的发展而明显起来的。这一状况的缘由,一则是清末炙人的国内局势之刺激,有识之士言说的欲望远高过以往;二则是清政府中兴派官员为救亡图存,亦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尽管仍多局限于器物层面;三则是始于19世纪20年代传教士的中国近代报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办报之经验,尤其是技术形态,已经为较多国人所熟知,传教士的实践可以说为国人办报在思想和物质方面做了准备。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之第四条,即主张办报。梁启超引用日本人犬养毅所谓“文明传播三利器”说:“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①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1页。直到光绪帝于1898年6月下令变法,开放报禁,准许官民自由办报之后,中国的报业才迎来第一个勃兴时期。报业为扩大影响力,追求“新闻性”与“时效性”,而后者又是前者之重要保证。在物质层面,铅字印刷因其速度和质量优势,又成为保证报纸之“时效性”的武器。由于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报业的发展,社会上对于印刷机械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根据芮哲非的研究,最早在1895年,在中国上海已经出现了中资的印刷机制造厂商,他们可以生产和维修印刷机②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31页。。铅字印刷技艺的进步,随着近代报刊出版业的发展亦获得了同步的发展。
中国的“铅字时代”的起讫时间,当在19世纪末使用铅活字印刷的中文报刊之大量的出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电脑取代、淘汰铅字成为汉字处理的主力为止。在起点之前,或有铅活字或少量的铅活字印刷,在讫点之后,或有特殊出版之需要而使用铅活字印刷,似不足以在整体上否定上述判断。
陈平原先生将新小说视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而新小说的诞生则需要从1898年讲起。他说:“戊戌变法在把康、梁等维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把新小说推上了文学舞台。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的阵地。此后,刊载和出版新小说的刊物和书局不断涌现,新小说始蔚为奇观。”③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在新小说出现之前,文学类文章虽然未在近代中文报刊缺席,但绝非彼时报刊之主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第三章《外报初创时期》中罗列了最早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刊于1815年)至《大同报》(创刊于1906年)主要的外国人办中文报纸,并简要介绍了它们的内容。它们存在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纳入铅字印刷的时代。其中,杂志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新闻、宗教、政治、科学、历史、商业、杂记等,含有文学的杂志仅列出《中外新报》《中外杂志》两种。进一步细查二杂志之所涉文学内容,也以旧诗词为主。此外,白瑞华所著《中国报纸(1800-1912)》,亦提及几乎同一时期重要的中文日报之情况,包括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循环日报》(创办于1873年)和《华字日报》(创办于1872年),上海的《上海新报》(1846年创刊)、《申报》(创办于1872年)、《万国公报》(1875年由原《教会新报》发展而来)、《小孩月报》(1875年创办)、《格致汇编》(创办于1876年)、《沪报》(创刊于1882年)、《新闻报》(创办于1893年)等。除了《申报》之外,其他报刊似乎均未将文学作为其重要的内容构成。即便是《申报》,在它的早期,虽然第一任编辑钱昕伯计划将其办成“小说、诗词韵文和小论文等体裁的综合性报纸”,第三任主编黄协埙将其改版为“更加具有文学性的报纸,使报纸为更多的文人读者所接受”,但是“这样的改进在19世纪末才得以进行”,而“报纸的成功首先归于新闻报道”。④[美]白瑞华著,王海译:《中国的报纸(1800-1912)》,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上述有关19世纪中国报刊情况的简要考察,或可旁证陈平原关于新小说之崛起于世纪末,并视其为20世纪中国小说之开端这一判断。的确,在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之前,国人对于小说之于社会的作用仍评价不高,近代报刊尽管是彼时充满新鲜气象的事物,它们对于中国小说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也十分有限。因此,本文认为近现代中国小说之于铅字时代发生可靠的关系,当在“新小说”兴起之后。由于“铅字时代的中国小说”这一提法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切入,探讨铅活字印刷所导致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对中国小说生产过程的影响显得尤为迫切。
二、铅字时代与中国小说
铅字时代的中国小说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出现大多基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报纸、杂志和书刊的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而伴随着晚清社会整体的现代化步伐,尤其是交通运输业、通信电讯事业发展带来的传播速率的提高,以报纸杂志和书籍为载体的近代中国小说在晚清迎来了第一个勃兴时期。阿英《晚清小说史》第一章即指出晚清小说的繁荣局面形成的第一个原因就在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①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1847年王韬参观墨海书局的时候,看到的是用牛拉的活字版印刷机,每天印数千页以上;1872年《申报》刚刚创办的时候尚且使用手摇轮转机,到1890年引进煤气动力印刷机,速度提高了三倍,再到1916年使用日本制造的新式卷筒轮印刷机时,每小时印数已经达到8000张。又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这家初创于1897年的出版机构,一开始只有两部手摇印刷机、三部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搬压印机,经营的业务多以账本和表册为主。到了1900年,商务印书馆收购了经营不佳的日本修文书馆后,才获得了较为先进和完备的大小印刷机、铜模和铅字制作材料,随后在1902年分设了自营的印刷所。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金港堂合资,学习到了日本的印刷技术和管理经验,刻印能力大大提升。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始终关注出版设备的改进和提升,他始终跟踪和积极运用发达国家相关的最新技术发明,还注重自我的创新,他亲自改造了姜别利发明的元宝式排字架,不但缩小了字盘占地面积,还大大减轻了排字工的工作难度,提高了效率。另外一家重要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亦十分重视技术手段的提升。根据陈平原的统计,由于新学知识分子的大力推荐,小说读者的群体由粗通文墨的“愚民”扩大到所谓士子,由是导致清末民初的小说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比重极大,而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至1920年间出版的书籍中,有四分之一为文学书,而所谓的文学书绝大部分又是小说。②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7页。可以说,正是到了铅字的时代,小说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平台、更广的传播面以及更多的受众,从而才有可能更显著地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铅字时代的中国小说所面临的新问题,从整体上讲,是读者、出版社、作者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三者的此消彼长,影响了小说的方方面面。更准确的说法其实应该是:由于铅字时代印刷工业技术的发展,为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中国小说正是在近代报纸、杂志和书籍的登载和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平原曾指出:“清末民初报刊出版业的繁荣与小说市场的迅速拓展对文学界的影响,远不只是促进了著、译小说数量的增长,而且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力量,直接介入了中国小说形式变革的历史进程。报刊登载小说与小说书籍的大量出版对小说形式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传播方式的转变促使作家认真思考并重新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小说创作不再是藏之名山,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古代小说家好多生前不曾刊印自己的作品,而‘新小说’家迟则十天半月、快则一天两天,就能见到自己的精神产品以书面形式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作家不再拟想着自己是在说书场中对着听众听故事,而是明白意识到坐在自己书桌前给每一个孤立的读者写小说。说起来简单,似乎不过一念之差,可在中国却是走了几百年的历程才完成的小说观念的转变。”③同上,第91页。作家创作意识的转变从注重“说-听”转为注重“写-读”,从而导致了小说创作的“诗化”、“文人化”和“书面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小说脱离了一般民众的审美趣味,而使得“旧小说”仍旧有较大的市场。当然,如果在更大意义空间中看待“中国小说”,而将所谓“新小说”与“旧小说”均纳入“中国小说”之麾下,可以说,在铅字时代,此二种小说都受益于印刷工艺的进步,而不同处在于前者的目的主要在“启蒙”,后者的目的主要在“娱乐”。
以一部具体的中国小说而言,它在中国的铅字印刷时代里,一般需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作者的构思、编辑的选取、出版机构的审查、印刷厂印制、读者阅读。而读者的反馈意见,包括个体读者的具体意见,亦包括由销量为依据的读者群意见,将返回至作者和出版机构,从而影响作者下一步的构思,也影响出版机构对于作品的选取。此外,印刷厂的印制,还受到印刷机器先进程度的限制,受到工人工作熟练程度的限制。显然,好的出版机构,好的印刷厂,好的发行渠道,与之配套的评论体系,都有可能对小说的流行程度产生影响,或者说对于小说市场的优劣产生直接影响。上述影响回溯而来,又可能导致小说生产各方面的调整。比如说:出版社的编辑策略、书籍的装帧、印制的纸张及油墨、发行地域的调整、上市的时间、评论界文章的组织等。不难发现,上述小说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旧时的同侪。
以出版审查为例,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出版管理办法,对于书籍的出版管理,主要根据最高统治者或者地方行政长官的意愿,依靠强令来实施的。1901年《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公布,《苏报案》曾援引此律相关条文判决。1906年6月,清政府刊布《大清印刷物专律》,专门应对维新运动之后大量出版的各类书报刊,该律法规定设了印刷总局,管理“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对出版和发行的诸多事项进行了说明,关于违反规定的处罚尤为详细。1907年12月,清政府颁布了《大清报律》,凡45条,内容包括报纸的注册、经营限制事项和违反者的处罚规定。除了政府审查,著作权的保护也是出版业必须面对的问题。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刊行,虽然清朝很快灭亡,但是该法律因从保护著作人的角度而制定,其思想基本为后来的民国所继承。后来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亦制定了多种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条文成为当时出版业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也成为作者在创作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来自读者和市场的反馈,对外翻译传播的需要,也将影响到作者的创作思路,促使作者对小说的情节、结构、语言文字等作出调整或改变。上述问题,此处不一一分析,但可以肯定是,中国小说在这一时代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在以往虽然或有萌芽,但并不会对小说的整体构成产生影响,而在此一时代里,则可衍生出诸多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而越来越与外在于它身上的其他因素发生联系,从而使得其复杂性越来越显著。
三、铅字时代与汉字改革
“汉字改革”成为一个问题,当在19世纪下半叶。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在厦门刊印,书的主要观点,是对汉字进行拼音化改革。于是,此书开启了中国的汉字改革,这一年也常被认为是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始。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出版,梁启超评论该书说:“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3页。书中跋说道:“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所同与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所在,然后蒙童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②马建忠:《马氏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页。几乎与之同时,章太炎亦对汉语言文字的诸多问题进行着思考,最早于1900年刊行的文集《訄书》中即有多篇涉及语言文字问题,后章太炎在日本还与“汉字统一会”辩论汉字改革问题。在《小说要略》结尾中,章太炎说:“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源,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又说:“大凡惑并音者,多谓形体可废,废则言语道窒,而越乡如异国矣!滞形体者,又以声可遗,遗则形为糟粕,而书契与口语益离矣!”③可参考上下文: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汉字自古籍以下,改易殊体,六籍虽遥,文犹可读。古字或以音通借,随世相沉,今之声韵,渐多讹变。由是董理小学,以韵学为信人。言形体者如《说文》,言故训者如《尔雅》,言韵者始《声类》;《广韵》者,今韵之宗,其以推迹古音,犹从部次,上考《经典释文》,下及一切经音义,旧意绝响,多在其中;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大凡惑并音者,多谓形体可废,废则言语道窒,而越乡如异国矣!滞形体者,又以声可遗,遗则形为糟粕,而书契与口语益离矣!末代清政府之学部,也曾在1912年提出了统一国语办法案,终因亡国而未能实施。民国之后,中国思想变动之剧烈更甚于以往,而语言文字作为文明的载体,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制定第一套法定的注音字母,并于1918年正式公布。新式学堂的小学生由此开始先学注音字母,后学汉字。“五四”一代,对于汉字改革,更是提出了一些极端的观点。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刘复、叶籁士等人不但为汉字改革运动摇旗呐喊,还以实际行动提出了多个具有操作性的建设方案。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非常重视文字改革。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的关心和指示下,政府先后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①参与上述委员会的有吴玉章、马叙伦、丁西林(丁燮林)、胡愈之、黎锦熙、罗常培、王力、韦悫、陆志韦、林汉达、叶籁士、倪海曙、吕叔湘、周有光、叶恭绰、朱学范、邵力子、季羡林、林汉达、胡乔木、胡愈之、傅懋勣、叶圣陶、董纯才、赵平生、聂绀弩、魏建功;审定委员会的委员有张奚若、沈雁冰(茅盾)、许广平、朱学范、邵力子、张修竹、项南、徐忻、老舍、曾昭抡、邓拓、傅彬然。1955年,由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简化汉字修正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1956年1月31日,《汉字简化方案》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毛泽东也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②见王爱云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
同年八月,《拼音》杂志创刊,作为讨论汉字拼音化的一个主平台。刊物名为《拼音》,可见汉字拼音是汉字改革之重要内容。1957年,该刊更名为《文字改革》③1986年,该刊又更名为《语文建设》,至今仍出版。,更是汉字改革这一个话题明确化的标志之一。该刊物中头两年的文章,主要以支持扩大汉语拼音的使用、大力推行简化字为主,偶有批评,也多从修补修订角度出发。王重言《关于汉字改用拼音字的商榷》是少见的直接对拼音化表示怀疑的文章,但他的文章受到了较多的批评,不过主要还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然而,“反右”扩大化之后,刊物学术性即有很大的下降,“汉字简化”和“汉字拼音化”基本成了攻击的武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恢复。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对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的汉语文字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以及执行国务院所决定的对于文字使用方面的政策和法令。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为了打消人们关于“汉字”与“拼音文字”的疑惑,中国政府在1958年曾正式声明,称“拼音”不是“拼音文字”,汉字才是中国的正式文字,而拼音只是辅助的表音符号。周有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汉字改革的主要参与者,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国的汉字改革做过总结,他说:“1958年把文字改革工作归纳为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④周有光:《中国的汉字改革与汉字教学》,《语文建设》,1986年第6期。现在看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这些任务得到了较好的完成。
在上述简要回顾中,关注汉字改革的研究者从很多方面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但是较少有人从印刷这一角度来看待汉字改革活动可能带来的影响。在《文字改革》上,仅有几则新闻信息类的文章涉及到了这一角度。发表于1957年10月份的题为《注音汉字铜模铸成》是则简短的消息,全文内容如下:为了便利大量出版汉字注音读物,文字改革出版社已制成注音汉字铜模,向国庆献礼。与此同时,他们还制出音节铜模和声韵母铜模。这些铜模的制出将大大提高拼音出版物的质量和生产速度。《我们开始按照音序进行字架改革工作》一文来自屯溪日报印刷厂的技术工人吴扬荣,他自称受注音字模铸成消息的鼓舞,而对本厂排列字架进行技术改革,并认为按照拼音顺序改革字架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
上述两篇文章主要还是通过印刷工业的实际应用情况来关涉到汉字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而较早的关于印刷工业与文字改革关系的深入思考则来自郭沫若。在《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①文见1964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文字改革》1964年第6期、《科学通报》1964年第5期均转载。一文中,郭沫若详细介绍了日本在二战后十余年间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情况。他认为日本的汉字改革循序渐进,而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因而能够平稳的过渡,完成了对汉字的改革。他说:“日本能够把一般用的汉字规定为一千八百五十个,把小学用字规定为八百八十一个,这是由于有日本字母假名,并发挥了假名作用的原故。日本小学课本的编制,开头全用假名,继后逐渐在假名中渗入少许汉字。这样就减轻了儿童学习汉字的困难,并培养了儿童用文字表示语言的能力。汉字就不会成为‘拦路虎’了。这个经验,似乎是值得我国重视的。”他又认为:“看来,他们的目的是在通过日文的罗马字化以促进事业的效率化。据说,用日文罗马字,术语用原文,便可以用拉丁字母打字机打字,速度便和欧美人不相上下了。这是从实业方面发起的促进日文拉丁化运动,看来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运动。”关于文字工作的机械化,郭沫若认为文字工作的机械化要求文字的符号单元不宜过多,拼音文字能够适应这个标准。汉字则单元太多,即便制成机器,使用还是不够灵便,效率不高而成本不低。日本就是因为假名的使用以及日文罗马字的使用,能够较快地走上文字机械化、自动化和高速化的道路。他又以汉字打字机和字母打字机作比,指出汉字打字机单是字模就有几千个,而字母打字机仅需几十个字母和必要的符号,无论是携带还是应用,前者均远不如后者。郭沫若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对印刷工业中汉字印刷与字母印刷作业进行对比,但是不难推论,在铅字印刷时代里,汉字出版物比之字母文字出版物,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有着天然而巨大的劣势。或许是因为如此,后来甚至有研究者认为铅字是汉字的克星,因为对于西方来说,铅字时代使其摆脱愚昧,走向繁荣;而对于中国来说,铅字时代恰好与近现代民族的屈辱受难史同期。同时,他们还认为近现代以来主张汉字改革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因为始终生活在铅字时代,只能看到汉字机械化处理能力低于拼音文字这一情况,他们做出的改革汉字的言行,都是可以理解的。幸运的是,随着电脑时代的到来,上述汉字相对于字母文字的劣势已经不那么明显了,而且在新式的印刷出版工业所涉及的所以技术层面里,汉字甚至还有了某些优势,比如在存储、输送和检索方面,通过特定的运算法则,汉文的表现将优于英文。②许寿椿:《用铅字时代思想“规范”电脑化了的汉字,必将碰壁——评说〈通用规范汉字表〉》,《汉字文化》,2010年第1期。
中国的铅字时代似乎与汉字改革处于同步,但是二者的关系却不容易把握。一方面,二者在时间上确乎有所呼应;另一方面,汉字改革之缘起和发展过程中的确少见技术物质层面的探讨,似乎政府只要依靠行政能力即能完成改革,而且主要依托教育来完成。正如前文曾经提到,时至今日,汉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基本得以完成:简体字是国家法定的流通文字,注音成为学习汉字的第一步,普通话早已风行全国。正如周有光在《中国的汉字改革和汉字教学》最后一段文字所表述的那样:“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汉字和汉字文化也是发展的。一方面向古代发展,一方面向将来发展。向将来发展必须扩大文化的领域,使东西方文化合流。汉字和罗马字是一对情侣,他们俩,东西相隔十万里,不通音信三千年,现在来到一起,结成姻缘了。这象征着文化孤立时代的结束,文化合流时代的来临。祝愿汉字和罗马字百年好合,各尽所长,分工并用。”可以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跋中期待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付国锋】
作者简介:马正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