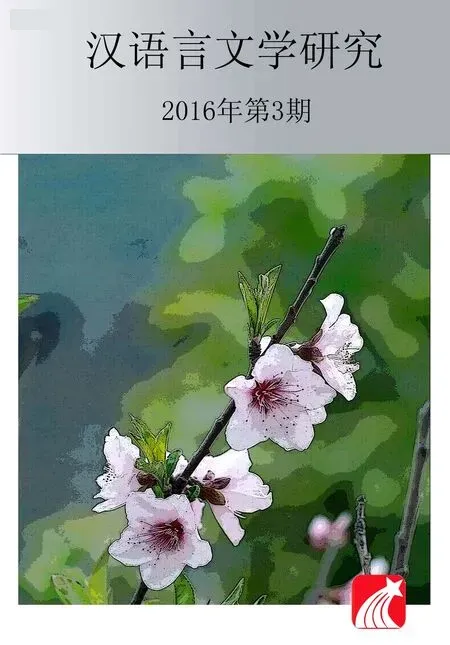抒情美典的追寻者:奚密现代汉诗研究述评
2016-12-27张森林
张森林
抒情美典的追寻者:奚密现代汉诗研究述评
张森林
美籍华裔学者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独树一帜。本文以奚密的诗论集《台湾现代诗论》为中心,围绕其对台湾现代诗的创作特质和文学思潮的细致论述,评述其学术研究思想,并提出个人的一些观察思考和商榷意见。
奚密;现代汉诗;研究述评
引言
以现代汉诗和比较文学为研究领域的美籍华裔学者奚密(Michelle Yeh),其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成就之一,便是以“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和分析范畴来研究世界范围内以中文书写的、有别于古典汉诗的华文诗歌。①奚密的主要学术论著包括《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现当代语文录》《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芳香诗学》《谁与我诗奔》《台湾现代诗论》等。主要编译(含合译、合编)著作包括《现代汉诗选》《不见园丁踪影:杨牧诗选》《台湾现代诗选》《海的圣像学:沃克特诗选》《航向福尔摩莎:台湾诗想》《黄翔诗选》等。奚密认为,现代汉诗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它勇于在古典经典传统之外另辟蹊径:从诗人何为到何谓诗,如何诗的反思,几十年筚路蓝缕,引发了多少争议?又开创了多少新局面?现代汉诗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对诗作为一个形式与内容之有机体的体认和实践:没有新的形式,哪能包容新的内容?没有新的文字,哪能体现新的精神?所谓现代,所谓先锋,如此而已”②[美]奚密著,奚密、宋炳辉译:《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文版自序第1页。。
张松建总结过奚密现代汉诗研究的四个特色:现代汉诗的学术视野、从边缘出发的研究方向、内在状况的研究范式和四个同心圆的方法论③张松建:《边缘性、本土性与现代性——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305页。,这对笔者颇有启发。在这个基础上,笔者尝试以奚密的诗论集《台湾现代诗论》④[美]奚密:《台湾现代诗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为中心,围绕其对台湾现代诗的创作特质和文学思潮的细致论述,评述她的学术研究思想,并且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思考和商榷意见。
《台湾现代诗论》收入奚密自1996年至2005年发表的12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有的以一位或数位诗人的作品为切入点,例如《燃烧与飞跃:1930年代台湾的超现实诗》;有的以一本诗刊为切入点,例如《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1950年代的〈现代诗〉季刊》;有的以文学思潮展开论述,例如《边缘,前卫,超现实:对台湾1950-1960年代现代主义的反思》;有的以诗歌论战展开论述,例如《台湾现代诗论战》。但毋庸置疑,全书的压轴之作当推《台湾新疆域:〈20世纪台湾诗选〉导论》,其不只是《20世纪台湾诗选》的导论,也可作为《台湾现代诗论》这本诗论集的提纲挈领式的导论。从1917年现代汉诗的起源一直论述至当代台湾现代汉诗的状况,论述全面,引证有力,在台湾洋洋大观的现代诗论中独树一帜。①台湾的其他诗论见诸简政珍的《放逐诗学》《台湾现代诗美学》、萧萧的“新诗美学三部曲”《台湾新诗美学》《现代新诗美学》《后现代新诗美学》、罗任君的《台湾现代诗自然美学》和阮美慧的《战后台湾“现实诗学”研究——以笠诗社为考察中心》等书。
一、界定“现代汉诗”
何谓现代汉诗?何谓现代汉诗研究?综合中外各家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在本质上,现代汉诗的命名在于取代1917年以来流传于中国大陆和境外的 “新诗”“白话诗”“现代诗”“朦胧诗”等既有名词,意指同一个时期的世界范围内有别于古典诗歌的华文诗歌。既然命名为“现代汉诗”,奚密对于现代汉诗的现代性自然是有所期许的。她曾撰文讨论过现代汉诗之现代性的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世界性和糅合性,这个特点暗示自我革新的新模式的建立;第二,反传统和实验精神,这个特点同样体现在内容和形式、美学取向和艺术探索上。她认为现代汉诗对诗的本体论思考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诗?诗为谁而做?为什么用诗写?②[美]奚密著,李章斌译:《“〈可兰经〉里没有骆驼”——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在对现代汉诗的现代性的认知上,奚密也很重视其前卫性,“现代汉诗的前卫性在于它的动力源自诗人对文学传统几乎全面的扬弃,及对‘新’或‘现代’的自觉与提倡,在精神上,早期现代诗是‘新文艺’的先锋,强调新社会,新时代,新经验的表现”③[美]奚密:《边缘,前卫,超现实:对台湾1950-1960年代现代主义的反思》,《台湾现代诗论》,第78页。。
至于现代汉诗研究,顾名思义,是在现代汉诗定义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与之相关的文学研究。由于奚密无法忍受过去现代诗论中“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僵化对立,以及把主题题材与语言风格混为一谈的做法,④[美]奚密:《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1950年代的〈现代诗〉季刊》,《台湾现代诗论》,第42-43页。她最终在1980年代末期举起“现代汉诗”的研究大旗,积极响应并带头参与现代汉诗的研究工作,以此作为一种书写策略。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既可超越现代/当代的时间划分,又可超越大陆/港澳台/海外的地域疆界,在广阔的文学视野中细查现代汉诗的渊源与趋势;并且通过与“古典汉诗”的联系和对照,凸显“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整体“现代性”。
二、现代汉诗边缘性的语境化
“从边缘出发”是奚密现代汉诗研究中的核心论述方向之一,也是《台湾现代诗论》中着墨最多的研究面向。她曾用“诗的边缘化”来形容现代汉诗的历史语境与本体精神,并认为随着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结构性的改变,诗失去其原有的特殊地位,而必须重新建立其生存逻辑。⑤[美]奚密:《边缘,前卫,超现实:对台湾1950-1960年代现代主义的反思》,《台湾现代诗论》,第76页。类似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现代汉诗地位的论述比比皆是。例如:“20世纪以降,诗不再是社会主流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众多文学艺术类型中的一员。在‘文学革命’以后的数十年,现代诗的合法性和价值不时受到质疑,其正统性仍有待争取。”⑥[美]奚密:《台湾新疆域:〈20世纪台湾诗选〉导论》,《台湾现代诗论》,第207-208页。
奚密的这种研究自觉使得她在检视上世纪中期台湾现代汉诗的收获时,敏感且悲观地发现,“新诗在出版市场里的劣势持续于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新诗在当时受到歧视(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和古典诗相比,显得容易浅俗,好像不需要高深的文化素养即可为之”⑦[美]奚密:《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1950年代的〈现代诗〉季刊》,《台湾现代诗论》,第47页。。除了关注在台湾诗坛起步艰难的现代汉诗之外,奚密也对另外两种“边缘诗学”给予重视——女诗人和海外汉诗,前者处于性别的边缘而后者处于文化的边缘,这很好地补充了她在前面的边缘思考。
文学脱离不了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现代汉诗亦不例外。在突出台湾现代汉诗的“边缘化”地位之际,奚密更结合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和政治元素来论述现代汉诗的边缘性。1992年,奚密在编选《现代汉诗选》时撰写的导言中,以“边缘”(periphery/margin)的概念来讨论现代汉诗的历史脉络,认为“边缘”可以触及诗史上几个重要的运动和争议,并提供一种理论架构来分析现代诗(美学和哲学的)的现代本质:“边缘”的意义具双重的指向,它既意味着诗之传统地位的丧失,亦暗示着新的空间的获得,使诗得以与中心文体展开批判性的对话。①[美]奚密:《从边缘出发: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1996年,奚密在讨论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台湾现代诗的“边缘化”地位时,认为“战后台湾的现代诗所面对的困境又可进一步从三方面来看,即:官方意识形态所推广的反共文艺,传统文化对现代诗的反对与压抑,以及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断裂”②[美]奚密:《边缘,前卫,超现实:对台湾1950-1960年代现代主义的反思》,《台湾现代诗论》,第77页。。
三、强调“内在状况”
东西方文化的影响研究历来是学者们重视的研究方法之一,但奚密独树一帜,强调现代汉诗的“内在状况”(internal conditions)多于强调来自西方诗的影响。她不考察西方诗对中国诗的冲击和中国诗的回应,而是追问现代诗自我演变的机制和追求变革的内在动力。尽管在《台湾现代诗论》中,有关“内在状态”的论述相对而言比较少,但读者还是可以从中找到蛛丝马迹。例如,在探索台湾诗人陈锦标早期诗作的主要精神和艺术资源时,奚密指出“它融合了西方存在主义的精神取向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意境,来表现怀旧,再现故乡”③[美]奚密:《乡土花莲与诗歌想象:四“陈”举例》,《台湾现代诗论》,第191页。;在解读杨牧的诗作《近端午读Eisenstein》时,奚密指出这首诗“用了两个端午节的典故,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屈原自沉与白蛇遭困”④[美]奚密:《杨牧诗评析》,《台湾现代诗论》,第184页。。
换句话说,在强调现代汉诗的现代性的同时,奚密也没忘了重视现代汉诗的血缘传统:“在实践上,现代诗人的写作并非抗拒传统(against tradition),而是透过传统(through tradition)。他们运用各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新改造着传统,并从中寻找新的意义,表达新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诗人是没有选择的,他们必须和传统对话,因为现代白话已经融合了各种古典文学的元素。”⑤[美]奚密著,李章斌译:《“〈可兰经〉里没有骆驼”——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
四、“四个同心圆”的方法论
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四个同心圆”,即从文本、文类、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切入现代汉诗研究。对于奚密的这个研究特质,张松建深有同感:“奚密的‘四个同心圆’的命题,自内向外,层层推进,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整体,既聚焦于文本自身,亦不忘外缘因素,既超越英美‘新批评’的人为藩篱,又避免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化约论’危险,高屋建瓴,举重若轻,把握住text与context之间的互动,打通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确立了一种理智审慎的文化历史观。”⑥张松建:《边缘性、本土性与现代性——奚密的现代诗研究》,《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303-304页。
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层面上,奚密曾一再强调台湾现代汉诗的源头,“毋庸置疑的,白话文运动为台湾现代诗做了铺路的工作。不仅如此,它更可以视为推动台湾本土文学的初步努力,是70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及80年代以来台语诗写作的先声”⑦[美]奚密:《台湾新疆域:〈20世纪台湾诗选〉导论》,《台湾现代诗论》,第221页。;“从一开始,台湾现代诗就建立在两个传统上:中国大陆的新诗和日本现代诗。这两个传统不但不是对立的,反而有互补的关系,因为它们启蒙的源头相似(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①[美]奚密:《台湾新疆域:〈20世纪台湾诗选〉导论》,《台湾现代诗论》,第222-223页。。
五、重视美学素质和本土性
除了上述四个面向的研究之外,奚密在《台湾现代诗论》中对现代汉诗的研究与分析还可归纳为两个层面的聚焦:台湾现代汉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台湾现代汉诗的本土性。
相对于诗的主题和内容,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更表现出对诗的语言与表现手法的绝对重视,这一点在《台湾现代诗论》诸篇章中有着立体呈现。我们不妨先来了解奚密对于现代汉诗的主体性的看法:“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词来形容现代汉诗,我以为那就是‘革命’。现代汉诗是一全面的美学革命,企图推翻原有的诗歌成规,包括形式、音律、题材、以及最根本的——语言。”②[美]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见2015年9月《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网》,网址: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2333。
奚密深刻地意识到现代汉诗的语言的丰富性,因此,她形容现代汉诗是“一个包容了多种语言维度的混血儿,包括文言、古代白话、现代白话、日本欧洲的外来语、新造的词语、中国方言、翻译词和短语、欧化句法以及西方现代标点符号”③[美]奚密著,李章斌译:《“〈可兰经〉里没有骆驼”——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她指出,由于现代诗人拥有非常丰富的可供利用的语言,加上形式的自由、本土与外来的意象和思想宝库,他们得以进行大胆的艺术实验。“现代诗既可以表现古典诗的高密度,也可以有意地散文化或使用复杂的语法。现代诗既可以是意象派式的‘表意符号’(ideogram),也可以表现高度的抽象”。④同上。所以,在2011年与学界的一次访谈中,她建议读者在阅读现代汉诗时应该从语言层面上来看,如果现代诗人能像古典诗人那样,塑造一些新的词句、意象,融入我们的日常语言,那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⑤但凝洁、奚密:《现代汉诗的海外传播与阅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奚密教授访谈录》,《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
基于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奚密对台湾诗人陈黎的诗作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其“本土+前卫”诗作《战争交响曲》《腹语课》,更是花大篇幅来加以解读。⑥[美]奚密:《陈黎论》,《台湾现代诗论》,第303-308页。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奚密会以女诗人夏宇的诗作《连连看》作为诗人对现存诗歌模式的反叛的例子。⑦[美]奚密:《夏宇的女性诗学》,《台湾现代诗论》,第299页。
奚密对台湾现代诗的思考维度,也表现在她对台湾本土性的重视上。在追溯台湾现代诗的演变进程时,奚密从历史角度、种族结构、教育水平和“文化混血”等方面来剖析台湾现代诗与大陆现代诗的不同之处:“台湾除了丰富的原住民文化之外,又融合了汉人、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多样元素。最早的台湾现代诗是用两种语言(中文和日文)写的。……在了解台湾时,‘混血’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观念,有助于我们了解台湾,因为这个岛屿的身份和其近四百年来的多元历史的确是不可分割的。”⑧[美]奚密:《台湾新疆域:〈20世纪台湾诗选〉导论》,《台湾现代诗论》,第211-212页。基于对台湾现代汉诗的本土性的认识,刘克襄 《遗腹子》和陈义芝 《破烂的家谱——川行即诗》成了奚密眼中两首可读性极高的本土诗作。⑨同上,第248-249页、256-258页。
六、发现现代汉诗的新传统
除了《台湾现代诗论》之外,《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也凝聚了奚密对现代汉诗的许多独到观点。作者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个私人的、内向的、与众不同的世界,传统诗歌中不能想象的艺术实验可以轮番试行。经过不断的研究与对比,在《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①[美]奚密:《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传统》,第56-86页。一章中,奚密具体演示了古典诗歌与现代汉诗的不同,并尝试由此建构现代汉诗的“新传统”。
从诗的内部结构而言,奚密指出,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现代汉诗经历了形式与意象上的转化过程。古典诗歌都有固定形式,而且不断行;现代汉诗没有固定形式,也没有规律化的押韵格式。中国古典诗歌运用古典意象,例如松、花、云、月;现代汉诗运用现代事物作为意象,例如汽车、邮筒、大街。此外,现代汉诗经历了从预设主题到不预设主题的转化过程。中国传统诗学跨越了从偏重实效道德到偏重美学表现的范围,诗是诗人与自然之道认同的体现。中国古典诗歌中预设的普遍性对现代诗人来说是不存在的,现代汉诗所传达的不是一种预设主题的蓄意呈现,而是一个直接而自发的感受过程。
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奚密认为,现代汉诗经历了从读者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的转化过程。中国古典诗歌的读者必须具备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其他文化领域的背景,现代汉诗的读者首先必须参与意义创造的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国传统诗歌的作者和读者基本上是一群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精英分子,在创作群(诗人)和诠释群 (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当密切的契合;但是,这种诗人和读者的同质性(homogeneity),对现代汉诗来说,已不再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前提。
谈到现代汉诗建构新传统的内在动力,奚密解释说,尽管现代诗人没有一个普遍性的价值系统和整齐同质的读者群,他们却拥有探索诗之内质的充分自由,诗人在古典传统的范畴之外实验和探索诗的形式、意象、韵律等。中国现代诗人一直在从事种种原创性实验和理论陈述,尽管他们的努力有时显得仓促而肤浅,有时是对西方思潮和风格不成熟的模仿,但不可否认,通过对与古典诗歌传统有着根本差异的诗观诗艺的探索,现代诗人已经迈进了一个新纪元。
奚密指出,现代汉诗在推进的过程中建构了诗的“非指涉性”(non-referentiality)理论概念。诗的 “非指涉性”即内容或信息本身非诗的重点,“怎么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这一观点为众多的中国现代诗人,尤其是那些受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影响、不以与广大社会交流为目标的诗人所接受。诗的最初和最终的目标就是完成其自我实现,将过程实现化,或创造一个完整世界,而不是提供一个经验世界的指涉或相关信息。奚密进一步清楚地表明:“诗的价值跟主题的大小轻重完全没有关系,完全看它使用的语言,语言的原创性。因为诗的目的不在传达任何信息,信息不是诗最重要的层面;表达的方式本身才是诗的核心。”②但凝洁、奚密:《现代汉诗的海外传播与阅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奚密教授访谈录》,《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
纵而观之,在奚密的论述中,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汉诗在诗歌前提和表现方式上的区别并非仅限于个别的诗人,它暗示汉诗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根本性。与传统诗人力求个人名声历久不衰的愿望相反的是,现代诗人往往推崇诗本身的超越和不朽。换句话说,诗被理想化和抽象化了。
七、杨牧作为现代汉诗的“格局改变者”
在现代汉诗的版图中,杨牧应该是奚密最为推崇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曾在一篇文章中以“Game-Changer”一词作为对杨牧的文学影响力的概括:“评者曾从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阐释杨牧的诗。……他是一个复合体,汇集了错综复杂的资源和资本,凝聚着主观客观的元素和能量。在回应、协商结构性的局限之同时,Game-Changer以其独具原创性的介入转变他所处的文学场域。”③[美]奚密:《杨牧:台湾现代诗的Game-Changer》,《联合报》2014年9月5日。
在《杨牧:现代汉诗的Game-Changer》④[美]奚密:《杨牧:现代汉诗的Game-Changer》,《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这篇论文中,奚密从四个大的方面——文学(诗文)创作、文论撰写、丛书编纂、教学影响,以实例全面论述了杨牧60年来的文学实践,并由此验证杨牧改变现代汉诗格局的事实。在《浪漫与现代》这一节中,奚密指称叶珊(杨牧)在诗歌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具有一种独特的异质性,这点表现在两个面向上:第一,叶珊早期作品充满了数字的奇想;第二,叶珊诗作运用了突兀错愕的意象:异质的意象、奇异的意象、暴烈的意象。叶珊的语言融合了中外古典,他的书写模式也以抒情为大宗,但是,他的意象超越了传统的婉约或纯粹的抒情。奚密总结说,叶珊同时拥抱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游离在边缘的现代主义者,叶珊对现代主义的局部吸收除了体现在观察角度和书写手法之外,主要表现在他对现代诗必须革新、必须具备现代性的认知上。①[美]奚密:《杨牧:现代汉诗的Game-Changer》,《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
在《古典与现代》一节中,奚密指出,早在1970年代初期唐文标和关杰明点燃“台湾现代诗论战”之前的五六年,杨牧对现代诗西化的问题已有了自己的反思和回应,这一点从他的作品和文论里都得到印证。②同上。如果杨牧早期作品的古典印记来自它对中国诗词语言和意象的熔铸,那么,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10年里,杨牧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对古典题材的处理与古典资源的运用(“表演”和“改编”)。虽然题材是古典的,杨牧的诠释角度和书写方法却是现代的。③同上。奚密对杨牧诗作的评价,一言以蔽之,就是浪漫主义、存在主义、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体。
在《现代诗史的梳理》一节中,奚密胪列了杨牧关注台湾现代诗发展的一些文论,例如杨牧对古典的重视和转化使他对早年现代诗的某个面向提出质疑和否定,对前辈诗人纪弦1950年代“横的移植”的批判也体现了他对现代诗史的重新梳理。④同上。杨牧曾强调,台湾现代诗是本土诗人和1949年以后大陆来台的外省诗人共同努力的成果,而他将笠诗社和战后的三大诗社相提并论,也暗示着对本土新诗传统的彰显。他所持的历史角度反映了1960年代后期以来对文学史的重新思考。除了徐志摩和郑愁予之外,杨牧还评述过夏菁、商禽、痖弦等诗人的诗作,其中有几篇是掷地有声的长篇论述,有几篇是珍贵的史料,生动地描绘了1950-1960年代的诗坛。⑤同上。
在《“学院派诗人”的代言人》一节中,奚密追溯至杨牧以新锐学者的身份主编新潮丛书的1970年代。当时杨牧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过分西化的批判,反映在他执笔的《新潮弁言》中:“对于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谓‘新潮’曾经是‘西潮’;对于我们来说,‘新潮’并不完全如此意味。这个时代的文化是彼此撞击互相建设的文化。我们肯定新生的广义的中国文明。”⑥同上。除了丛书编纂工作之外,杨牧也参与杂志的编辑和诗选文选的编选工作,影响力无远弗届。
奚密还在同一节中指出,杨牧在1970年代中期于台湾国立大学外文系担任客座教授期间,一群年轻诗人追随左右,包括杨泽、廖咸浩、罗智成、王裕仁(笔名苦苓)等,这些学生还成立了“台大现代诗社”。杨牧不仅是他们的文学导师,更是他们的诗人楷模,他们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杨牧的影响,“杨派”头衔于焉形成。相对于1950-1960年代的诗作,1970年代的“杨派”对中国古典的深入研究和纯熟运用,对文史哲传统的认同,对现代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期许,标志着一个不同的诗人形象的形成。⑦同上。
作为学院派诗人的创始人,杨牧的影响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除了诗、散文、学术论文的发表,以及杂志、丛书、文学选集的编辑之外,他还在报纸副刊写专栏文章。同样重要的是,杨牧为《人间》副刊荐选投稿诗作,因此发掘了不少新秀,例如陈义芝、向阳、焦桐等,深远地改变了台湾诗坛的生态。1976年,杨牧和花莲老同学叶步荣共同创办洪范书店,虽然规模不大,出版的书却精致而高质,长期以来是台湾一个重要的文学出版社。①[美]奚密:《杨牧:现代汉诗的Game-Changer》,《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除了在台大外文系担任客座教授,杨牧还和侯健、姚一苇、叶维廉等学者在1975年创办《文学评论》期刊,②同上。这无疑提升了杨牧对台湾现代诗坛的影响力。
奚密把杨牧的文学实践置于大的时代框架下加以论述,认为战后台湾的文化氛围可以三者来概括:保守主义、国族主义和“反共抗俄”政策。对于被古典诗和当时的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战后新诗先行者如纪弦、覃子豪等人,奚密把他们视为一个集体的Game-Changer。透过文本和其他文学实践,他们建立了新的文学习尚和文学价值。作为一个后来者,杨牧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台湾诗坛的地位。在奚密的理解中,杨牧所强调的“冷静的文学态度”和“健康的文学态度”,既是对“冷静文明的现代诗人”前辈覃子豪的肯定,也反映了他作为诗人及学者的态度。
八、两点商榷意见
在传统的继承与西方的影响之间,奚密曾不断叩问和权衡轻重:“追溯文学影响的根源和接受的来龙去脉,当然有其重要的价值,但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使现代中国诗人开放接受某些外来影响的本土因素。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追问:在特定的中国文学语境中,哪些内在条件有利于外来模式的输入?为什么在那么多可能的外来模式里,有些落地生根,有些却昙花一现呢?”③[美]奚密:《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传统》,第63页。“‘五四’以来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应视为诗人在多种选择中探索不同形式和风格以表现复杂的现代经验的结果。尽管其中可能有来自外国文学的启发,甚至是直接对后者的模仿,更重要的是来自内在的要求和在叩应这些要求的过程中所从事的可能类似于外国的本土试验。”④同上。
很明显,在纵的继承与横的影响之间,奚密选择了前者。凭着这条自古而今的纵深研究思路,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呈现出一种特有的魅力。然而,这种独特的研究风格难免有其一定的风险,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积极的一面是,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超越了影响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中西诗学对话之间的话语不平衡状态,通过对文本解读及其与古典诗传统的联系,细察现代汉诗80余年的内在理路、演变机制和创造源泉,从而推进了现代汉诗的学术研究;消极的一面则是,这个研究特征的根源在于她对“影响研究”的理解过于狭隘。
奚密在《杨牧:现代汉诗的Game-Changer》中滔滔不绝地评述了杨牧60年的文学实践,“企图分析杨牧如何透过这些实践建立了新的文学习尚和文学价值,并进而改变了诗坛的生态,为日后深远的影响打下基础”⑤[美]奚密:《杨牧:现代汉诗的Game-Changer》,《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但是,她却没有很好地把杨牧的文学实践与其作为“现代汉诗的格局改变者”的影响联系起来。纵观全文,只提及杨牧的几首诗作如《当晚霞满天》《屏风》,这实在不足以支撑杨牧作为一个 “现代汉诗的Game-Changer”的论题,作者之前所表明的写作“企图”并没有获得完整落实。除了描绘杨牧诗歌融入“浪漫与现代”的元素,以及兼有“古典与现代”的特征之外,该文并未具体描述杨牧崛起后的台湾诗坛格局,例如跟随杨牧学习的台大学生群(杨泽、廖咸浩、罗智成、苦苓等)或者被杨牧发掘的台湾诗坛新秀群(陈义芝、向阳、焦桐等),在现代诗创作上如何具体地被杨牧的诗风所影响。
无论是思想内容或者艺术追求,一个作家一生的作品是不可能全部完美无瑕的。该文自始至终只对杨牧的文学实践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更在《结论》中直言:“杨牧承袭了1950-1960年代现代诗运动对诗的宗教式投入。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他赋之以最崇高,最纯粹,最贴近生命的意义。不辍的实验和创作数十年如一日。与此同时,杨牧也塑造了一个与1950-1960年代有别的诗人形象与角色。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的提倡,既是个人气质和知识取向使然,也是对现代诗运动及现代诗论战的反思与回应。”①[美]奚密:《杨牧:现代汉诗的Game-Changer》,《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这就丝毫没有提供一己之商榷、异议和批评,给人的感觉是,杨牧俨然是巅峰在望、难以企及的一代宗师,现代汉诗之百川归海的终极所在。这在一般的作家作品述评中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完全“一面倒”的论述有时或会欠缺说服力。
结语:现代汉诗研究的新境界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实际上就是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化。有论者对奚密“从边缘出发”的现代汉诗研究策略表示支持:“边缘化”不是一个短暂现象和特例,而是现代汉诗必然要承担的命运和内在化了的现代本质,也是其美学和哲学特征的显现,因此奚密使用“边缘”这一诠释、批评观念来概括现代汉诗的本质特征。②彭松:《边缘的探求者——奚密的诗学研究和诗学建构》,《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用“边缘”的概念来讨论诗史,确具睿见。奚密洞察现代汉诗从边缘出发的历史位阶,在“实验中摸索自身的规则,测定并维护自身与中心论述的距离”,从而可以看出现代汉诗近百年发展历史的脉络。③林淇瀁:《长廊与地图:台湾新诗风潮的溯源与鸟瞰》,见2014年8月《新诗风潮研究网》,网址:http://tea.ntue.edu.tw/~xiangyang/chiyang/poet1.htm。
奚密企图形塑并建构现代汉诗的规范与传统的想法,与重视文学内部结构的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所一再强调的“今天的诗歌需要一种新的诗学、一种新的分析技巧,这种新的标准仅仅靠简单地移植和套用美术的术语是不能取得的”④[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增订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等前沿文学理念不谋而合。奚密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为了理解汉语诗歌这一根本新开端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必须走出表面的影响研究,进一步考察1917年现代汉诗的主要前提和理论。由于它摒弃了大多数的传统诗歌规范,现代汉诗很自然地、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对基本命题的反思来为诗重新定义,并尝试建立一套新的诗歌规范。”⑤[美]奚密:《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传统》,第63-64页。奚密在尝试分析诗歌规范根本变化背后的“不可控制的力量”时,考虑到某些诗歌以外的因素,并从社会政治和教育这两个角度来讨论,这就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解读现代汉诗的具体表现。
作为一位抒情美典的追寻者,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以前沿概念挑战与颠覆既有的、权威的文学研究与欣赏传统,以现代汉诗的历史沿革与理论架构分析其艺术成就,并且以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为线索,孜孜不倦地追述并梳理现代汉诗的发展脉络,为现代汉诗研究开拓新的境界。她在这个研究领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责任编辑 穆海亮】
张森林,新加坡华文作家,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马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