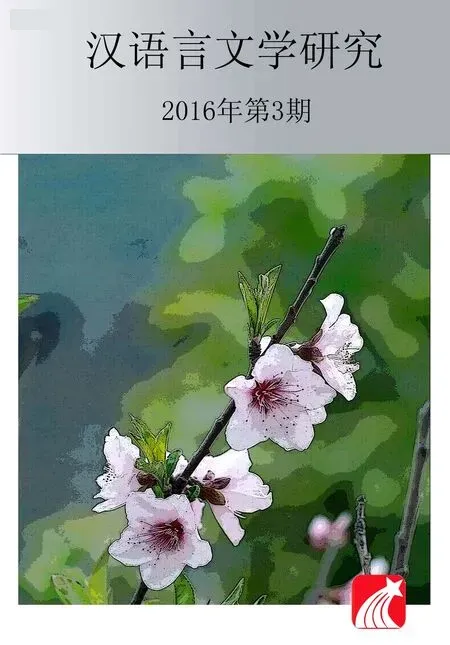实践存在论美学与中国美学境界思想*
2016-12-27刘凯
刘凯
实践存在论美学与中国美学境界思想*
刘凯
境界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当代实践存在论美学关于境界的思想,既是对古典美学境界概念的继承与深化,同时,也体现出西方存在论思想与中国美学境界论思想的对话与会通,从而凸显实践存在论美学在当代美学建设中的突破与创新。
实践存在论美学;境界;中国美学
作为对传统实践美学的推进与发展,实践存在论美学近年来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推出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①除相关论文外,还包括朱立元主编《美学》(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范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审美活动的界说中,“实践存在论美学”以“境界”概念来思考审美,提出了“审美是一种高级的人生境界”的理论命题,把人生境界的创造与提升作为审美活动的最终指向,体现出力图会通中西方美学思想的理论尝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目前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讨论中,这一指向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全面理解与准确评价。因此,本文试从辨析“境界”概念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内涵入手,思考实践存在论美学境界论指向的理论内涵及其对古典美学境界概念的继承与深化,进而凸显出实践存在论美学在当代美学建设中的理论突破与创新。
一
境界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境界概念在中国美学史上的详细梳理,在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已多有论及,这里毋庸赘述。本文拟从现象学的视角进行尝试性地思考,力图探查出这一概念的文化语境。或许,境界概念之后的种种复杂流变均奠基于这一文化语境之上,并在其中获得某种整一性。
“境”,本字为“竟”,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乐曲尽为竟。”作为一种时间艺术,乐曲总是在时间之中展开、呈现和完成。因此,“竟”首先包含着一种内在的时间性。按许慎的解释,“竟”意味着时间的终止(“乐曲尽”)。然而在中国艺术中,“乐曲尽”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完成、终止,同时还是一个发生与展开,“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乐曲的终了总是一个更大的无限空间的展开。因此,“竟”又不是一个终止、结束,而是对一个过程的言说,指向的是时间的绵延与展开(“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界”,许慎的解释是,“界,竟也”。段玉裁对此的注解是,“乐曲尽为竟,引申为凡边竟之称。界之言介也,介者画也。画者,介也。象田四界”。“象田四界”既表示着对空间的限定,同时也意味着空间的绵延、延展。可以看到,段玉裁的解释中既注意到了“界”与“竟”的相通,又突出了“界”之中所包含的空间隐喻(不同于“竟”中的时间隐喻)。
如上所述,“竟”与“界”二者之中既隐喻着绝对的终止、界限,也隐喻着绵延和展开。或许由此才会有许慎“界,竟也”的断语。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段注中所凸显的“竟”与“界”二者内涵上的差异。也许通过这种判断形式,许慎并不是要言说二者的同一,而是二者的统一;不是二者的相同,而是二者的相通。由竟到界,由时间到空间,这一延展在段注中归为所谓“引申”。“引申”,由此及彼,既不是相同,也不是相异,而是连续着的断裂,同一着的差异。因此,在这一似乎平淡无奇的“引申为”中,就隐藏着“竟”与“界”二者的复杂关系。
可以看到,《说文解字》中已经以“竟”来解“界”,段玉裁对此的解说也进一步突出了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因此,“境界”一词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竟”与“界”二者共通的基础。虽然“境界”一词出现稍晚,在汉代班昭《东征赋》中有“至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的句子,郑玄对《诗经·大雅·江汉》中“于疆于理”的笺注,“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在古代艺术理论中最早出自北宋郭熙的 《林泉高致》(“境界已熟,心手相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但在二者的字源中已经透露出这一连接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如上所述,“竟”与“界”二者之中都隐含着“界限”的意味。但是,当我们谈到界限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界限的两边,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界限。因此,“界限”本身总已经包含了对自身的超越。“终止”与“绵延”、“界限”与“展开”由此就获得了统一性和共通性。而“境界”,当这两个字并置在一起时,就意味着双重的限定、双重的超越。既生成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又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可以说,这一并置本身就是一个“境界”。在中国诗学传统中,词语的并置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叠合或相加,而是一种独特“境界”的生成(“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因此,我们需要把“境界”这一词语看作是一种诗意的言说:在“境界”中生成了某种东西,某种不同于“境”、“界”的东西。因此,境界与审美的联系绝非偶然,无论是以“诗”喻境界、还是以境界言诗都体现出来自“事情本身”的源初关联。
需要注意的,还有“境界”这一概念中的佛学背景。“境界”一词本为佛家语,意谓“佛教徒在修行、认识上达到的某种境地”,也指属于“十八界”中的“六境”(即“六尘”),是“六根”的对象。①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4页。“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也就是说,“唯有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具备的六识之功能而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种感受,才能被称为‘境界’。”②叶嘉莹:《对〈人间词话〉中境界一辞之义界的探讨》,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这一解释在境界概念中更突出了其形而上的超越特质,后面会看到,这一特质对于美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境界”这一概念并不始于王国维,然明清以降,这一概念广泛运用于各种诗论、画论、文论之中。但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境界理论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对境界的论说显然值得注意。首先,王氏将境界作为审美的本体论概念或审美得以可能的根据。因此,境界的有无就成为艺术评判的重要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本也。”对此王氏是颇为自信的。
关于“有境界”,王氏的理解是:“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可以看到,王国维所理解的境界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在境界的范围上,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感情;在境界的性质上,强调所谓“真”。
《人间词话》第九则,王国维引述了《沧浪诗话》中“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一段后,评述道:“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因此,境界作为艺术的本源,本身就具有超以象外、含蓄不尽的特征。
在那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名言中,王氏所言说的境界又不仅仅局限于艺术活动领域,而同时具有了人生况味。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最后强调,“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二十六则)。也就是说,只有对于艺术或审美有了深刻感悟和理解,才能体察到这三种人生境界。显然,这里透露出王国维关于人生与审美共通的思想倾向。
根据王氏的论述,结合我们上面对境界一词审美内蕴的现象学考察,可以看到,境界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对象,它并不局限于自然景物或人内心的感情,而是一种超越了二者的境域或场域;在这一境域中,体现出本体性的真,它构成了审美的本源。由于“境界”本身具有超出特定界限的特点,因此,这一境域又不断地超出自身,指向某种不确定的审美意蕴,体现出含蓄不尽的审美特性。同时,境界又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还体现出人生与审美的会通。这也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内在精神。《论语》中对于“曾点气象”的记载,《庄子·逍遥游》中对于“藐故射神人”的描述,既是人生境界的呈现,又无不体现出审美的内蕴。
二
以上我们对“境界”概念的审美特质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来讨论实践存在论美学关于境界的思想。实践存在论美学运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资源,从现代存在论视野出发,将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论思想与存在论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理论命题,对境界论美学思想进行了整体上的推进与深化,体现出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
首先,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人的生存是境界化的生存。实践存在论美学所理解的境界是指人生实践活动所达到的层次和水平,它主要标志着人在生存实践中的精神修养及思想觉悟程度,是人对宇宙和人生的自觉以及对生命意义、幸福感的感悟水平。因此,境界的高低与人的自觉有关,也就是说,它不仅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范围,也取决于人对自己所进行的实践的自觉程度。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因此,马克思所理解的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人,而是有着世界性联系的在世生存(In-Der-Welt-Sein)的人。他所面对的,是处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与人有着丰富联系的人化世界。在其中,渗透了人的所有欢乐与痛苦,愉悦与忧伤。“人在各种生存实践活动中,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同的经历和体验,这些经历和体验会有不同的层次和水准,也就会形成不同层次的境界”。因此,“人的生存是讲境界的,世界上也只有人的生存是讲境界的”。②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7页。
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同样认为人的生存并不是孤立的生存。《论语》中,孔子对君子、对“仁”的描述,都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生存境域中展开的。如:“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这里,对一个人的评价要参照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不同反应。又如,“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君子不仅仅意味着自我修养(“修己”),还包含着特定的社会责任(“安人”、“安百姓”)。因此,有学者认为,对孔子来说,释“人”总需要他者的参与,而且“成人”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人际沟通和交往的过程,这一过程会体现出“礼”、“义”、“仁”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该关系将文化环境设定为成人过程的基体。③[美]郝大维、安乐哲著,何金俐译:《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88页。
而在我们上面引到的王国维关于人生三阶段的描述中,也可以清晰看到从人的生存来理解境界的思想路向。因此,实践存在论美学关于人的境界化生存的思想不仅吸收了西方思想资源,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也有其基础。
其次,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人生境界在实践活动中得以展开。
实践存在论美学从整个西方思想传统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坚持人生实践的理论取向,始终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来规定人、理解人。实践不仅使人成为人,更使世界成为世界,也就是说,使人成为真正世界性的存在(Weltlich Sein)。因而,实践的展开过程就是人本身和人的整个世界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对人本身不断确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①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因此,实践就成为使人和整个感性世界得以生成的“境域”。它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之分,而是使这二者成为可能的本源和基础。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实践观念中所蕴含的存在论思想有着清醒认识,“马克思以他的方式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这样他就要求给予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地位。……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②[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也就是说,作为生产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源初的存在方式。
因此,在实践存在论美学看来,实践就构成了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建立起“实践”的在世结构,使“实践”成为人的本真的存在方式,成为审美活动得以开启和展开的一个源初“境域”,这样就能够以“实践”概念为契机开启出崭新的理解视域和话语空间。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这一思想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生的实践性、现实性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李泽厚将其概括为“实践(用)理性”:“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③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6页。实践概念的包容性使得它可以有效涵摄境界概念中的人生意蕴,并与中国传统的实践(用)理性相接合,体现出中西会通的创造性维度。
第三,审美是一种高级的人生境界。
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审美就存在于人生实践之中,二者具有存在论的相关性。因此,对美的理解始终应以人的实践存在为基本视野,在人的在世生存中凸显审美的意义。如果说,人的存在总是境界性的生存,那么,审美也必然是境界性。它不会局限于审美主体,也不会局限于审美对象,而是体现为超越二者、使二者得以生成的源初境界。随着人生实践的不断拓展,这一境界也会不断展开、丰富和提升。沿着这一思路,当代美学可以尝试在存在论的基点上超越传统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论的理论框架,突破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二分,重新思考审美的存在方式和美学的学科形态。
审美是一种高级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当人的境界性的生存达到了一种较高层次的时候,就会体现出审美的内涵。这点也同样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精神,即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④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宗白华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⑤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而所谓人格美,实即一个人在其人格之中所体现出的具有审美意味的人生境界。徐复观通过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考察,认为尽管在对人生境界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但二者都体现出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因此,“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⑥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三
可以看到,实践存在论美学以“境界”作为审美的基本存在方式及最终指向,对传统境界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体现出西方存在论思想与中国美学境界论思想的对话与会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实践存在论美学从现代存在论的思想出发理解境界,赋予境界以人生在世的生存论基础,使之成为一个现代美学概念。实践存在论美学从广义的人生实践的角度理解审美,因而审美不是人所面对的客观对象,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状态,而是伴随着人生实践不断开拓的、生生不息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本身是境界化的。境界由此成为对人生、对审美的基本规定。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文化中这种生生不息的内蕴构成了中国式人生境界的基本指向。它意味着对于人生的高度肯定与尊重,对于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的赞许与发扬,体现出强烈的现世情怀。这种致力于不断拓展与提升的境界追求与实践存在论美学思想之间具有着内在的契合。当这种现世情怀与存在论思想相遇时,存在论思想中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对于人的源初生存方式的思考,就成为对境界概念的基本规定,使之成为一个贯通了审美与人生、构成审美的生存论基础的现代美学概念。
其次,实践存在论美学从广义的实践出发对境界概念的扩充与奠基。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实践构成了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作为世界性的活动,实践的具体展开就构成了特定的人生境界。而随着实践的不断提升,在超越性的人生境界中就体现出审美的内涵。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审美的境界。但人生如何能够是境界性的、人生境界如何能够是审美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自明的。正是实践的引入才使彼此之间的关联成为可能。因此,现代西方存在论思想资源的引入使境界概念有了内涵上的进一步扩充和学理上的依据。它不再是对某种个人人格的描述(如宗白华对于晋人的美的描述),不再是对某种生活理想的描述,不再是对某种审美趣味的描述,不再是某种对于人生过程的描述(如王国维的三境界说),而是构成了所有这些得以可能的源初境域,成为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言说。可以说,正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使得境界真正获得了理论的深度。
再次,实践存在论美学境界概念中关于生存与审美相通性的思想,体现出对现代人的生存境况的关注和思考,使这一概念体现出现代意义和开放性的内涵。实践存在论美学立足于一元化的存在论的实践活动,把审美与人的生活、人的现实的存在联系起来,突破了审美与人生各自的囿限,以境界概念沟通二者,凸显了人生的审美指向。这样就在审美与人生的共通性中来理解境界,从而赋予了传统境界概念以全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加重要的在于,这一思想可以有效涵纳当代西方后现代思想资源,体现出极为开放的理论视野。
当代后现代思想对生存美学高度关注,力图破除审美与生存之间的隔阂。这一思想从尼采露其端倪,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明确指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因此,“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①[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181页。在《性经验史》第三卷中,福柯通过对古希腊人生活的考察,提出了生存艺术的设想,强调“发展为了确保对自我的控制并且最终达到一种纯粹的自我愉悦而进行所有实践和训练”。②[法]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7页。“从自我不是被给予的这个观念出发,我认为,只存在着一种实践后果: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创造成为一件艺术品”。③转引自[英]路易丝·麦克尼著,贾湜译:《福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在人生之中不断探索生存的可能性
在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古典美学的概念来描述当下的审美体验,这就需要我们对古典美学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有效阐释,建立起其与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和生活世界的相关性。在这方面,实践存在论美学对境界概念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责任编辑 付国锋】
刘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部电影: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10K090)、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项目:“康德美学的时间性问题研究”(11SZYB22)、陕西师范大学双语课程研究项目:“西方美学名著选读”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