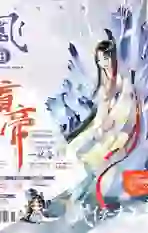盲帝
2016-12-22鹿聘
鹿聘
【一】
这一夜,年老的天子与年老的宦官对坐,中间隔着一盏烛火,映出天子神情寂然的脸,他道:“越老越糊涂,寡人又频频想起皇后,她每每要我性命的模样,真是可笑,真是让人怒得发狂。”
话中的皇后,不是如今在宫中一起跟他维持恩爱表象的女人,而是永久沉寂在冰冷皇陵,背负着滔天骂名,他的第一任妻子,慎独。
世人说少年夫妻多恩爱,可自他十七岁娶她,便没有一日不被这个女人欺瞒算计,将他年少的爱慕消磨殆尽。
“您当年不许人找她的尸骨,埋在皇陵的不过一副衣冠,您纵容天下士子著文章唾骂她,一桩桩罪名安在她头上,这些年她死着也很不好过了。”固安道。
帝王没有恼怒固安的僭越,只是默然。
“当年因为那个女人没做成的一桩事,始终是这些年的心结,我哪怕死了,也得做成。”
“是。”固安答应,他曾经是慎家的人,京都慎家侍奉神明,每一代都会有一人天赋异禀。
两人合眸,天子的神海被抽离,纳入固安七窍中,然后,固安站起身,慢慢推门出去,转过角门,经过莲叶湖畔,穿过重重长廊。
佝偻的背直起,白鬓复青,沟壑复平,混浊的眼珠渐渐清亮,垂老的腐气散尽,如一截朽木的身躯重焕神采。
蝉蜕之术,蜕躯壳,蜕时光。
眼前是一个清晨,七十年前王宫中的一个清晨,谢邈第一回被人从那遥隔千里的封地接来,立于空旷的天地间,一动也不敢动。
固安就站在小谢邈身后,一个稚嫩清俊的小内侍,无人知道他的身体里其实是七十年后的谢邈,他看着曾经的自己,这样惶恐不安,稚嫩易骗。
谢邈借助固安的身体,眯眼望向远处一顶越来越近,不能再熟悉的小轿,里面的姑娘掀开了帘子。
这一日天徽十四年初春,谢邈与慎独的初遇,也是重逢。
【二】
天子的魂魄随着宦官的身躯一同回到那个清晨,固安不再是固安,而是多年后的谢邈。
他蹲下身,指着那顶轿子,对小谢邈轻声道:“不可以相信轿子里的女人,她会害了你。”
十七岁的谢邈已经是个风姿卓然的男子,雪氅加身,纤尘不染,除了眼眸上覆的一条白绫,人总有缺憾,谢邈目不能视。
他一笑:“我知道,反正我眼睛看不见,再漂亮的姑娘,我看不着,就不会脸红。”
固安想带着谢邈避开那顶轿子,或许走得太急,谢邈一个趔趄,扑倒在地,雪粒子如尘四散翻腾,他久久不肯站起来,双眉如同蜷缩的身躯紧皱,捂住小腹喊痛。
谢邈的肚肠没来由地剧烈绞痛,固安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那顶软轿嘎吱轧过冰雪,在轴印尽头,停住,她跳下来,金黄的琉璃瓦与白雪辉映,灿灿的日头熠射,仍无法越过她春水粼粼,秋霜高洁的美丽。
谢邈听到了她鬓间一只金蝉翼的颤鸣,心神也随之颤动,知道这样好看的姑娘,是他未来的皇后,唾手可得的人。
“我听说,你刚刚从南边回来,那里是不是早就暖和了,你进京都的时候,有没有瞧见西直门桥下吹糖人和掌中戏,我长这么大,就去过一次。”她不住发问。
谢邈不知从何答起,半晌,道:“我眼睛看不见。”
“这样啊,”她声音满是遗憾与怜悯,“真可怜,他们说你从小就瞎了。”
“是啊,嬷嬷说我一出生不仅眼盲,身体多病,母亲又不讨父王欢喜,他甚至没有多看我两眼,就赶忙叫人将我抱走。”谢邈慢慢道。
“还好,如今你苦尽甘来了,”她像个狡黠的小兽,拉过他,在他耳边低声道,“你这次回来是要做皇帝的,你五姐姐在战场上被人抓去了,估计不会回来了,再也没有女帝了,你就是你父亲唯一的子嗣。”
这一年女帝挥兵亲征鞑靼,兵败被俘,如果不是这样,谁又能想到这个在穷山恶水将养的目盲皇子。
蛊惑的温柔声音,温暖的掌心相触,谢邈耳根通红,听她一字字道:“在宫里头,你不能信任何人,连你身后的小公公也不可以。”
“你能信的只有我,因为我是你的皇后。”她缓缓一笑,唇红齿白。
固安知道这一刻的谢邈已经心动得一塌糊涂。
相同的话语,相同的场景,令侍奉在后边的固安心头愤怒,为什么避免不了。
固安在她走后抚上谢邈的肩头,道:“她是慎家的女儿,比你年长两岁,她在京都的名声很差,无才无德,虐打下人,目无尊长,未出阁前就传出与男子有染的传闻,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女人会成为你的皇后吗,她是权宦王前春选来监视你的人,谁管她风闻如何,只要能掌控住你就行。”
“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谢邈道。
固安沉下脸:“你刚刚是故意装腹痛,只为了等她的轿辇前来是不是?”
被戳穿心事的谢邈没有慌张,他静静地承认:“是,我是为了等她,我知道固安你会生气,我早前就听说过,她是跟五姐姐很像的人,那时候就很想见一见她,更何况,她是我的妻子。”
“我和世人的认知不同,我想她是个很好的姑娘。”
固安再没有说话,他竟低估了曾经的自己对慎独的仰慕,跟五姐姐一样重要的存在,无论怎样躲避,生命中的那辆轿辇还是会迎面而来。
【三】
谢邈很小便知道慎独这个名字,当他被赶往自己贫瘠的封地,门庭冷清之时,五姐姐登门探望,两人设宴共饮,她拿出一个长盒,里面赫然是一卷画。
谢邈不解,仍笑了笑:“我看不见,如何鉴赏这幅画?”
五姐捉着他的手往画卷上移,慢慢抚下,山水线条竟凹凸有致,谢邈不住拿指腹摩挲,很是欢喜。
“多谢五姐。”
“这画是我京都的一个友人相赠,你该谢她。”她一笑。
五姐的友人,京都风闻最浪荡的女子,慎独。
每每他抚着那幅画从一路光阴踏来,便思考这名字后的那个人。
早朝过后,批阅奏折,先前天下人都无法理解,一个瞎子如何识字,自女帝被擒后便一直独揽大权的宦官王前春一笑:“那找人念给他听罢。”
他派固安日夜给谢邈诵读奏折,众人惊骇,先前帝王身旁有掌印监笔二位内监,在帝王身体不适时代劳批红,可这样明堂堂出来干预朝政,唯有王前春。
阉党势力壮荡,只怪当年女帝太过宠信王前春。
众人怒极却不敢言,除了慎独。
她在一个日头明艳的午后闯进殿,婢女急急地连唤皇后仍无法阻止她半分,她一扬宽大袖袍,青色霞光漫天泻下,她在大殿中央,倨傲地抬下巴。
谢邈只觉得鼻尖凑来一阵香风,身旁正念奏折的固安止住声音,静谧的大殿,只剩下她清脆的声音:“万没有一个阉人越俎代庖给天子读奏折的事,若你念错念漏,或是有意欺瞒,天子岂不给你左右!”
是他的皇后!谢邈心中激动又疑惑,固安公公曾告诫他,慎独是王前春派来监视他的人,可是她怎么会如此公然与阉党作对?他正想着,身旁的固安捧起奏折,又一丝不苟地继续念起来,分明不将慎独当回事。
于是谢邈在下一刻听见急促的鞋履上阶声,耳畔有风擦过,慎独抬腕,将一卷书高高举过脑后,砸向固安的面门,哗啦啦作响中,他没躲,鼻梁被砸得通红。
谢邈怔住,慎独眯眼,道:“我是皇帝最亲密的人,我没死,哪里轮到你给他念?”
固安神情阴沉,见慎独一步步逼来,终是将位子挪开,转而侍奉在谢邈身后。
慎独安然坐下,一只手抚上谢邈肩头,红唇白齿,给他一字字念起来。
固安看着眼前这场熟悉的恩爱场景,很多年前,朝堂大事,就是在这样柔软的一声声中道来。
慎独不是个安分的人,有一日她遣散了所有人,也不念书,就把脚尖儿放肆大胆地搭在帝王膝头,谢邈纵容,她咯咯笑起来,察觉她愈发凑近时,谢邈推手道:“天子书房怎可胡闹。”
“胡闹”二字未出口,她碰上他的双唇,不依不饶唇舌缠绵,谢邈惊慌中,羞涩中,紧紧闭上了双眼,肃穆寂静的御书房顿时暖融融。
“皇上,告诉我,您真的看不见吗,”她目光紧随,不肯放过他脸上丝毫神情,“真的完全都看不见吗?”
谢邈睁眼,那双涣散的瞳孔寻不到目标,慎独舒了口气,笑起来,窸窣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药包,将里面杏黄色的药粉倒入即将送入谢邈口中的茶水里。
在御书房亲热,于天子跟前下药,她向来胆大包天!
固安匆匆赶回殿中时,慎独已经离去,谢邈怔怔坐在高椅上,脚下是一地打碎的茶盏,固安一眼便知道发生了何事,当年这个女人欺负他眼盲,蓄意在他跟前下药,可她不知道一点。
谢邈抬起头,目光准确地落在固安身上,他道:“固安,我故意把皇后端给我的茶水弄洒了。”他脸色惨淡,第一次绝望,“怎么会这样,皇后为何给我下药?”
是了,固安眯眼,天子谢邈根本就没有目盲。
【四】
谢邈一出生便失明,去封地调养了几年竟慢慢好了,后来身为女帝的五姐战场被虏,王前春为了找一位可以堂而皇之掌控的傀儡,来到封地找到眼盲的他。
他听从固安的提议,假装眼睛依旧看不见,只有活命,哪怕是一个帝王的虚名,都能有一线机遇去救最重要的人,他的五姐姐。
固安跪在谢邈身前,他望着当年执迷不悟的自己,道:“臣有一个办法,替您试探皇后是真心或假意。”
谢邈开始每夜被噩梦惊醒,他猛然睁眼,大口呼吸如濒死的鱼,慎独以袖为他拭去额上汗珠,听他用颤抖的声音,一遍遍重复那个梦境,他说:“我瞧见咱们床头悬着一条巨蟒,吐着红芯子,冰凉黏湿,光滑的鳞片滑过我的脸,我好不容易抽出五姐姐赐给我的宝剑,一斩下去,却叫它溜走了。”
他不住地做到这个梦,不住地跟慎独诉说,他很认真:“下次梦见这条蟒,定将它斩杀。”
慎独将此事回禀给王前春时,正调香的青年宦官弯起嘴:“帝王卧榻之侧的巨蟒,小天子是意指我?”
他平静地道:“看看是他能斩杀大蟒,还是被蟒口吞食。”
第二日谢邈寝殿外便如铁桶般围了一层金吾卫,是承了王前春旨意,名为保护实为软禁,谢邈在那一日整整出了一炷香的神,直到固安提醒道:“您现在知道了,慎独一直是王前春安排的人。”
他心中失望、愤怒、不解,固安很清楚他的心境,正是不愿让当年的自己蒙受更大的欺骗,才要快刀斩乱麻。
“那个女人的尊荣日子到头了。”固安道。
这几日定远将军回朝,在驿馆安置好了人马,他世代镇守南疆,手握重兵,谢邈知道王前春一直暗中观察,看他是否会与定远将军私下联拢,为避嫌,谢邈索性一连多日不上朝,称病在寝殿中休养。
正待阉党放松了警惕的第四日,宫人慌忙来报,谢邈不见了。
那时王前春镇静地饮完茶,道:“带来慎独。”
日夜与谢邈在一起的,除了他自己,便是皇后慎独,她却也是从别人口中听闻此事,两唇发白,目光失神,什么也问不出来。
京都遍地是阉党的探子,很快便掌握到出逃天子的行踪,王前春在距离定远将军府两条巷子的地方找到谢邈,这里离定远将军府如此近,谁都能想到小天子想做什么。
王前春将他抱到马车上,笑着问:“陛下是如何出宫的,谁带你出宫的?”
谢邈默然,终于,他开口:“是皇后,她说想要定远将军府中一套掌中戏的玩意儿,可那是将军幼子的心头好,谁也不给,我便来了。”
任何人都能想到,谢邈一旦入了将军府,见到定远将军,得到的就不只是掌中戏的小玩意儿。
这是固安教给谢邈的说辞,他们并非要见定远将军,知道凭王前春的眼线根本就不可能让谢邈靠近将军府,最终目的是剜去离谢邈最近最深,影响力最大的毒瘤——慎独,借王前春之手。
慎独狂妄地赶走给天子念书的内侍在先,又令天子与定远将军见面,虽疑真假,王前春依旧下了命令,让皇后静养在寝殿,不得见谢邈,不得踏出一步。
谢邈知道这句谎言一开口,慎独就成了王前春的一枚弃子,迟疑之时,是固安紧握他的双手,义正词严地问:“您从封地来王宫做什么,您在阉人手下忍气吞声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被俘虏的正受苦的,我的五姐姐。”谢邈喉头干涩,艰难开口,“为了接她回家。”
这是小谢邈最终的目标,也是七十年后的谢邈的心头遗憾,因为这桩事被慎独这个恶毒女人破坏无遗,整整推迟了七年,他此次借固安身份回来,便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
【五】
慎独被囚禁在她自己的寝宫,整整十日,未进粒米滴水。
她费尽辛苦托心腹给固安带话,恳求他来自己宫中。
固安来到了她身前,不知是想当着她的面狠狠戳穿她的虚伪面孔,还是以她如今痛苦狼狈的姿态为乐。
“是陛下陷你入如此境地。”固安毫不留情地断绝她心头最后一丝念想。
“阿弟。”慎独声音虚弱,这个称呼却令固安身躯一震。
慎独是慎家人,固安也是慎家人,偶尔也听固安谈起过他们嫡姐庶弟的关系,他一直奇怪,以慎家名望,固安怎么会沦落为内侍。
她继续唤:“阿弟,我想见陛下,望你借我一套内官的衣裳,我好偷偷去见他一面。”
“陛下不会想见你,我已告诉他从前你在家中的一些事迹,他觉得恶心无比。”这些事迹是在慎独死后,他叫人从慎家问出来的。
“你在慎家名声坏极,伤害幼妹,辱打后母,据说,还有人曾在你的院内挖出一具尸骨。”他缓缓道。
慎独猛然抬首,泪水涟漪的双眸下,竟然是笑意,她道:“没错,庶妹故意剪坏了我及笄之礼的衣裳,我便划花了她的脸,后母偷骂我一句,我便在深夜叫人将她拖去祠堂,扇她巴掌,打到手肿为止。”
“我是个坏姑娘,虽然是慎家唯一的嫡女,可庶弟庶妹一大堆,个个比我乖巧更讨爹爹欢喜,他们从不与我玩,连下人都不和我亲近,他们说我脾气古怪。”
从小到大在慎家积郁的怨愤,缘于孤独,又只剩自己一个人的,快被逼疯的感觉。
“还好,还好有阿弟你不是吗,”她痴痴仿佛沉醉其中,“你是唯一一个愿意和我说话的人,我们一起牵手去灯市,去看掌中戏,我生辰那日,你送了一个木偶给我,我高兴得简直疯了,可是那个精致的木偶,被狠毒卑贱的婢女偷偷扔掉了,她还要给爹爹告状,说我用木偶做巫蛊之术咒后娘,我在愤怒与慌乱之中竟将她的头打破了,后来我找到你,求你帮我一起将她埋在院子的枣树下。”
神情凄迷中,她的声音却骤然凌厉起来:“自那日起,你竟然惧怕我,我唤住你,叫你给我的指甲涂蔻丹,你忙不迭地跑了,我怎么会让你逃开我的身旁,于是在王前春相中我做皇后之时,我跟他说,我要小弟陪着我一起入宫,王前春答应了。”
固安当年入宫的缘由竟是如此,缘于这个女人的偏执,慎独突然逼近固安,一只手做扼住他脖颈的样子,冷笑道:“可是,我的阿弟,你自己逃开不够,还要将我的陛下也带走,我怎能容许!我最深爱的陛下,你要敢再将他带离我身边,我一定亲手掐死你。”
固安眉目冷厉,道:“你这个疯子,你明明想害死谢邈,你公然在他茶水中下毒!”
慎独愣住,疑惑了一会儿,她脸上倏然泛起红晕,她笑:“那不是毒,那是房中之药。”
王前春一直催促她尽早为谢邈诞下皇子,可是谢邈生性腼腆,秉性自制,少与她有肌肤之亲,于是她便求来了这动情之药。
固安不解,怎么会是这样,无论是七十年前还是如今,他都认定了那是毒。
“我一开始确实对他存了欺骗之心,可他是那样一个性情柔软的人,将所有事告知我,每每将充满信任与爱慕的目光放在我身上,我感觉自己也成了一个善良的人,从没有人对我如此郑重其事,日日夜夜,铁人也动心肠,活了十九年,生平第一回逢此滋味。”
“所以不要说你,纵然权势如王前春,敢伤害他分毫,我也有一番拼死的筹谋,女人铁了心要杀人,往往比男人更冷静,更残忍,我的阿弟,你清楚我不是吗?”
固安陷入一种巨大的迷茫,他自以为是了七十年的事情,如此清晰又猛烈地颠覆他的认知,动摇他的意志,恍惚中,他不知何时将一套内侍的衣裳拿给了慎独。
清醒过来时,他扶着门框,踉跄追赶到谢邈的寝殿,悬挂的明珠光辉洒满大殿,固安看到遥遥几步外,身着宦官服的慎独,抱住了谢邈的腰,将脸庞埋在他怀中,哭道:“终于能再见到陛下。”
慎独对谢邈的爱意再无人质疑,而此时固安却明白,知晓慎独的背叛与过往的谢邈,心底已经不复当初。
谢邈将手搭在她的青丝上,温柔的动作,神情冰冷,他淡漠地一字字道:“是,寡人也想你。”
【六】
不断有名门女眷充掖后宫,众人心知,这个名义上的皇后,不过是被禁足中宫的弃子。
任众人如何议论,慎独只是冷笑,笑这些人的愚昧,在她心中,谢邈还是那个一心依恋她的男子,他一定会费尽心机将她解救出来。
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将这个清傲女子的孤骨一寸寸折断,她无比想让谢邈来看她,始终没有盼到,只等来了那一身靛青色的男子,阿弟固安。
病榻上孱弱却强撑精神的女子,满眸希望地问:“陛下何时才能来?”
固安不说话,他如何能告诉她:“其实我就是你的陛下。”
“陛下一定生我的气了,他觉得我在帮王前春害他,”她收敛笑意,“可他怎么不知道,落得如此下场的我,正是因为背叛了王前春,他竟然不知道,我是万般信任他,所以才与阉党敌对,斩绝自己一切退路,因为我认为他会护我周全。”
泪水滑过惨淡的面容,她立即转过身不让固安看见,直起身,道:“我会让陛下明白,我一直站在他这一边。”
固安依她之言,将王前春带来寝殿,他远远侍奉在身后,看见数过三阶,凤座上那个永远放肆轻狂的女子,金钗叮当清脆,玉石流光溢彩,她抬首:“听闻定远将军膝下有一女,年正当时,本宫要替陛下将她纳入宫,公公意下如何?”
“娘娘舍得?”阶下王前春不动声色,若是将定远将军的女儿纳入谢邈身侧,两家和姻,谢邈无异羽翼倍增,局势很可能发展到不可控。
慎独一笑:“你是在害怕和迟疑,可是她一入宫,你便多了一个可以牵制将军府的质子,通过她更可以掌握将军府与谢邈的一举一动,在宫中你的眼线无数,搭上她,不过多一个被监禁的人而已,究竟她是成为谢邈的助力,还是成为你的制胜之棋,你不是一向自信能牢牢掌握局面吗?”
她清楚,他们都是享受铤而走险的人,险中带来的利益最值得人垂涎。
固安无法预料到慎独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她那样一个自私的女人,对谢邈一向是独自占有,如今却甘愿让他人染指。
王前春只是一笑,不再多言,几日后,便有天子驾临将军府的传闻,是在王前春的默许下。
据说定远将军与谢邈相谈甚欢,甚至将小女引见,容若秋水性情率真的一个小姑娘。
那一日固安慢慢走到慎独冷清清的寝殿,她摆弄着封后大礼之时的衣裳,踮起脚,哼着小曲儿,这一刻好像一个寻常的女儿家。
固安说出那几个字只觉得喉咙艰涩:“定远将军的那位小女儿说,非后位不坐。”
【七】
固安以为慎独会大发脾气,然而她比预想的平静,只问了一句:“陛下他怎么认为?”
她很快被带去谢邈身前,多日不见,天子清减些,眉眼多了一抹气定神闲,以及阴郁。
她眼眶湿润,头一句“陛下”唤出声时,看见他眸色由惊愕转为漠然,谢邈转头问固安:“谁让她踏足这里?”
她欲握住他袖袍的手停滞在半空,听谢邈慢慢道:“寡人的皇后,会在一个月后病逝,寡人会为她备好一场隆重丧事。”
慎独连一句话都未说出口,又被人拉下去,固安望向殿外许久,道:“陛下为何如此?”
谢邈假装疑惑地偏了头,道:“不是公公你一直教我的吗,从一开始,你就告诉我,慎独并非一个好女人,她会置我于死地,一次次的试探中,我已然清楚她的真面目,这样一个女人,连为人都不配,遑论母仪天下。”
固安抬首,他看着眼前这个蕴藏野心的男子,正是七十年前的自己,只不过将那些情感一抑再抑,病态地压制,好似对一切浑然不觉,他最终选择了心盲。
“可您终究不能将所有事情当作没发生过,”固安仿佛一下子弯了背,转身走出去,“所以七十年后,您恐怕会后悔。”
固安再次踏入这座寂静的宫殿,这次没有嘲讽与冷笑。他只问了一句:“你仍然喜欢着陛下?”
这一次慎独没有回答,她抬首,动人心魄的笑意下是躲无可躲的哀恸,维持着这样的神情许久,道:“阿弟,小时候我和你偷偷溜出去,看大桥底下搭的掌中戏,后来被爹爹知晓,罚跪在祠堂前三夜,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再不敢去看,可我还是心心念念着那些木偶小人儿。”
她笑道:“我对陛下亦是如此。”
他有一个爱慕他的姑娘,可惜他到现在才知道。
固安静静凝视了一炷香,突然对这个姑娘撒了一个谎:“陛下并非对你无情,只是如今阉党掌势,有许多事不得已而为之,你始终是他的中宫。”
她愣了许久,终于像个得到点心的孩童般满足地笑起来。
这个谎好像耗费了固安毕生气力,他跌跌撞撞出门,望向天上皎月,这是德化三年的明月。
他突然如梦初醒,正是这一年,天子谢邈联合定远将军的精军,在冬猎时的翠苇山设计围杀王前春,那时他算尽天机,占尽地时人利,却万万没有料到他一直深信不疑的皇后慎独,竟然劝王前春等人早早退离猎场,导致功亏一篑,自那之后王前春愈发警觉,将定远将军调回南疆,也对谢邈严加防范。
被自己深爱的女人坑害,谢邈直至老年也咽不下这口气,当时激愤难忍的他竟然任人举箭射向慎独,令她永远地留在猎场。
他恨的不是大计未成,而是欺骗他的那个人是慎独。
如今,固安怎么也想不明白,慎独明明站在他这一边,为什么会在紧要的关头,与王前春沆瀣一气。
总之,不能叫计划再次失败,现在谢邈疏离慎独,是再也不会将事情透露于她,她不知情,自然也无法通知王前春,让她被冷落一世,也总比被谢邈射杀好。
十一月,大雪肃杀,白茫茫一片,天子出行,于翠苇山进行一场浩荡冬猎,难得王前春也出一回宫,随侍帝王身侧。
不知何时,谢邈已经率领一支轻甲精兵渐远林中心,呈广阔一线包围势,眯眼望着黑黝黝的山林,弓弩手搭好箭,草垛旁是举火把待命的将士,箭雨一波一波,再纵猛烈火势将人困在林中,烧得一片焦黑,一干二净,此行真正的猎杀开始了。
可是正当谢邈挥手放箭,却被固安唤住,他神色复杂,慢慢开口:“且慢,慎独在林中。”
【八】
固安知道被困于深宫中的慎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在猎场,可她的贴身婢女泪流满面地跑来,求他不要放箭,因为娘娘就在林中。
固安气得浑身颤抖,慎独是怎样知晓他们的计划!千回百遍,她终是要再阻拦一次吗!她就真的以为谢邈不忍心伤她性命吗!
苍茫密林中,慎独站在王前春队伍旁,没人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想什么,明明说爱着自己的丈夫,到头来却背叛了他,她仰起头,笑容像翻飞的雪粒子一般纯净。
“或许我在林中,陛下便不舍得投箭放火,”她喃喃,这是一个冒险极大的赌。
谢邈没有理会固安的请求,正亲自拉满了弓弦,固安突然极其无礼地按住他的手,谢邈惊讶地抬头,看见这个内侍嘴唇颤抖:“您爱您的姐姐,我也爱我的姐姐,天子与宦官的爱,会有什么不同吗?”
“固安,你不是一直告诉我,要以杀王前春为先!”谢邈咬牙。
“我也说过,七十年后,您会在某个清晨后悔。”固安溅下一滴泪,那是七十年后的谢邈的泪水。
那个姑娘会在很多年后一直藏在你的脑子里,她从不听话,犟得像牛,所以你赶也赶不走,你会在一个清晨,陷入梦境与现实的恍惚,像一个疯子一样问别人:“我的皇后呢?”
不是定远将军的女儿,也不是三宫六院中任何一人,你找不到答案了。
“所以不能放箭!”固安直视他的双眸,一字字从齿缝间蹦出,谢邈震惊,不是因为他的逾越,而是声音与神情中透露出的,一种远胜于自己的成熟的天子之威。
谢邈愣神间,固安已跨上马,飞快地疾驰。
固安的情绪如颠伏的马背,其实只要谢邈放箭纵火,王前春绝无逃离之机,五姐姐也可以很快被接回来,多年心结得解,可是为什么,到了这最后关头,阻碍一切的竟然是他自己,而他竟然是为了那个再三背叛他的女人。
那么,借助固安的身体回来,究竟是为什么,有什么意义?
答案静静站在他眼前,一身素白,笑得可恶的女人,缓缓走过来,在谢邈动手之前,她便劝离了王前春的队伍,让他们背向离开包围圈。
她知道面对气急败坏的谢邈会有怎样的下场,可她笑容平静从容。
“阿弟,你来了,”慎独眼眸中希望与失望并现,不是她预想的那个人,可在紧要关头,世间还是有一个人,会以她为先,前来接她。
身后不远处的谢邈,脸色铁青,挥指,一线火势瞬间蔓延开,漫天箭雨泼洒。
固安瞳孔骤缩,是不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可以原谅这个蠢女人所做的一切,但愿那一箭能落空。
“刺”的一声,箭头轻易穿透她单薄的躯体。
“不是这样,”固安的心脏瞬间停滞,脸色煞白,“我才不是你阿弟,我才不是太监。”
他疯狂地纵马前奔,箭矢穿透肩胛毫无痛楚,他只想嘶喊:“我是天子,我是谢邈。我是你丈夫!”
不知她倒下前的那一眼,那双动人的眸子,是否看出固安躯体下,是她深爱已久的陛下,可她再没有第二眼可以去看清了。
“我独一无二的慎独。”
极轻一句话语,是某个惬意至极的下午,御书房中掩于书卷下的,字字情动。
“慎独的独,是寡人心底,独一无二的独。”
【九】
年老的天子与年老的宦官终于对坐默然,固安嘶哑着声音道:“不知道,如今我说阿姐是个好女人,陛下还信不信?”
“在我眼里,她跟其他温柔的姐姐没有什么不一样,庶姐看不起我,慎独便划花了她的脸,后母打我耳光,她便替我打回来,后来有一次,我慌张跑来,我在玩闹中不慎溺毙了一个婢女,慎独替我将那个婢女埋在她的院中,王前春选她入宫,她惧怕院中的尸骨挖出来后,我会被偿命,于是她将我带在身旁。”
多么想昭告天下人,她应该是个好姑娘的,一直为弟弟承担一切罪责。
“她是个好姐姐啊,却不是个好妻子。”
谢邈起身离去,终于肯安生地放下这一切,他知道了慎独对他的心意,而他最后也并没有太对不起她,那么午夜梦回,负罪感就会减轻许多,即使永远不知道那样爱慕他的慎独,究竟为什么在最后背叛他。
那一晚的谢邈重新取出白绫,即使他不再需要扮演一个瞎子。
眼盲与心盲,他不需要知道真相。
身后的固安眯了眼,蝉蜕之术,在慎家这一代,不仅仅是固安一人,慎独同样可以。
其实,一开始的结局是,谢邈在那一次的冬日猎杀确实成功了,可惜王前春逃了出来,几年后,阉党凶恶地反扑,谢邈被毒死在寝殿,甚至都没有等到自己的五姐姐归来。
固安记得那一日,灵堂中慎独红肿着双眼,她对他说:“我一直都知道,陛下不是个瞎子,因为他看向我的时候,那双眼睛充满了神采,是爱慕一个人的神采。”
当晚慎独在灵堂中,实施了蝉蜕之术,回到冬猎之日,破坏了谢邈的行动,让王前春一开始就在不知情中逃走,后面虽然谢邈被阉党囚禁了七年,可他活到了女帝归来,并且福泽绵延,长命百岁。
哪怕,他会痛恨她,误解她,永不原谅她,只要他活在这世间,她就没有白死。
中箭身亡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没看到,这个担负罪名与脏水的女人,嘴角一弯,她渐渐笑起来。
“陛下对我而言也是独一无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