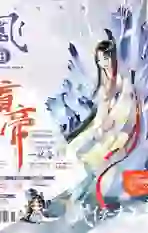萤火心裁
2016-12-22璇央
璇央
序
四十岁时我的兵马席卷大半个九州,这一世我历经过繁华与动乱,余生的心愿是乱世在我手中终结。
这个心愿还差一点、差一点就可以实现。
我在深秋时节向江陵进军,得到江陵后长江以南的分裂将由我来结束。
在逼近江陵城下时,我忽然记起了一位故人,那位故人平生最厌兵戈,不知这些年来乱世飘摇她可安好?
据说她这些年走过很多地方,最后落脚在江陵。
一
褚荧与程炎的初遇,是在二十五年前的洛阳城西大牢。
那年褚荧十八,此前人生中从未踏足过如此肮脏黑暗的地方,牢中的腥臭逼得她皱眉,充盈于耳的哭喊让她提灯的手微微发颤,却不得不咬牙跟在狱卒后面,一步步仿佛走向地狱。
终于狱卒停步,回头看了她一眼后悄无声息地离去。
她快步上前,灯火幽幽映照一张面黄肌瘦的脸。
褚荧忍不住哀泣,那人是她的父亲。
男子平静睁眼:“你不该来此。”
“听闻刘茴不愿放过父亲……”
“为父因弹劾阉党获罪,是为民受难,死又何妨?”
却听隔壁牢中忽地轻笑一声:“褚御史死了,阉狗刘茴不还是活着。”
褚父肃然:“若我之死能唤天下士人之良知,无憾矣。”
褚荧疑惑道:“你是如何得知家父身份的?”
“猜的咯,听人说如今朝堂除了混账与废物,便只剩一个褚御史还算得上是官儿。”
褚父闻言缄默良久,最终长叹:“阉党当道,奸佞掌权,为之奈何!”
褚荧不由得走到隔壁,然后模糊看清了那间囚室里的情形。
监牢无窗,缺墙漏进的月光晦暗,映照半腐草堆上躺着的瘦小少年。听闻衣裙窸窣后他仰脸,正对上她略带怜悯的目光,于是弯眼一笑。
“你年纪这样小,为什么会在这儿?”褚荧忍不住问。
“造反呗。”少年满不在乎的三个字。
后来褚荧才从狱卒口中得知,那少年的确是反贼,其父程元乃吴越一带的朝廷大患,而他是程元长子,名炎。
二
程炎再一次见到她,是在半年后。
半年后,褚御史死于狱中,褚荧前来收尸。
那日她一身素缟,在昏沉一片的囚牢之中白得刺目。牢门打开后她木然入内,抱住冰冷的尸首许久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动,跪坐在地是脊梁笔直的姿态。
那时程炎也快死了,狱卒不会因他年少而仁慈,入狱时便带伤的他在历经一系列拷打后患了风寒,更因为狱卒的苛待,病势加重。
但他不想死。
他一点点爬近,抓住铁栅栏。
少女偏头,他这才发现她原来已哭得两眼发红,只是哭声一直被刻意压抑着。
倒是个好强的。他心里暗暗想,开口:“姐姐可想报仇?”
狱卒说褚父是病死,但他知道并不是。
“昨夜,我亲眼看见两个宦官来这儿,毒死了他。”
褚荧早已料到了得罪权宦的下场,所以她惨白的脸上依旧是寂如死灰的静。
程炎哑声继续道:“做笔买卖,你给我水还有吃的,我帮你杀了刘茴,怎么样?”
“你能杀刘茴?”褚荧轻轻开口。
她尾音上扬的质疑语调刺伤了少年的自尊心,他扣住栅栏的手一紧:“给我一把刀,杀人又有何难?”他故意笑得狰狞且杀意凛凛,模仿记忆中的父亲的语气,道,“我自九岁起随父征战四方,死在我手下的人多不胜数——”
“杀人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她眉头蹙起,“何况……你才多大啊?”
程炎来不及回答她这个问题便毫无征兆地咳了起来,喉中腥甜涌上,他生生咽下,恶狠狠吐出两字:“十五!”
这个答案倒叫褚荧微愕。
原本她以为他最多十二三岁。原来竟是因为太过病弱,所以瘦削如同孩子。
褚荧不会天真到相信十五岁的少年可以做荆轲之辈,她看得出来,他只是想骗一条生路罢了。
最终她没有再多说什么,跟在抬尸狱卒身后,步履踉跄离去。
但次日,程炎当真收到了她费心托人送来的水和食物。
这施舍出于好人家闺秀自幼养成的良善慈悲,终究是靠着褚荧的怜悯,他一点点熬了过来。
一直熬到那年除夕,他的父亲没有放弃骁勇善战的长子,以七名亲信的死伤为代价将他从洛阳劫了出来。
三
重逢是在三年后。
三年后褚荧的姓名是褚英,身份是朝廷官僚。褚父死后褚家便没有姑娘只有继承父志的儿郎。
她被外放汝阴郡做太守佐官,那时天下并不安定,君王年少大权旁落,九州灾患四起各路乱军割据。但那时的汝阴好歹还是平静的,褚荧所见的汝阴一派悠然,百姓泰然安居,墟市喧闹繁华,四月春风拂过河堤柳,船舸流过,风中是清歌柔婉。
遇上程炎时褚荧正与一商贾争执。
确切地说,是为了一碗面被小贩数落得窘迫不已。
其实那日出门前褚荧是带够了面钱的,奈何店家见她外来书生软弱可欺,存心要讹她一笔。
正难堪之际,人群中忽地有人开口:“店家,昨儿我在你这儿吃面可只要五枚铜子。”
“记错了!我家向来是……”店家脱口道,然而不知怎的,话说了一半生生卡在了喉咙里。
那人笑得眉眼弯弯:“你方才说我记性差?”
“哟,程爷。”店家忙赔笑致歉。那人大剌剌地往褚荧身畔一坐,甩了几枚铜钱给店家,不多时一碗热面送上。
褚荧感激这人解围,道谢之后正欲告辞,却不防那人一把按住她落于凳上的袖摆:“不叙会儿旧?”
饶是褚荧记忆甚佳,也一时想不起面前这眉清目秀的少年姓甚名谁。
他笑:“从前见过的,忘了?”
这一笑,熟悉的狡黠让褚荧恍然大悟,“程炎”二字险些脱口而出,但她好歹还记着身为反贼的少年至今仍被朝廷悬赏人头。
犹豫了片刻后她压低声音,道:“你怎在这儿?快走,我今日就当没见过你。”
包庇乱民自是不该,只是褚荧终归是与他有几分交情,也觉得这少年不该如此年轻就被收押处死。
“你管我走不走。”他嬉笑道,黑白分明的眸子敏捷地将她上下打量,“倒是褚姑娘出现在这儿才不应该呢,啧,还一身男装。”
褚荧赧然,而程炎笑意愈浓,凑近了几分轻声开口:“近年来有个褚姓儒生名气很大,听说学问顶好,才及冠便得天子征拜为官。那人原来就是你……唉,你是想用这样的法子来复仇?”
她默认。
“可你是女人。”他撑着下颌,目光玩味,“小心穿帮后掉脑袋。”
心中隐忧被他道出,她咬唇,淡淡道:“与你无关。”
“还不如花钱雇我帮你,杀人嘛,不过一刀子的事。”程炎翻了个白眼。褚荧想要说什么,恰此时有三两乞儿挤上来,打断了她的话。
出乎意料,看起来既不算温柔也不算阔绰的程炎将那几个孩子招呼来身边,将身上所有的钱都摸出来分给了他们,又将大半的面也给了他们。
察觉到褚荧眼神有异,程炎扬起眉与之对视,倒叫她颇为尴尬,讷讷道:“原来你是善人。”
他冷笑:“莫非我是恶鬼?”
褚荧羞惭低头。在她认知中那些啸聚山林之辈都是凶残之人。
“这些孩子多半都是家中遭灾,活不下去了。”程炎也没有多说什么,对褚荧轻描淡写道。
“嗯,我知道。”
“那……你知道十年前的荆楚大旱吗?”他忽然问。
她点头。
“我原籍荆楚。大旱那年我老爹还不是反贼。”他说,“他带着家人向东逃难,一路上祖父母、阿弟先后饿死,叔父疾病,母亲为了替快死的小妹争一口吃的被人活活打死。”说这些事时他别开脸望向湖那边的景,褚荧看不到他的神情只能从言语间听出些许悲怆,“那年我八岁,可那年所历经的绝望,到了八十岁都不会忘。看着家人一个个死在面前,那时居然感受不到难过了,只是不停地想要吃的,一口就好……”
所以他可怜那些乞儿,因为可怜过去的自己。
褚荧不大会安慰人,想了想,道:“也许总有一日,这世上再无人受饥寒之苦,万民得以安康。”
程炎撇嘴:“你觉得会有那一日?”
她用力点头。
他笑了笑:“真不愧是读书人家出身。”
“你笑我书呆?”
“当然。”少年直言不讳,顿了顿,“不过我也希望你说的那些不切实际的话,有一天真的会实现。”
生活在肮脏世道上的人总会相信,一切苦难终有尽头,就好比走在黑夜里的人会期盼黎明。
但这个黎明,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必能等到。这个道理,是很多年后的程炎才会懂。
四
在汝阴为官的褚荧遇上程炎时,还以为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插曲。
在处理庶务之余她常见到程炎,或是在闾里,或是在市集,或是在郊野,他走了太多的地方,又是孤身一人,褚荧早该对他起疑。
后来褚荧才意识到程炎的狡猾,每当她觉察到什么不对想要诘问时,总被他三言两语将话引开,于是久而久之她便忘了问程炎为什么。
甚至久而久之,她可以心安理得地同程炎一起游湖、赏景却并不觉得有不妥,她早忘了彼此的身份。
当然,也许并不是程炎狡猾。与他并肩行过汝阴长街看日影斜长时,她也不知自己不多问是因为忘了问还是不想问。于每个俗世中人而言,总有些人是与众不同的存在。
她清楚地记得,上元那夜一瞬的悸动。
上元之夜他执意带她去赏灯,在一片炫目灯海中,他忽然将一物亮到她的眼前。
是支银钗,并未嵌宝镶翠,只是打造得尤为精巧,该于哪家碧玉小女髻上簪。
女子的首饰褚荧甚少碰过。她自幼丧母,父亲勤于治学无心管顾女儿家的喜好,而十八岁之后,她便是以男装示人了。
周遭太过喧闹,她用了很久才听清他说的是,送给你。
她自然是回绝:“无功不受禄。”
“你救过我,俗话怎么说来着,滴水之恩当涌泉报。”
褚荧愣了愣:“可、可这是女人的钗子,与我无用。”最后几个字说出来后她咬了咬唇。
“谁说无用了,难道你一世男装不成?”
“也许吧。”她黯然道。
“没有也许。”他撇嘴,“你既能为父报仇,也能风光大嫁,还能名留青史。要信自己有这个本事。”
“我的所作所为早已违背了闺训,谁会娶?”她苦笑。
“闺训是什么东西?”他翻了个白眼,“我要是娶媳妇,就娶不让须眉的女人。”
纵然她知道程炎只是在随口宽慰她,然而听到这句话的那瞬她还是忍不住偏头看向他。
十八岁的少年有着线条利落的侧颜,褚荧往日所见的每一个世家子都没有他那样锐利漆黑的眉,也没有他那般明熠生辉的眼。远处灯河涌流,而上元夜全部的华光,似乎都不及他笑容美好。
二十余年来只知圣贤的女儒生忽然就明白了话本中佳人们的心思。
她只是不明了未来。
就在上元过后的半个月,吴越反贼攻城,而上元之后,她再未见过程炎。
位于淮北的汝阴极靠近反贼老巢,身为程元长子的他带着刺探到的情报离开了汝阴,汝阴的地势、风土、气候乃至驻军薄弱都被他摸得一清二楚,城中守军听闻贼将至的消息后四散而逃,反贼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汝阴,大肆劫掠。
那是褚荧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惨烈”,放眼所见四处都是杀戮,鲜血铺满城中每一角落,火光直冲天际遮蔽了月。
她在城中狼狈逃窜,也不记得跑过多少条街。因为太过惊心以至于后来那夜逃亡的记忆全部模糊,除了血与火外,她唯一能清楚记起的只是她找到太守的宅院后,那六旬老者平静如死灰的神情。
“先生……不逃吗?”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老人端坐在席上,近百年的沧桑刻在每道皱纹中,“这是乱世,逃到哪儿都是一样的。”
五
汝阴的战报传到洛阳,不过寥寥数字而已。官僚依旧醉生梦死,天子依旧耽溺玩乐,而宦官刘茴依旧是这个王朝最高的主宰。
褚荧将洛阳百态收于眼中,沉默,很长一段时间闭门谢客。
但想要见她的人,总有办法见到的。
程炎来到洛阳是仲秋了,夜寒风凉,他于三更时分翻墙入室,十足的宵小行径,不过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想见褚荧又不想被其他人发觉,难道还要他光天化日递拜帖吗?
至于为什么要见褚荧,他自己也说不大清,也许是因为怕她死在汝阴,所以想来看一眼。
可是程炎终究太过年少,年少的人总会想当然,他赶了几个月的路北上,去见他想见的姑娘,却从没有想过如果她不愿见他,那该如何。
“你为何在这儿?”在惊讶之后,她换上了一副冷面孔。
“来看你啊。”他大大方方地往她书桌旁一坐,拾起一只茶盅把玩。
“出去。”
听到这两个字时他以为是错觉,可抬头,却真切地从她眸中看到了厌恶。
“请回。我不愿与逆贼来往。”她背过身去。
程炎愕然,过了一会儿他轻轻问:“你是怪我……怪我没有在我老爹进攻前知会你一声让你受了惊吓?”
“不。”褚荧说,“我怨你父子滥杀无辜。”
他很长的时间都无言以对,最后他道:“我们这些乱民不抢怎么活,没有足够的粮草怎么抵御官兵?嗬,你以为若是官兵遇上了我们又会仁慈到哪里去吗?”
“所以便可以杀百姓?”她冷笑。
“那我们被杀就是活该?”他针锋相对。
褚荧垂目:“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去劫掠汝阴,但,终究无法释怀。那么多条人命在我面前死去,整个汝阴一夜成灰。还请程公子日后别再来找我,否则我愿为朝廷捕杀叛逆。”
“你当真那么狠心?”
她从抽屉中摸出一物,正是上元夜他赠予的银钗,双手呈到他面前,她说:“愿与君,再无瓜葛。”
那支曾被褚荧妥帖珍藏私下反复摩挲的钗子在那夜被程炎从褚荧手中接过后掷出了窗。
他也跃出了窗,身形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褚荧一个人站在灯下发了很久的呆,直至烛火燃尽,她扶着墙缓缓坐在地上。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褚荧常有意无意在窗下徘徊,却再也没有瞧见那支银钗。
果然,有些东西失去后是无法挽回的。
六
之后又三年未见。
褚荧偶尔会想起程炎,可人生的意义并不只是在思念。
这三年里褚荧在士林中声望高涨,虽顾忌着自己女儿身份坚决不肯接受高官厚禄,可她的门生也逐渐遍布六部九卿,与阉党成分庭抗礼之势。
皇帝年岁渐长,她成为帝师,教导君王仁义道德与治国之术。尽管她的授课,皇帝不上心,但终归是对她日渐敬重。
刘茴愈发忌惮于她,三年来几次明争暗斗,各有输赢。
她慢慢意识到想扳倒刘茴不是靠着一腔热血就能做到的事,但她没有退路。
左右不过一条命,若能为百姓除奸邪那最好不过,若不能,死也无妨。她在心底这样告诉自己。
至于别的东西,譬如说寻觅良人、生儿育女——这些都太过美好,于她是奢望。
一年年春去秋来,王朝一年年在狼烟四起中苟延残喘。
好在世代的将门中仍有几个能征善战之辈,这几年替朝廷数次平寇。
褚荧敬重那几员武将,然而当她得知官军大败吴越程贼时,心中无论如何也畅快不起来。
九月,大军凯旋,在声势浩大的献俘仪式上,褚荧看到了程炎。
在她望向他时,他也正好看见了她,隔着那么远的距离那么多的人,他依稀对她笑了一下。
也许是想说别来无恙。
褚荧愣愣站在原地,在朝天子行跪拜礼时都险些忘了动作。
思量了一夜后,次日褚荧秘密探访程炎。
说起来,这是她第三次在昏暗的牢中见他。
油灯被点亮,她看清了他的脸,眉目依旧,却比起在汝阴时更瘦了些。他受了伤,利箭贯穿胸口的伤至今未愈合,他躺在污泥之中无力地看了她一眼:“不是说……再不愿与我有瓜葛吗?”
“我不想你死。”她扶着栅栏缓缓蹲下。
“为什么?”他抬头,因牵动伤口而皱眉。
褚荧犹豫着缄默。
她想,也许是因为不忍,她不忍让一个会施舍乞儿、会赠她银钗、会记得恩情、会飞扬轻笑的他去死。
“若真觉得咱们还算故人,那就送我一把刀。”他别过头,冷冷地道,“与其让我被困在这儿等待那些稀奇古怪的刑罚,倒不如给我个痛快。”
许久未听到她答话,他不由得抬眸,她迎着他的目光,想了想,一字一顿:“蝼蚁尚且偷生。”
程炎嗤笑一声:“你们士人不是最讲究什么气节吗?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是蝼蚁了?”
她低眸看着这个介乎少年与青年之间的人看了很久,最终沙哑开口:“我会救你。”
回到宅中褚荧连夜写了份奏章,这份长达数千字的上书说动了皇帝与丞相招安程炎之父程元。
只是前去招安的使者迟迟未定,毕竟谁都惜命,最后还是褚荧再次站出来受命,持节前往吴越。
没人知道她这一路上历经了多少艰险,总之她归来是在半年后。
半年后牢门打开,风尘仆仆的褚荧踏着一路洒落的阳光大步而来,对程炎说:“我带你离开。”
七
“我老爹接受招安了?”
“对。”
“他在哪儿?”
“荆楚一带为朝廷剿灭山匪。”
“那为何我还在洛阳?”
“因为现在你的身份是质子。”她将煎好的补药递给他。
这个身份他倒不是不能接受,悠然打量眼前古雅的陈设布置,他问:“那为何我住你这儿?”
“我对陛下说,反贼亦可教化。”她说,“所以陛下将你送来听我讲学。”
程炎的眉目扭成了一团,也不知是因为药太苦还是褚荧那句话。
无论程炎如何反对,师徒名分终究定下,褚荧在太学有弟子三千,可惜程炎自幼颠沛,也就能勉强书写自己的姓名,自然不能同太学生一起听讲。褚荧专程抽出时间为他授课,从最粗浅的《急就篇》《千字文》到后来的《诗》。听他抑扬顿挫地念“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时她会下意识心跳加快,她握笔教他书写时,每一画都极尽此生的温柔。
与他独处时她不会刻意压粗声音,也无须在意举止中的女态,后来有一日她忽然意识到,原来唯有和这个反贼在一起时她才是最轻松的。
程炎显然对诗词文赋兴趣不大,但他的聪明倒是让褚荧十分省心,这样一个悟性不输任何太学生的程炎让褚荧常常想,如他生在承平时,登科及第也不无可能。
那么他们之间,或许会有另一段故事。
甚至有一回她忍不住在他面前感慨:“若天子也能如你一般就好了。”
“你教了皇帝这么多年,那些圣贤哲言他还没学会?”
“陛下并不听我的。”她苦笑。
“在皇帝眼里,你还不如一个阉人重要。”他一针见血。
她抿紧唇一言不发。
程炎搁了笔,撑着下颌打量她:“怎么会有你这样死心眼的女人,我若是你……”
“你若是我当怎样?”
他促狭一笑,双眸弯弯:“我若是你,就抛下皇帝不要了,找个好看的男人跑了算了——就比如说我这样的。”
她陡然脸红:“胡说。”
“为什么不行?”他似笑非笑,也不知有几分认真,“不就是皇帝吗,有什么了不起。”
“慎言!”她慌忙去捂住他的嘴。
肌肤间的相触让他有些不自在,往后缩了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皇帝做得一团糟,倒不如推翻了!”
说出这番话后他心里其实是畅快的,却也忐忑,不知褚荧会作何反应。
灯火下她的脸色很白,白到近乎全无血色,垂目默然了很久,她轻轻说:“这样会死很多人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不喜欢流血,更不喜欢战乱,我希望天底下每一个人都能自在地成长、嫁娶、生子、老去。你懂吗?程炎。”
八
褚荧说的是她的心愿,亦是乱世中的奢望。
程炎不是不理解这个愿望,只是不能理解褚荧的坚持,在他看来,这个空有学问的女人实在太过天真,总之他是不会替一个黑白不分的皇帝卖命,而他的父亲在吴越一带叱咤了那么多年,也早就有了野心。
他明白自己的老爹是不会安分太久的,因此被困洛阳的那段时日他没有忘记伺机逃离。
他不知道褚荧有没有觉察到他的异动,但那日他晚归时一推门便看到她站在梅树下对他微笑,像是专程在等他。
他愣住,因为今日所见的她穿的竟是一袭浅绯女裙,袖边裙摆绣着藕花,长发绾成时兴的螺髻,她向他走来,步摇叮当作响。
“今日我生辰,可愿陪我出门走走?”她笑。
“不是……有宵禁吗?”他也不知为什么紧张。
“今夜上元,忘了吗?陪我去看灯火吧。”
他忽然记起似乎几年前他也曾陪她赏过灯,不过汝阴远没有洛阳繁华。
他牵着她的手穿行于车水马龙中,行人手中提灯,笑语盈盈,烟花从东西南北绽开,次第绚烂——那是程炎见过最美的上元,若干年后也能回忆起夜幕里烟花坠落时拖曳的那一抹华丽的尾光。
那夜的褚荧也极美,她戴了帷帽,他看不清她的脸,可他知道她在笑,隔着纱幕他隐约看见她的眼眸如月般明亮。
她和他一整夜都在被各色花灯点缀的洛阳游荡,猜灯谜、拉着他一起放烟花,最后买了一坛酒两人沿河边走边喝,双双醉倒在城郊某处无名园林的树下。
他记得她同他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说她孤独的童年、埋首苦读的少年、女扮男装的艰辛与恐惧,还有这些年的疲倦。
后来、后来他记得是她先吻了他。在最后的意志消散前,他反手抱住了她,之后发生了什么,他都不记得了。
次日醒来时,他以为他会看见她就在自己身边,可他睁眼,才发现自己身在一只小舟上。
水往东流,持桨的是个熟人。
“小姐让我送公子离开。”褚府老奴对他道。
程炎愣了很久,他自己都没有想好对策,一向恪守忠君之道的褚荧竟会助他逃离。
“是出了什么事吗?”
老奴摇头。
一个月后,程炎便知道是为什么了。
一个月后,朝廷征讨程贼的大军出征。
朝廷并不打算真正放过反贼,身为帝师的褚荧事先得到了风声,因为舍不得他死,所以不得不在他与道义之间做了一次选择。
九
暮春之时,程炎得到消息,褚荧与阉党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
他忽然有些后悔离开洛阳了。
又过了一个月,他听说刘茴被下狱,却并未被处死,反倒是褚荧不知为什么被打入死牢。
程炎将自己统领的军队交给了二弟,然后挑了十五位亲兵一同飞奔去洛阳。
打探好褚荧所在的地方后,他命手下在城内纵火,乘着混乱之际杀入了监牢。
说起来他们当真是与囚笼有缘,几次相见都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只是这一次困在里面的人成了她。
许是因为她曾经的身份,牢房尚算干净,她半躺在床上,盖着一张厚毯,远处火光剪出一个憔悴的影。
“褚荧!”他大步上前,试着用方才从狱卒手里抢到的钥匙开门。
“你……来了。”褚荧的语调太过复杂,至少当时的程炎听不懂她的悲喜,“这把火,是你放的?”
“我是为了救你。”他动作一顿。
“多少人会死于火中,多少人将无家可归!”她冷厉质问。
“那些人与我无干,我管他们是死是活!”他仰起头,“人只能保护那么几个心里在意的人……阿荧,我也不想你死。”
“我的生死,不是你可以决定的。”她合上眼。
“怎么不可以,只要你和我走!没有人可以动你。”
“我不会和你走。”从来都是文雅温柔的一个人,说出这句话时冷硬如铁。
“为什么?”
“为我定下死罪的,是天子。”她慢慢说,“君要臣死,怎能违背。”
“愚忠!”
“我死,自有我的理由。”
“由不得你!”锁终于被打开,他一脚踹开门。
她立时拔下头上簪子抵在喉间,不语,目光冷冷。
程炎停住了脚步。
其实褚荧根本威胁不了他,他清楚绾发的簪子并不锐利,以他的本事绝对能在簪脚刺破皮肉之前制住她,顺便将她打晕带走。
他只是惊讶于她眸中的决绝。
“还不快走!”她喝道,“我褚荧堂堂名门之后,死也不会与你这贼子死一处!你走!”见他仍是不动,她放声大喊:“来人!有人劫狱!来人呐!”
数不清有多少脚步声迫近,而他只是怔怔看着她,这夜的火光映照在她瞳孔里,她目光能将他灼伤。
有人挥刀砍向他,他侧身躲过,又有一人横斩,他再躲,劈来的刀断了他耳畔鬓发,而她背过身去,再不看他。
他最终死心,转身突围,走得狼狈且匆匆,甚至再没有看她一眼。
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遇见她。
缘分是何其玄妙的东西,到了四十岁时,踏遍了大半个九州的他终于相信,他们之间的缘分,早在那一年便被耗尽了。
后来程炎偶尔听过她的传闻,她没死,皇帝后来又赦了她,只是不许她再为官。阉党终究是倒了,然而已然走到尽头的王朝回天乏术,数年之后终是亡国,天下四分五裂,群雄逐鹿。
程元战死后程炎继承了父亲兵马,从贼寇渠帅逐渐成长为一代枭雄,乃至最可能成为皇帝的人。
近二十载流光匆匆,天下大势已定,乱世也许就要结束了。
终
当我终于兵临江陵城下时,城内太守打开了门,愿主动献城投降。
这些年混战不断,一城太守往往相当于一个小的诸侯。让我意外的是,江陵的太守竟十分年轻,言行谈吐皆儒雅。
他说他之所以是太守,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
我问是谁。他不答,只是将我带到城内的一处祠堂。
那里供奉的人是——
“褚荧。”我轻轻念出这两个字,恍如隔世,“她,死了?”
“对,死了。要不要听听这些年来她的故事?”年轻人说,“十八年前她因为欺君之罪下狱,狱中仍不忘社稷苍生,上血书恳请天子除奸佞。最后天子只得感慨‘妇人尚知忠奸,何况君王,终是狠下心将刘茴斩首。”
“难怪她不跟我走,那时刘茴未死。”我苦笑。
“她太过传奇,天子终因民心所向将她赦罪,之后她游历大江南北,于八年前定居江陵。在这里她开设学堂、辅佐太守,使一方安宁。她死后不久,恰好太守也去世,我被推举为新的太守。”
“你和她,什么关系?”
他看着我:“将军可知十八年前褚荧为何犯下欺君之罪?”
“因为她……女扮男装被人发觉?”
“她之所以被人发现是女儿身,是因为那时她怀有身孕。”
我倒吸口气,猛地转头。
年轻人眉清目秀,像极了记忆里的那个人。
他说:“母亲死在三年前。有一伙乱军想要劫掠江陵,母亲率江陵百姓抵抗,战死。她死前对我说,这个乱世,凭杀戮只能成为贼寇,想要得到天下,非民心不可。”
我知道她这话的意思。昔年我在洛阳时,褚荧教过我什么是仁政,什么是君王之德,那时不懂,可后来,便明白了。
“母亲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的父亲能够得到大半个天下,说明他已不再是那个只知打打杀杀的反贼,那么天下可以托付给他,江陵也是。”他朝我跪下,叩首,“父亲,母亲的江陵,如今交给您了。”
我不得不闭眼,否则怕酸涩的眸中会有泪涌出:“她还说什么了?”
“她说,她的愿望没能实现,是她的遗憾。她希望她的遗憾不要在别人身上重演。”
掌心忽然刺痛,是一支银钗被我握得太紧,刺破了手心。多年前我以这支钗报褚荧救命之恩,她后来退还给了我,此后这支钗一直被我收在袖中,想她的时候我会无意识地摩挲,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它竟能刺伤人。
我摊开掌心,鲜血缓缓淌下,耳畔依稀有人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她希望天底下每一个人都能自在地成长、嫁娶、生子、老去。
生不逢时的,岂止我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