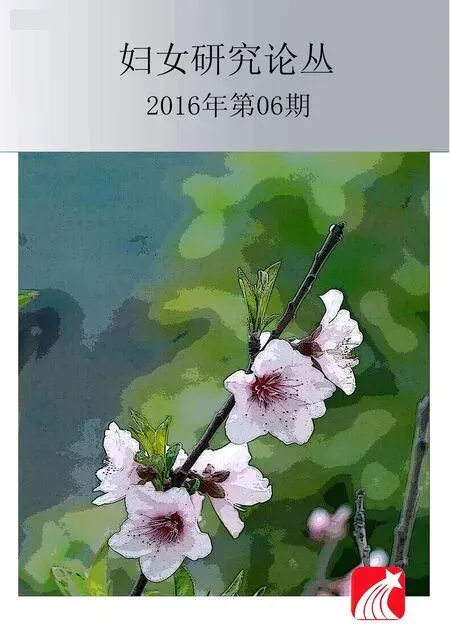爱恨交织的母女关系叙述
——加勒比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母亲话语
2016-12-18张雪峰
张雪峰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爱恨交织的母女关系叙述
——加勒比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母亲话语
张雪峰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加勒比女性文学;母女关系;依赖;疏离;母亲话语
加勒比地区漫长的殖民历史、奴隶历史与父权社会体系等因素不仅丰富了母亲在加勒比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寓意,也成为孕育加勒比女性话语力量的沃土。本文通过追溯加勒比女性文本中母女间爱恨交织、依赖与疏离共存的关系叙述,揭示加勒比母亲话语诞生的社会历史成因,解析母亲这一书写主题在加勒比文化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寓意,映射加勒比女性的历史记忆与生存境遇。
母女关系叙述在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中大体经历了19世纪末的母女分离时期、20世纪初的女儿反思时期以及20世纪中后期的母亲回归时期,这既是母女关系从分离走向弥合的一个转变过程,也是女性心理与女性身份从对立走向认同的一个认知历程。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母女关系书写构建母亲话语以及展现母亲与女儿共性的女性心理与女性身份认知逐渐成为女性主义的主流思潮。继西方女性作家与非裔美国女性作家之后,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起步的加勒比女性作家也随即加入这一潮流,但殖民历史、奴隶历史、加勒比父权社会体系以及多元的地域文化等诸多因素的融杂又使得加勒比女性作品中的母女关系叙述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寓意。为此,本文将首先厘清母女关系叙述在女性主义写作发展中的转向,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追溯加勒比女性作家作品中女儿与母亲间爱恨交织、依赖与疏离共存的复杂关系叙述,揭示加勒比母亲话语诞生的具体社会历史成因,解析母亲这一书写主题在加勒比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寓意,并以此辨析加勒比女性书写集民族身份构建与女性身份构建为一体的书写特征。
一、母亲声音的回归
1976年,女性批评家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天生女人》(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中表述了以下观点:“曾经一度被扭曲、误用的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重要情感是一部尚未书写的巨著。或许在人类天性中,没有什么能比这两个具有生物相似性的身体可以生产出更有共鸣性的情感。”[1](PP225-226)此番言论不仅迅速掀起了借助于母女关系叙述探究女性主义话语的热潮,也使得追寻母亲、凸显母亲的女性声音、展现母亲与女儿共享的女性话语世界成为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发展的风向标。伊莱恩·肖尔沃特(E-laine Showalter)指出,“70年代的女性文学已经从厌母时期跨越至对母亲孜孜不倦的追寻时期”[2](P135),而评论者罗西·布莱多蒂(Rosi Braidotti)更是将这种通过母女关系链接女性话语传统中共性的女性心理与女性身份认同的书写方式视为“女性主义思潮的新范式”[3](P96)。
虽然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母女关系叙述在女性主义话语建构体系中也占据一定的位置,但女儿的话语视角却在母女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母亲往往成为女儿主体叙述中的客体,“女性主义写作与研究中大多关注的是女儿的视角,母亲却被置于客体位置,即母亲常游离于女性表征之外,母亲话语亦成为理论盲点,构成与父权世界的同谋”[4](P163)。因此,19世纪女性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或者如同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笔下的简·爱一样成为年幼丧母的女儿,或者如同简·奥斯汀(Jane Austen)笔下的伊丽莎白一样成为无法认同母亲生活价值的女儿①玛丽安·赫西(Marianne Hirsch)将奥斯汀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大致归纳为两类:一是常常表现为暴怒或是恶毒的强权型母亲,如凯瑟琳·德·包尔夫人(LadyCatherine de Bourgh)与邱吉尔夫人(Mrs.Churchill)等,另一类是柔弱、贫穷又略显愚笨型母亲,如贝内特夫人(Mrs.Bennet)与贝茨夫人(Mrs.Bates)。参见Hirsch,Marianne.The Mother/Daughter Plot:Narrative,Psychoanalysis,Feminism[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89,pp.47-48.,形成“缺场的母亲”“恶魔母亲”与“失去母爱的女儿”构建的母女叙述情节。这种失去母亲与母爱的女性叙述一方面是女性在19世纪的男权社会中普遍无话语权力的象征,“女性在父权社会中都是丧失母亲的孩子”[5](P90),另一方面则为女儿挣脱母亲遗留的女性传统约束、寻求女性话语权力创造可能,“母亲与女儿、女儿与母亲之间的纽带不得不中断,只有这样女儿才能成长为女人”[6](P108)。但正是这样的中断却使得母亲与女儿之间搭建的女性谱系遭遇断裂,而19世纪女性文本中单纯凸显女儿的叙述亦依然难脱男权世界的束缚,“屋里的天使”的命运归宿使得女儿这一女性形象所承载的女性话语诉求最终同样陷入了与父权社会同谋的结局,“女性谱系受到了压制,支持的仍然是父子关系以及将父亲与丈夫理想化的父权世界”[6](P108)。
自20世纪初开始,世界战争引发的欧美社会格局的变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于人类前俄狄浦斯心理的探索以及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都使得现代主义时期女性作品中的母女关系书写发生了变化。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为首的女性作家一方面公开拒斥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柔弱、温顺、无私又纯洁的“天使”女性形象,视“杀死屋里的天使”为其女性书写的使命[7](P721),另一方面又倡议通过“反思我们的母亲”(think back through our mothers)来建构女性话语传统,争取女性权力话语[8](P132)。因此,与19世纪女性作品通过压制母亲声音凸显女儿叙述声音的书写有所不同,20世纪现代主义女性作品在通过女儿的记忆重新揭开被埋藏的母亲的故事并以此实现与母亲情感衔接的同时,又以拒绝母亲或母辈的生活如对于浪漫爱情、婚姻生活的追求甚至是选择自杀的方式切断19世纪母系传统文化的毒瘤,重新探索女性身份话语的构建形式。譬如,伍尔夫在《一间屋子》(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重构其文学母亲朱迪斯·莎士比亚(Judith Shakespeare)的生活之时,宁可赐予其自杀的结局也不会让她成为母亲;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中,被视为另一女儿的莉丽也只能在“屋里的天使”拉姆齐夫人死亡之后,借助于其画作重新回溯、质疑拉姆齐夫人的传统女性生活并且探寻自己的女性自我,“莉丽对于母亲—孩子这一结构的重新建构既是对于自己画作的一种阐释亦是对于其自我的一种界定方式”[9](P688)。这种通过女儿视角拒斥母系女性文化传统束缚,同时又对母亲生活进行想象性的重构方式,使得断裂与依赖、反叛与合作同时交织的混杂性成为现代主义女性文本中的母女关系书写的主要特征。玛丽安·赫西(Marianne Hirsch)将这一时期的母女关系书写特征描述为一种“双重意识”:“这种双重意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女性主义批评探讨女性写作的范式……这些(20世纪现代主义时期)女性文本使得曾经被淹没的母女情节浮出水面,尽管各种矛盾性元素互相抵触、交织,但却创造出双重或是多重的母女关系层。”[4](P95)
时至20世纪后半叶,当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其“修正”范式,“以新的眼光、新的批评角度审视旧文本”之时[10](P18),当母亲与因其而衍生的母系文化谱系成为其“无法逃避的问题”之时[11](Pxx),重新审视母亲所承载的性别文化身份、关注前俄狄浦斯阶段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也成为女性主义力图修正的内容。除去里奇之外,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与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等美派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纷纷采用心理分析与社会学的方法探究产生母亲与母性的家庭与社会心理生成机制②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乔多罗(NancyChodorow)的著作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与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著作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对于推动美国女性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参见NancyChodorow.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 Press,1978;Carol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2.。而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为代表的法派女性主义批评家则将母亲与母性所负载的女性话语功能视为一种先于语言存在且蕴含无限“危险特质与颠覆潜力”的象征符码[4](P135)。不难发现,尽管这些话语理论建构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呼吁母亲声音的回归、撕裂母亲的生物性面纱以及揭示母亲背后的社会文化建构是这一阶段女性主义批评的主流导向。
然而,欧美女性主义通过母亲声音的回归以及母女关系的叙述,构筑起的只是白人女性身份的话语理论体系,这种由母女关系而延伸出来的母亲话语往往忽略了民族、种族与社会语境的差异,终归只能停留在隔靴搔痒的理论层面:“女性主义理论无法逃避母亲这一问题,但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11](Pxx)而同时代的佐拉·赫斯顿(Zora Hurston)、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与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等黑人女性作家无疑是将种族与母亲话语结合为一体的实践派典范,“作为界定与母亲关系的女性主义写作的一代,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探寻母性话语的有力场域”[4](P177),母亲在她们的作品中不仅仅是女性身份的象征,更是非裔美国女性文化传统的象征。种族与性别压制的创伤记忆也使得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女性文化纽带更为紧密,最终形成母女共同体的美国非裔女性话语体系特征。或许沃克在《追寻我们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Womanist Prose,1983)中颇具诗意的叙述是对美国非裔女性母亲话语的最佳阐释,“所有的年轻女性:我们的母亲、祖母与我们自己永不会逝于荒野之中”[12](P235)。
在非裔美国女性作家群体之外,加勒比女性作家对于推动母亲话语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但加勒比女性文学中的母亲话语却要么被置于边缘化的位置,加勒比文学评论者多莉莎·史密斯·希尔瓦(Dorisa Smith Silva)与西蒙·A.詹姆斯·亚历山大(Simone A.James Alexander)就曾愤愤不平地指出:“如果母亲是许多女性作家反复书写的一个主题,那么加勒比女性作家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13](Pvii);要么被笼统地纳入与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共享的黑人女性话语的建构体系,盖·威伦兹(Gay Wilentz)就曾将加勒比女性作家与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同时置入非洲文化传统进行考量,认为始发于非洲母亲谱系的口头文学是加勒比女性作家与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创作的源泉:“对于现当代非裔美国女性作家与加勒比女性作家而言,从母亲、祖母以及其他女性亲属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都是她们创作与汲取力量的源头。”[14](P394)的确,共同的奴隶历史与父权社会体系使得加勒比女性作家与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对于母亲或是母亲谱系文化都有着共通的情感寄托,但是加勒比地区漫长的殖民历史与地域文化特征又赋予加勒比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母亲不同的文学分量与文化内涵,形成的是不同于非裔(美国)女性作家的母亲话语范式:“加勒比女性作家承担着重构这一地区历史的重任,她们恢复加勒比‘母亲’历史的集体性行为与非裔美国女性作家的书写范式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巨大的差异。”[15](P108)忽略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历史与多民族、种族混杂的地域文化语境,一味地从种族与女性性别元素探究加勒比女性作家与非裔(美国)女性作家母性话语书写的共性,显然难以充分展现加勒比女性文学中母亲所承载的特殊历史文化寓意,也无法具体呈现加勒比女性文学的书写特征。因此,回归到加勒比地区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揭示加勒比母亲话语诞生的历史成因就成为解析母亲在加勒比社会语境中所承载的文化寓意以及展现母亲话语对于加勒比女性身份构建重要性的首要条件。
二、母女依赖关系背后的社会历史成因
对于母亲在加勒比文学与加勒比女性文学中的重要性,加勒比女性作家兼评论家奥利弗·西尼尔(Olive Senior)曾经在采访中做出这样的评述:
加勒比文学的主题这些年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四五十年代开始一直贯穿至现当代作品的主线就是寻求个人与民族身份以及探讨种族与阶级问题……所不同的是表现这些主题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譬如,加勒比女性作家就为我们开创了书写(女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加勒比母亲这一加勒比文学传统的新方法,我认为这是一种将社会政治问题个人化的方法[16](P485)。
西尼尔这一归纳性评述至少反馈出以下几点重要信息:(1)书写母亲是加勒比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加勒比(男性)文学至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的加勒比女性文学始终如此。(2)加勒比文学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常常成为探寻加勒比民族身份与个人身份的重要隐喻。(3)加勒比女性作家在作品中通过聚焦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个人叙述折射的是蕴含种族、民族、阶级等要素的加勒比民族叙事。作为加勒比文学的重要母题,母亲这一女性形象首先屡屡出现在许多加勒比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成为抒发其民族情怀的隐喻。譬如,爱德华·卡姆·布莱斯维特(Edward Kamau Brathwaite)曾将其一本诗集命名为《母亲诗歌》(Mother Poem,1977),以诗歌中的母亲形象隐喻其故土巴巴多斯(Barbados),“这是一首关于我的母亲——珊瑚石灰岩巴巴多斯海岛的诗歌”[17](Pix);乔治·兰明(George Lamming)在《我皮肤的城堡》(In the Castle of My Skin,1953)中则刻画了一个在家庭中集父母亲职责于一身的坚强女性形象。在故事开始处,男性人物G叙述道:“我的父亲只是留给了我父亲的概念,而离开我的他留下的只是让我的母亲承担起父亲的责任”[18](P3);在维迪亚达尔·拉萨德·奈保尔(V.S.Naipaul)的半自传体作品《米格尔大街》(Miguel Street,1959)中,唯一一个对于叙述者“我”的生活具有正面影响力的女性人物就是他的母亲;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在《星苹果王国》(The Star-Apple Kingdom,1979)这一首长诗中将母亲直接喻指为加勒比人的民族母亲,“她将我们凝聚在一起,而我们只是被历史遗弃的孤儿。我们姗姗来迟,如同缪斯,我们的母亲哺育着这些岛屿”[19](P278)。
尽管加勒比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母亲这一女性形象,但这一母亲或者只是加勒比人民族母亲的象征,而母亲所指涉的女性话语身份却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将母亲歌颂为民族母亲的比喻处处皆是,但是女性在民族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被普遍忽略”[20](P91),或者只是男性人物探寻自我身份的垫脚石,母亲这一女性人物完全失去其性别特征,更谈不上以主体身份展现其话语权力。譬如,有评论者就曾批评兰明在《我皮肤的城堡》中只是将母亲视为男性人物G的“陪衬”:“母亲只是被G视为去人性化的陪衬,G以反抗母亲来投射他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在他的叙述中,母亲只是一个毫无历史感却要受制于儿子赐予她的母亲角色……除了母亲这一身份之外,因为父母、丈夫和情欲的缺场,她无法拥有其他的社会身份。”[21](P46)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简·里斯(Jean Rhys)、米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与艾德维奇·丹蒂凯特(Edwidge Danticat)等诸多加勒比女性作家则是在延续书写母亲这一母题的基础之上,又通过聚焦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即西尼尔(Olive Senior)所言的“加勒比女性作家就为我们开创了书写(女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加勒比母亲这一加勒比文学传统的新方法”[16](P485),在加勒比文化语境内赋予母亲这一女性形象多重的文学寓意,将加勒比女性个人叙事与加勒比民族叙事融于一体,使得性别元素与民族、种族元素融合,重新凸显女性话语在加勒比历史文化中的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与兰明、奈保尔等加勒比男性作家一样,加勒比女性作家笔下的母亲依然是坚强的母亲形象,但这些母亲形象却不再是男性的陪衬,而是支撑家庭的核心人物,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里斯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中,女性人物安托瓦内特的生父在文本开始时就已死亡,只有其母亲安妮特支撑日益衰败的家庭,“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的生活,但是我的母亲却依然心怀希望”[22](PP15-16)。在金凯德的《安妮·约翰》(Annie John,1985)中,母亲同样是家庭的核心支柱,母亲对于女儿安妮的成长也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而父亲则只是可有可无的陪衬。在克里夫的作品《阿本》(Abeng,1984)中,克莱尔的母亲吉蒂同样是一个坚强的母亲,她的女儿“很少见她流泪”[23](P52);丹蒂凯特《呼吸、眼睛与记忆》(Breath,Eyes,Memory,1994)中的母亲玛蒂娜背井离乡并同时做两份工作,竭尽全力地维持女儿索菲与家人的生活。
然而,与母亲的坚强形象形成明显反差的是,父亲这一男性人物形象却常常处于缺场的位置,他们在作品中或是去世或是抛弃、远离家庭,即使偶尔出现,也少有男性的威严感。有研究者认为,这一缺场的父亲既是父权受到“殖民文化阉割”的产物,又是加勒比“民族集体记忆丧失”的象征[24](P129)。这一阐释准确地阐释了缺场的父亲所承载的文化隐喻功能,但是除却这一文化功能之外,这一缺场的父亲以及由此而致的强势母亲形象亦是加勒比社会历史与文化现实的产物。一方面,加勒比奴隶庄园制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男性奴隶成为主要劳动力,这就迫使父亲们远离家庭,在孩子的记忆中留下缺场的印记:“在加勒比新世界,受奴役的父亲被剥夺了在孩子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权力与资格。”[25](PP183-184)另一方面,殖民入侵、奴隶庄园制经济的需要又使得大量非裔移居加勒比地区,一夫多妻与纳妾等非洲旧习俗也随之在加勒比地区生根发芽,这一民俗传统的渗入对于加勒比社会的家庭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父亲常常游离于家庭之外,母亲成为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1957年,伊迪丝·克拉科(Edith Clark)在其人类学研究著作《我的母亲以父之名养育了我》(My Mother Fathered Me)中就曾以牙买加社会体系为例,揭示出母亲在西印度家庭结构中的主导地位③西印度(West Indies/West Indian)群岛通常指加勒比地区前英属殖民地,如牙买加、特立尼达、巴巴多斯以及安提瓜、圭亚那等。而“加勒比”(Caribbean)一词则指该地区所有的岛国。为便于论述,本文文内所提及的加勒比文学或西印度文学均指涉加勒比英语文学。。加勒比女性作家兼批评家莫莉·霍奇(Merle Hodge)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新世界,父亲的功能仅限于使女性孕育。家庭的状态在这里完全丧失,因为这里没有家庭的概念,他不会与妻子和孩子生活在一个家庭单位,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孩子,或者那些孩子有多大概率不是他的孩子,他也不会抚养这些孩子……于是,女性就只能既是母亲又是父亲。”[26](P3)
父亲在家庭结构中的缺失加固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加勒比作家凸显母亲在家庭关系中重要性的主要诱因,就像兰明作品中的男性人物G对于母亲世界的感悟:“受困于被遗弃这样一种思维,她总是对自己的孩子充满憧憬,却总会面对更强大的反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总想着会渡过难关,因为她对于孩子就意味着一切。”[18](P11)这也正是促使加勒比女性作品中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依赖关系变得更为明显的原因所在,母亲始终是女儿最为依赖的人。《藻海无边》中孤独无助的女儿安托瓦内特在母亲安妮特疯癫之后依然想要寻求母亲的关爱,“她低着头,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是我认识她的头发……我搂着她、亲吻着她;”[22](P40)《安妮·约翰》中不断反叛母亲的女儿安妮在叙述中也屡次表述自己对于母亲的情感依赖,“与母亲在一起的感觉竟然是如此重要”[27](P15);对于母亲的记忆也充斥于《露西》中远离故土的小女孩露西的全篇叙述中:“我过去的记忆里全是我的母亲。”[28](P90)加勒比女性文本中这些母女之间的亲密与依赖关系不仅能够展现出母亲在加勒比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重要性,更能映射出女性在加勒比社会的生存现实。
三、母女疏离关系背后的文化寓意
颇为有趣的是,与布莱斯维特、兰明、奈保尔等加勒比男性作家在作品中常通过男性人物即“儿子”的叙述声音歌颂母亲以及表述思念母亲之情不同,在加勒比女性文本中,母女之间的依赖感却逐步转变为疏离与仇恨感,女儿对于母亲总是充斥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在《黑暗中航行》(Voyage in the Dark,1934)里,母亲海斯特与女儿安娜彼此排斥,西印度女孩安娜在白人继母海斯特的眼中“完全是一个黑鬼”[29](P56),而安娜则认为海斯特的言辞对她而言“毫无意义”[29](P54);《藻海无边》中的母亲安妮特对于女儿安托瓦内特想要“抚平皱眉”的关爱,却表现出强烈的冷漠,“她推开我,不是粗鲁地推开而是平静地、冷冰冰地推开,不说一句话,好像要永远将我视为一个与她毫无关联的人”[22](P17);《安妮·约翰》中女儿安妮对于母亲从依赖至疏离的关系变化,也使得母女间由爱至恨、爱恨交织的情感更为强烈,“如果我的母亲有机会,她会杀了我,而如果我有勇气,我也会杀了我的母亲”[27](P87);在《露西》(Lucy,1990)中,女主人公露西则将自己对母亲的复杂情感转嫁到女主人玛利亚身上:“我爱玛利亚的时候是因为她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而我不爱玛利亚的时候也是因为她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28](P58)
加勒比女性作品中之所以出现诸多由爱至恨、爱恨交织的母女关系叙述可以归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加勒比女性作家常将自己对于生物母亲的记忆与认知融入作品之中,形成具有自传性质的母女关系书写特征。作为“第一位书写母女关系的加勒比女性作家”[30](P13),里斯就将其对于母亲的记忆与情感体验渗入自己的作品中。在里斯出生之后不久,其年幼的姐姐不幸夭折,一味沉浸于丧女之痛的母亲对于里斯表现得极为冷漠。在其未完成的自传《请微笑》(Smile Please,1979)中,里斯这样叙述道:“甚至在另一个孩子出生后(五年后里斯的妹妹出生),有一段时间她似乎还是觉得我非常讨人厌,我越来越害怕她……是的,她离我越来越远,当我想让她注意我时,她是那样的冷漠。”[31](P33)这样的童年记忆对于里斯的创作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有评论者曾指出,里斯作品中的母女关系叙述源于其对于母亲的创伤记忆,认为评论界常常“忽略”了里斯母女关系中存在的“虐待”(abusive)属性[32](P99)。虽然“虐待”一词过于严重,但却能够从另一侧面证实里斯本人与母亲的关系对其作品中母女关系叙述的影响。而作为将加勒比母女关系书写推向另一高点的当代加勒比女性作家,金凯德同样也将自己与母亲的故事渗透进其作品中。与里斯的童年经历较为相似,金凯德与母亲安妮之间的关系在其弟弟约瑟夫出生之后也发生了变化,“在约瑟夫出生之后,金凯德的妈妈转移了对于女儿的关注,全身心抚养这个男孩子”[33](P3),母女间的亲密与依赖也随之转为冷漠与疏远。金凯德在《我的弟弟》(My Brother,1997)这部具有浓烈自传色彩的作品中回忆道:“小的时候,她(我的母亲)看我的眼神里总是充满惊喜与欣赏,也会表扬我的超强记忆力……当我长大了,她却开始讨厌我了,因为我的超强记忆力总是让我能够记住一切,而这恰恰是她竭力想让大家忘却的。”[34](P75)于是,金凯德将自己对于母亲的记忆与母爱的认知刻写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安妮·约翰》中的主人公安妮与自己的母亲同名,《露西》中的露西与玛利亚之间依赖与隔阂共存的情感关系是金凯德与母亲情感关系的再现,而《我的弟弟》中对于母亲的叙述亦是金凯德童年记忆的复苏。
二是加勒比女性作家通过女儿对于母亲由爱至恨、爱恨交织的情感叙述,映射出的正是加勒比女性对于英殖民“母亲”由爱至恨、爱恨交织的殖民心理认知历程。漫长的英殖民历史与英殖民教育使得“西印度人都将英国视为自己的家园”[35](P32),加勒比女性作家借助于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声音道出西印度人最初对于英国这一殖民母亲的痴“爱”。《黑暗中航行》中的安娜叙述道:“自我能够阅读之时,我就读到了关于英国的一切,狭小与破旧(这类字眼)从不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29](P15);《藻海无边》中的安托瓦内特更是沉迷于自己编织的梦幻世界:“浪漫的小说、令人难以忘怀的流浪、画板、美景、华尔兹、音符……这就是英国与欧洲。”[22](P78)而在《第一次看见英国》(On Seeing England for the First Time,1991)这篇杂文的开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就以孩童的视角叙述出英国殖民母亲在西印度“女儿”眼中的完美形象:“温柔、美丽、细腻,它就是一颗奇特的宝石。”[36](P32)然而,当这一梦幻色彩被一一剥离,安娜、安托瓦内特以及“我”等西印度女儿对于英国这一殖民母亲随之产生的则是爱之切亦恶之切的情感变化。曾经幻想与“狭小、破旧”毫无关联的伦敦大都市与安娜的想象大相径庭:“这就是伦敦,数以千计的白人拥拥攘攘,灰暗、沉闷且看不出任何差异的房子一栋连一栋,街道如同封闭的沟壑,而那些灰暗的房子则显得阴郁沉闷。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不喜欢这个地方”[29](PP15-16);而一步一步被逼向疯癫的安托瓦内特对于英国的梦幻想象最终也被瓦解得支离破碎:“我厌恶这个地方,我厌恶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雨;我厌恶这里的夕阳,无论它是何种颜色;我厌恶它的美丽、魔力与秘密,这些我都无法感受得到;我厌恶它的冷漠、残忍,而这竟然是其魅力的组成部分”[22](P141);在《第一次看见英国》中,成年的叙述者“我”在亲自去往英国之后,同样愤怒地叙述道:“唯有仇恨能填补充斥于英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空间。”[36](P37)这一连串的视觉感知与一系列的“不喜欢”“厌恶”与“仇恨”不仅仅描述出西印度女儿对于英国殖民母亲由爱至恨的心理反差,也映射出英殖民“母亲”强制赐予的乌托邦幻想世界的最终坍塌。正如托拜厄斯·多林(Tobias Doring)所言,加勒比女性“来到母国的初衷是为了寻求有意义的体验,但是看到的却是这一意义是如何被生产制造。”[37](P128)
究其实质,加勒比女性文本中母女之间从依赖到产生矛盾与冲突的变化关系,亦或是西印度“女儿”对于英国殖民“母亲”由爱至恨的情感变化,彰显的正是存在于西印度殖民地与欧洲殖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对此,金凯德本人的评述可谓一针见血:“我作品中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指涉的就是欧洲与西印度的关系,亦即权力强者与无权力弱者的关系,女儿是弱势一方而母亲则是强势的一方……母女之间的关系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并无二致。”[38](P12)“女儿”成熟的前提是挣脱“母亲”的强势束缚,这是母女之间产生异化心理,即由依赖至分离、由爱至恨的原因所在。同理,西印度被殖民者获取独立自由的前提是反抗一切殖民强权的主宰与压制,虽然异化心理同样会在对欧洲殖民者的被迫依赖到主动决裂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但此时的异化心理已经不再是弗朗茨·法侬(Frantz Fanon)笔下被“白面具”所遮蔽的自卑扭曲心理:“‘妈妈,看那个黑人,我好害怕!’害怕!害怕!他们已经开始害怕我了,我想笑,笑到自己流泪,却怎么都笑不出来”[39](P112),而是西印度人获取自由的必然途径,犹如塞布丽娜·布兰卡托(Sabrina Brancato)所评述的那样:“对一切政治主宰的反抗是获取自由的基础,而心理异化恰是抵达自由的路径。”[40](P23)借助于家庭领域中母女间依赖与疏离、爱恨交织的关系叙述,加勒比女性作家将西印度女性的个人叙述与西印度民族叙事融为一体,以女性个人叙述折射宏大的民族叙述,在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加勒比民族殖民历史的同时,又展现出女性性别元素在加勒比民族文化建构中的话语力量。
四、结语
加勒比漫长的殖民历史、奴隶历史与父权社会体系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不仅丰富了母亲在加勒比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寓意,也成为孕育加勒比女性话语力量的沃土。借助于文本中母女间依赖与疏离、依赖至疏离的关系叙述,加勒比女性作家一方面将宏大的民族叙事消解为女性个人叙述,又以女性个人叙述反射加勒比民族文化历史与社会现实,将长期受殖民与父权压制的女性性别元素注入加勒比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映射加勒比女性的殖民历史记忆,展现加勒比女性在构建加勒比民族文化身份历程中的重要性,形成了具有含混性情感张力的加勒比母女叙述话语形式。这种女性书写形式不再如西方女性文学那样一味地强调母女之间的女性认同关系,也不像非裔(美国)女性文学那样单纯地强调母女间共同的女性纽带与情感共鸣,而是以母女间爱恨交织、依赖与疏离共存的复杂关系与情感变化,将民族身份与女性身份融为一体,彰显母亲在加勒比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文化与性别话语功能,折射加勒比女性在殖民与后殖民时代的生存困境,凸显加勒比女性身份构建的话语特征。因此,“母亲”一词在加勒比社会文化语境中实际上已超出了其原有之意,不再是限于生育、照料,而是抽象的哺育与关爱,这也正是为加勒比地区漫长的殖民历史、奴隶历史与父权社会体系所贬抑的女性话语和价值体系。
[1]Adrienne Rich.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M].NewYork:Norton,1976.
[2]Elaine Showalter.Toward a Feminist Poetics[A].In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C].Ed.E-laine Showalter.NewYork:Pantheon,1985.
[3]Rosi Braidotti.The Politics ofOntological Difference[A].In Betwee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C].Ed.Teresa Brennan.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0.
[4]Marianne Hirsch.The Mother/Daughter Plot:Narrative,Psychoanalysis,Feminism[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89.
[5]Adrienne Rich.Jane Eyre:The Temptation ofa Motherless Daughter[A].In On Lies,Secrets and Silence:Selected Prose,1966-1978 [C].Ed.Adrienne Rich.NewYork:Norton,1979.
[6]Luce Irigaray.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M].Trans.Carolyn Burke.Paris:Minuit,1984.
[7]Beth C.Schwartz.ThinkingBack Through our Mothers:Virginia WoolfReads Shakespeare[J].ELH,1991,58(3).
[8]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M].NewYork:Harcourt Brace,1929.
[9]Joan Lidoff.Virginia Woolf's Feminine Sentence:The Mother-Daughter World ofTothe Light House[A].In Virginia Woolf:Critical Assessments(Vol.3)[C].Ed.Eleanor McNees.Mountfield:HelmInformation,1994.
[10]Adrienn Rich.When We Dead Awaken:Writingas Re-Vision[J].College English,1972,34(1).
[11]Patrice DiQuinzio.The Impossibility of Motherhood:Feminism,Individu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Mothering[M].NewYork: Routledge,1999.
[12]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Womanist Prose[M].San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ich,1983.
[13]Dorisa Smith Silva and Simone A.James Alexander.Introduction:Caribbean Mothering:AFeminist View[A].In Feminist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Caribbean Mothering[C].Eds.Dorisa Smith Silva and Simone A.James Alexander.Trenton:Africa World Press,2013.
[14]GayWilentz.Toward a Diaspora Literature:Black Women Writers fromAfrica,Caribbean and United States[J].College Englis,1992, 54(4).
[15]Caroline Rody.The Daughter's Return:African-American and Caribbean Women's Fictions of History[M].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1.
[16]Charles H.Rowell.An InterviewWith Olive Senior[J].Callaloo,1988,(36).
[17]Edward Kamau Brathwaite.Mother Poem[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77.
[18]George Lamming.In the Castle of My Skin[M].NewYork:Schocken Books,1983.
[19]Derek Walcott.The Star-Apple Kingdom[A].In The Poetry of Derek Walcott 1948-2013[C].Ed.Glyn Maxwell.New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4.
[20]Elleke Boehmer.Stories of Women:Gender and Narrative in the Postcolonial Nation[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Press, 2005.
[21]Rhonda Cobham.RevisioningOur Kumblas:TransformingFeminist and Nationalist Agendas in Three Caribbean Women’s Texts[J]. Callaloo,1993,16(1).
[22]Jean Rhys.Wide Sargasso Sea[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7.
[23]Michel Cliff.Abeng:A Novel[M].Trumansburg:CrossingPress,1984.
[24]张德明.成长、筑居与身份认同——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的成长主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25]Antonia MacDonald.MakingRoomfor Tantie:Motheringand Female Sexualityin Crick Crack,Monkey[A].In Feminist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aribbean Mothering[C].Eds.Dorsia Smith Silva and Simone A.James Alexander.Trenton:Africa World Press,2013.
[26]Leota S.Lawrence.Women in Caribbean Literature:The African Presence[J].Phylon,1983,44(1).
[27]Jamaica Kincaid.Annie John[M].New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5.
[28]Jamaica Kincaid.Lucy[M].New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0.
[29]Jean Rhys.Voyage in the Dark[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9.
[30]Niesen De Abruna.FamilyConnections:Mother and Mother Countryin the Fiction ofJean Rhys and Jamaica Kincaid[A].In Jamaica Kincaid[C].Ed.Harold Bloom.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8.
[31]Jean Rhys.Smile Please[M].London:Deutsch,1979.
[32]Patricia Moran.Virginia Woolf,Jean Rhys and the Aesthetics of Trauma[M].Palgrave Macmillan,2007.
[33]Justin D.Edwards.Understanding Jamaica Kincaid[M].Columbia:the UniversityofSouth Carolina Press,2007.
[34]Jamaica Kincaid.My Brother[M].New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7.
[35]Kenneth Ramchand.The West Indian Novel and Its Background[M].London:Faber and Faber,1970.
[36]Jamaica Kincaid.On SeeingEngland for the First Time[J].Transition,1991,(51).
[37]Tobias Doring.Caribbean-English Passages:Intertextuality in a Postcolonial Tradition[M].London and NewYork:Routeledge,2002.
[38]Allan Vorda.An Interviewwith Jamaica Kincaid[J].Mississippi Review,1991,20(1/2).
[39]Frantz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M].Trans.Charles LamMarkmann.NewYork:Grove Press,Inc,1967.
[40]Sabrina Brancato.Mother and Motherland in Jamaica Kincaid[M].NewYork:Peter Lang,2005.
责任编辑:含章
新书推介
《“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宋少鹏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5月。
该书以全球史的视野,探讨了中国女权思潮和实践的缘起,尤其把晚清中国的“女权”论和改革实践放在西方文明论在近代中国传播、转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究欧美文明论中的性别标准以及成因,考察欧洲文明论的性别标准在晚清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社会、中国妇女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晚清女性论者的“女权”论述,探讨女性是如何回应由男性开辟的“女权”论述的。(妇女研究所信息中心)
The Ambivalent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Anglophone-Caribbean Women's Writings
ZHANG Xue-fe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Anglophone-Caribbean women's writings;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dependence;split;maternal discourse
The legacy of European colonialism,slavery as well as the patriarchy not only expands the cultural tropes of the mother figure in Caribbean literature,but also fertilizes Caribbean female discourse.This article traces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Anglophone-Caribbean women's writings and highlights the love and hatred,dependence and splitting between the mother and the daughter,on the one hand,to uncover the hidden subtexts giving birth to Caribbean maternal discourse and foregrou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gure of mother in Caribbean society,and on the other hand,to mirror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living situation of Caribbean women by analyz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mother figure.
I106.4
A
1004-2563(2016)06-0100-09
张雪峰(1982-),女,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