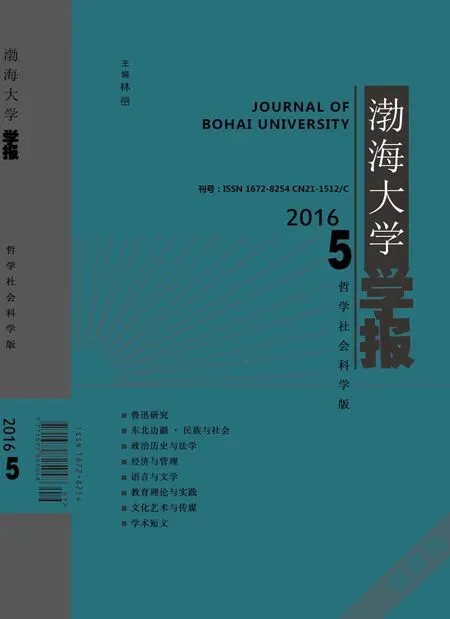从“本体”到“体制”
——艺术的审美观念转型及其反思
2016-12-18何晓军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何晓军(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从“本体”到“体制”
——艺术的审美观念转型及其反思
何晓军(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随着艺术的发展以及艺术史的变迁,艺术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转型。20世纪之前的艺术更多的是关注于艺术的本体性审美,而20世纪之后的艺术的判定则更多的是依赖于一种艺术的“体制”。本文从探究艺术的定义出发,深层揭示了艺术审美观念从“本体”到“体制”的转型,并对艺术审美观念转型进行当代性反思,从而明确当前艺术发展的特定言说立场和内在逻辑。
艺术;本体;体制;审美观念转型;反思
伴随着艺术以及艺术史的变迁,艺术的审美观念发生了转型。早从古希腊开始,人们便开启了对艺术的追问,18世纪之后,艺术逐渐被并入美学的审美体系之中,并与美发生深度的关联。在此期间,从艺术题材、艺术对象、艺术创作到艺术价值,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对美的探寻。进入20世纪,当传统的艺术审美经验遭遇到以先锋艺术、偶发艺术、波普艺术等为代表的当代艺术时,传统的艺术阐释经验已不再适用,由此引发了艺术审美观念的转型。可以说,20世纪之前的艺术更多的是关注艺术的本体性审美,而20世纪之后的艺术的判定则更多的是依赖于艺术的“体制”。艺术审美观念从“本体”到“体制”的转型,一方面直接表征了艺术的时代变迁,另一方面则深度隐喻了艺术话语权的陡然转变。在此,本文从探讨艺术的定义出发,深层揭示艺术审美观念的转型,并对艺术审美观念转型进行当代性反思,从而明确当前艺术发展的特定言说立场和内在逻辑。
一、艺术的“本体”定义与审美困境
从西方艺术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之前,学者们对艺术进行定义主要聚焦于艺术的“本体”,“所谓本体,指终极的存在,也就是表示事物内部根本属性、质的规定性和本源而与‘现象’相对。”[1]艺术的“本体”定义经历了诸多的历史嬗变,并逐渐形成了审美理论、模仿理论、表现理论、形式理论、价值理论。
自古希腊以来,艺术与审美便有着深层的关联。柏拉图曾对美的不同特性进行过阐释和区分,巴托于1746年首次对“美的艺术”的概念展开界定,鲍姆嘉通则在其《美学》一书中强调应该把艺术纳入美学的研究范畴。在此之后,阿尔伯蒂要求画家的作品需充分向“美”这一中心聚拢,以表现美的内涵。康德认为,艺术之所以是美的艺术,是因为它是天才的艺术、自由的艺术。蒙德里安则直接强调,“作为人类精神的纯粹创造,艺术被表现为在抽象形式中体现出来的纯粹的审美创造。”[2]艺术的审美理论恰是在艺术与审美的纠葛中形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艺术是模仿或再现”的艺术定义影响深远。苏格拉底和列奥纳多认为,艺术的模仿或再现具有合理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曾对此进行过论述,不过在柏拉图看来,艺术通过模仿所再现的只是外在事物的各种表象。巴多强调艺术的共同职责乃在于对自然的模仿,而德谟克利特则认为模仿能再现真实事物本身。不难发现,虽然学者们对“模仿”的认识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论点都指向了对艺术“对象性”的求索。
“艺术是表现”,该艺术定义路径诞生较晚,但它却把创作主体的生命意识纳入到了艺术之中。实际上,“表现”一词在19世纪之前很少被人们使用和关注,而浪漫主义者们则把艺术表现情感放在突出位置。华兹华斯就曾明确强调,诗歌之所以优秀,乃是因为它自发地流露出强劲的感情。德国音乐家巴赫也曾指出,音乐家在演奏时要想感动观众,其自身也必然会被音乐表现出来的情感所打动。然而,艺术表现理论成熟化和体系化的标志则在于1902年克罗齐《美学》一书的出版。在克罗齐之后,托尔斯泰和科林伍德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什么是艺术》和《艺术原理》中对“艺术与表现”的关联进行了深入探究。梅洛庞蒂也曾强调艺术的核心作用乃在于表现,他认为“在表现以前,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热切,只有当作品完成并被理解了之时,才能证明人们应该在这里找到某种东西而不是什么也没有。”[3]
在此之后,“艺术是形式”的定义开始流行。尽管亚里士多德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曾指出,艺术品除了应该具备相应的形式之外别无他求,但是直到20世纪,该理论才发展成为定义艺术的重要一环。克莱夫·贝尔、奥古斯特·查莫斯基、罗杰·弗莱、苏珊·朗格以及维特基维奇等艺术家,都曾主张艺术是一种形式的构造,法国理论家福西永还系统性地研究了艺术的形式问题,并出版了专著《形式的生命》。
此外,艺术的“价值论”、“美感经验论”以及“艺术源于激动”等论点,都曾对艺术有过深刻的影响。
不难发现,无论是审美说、模仿说、表现说,还是形式论、价值论和美感经验论,它们都是从艺术“本体”的视角出发,寻求对艺术的定义。显然,“审美说”关注的是艺术本体的根本属性,“模仿说”侧重于对艺术本体中“对象”的关注,“表现说”注重对艺术本体中“创作主体”的表达,“形式论”专注于艺术本体中艺术的“存在方式”,“价值论”则注重对艺术本质的多重评判。很明显,20世纪之前的艺术审美观念把更多的关注聚焦于艺术的本体之上,并试图从艺术的内部出发,挖掘艺术的审美张力和内在深度。
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艺术的本体性定义观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困境。当杜尚在1917年把其《泉》送往艺术家展展出时,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便开始遭到极大的冲击和颠覆,人们不得不怀疑一件既无高雅外形又无深刻寓意的平常小便器何以能成为艺术品?在《泉》事件之后,对传统艺术认知观念发起挑战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美国作曲家凯奇于1952年创作了《4分33秒》,这一作品空有一段时间的限度却并不演奏任何声音,如果非说有什么音响的话,有的只是在这段时间限度内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偶发性声响,这也能称得上是合格的声乐作品?此外,劳申伯格于20世纪50年代所创作的“混合绘画”作品,卡普洛于1959年开始践行的偶发艺术,曼佐尼于1961年所“创作”的《艺术家之屎》,以及沃霍尔于1964年展出的《布里乐盒》,它们的出现,都是无法用传统的艺术审美标准来衡量或评价艺术的。这便造成了艺术定义的危机。
基于无法及时、有效地对新出现的当代艺术进行定义或阐释,这一方面引发了当代艺术表征的危机,克莱尔、波德里亚以及福马罗利等理论家都曾宣称当代艺术正遭遇着困境;另一方面它还诱发了“艺术的终结”话语。然而,恰如丹托所指出的那样:“所终结的是叙事,而不是叙事的主题。”[4]由此可见,所谓艺术的终结,终结的只不过是一种艺术的表征或叙事模式,而作为叙事主题的艺术却并未终结。基于此,当代艺术继续寻求着有效的艺术定义路径。贝克尔就曾指出:“当旧的理论不能对相关艺术界中有见识的成员所普遍认可的作品的价值进行阐明时,新的理论就登场了。”[5]显然,当20世纪60年代学界对艺术的本体性审美定义遭遇困境而又束手无策时,新的“艺术界”理论和“艺术体制论”应运而生了。
二、艺术的“体制”言说与审美转型
自杜尚的《泉》开始,艺术学界便开始广泛关注当代艺术的新趋势和新动向,但是却并未形成能系统性阐释当代艺术的新理论。直到受沃霍尔《布里乐盒》的启发,丹托才开始从哲学思辨的视角介入对当代艺术的深入剖析,并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其极具影响力的“艺术界”理论。丹托指出,“把某一物品看成是艺术需要某种目不可见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便是艺术界。”[6]需要强调的是,艺术界作为一种“氛围”或是“知识”,它是处于持续运动之中的,霍华德·贝克尔在其《艺术界》中就曾强调了艺术界的新旧交替和不断变化。其实,当丹托提出“艺术界”时,实际上标志着艺术的审美观念已经悄然转型,因为自丹托之后,人们对艺术的追问或定义便开始由关注艺术品“本体”的审美特质转向了对艺术品外部氛围或语境的聚焦。受丹托启发,迪基建构起了其艺术体制论。迪基认为,某物之所以能被称为是一件艺术品,乃是因为它具备了两个条件,他强调,“从分类意义上说,一个艺术品是(1)一个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体制(艺术界)的一些人或一个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一组特征。”[7]显然,迪基一方面重视艺术的“人造性”,另一方面则高度强调了“艺术品资格授予”的关键性。在迪基看来,一切艺术活动都是在某种“艺术体制”之下进行的活动,作品被艺术体制授予“艺术品资格”之后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基于对艺术体制的发现,克鲁兹也强调道:“当前艺术的实质并不在于一些或成套的感知性特征,而是在于艺术的体制性背景。”[8]不难发现,体制论试图从艺术的外部体制或氛围出发,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艺术定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对阐释和定义当代艺术具有启发性和可操作性。
面对当代艺术的现状,分析美学家古德曼则认为,人们应当转变对艺术的研究思路。他强调,“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什么对象是(永久的)艺术品’,而是‘对象什么时候才算是艺术品’,或者更简单地说,恰如我的题目一样:‘何时是艺术’。”[9]显然,在古德曼看来,艺术是可以定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介入对艺术的提问。传统的观念试图从“艺术是什么”的路径出发定义艺术,而古德曼则更强调一种艺术作品的阐释语境和当下存在。其实,“从‘什么是艺术’到‘何时是艺术’,实际上表征了艺术观念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揭示了艺术定义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路径:功能性定义和惯例性定义。”[10]笔者认为,“什么是艺术”主要是从探究艺术本质的角度出发,揭示出艺术的本体性审美内涵,而“何时是艺术”则主要考虑到的是:决定作品之所以为艺术的特定情境或氛围语境。由此可见,在“艺术是什么”到“何时是艺术”的提问方式的转变中,实际上已经蕴含着一种艺术欣赏从关注“本体”到重视“体制”的艺术审美观念的转型。
在艺术体制论的特定情境下,各种以前无法用传统艺术审美经验界定的当代艺术逐渐被艺术的体制收编,并以其深远的影响改变了西方传统艺术的审美范式。在艺术体制之中,作品只需得到体制成员的认可便能成为一件艺术品,而不必在意它是否具有审美的外形或意蕴。正是因为如此,那件被杜尚送去展览馆展览的普通小便器便成为了艺术品,凯奇的《4分33秒》成为了艺术品,一条现成的海上漂流木也具备了艺术品的资格,沃霍尔的《布里乐盒》和《坎贝尔浓汤罐头》成为了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曼佐尼的《艺术家之屎》竟然能以黄金的价格进行拍卖。显然,艺术体制通过“艺术品资格授予”可以使任何事物具备成为艺术品的条件,因而诸多无法用传统艺术审美经验界定的当代艺术,在艺术的“体制”之中找到了家的感觉。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丹托和迪基看来,艺术界中掌握“艺术品资格授予”的人,需要懂得或多或少的相关艺术技能,艺术品资格的授予并不是随意的。斯蒂芬·戴维斯则进一步强调,应该把艺术身份的赋予视为一种权威的运用。
显然,在艺术的“体制”言说之下,艺术的审美观念发生了从“本体”到“体制”的转型。这一审美转型一方面诱发了当前艺术审美实践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对艺术的审美观念转型进行当代性反思就变得十分必要。
三、艺术审美观念转型的当代性反思
很明显,随着时代的更替以及艺术的发展,艺术审美观念的转型具有历史必然性。由于主宰不同时代的思想各有不同,因而在特定的艺术环境下将会诞生诸多各具特色的艺术理论。在艺术史上,艺术的审美观念由“本体”到“体制”的转型,也恰是因为时代变迁对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此,伴随着艺术审美观念的转型,当代艺术无论是在艺术对象、艺术形式,抑或是在艺术内容、艺术表现上,都与传统艺术有着众多的差异。
需要强调的是,艺术审美观念转型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其中,有三个问题极具代表性。首先,是艺术品资格授予的“权威性”问题。由于艺术体制成员对作品进行艺术品资格授予是决定作品能否成为艺术品的关键一环,因而艺术品资格授予的“权威性”问题亟待重视。丹托和迪基认为,艺术体制成员应该具有相关的知识或技能;贝克尔则提出谁有资格授予“艺术品资格”尚未有统一的看法;而约翰·凯里则走得更远,他指出,“尽管也许只有某人认为某物是艺术品,但只要某人认为某物是艺术品,它就是艺术品。”[11]可见,在凯里看来,人人都能授予作品以艺术品资格。但在笔者看来,对艺术品所进行的资格授予应当具有权威性。综合丹托、迪基以及戴维斯各方论点的相对优势,笔者认为,艺术品资格授予的“权威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艺术体制的成员具有较高层次的知识或技能;另一方面,艺术界具有受社会认可度高的相关“艺术品资格授予”规则或程序。显然,只有在艺术品资格授予具有权威性的前提之下,艺术体制影响下所诞生的艺术品才会具有公信力,从而才不会导致艺术品的无序化或泛滥成灾。
其次,是艺术的过度商业化和技术崇拜问题。在如今这个消费时代,再加上当代艺术的艺术品资格获得主要依赖于艺术的体制,这就为艺术的过度商业化提供了便利。一些艺术体制内的艺术家、博物馆负责人抑或是艺术评论家,他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不惜把艺术与商业混为一谈,把艺术的最终拍卖价格视为艺术价值实现的最高标准,而忽视了认真审视艺术的审美内涵。在艺术的审美观念转型中,技术在为艺术的发展提供诸多支持的同时,也导致了艺术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许多艺术品和艺术展脱离了技术的光环甚至无法进行欣赏或展示,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一定要把商业化和技术依赖的“度”把握好,而不是放纵其发展。
最后,是艺术的审美性问题。传统艺术注重艺术的本体性和审美性,当代艺术则不然。马克·吉梅内斯认为,当前艺术的审美标准已经不再可见或已消失;卡斯比特则强调,当今的艺术已经呈现出一种“后审美性”,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审美”的艺术。由此可见,伴随着艺术的审美观念转型,艺术的审美性问题值得重视。
更为重要的是,在艺术从“本体”到“体制”的审美观念转型中,人们需要理性地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一方面,中国传统艺术在艺术形式、艺术内容或审美意蕴等各方面的精髓都需要得到传承,以保证中华艺术不失“中国特色”和“民族之根”;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应看到西方艺术理念的独特之处和可取之处,并进行辩证地学习和吸收,以确保中国当代艺术在展现艺术审美内涵的同时更具时代性和包容性。总而言之,随着艺术的发展以及艺术史的变迁,当今艺术的审美观念已经发生了从“本体”到“体制”的重大转型,不论是艺术创作、艺术界定抑或是艺术欣赏,都无法脱离这一特定的时代语境。
[1]王岳川.当代美学核心:艺术本体论[J].文学评论, 1989(5):108.
[2]Piet Mondrian.The New Art-the New Life: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Piet Mondrian[M].eds.&trans.Harry Holtzman and Martin James,Boston:Da Capo Press,1986:28.
[3][法]梅洛庞蒂.眼与心[M].刘韵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53.
[4][美]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M].王春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
[5]Howard S.Becker,Art World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145.
[6]Arthur C.Danto,“The Artworld”,Aesthetics:The Big Questions[M].ed.Carolyn Korsmeyer,Cambridge:Blackwell, 1998:40.
[7]George Dickie.Art and the Aesthetic: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Ithaca[M].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34.
[8]Crowther,P.A,Cri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modernism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24.
[9]Goodman,N.Ways of Worldmaking[M].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1978:3.
[10]杨向荣.从“美”到“惯例”——艺术的现代观念转型及其中国情境的反思[J].文学评论,2015(3):42.
[11][英]约翰·凯里.艺术有什么用?[M].刘洪涛,谢江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29.
(责任编辑陈佳琳)
J01
A
1672-8254(2016)05-0124-04
2016-04-17
何晓军(1989—),男,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美学、艺术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