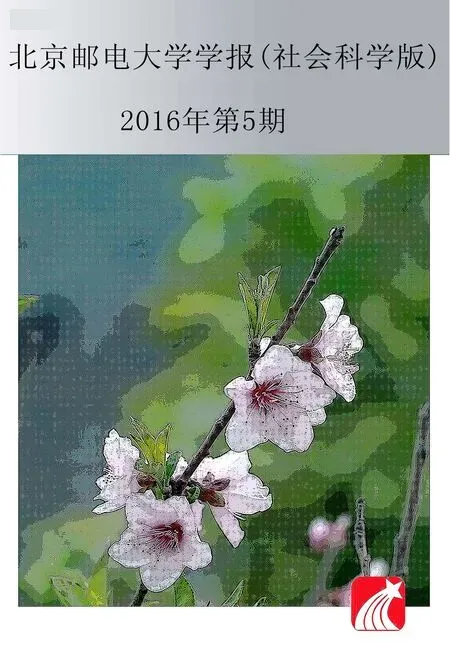“互联网+”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应用的问题及对策
2016-12-18李长远
李长远
(甘肃政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互联网+”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应用的问题及对策
李长远
(甘肃政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互联网+”思维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应用,可以创造智能养老产业新业态。实现我国“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面临政府、平台、服务商和技术四个方面的障碍。促进两者深度融合的策略在于:加强政府顶层设计,推进部门协作;引导、支持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和服务递送;搭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推动养老服务信息技术研发。
“互联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一、引 言
“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战略,核心是将互联网和养老服务业整合起来,以信息流带动养老服务,创造智能养老产业新业态。在“互联网+”的运用下,将互联网、物联网和移动通信网三网融合,并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集成和优化作用,促使社会各方面资源进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立信息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和服务高效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从而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2015年3月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同年4月,发改委、民政部、老龄委等部门在《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服务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互联网+养老服务”这一新课题。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专门指出“要加快发展居家网络信息服务,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新兴业态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上海、苏州、兰州等地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建立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如何在养老服务领域推进“互联网+”行动,利用“互联网+”来拓展社区居家养老的发展,实现“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且养老服务发展滞后的背景下,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将“互联网+”思维应用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将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打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瓶颈,但学者对“互联网+养老”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养老”内涵阐释、应用价值、优势、发展前景分析方面。张泉等[1]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对“互联网+养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总结了学者对其内涵理解的三个共同之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通过“互联网+养老”,可以实现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养老服务体系。童星[2]认为“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以发挥互联网集成和优化作用,促进社会各方面资源进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潘峰[3]认为“互联网+养老”的运用,可以妥善解决社区养老发展中面临的服务资源难整合、服务供需不匹配、服务效率低等问题。熊文静等[4]提出了电子养老的概念,认为电子养老可以降低服务成本,减轻政府、社区、家庭的负担,弥补护理人员短缺。睢党臣等[5]在分析了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 “互联网+”理念可以拓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分析了“互联网+”给居家养老服务带来的机遇。同春芬等[6]阐释了“互联网+”思维在养老服务中应用的价值:彰显了人本的养老理念;可以实现养老服务的转型与优化;预示着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
第二,“互联网+”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方面。郝涛等[7]在“互联网+养老”背景下探讨了老年残疾人养老服务社会支持体系的内涵及责任主体,提出了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途径与方法。陈莉等[8]在“互联网+”背景下,探讨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原则、内容、载体及平台设计,提出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构的难点与对策。
第三,虚拟养老方面。虚拟养老作为信息技术在养老服务中应用的雏形,相对于“互联网+养老服务”,较早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张国平[9]和刘红芹等[10]分别以苏州市沧浪区和兰州市城关区为例,介绍了两地的虚拟养老运行模式、存在的不足、可复制性及对策建议。
二、“互联网+”思维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应用的行动逻辑
1.“互联网+”解决养老服务供求信息不对称问题
养老服务供需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传递的滞后性,是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的现象比较严重,养老服务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的情况同时存在。通过调查发现,老年人在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服务需求和服务利用之间落差明显。与需求比例相比,供给比例总体较低,服务供给满足不了老年人的服务需求。精神慰藉类的服务需求大于供给比例达到了22%。相对于供给水平,养老服务各项目利用水平也普遍较低,服务利用远远低于服务供给,其中,上门看病服务过剩比例最高,供给与利用之间的落差比将近30%。[11]养老服务供需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这一矛盾的重要原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链的供给、输送和利用三个阶段都存在信息交流不通畅现象,由于缺乏深入挖掘养老服务需求信息,再加上服务信息传递中的障碍,服务信息不能被服务对象所熟知和理解,服务供需不能有效对接,导致老年人部分需求反映不及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而另有一些服务则利用率低导致资源闲置甚至浪费。
“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以有效解决信息狭窄、封闭和流通不畅的问题,使养老供需相匹配。发展“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挥互联网低成本、及时性、开放性、兼容性的优势,实现养老服务供需信息的及时、无障碍传递与对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服务需求挖掘方面。利用互联网的信息集成和挖掘功能,建立养老服务需求信息资料库,摸底调查老年人的需求,为每位老年人建立档案,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据处理技术深入挖掘老年人服务需求,将老年人的需求信息化,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确定、费用补贴、服务项目确定等提供依据。第二,供求服务信息交互方面。依托手机APP平台和PC客户端,可以为养老服务供求信息提供交互的平台,内联辖区内有实际服务需求的老人,外联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服务商和加盟企业,信息交互平台利用互联网、射频识别技术,将记录、统计及监控到的需求信息集中汇总并分别传输给外联为老服务团队,由其提供上门服务,促使养老服务供需有效对接、资源有效匹配。
2.“互联网+”解决养老服务资源离散化问题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资源在服务主体、服务信息、服务项目等方面呈现出离散化的态势,养老服务资源缺乏有效的协调与统筹。[12]造成我国养老服务资源离散化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养老资源归属不同社区,各个社区之间资源缺乏链接与整合。社区养老资源通常不对外开放,缺乏调配平台,养老资源无法在各个社区之间自由流动,导致资源浪费与利用效率低下。第二,各个养老服务主体之间沟通、互动不足。社区作为养老服务多元合作的平台功能没有很好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家庭等多元主体之间互动不足、缺乏沟通,各主体掌握的软硬件资源尚未实现实时性链接。政府服务资源没有实现普惠化,而市场、社区和民间的资源进入养老服务动力不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不稳定。第三,养老服务项目采取分级分类的管理模式,难以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合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要涵盖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家政服务、精神慰藉等项目,不同行政管理部门主管不同服务项目,例如,民政部门负责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养老机构、社会工作等;卫生部门负责医疗服务、保健、康复等;工商部门负责家政服务。这种条块分割型的管理体制,难以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合作。
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可以实现养老服务资源的有效链接与整合。互联网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各领域深度融合,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实现养老资源在各个社区之间的无缝链接。利用互联网工具和平台成立社区老年照顾协会或互助养老服务组织,开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论坛,充分挖掘社区内部养老服务资源,发展互助养老服务。通过养老资源调配平台,可以促进养老服务资源在各个社区之间自由流动。第二,实现养老服务各项目间的整合。将社区养老服务所需的照看护理、家政服务、医疗保健、社会工作、精神慰藉等资源整合起来,形成社区养老服务集成系统,合力助飞信息化养老。第三,推动养老服务主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型。利用互联网平台链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志愿者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定期不定期发布为老服务、优惠政策、志愿者征集等信息,便于多种社会资源进入社区为老服务。
3.“互联网+”解决养老服务管理部门碎片化问题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部门的碎片化,难以形成统一协调机制。管理层面上,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行政分割、管理分治现象较为严重,决策和执行网络涉及老龄、民政、财政、卫生、社保等职能部门,养老服务部门化、部门服务单体化,导致社区养老服务部门条块分割严重,各部门间尚未形成共同决策和信息资源共享机制。[13]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化网络建设滞后,影响了网络协同治理的形成。政府购买服务的顺利推行不仅取决于资金是否到位、相关政策法规是否完善,而且还有赖于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持。但是政府在推进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购买方和服务提供方信息不对称影响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另外,在政府养老服务外包的过程中,购买信息发布、购买政策咨询、服务量的核算、服务质量反馈、服务评估、社会监管等对完善政府购买服务至关重要,但目前我国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化网络建设滞后,影响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
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不仅需要变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同时需要发挥多网融合等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实现政府对养老服务管理的信息化、集成化。政府将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运用到日常养老服务的管理中,来提升服务管理的深度和管理水平,已经成为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出资建设平等共享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确定养老服务业务规范及流程,实现养老服务信息采集、信息沟通、回应、反馈等全程闭环式管理流程,有效将自上而下的行政资源与自下而上的社区民间资源对接起来,不仅降低了管理过程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而且切实促进社区养老服务的网络化治理,使政府购买社会居家养老服务更加公平和有效。第二,政府政策与管理工具也可依托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达到其预期目的,如合同外包、服务券、税收优惠、补贴等。第三,政府通过信息化技术能够对养老服务实施全程监控,信息平台产生的相关数据,可以为养老服务统计管理与效能考评提供重要依据,从而成为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
三、“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面临的障碍
“互联网+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四大参与主体,即主导者(政府)、大平台(养老服务信息系统)、服务商(服务承接者)和专业化环节(信息技术)。[14]目前我国要实现“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参与主体主要面临如下四方面障碍。
1.政府层面:顶层设计、政策扶持和部门协作不足
目前由于我国政府在智能化养老过程中职能的偏差,影响了互联网与养老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缺乏统一规划。虽然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和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都提出,“加强养老信息化建设,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和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率和管理水平”,但两者都属于政策引导性文件,对智能养老服务未来发展缺乏细化,缺乏统筹规划和具体引导扶持政策,“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更多地依赖地方政府试点,短期内很难实现深度融合。
第二,缺乏行业标准和有效监管。目前我国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化的标准建设方面滞后,在政策层面,全国还没有形成“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行动的相应管理规范和服务标准,政府自上而下尚未对智能养老服务的行业准入与退出、智能社区居家养老系统、智能养老机构的鉴定及等级划分、智能化养老产品标准、养老服务的质量与评估等作明确规范。由于缺乏相关标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且难以监督,政府也没有担当好监督评估的裁判者角色。
第三,优待办法和扶持政策难以落实。虽然国务院在2013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2015年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都提出,“地方政府要支持养老机构和企业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促进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但出于部分优惠政策缺乏可操作性,财政投入不足,一些优惠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分属不同职能部门等原因,导致部分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难以落实。[15]
第四,部门协作不足。目前智能养老行政分割、管理分治的局面,影响了“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行动顺利地推进。目前我国老龄事业缺乏统一的、常设性组织领导机构,决策权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需要老龄、民政、卫生、人保、科技等部门的相互配合。负责全国老龄工作的老龄委权威性不够,不足以调动其他社会资源,也难以履行综合协调职能。
2.市场层面:市场化程度低、高度依赖政府支持
目前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水平较低。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政府也试图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经营、公私合作PPP等模式缓解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但效果并不明显。以社会养老服务较发达的上海、江苏为例,多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主要用户仍然是政府“兜底”的购买服务对象,中高收入老年人比例偏低,且增长速度缓慢。[16]市场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积极性不高,民办养老机构普遍面临营利困境。优质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受益覆盖面过窄,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目前少数发达地区虽然在市级或区级已经建立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但受益覆盖面过窄。以南京鼓楼区“智慧养老”项目为例,只是在两个试点小区和社会福利院推开,受益老年人仅300位。[17]目前我国养老服务市场化程度低,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市场组织缺乏深入调研,提供的服务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存在偏差。由于没有准确把握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多数企业将自身定位于高端养老服务项目,脱离了老年人实际购买力,形成市场错位,而不能获得利润。[18]
第二,加盟的企业、单位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服务对象缺少互动,彼此间没有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以苏州沧浪区虚拟养老院为例,企业、单位对加盟虚拟养老院积极性不高,除了利润较少外,加盟虚拟养老院的企业、单位与服务对象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和互动,导致彼此之间缺乏相互信任。[9]
第三,服务商个性化服务缺乏,营销手段不足。作为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承接者的服务商,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内容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餐饮、保洁、打扫卫生等家政服务方面,对专业化较高的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提供不足,不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起步较晚,但技术更新快,承接服务的企业缺乏有力的营销手段,限制了养老服务市场的扩展。
3.平台层面:信息平台狭窄、封闭和功能单一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狭窄、封闭。从服务信息来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采取以部门为中心的政务信息化发展模式,老龄、民政、卫生、社保、残联等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彼此孤立运行或有限开放,形成了许多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同时,我国大多数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化管理平台只搭建到区级,没有将信息化平台延伸到老年人所在的社区,难以实现管理重心的下移。从事智能养老的各类不同企业各自研发的信息平台和服务终端互不兼容,也没有与各政府部门的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对接,各个系统独立建设、条块分割。由于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使得各部门长期积累的海量数据与信息不能彼此共享,各部门横向沟通协作比较困难。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功能单一,难以实现管理模式信息化,即利用互联网完成养老服务需求信息收集、制订服务计划、组织服务过程、进行服务监督评估等工作。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功能的缺失,致使一系列问题的发生,主要表现在:供需信息搜集反馈机制不完善,养老服务接单与派单只能依靠语音呼叫系统,养老机构和服务人员服务量的核算只能通过手工完成,对养老服务质量监督和评估主要依赖传统四级网络(市区街居),服务对象对服务质量反馈途径有限,主要向养老服务中心或居委会反馈。[19]
4.技术层面:信息传递方式滞后、智能化水平低
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信息传递主要依靠两种渠道:一是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为中介,当老年人有养老服务需求时,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登记,对符合条件的老人,由服务中心选派服务人员上门为其提供服务;二是设置“一键通”呼叫中心,依托通信网络连接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为有需求的老人家中安装“一键通”服务器,呼叫中心通过语音程控交换系统(电话)接受服务请求,目前各地广为推崇的虚拟养老院大多采用此方式。第一种信息传递方式具有滞后性,仍然属于传统中介式信息传递方式,没有采用现代化信息传输手段,养老服务供求与需求信息主要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进行交换,养老服务供需对接主要依赖于服务中心所掌握的服务资源和信息,如果服务中心所掌握的需求信息不足或手头没有合适的服务人员,便导致供需不能有效对接。第二种方式虽然采用了“一键呼叫”信息化的手段,但缺乏互动性,没有可视化界面,服务需求者无法直观地选择服务内容和服务人员。大多数养老服务中心网站只具有信息查询功能,很少嵌入在线咨询服务,即便少数网站具备咨询功能,也并非实时咨询,大多处于离线模式。同时,现存的可提供养老服务的网站存在信息系统彼此孤立运行、信息重复多、信息不完整、实效性差等诸多弊端。
四、促进“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的策略
1.加强政府顶层设计、推进部门协作、建立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
政府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规划者、政策制定者、推动者、扶持者、协调者和监管者的重要角色。[20]在“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过程中,政府在养老服务信息化政策网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制定并落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化规划。在认真总结“十二五”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同时,精心制定并落实“十三五”规划,从政策层面上完善相关立法,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出台自上而下的指导意见和宣传措施,进一步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第二,建立统一部署、各部门间协同与合作的组织管理体制。组建统一的、常设性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组织领导机构,由各级民政和老龄委牵头,人保、卫生、科技、文化等部门参加,统一部署、总体决策“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行动计划,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由民政和老龄委负责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并在其协调下,实现信息在各部门间互联互通。第三,建立统一的养老服务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养老服务信息化标准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也是“十三五”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总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五”期间,我国应加快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化领域的标准制定,研究和制定符合实际要求的养老服务信息化标准,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化国家标准规范体系,以规范和统一信息平台中养老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养老机构等级鉴定、养老服务产品标准、服务绩效评价指标等内容。建立统一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和智能养老行业标准,实现跨系统技术集成与信息共享,尽量减少“信息孤岛”,为政府不同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主体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搭建资源共享、信息交换的平台,促进各主体相互间的互助与合作,并为行业内部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以及市场扩展打下基础。
2.引导、支持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和服务递送
根据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多中心参与供给公共服务,通过引入多元竞争的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水平。[21]以政府为主导的“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同样需要社会组织、市场力量积极参与,才能缓解养老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参与“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行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采取政府购买和项目合作加盟的形式,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在政策上支持各类网络技术企业、单位自主研发系统管理软件、终端应用软件和智能老龄服务设备用品。以厦门市为例,政府通过指定采购方式采用了由市民养老服务中心自主研发的移动终端应用设备,该设备是一款子女远程健康管理类APP,通过该设备子女可以清楚了解父母健康状况,厦门市政府采购后,将其应用于本区域的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工作中,扩大了该设备的应用范围,吸引了更多民营资本的参与。
第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生产和递送。政府通过公办民营、直接资助、购买服务等方式,积极鼓励和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承接各类服务项目,使政府与市场和民间组织之间形成互动合作、协同增效的伙伴关系。通过竞争性独立购买服务为各类组织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政府也可采取通过发放代金券或补贴直接向老年人购买服务,然后由服务对象在市场上自由购买相关服务。
第三,制定优待办法和扶持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投入到“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来。黑龙江为了推进“互联网+老年产品开发”,在融资、税收、土地等方面给予投身智能养老服务业的市场和社会组织提供优惠政策,计划利用3~5年时间,投资100亿元建成老年系列用品产业园区,专门生产老年生活用品和老年辅具用品。同时,支持“互联网+消费养老”,支持开发养老保险产品和老年专用系列绿色食品。
3.搭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是“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综合信息平台应包括三大子系统:基础数据库系统、服务子系统和操作子系统。[3]建立并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政务数据库系统。该系统由政府统一规划,以大数据为核心,整合民政、卫生、残联、社保等涉及决策和执行的各职能部门基础数据库,该系统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服务项目的确定,服务对象及家属服务种类的选择,服务券发放和补贴对象的确定,养老服务机构上门服务提供,服务效果评估等提供基础数据。该数据库主要涵盖老年人基本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服务需求信息和健康档案四个方面内容,数据录入工作由上述主管部门根据职能分工进行信息录入和补录。
第二,建设社区养老服务和卫生服务集成子系统。黑龙江为了推进居家医养结合,计划建设全省统一的社区居家老年人电子健康档案,实现社区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和三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信息对接,形成社区医养服务集成系统,为老年人提供疾病预防、远程医疗、康复等医疗服务,通过医养信息互联互通助飞信息化养老。
第三,搭建统一的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上述三系统之间的融合。2016年1月,广东省民政厅与广东电信公司签署了《广东省居家养老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合作框架协议》,民政厅利用中国电信的核心业务优势与服务资源,委托其构筑了全省统一开放的居家养老信息化服务平台和O2O养老服务体系,该平台的建设覆盖广东省21个地级市,届时将有效整合各方养老服务资源,利用该平台可以汇集养老服务大数据,掌握市场需求动态,实时发布全省各类养老服务供需信息,可以有效推进“互联网+养老服务”,实现增量增效的目标。
第四,建设服务终端或监测系统。建立一个有传感系统的服务平台,通过智能可穿戴设备搜集老年人相关服务需求信息,监管失能老人,提供事件预警及服务应急响应。
4.推动养老服务信息技术研发
技术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七大基本要素之一,分层养老服务的实现需要以养老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作为保障和支撑。[22]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科技含量决定了其发展的效率和质量,科技创新是“互联网+社会居家养老服务”行动的关键支撑,可以为互联网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提供可实际操作、完整有效的解决方案。要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和动力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格局,需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的养老服务信息化技术创新体制。鼓励更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投入养老服务信息化系统、智能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等软硬件的技术研发,形成从研发到市场推广一体化的产学研产业链,开发通俗易懂、操作方便、可视化、易于老年人接受的信息系统和产品。
第二,健全政策保障机制。支持企业从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信息系统和智能产品的研发,鼓励企业着力突破我国养老服务信息化系统和智能养老设备发展薄弱环节的关键技术,并重视对技术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成果试点应用推广等的指导、组织和实施工作,引导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参与方给予资金支持,并逐步扩大购买服务和承接商的范围,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金融杠杆作用支持推动产学研用。通过定价机制、招投标制度、购买服务流程、评估机制等,扶持参与“互联网+社会居家养老服务”行动研发的重点企业。
第三,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整合、改造和新建社区内部无线网络、宽带网络、广电网络、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实现老年人生活和活动区域网络畅通,以便于支撑“互联网+社会居家养老服务”行动的高效运行。
[1] 张泉,邢占军. “互联网+养老”概念辨析[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6(1): 12-16.
[2] 童星.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应对老龄化[J].探索与争鸣, 2015(8): 69-72.
[3] 潘峰, 宋峰.互联网+社区养老: 智能养老新思维[J].学习与实践, 2015(9): 99-105.
[4] 熊文静, 张永泽.基于信息技术的社会服务模式探讨——电子养老[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5(4): 40-44
[5] 睢党臣, 彭庆超. “互联网+居家养老”: 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5): 128-135.
[6] 同春芬, 汪连杰. “互联网+”时代居家养老服务的转型难点及优化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 2016(2): 160-166.
[7] 郝涛, 徐宏.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老年残疾人养老服务社会支持体系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2016(4): 158-164.
[8] 陈莉, 卢芹, 乔菁菁.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人口学刊, 2016(3): 67-73.
[9] 张国平.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的新模式——以苏州沧浪区“虚拟养老院”为例[J].宁夏社会科学, 2011(3): 56-62.
[10] 刘红芹, 包国宪.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管理机制研究——以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为例[J].理论与改革, 2012(1): 67-70.
[11] 王莉莉.基于“服务链”理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供给与利用研究[J].人口学刊, 2013(2): 49-59.
[12] 贾海彦, 张红凤.基于产权约束的基层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6(1): 16-22.
[13] 翁列恩, 王振, 楼佳宁. 集成化、信息化与标准化的居家服务创新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 2013, 10(3): 1-11.
[14] 孙文灿. “互联网+养老”空间无限[N].中国社会报, 2015-05-14(4).
[15] 张孝廷, 张旭升.居家养老服务的结构困境及破解之道[J]. 浙江社会科学, 2012(8): 81-86.
[16] 朱勇.中国智能养老产业发展报告(2015)[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7] 张丽雅, 宋晓阳.信息技术在养老服务业中的应用与对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5(5): 170-174.
[18] 张乃仁.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中州学刊, 2015(10): 74-78.
[19] 马贵侠, 叶士华.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地方性实践成效、挑战与展望[J].山东社会科学, 2015(7): 125-130.
[20] 高祖林.政策网络视域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苏州市虚拟养老院为例[J].江海学刊, 2013(3): 201-207.
[21] 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 35-37.
[22] 席恒.分层分类: 提高养老服务目标瞄准率[J].学海, 2015(1): 80-87.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Plus” in the Community Home-based Endowment Services
LI Chang-yu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70, China)
“Internet plus” thinking can create a new format for the smart pension industry in the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home-based endowment service. The realization of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home-based endowment service” faces the barriers from the government, platforms, service providers and technologies. The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s to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government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departments; to guide, support multi-subject coope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nsion service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delivery;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and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ension servi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home;endowment service
2016- 05 - 17
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15B-077);甘肃政法学院青年科研资助项目(GZFXQNLW008)
李长远(1982—),男,河南南阳人,甘肃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
D669.6
A
1008-7729(2016)05- 0067-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