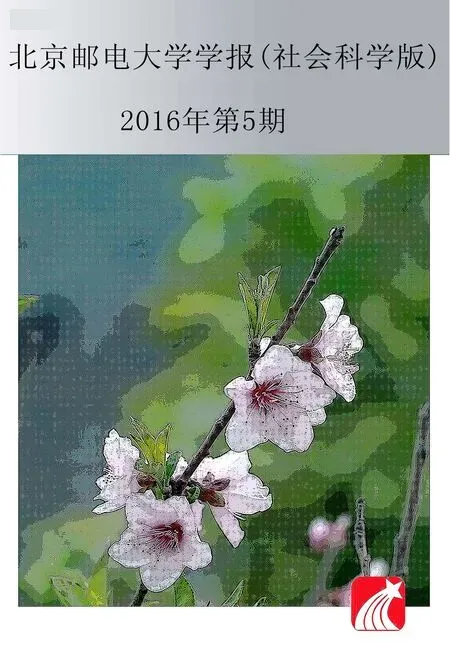网络名誉权与网络言论自由的冲突与制衡
——再论“微博第一案”
2016-12-18李伟平
李伟平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网络名誉权与网络言论自由的冲突与制衡
——再论“微博第一案”
李伟平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互联网社会中利益多元化的群体对于名誉权和言论自由的理解和需求是不同的。网络中发表的言论时常伴随着对他人名誉权的侵犯,网络言论包括在互联网中陈述事实与发表观点。为减少网络言论对他人名誉权可能造成的侵害,网络言论自由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司法实践在规制此种冲突时,应该遵循利益平衡的原则,在民法没有对言论自由做出规定的当下,应按照宪法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平衡网络言论自由和网络名誉权的关系。在具体个案认定时,应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给予网络言论不同的自由程度;此外,对于网络名誉侵权主体和网络名誉被侵权人,应根据两种主体的身份特征、身份属性对自然人和法人、公众人物与普通大众、专业者和非专业者区别对待。
网络名誉权;网络言论自由;冲突与制衡;微博第一案
一、问题的提出
1.基本案情
2010年5月25日—27日,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在新浪等微博网站上,每天密集地发布数十篇博文,以其特有的调侃方式和犀利的言辞,公开曝光奇虎360和金山公司之间的恩怨和杀毒软件行业的一些黑幕。随后,金山公司也在四大门户网站注册了微博,针对周鸿祎言论作出回应。由于双方在IT界的知名地位以及微博网站推荐,这一事件一度引发了数十万网友的关注,其影响力巨大,被网友称为“微博第一案”。[1]
在该案中,金山公司诉称,被告周鸿祎使用了大量的侮辱性、贬损性语言,通过微博恶意、大量、密集发表针对金山公司的文章,这些文章虚构事实、恶意诽谤,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造成金山股价大跌。针对金山公司的指控,被告周鸿祎及其律师认为被告发表的微博是在履行公民舆论监督的职责,是言论自由的体现,且被告的微博言论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不存在侵犯原告名誉权的情况。金山公司的股市大跌,主要原因是其自身业绩的下滑,而不是周鸿祎的微博言论。
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定周鸿祎利用微博进行网络营销,针对原告金山公司发表了不正当、不合理的言论,其目的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造成了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已构成名誉侵权,被告周鸿祎应承担删除侵权微博、公开致歉、赔偿损失等责任。但对于金山公司诉请的1 200万元股价下跌带来的经济损失,法院认为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由周鸿祎侵犯名誉权的行为造成的,故不予支持。
2.提出问题
互联网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和普及,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它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和行为能力,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自由地发布和传播信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6年1月最新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中国居民上网人数已过半。较2014年底提升6.1个百分点。用户逐渐移动化,网民的上网设备正在向手机端集中,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手机成为拉动网民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截至2015年12月底,如QQ空间、微博等各类信息汇聚的综合社交类应用,继续扮演着社交平台的作用,其中QQ空间、微博,网民使用率分别为65.1%、33.5%。[2]互联网的极速发展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道德与法律层面的问题。通过在网上发布的言论侵犯他人名誉权的事件常诸报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不但给人们提供了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广阔平台,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言论自由侵害他人名誉提供了便利。
言论自由权,作为宪法赋予的权利,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重要前提,它对开启民智、帮助人们追求真理、行使社会监督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用户通过网络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会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地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权的保护与言论自由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天生的冲突根源,网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两者的冲突。比如在此案中,金山公司认为周鸿祎借助微博这个网络平台侵犯了金山公司的名誉权,而周鸿祎则声称其在网上只不过是行使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当。法律应该优先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认定这种言论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名誉权?网络言论自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边界,那么如何确定这个边界?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在两种权利所代表的价值之间寻求最广泛的平衡?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大量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可知:网络言论自由与网络上名誉权的保护,由于发生在网络这个媒介之上,网络(尤其是微博)有着不同于普通的口头侵权或通过其他媒介侵权的地方,要回答上述提出的这些问题,必须结合网络侵害名誉权行为的内在特殊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益的衡量,以期能够解决网络层面上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行使直接冲突与制衡的问题。
二、网络名誉权与网络言论自由的理论基础
1.网络名誉权
作为民事主体人格权的一种,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获得客观公正评价、免受侮辱、诽谤等加害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的一种民事权利。它以名誉利益为客体,由特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具有法定性、专属性、非财产性、受限制性等特征。这里的受限制性是指当名誉权与其他权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可能会对其做出一定的限制。学理上认为能够限制公民名誉权的权益,一方面来自于公权力,即当名誉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其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方面当名誉权与个人私权发生冲突时,根据利益衡量,名誉权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网络名誉权,为非现行法中的法学概念。作为网络时代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人们对于这一新事物的认可。网络名誉权是指人们在网络环境下依法享有的保有和维护名誉的权利。网络名誉权与传统的名誉权相比并无本质差别,均包含名誉的享有和维护以及排斥他人侵害的权能。唯一有区别的地方是网络名誉权的侵权媒介是网络,由于人们保有和维护名誉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名誉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在网络环境下又呈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网络名誉权的本质并没有因为网络这一载体而不同,它具有与一般名誉权同样的法定性、专属性、非财产性、受限制性等特征,发生媒介的网络性是两者主要的不同之处。网络承载着名誉权人的权利,网络名誉权发生于网络这个大环境之下,并不得在此环境中受到侵害。
2.网络言论自由
(1)网络言论自由的概念与价值
言论自由被誉为宪法上“第一权利”,已经得到国际人权文件和世界各国的肯认,世界各国大都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将其纳入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范畴。“言论自由是公众讲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包括对政治社会问题的思考公之于众,交流表达不受非法干涉的自由。言论自由的精神实质是对真理的追求,以达到社会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的准确评价。”[3]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传统上言论自由主要通过口头、书面的方式行使,亦可通过电视、广播进行传播。在当今时代,互联网已成为了人们交流、获取信息最重要的平台,现在所说的言论自由当然还应包括网络言论自由。尤其是博客、微博、微信的出现使得网络言论越来越多,民众对网络言论自由的呼声亦随之升高。网络言论自由是人们以网络作为载体,在网络上享有高度的、符合现代社会正义的言论自由。只要有电脑并且连接了互联网,或者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就可以在网上发表个人言论。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言论自由日渐成为言论自由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网络言论自由被认为是旨在追求真理、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维护和发展民主政治、实现多元意见等多重功能。当下网络言论自由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其中微博问政、微博反贪、微博维权都常见诸于网络和报刊,网络在民主政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唐慧案、薄熙来案等案件的微博全程文字直播,更是拓宽了人们通过微博等各种网络渠道对该案发表看法的途径,形成了一次次“全民的大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让民众看到了我党致力于建设一个开明的、言论自由的政府的决心。因此,网络言论自由在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言论自由的价值需要弘扬,但如何正确行使网络言论自由权则更需要制约,以免成为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的工具。
(2)网络言论自由的相对性
①言论自由需受一定之限制
尽管宪法赋予了人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也不是绝对不受限制的。当世没有一种权利是绝对的,包括言论自由权。与其他权利冲突的言论自由,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表达自由必须得到保证,只有为了保护合法的权益(包括名誉权)是必要时,才可以对表达自由作限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就规定了“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来对同条第2款的言论自由权进行约束和限制,并要求缔约国的国内法制定相应的约束条款。
在网络中,言论的内容也可能会涉及到他人的名誉。这就需要对言论自由做出相应的限制。在网络环境下,由于网络的随意性和虚拟性的特点,使得很多网络名誉侵权并不是行为人的“有意而为”。他们更多地是为了分享自己的感性认识而不是刻意去“冒犯”他人,很多人因此无意地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因此网络中言论自由与非网络情况下的言论自由是不同的,需要将这些有侵权嫌疑的言论放在网络的大环境下考虑。在“微博第一案”中,法院也认为“个人微博的特点是分享自我的感性认识而非追求理性公正的官方媒体,微博上的言论随意性更强,主观色彩更加浓厚,相应对其言论自由的把握也应更宽。但微博作为公民现实社会的投影和延伸,微博中的言论自由并非没有限制,其行使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4]。
②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
网络用户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按照言论属性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对这两种言论应该给予不同程度的自由。“事实陈述”更多涉及的是以诽谤为方式的名誉侵权,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第8条将事实陈述区分为“基本真实”“基本属实”“基本内容失实”三个层次。对于事实陈述,加害人需证明其陈述的事实为真实,并与公共利益有关[5]。也就是说,对于“事实陈述”,对其言论自由应该课以更高的要求,言论作出人不但应证明陈述属实,还应证明本人的真实陈述无侵权之故意。因为“真实”不一定不构成诽谤。如在一则真实的案例中,原告到被告医院就医,因疑似“艾滋病毒感染者”而无法确诊并另寻机构检验过程中,被告向原告单位领导通报了病情并且原告单位领导在职工大会上通报原告病情致使原告的病情得到扩散。可以认为,在未确诊之前,被告应对原告负保密义务,不得无故泄露原告病情,虽被告透露的病情属实,但其行为具有了侵权的违法性,应构成名誉侵权。
此外,对于事实的证明不必遵循完全的客观真实,其基本重要事项相符时,即可阻却违法。如指称某官员贪污500万,而实际贪污50万;某饮料厂卫生不符合标准,则不必追求报道中关于苍蝇、垃圾的数量的确切性[6],因为这属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基本事实属实并不因此受影响。
关于“意见表达”,须达到“系以善意发表言论,对于可受公评之事,而为适当之评论”[5]的要求。“意见表达”对应的是以侮辱这种侵权方法。因此认为,对于“意见表达”这种价值判断应给予比“事实陈述”更大的自由度,只要其满足“善意”并且“合理适当评论”就可阻却违法,并且对“是否恰当”应作较为宽松的认定,其措辞得为尖锐,带有情绪或感情,对错与否,能否为多数人所认同,在所不问,惟不能作人身攻击。[7]
三、网络名誉侵权的认定
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专门对网络名誉侵权做出规定,学界对于网络名侵权的内涵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司法实践中处理网络名誉侵权问题,主要还是参照传统名誉侵权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就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因此可以认为,在构成要件方面,网络名誉侵权作为一般侵权的延伸,在认定网络名誉侵权的要件上与一般侵权并无不同,也就是需要具备有侵害名誉权的违法行为、有损害、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人主观上的过错。但是因为网络名誉侵权是发生在网络环境下,这就使得其与一般名誉侵权有着一些不同的特点。
首先,网络名誉侵权的侵权主体具有复杂性。网络名誉侵权包括网络用户、评论者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不同情况有不同侵权主体范围。此外“为了促使网络用户自由发言,当事人可以匿名发表言论对他人的网络内容进行评论甚至可以以假身份出现在网络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充满假象的虚拟世界。”“在这样一个假象世界中本来不管发言内容如何都不存在形成名誉毁损的问题。”[8]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受害人可以是具体的。事实上,网络上特定的人遭受名誉侵权的情况很多,而侵权主体却大多是匿名的。
其次,网络名誉侵权的损害程度不确定。由于网络侵权内容传播范围难以确定,并且访问或者接触载有侵权信息的网络的人数也难以确定,故而网络名誉侵权的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有些网络网站上可以统计访问人数,但是并非每一个访问其网络的人都浏览了侵权信息。
再次,网络名誉侵权难以证明。网络的不断更新,发布的网络侵权信息可以在任何时间更新和被其他信息替换,这就必然给网络名誉侵权的受害人收集证据证明加害行为带来困难。同时由于网页是可以仿制的,即使受害人出示载有侵权信息的网页备份等证据,也难以证明网络内容就是被告所写。[9]
最后,网络名誉侵权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程度。网络名誉侵权的载体是互联网,而几乎所有的网络都提供了手机绑定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发布信息。因此信息发布的便捷性决定了网络名誉侵权造成的影响传播非常迅速;网络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使得网络用户可以自由地浏览载有侵权内容的信息;其他网络用户也可以便捷地为带有侵权内容的信息设置链接。网络强大的互动性使得他人不仅可以阅读侵权信息,而且可以随意进行更改。这就使得其侵权程度比普通的名誉侵权更深更广。
四、网络名誉权与网络言论自由的冲突
在网络这一媒介上,当事人的名誉权有被侵害的风险因而需要进行保护,而作为言论自由权行使越来越广泛的主要阵地,网络社区中常发生通过言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情况发生,因而难免发生两者在法律适用与保护上的冲突。可以看出,两者发生冲突不仅是在现实价值层面上的冲突,即对其中之一的保护与倡导必然会侵蚀另一者的合理行使与存在。两者冲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应是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社会层面其他配套社会制度的缺失造成。
1.法律层面
就法律层面来看,虽然两种权利都是宪法所明定的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法律规定所彰显的对两者的保护程度是不均衡的,这难免造成实务中无法处理好两者冲突的情况。关于名誉权的保护,不但《宪法》、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有所提及,尚且还有专门保护名誉权的司法解释。
而制定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相对前者就很单薄了,除了在宪法中简单提到要保护外,民事法律与法规中基本无此权利的法律规定,如是造成司法实务中对于关涉言论自由的案件中找不到裁判依据。而在宪法不能作为裁判依据的我国,宪法条款作为转致条款间接适用的学说也尚且未在我国实务界得到认可和贯彻,加上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也少有像英美法制国家那样在具体案件中阐释言论自由保护的重要性,来对两种权利的利益衡平进行论证与阐释,较为常见的做法,即是简单地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名誉权保护的规定,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以及与名誉权冲突的平衡做得不够。言论自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因而网络言论自由传播得到限制,言论自由的边界过窄与公民的现实需求不符,与名誉权发生冲突则在所难免。
2.社会层面
除了法律方面规定的缺失,另一个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即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处于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凸显,加上国家对于人们向上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的相应制度并不完善,人们迫切需要表达意见以及诉求的愿望亟待得到满足,网络这一媒介的出现成为了人们宣泄不满、表达意见、诉求表达的重要“阵地”。而由于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层和多元化,人们对于名誉权和言论自由的理解和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对网络名誉权和言论自由的保护也不应一概而论。不同群体对于言论自由的界限需求以及名誉权的保护程度是有差异的,对于已经拥有足够话语权的公众人物来说,其看重的更多的是名誉的维护以及其他相关的衍生利益的保护;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更希望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权限,对社会中的人和事可以自由地揭示和评论。
虽然我国现在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法治国家,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观念不可能绝对地并肩前行,与比较成熟的法治国家相比,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是显得淡薄一些。的确,有些网络侵权者非为名利,只是娱乐,以彰显自己的人气和能力,把网络当成一个绝对言论自由的平台,法律在他们眼里少了神秘感与威严性。方寒事件中,方粉和韩粉各自的诋毁也许起初并无恶意,这种观望转发随意评论,已经给当事人带来了精神影响。显然法律意识淡薄,自由言论的同时忘记甚至不知社会公德及法律规定。
既然冲突在所难免,那么如何有效地平衡这种冲突呢?有学者认为言论自由应置于高于名誉权的地位,来解决两者的冲突问题。如苏力教授在《〈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指出,言论自由促进了近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而且是我国改革和追求更为开放的社会所必需追求的方向。故言论自由相对于其他权利,应当处于一个相对更高的位置。[10]对于此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名誉权与言论自由两者同为宪法所明定的基本权利,对此二者不应有位阶先后之分,较为妥适的方法,莫不如在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导下,在个案中追求法益的平衡,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制衡。
五、网络名誉权与网络言论自由的制衡规则
1.制衡的原则
处理网络名誉权与网络言论自由可能发生的冲突时,应当遵守利益平衡的原则,一切制衡的规则都要以此为基础展开。具体而言,即是要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衡量,权衡出何者需要更大的保障。公民在网络环境下实现言论自由,如果其中涉及的公共因素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例如言论所针对的是政党、政府机关等具有公共属性的主体,或者事件本身与多数人利益相关联,则表明该纠纷属于公共领域的事件,与公共利益关系紧密,应当更倾向于保护网络的言论自由,保障社会舆论监督权利的行使,使不同意见可以自由地表达,而对名誉权应当进行适当地限制,权利人只有在受到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可以起诉,并且要对对方存在“实际的恶意”进行证明。如果其中涉及的公共因素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与公利害无关的私人事务,则更应倾向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名誉权,权利人只需要证明侵权行为符合名誉侵权的一般构成要件即可。
2.制衡规则的具体展开
(1)区分网络言论中的“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
前文已经提到过,网络用户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按照言论属性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对这两种网络言论应该课予不同的自由程度。有学者认为只有事实陈述才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而发表意见的评论则不会侵害名誉权。[11]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论“事实陈述”还是“意见表达”在满足了一定侵权条件时,都可能会构成名誉权的侵权,只是苛责的程度不同罢了。
关于网络言论中的“事实陈述”,由于大多数的网络言论发布者和评论者毕竟不是专业的信息传播机构,让他们自己对所描述的事件的言论绝对真实难免过于苛责,因此只需要保证基本真实即可免责,即“真实并不意味者每一个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而只是要求与本案有关的关键性言辞是否真实”[12]。然而该免责事由的适用是有限度的,网络言论内容基本属实也可能构成名誉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40 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也就是说,我国把对隐私的保护放在了名誉权中进行。即使网络言论所反映事实内容基本属实,但是如果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开了他人的隐私,同样构成名誉侵权。在“王菲与‘北飞的候鸟’网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中即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被告在博客中发表的博文中尽管透露的王菲有婚外情、婚姻不忠的行为属实,法院亦认定了被告侵犯原告的名誉权。
而意见表达关切到民众追求真理、人格的体现,达到“越辩越明”的目的,因此应给与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意见表达的内容不涉及个人隐私或进行人身攻击,所评论的是针对他人观点或言行,内容合理且适当,符合一般人的逻辑思维,即使措辞稍有尖锐,通常不应该被认为侵犯名誉权。
关于“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的认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依照一定的标准,并不可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的发挥。王泽鉴先生对此提出了“可证明性”和“受领人的理解”两个标准[5]。应该看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又不同于面对面交流、在其他媒介上的交流,尤其是微博的急速发展,带来的是对“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不同于以往的区分规则。有些网络媒介,比如人人网、微博、QQ空间等都有转发功能,网络用户可以转发他人的言论,甚至可以在转发时发表一些自己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往往难以界定“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对于这类情况应该这样看待:如果转发的人仅仅直接转发或者引用,并且没有进行编辑和修改,所评论的是针对他人的观点和言论,则应认定为“意见表达”,他的这种行为内涵的是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如果转发者在转发时对信息进行了大量的编辑修改,加入了自己一些不实的言辞,则应当成“事实陈述”对待,认定名誉侵权时应该较之于“意见表达”更为严格。
(2)区别对待自然人和法人网络名誉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一并规定了自然人和法人的名誉权,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将法人和自然人的名誉权作一体保护。但是,自然人的名誉权应与法人名誉权有很大的差异,对其名誉权的保护也不应完全等同视之。这是因为,人格权作为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的统一,是在自然人人格权方面的集中反映,而法人因其拟制人的法律属性,其人格权更多地仅反映其财产利益。作为名誉权客体的两方面——外在名誉、内在名誉,仅能为自然人所同时享有。而作为精神利益存在的内在名誉(即名誉感),是指权利主体对自己内在价值所具有的感情和自我评价。这种具有主观性的名誉感只能为自然人所享有,并在侵害时可产生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自然人与法人的名誉权权利内涵是不同的,这是对两者区别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与自然人相比,法人更多地具有公共的属性,特别是公司法人这类营利性法人,其在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常与公共利益有重大关联,因此法人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况更多于自然人。故为公共利益保护之考量,对于法人的名誉权的保护程度与条件应低于自然人,相应地针对法人的言论自由应给予更宽泛的保护,只要他人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法人较之自然人应对他人的问题反映与质疑负有更大的容忍义务,对于他人质疑或批评的言论的言辞的激烈程度亦应多加忍受,以期通过言论自由的行使保障社会舆论监督。可以这样说,如果网络言论针对的对象是自然人的,应侧重对其名誉权的维护;若针对的是法人,则应以言论自由表达的保护为先。
(3)区别对待公众人物与普通大众
对于网络名誉权与网络言论自由冲突的制衡,也要区别言论所针对的对象是否是公众人物来分别视之。所谓公众人物,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知名度,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这一比较法上的概念自2002年的“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名誉侵权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2)静民一初字第1776号民事判决书。中被提出以来在我国司法实务界得到认可。它分为完全性公众人物和有限性公众人物,前者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公众所关注,具有能够影响公众的地位和能力的知名人士,主要包括政府公职人员、演艺明星、知名企业家等;有限性公众人物是指因偶然事件为公众所关注的普通人,如罪犯、卷入新闻事件中普通人等。公众人物因其身份或行为而与公共利益较为关切,诸如体育明星、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人们对于其品行具有较高的期待,且他们享有了因为公众人物的身份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对于媒体等公众在行使正当的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对其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公众人物应当予以容忍和理解。即一般情况下,应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进行限制,法律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力度要弱于普通民众,但如果仅仅涉及私人利益,则应与一般民众同等保护;在认定对公众人物的名誉侵权时,公众人物除了需证明名誉受到严重损害外,还需证明对方存在“实际的恶意”时,才可认定名誉侵权成立。
在另一个方面,公众人物作为网络名誉侵权人,应该从严认定,公众人物发表网络言论时应该比普通民众拥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这是因为公众人物往往在网络上有大量的粉丝和关注者,如果其做出了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将比一般大众侵犯他人名誉权产生更大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因此公众人物应该对其发表的网络言论较一般民众来说应履行更大程度的确保真实的义务,公众人物与一般大众发表同样的网络言论,对公众人物的网络名誉侵权应该更加严格认定。
(4)区别对待不同网络侵权者的身份
这里是要求区分与网络言论相关的发布者与传播者是否为相关专业人士。平等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但现实社会中为了实现个案的公正,必须要在具体案件裁量中考虑当事人的身份,尤其是弱者的身份。因此网络用户在发表网络言论时其身份的不同也将影响到其是否应该承担网络侵犯名誉权的责任。专业人士在网络上发表的网络言论如果涉及专业领域则应该比非专业人士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对于专业人士在网络上发表的涉及专业领域的网络言论侵犯他人名誉权应该从严认定,比如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包括律师、法官、法学教授等)从自己专业角度针对他人发表的涉嫌侵犯名誉权的网络言论应从严认定责任的成立,在后果的承担上也应该酌情比非专业人士承担较为严重的责任。因为专业人士在自己专业领域内应该合理推断其专业性的言论可能导致的后果,这是法律保护弱者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的应有之义。
六、案例评析
轰动全国的“微博第一案”,集中体现了网络环境下网络名誉侵权与网络言论自由冲突的社会问题,又因诉讼双方网络粉丝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而具有天然的影响力与典型性。对本案的正确裁判及理解有助于引导司法实务界对类似案件的正确处理。
首先,该案判决书中将言论自由的保护进行了肯定,在我国宪法不可诉的大背景下提出对宪法规定的权利进行保护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进步,特别是二审判决书中指出:“个人微博作为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为实现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平台”。明确肯定了公民网上发表言论的宪法权利地位,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按照宪法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进行网络言论自由和名誉权关系的平衡,是一次大胆而又值得肯定的尝试。
其次,判决肯定了网络言论自由的相对性。判决指出“个人微博的特点是分享自我的感性认识而非追求理性公正的官方媒体,微博上的言论随意性更强,主观色彩更加浓厚,相应对其言论自由的把握也应更宽”,肯定了网络这种媒介发布言论随意性、主观性的特点,给了网络言论自由不同于一般言论自由更宽的认定标准,并指出“但微博作为公民现实社会的投影和延伸,微博中的言论自由并非没有限制,其行使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论证了对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的合理性,摆正了网络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价值位阶关系,即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要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而进行衡量。这些前提性的观点都是值得肯定的,为下一步判决根据具体情况分配案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划定了前提和基础,是贯彻个案法益平衡原则的体现。
再次,在对周鸿祎的侵权认定方面,法院考虑了“发言人的身份、所发布言论的具体内容、相关语境、受众的具体情况、言论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具体后果等加以判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09328号民事判决书。,受案法官与时俱进,考虑到网络这种媒介的特殊性,明确指出了在认定名誉侵权方面的几个参考因素。周鸿祎作为奇虎360公司董事长,本身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其在微博上有大量的粉丝和关注者,造成的影响要广于普通名誉侵权,因此其发表网络言论时应该比普通民众要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再加上周鸿祎作为IT行业的专业人士,其发表的针对金山公司的言论应该是在自己的专业内的,应该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认为公众人物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基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理,认定周鸿祎的微博言论对金山公司构成名誉侵权。
但是,应该看到,“微博第一案”的判决也存在不足的地方,例如一审法院以被告周鸿祎是同业竞争的负责人,作为认定其构成名誉侵权的依据之一,是不恰当的。批评监督的权利并不因存在竞争关系而被剥夺,相反,越是竞争对手越了解行业的内幕,越有揭露竞争公司问题的动力,我们不能也不应凭此推断其主观是否恶意,只要其没有捏造事实,没有使用过分侮辱的言词即可免责,从而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尤其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再者,法院判决被告在新浪等网站上,向金山公司公开道歉,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根据上面的分析,应该对法人和自然人的名誉侵权认定进行区分。法人是一种法律拟制人格,不可能承受类似自然人的精神痛苦,不存在对法人进行精神上抚慰的必要。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让被告在新浪等网站上向原告公开道歉,赔礼道歉应该是对自然人名誉侵权的一种救济手段,对被侵害名誉权的法人救济只需要赔偿损失和公开判决书即可。
无论怎样,“微博第一案”的司法实践都是划时代的重大突破,判决书中的很多创造性的观点可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判决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从另一方面讲,司法实践的突破,也将推动相关立法完善,引导良好社会风尚。
[1] 新华网. 庭审实录: 金山诉奇虎董事长周鸿祎案[EB/OL]. (2010-12-06)[2016-03-20]. http: //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12/06/c_12852523.htm.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1-22)[2016-03-20].http: //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_53271.htm.
[3] 肖蔚云.宪法学概念[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63.
[4] 中国广播网.微博第一案周鸿祎落败 微博时代私权保护引热议[EB/OL].(2011-03-28)[2016-04-10].http: //china.cnr.cn/newszh/yaowen/201103/t20110328_507833572_1.html.
[5] 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王利明, 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5: 596.
[7] 张红.事实陈述、意见表达与公益性言论保护——最高法院1993年《名誉权问题解答》第8条之探讨[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0(9): 106-117.
[8] 王浩.微博名誉侵权中的法律责任[J],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2, 24(2): 44-47.
[9] 找法网.网上名誉权侵权纠纷实务探讨[EB/OL].(2010-08-26)[2016-04-10].http: //china.findlaw.cn/info/qinquanzerenfa/tsqqzr/wlqqzr/20100826/130694_8.html.
[10] 苏力.《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J].法学研究, 1996, 18(3): 65-79.
[11] 毛蜀湘.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弱化保护原则及其界限[J].金融时代, 2012(15): 271-272.
[12] Rogers W V. Damages for non-pecuniary los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 New York: Springer, 2001: 840.
Conflicts and Balance of Network Reputation Rights and Free Expression on Internet——Further Discussion on “Micro-blog First Case”
LI Wei-ping
(Civil and Economic Law Institut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The nee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putation rights and the free expression are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n the Internet. The network remarks which include a statement of fact and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violation of others’ reputation righ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eputation infringement, the free expression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judicial practice, when regulating such conflicts, the cour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interests, and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s protecting free expres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reputation rights and free expression on the Internet should be balanced. In specific ca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tement of facts” and “expression of opinion”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different degree of freedom should be given; in add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infringer and the infringed, natural person and legal person, public figure and the general public, professional and non-professional should be differently treated in view of identity.
network reputation rights; free expression on the Internet; conflict and balance; “Micro-blog first case”
2016- 05 - 25
李伟平(1989— ),男,山东高密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
D923.14; G210 ;G206.3
A
1008-7729(2016)05- 0021-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