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中的形而上学※
2016-12-17贺伯特博德戴晖
[德]贺伯特·博德 戴晖 译
历史现实中的形而上学※
[德]贺伯特·博德 戴晖 译
人们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一种类型,而哲学又作为科学的一种类型,如果它落入这种一般的观念,就应该在当今的科学协作中找到它。然而如今它出现在哪里呢?它,带着它的本质的要求,即:是第一科学。甚至没有一次出现在“哲学的”诸学科下。它总还在这里和那里,以这样或那样一种从前的形态,甚或只是东拼西凑地加以讲述或研究,在这种和那种原理中它显得尚可以接受或者被加工得可以接受,所有这些并非将它作为始终具备当下的第一科学予以尊重和推崇。
众所周知,形而上学不是今天的,而一种科学似乎只存活于进步中,也许应该可以重复这个老问题:“形而上学有史以来”—不过,怎样的时间—“所做的真正的进步是哪些?”这里所考察的如果不是到黑格尔为止的时间跨度,还有什么其他的时间段呢?人们想在此表明哪些“真正的进步”呢?
如果这个问题并不令当今的人陷入难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像这样的回答早已不是闻所未闻:自从黑格尔时代以来,形而上学的唯一真正的进步是它的没落,它再也不自以为是科学,更不用说是第一科学。
会有如此之答案,却是值得注意的。自黑格尔以来,围绕从前的第一科学所发生的一切,显然已经越过了那种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康德曾经提出决定性的质问:“诸如此类是否也可能是形而上学”。今天谁愿意像康德那样认为,“还根本没有形而上学”?谁能够重复这个“还”字,并给予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一个未来?因为和康德分享这样一种信念,“对形而上学的探究却也从来不会失去”(《导论》Prolegomena)。今天将如何面对这个“从来不”呢?
首先重新提起世所公认的:曾有过形而上学,即使并且恰恰在康德对其可能性进行了检验之后。抑或诸如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不是形而上学的著作?对形而上学的新的进步的追问必须回顾至此。
而相应的回答如何呢?它表现在如下诸信念中:不可能有形而上学;不必有形而上学;不允许有形而上学。在今天,怎样的理性如此判断“纯粹理性科学”呢?一种从“自然”理性分离出来的“世界”理性—世界的,因为它只把自己理解为人及其本具的创造性的。上述判断的独特位置进而也是世界理性对理解及其世界的省思,而理解是对体验的理解。
一、世界理性①世界理性(die weltliche Vernunft)、自然理性(die natuerliche Vernunft)和概念把握理性(die conceptuale Vernunft)是三种不同的思想形态。它们出现在形而上学的诸时代,而只有概念把握理性珍藏并论证了智慧的天赋。现代思想在充分展开世界的三维(科学技术的世界,生活实践的世界和人的创造本质的世界)之后,也显示出其思维的理性特征,作者称之为世界理性。—译者判断中的形而上学
历史当下的“哲学”思想表现在一种三重的省思中:首先,对科学研究;第二,对科学研究赖以为基础的生活;第三,对规定这种生活的存在。
至于第一种省思,它首先在自然科学研究那里看到科学性的标志。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形而上学不可能是科学。或者必须有两种科学性。但是即使如此,尽管允许有关黑格尔“科学体系”的模糊说法,也丝毫不改变这种无疑为自然科学研究所独具的声望的权威性;和技术认知相统一,它处处树立自己的权威性。
形而上学不可能是科学,与这种朴素的判断相比,如果人们为了满足认知以外的诸需求而又想方设法让形而上学在种种科学之外成立,这就使得形而上学蒙受蔑视—更不屑于这样一种手法,即从形而上学的大量遗产中挑拣看起来和科学命题类似之物;不值一提的是那种拙劣的纠缠,在传承下来的东西中翻寻兴奋剂。
形而上学不可能在了,如果它的科学要求为一种理性所检验,而这种理性在其世界性中不能够把自身理解为“原则能力”。这种理性同样知道:形而上学不必在了;因为这里规范性的诸科学从自身出发不需要“建筑学的”统一,也不需要第一科学;它们处于一种技术关联之中,相分相合各依其研究的变化不定的需求,假定需要一种第一科学,那将是普遍的“科学理论”。进而假定在不同的方法论中有一种等级秩序,诸演绎科学的逻辑将是第一位的,就它—用塔尔斯基(Tarski)的话来说—表示“联合起来的概念机制”而言,它“为人的认识整体提供共同的基础”。
在当下省思的每一个维度中,对形而上学的拒绝都以这样的判断为结束:不允许有形而上学—为的是再次且最后一次排斥它作为一种智慧的形态①博德先生后来称已经完满的哲学为“知的形态”,而“智慧形态”则用来表示西方智慧传统的理性关系的完整性。—译者。形而上学要求知道“人人必然感兴趣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奢求,它压制所有相关者的合理对话、妨碍他们在最关心的事务上参与决定。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极权思想的安全地,埋葬社会在辩护与要求辩护中的开放性。形而上学智慧的祸害迫使自己结成强制的封闭体系,这些体系从“第一真理”那儿获得统一性。这是真的吗?无法用历史的正确与否来对待世界理性对形而上学所做的这种乃至种种断言。为什么—这会在以下的省思维度中变得更加清楚。
对于在生活关联视野中世界理性,形而上学是如何呈现自身的呢?科学认识退回到体验的理解,那里每次所理解的首先是一个意义;意义特有的结构造成生活或者行动的内核,正如它整体上按照其历史性、世界性和语言性所规定的那样。
什么是这里的生活,在其客观化上来理解;客观化的第一种是被理解的体验的历史,一如它在世界观上表现为共同的那样(狄尔泰);客观化的第二种是世界,一如它产生于个人的意向性体验(胡塞尔);客观化的最后一种是语言,一如它总是作为许多不断变化的个人小组中的一个,而服务于交往行为(维特根斯坦)。
与对科学认识的省思不同,对生活的省思不仅排除形而上学,而且自己占据了从前的第一科学的位置。
狄尔泰在学院演讲中说:“我已经开始奠基关于人、社会和历史的个别科学的基础。我为它们寻找一种基础和联系,不依赖于形而上学,而是在经验之中。因为形而上学的体系已经崩溃,而意志不断地重新为引导个体生活和领导社会而要求稳定的目标”②Wilhelm Dilthey, Ges. Schriften, Leipzig, 1924.(V, 11);它们应该在形而上学崩溃之后重新规定人的行为的意义水准。狄尔泰试图以经验为依据满足这一实践要求,而经验带着人的生活的对象化的表现。将之理解为同一物的不同方面,是历史意识的事情,而历史意识是每一种世界观无法扬弃的片面性的意识。
诸形而上学体系为什么必定崩溃呢?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概念描述”(VIII, 30),作为看起来是客观的知识,每每都要求普遍有效性,而反对一种开放历史序列的惟一可能的统一性。形而上学的体系压迫所有生者(8)的多面性,忘记它的生活的源泉(78)。脱离“世界关联被赋于其中的生活性”(8),世界观就变得教条,而作为教条的世界观与世界格格不入。
这里狄尔泰总结道:“消极和辩解地: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无论作为超验的还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因此排除了意识局限于某种教条……积极地:通过自身省思和整个历史社会的生活关联的分析,哲学装备起来,以把握生活,理解历史并且胜任现实。”(192)正是这种有用性使哲学不再成为形而上学;作为教条的,它否认它的源泉,陷自身于与生活的矛盾并且自己使自己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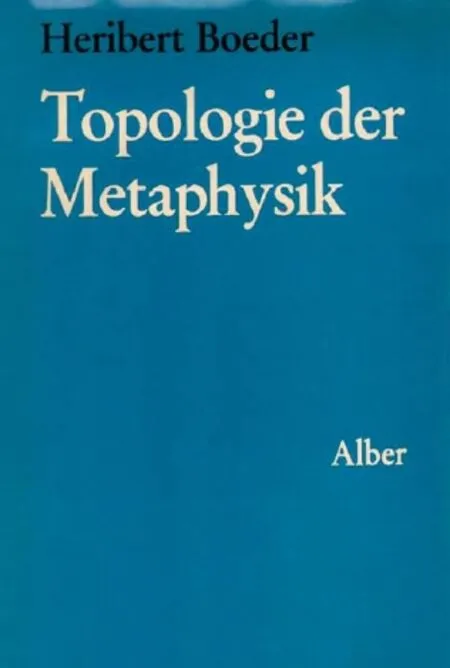
它不可能在了—并非着重于逻辑意义,而是在无能立足于生活的意义上,它不能为世界观的历史性负责,它作为它自认的科学,追随着永恒真理的幻象。它不必在了,狄尔泰只是要求以“普遍的科学理论”取而代之才这样认为。因为“(个别科学的)联系过去在形而上学中。如果抛弃形而上学,只承认经验科学,那么这个任务必须由一种百科全书,一种科学的等级制来解决”(199)。
胡塞尔用一种第一哲学的努力接受了这个任务。显然在转化了的规定之下。它表现在,胡塞尔即使用世界观理论也摒弃这样的做法,即把所要求的科学理论置于一种解释学之下。因为科学理论只有形成独立于个别科学的科学自我规定,才成为各门科学的坚实基础。它要求注意力从“生活之流”的历史“客观化”转向主观意识功效之整体,整体于个体“体验之流”中完成,其最高成就是:判断作为科学判断的自觉的责任。
可以科学地开阐“主观性”,但是,体验是特地“作为意识统一性的组成部分,在经验之我的现象学的统一意识流中”加以观察①Edmund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3.Aufl, Halle, 1922.(Log. Unt. III, 352)。“绝对被给定的意识”的孤立—重复一遍:“被给定的”—通过“悬置”,通过克制对世界的自然信仰②Husserliana (Ges. Werk), Den Haag, 1950ff.(Husserliana I, 8)而达到明见:一种原初的体验隐蔽在对象的相对体验下,承载着控制着相对体验。这种原初体验不再被关涉,而是纯粹关涉者,并且作为如此关涉者而敞开其“意向性”基本特征。只因此,对象的被给定状态的“如何”才能够单独地对象化,而随之才给予人充实的意义。
形而上学从自身出发给其“自然”的各部分规定对象和科学形式—完美地见于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相反,胡塞尔的第一科学置身于与已经具备扎实根底的诸科学的关系之中。在“精密”科学中它有效地作为第一,因为它把其他科学与更高的抽象知识只是连接起来—首先和“实质的区域本体论(materialeregionale Ontologien)”,然后和一般的形式本体论;其“存在者”“对于哲学、进而也对于现象学的关联作用研究(是)一个实践(!)理念,即起理论规定作用的工作的无限性理念。”(Husserliana I, 12)。实践理念不是在形而上学的道德意义上,而是一种献身于科学的生活理念。
科学赋予它从事的工作一种意义;而这个意义只由此可见,即正在出现的科学是“生活世界经验的理想化”的产物③Edmund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Hamburg, 1948.(Erf. U. Urt., 44)。理想化行为的“隐蔽的主体性”工作能力,就自身而言,仅在“从生活世界向主体功效的进一步查问”中得以衡量,“它本身产生于主体功效”。从科学经验来说,它需要一个本身仍是科学的回溯,通过生活世界的经验到“完全出于主体本源的可能世界的结构和源泉”(同上,47)。在不同的经验之我的世界的前世界源泉,可以看到一个世界,它—与自然不同—不仅是为人的,而且也是由于人的。不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不需要神学,而需要方法论地建立起来的第一哲学,也就是先验的原则理论,作为“说明性的”实事科学的基础。
然而,处于当下状态的实事科学对胡塞尔的奠基努力漠然视之。这是由于—胡塞尔这样以为—近代形而上学给它们的“客观主义”烙印;它们忘记了其生活世界的源泉,因而也排斥从生活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原始主体及其给予意义的工作的进一步追问。
胡塞尔曾著《纯粹语法的观念》,语法规则有“区分意义和无意义的功能”—为纯粹逻辑做准备,这种逻辑应该防止“形式上的悖谬”(Log. Unt. II 1, 294以下)。对生活的省思最后采取语法的形态,这种语法不是为了固定规则,而只是对遵守和建立规则进行描述,人通过这些规则巩固语言功能,亦即人所特有的行为的功能。
这里人的意义实现似乎达到理性,它为自己免除了一切对我的设想和意见的询问。所有意义在这里是意义充实的言谈的意义。除了理解这种言谈之外,不需要其他的意义实现。言谈应该不只是可理解的,也应该直接被理解。直到这里,“不允许有形而上学”这个判断才找到其本真的位置。据此,形而上学不再被看作一种世界观的体系、看作为精密科学奠定基础的努力,而是处于命题的形态之中,这些命题包含“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将自身表现为一个规定科学世界的序列,此科学世界是唯一的—从名称的解释,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有意义的命题?什么是基本命题的真理功能?到一般的命题形式;命题形式“是命题的本质。说明命题的本质意味着说明一切描述的本质,亦即世界的本质”④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1922.(5.471)。这种世界的什么(Was)的规定抓住了这样的中心,其一边是世界的怎样(Wie)的描述或者所有的“情形所是”(1.),另一边是怎样的感觉或者体验,即世界存在(6.45)。说世界是什么,是哲学的事;世界是怎样的,自然科学的事;说世界存在,形而上学的不可能的事。
有意义的命题仅允许描述怎样;说世界存在或者陈述那种感觉,终究是无意义的。说“什么”,也就是描述语言本身或者语义分析,抓住了中心。这个唯一可能的哲学的中心是转瞬即逝的,因为它必须不断使自己多馀,只服务于将语言把握在工作范围的极限内,即有意义的命题中(6.54)。按照这一批判性的任务,“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行动”(4.112)。这里再次跃入眼帘,形而上学究竟作为什么被第三种省思抛弃:不只是作为科学,不只是作为第一科学,而最终是作为智慧。
维特根斯坦趋向这样的信念:“哲学的正确方法本来是:什么也不说,除了让自己说的,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一些与哲学无关的东西—之外,并且,只要他人要说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时,就向他指出,他的命题中的一些符号没有意义。”(6.53)他没有将它止于那个世界存在的感觉而就此罢休,而是将情感贯穿于描述怎样,说出不可说的(6.522),说了无意义的。
意识,观念及其主体正是这样导向无意义,意识想要更多,而不满足于作为世界的界限(5.632),因而倒向界限之内的某物。那里它碰到“世界的意义”(6.41)这样无意义的问题,并且用所谓的智慧在一种伦理学的无意义的句子中说出它的价值观念、什么应该是好的的观念。
形而上学用语言“来表达作为有限的整体的世界感觉”(6.46)。《哲学研究》用“命题的一般形式”反对语言的观念统一①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gen, Oxford, 1953.(§65)。语言不是一个世界的统一性,也不以任何方式是系统的统一—就像胡塞尔的主体世界仍旧是的那样。“不是提供某些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一切所共同的东西,我说,对于语言的诸现象根本没有一种共同,因为这种共同我们对什么都用相同的话—语言现象是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互为亲缘的。”(§92)
这里试图彻底清除对于形而上学似乎是理念并且就是概念的东西;因为被形而上学所侵蚀的思想的所有病兆都归于这种“言过其实(Über-Ausdruck)”(§192)—首当其冲的是寻找一种“共同”的“定义”(§65),其次是制定认识的唯一方法(§133),按照形式逻辑的唯一尺度判断所言的清晰明确(§81),将理解作为“心灵的过程”(§153)加以研究以及相应的个别思想主体的虚构(§293)。
“理解一个命题,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意即掌握一门技术。”(§199)理解的技艺,命题“工具”的运用(§421),要在所有的理解方法之前得到锻炼。如果这种开始的技艺有一个主体,它练就这种技艺,那么它每每都是具有诸多特定“习俗”或“生活形式”的社会;这些“习俗”和“生活形式”对于所有的意义理解是首先“须接受的、给定的”(II, 226)—已经融入并且游戏于理解规则,为它们所掌握并且也掌握它们的人可以改变它们,或者以新的“语言游戏”丰富它们。
在命题是真的以前,必须有意义,而它只有按照语言游戏的规则才有意义。这并非意味着“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241)或者“行为方式”的一致(§206)。不是在任何一种真理上,而是在如此之协同一致上,社会具备其凝聚力的基本因素。在这一基本理解的视野中,有真理要求的命题,即陈述,失去在其他语言工具面前的优势,如命令、请求或者提问。
因此,科学中的理解就不能在日常理解面前要求优先地位了。科学的理解技术本身日常化了,并且正因此而不能够透达并且掌握“生活世界的经验”;数学和逻辑没有表现出“理想的”理解技术,也没有带来立于日常理解之彼岸的“更高的”知识。理解技术没有等级制度。和科学本身一样只是工具性的。“这里我们的整个观察在旋转”,并且是“围绕着作为支点的我们原本的需要”(§108),也就是实践的清晰性和综观性(§122, 132);并非在语言功能的理论化解释中,而是对多种形态的语言功能进行同样实际的描述,满足了这种需要。
“哲学的整个迷雾凝聚成语言理论的小水滴”(II, 222)—这是对生活的省思的最后收获。其整个智慧是治疗性的,并且是对于这种说话者,他自身始终是与“不可说”、但却自身“显示”(6.522)的东西的界线—显示于情形的多样性之外,不可能是任何特定的东西,或者在“必须对此保持沉默”—为什么“必须”—这一表达中所标识出的矛盾的东西。
历史、世界和语言之全体性,每一个皆规定着本具的对象领域,这种整体性似乎是得自抽象理论化的风格。如是,则狄尔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的位置也不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关联之中。问及他们对形而上学的态度时,作为意义的体验和理解的理论,他们的整体关系才为人所知。意义这里是世界理性索取和赋予的意义。
对形而上学的逐步排斥是与排斥性的省思的逐步自我限定同步而来的,开始于生活给思想的界限—狄尔泰的基本洞见。在这个局限之内呈献给思想的还有历史理解的整个领域,表现在艺术、宗教、哲学,尤其是国家的形象中。在胡塞尔那里,理解的考察集中在科学和生活世界这两个相隔离的领域中的对象的先验结构。随着维特根斯坦的语法,省思从对可供理解的东西的所有对象性规定中抽身而出,以巩固已有的、且须不断扩展的理解技术,防止理解技术的滥用。
世界观历史的兴趣、生活世界的兴趣和日常语言的兴趣,这一兴趣之序列表明了什么?若仔细考察,它不是发展,而是某种莱布尼兹—解释自然的死亡时—叫做involute(内敛)和contractio(集中的东西)①G. W. Leibniz, Math. Schriften, ed, Gerhardt, Halle, 1855.(Math. Schr. 3, 553, 560)。对生活的省思的诚实正见于:它—由于代替从前形而上学的位置—自己枯萎了。
它给了这样一个信号,不是教我们愤怒地或者胆怯地矢口否认维特根斯坦的结论,而是注意到一种省思,在这种省思中世界理性适应于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那么迫切地区分意义和无意义,而需要意义和荒谬的区分。这里关系到存在,因为一切理论和实践的荒谬首先渗透人的生产。
二、形而上学的历史当下
科学认识的省思致力于合理性,与科学亦或技术的工作方法的效果相一致,而对生活的省思与认识之思相区别,致力于前科学的理解,其“成绩”最突出地表现在历史、世界和语言的理解中。所有社会理解都蕴含于这种理解中,就此而言它是“实践”的。对生活的省思在社会及其需求中获得规定基础。
狄尔泰清楚地保证并且反复重复,哲学是一种“社会功能”(和York von Wartenburg的通信,全集V, 365);“历史世界观”尤其是“人类精神的解放者,将之从自然科学和哲学尚没有挣脱的最后锁链中解放出来”(VIII, 225);不过它掩盖着对“迫近的信念混乱”(V, 9)的担忧。
胡塞尔的“绝对自我负责的理念”(Husserliana VIII, 197)想控制这种无序;因此哲学不仅必须—在所有世界观之先—成为“严密的科学”,而且必须自许为相对于所有科学的第一科学,为所有以理据获得正当权利的知作最后的论证,并且在从“主体源泉”解开哲学所承载的“生活世界”的同时,巩固一个对所有人有约束作用的理解基础。于是胡塞尔相信:“我们做哲学,我们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人性的公仆。”(Husserliana VI, 15)
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相反:从一种前世界的“主体性”出发,哲学地说明理解活动,这本身干扰了语言中已经起作用的理解。相应的哲学只能是对语言误解的“治疗”—特别是哲学自身固定在“诸学说”中的误解。“如果要在哲学中建立命题,就永远不能去讨论它,因为所有人都同意它们了。”(Phi. Unt. §128)它们有社会理解基础作为内容—并非特定的意见,而是语言游戏规则,而意见也在这种规则中形成并且得到确认。
退回到语言理解,对生活的省思达到其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最疏远状态。马克思关于“社会”所说的也适用于这里:它“不是由个体组成,而是表达了个体之间的关系总和”②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953.(Grundrisse, 176)。个体只是在社会力量之维度中才是具体的,而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社会力量是“经济的”。这里个体关系才从本质上是社会关系,因为不再只是人的活动的关系,而首先是人的生产关系。
亚里士多德就曾提示:如果在人的知识的“建筑艺术”中,“神学”—形而上学—不一定是第一的话,那么“政治学”将会是第一。近代政治学本质上是“国家”政治学;针对国家作为业已实现的道德“理念”,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概念的国家是一种假象,它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一科技—“政治经济学”。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所缺乏的不是理智(Verstaendigkeit);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中它是最富于合理性的。然而马克思看到这个社会中违背理解力的暴力,显然这要区别于违背概念的虚无。
为了在自然的和精神的自然整体中概念地把握已经实现的理念,人作为理性本质,自身与自身相区分。并非上述这个人,而是与自己相同的人—他理解他的需求和劳动的世界—肩负生产的历史。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在这个历史中分别在人的生产力、创造性意志、创造性之知上看到当下的荒谬统治的来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扭曲了依靠双手的人和自然的本源关系,在他必须出卖劳动力之处,他完全失去了力量。道德的行为方式扭曲了艺术与生活的本源关系,终于主人意志失去了目标,创造者屈服于反生命的评价。技术的思维方式扭曲了思想和语言的本源关系,排斥诗性的思,把烦恼的人交给信息运转活动。
黑格尔已经指出:违背概念的或者坏透的东西,其存在不以任何方式与其应该相吻合,它瓦解于自身中,从而没有现实性。荒谬却非如此,它渗透人的创造活动的世界。只有它达到其最高效用时,才毁灭自身。资本通过其自身平息“自我兑现”的过程;道德由于自己对真实性的要求和其谱系的相应揭示而削弱自身。技术的本质随着其效应的滥用无度而调整自身。
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省思集中于历史当下的交锋,他们是如何面对形而上学的呢?
形而上学的完美体系,即黑格尔的“逻辑科学”,在马克思那里降低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科学”呈现的方法工具;相反,黑格尔的实在哲学却没有用,沦为意识形态的非本质性,它引起这样的幻觉,即当下生产关系的世界能够通过“意识改造”而改变。
对于尼采,形而上学显现于寓言的无本质性;只有在宗教现实性中它的道德能够规定意志;是基督教才使柏拉图主义诞生。因此尼采把他的历史态度概括为一句话:“狄奥尼索斯反对十字架上的耶稣”;局限于虚无主义的末流才有“尼采反对瓦格纳”,后者是堕落的艺术宗教的首席演员。
直到海德格尔才找到将形而上学理解为历史当下的形而上学的根据;作为思的形态,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来源似乎在形而上学,这里,形而上学就自身而言不是被理解为知的形态,而是作为思的形态—作为第一哲学是技术之思占统治地位的根据。渗透人的生产性本质的,不仅是技术知识,而且还有人的思想和语言的技术性自我阐释。正是因为这一技术性的自我阐释,海德格尔看到自己应该去揭示形而上学在当下的历史整体。进而也为了将来的缘故,因为“另一种”思,海德格尔将这种思作为“本源的”与“迄今的”相区别。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省思只是表面上能够与哲学史(Philosophie-Historie)有共同之事,而哲学史的考证并非他的话题。
当下省思的第一、第二种形态不是通过它之外的考虑,而更是在它本身确立了这样的信念:形而上学不可能在,不必在,并且不允许在。这样一环紧扣一环地,它就自己方面而言将形而上学之思排除在社会理解之外—如形而上学之思最后只还出现在个别措辞上一样。直至维特根斯坦,建立在理解技术之描述上的判断才使针对形而上学的暴力明朗化,它胜过所有对其矛盾和多馀的论证。
以“实在的”,因为它贯穿人的创造的世界,荒谬经验为动力的省思,才以第三步真正深入形而上学之思。形而上学之思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只是作为幻象而登场—其规定性对立于社会理解基础所容许理解的东西—而对于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达到经过区分的—按照开端和终点—因为是历史的规定性。这让他追问形而上学的规定。正是因此,“不允许形而上学存在了”的断言才被对其历史必然性的认可所打破。所以,不是要剔除形而上学,而是要“忍受”它。
然而,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的判断,尤其是海德格尔的须读作一种本身仍为历史的标记—甚至是路标。指向哪里呢?并非走向相对于技术思维的“另一种”思想,它不再过问在技术思维中现前的形而上学(见于《存在与时间》);亦非走向不同于形而上学之思的另一种思想的将来,而是进入形而上学自身本具的当下。但是只有假象消逝,形而上学才是其本具的当下,而这假象就是:形而上学是形成技术思维的历史。必须打破这种连续性。不过,如果不是“存在”之历史在正当优势的技术思维中的当下,还留下怎样的当下给形而上学呢?诸如“长久以来尚未彻底清除的残渣”?或者干脆又是那些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历史(historisch)再现的观点的灾难?
世界理性对科学认识的省思和对前科学的生活的省思,只把形而上学认作一种偶然现象;因为它虽有可认识的起因,却没有根据—就这样出现了。而对于“存在”历史的省思,形而上学成为相对必然的现象—相对于一种“本源的”、从不事先展开并固定的关系,它就是生产性的人与他的既定情况(ihm Gegebenen)的关系,具体说:与其权力、意志、思想的关系。这里形而上学是如何达到历史当下的,这显然表现在为将来所排斥的以往这一面,其规定性为听任自身—意即:听任从属于形而上学的技术思维的自身消耗。
根据黑格尔的本质逻辑中的“现实性”模态,思想对形而上学的第三种态度一定是可能的,照第三种态度,形而上学将是绝对必然的。然而,只要其现实性没有先行于这种可能性,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直接权衡就仍是空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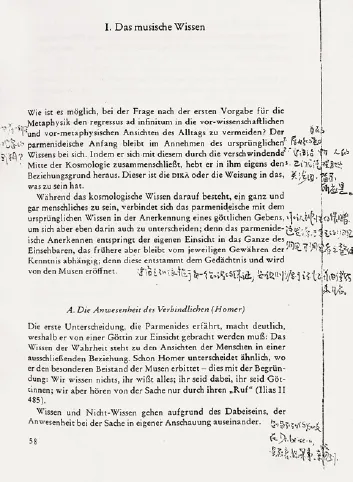
《形而上学的拓补学》第一部分第一节“缪斯的知”(旁注为戴晖作)

《形而上学的拓补学》第二部分第一节“基督的知”
三、永逝的形而上学当下
没有假设并且规定形而上学的统一,就无从谈起“这一”形而上学的当下。这一点针对那种直接的印象,即流传下来的诸学说是一种无规定性的多样性,它按照时间的顺序设想相关的历史(Historie),按照学说的相似性编排相关的历史。如果从它们从前的传统长河中还偶尔露出当下的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的影响延伸到同时代的观念方式—典型地不着重于形而上学理性的判断甚或推论,而更多地是它的“概念”。按照对概念的“意义”的主导兴趣进行判断,那里所涉及的不如说是哲学语言史考察范围内的诸名称。
形而上学在其每一种形态中都是一种经过论证的洞见,一种知的统一性—区别于种种知见—或者最终为第一科学的统一性;其最高体现是黑格尔体系。在形而上学被公认为非科学、更不是第一科学之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给它一种思想方式的统一性。维特根斯坦视形而上学为一连串病兆,总是损害语言的理解,而对于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在于历史的规定性,并且它已经到达一个终点—由这样的开端表露出来,它把形而上学规定为遗忘的历史,遗忘本来须思想的。
黑格尔的“科学体系”—不过只在时间的外在性上—“有”一个历史,而海德格尔眼中的形而上学“是”历史并且甚至是“这一”历史。如此之历史不能够由事件的时间顺序来规定;它的规定—正如黑格尔的“世界审判”对于所有历史(Historie)已经没有对象一样—在于其开端的唯一命运(Geschick赠达)。正在这里海德格尔看到它的统一性的根基。
这种统一性的目光与其说是被历史(historisch)习惯,不如说是为功利的“研究兴趣”所遮蔽。此外,与“伟大的”哲学家交锋并且在最高威望面前确信其身,这样的机会总还是显得富有魅力—看起来继承哲学家们批判性的努力,同时无须担忧自己的批评没有在整体上做任何区分,因此也不留下任何历史。对形而上学统一性的淡漠还装出一付美德,即所谓面对形而上学现象的多样性的“公正”。
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往往为对其形态抑或传统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偏爱所掩盖。这种偏爱容易与“爱-智慧”相混淆。其影响之远,显示在它试图把这种或那种形而上学变得可以让今天的理解接受—就像它首先投合各人自身的体验。如此之审美活动永远逃避—用康德的话说—形而上学诸原则的“棘手”,它要求人做出与他自身的区分。在对此保持安全间距的同时,也留有对“本体论”或者“一论(Henologie)”的兴趣,它看来是最早把形而上学作为整体来对待的,而对于今天的本体论兴趣,这个整体剩下的只是漫无边际的“以往”的联系。这种兴趣恰恰从海德格尔对“存在”及其“差异”的追问中—包括对他的通常毫无建设性的批评—借来当前使命的招牌。
不是在科学的完善上,海德格尔能够看到形而上学的规定已经完成了,而是仅仅在思想的开端上,而这种思想的历史就是形而上学。思想作为“更接近开端的”抵达与它迄今的规定的区分,于是上述目光把自身理解为历史的。思想随着它迄今之规定的完成“失去了命运(无所赠达)”并且成为“技术的”思想,就此而言,它已经与迄今之规定永诀。

《形而上学的拓补学》第三部分最后一节“形而上学整体的闭合”
在技术思维中形而上学变为世界的,并且仅作为如此之世界的形而上学而有历史性当下。所以海德格尔必然把向形而上学思想的告别和世界的区分相提并论,把它和世界从技术烙印中的解放合在一道考察。而这种区分的所在是“语言”;这里区分才是当下的。如果不是通过在技术思维中的当下,形而上学的当下还会是怎样得以保存的呢?鉴于上文曾提到的可能性问道:形而上学怎样才是绝对必然的?在何种规定性中那种可能性已经具备现实性?为了它已经做了些什么?
坚持或者甚至革新这种或那种形而上学传统的所有尝试都毫无结果。无能再现当初之所思,只好滥竽充数地掩盖这一无能,即从历史当下中,准确地说,从省思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中搜刮些思想—无视省思所独具的世界理性与自然理性以及相应的形而上学理性的区别。想暗中绕过历史的完整性(Geschlossenheit),而历史即形而上学的历史,于是人们就更不得不抑制这样一种预感,即:上文中所勾勒的省思领域就它自身而言可能已经结束了。
如果在它之外已经做了某些,那么在于完成海德格尔的那个要求,已经重复暗示过的要求:“放弃克服(形而上学)而让它听凭自身”(vom überwinden abzulassen und sich selbst zu überlassen)①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Tuebingen,1969.(《面向思的事情》,25)尽管他的关于放下(Lassen)的思想,海德格尔还是误认了这一要求的双重意义,准确地说:它的两面性(Zwielichtigkeit),而仅于这一面解读它:“不考虑形而上学而思考存在。”但是在另一种光线中—并且正是因为“存在(Seins)”和“兹予(Es gibt)”—这一要求说:把形而上学从与技术思维的连续性中释放出来,让它回到自身,回到它自己所造就的概念,并且是在它自己“纯粹的”和“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n)”理性之中造就的。这样一种放下是怎样的作为呢?应从(本书)正文的阐述中水落石出。
现在只针对形而上学自身的现实再说一句。形而上学在一种“永逝的(verschiedenen)”知的唯一性中得到尊崇,它就交付给自身的现实。与什么有别呢?与什么—这从决绝(Verscheiden)的意义上规定自己,决绝并非见自于泛泛而谈的形而上学“终点”,甚至不见自于它的完善,而仅见自于它的完美的造就(Vollbrachten)。
谈起永逝之存在,直接地是刺耳的,因为似乎在玩弄死之隐喻。然而今天还能影射怎样的死亡呢?如果不是指生命的衰竭。或者对体验的生活的省思教会我们另一种对死亡的理解?当然不是死之概念,形而上学并且只有它已经赋予此概念以规定性—心灵的理论规定、人格的实践规定和精神的创造性规定;这里死就已经不是从死之现象,而是每一次都从一种决绝来加以把握,因为永逝之存在。
对那种所谓“隐喻”的敏感为一种理解所特有,它不仅“不能够谈论”那种永逝之存在,而且简直不“必须保持沉默”,因为它似乎一定对此有所了解。
相反,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省思对死亡知道些什么呢?死每次都鉴于生产性的人而露面。
死首先面对依靠双手的人,他作为雇佣劳动力用陌生的工具进行生产;“资本”在工具中显现为“死的劳动,控制并且榨取有生命的劳动力”①Karl Marx, Das Kapital, Berlin,1953.(《资本论》1,144)。通过革命的劳动力群众夺取这种工具,对其占有者采取暴力而使这份“过往的劳动”服从于自身,劳动力群众自身变得人化并且充分实施了人对自己本身的最高公正。
然后,死不再于工具上,而是于生产的目的上面对人,人的意志这里屈从于基督教的、最终为社会主义的道德。有甚于死,从前所要的这种道德当下地是极端反生命的、颓废的意志的暴力。通过“一切价值的转换”来征服颓废意志,并非以人—在盲流中他已经是人—而是以超人为目标。其得以提升的生命的证明是善的流溢—不是同情②Friedrich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Berlin, 1968.(《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III,伟大的渴望)。这并非为人的维持生存着想,更不是为了从劳动中恢复健康,而是赞同毁灭,哪怕是毁灭他自身的形象、最终乃至超人自身。
最后,死不再面对现代人,既不对象化于生产的工具上,亦非于目的上,而是从对象化中抽离出来,以便首先在畏惧的气氛中粉碎人的理解技术的基础。相应的省思既不面向以非人的方式进行生产的大众,也不面向在少数“创造者”中的人的超越,而是面向“可朽者”的创造性的人之本质。
然而,畏惧—世界统一性的崩溃—才只是个别化;因为对于它死尚没有与自然的死分开,更准确地说:与世界内部的表象分开。海德格尔引入了相应的分野,他以令人瞩目的方式让它萌发于“什么是形而上学”的问题。随着这个问题,“存在问题”进入历史的规定性,遭遇到尼采的“虚无主义”经验;虚无主义似乎是形而上学在其颠倒中的终点。
只有终究不可支使的死—对于超人它也还是可支配的—让人成为“可朽者”。这是怎样的死呢?海德格尔回答了这个问题:“虚无的呐喊。”这里虚无“在所有方面中从来不只是单纯存在者的东西”—在存在的本质“差异”意义上的存在。虚无作为存在之虚无而“在(west)”③Martin Heidegger, Vortraeg und Aufsaetze, Pfullingen, 1954.(《演讲与论文集》,177)—历史地:作为“虚无主义”,或者是清算和了结那“就存在而言一无所是”④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1950(《林中路》,244);这是形而上学的一贯历史。即使揭示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一论(Henologie)”,也不应隐瞒,海德格尔未能找到这样的思想的根据,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彼岸把存在者的虚无作为一亦即善,海德格尔相反地着意排斥这样的根据。如果在上述关联中虚无“作为存在本身的秘密”而本质地在,那么不是作为流溢的善的秘密,而是遗忘存在的命运(Geschick赠达)的秘密,亦即虚无主义的馈赠:存在于整个历史中抽身远去。因为虚无“甚至”须作为这种秘密来思想,所以死在历史意义上是虚无的“呐喊”;作为如此之呐喊它“于自身中隐藏着存在的本质之在(das Wesende)”。
历史的死是从存在本身的“差异”来规定的,而非相反。这里死具有历史的唯一性,既脱离自然也脱离人的世界。这一“呐喊”所隐藏的,是因人的本质而不可触犯的:存在最终的本有,正如它一直收藏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它不是神,却是“神圣的(das Heilige)”⑤荷尔德林说:“das Heilige sei mein Wort”(“神圣的是我的话”),见于“Wie wenn an Feiertage…”(“犹如在节日……”),254页,20行,Carl Hanser出版社,慕尼黑,1989年第5版。—译者。作为上述之死亡,它自己为它的不可触犯而倾注心力。
正如死在历史省思的顺序上—脱离人类学的理解基础—得到规定,接踵而来的是公正、慈爱和神圣。如果愿遵循康德的一个提示,形而上学准确地了解自己的统一性(VIII, 257)。
马克思已经看到:历史的人的一切世界观的理解不是别的,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贯彻,理解的原本之事,也就是生产关系中的公正,已经隐退,而意识形态当下地掩盖了这种隐退。尼采:人的理解的每一种科学基础都出于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的真理”的意志,它向自己隐瞒了最高的代价: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它否认“创造者”及其弘扬生命的意志之善。海德格尔回忆:理解技术的编织使人听不见沉默,这是终究不可支使的语言的沉默,亦即来自神圣的理解。
这里的每一种经验都伴随着对当下的历史转折的期待而来。像马克思所期待的,它以必然的方式到来。像尼采所期待的,它以可能的方式到来。而海德格尔想,它不是不可能的。理解期待的这些模态转换并不着重于它的衰减—趋于这种既为毁灭又为缓解的判断,它增强了人类学的嘲弄:所期待的是不可能的—而是把它作为期待着的思想自身的转换,转向安处当下危机的沉着,也就是思想自身的区分。
只要每次得出的另一种规定性的当下尚缺席,这种思想就恰恰不能在它“牵涉到定夺”的关键上达到知的已然和决断;因为海德格尔虽然把思想区别于它迄今的、形而上学的技术特征,但是也不能造出世界本身的转化或者历史意义上的“兹予”的转化;原因在于“存在”自身的“差异”。
因为一种缄默和保留守在本源的“兹予”之中,存在的历史是遗忘存在的历史。海德格尔的这种经验一直为“真理的本质”(ALAETHEIA)所推动,为真理中须思想的遗忘—因为掩藏—所推动。此外,同在这一点上须认识到:如果海德格尔看出形而上学是“存在”的一种“遗忘”(LAETHESTHAI),那么这也就它一方面跌落到一种隐瞒(LAETHEIN);因为听任自身的世界理性为了其省思所独具的事业必须向自己隐瞒形而上学完满造就了什么。这种情况持续着,只要世界理性仍致力于造就其独立性的诸可能地位并且完善这种思想自身独具的领域。即使对于这一领域那种无理性的感觉仍是外在的,即形而上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已经变得“不值得相信了”。为什么不是:不可忍受了呢?自从恩培多克勒斯以来自然理性就已经知道形而上学是这样的。
形而上学业已完成,可以从它自己造就的概念、进而从它的哲学“理念”得知这一点。它的成就只能在它这一方面看到—在它自身曾是的历史,而不只是外在地“具有”的历史。这不是让哲学在“这一”科学中成长的历史,而是诸时代的历史,每一个时代都在自身本具的原则中;原则每次都要求与之相应的理性把洞见塑造成为科学的说服力。每一个时代原则都让人们认识到,形而上学是并且如何一直是爱-智慧,它每次都关怀并接纳一个并非由它带来的本源之知。这一“有”“给予”形而上学的,首先并非任何“存在者”,也不是存在者之“存在”,而是关于人之规定的知,具体说:关于人的思想之规定的知。
由于这样的知,形而上学的理性是“概念把握的”;它每次从“不值得相信”的假象中把知掩护到它的说服力中,正因如此它是“纯粹”理性。为了适应被给予的知,理性必须自己规定自身。这种自由在那些只是观望自由之实现的人那里唤起一种印象,自由与一切无系,游戏于“涉及定夺”的一切的彼岸。
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把握理性总是一再特意与“自然”理性相区别;在概念把握理性证明自身涵盖自然理性之处,对于自然理性它才是最终的主人,具体地说在自然的和精神的自然之理论中,它作为《哲学全书》阐述了与理念达到齐一的哲学。概念把握理性同样也与“世界理性”相区别,直到形而上学完成之后世界理性才将思想展开到诸位置的体系之中,这里只是用省思的不同维度提示了这一点,尚需单独著书阐述①参见贺伯特·博德《现代的理性-形构》(Das Vernunft-Gefuege der Moderne, Verlag Karl Alber Freiburg/Muenchen 1988) —译者—在《形而上学的拓补学》向详细论述概念把握理性之当下使命的过渡之中。
在对“存在”的省思中,世界理性区分并且规定了这样一个整体,它是历史当下中的人最吃紧之处:面向相应的另一个世界,按照他的权力、意志和知。即使另一个将来之思想已经为另一个世界预先作好准备,而期待的上述模态转换则让我们认识到,那个另一世界的将来什么都不是。对“兹予”的辨别,而不仅是思想的区分,必须在历史当下中本身变得清晰可见。这儿“给予了”爱-智慧的理性什么?不再是本源之知,而是历史之知,历史是处于自己所造就的圆满中的形而上学。而作为如此之形而上学,却是“永逝”之形而上学。
关键并不在于—甚至是不适当的—置身于形而上学的“立场”上,而是回忆并且继承(concipieren),它给予我们理性的先行赋予(Vorgabe)。正如形而上学的理性从来不直接地关涉到本源之知的诸形态,而始终通过一种与之相对的否定的知作为中介与之相结合—这种推求是纯粹理性自身最有特色的行为—当下与历史地给予的形而上学整体的关系也只能够是间接的,如果应富有成效的话;而它也通过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历史省思得到了中介。这一点在下面的阐述中作为业已承认的。
正是如此,这部拓补学只能是事业的第一部分,它的另一部分针对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构造(Gefüge),而最后一部分致力于知的先行赋予,它在拓补学中已经通过时代原则的发现②时代原则亦即一个时代的智慧给予哲学的知,《形而上学的拓扑学》用独立的章节专门阐述了哲学史的三大时代的“先行的”知,见于此书第一部分“形而上学的第一个开端的时代”的第一章“缪斯之知”,第二部分“形而上学的居中之开端的时代”的第一章“基督的知”,第三部分“形而上学的最后的开端的时代”的第一章“实现了的知”以及第三章“形而上学的知”中关于卢梭的章节“自由的情感”。而彰显出来。
※ 本文德语标题为“Die Metaphysik in der geschischtlichen Gegenwart”,是博德先生所著的《形而上学的拓扑学》一书的前言。译文曾以“历史现实中的形而上学”为题发表于《哲学与文化》月刊第26卷第2期,1999年2月,第152页至167页。文句有所修正。
把握形而上学是将它作为已经结束的整体,划分其历史是按照时代的基本关系
(rationes)的三重性。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形而上学的理性(Vernünftigkeit)在每一时代都以一种独特的智慧为先导或者与之交相辉映,使智慧之知具有逻辑的说服力。爱-智慧寻得固有的本源,因而是“纯粹理性”;智慧在各个时代的形态依次是:缪斯之知、基督之知和对义务和自由的觉悟。
历史(die Geschichte)就是形而上学的“这一”历史,不同于按照时间、地点安排的事件及其效应的历史(Historie)。译文中的“历史”及“历史的”均为前者意义上的,个别后者意义上的“历史”都缀有原文,以示区别。
本文中的Gegenwart和gegenwaetig统译为“当下”和“当下的/地”。形而上学自身的“当下”已经脱离了所有再现(Vergegenwaetigen)意义上的假象,不受任何时间、地点上的规定;它是有别于现代省思的另一种知,处于自身本具的现实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