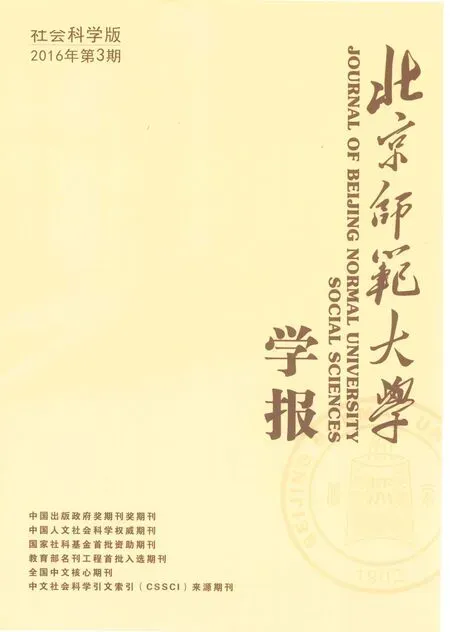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
2016-12-17梁涛
梁 涛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孟子研究院,邹城 273500)
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
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孟子研究院,邹城 273500)
[摘要]王安石融合儒道,将道家的理论思维引入儒家的政治实践,建构起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相贯通的政治哲学,为儒家政治宪纲作出理论论证。王安石肯定杨朱“为己”的合理性,表现出对个体物质利益、生命权利的关注。同时又区分了“生”与“性”,力求做到“为己”与“为人”的统一。如果说程朱还只是中世纪的思想家的话,那么,王安石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了近代。王安石的政治哲学也存在内在的矛盾,其天道本体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主要是为儒家的礼乐刑政提供了形上依据,而没有或无法为儒家的仁学奠定理论根基。他虽然重视个人的感性生命和物质利益,但认为一般的百姓只知“生”,不知“性”,没有赋予个体应有的自由和权利,王安石的另一只脚还停留在古代。
[关键词]王安石;庄子;天道性命;礼乐刑政;至理
一、北宋儒学的整体规划与引庄入儒——王安石政治哲学的历史、思想背景
赵宋王朝建立后,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剥夺方镇的权力,收精兵由中央统一指挥,粮饷由中央负责供给,任用文臣代替飞扬跋扈的武人充任将帅,同时增设机构、官职,以便分化事权,使官吏相互牵制,结果造成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财政上冗官冗费不胜负担,军事上在与辽与西夏的对抗中屡屡处于劣势,不得不割地赔款,输纳币帛,陷入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之中。北宋以文立国,虽经80年升平世,但法久必弊,政久必腐,至仁宗时各种矛盾已充分暴露出来,迫切需要一场变革来扭转颓势。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称: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①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
政治上“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思想文化上同样面临种种危机与挑战。赵宋立国之后,沿袭了唐代儒、道、释三教并行的政策,积极扶持佛、道二教的同时,尤关注儒学的复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儒学的地位。北宋政府倡导、崇奉的儒学乃是汉唐以来的注疏之学,这种儒术恪守于章句训诂,拘束于名物制度,存在着“穷理不深,讲道不切”的弊端,成为博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与之相反,佛、道二教则由于相对超脱于政治之外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分别从缘起性空和天道自然的角度对宇宙人生做了形而上的理论阐发。佛教视现实人生为虚幻烦恼,不过是苦难轮回的一个阶段,道教则追求长生不死、变化飞升,视现实世界为获得自由幸福的羁绊,二者都主张在名教之外去寻找生命的最终归宿和精神寄托,这对积极入世、视生生之仁为宇宙人生本质的儒学形成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据宋释志磐《佛祖统纪》记载: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志磐著,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下册,第1091页。
“收拾不住”说明此时官方倡导的儒术在社会上已失去了影响力,在佛、道的出世主义面前败下阵来。而一种学说一旦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只能靠政府的提倡维持表面风光,那就离真正的没落不远了。这样,作为对官方化儒术的反动,仁宗庆历时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在民间士人中不可遏制地出现了,儒者蜂拥而起,各立学统,力图突破章句注疏之学的束缚,回归孔孟,重新阐释儒家经典,从六经中寻找振衰救弊的思想方法。这一儒学复兴运动的主题有二:一是阐发道德性命之学,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二是复兴三代礼乐王政,以重建人间秩序和政治宪纲。某种程度上实际是回到了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仁、礼并重的整体规划——以仁确立人生意义、价值原则,以礼建构政治制度和人伦秩序。北宋儒学复兴的两大主题具有内在的联系,其中礼乐刑政、名教事业以天道性命为理论依据,而天道性命则以名教事业为落实处,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名教并重。但在历史的演进中,二者的结合则经历了一个过程。庆历时期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治道问题,对天道性命相对涉及较少,视为不急之务,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一种经世之学。但到了神宗熙宁前后,道德性命却成为学者热议的话题,通过诠释《论语》“性与天道”、《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庸》“天命之谓性”等命题,构成儒学复兴的又一主题。其中新学、蜀学、关学、洛学等均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兴趣,而尤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开风气之先,所不同者只是各派对道德性命各有各的理解而已。
王安石首倡道德性命之功,在宋代学者中已有共识。王安石之婿、曾拜尚书左丞的蔡卞称:“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语见蔡卞所著《王安石传》,此书已遗。引文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一,《经籍考·王氏杂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页。南宋学者郭孝友亦称:“熙(注:熙宁)丰(注:元丰)间,临川王文公又以经术自任,大训厥辞,而尤详于道德性命之说,士亦翕然宗之。”*谢旻等:《六一祠记》,《江西通志》,卷一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7册,第402页。都是肯定经过王安石的倡导,道德性命之说始成为士人热衷的话题。北宋儒家学者关注道德性命问题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是从天道或道体的高度寻绎性命本真,以解决人生信仰和意义的问题。姜广辉先生指出:“宋明时期的‘问题意识’是解决人生焦虑或曰‘内圣’问题。此一时期,儒者突破经典笺注之学,在‘性与天道’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上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本原。”*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卷,第18页。《论语》有子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之语(见《公冶长》),似表示对于“性与天道”之类的问题,孔子与弟子尚未有深入讨论,而此时却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究其原因,就是要从儒学内部寻找资源以应对信仰危机,解决精神超越的问题。其次是推论天道、道体为自然、社会的统一性、普遍性原理,为政治宪纲寻找形上依据。这样,经过北宋儒者的不懈努力,终于突破了章句注疏之学的藩篱,打开了义理诠释的新方向,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新儒学。
在北宋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下,庄学与道家(教)其他学说一样,也得到一定重视和发展,太宗、真宗朝都有提倡《庄子》的举措*参见方勇:《庄子学史》,第2册,第6-7页。。但《庄子》受到士人的关注,言《庄》成为一时之风气,则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开始之后,而真正推动庄学发展的则是当时两位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和苏轼。此于文献有徵,如宋人黄庭坚说:“吾友几复,讳介,南昌黄氏。……方士大夫未知读《庄》《老》,时几复数为余言。……其后十年,王氏父子以经术师表一世,士非庄老不言。”*黄庭坚:《黄几复墓志铭》,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三十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5-836页。据黄氏之说,在王安石父子以经术师表一世,并大力倡导老庄之前,士大夫中仅有少数人关注《庄子》。但经王氏父子大力倡导之后,便出现了士大夫“非庄老不言”的局面。今人郎擎宵也说:“庄学得王、苏之提倡,故当时治《庄子》者已次第臻于极盛,而《庄子》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郎擎宵:《庄子学案》,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37页。我们知道,北宋中期开始兴起的新儒学在对待佛老的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虽然也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但对佛老则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并自觉吸收、接纳佛老的思想以运用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之中,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隋唐以来三教合一的思想方式。另一种则是严守儒家的价值立场,对佛老持批判、排斥的态度,其受佛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或者是“隐形”的。在这二者之中,张载、二程等人无疑属于后者,而王安石、苏轼则为前者。王安石、苏轼对庄子的肯定和提倡,正可以从这一点去理解。
王安石等人关注《庄子》不是偶然的,《庄子》不同于先秦诸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宏阔的宇宙意识和超越精神,打破了自我中心,抛弃了个人成见,从道体的眼光来看待人世间的分歧和争执,视各家各派所见不过是主观给予外界的偏见,并非道体之全、宇宙之真。在《齐物论》中,庄子批评了当时争论不休的“儒墨之是非”,不过是“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主张“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也就是以破除了成见之后的虚静之心关照人间之是非。而《庄子》中的《天下》《天道》等篇,则着力阐发了“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就是大道或道体大全,以针砭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弊病,破除诸子百家的精神局限,同时兼取各家之长,表现出统合百家的宏大气魄。因此,当王安石等人希望通过吸收佛老以创新、发展儒学,并为此寻找理论依据时,把目光投向《庄子》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正如卢国龙先生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得之于《庄子·天下》的道体大全观念,或许就是王安石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政治家力主改革的思想根源。从庄子的逍遥一世到王安石的以天下为己任,差距似乎很大,但二者的背后都有一个道体大全作为精神支撑。”*卢国龙:《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需要说明的是,王安石主要接受的是庄子后学黄老派的思想,《天下》《天道》等篇均属于黄老派的作品,而黄老派与庄子的最大不同,便是一改其超然出世、消极无为为循理而动、积极进取。从这一点看,庄子后学黄老派的内圣外王理想与王安石的以天下为己任之间,差距似乎便没有那么大了。
王安石引庄入儒,对其做儒学化阐释,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儒学占有绝对的影响,不如此便无法消除对庄子的排斥和反感。另一方面,也是为其融合儒道做理论铺垫。在王安石看来,儒家固然缺乏对道体的关注,但道家同样忽视了礼乐教化,二者存在着融合、借鉴的必要。在《老子》一文中,王安石对“道”做“本”、“末”的区分:“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本”是天道自然,不需要人力的参与而生化,以自然而成为特征;“末”指人类以礼乐刑政等方式参与到自然的造化之中,使其具有人文化成的意味。因为涉乎形器,需要人力方可完成。“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因此,道家的无言、无为只适用于天道自然之体,而不适用于礼乐刑政之末。“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但是,老子不明白这一点,“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以上引文均见王安石:《老子》,《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3-724页。故是明于天道而暗于人道。与此相反,汉唐儒学有一套礼乐刑政的治世理论,但缺乏对天道性命的思考,是详于人道而略于天道。道家在礼乐刑政人道方面的缺失,表明儒家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而对于儒家而言,同样也需要以道家之天道补其人道,将自然天道与礼乐刑政相结合,建构起不同于汉唐儒学的新儒学。
二、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王安石的政治哲学建构
王安石引庄入儒,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从天道性命的角度对礼乐刑政作出论证和说明,将《庄子》的大道、道术与儒家的治世理论结合在一起,而王安石完成这一结合的理论根据,正是来自属于庄子后学黄老派的《庄子·天道》篇。在《九变而赏罚可言》一文中,王安石引用《天道》篇“先明天而道德次之”一段文字为据,展开铺陈、论述:
万物待是而后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爱者,仁也;爱而宜者,义也。仁有先后,义有上下,谓之分;先不擅后,下不侵上,谓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因亲疏贵贱任之以其所宜为,此之谓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为矣,放而不察乎,则又将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谓原省。原省明而后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后可以施赏罚。故庄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己明而赏罚次之。”是说虽微庄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不属之天者,未之有也。*②王安石:《九变而赏罚可言》,《临川先生文集》,第710页、710-711页。
《天道》篇的这段文字意在通过区分“道之序”,“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将仁义、形名、赏罚等纳入大道之中,建构起黄老派的政治纲领。王安石的立论则与此稍有不同,其目的是将道家的形上理论与儒家政治实践相结合,阐明天道以建立政治宪纲,建构儒家的政治哲学。王安石认为,《天道》篇所言实际揭示了政治运作的普遍原则,在儒家《六经》中可以找到根据,二者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如“尧者,圣人之盛也,孔子称之曰,‘惟天惟大,惟尧则之’,此之谓明天;‘聪明文思安安’,此之谓明道德;允恭克让,此之谓明仁义;次九族,列百姓,序万邦,此之谓明分守;修五礼,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谓明形名”等等②。因此,以《天道》篇的“九变而赏罚可言也”为纲,将道家的理论思维引入儒家的政治实践,以庄补儒,建构起儒家政治宪纲,克服君主直申己意的弊端,便成为合理的选择。
在王安石看来,居于权力顶峰的君主究竟以什么为意志,是天命、天道,还是其个人的好恶之情,将最终决定国家的命运,是一个需要追根究底、认真对待的问题。汉代董仲舒曾提出“屈君而伸天”,试图在君主的个人意志之上建立起一个更高的人格神——天,认为“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视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董仲舒著,钟兆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二端》,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346页。按,此段文字原属《必仁且智》,钟兆鹏称“旧本有‘其大略之类……而况受天谴也’一大段,与仁、智无关,乃《二端篇》之文,错简于此。今移入《二端篇》末”,同上,第588页。。以天为儒家价值的体现者,“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又)养而成之……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董仲舒著,钟兆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王道通三》,下册,第732页。。试图以此神学化、伦理化的天规范君主的行为,限制其肆意妄为,建构起汉唐儒学的政治宪纲,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其粗陋的天人感应的论证形式,逐渐遭到人们的怀疑和否定,由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根本怀疑、否认天的神圣、超越性存在,认为天不过为头顶上的自然现象而已。“仰而视之曰:‘彼苍苍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几千万里,是岂能如我何哉?吾为吾之所为而已,安取彼?’”认为天与人事包括政治活动根本无关。于是君主不再相信个人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和法则,“遂弃道德,离仁义,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申)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赏罚。”凭一己之私意判定是否,施行赏罚,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如何恢复天的权威,重建儒家政治宪纲便成为急迫的理论课题。而在神学感应论和怀疑论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王安石把目光投向了《庄子》,取《天道》篇的大道概念为己所用,作为其理论的重要基石。与董仲舒神学意义的天有所不同,王安石的天是指“万物待是而后存者”,即万物赖以存在的形上依据,实际也就是道,故说“天与道合而为一”,“道者天也”*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45页。。道的另一层含义是“莫不由是而之焉者”,即万物所遵循的理则、法则,而掌握、认识了这一理则便是德,根据德去爱便是仁,爱而得其宜便是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王安石将天理则化了。由于天是“万物待是而后存者”,故理则也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是人们包括君王所必须遵守、服从的。具体到政治实践中,君主必须遵守、执行“九变而赏罚可言”的政治程序,将主观意志客观化,消解其因权力而产生的非理性冲动,将权力运作纳入理性轨道,以实现对君主权力的规范和制约。王安石钟情于《庄子》,正在于这一点,故认为庄子(实际为庄子后学黄老派)的“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语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圣人亦不能废。”*以上引文均见王安石:《九变而赏罚可言》,《临川先生文集》,第711页。这样,通过引入庄子(实际是其后学)大道和天的概念,王安石重建儒家的政治宪纲,既可以坚定地主张“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所得失所致”,又消除了人们对于“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的担忧*脱脱:《宋史·富弼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册,第10255页。,对儒学理论作出重要发展。
在大道的九变之序中,天、道德为天道自然,属于本;仁义、分守、形名等,功能上类似于礼乐刑政,属于末。这样王安石便从本、末的角度,对道家的天道自然与儒家的礼乐刑政作了区分和说明,并试图将二者融为一体。一方面,儒家的礼乐刑政应以道家的天道自然为依据,需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之上,符合“天下之正理”。另一方面,礼乐刑政又是“人力”的产物,需要符合人心人性,随人心人性的历史变化及时代特征而进行调整。只讲天道而不讲人为,则流于道家式的消极无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只讲人为而不讲自然,则流于法家式的刻薄寡恩,“蔽于法而不知贤”(同上)。故在《礼论》篇中,王安石明确提出,“夫礼始于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则野,知人而不知天则伪”。这里的“天”指天道,也指人之天性,由于天道性命贯通,二者实际是一致的。而“人”指人为制作。虽然礼出于人为制作,但必须符合天道、人性,否则便蜕化为法家之法,成为外在的强制和压迫。
在人性问题上,王安石对于孔子以后的观点均持否定态度,而主张回到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这可以说是王安石对于人性的基本态度。在对“性相近”的理解上,王安石早期曾一度接受了孟子的性善说,以性善理解“性相近”*今《临川文集》中收录有《性论》篇,该文原见《圣宋文选》,实际主张性善论。陈植愕认为,王安石的人性论经历了由早年的“性善论”向成熟时期的“性情一也”和“以习言性”的转变,并将《性论》看做前一阶段的作品(见氏著:《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279页)。,后又以太极言性,持自然人性论,这与其受《庄子》的影响,以自然天道为本显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在《原性》一文中,王安石提出:“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王安石:《原性》,《临川先生文集》,第726页。太极即道,太极不同于具体的五行,故不可以五行理解太极。同样道理,性作为太极,也不同于具体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亦不可以五常视之。这代表了王安石成熟时期的思想。在王安石看来,性与情不同,存在“未发”、“已发”,也就是体用的区别。“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人们所说的善恶只能是就情而言,而不能指性。“性情之相须,犹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恶,则犹中与不中也。”*以上引文均见王安石:《性情》,《临川先生文集》,第715页。“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王安石:《原性》,《临川先生文集》,第726页。所谓善恶只能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是对于一定的社会伦理准则而言,情感的表达符合此准则便是善,不符合便是恶。因此,在王安石那里,仁、义是一个伦理性的概念,是对情感表达结果的判断和称谓,而不是心性中固有的内在品质*王安石某些表述似乎也承认性有善有恶,如,“盖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性情》,《临川先生文集》,第715页)“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则命有顺有逆,性有善有恶,固其理。”(《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临川先生文集》,第765页)但这里的善恶应是指性中所具有的可能导致善恶的倾向或因素,与情之善恶有所不同。。它们只能说明情和习,而不能规定性。故对于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以及韩愈的性三品说,王安石均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都是情、习,而非性。“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相比较而言,扬雄的性恶混相对可取,但仍未摆脱以习言性的藩篱。“杨子之言为似矣,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也。”*王安石:《原性》,《临川先生文集》,第726页。他认为表达人性最为恰当,最有价值的,还是孔子的观点。“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是以与孔子也。”*王安石:《性说》,《临川先生文集》,第727页。
与其他人性观点不同的是,孔子的“性相近”没有对人性做善恶的判断,只是指出其有相近或相同的本性,这为理解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人性本来就有多种表现,而最突出的莫过于情感和欲望,这些表现又往往是相近的,是人类所共有的。对于人性而言,重要的是相近和共有,至于善恶倒在其次,或者说可共存、共有的便是善,不可共存、共有的便是恶。将这一理念应用到政治中,便是执政者不可用预先设定的道德标准对民众做“穷天理,灭人欲”式的道德教化,而应努力发现民众共有之本性,以立法的形式承认其合理性,列入国家政治宪纲,作为行政举措的重要内容。这,或许就是王安石从孔子“性相近”命题中获得的启示。的确,与北宋时期突出道德人性,严分天地、气质之性的理学家相比,王安石的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对民众的物质利益、情感欲望的关注和肯定。如,“世俗之言曰,‘养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礼乐之意也。养生以为仁,保气以为义。”*王安石:《礼乐论》,《临川先生文集》,第703页。这是明确肯定先王制作礼乐的目的就在于养生,并以养生和保气来理解仁、义,这不仅在北宋时期显得较为特殊,在整个思想史上都值得特别关注。正因为如此,王安石高度肯定杨朱“为己”的合理性,其人性论实际是从“为己”讲起的。“杨子之所执者为己,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由是言之,杨子之道,虽不足以为人,固知为己矣;墨子之志,虽在于为人,吾知其不能也。……故杨子近于儒,而墨子远于道,其异于圣人则同,而其得罪,则宜有间也。”*王安石:《杨墨》,《临川先生文集》,第723页。与孔子的为己之学不同的是,杨朱的为己不是就修身、成德而言,而是包含了对个体物质利益、生命权利的关注。王安石主张“为己,学者之本也”,正是着意于这一点。但是“杨子知为己之为务,而不能达于大禹之道也,则亦可谓惑矣”,杨朱没有由“为己”进一步达到“为人”,“失于仁义而不见天地之全”*同上,第723页。,这是其不足和问题所在。而儒家则是在“尽己之性”的同时,又“尽人之性”,是为己、为人的统一,是全学,而非偏学。而这,恰恰是建立在“性相近”的基础之上的。
在王安石看来,每一个体都有其喜怒哀乐未发之性,包含潜在的情感、欲望等,代表了个体的感性存在。但个体之性还只是一己之私性,会受外物的引诱而流于偏狭,甚至导致个体之间的冲突。但由于“性相近”,人与人之间的性是相近、相通的,可在个己之性的基础上归纳出彼此都可认可的共性,既肯定个己之性,又不侵害他人之性,使天下之人各遂其性。这可以说是王安石从“性相近”命题中引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已触及到近代政治哲学的主题,在思想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个己之性,王安石也称为“生”,而对由其进一步发展出的共性,王安石则称为“性”,此性也可称为“大中”之性*王安石常常使用“大中”的概念,如,“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上张太博书二》,《临川先生文集》,第810页)“伏维皇帝陛下,绍膺丕绪,懋建大中。”(《贺南郊礼毕表》,《临川先生文集》,第1061页)。“大”言其普遍也,“中”言其恰当也。根据古代“即性言性”的传统,生、性往往可互训,生也就是性。但在王安石这里,生、性则是有区别的。他在《礼乐论》一文称:“生浑则蔽性,性浑则蔽生,犹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生指个己之性,其不明则会遮蔽大中之性。同样的道理,不确立起大中之性,个己之性也无法真正实现。二者相依而相成,正如志、气可以互相影响一样。一般的人喜欢随情逐欲,向外追求,故往往面对的是“生”,而难以认识到普遍的“性”。只有少数的圣人能够通过反求诸己、推己及人,发现普遍之“大中”之性。“圣人内求,世人外求,内求者乐得其性,外求者乐得其欲,欲易发而性难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如果说“性本情用”是从本体、本源立论的话,那么“欲易发而性难知”则是从作用、表现而言。“性情一也”与“情性相反”在形式逻辑上似乎是矛盾的,但若换一个角度,二者又是统一的。前一命题从本体的角度肯定了性情的统一性,后一命题则从功夫、实践的角度提示人们,还需由情及性,由个己之“生”达至普遍之“性”。对此,王安石有详细的描述:
神生于性,性生于诚,诚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故养生在于保形,充形在于育气,育气在于宁心,宁心在于致诚,致诚在于尽性,不尽性不足以养生。*以上引文均见王安石《礼乐论》,《临川先生文集》,第702-703页。《礼论》、《礼乐论》等篇,李之亮认为皆荆公“元丰(注:神宗年号,1078-1085年)初年居金陵时作”(《王荆公文集笺注》,第1030、1033页),故代表了王安石变法政治实践时的思想。
这段文字涉及“形”、“气”、“心”、“诚”、“性”、“神”等概念,是王安石思想中最为晦涩难懂,也是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以往研究者或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鲜有探其旨者。其实,这段文字乃是从功夫、实践的角度阐明由“生”到“性”乃至于“神”的提升过程,是破解王安石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形”是“生”之载体,有生则有形。由“形”生发出“气”,此气与形相连,故属于与人之生命力有关的血气、情气*参加拙文:《“德气”与“浩然之气”》,《中国哲学史》,2008年1期。,指情感、欲望而言。由“气”生发出“心”,也就是理智开始发挥作用,对由气而来的情感、欲望等作出选择、判断、取舍等。在“心”之上又有“诚”,此诚即《中庸》之诚,不仅指真诚、真实无妄的内心境况,还指推己及人的感通能力,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礼记·中庸》)。王安石看重诚,并将其置于心之上,其用意也在于此。“诚”之后才是“性”,此性乃大中之性,是普遍之性,其源于生而又不同于生。“性”之上又有“神”,此神乃“与道为一”、“同于大通”后所获得的神秘的感知、领悟能力。由于神的获得是在由生及性的提升之后,故王安石称“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④⑤王安石:《礼乐论》,《临川先生文集》,第703页、703页、703-704页。,“去情却欲”不是要完全否定情,不同于李翱的“灭情”,而是要舍弃不符合大中之性的情,实际涉及的还是生和性的关系。在王安石看来,生与性是相依相成的,“生与性之相因循,(犹)志之与气相为表里也”。一方面“不养生不足以尽性也”,养生的目的是为了尽性——此“尽性”虽来自孟子,但不同于孟子的扩充四端之心,而是要达至大中之性。另一方面“不尽性不足以养生”,不确立起大中之性,不确立起社会的秩序、法度,则不能使天下人养其生。“先王知其然,是故体天下之性而为之礼,和天下之性而为之乐。”④先王体察天下之性,通过制礼作乐,以立法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使天下之人得以“养生守性”。这是礼乐得以产生的原因所在,也是礼乐在人类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所在。
衣食所以养人之形气,礼乐所以养人之性也。礼反其所自始,乐反其所自生,吾于礼乐见圣人所贵其生者至矣。
圣人之遗言曰:“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盖言性也。大礼,性之中;大乐,性之和。
礼者,天下之中经;乐者,天下之中和。礼乐者,先王所以养人之神,正人气而归正性也。⑤
衣食是养人之形气,即个己的情感、欲望,礼乐则是“养人之性”,此性为大中之性,普遍之性,而“养性”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贵其生”。只有圣人帮助我们确立了普遍的性,我们才能更好地满足生,这正是圣人制定的礼乐所具有的功能,因为它既符合天道,又合于人性,是“性之中”、“性之和”,所以能够“正人气而归正性”,规范个体的情感、欲望,使其达于普遍之性。这样圣人制定的礼乐便成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大纲大法,而刑政则是实现这一原则的法律制度、行政举措等。
由于王安石强调礼乐之“养生”、“贵生”,其论刑政更多将理财作为重要内容。“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王安石:《答曾公立书》,《临川先生文集》,第773页。他在《上仁宗书》中指出:“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临川先生文集》,第417页。在《马运判书》中则提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与马运判书》,《临川先生文集》,第795页。“资之天地”即通过发展生产,向大自然索取财富。不过,政事的根本还不在于生财,更重要的是理财,即财富的分配。“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王安石:《乞制置三司条例》,《临川先生文集》,第745页。这里的“义”便是财富分配中应遵循的道义、正义。王安石接受了孟子“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和“明君制民之产”(《梁惠王上》)的思想,主张使民“得其常产”,“得其常产则福矣……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产,而继之以扰,则人不好德矣”*王安石:《洪范传》,《临川先生文集》,第697页。。但在井田(均田)废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土地兼并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结果只能是贫者益贫、富者益富,“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册,第5830页。。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世人外求……外求者乐得其欲”,一般人只知生,不知性,故寻情逐欲,不知节制;而只有少数圣人可以通过内求,发现普遍的性,故“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王安石:《礼乐论》,《临川先生文集》,第703页。。历史上,《周易·谦》卦曾提出“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孔疏:称此物之多少,均平而施)”,《老子》更是宣称“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在王安石看来,这些都是属于“圣人内求”的见道之言,故多次引用,表示赞叹和欣赏*王安石:《易象论解》、《与孟逸秘校手书》,《临川先生文集》,第698、823页。,并作为变法实践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义”重新分配财富,真正实现“先王建礼乐之意”。
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王安石:《乞制置三司条例》,《临川先生文集》,第745页。
“不可以无术”指对“轻重(注:即‘币重’、‘币轻’,指货币价格的变化)敛散(注:聚集和发散,指国家对粮食物资的买进和卖出)之权”必须有所控制。北宋虽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由于采取了不抑兼并的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出纳敛散之权,一切不归公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一,第17册,第5623页。,国家经济命脉并不掌握在国君之手,而是被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所控制,他们聚敛财富,造成贫富悬殊,加剧社会内部的对立。然而当时的“俗儒”却对这种兼并、聚敛熟视无睹,采取宽容、放任的态度。结果是“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临川先生文集》,第861页。。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将“轻重敛散之权”收归国家,“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王安石:《兼并》,《临川先生文集》,第114页。。只要国家重新掌握了“轻重敛散之权”、“取予之势”,就可“以政令均有无,使富不得侵贫,强不得凌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第17册,第5830页。,“裒多益寡”、“损有余补不足”,“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了*同上,卷二百二十三,第16册,第5434页。。
三、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王安石政治哲学的定位与评价
王安石通过吸收道家尤其是《庄子》中的大道、道术概念,作本、末的区分,将道家的天道自然与儒家的政治伦理相结合,为儒家的政治宪纲寻找形上根据,建构起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相贯通的新儒学体系。这一体系曾在北宋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随着北宋的灭亡以及理学的兴起,又遭到彻底的否定和批判。今天如何重新审视这一曾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学体系,作出合理的评价,检讨所得和所失,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从内容上看,荆公新学的突出特点是融合儒道,这样如何协调道家之体与儒家之用的关系便成为理解和评价其思想的关键。如有学者指出的,荆公新学的不足就在于没有将道家的自然理性与儒家的人文情怀有机地结合起来,自然理性被看作第一义的,人文情怀被视为第二义的,关于天道的解释不受人道人文、人心所向的制约,这就难免走向独断,成为政治强势的特权*卢国龙:《宋儒微言》,第24页。。不过从王安石的思想来看,他还是试图贯通天道与人道,认为政治实践既要体察天道,符合天下之正理,又要考察人心人性,并上升为性命之理。只不过所谓天道是自然天道,其性命是自然人性,人道则主要落实为礼乐刑政,这与程朱理学以天理或仁义为中心所建构的天道性命之学显然有着根本差别。或许我们可以说,王安石将自然理性看做是第一义的,将道德仁义看做是第二义的,道德仁义甚至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在北宋儒学以仁确立人生意义、价值原则,以礼建构政治制度和人伦秩序的两大主题中,王安石明显偏向后者,他所建构的主要是一种政治儒学,是外王之学,而没有从仁学的角度建构起儒家的内圣之学或心性儒学。
从儒学内部的发展来看,孔子创立儒学重在仁与礼,仁指成己、爱人,主要属于道德的范畴;礼的核心是名分,代表人伦秩序,偏重于政治。仁与礼的关系如何,或者如何使二者得到统一,便成为儒学内部的一个基本问题,所谓内圣外王某种意义上实际也就是仁学与礼学的关系问题。从孔子的本意来看,他是想以仁成就礼,以礼落实仁,故一方面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另一方面又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但不论是仁还是礼,都有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理论建构。就人性论而言,由于仁代表一种自觉向上的道德力量,突出的是人的自主性、主体性,故由仁出发必然走向性善论,后来孟子“道性善”,提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以四端之心释仁,使夫子之旨“十字打开”,“更无隐遁”,可谓是孔子仁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后世称为“孔孟之道”,确乎有因。与之相反,礼则代表了一种规则和秩序,其本质是对人的情感、欲望及需求的调适和节制,更多强调的是规范性、外在性,故以礼为本往往会走向自然人性论,甚至强调人性之恶,竹简《性自命出》提出“礼作于情”,荀子主张“礼者,养也”,认为礼之作用是消弭纷争,“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可谓是这一理路的必然发展,先秦儒学史上同样存在着“孔荀之制”。如果说孟子主要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发展出一套心性儒学的话,那么,荀子则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建构起一种制度儒学。前者偏重于道德,后者侧重于政治,二者虽互有联系,但却有不同的适用范围,遵循不同的原则,自然也有着不同的人性论建构。就形上学而言,以仁为中心,为仁学寻找形上根据,必然突出天的道德属性,以德(仁、诚、心等)为联系天人的纽带,《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礼记·中庸》)。孟子提出“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走的均是这条路线。相反,突出礼的地位,为礼学寻找形上根据,往往会侧重天的自然属性,荀子讲“礼有三本”,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这里的天地主要自然生长意,其学说也落在“天生人成”之上。从这一点看,王安石取道家之天道,又持自然人性论,虽然“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开一时之风气,但其所建构的主要是一种道家的形上学,其言天道性命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主要是为儒家的礼乐刑政提供了形上依据,而没有或无法为儒家的仁学奠定理论根基。所以王安石虽然在思想、情感上更倾向孟子,并一度接受性善论,但部分由于道家形上学的缘故,最终还是选择了自然人性论。在政治实践上,王安石重视的也是孟子善、法并重的有关论述,而不是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过分强调性善作用的主张。表面上看,孟子和王安石都主张仁政不难,尧舜易法,但孟子强调的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而王安石则是说明圣人之政、先王之法并非高不可及,而是根据常人的情性、需求制定的。“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常以为高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以中人为制也”*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王安石传》,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册,第662页。。孟子由于突出仁心、善性,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故将“格君心之非”视为政治的关键和根本(《离娄上》);而王安石则强调在君主之上有更高的天或天道,并将礼乐刑政的建构以及“九变而赏罚可言也”的权力运作作为政治的主要内容。就此而言,王安石虽然对荀子存在较多误解和批评*王安石对荀子的批评或出于误解,或出于成见,如《荀卿》、《周公》两文(见《临川先生文集》,第721-722、677-678页),关于王安石与荀学的复杂关系,将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展开。,而与孟子思想一度更为密切,但所延续的仍主要是“孔荀之制”,而不是“孔孟之道”;选择的是孔荀的路线,而不是孔孟的路线。
当然,作为生活于北宋并受到佛老影响的思想家,王安石不是简单回归早期儒学,而是从形上本体或天道性命的高度对儒家基本问题作出论证。一方面由天而人,推天道以明人事,将天道的普遍原则贯彻到具体的人事之中;另一方面由人而天,从具体的人性中抽绎出普遍之性,安身崇德,以德配天,二者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不过由于王安石将道理则化,认为“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认为道乃万物普遍遵循的理则、法则,故在思想上表现出重“理一”,以“理一”统摄“万殊”的倾向。在《致一论》中,王安石称:
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虑”,言百虑之归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则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则道之至也。夫如是,则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时也。虽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则岂可以不通其故哉?此圣人之所以又贵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见乎安身,盖天下之物,莫亲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则无所往而不济也。无所往而不济,则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④⑤王安石:《致一论》,《临川先生文集》,第707页、708页、708页。
“至理”即最高的理,是万物遵循的普遍原理。掌握了这一“至理”,运用到具体的事物中,就可以执一御万,“不思而得也”。认识“至理”的方法在于“致其一”,这里的“致一”不仅仅指内心的专注、专一,更重要的是从万殊之理中认识最高的理,“百虑之归乎一”。一方面“至理”是最高的,体现在万物之中;另一方面,事物的理又是具体的,具有分殊的特点,故需要从分殊之理中体会、把握、认识最高的理。“圣人之学至于此,则其视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则莫能以惑其心也。”④这样便进入“入神”的境地,是为道之极致。入神属于道之本,是形而上的,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其目的则是要致用。致用属于道之末,是形而下的,是“可思可为”的,其表现则首先是要安身。王安石突出安身,主张“利其用以安吾之身”,表现出对个体感性生命及物质利益的关注,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不过王安石既谈“爱己”,也谈“爱人”,“爱己”、“为己”恰恰要通过“爱人”、“为人”来实现。如果说爱己主要体现在安身上,那么爱人便要崇德了,只有从个己之性中发现普遍的“大中之性”——实际也就是理,以此制礼作乐,完成制度建构,才可以“安身以崇德”矣。故在天道方面,王安石强调“致一”、“入神”,要求认识、掌握普遍的理,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人事中,“推天道以明人事”;而在具体的致用过程,则要求从人性、人事中发现普遍的理,“明人道以达天理”,呈现为双向互动的过程。王安石说:
语道之序,则先精义而后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则先崇德而后精义。盖道之序则自精而至粗,学之之道则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⑤
从“道之序”也就是理论上讲,应该是先明理而后致用,“先精义而后崇德”。但从“学之”(“修之”)也就是实践道的秩序上讲,则应在致用中以明理,“先崇德而后精义”。前者是自抽象到具体,“自精而至粗”;后者是自具体到抽象,“自粗而至精”。这是对“精义”和“崇德”而言,若联系到“入神”和“安身”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将“精义入神”看做内圣,将“利用安身”理解为外王的话,那么在王安石这里,显然是存在着由内圣而外王——“精义入神以致用”,和由外王而内圣——“利用安身以崇德”两个向度。二者虽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整体,但就“语其序”而言,又是有所不同的。一个是“道之序”,一个是“学之”即实践道的秩序。
王安石融合儒道,贯通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建构起儒家的政治宪纲,主要是解决了儒学的制度建构,也就是外王的问题。而没有对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对仁义作出有效论证,没有建立起儒家的心性或内圣之学,没有确立起儒家的人生信仰。在其思想中天道自然与道德仁义依然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二者关系如何仍需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当其理论思考与变法实践相结合,不得不服从后者的需要时,更是增加了思想的复杂性。例如,王安石倾心于《庄子》的“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就是“道体大全”,试图打破个人成见,兼取各家之长,为其融合儒道包括各家提供理论基础,表现出开放、包容的宏大气魄。但在具体理解上,又将道理则化,提出“莫不由是之焉者,道也”,认为世间存在着最高的“至理”,以之为政治运作、是非善恶的终极标准,甚至主张“百虑之归乎一”,又表现出一元、独断的思想特点。毕竟,所谓“道体大全”只能是观念的产物,是一种价值原则,只能从“无”去理解,而一旦进入“有”,进入实践的层面,就必然要落实为可认知、可把握的理甚至是法,王安石正是走了这样一条由自然之道衍生出严苛之法的路线。再如,王安石钟情于《庄子·天道》篇中的“大道”及“道之序”观念,本意是要在君主的政治意志之上建立起某种更高的理性原则,通过“九变而赏罚可言也”的政治程序,将君主的主观意志客观化,将权力运作纳入理性轨道,实现对君主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但是当变法实践遇到反对势力时,王安石又不得不寄希望于君主的权力,毕竟能够认识、把握“大道”或“至理”的只能是现实中君主,而既然政治运作的根据在于“至理”而不是其他,那么,君主一旦把握了这一最高“至理”,便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是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影射,但学者认为其基本符合王安石的思想。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2-111页。,其权威反而进一步强化,不可动摇。这样,王安石从规范、约束权力出发,又以强化、巩固权力终结,走入自我矛盾的怪圈。还有,王安石重视“己”或个体,强调“为己,学者之本也”,表现出对个体感性欲望及物质利益的关注。如果说程朱标榜“存天理,灭人欲”,还只能算是中世纪的思想家的话,那么,王安石的一只脚显然已经迈向了近代。他认为“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王安石:《虔州学记》,《临川先生文集》,第859页。。这里的道德是广义的,包括了礼乐刑政在内的社会规范。道德或礼乐刑政的根据不仅在于天道,更重要的是要符合人道,符合人心人性。人心指百姓的情感愿望、物质需求等,而性命之理则是对人心的进一步抽象和升华。在王安石看来,一般的百姓只知“生”,不知“性”;只知“为己”,不知“为人”,还需要王安石这样的圣人“为生民立命”,确立人生的行为法则。虽然政治的目的在于仁民、安民、富民,但政治举措却不能以百姓的具体感受为依据,不能以眼前的利益为取舍,只有从具体的“人心”中抽绎出更为普遍的“性命之理”,“任理而不任情”,这样才可为礼乐刑政奠定人道的根基。在这一点上又暴露了王安石思想的局限和不足,他虽然强调为己,重视个人的感性生命和物质利益,但没有赋予个体应有的自由和权利,王安石的另一只脚还停留在古代。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强调政治运作固然要以仁民爱物为主要内容,但还需要符合天道、至理,“后学者专孑孑之仁,而忘古人之大体,故为人则失于兼爱,为己则失于无我,又岂知圣人之不失己,亦不失人欤?”*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第11页。“古人之大体”也就是“大道”或“道体”,在王安石那里也可理解为至理,如果知仁而不知理,难免流于妇人之仁,结果不仅“失己”而且“失人”。“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有爱也,有所不爱也。爱者,仁也。不爱者,亦非不仁也。……天地之于万物,当春生夏长之时,如其有仁爱以及之;至秋冬万物凋落,非天地之不爱也,物理之常也。”“圣人之于百姓,以仁义及天下,如其仁爱。及乎人事有终始之序,有死生之变……此亦物理之常,非圣人之所固为也。此非前爱而后忍,盖理之适焉而。故曰:不仁乃仁之至。庄子曰:‘至仁无亲,大仁不仁。’与此合矣。”*②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第9-10页、18页。仁与不仁不在于其表面形式,还要考虑人事的“终始之序”、“生死之变”,以及“物理之常”,只要是“理之适焉”,表面的不仁、不爱实际也可以是仁和爱。“爱民者,以不爱爱之乃长。治国者,以不治治之乃长。惟其不爱而爱,不治而治,故曰‘无为’。”②据史载,新法推行后,“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脱脱:《宋史·王安石传》,第30册,第10546页。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连神宗都有所不忍,王安石却不为所动,斥之为蠢愚之人的个别行为。这实际已经不是“不爱而爱”的“无为”了,而是由“任理而不任情”走向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安石的某些变法措施虽然从爱民、惠民出发,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却走向了扰民、害民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蒋重跃责任校对侯珂宋媛)
[主持人语]在当今世界,无论有多少种哲学流派和理论,都少不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美国的实用主义。这两种哲学与历史的联系表现出来一种截然分明的特征:儒家思想深厚的历史根源往往使得我们更加关注它在后世的更新发展,而实用主义哲学的短暂历史则更需要我们关注它与西方传统哲学之间的血缘关系。然而,我们对实用主义的历史考察并非出于对其自身起源的发生学兴趣,而是为了更准确深入地把握这种哲学的鲜明特征。不同历史背景中的实用主义的确向我们显示了不同的实用主义维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种哲学的多重特征。为此,我们专门组织了这个专栏,目的就是要说明,实用主义哲学总是以其特殊的思想形式与各种不同的思想资源发生着多种联系,并把这些资源最终转化为自身的思想内容,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哲学立场和观点。陈亚军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德国古典哲学渊源的剖析,向我们清楚展现了当代实用主义的历史背景及其问题生发的真实意义。卢德平对皮尔士符号学的细致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实用主义哲学原创性的一个新的版本。季雨、王成兵以普特南客观性思想为视角评析了伦理价值的类型化策略。我们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对国内的实用主义研究以及当代哲学研究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江怡)
WANG An-s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LIANG Tao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WANG An-shi,by combining the essential idea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that is,building the Taoist theoretical thinking into the Confucian political practice,set up a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unites the former’s natural or celestial law with the latter’s mundane view of human nature cultivation and administrative/social norms observation.That provided a theoretical support to the latter’s political creed.WANG was positive of YANG Zhu’s world view of “being for oneself”,which pays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material profit and life right.At the same time,he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sheng”(life;individual nature;生)and “xing”(nature;shared characteristic;性)and aimed to integrate the advocating of “being for oneself” and “being for others”.If the Confucianists CHEN Hao,CHEN Yi and ZHU Xi in South Song can be said to be medieval thinkers,then WANG had made one step forward into the early modern epoch.However,he has some conflicts and drawbacks in his argumentation.
Keywords:WANG An-shi;Zhuang Zi;natural/celestial law;mundane exercise;ideal truth
[收稿日期]2015-11-06
[中图分类号]B2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3-00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