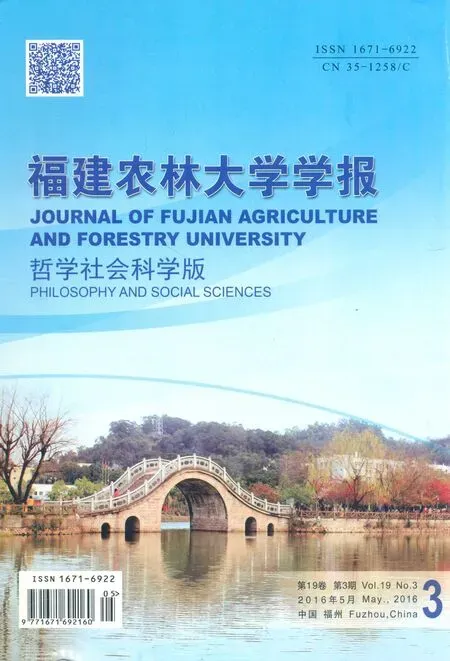论资本逻辑与出版伦理的内在关联
2016-12-16何华征
何 华 征
(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遵义563002)
论资本逻辑与出版伦理的内在关联
何 华 征
(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遵义563002)
[摘要]出版社企业化使出版业进入到资本逻辑的框架。一方面,资本逻辑在促进出版界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即个人主义、价值通约主义和物质主义对出版伦理的挑战,自由、公正、信用、良知等出版伦理原则遇到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出版伦理在实践中并未丧失其主体性价值追求,而它对资本逻辑的约束既可能使出版市场进入良序发展,又可能因出版伦理的激进化而导致资本逻辑的失灵,从而使市场经济的活力受到压抑。因此,构建一种“伦理限制性”资本逻辑,并使这种资本逻辑从主观性约束进入到制度性控制,显得十分紧迫。
[关键词]资本逻辑;出版伦理;价值通约主义
[DOI]10.13322/j.cnki.fjsk.2016.03.017
与出版社企业化伴随而来的是出版资源的资本化。出版行业的市场运行遵循一般价值规律的指引而不限于这种指引,因为出版行业作为精神产品生产的阵地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进入市场竞争场域的出版资本在现实出版实践中展示了资本逻辑的负面影响,资本的伦理劣根性使其在出版物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刺激了义利观的转变,过度追求企业盈利能力的表面功夫远远大于加强伦理内涵建设的深层力度。出版资本的逻辑与出版伦理的要求出现悖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出版业既有较高经济效益,又有良好社会口碑,就需要实现“出版资本伦理化”与“出版伦理资本化”的双向融合。
一、出版社企业化与资本逻辑的展开
早在1985年全国出版社(局)长会议提出出版社要从单纯的生产性单位向生产经营单位改革以后,人们对出版社的性质问题就做过争论。唐砥中认为,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但可以有企业化管理方式。“出版社虽然要努力讲求经济效益,但首先要讲社会效益,两者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1]。金仲萍也指出,企业化管理的出版社“不完全受价值规律支配”[2]。在出版社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阶段,“出版社不宜单独搞经济承包”,而应当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3]。1989年,有2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篇是石峰所写的《企业化是出版社改革的方向》,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版社必然要进行企业化改革,出版社也要注重经济核算[4];另一篇是张训智的《论出版社的性质》,他坚持认为图书的性质和国家法律规定了出版社是事业单位而不是企业[5]。在“经济效益论”和“社会效益论”之外,还有一种声音,那就是“2种效益兼顾论”[6]。 1992年石峰还强调:“图书就是商品,出版社就是企业,经济效益必须追求。”[7]而此时,反对者仅仅表达了出版社不能仅仅“赚钱牟利”的希望[8]。1994年以后,出版社作为企业化经营主体已经毫无疑问,人们研究的是出版社如何适应市场竞争的问题[9]。
企业化使出版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而参与到商品经济的竞争当中,出版社的生产性资料也就必然被资本化为盈利手段,这是整个社会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出版社企业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生产和需求的全面市场化。从生产端看,资本化(或资产股份化)成为出版社改制的方向,这造成了“生产激化消费”或“生产迎合消费”的结果,即出版供给决定书刊消费。从需求端看,市场化对书刊(商品)的质量要求更加表面化,这是商品符号化和品牌化的必然结果,即现实书刊消费诱导出版供给。两方面的结果都指向“效益论”的演化——资本逻辑必然要求出版业进入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实践框架。“资本来到世间,天生就具有增值欲望和强烈的利润最大化冲动”[10]。而“为了使资本生出利润,以盈利为目的的运营活动从根本上说是有选择性的”[11]。出版业强硬的市场化和资本化趋势如果不加限制地发展,就会陷入极端片面的“资本万能论”的泥潭,资本逻辑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整个社会被纳入到以“物资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物化社会。正因为如此,资本逻辑对出版伦理就会提出诸多反对意见和行动方案,削弱出版企业作为独特的生产经营部门的社会价值。
二、资本逻辑对出版伦理的悖逆及其影响
资本是支配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的最高权力[1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出版企业化的前述2个后果,即出版供给决定书刊消费,书刊消费诱导出版供给,使出版运营进入到资本逻辑的统治架构,它对出版伦理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一)经济个人主义对出版实践主客平衡体系的破坏
1.“出版共同体”关系的异化。图书出版运营的主客体及其中介在现实中具有共同体的属性,而共同体应体现出相互补益、相互促进、相互需要的内在价值。出版者、经销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补益、相互促进和相互需要的关系链在于信息交换所起到的生产-经营-消费反馈机制的正常运转。在资本逻辑出场后,追求个人利益导致这种关系式微,信息不对称反而成为生产-经营-消费诸方的实际状态。共同体信任关系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间的不信任。书刊消费者怀疑经销商只提供利润最高的图书商品,图书经销商怀疑出版社供给商品的市场潜力,出版社怀疑消费者和经销商的鉴别能力等。这种相互怀疑是资本逻辑下原子个人主义对共同体相互倚靠关系的破坏,从而导致伦理上信用机制的心理基础缺失。
2.“思想共同体”关系的异化。图书出版运营各方除了是利益共同体之外,理想的状态是:他们同时也是思想共同体。思想共同体即出版者、经销商与消费者(读者)、作者对出版物思想价值的认同。共同的思想基础或对思想性的追求能够使各方的“相互需要、彼此依赖”关系加强,从而促进出版运营的良序发展。然而,在资本逻辑下,运营方片面追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导致思想共同体的瓦解。思想共同体关系的解散使出版活动变成没有灵魂的纯粹经济活动,它对出版伦理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出版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尊重,个别劳动难以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一方面出版劳动无效化,另一方面文化消费的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导致资源浪费。
在资本逻辑统治下,平等、协商、和谐的出版运营人际网络关系被个人利益驱逐,相互信任与相互需要被利润计算和消费经济性所取代。经济个人主义破坏了出版实践主客关系的平衡体系,在现实中也导致了“滞销”和“无书可买”的双向困局。
(二)价值通约主义与单向度的人
1.思想自由与学术精神被简化为盈利能力。图书的出版策划所遵循的原则是市场前景,而市场前景被简化为盈利能力。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理性精神的发展给予“精于计算”以高度的认肯。在资本化市场环境中,数学计算被认为是可行而有效的,对精神价值的标定与划界却显得无能为力,从而思想自由与学术精神(即对价值与真理的探求)在不能肢解为要素化的数据时,就显得脆弱和难堪。“一大批传媒公司开始迈上上市的进程,经过一系列的转型、整合、扩张后,成为适应市场规则、满足盈利模式及更符合资本逻辑的‘传播机器’”[13]。“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内部,政治性组织、非盈利性组织的出现同样与资本逻辑的逐利本质相关”[14]。出版机构及其运营相关方的对资本逻辑的过分倚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出版伦理的内在价值。
2.创造性和启蒙价值被通约为货币量。在出版运营过程中,随着资本逻辑的扩张,文化价值、启蒙价值、创造精神、审美情绪、美善意志等被通约为货币量。“尤其是在‘资本主体性’的统治下,文化与资本的结合使文化更明显地表现出资本的本性,文化被资本化了,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到了资本增值逻辑的先行定向”[15]。在资本逻辑下,知识是集聚货币资本的力量但不是弘扬价值观的美德,人性被吸纳进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当中,成为冷酷无情的计算工具。价值通约主义背后的人性假设设定了人的伦理道德的边界,从而使出版伦理降格为一般经济伦理:公平竞争和按物质要素或劳动价值(以时间衡量的)等价交换。
“资本力量把人类生活世界货币化了,价值通约主义的盛行必然带来伦理道德的下滑及丧失”[16]。这使义利观发生变化,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只要在有形规范(法)的许可内便肆无忌惮,而对无形规范(道德)视而不见。人的“经济人”化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三)物质主义导致出版主客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增生
1.出版者及营销人员为追求物质利益而追求过度符号价值,刺激文化消费主义的发育。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在于创造价值链供给。“现代社会体现出的资本逻辑,表现出追求利润的典型特征”[17]。出版企业及营销中间商追求利润是企业化运作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为实现图书商品的价值,刺激消费成为出版商和经销商的首要任务。文化消费主义顺势而生,消费的等级性和符号化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奇观[18]。为广义虚拟化的景观社会设置铺垫的,是物质主义在符号化进程中必然要采用的手段,对品牌化和包装符号的重视。激活消费者的欲望,营造文化消费的氛围成为出版物营销的策略。图书“品牌热量”被等价于注意力强弱,等价于事件消费的诱惑力[19]。出版物在启蒙、美育和“化人”上的功能被弱化,物质性堆砌及其外在包装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砝码。
2.作者为追求物质利益而采取欺骗行为。参与到出版伦理境域的还包括图书作者。作者在版权转让上拥有的利益索取权在资本逻辑下得到扩大。为了获得更大利益回报,作者存在参与数据欺骗、身份欺骗、事件欺骗的可能。传播学术观点和思想文化、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作者身份”被类似于“股权身份”的角色所控制。而出版经营方对作者的欺骗性行为采取默许的态度,甚至鼓励其运用包装技巧为其作品进行粉饰。相对而言,消费者(读者)则处于“无知之幕”的遮蔽下,在对书刊进行消费之前,所能获得的外在表意符号决定了他们的消费决策。这时,商业性的“密谋”对市场交易的公开透明和相互信用无疑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出版生产经营方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资本的野蛮本性。物质主义盛行,使精神生产沦落为它的外壳(物质符号生产)而丧失人文价值。
经济个人主义、价值通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使出版市场鱼龙混杂,出版伦理受到威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资本逻辑所能起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然而也必然需要有形约束(法)和无形约束(道德)的双重宰制才能使出版市场进入良序发展的轨道。
三、出版伦理对资本逻辑的规约及其影响
伦理道德是社会生活的无形约束体系,它依靠舆论监督和道德规范的内化而起作用。出版伦理包括出版制度伦理和出版行为伦理,是对出版运营所涉各方的道德规范和美善原则。在出版社企业化走向深入发展阶段,资本逻辑的弊病已露端倪,减少出版业资本逻辑形成的负面影响,有必要构建基于市场德性的出版伦理,以规范出版市场和维护各方利益。胡虹霞把出版伦理分为“出版的伦理”和“伦理的出版”,前者是指“出版实践本身的道德合理性,它是一种公共性、导向性、教化性、职业性的伦理”,后者是指“出版行为应遵循的道德秩序和伦理准则,包括出版自由、出版义务、出版良心、出版公正和出版诚信”[20]。出版业的价值观念体系与伦理道德规范是出版伦理的重要内容。
(一)出版价值观念体系对资本逻辑的约束
出版价值观念体系是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并内化于心的思想意识,是出版人及相关经营管理者、消费者及其他参与者对出版实践和出版物有用性的认同。出版价值观念体系的嬗变根源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出版实践。
1.现实出版价值观念体系源于出版实践改革。任何思想观念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出版价值观念体系的嬗变是在出版社企业化进程中,与社会时局保持相对稳定联系的必然结果。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市场经济以它的客观经济效益决定竞争参与者的前景。出版社市场化跟进了这种一般的社会物质活动,精神生产物化为经济生产,社会效益通约为货币价值。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出版业竞相发育。书刊编辑伦理、书刊流通伦理和文化消费伦理集合并转化为商业伦理。出版价值观念体系被经济效益(金钱、关注度、销售排行榜)绑架,从而“制造公器以谋私利”成为一种异化状态的现实价值观念。图书商品作为流通进公共市场的利器而成为获取利润的手段,而公共性、导向性、教化性、职业性的旨趣被轻视。将(出好书的)目的作为(赚好钱的)手段,在伦理上是一种精神与物质的颠倒状态(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赚好钱”的手段是为了“出好书”的目的)。
2.现实出版价值观念体系反作用于出版实践改革。“恩格斯‘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的科学论断,深刻阐明了思想要转化为现实,变为物质力量,就要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必须反映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21]。出版价值观念体系的更新只有被出版人及营销方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这就需要厘清2个问题:(1)需要构建怎样的出版价值观念体系;(2)这种价值观念体系通达出版实践的桥梁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可以从“制造公器以谋公利”的角度来探讨,从原则高度来看,图书出版经营应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因而出版价值观念体系一般从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并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和立世理念。对第二个问题,只有进入到道德心理学的发生机制,创造客观激励机制才能使出版价值观念内化于心。仅靠精神教化是难以达到“内心信仰、坚定执行”的效果。
适应市场机制的出版价值观念体系的构建任务是紧迫而艰巨的,但仍然是出版伦理对资本逻辑造成的后果起限制作用的重要方面。
(二)出版道德规范对资本逻辑效力的约束
出版道德规范包括编辑、作者、审稿人、图书经销商的职业道德标准,以及与出版实践活动相关的其他行为规范。一般而言,“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出版活动的有形约束性条款,而此处所讲的“道德”仅限依靠人们自觉遵守和舆论监督而形成的无形约束性因素。出版道德规范对资本逻辑效力的约束主要通过2种途径实现:出版行业基本伦理规范的制度化和道德行为的激励机制。
1.出版行业基本伦理规范的制度化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抑制资本逻辑的肆行。厉以宁教授说:“我们的社会有3种调节方式。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靠一只无形的手来支配资源的配置。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靠政策、法规、法律起调节作用,这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22]他认为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使市场在非交易领域中无法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就算在市场起作用的经济领域,信用体系的建立就必须依靠道德调节发挥作用。出版伦理规范是在社会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只有将这种自发形成的规范落实为自觉的制度设计,才能在出版实践中有章可循。如“出版良心”,它是指出版者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内在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如果不将其具体分解为要素化的行为规则,单纯靠内心信仰是难以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对资本逻辑的道德蚀力起抵抗作用的。将出版伦理的一般原则制度化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能脱离伦理准则的抽象性,并加强伦理意向的执行力度。
2.道德行为激励机制促进出版相关方对经济效益的正确取舍。道德行为的奖励能够强化行为者的自觉性和荣耀感,从而对社会秩序起到引导作用。相反,悖德行为的惩处能够对行为者起到警示作用,而对其他人起到诫勉醒示的功效。出版相关方无论在书稿撰写、图书编辑、审校还是发行环节,都应当使伦理激励措施介入其中。尤其是在资本逻辑施展它增值的强力之时,道德激励机制能够在人们面对物质诱惑之际,被更高层次的内心需求所约束。马斯诺是从人的需要等级来说明人对更高层次的需求的向往要强于较低层次的需求,而资本逻辑展开的结果所能提供给人们的,除了物质财富之外,别无他物。出版伦理激励机制的设定就是为了让出版相关方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金钱与信誉等存在冲突的时候学会取舍。
总之,出版道德规范的制度化趋势是为了在出版运营过程遭遇资本自身的扩张逻辑时能够有所作为,从而维护出版企业和利益相关方的独特社会价值和自身利益。
四、资本逻辑与出版伦理融合的现实途径
如前所述,出版社企业化使出版行业进入市场逻辑,资本自我扩张和增值的内在逻辑力量席卷一切,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对出版伦理形成挑战。出版行业的产品特殊性决定其伦理规范不同于一般的经济伦理,在公平交易、效率优先等一般经济伦理之外,还有公共性、导向性、教化性、职业性的旨趣,以及在出版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信用、公开、良心和正义等。弥合资本逻辑与出版伦理之间的隔阂,是建设社会主义出版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为此就要实现“出版伦理资本化”和“出版资本伦理化”,并使二者交互作用。
(一)出版伦理资本化
出版伦理资本化是指在出版实践中,伦理性投入的大小在人们获得利益索取权上起到正相关作用。“出版伦理资本化”不等于“伦理关系资本化”,前者更多体现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奖励机制,而后者则会恶化人际关系,导致道德滑坡。资本的本性是通过构建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带来自身价值的增值,出版伦理的资本化就是要构建更加符合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所需的运营秩序,以便获得基于道德口碑的超额利润。由此可见,出版伦理资本化的实现路径有2个方面:(1)“道德收益”,就是通过使出版运营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从而获得来自公共管理部门的奖励性赞助,同时亦获得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2)“伦理要素化”,即在出版管理部门设置伦理审查专门机构,拟定相应制度,从而使伦理因素成为出版生产的前提性要素,这就在源头控制了不道德的出版行为。
(二)出版资本伦理化
资本具有本质层面的伦理劣根性,它对操作层面的伦理建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但资本并非妖魔,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本才能变脸为魔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资本伦理化存在如下可能条件:(1)经济个人主义受到限制;(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前提。挖掘资本自身蕴含的伦理属性,限制资本本性的恶性发展,有利于出版资本校准角色意识,调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为此,就必须从2个方面搭建出版资本伦理化的转化:(1)“资本的人本约束”,即将资本逻辑纳入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中,使资本逻辑隶属于人的发展逻辑,而不是相反;(2)把被颠倒的手段与目的关系再颠倒,“出好书”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出版资本的目的性存在根据,而资本自我增值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目的性根据。现实生活中被颠倒的目的与手段关系经过再颠倒,从而适应社会主义出版行业发展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唐砥中.谈谈出版社的性质[J].出版与发行,1985(2):27-28.
[2]金仲萍.出版社经营管理的含义和特点[J].出版发行研究,1988(1):49-52.
[3]陈志强.出版改革如何深化[J].出版工作,1988(2):10-13.
[4]石峰.企业化是出版社改革的方向[J].出版工作,1989(3):52-54.
[5]张训智.论出版社的性质[J].出版工作,1989(9):16-22.
[6]李果.浅论出版社的“双效益”目标管理[J].甘肃社会科学,1991(4):118-120.
[7]石峰.关于转变观念深化出版改革的思考[J].瞭望周刊,1992(50):30-31.
[8]王仿子.出版社是企业,又不同于工业企业[J].出版发行研究,1992(4):54-55.
[9]徐方.出版企业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J].出版科学,1994(4):22-23.
[10]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59.
[11]栾文莲.全球的脉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51.
[12]覃志红.马克思总体生产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7.
[13]李希光,毛伟.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闻媒体发展困局[J].青年记者,2015(21):12-13.
[14]邓宏图.马克思“三论”与制度变迁——一个有关中国转轨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5):20-30.
[15]刘梅.马克思“资本主体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0.
[16]张斌.麦当劳文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特质解读[J].现代经济探讨,2011(12):81-84.
[17]韩秋红.现代性的迷思与真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17.
[18]何华征.新媒体时代的娱乐文化及其生存论警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6(1):183-189.
[19]何华征.论新媒体时代经济的广义虚拟化及其实现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15(2):34-38.
[20]胡虹霞.出版的伦理与伦理的出版[J].编辑之友,2013(12):39-41.
[21]徐琳.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94.
[22]厉以宁.道德调节市场的力量[J].资本市场,2014(7):9.
(责任编辑:何晓丽)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publishing ethics
HE Hua-zheng
(CollegeofMarxism,ZunyiNormalUniversity,Zunyi,Guizhou563002,China)
Abstract:The enterprises of publishing house make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enter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 logic. On the one h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in facilitating the publication of fre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a series of negative effects, those are the publishing ethics challenges of individualism, 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 and materialism. Freedom, justice, credit, conscience and other publishing ethical principles in the moral hazard brought by market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shing ethics has not lost its subjective value in practice. Its restriction of capital logic may enable publishing market to enter the well ordered development, may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lead to the failure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so that the vitality of the market economy is depressed. Therefore, it is very urgent to construct a kind of capital logic of "ethics restriction", and to make the capital logic from the subjectivity restric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control.
Key words:capital logic; publication ethics; value commensuration doctrine
[收稿日期]2016-03-21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SH008)。
[作者简介]何华征(1977-),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哲学、媒介哲学。
[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22(2016)03-00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