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堂吉诃德请到中国来
2016-12-14杨恒达
杨恒达
今年是伟大的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他笔下的不朽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始终活在世界各国人们的心中。在中国,他更是同中国文化相结合,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令人难忘。其实,塞万提斯甚至早就预言了堂吉诃德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包括在中国成立的塞万提斯学院之类的机构,也早已出现在他的预言之中:“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卷)献辞》)虽说塞万提斯不过是说笑而已,但毕竟他想到过他的堂吉诃德要来到中国,而且在中国的接受非同一般。现在看来,他终于心想事成,尽管把堂吉诃德请去的并非中国的大皇帝。
相比于西方一些著名文学作品,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流传到中国要略晚一些,但是一经流传到中国,其影响就经久不衰。其主人公瘦高的个子,穿一身骑士盔甲,头顶一个破铜盆,手持长枪盾牌,骑在一匹驽马上,旁边有一矮胖的农夫骑在一头低矮的毛驴上陪伴他,这形象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堂吉诃德》翻译的版本之多,也非大多数外国文学作品可比。
鲁迅(1881—1936)和他胞弟周作人(1885—1967)属于我国最早对《堂吉诃德》发生兴趣的学者。早在大约1908年,他们兄弟俩在日本时,就为得到了一本德文本的《堂吉诃德》而兴奋不已。周作人甚至说,这部作品是他“很喜欢的书的一种”,于他“比《水浒》还要亲近”。(周作人:“塞文狄斯”,《自己的园地》)在1918年发表的一本教科书《欧洲文学史》中就描述了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强调了这个人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颇在意于他的信仰与理想。周作人在“五四”期间宣传的新村运动被认为就带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色彩。鲁迅则约郁达夫(1896—1945)为他们合编的《奔流》刊物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文章“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说:“Turgenjew(屠格涅夫)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Don Quixote type(堂吉诃德式)’,来和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Hamlet(哈姆雷特)相对照。”(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鲁迅按照屠格涅夫的观点,把堂吉诃德解释为一个在理想驱使下积极进取的人。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1899—1935)一起翻译过当时苏联的教育家、文学家、政治活动家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在后记中说:“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这是对堂吉诃德本身的评价,但是由于卢那察尔斯基将堂吉诃德这个形象用来适应当时苏联的革命形势和他本人的思想倾向,剧本中的堂吉诃德被塑造成一个政治上糊涂的人道主义者,“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帮着使世界留在黑暗中”。虽然这是对经过改编的堂吉诃德的评价,但是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思想倾向是和卢那察尔斯基一致的,试图从政治角度来评价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吉诃德主义的缺点。但是,鲁迅毕竟认为堂吉诃德虽傻却仍是老实人,他对堂吉诃德精神的认可,竟然使他自己也被称为“同风车格斗的Don Quixote”(李初黎,《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遭到创造社、太阳社一帮年轻作家的攻击。他在《真假堂吉诃德》一文中称堂吉诃德为“戆大”,但又说“他其实是十分老实的书呆子”,他借堂吉诃德来批判那些装疯卖傻却自以为很革命的人:“真堂吉訶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堂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鲁迅,《真假堂吉诃德》,《鲁迅全集》)鲁迅对堂吉诃德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堂吉诃德这个形象进入中国初年,中国进步知识界对他的普遍看法。对鲁迅、周作人及其与堂吉诃德的关系深有研究的学者钱理群指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堂吉诃德的看法为后来堂吉诃德精神的大发扬做了铺垫。后来,抗日的烽火燃起,杂文家唐弢写出了《吉诃德颂》,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为被世人认为可笑的堂吉诃德翻案,认为堂吉诃德是一个光荣的名称,强调堂吉诃德精神的战斗鼓舞作用。钱理群进一步指出,“这确实是一个堂吉诃德精神大发扬的时代。许多怀着中国将在这场战争中发生根本蜕变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第一线的热血青年都自称为‘堂吉诃德’或‘吉诃德先生的门徒’。他们也确实不愧为那位西班牙骑士的东方精神兄弟,他们把堂吉诃德由幻想激发起来的不可遏制的热情,不屈不挠的意志,完全忘我的牺牲精神,都发挥到了极致。”(钱理群,《丰富的痛苦》)
1955年,中国政府出面组织了纪念塞万提斯不朽作品《堂吉诃德》(上卷)诞生350周年的活动,肯定了这部作品的人文价值。中国学术界由此而形成了对堂吉诃德比较一致的评价趋向,强调这部作品通过堂吉诃德这个形象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强调他坚持社会正义和高尚理想,也指出他理想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倾向及其同现实的距离。在艺术上,这个形象被认为其中所包含的美学上两个对立概念因奇特的结合而产生强烈审美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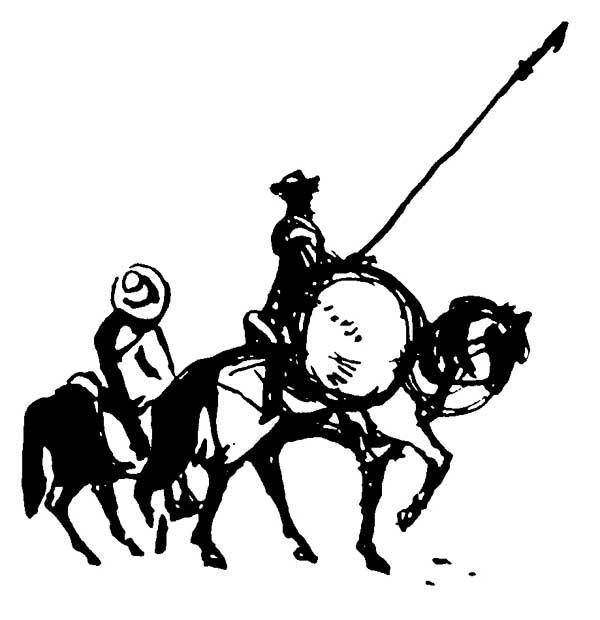
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在中国的接受,也由于1957年以来苏联、西班牙拍摄的关于堂吉诃德的多部故事片及一部卡通片的上演而多次出现高潮。2010年,中国有一群年轻人拍摄了一部后现代式的短片,叫作《堂吉诃德们》,除了片名和堂吉诃德有关,其他毫无关系,展示的完全是中国的事情,但是仔细想想,片中年轻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就是对《堂吉诃德》的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演绎吗?这也可以看作新一代中国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对堂吉诃德的接受。1977年以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过中国画家周有武(1941—)、雷时圣(1939—)、罗盘(1927—2005)等人画的连环画《唐吉诃德》,在中国少年儿童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这个形象在广大中国孩子的心中扎了根。今年在绘画界,上海的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图书馆为纪念西班牙文化名人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并庆祝塞万提斯学院成立25周年,举办了“堂吉诃德在中国”的绘画大赛,通过艺术审美来加强年轻人对堂吉诃德接受中的审美情趣。1965年首演于百老汇的音乐剧《我,堂吉诃德》经多年成功上演之后,于2012年由七幕人生音乐剧团队独家引进,走上中国舞台,经过两轮60场的演出,大获成功。2015年,《我,堂吉诃德》又在《堂吉诃德》(上卷)诞生400周年之际进行了中文版的制作,在上海连演18场,到今年,又继续在北京、上海演出。该剧以“戏中戏”的形式将作者塞万提斯的经历与其作品《堂吉诃德》融为一体,为中国观众更深入全面地接受堂吉诃德及其作者做了出色的引导,再加上音乐的效果,又将这种接受推向更完美的艺术境地。
翻译是对外国作品的接受的一个重要方面。《堂吉诃德》在中国最早由不懂外文的林纾(1852—1924)于1922年在陈家麟的帮助下用文言文翻译了其中的第一部分,并有删节,取名《魔侠传》。在30年代,《堂吉诃德》的翻译版本竟达四个之多:开明书店的贺玉波(1896—1982)译本(1931),世界书局的蒋瑞青(生卒年不详)节译本(1933),上海启明书局的温达之(生卒年不详)译本(1937),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傅东华(1893—1971)译本(1939)。此外还有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汪倜然(1906—1988)编写的该写本(1934)。傅东华翻译的《堂吉诃德》后来在1959年至1962年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全二册带有精美插图的版本。至此为止,所有译本均非直接译自西班牙语原文。
杨绛女士(1911—2016)一直喜爱《堂吉诃德》这部作品,后来一位中宣部的领导请她翻译这部纳入国家翻译计划的作品,她欣然接受。但她认为,要译好这部作品,她必须首先学好西班牙语。于是她自1959年起,从零起点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凭着她已有的英法两门外语的基础,她的西班牙语水平提高很快,到1962年她已有把握进行文字翻译了,就开始《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到1966年已完成了大部分的翻译工作,但不久后译稿不幸丢失,虽然后来失而复得,她还是决定从头再来,终于在1976年秋冬大功告成。她的译作不仅畅销,而且还成为她送给到访的西班牙国王、王后的礼物。虽然有人批评杨绛的译文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是她以古白话小说风格翻译的这部作品,其如此挥洒自如、娓娓道来的优美文笔,却无人能比。尤其,这種古白话小说风格正是中国人接受《堂吉诃德》一类作品的最佳土壤,一旦作品植入其中,很自然地就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和接受。所以,杨绛的翻译对《堂吉诃德》在中国的接受有着独特的贡献。
在杨绛译作大获成功的同时,我国又出现了一大批《堂吉诃德》的译文。其中董燕生(1937—)、孙家孟(1934—2013)、屠孟超(1935—)、张广森(1938—)大多是学习西班牙语的科班出身,都是教授西班牙语的大学教授,他们在翻译《堂吉诃德》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对译文精确度和文笔的严格要求。他们都对我国读者解读和接受堂吉诃德这个形象作出了贡献。
我国读者对堂吉诃德别具一格的接受,与对作品的出色翻译和介绍有关,也跟我国的文化土壤有关。从鲁迅笔下产生阿Q的形象并非偶然,中国文化土壤中滋生出阿Q的那种“精神胜利法”,人们很快会联想到堂吉诃德总是生活在骑士的幻想和骑士信条可以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胜利幻觉中。但是,按照钱理群的说法,堂吉诃德精神包含两个侧面,一方面是对于超越现实的理想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堂吉诃德显然存在着精神的迷乱。“鲁迅将堂吉诃德精神的这一消极面,加以突出、强化,把堂吉诃德式的精神迷乱视为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麻醉剂,这样的严峻批判态度,是由于他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一种痛苦体验与深刻观察,更是出于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与巨大热情。作为一个自觉的启蒙战士,鲁迅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部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部排斥’……”(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在阿Q身上,鲁迅夸大了堂吉诃德式的弱点,目的是和真正的吉诃德精神进行对照,还是要中国人在国民性改造中接受堂吉诃德这个老实人。
中国人对堂吉诃德的接受的真正土壤,还在于中国的儒家文化。虽然堂吉诃德的出现是要扫除风靡一时的骑士小说,但是堂吉诃德所遵循的骑士精神、所恪守的骑士准则,却反映出骑士所追求的平等和正义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对欧洲读者,也对中国读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堂吉诃德的理想和行为准则很像中国儒家提倡的义字当头的君子理想。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堂吉诃德的道德理想,他对正义的追求,触动了恪守君子准则、义字当头的中国人的心弦。中国人在孔子的道德理想和侠客的行为准则中理想化了他们对义的爱好。在武侠小说中,所有的武侠行为都像君子,他们代表了对义的追求。无论是堂吉诃德走遍天下、打抱不平的骑士精神,还是中国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其实都是一种社会正义理想的追求,所以说,堂吉诃德在中国受到独特的、非同凡响的接受,是因为他在中国找到了理想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