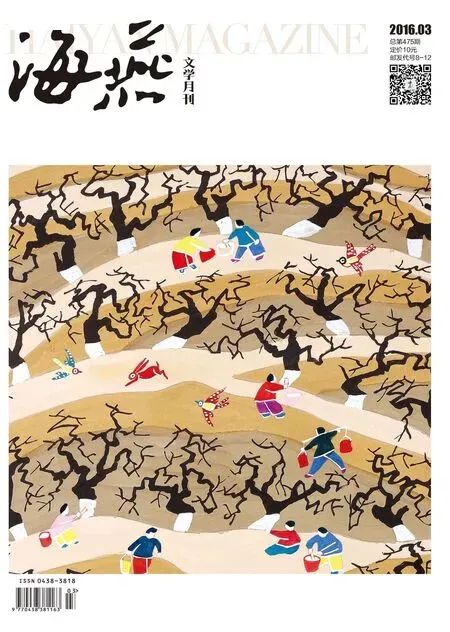一只不愿出窝的飞虫(外一篇)
2016-12-08成兆文
□成兆文
一只不愿出窝的飞虫(外一篇)
□成兆文
冬日凛冽,本应是万物冬蛰的时候。当冷气自北而来,到处是躲藏寒流而瑟瑟发抖的人群,电热毯、暖手宝的厂家以及卖无烟炭的小贩们几天之内赚满钵。城市的屋内随之而安静,夏日顽强爬过纱窗的飞虫们都销声匿迹了。没过几天,暖气进屋,屋外寒气愈加逼人,屋内俨然春天又来。
灯光渐起,不知什么时候,一只飞虫又在屋内翩然漫游了。我正在盯着电脑屏敲击无望的文字,搜肠刮肚的几百字,刚得意洋洋发出去,就被微信抢红包的洪流淹没。这时候,不知从哪里闯入的一只飞虫,在我的眼前飞晃,令我无法安宁。
如果是早年,我会寻找驱蝇的拍子,到处追逐这个空中小姐。年华渐长,知道万物各自有性,人不必自寻烦恼,也就只能采取温柔请走的措施。记得数年前访学京华,和我同一学府研修的有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德,当我造访时他正挪动高大的身躯,打开窗子,卖力驱赶几只闷声闷气的蚊子。我自作聪明,隔天给他送去一只精致的塑料蝇拍,让他不用灭虫剂就能惩罚那些骚扰不停的飞虫。长者笑呵呵说:“不用不用,赶不出去就随它们去,何必动用刀戈?”我愧然而退。
飞虫继续它的漫游,它一定是搞错了季节,以为这是万物复苏的春天吧,它在空中得意地划出弧线,俨然,这寓所是它的后花园。我掀纱,开窗,想让它自觉而退。顺手捡起匍匐在地上的一张报纸,那上面有我上个月发表的文字,赚取过一百元的稿费。我卷起报纸,吓唬那空中快速移动的弧线,示意它赶紧离开。生命不易,我虽无缘成为走起路来到处躲闪蚂蚁的圣人,也不想做一个滥杀无辜、心肠很硬的恶人。
飞虫来到暖房,俨然是出了窝,估计它正准备拥抱整个春天呢。
众生平等,生死转化的大权有时候就在懵懵懂懂的人手里。记得小时候,胡子雪白的祖父曾教导我,无论怎样,春刚来的日子里,既不能随便折断花木,也不要脚踩野虫。我问爷爷为何,祖父说,不知道啊,反正他家的老人一直这样要求着、流传着。成人后,读到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的趣事,讲他曾严厉训斥春天折柳枝的皇子,忽然心有所动。老家客居京华的一位宿儒,在我造访期间,常讲他小时候家里缺柴火,却不去砍关山密林的故事,他说传统的国人有敬畏在心中。
这只飞虫从客厅飞进了书房,我关门,开窗,将窗户尽可能张大,一股初冬的寒流扑面而来。我挥舞报纸,也在空中胡乱划着弧线。飞虫不为所动,就是不到窗口去。门外的妻子笑呵呵说,你的灯光这么亮,如何赶得了虫子?我旋即熄灯,远处万家灯火如星光闪烁,瞬间有置身星汉的错觉。然而,屋里也随之一片安静,飞虫与夜色一同静谧。我只好重新亮灯,灯光一起,飞虫就又开始它误把严冬当早春的旅行。它飞箭一般飞向窗口,然后无影无踪。我关窗、挪纱,心神不宁,思忖自己,究竟是不愿杀生还是嫌弃那飞虫弄脏了我的报纸。
人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十多年前,我曾在兰大门口遇到一名衣衫褴褛的老大爷,他说从遥远的外省乡下来,找工地干活的儿子,儿子没找到,钱也花光了,请求我给他一元钱买馍吃。我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块三毛钱放到他满是风霜的手中,自然得到一番千恩万谢。半个月后,在相同的地点又遇到此人,所不同的是,他把原话说给了我身旁开电脑店的友人。那一身崭新的友人展开钱夹,就要抽出一张百元大钞。我毫不留情地说这是一个职业骗子,何必同情?友人立止。那老人满脸愤懑,教训我说,社会完了,我自己想法子要点钱有何不可?我竟然一时语塞。
如果万物平等,生死是否也是万物转换的一种?行善者食素,但任何食物在显微镜下都有着无数的生命。看见电视上急速奔跑的可爱麋鹿,成为快如闪电猎豹的爪下猎物时,既有目不忍视的残酷感,又目睹生存竞争中爆发的强烈动感与激情,产生莫名其妙的快感。相信有此感者众多,否则,曾经主持《动物世界》相貌平平的赵忠祥不会变得家喻户晓。
我已准备继续自己敲击键盘的事业,飞虫不知又在何处升起,在房间中急速乱飞。它显然意识到了危险,但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甚至无法领会我的好意。妻子一边在努力寻找蝇拍,一边说我知道飞虫为何不出屋的原因了。我没问,只告诉她蝇拍早已扔掉。话虽如此,但已经失去了刚才的从容。我要尽快结束这个战斗,手头还有一大堆活需要干呢。看到飞虫在透明的玻璃窗上停歇,我顾不得许多,直接将报纸卷成一只棍子,急速砸下去……报纸掉落在地,我换回一片安宁。
善待万物是多么美好的理念!可惜,每个人都长着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巴,需要能量的输入,并且不断制造垃圾,这就使得自己总是万物的首席成员。女儿两岁多的时候,我带她到老家去玩,她抓起布袋中的小麦,高兴地撒到院子里。我厉声制止,她的祖父祖母笑呵呵地说:“让娃玩吧,娃的眼里这就是沙子嘛。”我也曾大声呵斥从门外带回一只母狗的点点,吓得点点躲到后院里不敢出来。如今,我的女儿时不时会教育我要爱护环境,不能随手乱扔纸屑,她甚至对我早上下楼重重的脚步声都提出抗议,说同单元中许多人还没有睡醒呢。老家那可爱的狗狗点点,在前年永远失踪了。十年间,它给孩子们留下许多无法忘怀的美好记忆。多年前,我曾与一位宗教上师对话,说佛教舍身饲虎故事中王子自身生命谁来负责,老虎活过来再去吃人怎么办?上师笑呵呵说人只能干自己认为善的,但不能完全期待善念就带来善果。这话引发我长时间的沉思,以至于看到蚊子落到自己胳臂上,贪婪吸食自己鲜血的时候,犹豫是否需要将其拍死。
人力可以局部改变季节,在严冬中让满屋春天。飞虫在躲避危险的时候,自然会动用自己的感官,向往春天是本能,危险让它躲避,适宜的温度又让它重新回到危险当中。就像聪明的人类知道那透光的玻璃,但飞虫会永远向着玻璃外的光亮作无谓的挣扎。这样说,每一种生灵都活在自己的经验里,经验的局限就是那不可抗拒的天命。因此,救了蛇的农夫,被从冻僵中苏醒过来的蛇咬了一口,有人看到了对毒蛇不能有丝毫怜悯之心,也有人说,是否有毒是蛇的天性,而救不救它是我的事情。人眼观之,飞虫卑微甚至丑陋,但也许在它的同类中颇受欢迎。飞虫眼里,人一定是庞然大物,人的手中,自己可以对飞虫行使生杀大权。然而,在另外更高智慧、更高时空维度的生命体眼里,人不就是拘囿于经验、盲目乱动的飞虫吗?飞虫是不愿出窝还是出不了窝?思绪时断时连,睡意早已朦胧。
今早,东边的窗户上升起那血红的太阳,朦胧的云雾将半醒的城市装点成空中仙境。我打开窗,想呼吸一下外面清新的空气。不知那只飞虫在何处埋伏,它振翅如箭,毫不犹豫地扑向无边无际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