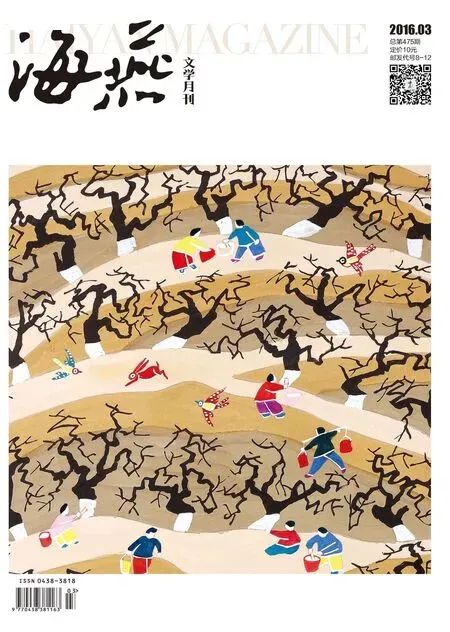母亲·父亲和招魂
2016-12-08
母亲·父亲和招魂
母亲的去世意味着人生最原始的开始失去了支点,人生只剩下向前奔跑!
一
九年来,有关母亲的许许多多都被我们刻意压抑,尽量不去触碰,因为任何扰动都会是溅起沉积多年的心灵之暗潮,那扰动,几乎让我们任何人无法承受。
作为指腹为婚的娃娃亲,父母正式订婚是在他们各自只有两三岁的时候。从不到十七岁就嫁给父亲算起,母亲四十多年来的生活可以用“忙碌”概括。
父亲有很多奇思妙想,母亲心灵手巧,但生活一直波澜不惊,我们私底下以为自己的父母亲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人。直到成人后我们才意识到,健康成长的弟兄姊妹就是他们非凡的作品。
十二年前,女儿的降生带来了许多乐趣,初为人父也让我从此明白为父母者之艰辛。因而,我和兄姊开始常常感叹养育六个孩子之不易,对父母的感情一下子倍增。
然而,没有多久,在几乎毫无预兆的境遇下,母亲病倒了。那年我三十而立,母亲才五十五岁。
为了给母亲治病,我和妻子联系了省城最好的医院,成功进行手术后,我们曾经幻想病魔已经被彻底击退,至少,上苍将再留给我们母亲十年的时光。
要知道,我们才刚刚懂得什么叫孝顺。
为了减轻化疗带来的痛苦,我一下子学会了打针。
母亲说,我的手很轻,打针几乎毫无感觉。
要知道,我过去手脚笨拙缺乏灵气,在兄姊的呵护下,除学习之外,我几乎不会干别的活计。
大病初愈,母亲执意要替我们照看女儿。两岁多的孩子正是顽皮好动的时候,如风一样到处乱跑,母亲便扔掉数十年的文雅,跟着到处追随,生怕小孙女不小心摔倒。在母亲呵护的那段时间,女儿几乎是横行霸道的小公主,从来没有任何人敢重言语呵斥女儿,想来,那应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两年半后,母亲旧病复发。家庭一片沉重。
那是九年前的国庆节,二哥和我陪脸色焦黄的母亲到庄浪县医院复查。一位略上年纪的医生看完B超后说这是普通的胆结石,需要静养,转身又小声而严肃地告诉我们弟兄,我们的母亲很难熬过年底了。
我们努力宽慰家人。第二天我们还要各奔东西,那是母亲最后一次送我出门,她站在老家门口向我们挥手,神情困倦而留恋。告别母亲回省城的车上,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奔涌……
那时的悲伤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妻默默拭去我的泪珠,女儿一遍又一遍问:“爸爸怎么了?爸爸怎么了?”
父亲遍访风水高人,算卦祈禳。长兄到处打听民间秘方,曾经很细心地将刺猬皮烘干,用石臼砸成细末,给母亲止血。二兄、二嫂高价从外省购买松花粉,据说能有益于母亲的健康。大嫂、二姐和小妹更是不离病榻半步,精心伺候母亲。大姐适逢婚姻变故,曾愤而出走,但不放心母亲,从远方又赶回来,俯身在母亲面前。我和妻子踏遍全省多个著名的医院,拜访名气很大的医生,购买营养药品和秘制药丸带给母亲。
然而,母亲还是没有熬过那年严冬,在九年前的今天,那个飘雪的日子永别我们而去。
当她停止了呼吸后,我强忍泪水,抱着母亲。母亲双手开始松弛,体温尚存,那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温度。
母亲最后的泪滴从眼角慢慢溢出,我轻轻擦拭,然后和家人轻轻地把轻轻的母亲转移到地上。母亲神态安详,就像睡去的样子。
我们在草铺里日夜伴随母亲。当五天后送别母亲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世界为我永远封闭了,生命而出的支点没有了。就在黄土永隔黑暗的那个瞬间,我忍不住向母亲表达做儿子的无能与愧疚,没有将母亲留在我们的生活里。
母亲知道我们大家都尽力了,她没有怨言,也似乎没有遗憾。
但没有了母亲的庇护,我们的世界一下子失重。
我不知道我所谓追寻人生真相的活动意义何在。
那时,我仍然执着于生死的名相,深深沉浸于失去母亲的悲伤中难以自拔。
二
我在九岁的夏天掉到数丈高悬崖下面差点丧命,身体稍好后,是母亲拿了新做的糜子笤帚扫路,一遍遍呼唤我的名字,让我回家。那就是中国民间流传的招魂。
母亲走后,我失了魂,很长时间觉得人生虚无。
再也没有人那样热烈而温情地呼唤我回家。
妻子说我从此判若两人。
然而,最悲伤的还是头发苍白的父亲。
母亲去世后,最苦的不是我们儿女,而是突然苍老了的父亲。父亲说,即使祖母去世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如此伤心过。
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悲伤之后,都还有另外的安慰。当我哭得最悲伤的时候,是妻子替我擦干了泪水,而三四岁的女儿取笑我说:“爸爸的黑眼窝像张飞!”
只有那一夜之间苍老了的父亲,在晚间的时候显示出格外的苍凉与落寞来。
儿女们长大了,有了各自的家庭,而父亲的世界从此破碎。
父母感情甚笃,往日的幸福时光此时变成了痛苦的源泉。
我们都很悲伤,但最无力安慰的是才过中年的父亲。
我彻底丧失了对自己工作的兴趣,质疑连自己母亲都无法挽留的工作是否值得继续,那种废寝忘食的工作节奏突然间慢了下来。
我知道从此以后家园里没有了母亲,那种熟悉的声音和人世间最亲切最慈祥的面容离我们而去。
父亲年轻时候力气很大,由于子女众多,他不得不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气力。
父亲只会干重体力活,闲了写几笔字,对于家务几乎毫无所知。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段时间蛰居老家,尤其半夜常常醒来发呆。
我们劝慰,而父亲也让我们注意这段时间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失去亲人的时候很容易在工作中出差错,甚至和别人争吵打架。
短暂的消沉后,父亲似乎突然意识到,再美好的幸福都是有限度的,而即使勤勉奋斗也并没有那么痛苦害怕。
父亲要以自己为榜样,把我们带出低落情绪的阴影。
为了鼓励子女,父亲很快学会了打扫卫生干家务,甚至做饭。
二哥据说在家中脾气暴烈,在工作单位变得咄咄逼人。
父亲仍然生活在老家,我第一次向大哥请求,今后如果父亲训斥他,希望他不要再顶撞。果然大哥从此后更加低言顺气,绝不再说“我也是四十多岁了”之类的牢骚话。
二哥生活干净,依然对父亲的生活习惯要求多多,戒烟洗脚,多菜少面,说的次数多了,引得父亲不快,二哥偶有顶撞,他不让父亲觉得自己生活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我理解二哥,但暗暗告诫自己,从此后顺着父亲。
三
我们的共识是不能让父亲清闲下来。
老家莲花峰要立碑,我大包大揽,亲自撰文,组织几十人的全国专家团莅临。活动密集,参与者数以万计。
父亲和镇上几位老者是这个活动的中心人物。
此前,父亲从未参与和组织这么重大的活动,时逢雨季,容不得半点差池。父亲压力巨大,曾在电话中忍不住训斥我为何要干这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我不解释。
那些日子里,父亲召集全镇最有头脑的村老乡贤,几乎昼夜不睡觉策划这次重大活动。
他们个个紧张而兴奋,尤其是父亲,知道儿子给他找的事情,除了勇往直前他别无选择。
从精心策划到具体实施,立碑活动历时一年,后来演变成了万人空巷的狂欢节,那次巨大的成功给父亲带来了久违的笑容。
此后,父亲和他的老哥儿们又幸福地谈论了一年。
隔年,二哥的书法在全国大展中获奖,跻身为有名气的书法家行列,父亲眉毛舒展。
当第三年父亲显得无聊的时候,我们弟兄密谋如何修楼盖房。
数年前,陇东农村修楼房还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
父亲曾经很羡慕别人新修的房子,说人家是“白查查一片”。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年除夕坐夜,最后的话题是修房。
老宅子是几十年前祖父在世的时候修的,过去还算不错,新时代中显得既矮又小,且年久难修,每到雨季,每个屋子都像漏雨的筛子。我们弟兄成家后,每年春节回家,不得不挤在几间很小的房子里。三个儿媳妇进门没有住上新房,这让父母觉得很过意不去。
“你们弟兄都娶的是人梢子,却给人家没有新房住!”父母时不时这样叹息。
母亲病倒前的那一年,当我们夜半打着手电筒用米尺量度老家的院子,你一言我一语议论未来新房样式时,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意。
四年后,这个计划终于付诸实施。
它既是母亲未竟的心愿,又是父亲仍为之奋斗的目标。
传统的房子不但是遮风挡雨的地方,更是心灵的庇护所,是祖业与家势的象征。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陇东人家,把房子看作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衡量某家光阴好的标志是房子,姑娘嫁人看的首要条件也是房子。安土重迁的农垦文明中房子有着形而上的意义。
我们准备修楼房的构想超出了父亲的想象,因为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人敢奢望像城市人一样。
父亲知道家庭收入仍然微薄,知道我们给母亲治病和在城里购房而举债,于心不忍。
但我们放言即使债台高筑也要修起楼房,这是信念,毫不动摇。
父亲看着儿女们憋着一股劲,所以他一展愁云,丝毫也不松劲。
年过六旬的父亲顾不得年轻时劳累过度留下的顽疾,和大哥、二哥一道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楼房的设计、买料中,施工的时候他亲自给施工队当小工,丝毫不觉得疲乏,这让一起干活的年轻人大为惭愧。
乡邻说在您老的手里将办置真正的家业。父亲听了更有精神头了。
从一个冬天到另一个冬天,别致气派的小二楼矗立起来,引来路人的啧啧夸赞。
父亲反而变得淡定,他的兴趣是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练习书法,读读我发表的文章,督促孙子学习。遇到乡邻有事,他会主动帮忙。
父亲比过去变得大度而仁慈。
父亲夏天还要继续驻守桃园,稍有工夫会照看街道上的铺面,他觉得我大哥大嫂太辛苦,能帮一把是一把。
好多乡邻劝他闲游闲转,问他后人们给的大钱花不完吧。父亲笑而不答。
二哥的书法继续蜚声海外。父亲也开始忙着练字,他的书法一改过去的狂躁,书体像二哥,但书气多了一份淡定。父亲还学会了写古体诗,有几首发表在《天水日报》上,编辑打电话直夸父亲的灵感要高于我,这让他洋洋得意。
父亲的身体竟然健朗了。他时不时打电话让我多锻炼,少喝酒,珍惜大好时光。然而他的烟瘾愈发大了,只是,他会把我们带给他的中高档香烟悄悄变卖成价格低廉的“红兰州”,说反正都是冒一股子烟,一条顶三条,何必那么高档。
父亲彻底丢掉了人生即享乐的本能想法,他不再流泪,不再叹息,彻悟了“人生来就是奋斗的”这个朴素道理,在和母亲离别后的岁月中,终于爆发出新的生活热情。
故园依然温暖,只是,我们都无法忘怀母亲。
每次到老家,我都要到母亲的墓地磕头、祈祷!
有好多次是父亲陪着我前往。
今天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用心,九年来的疏懒又让我愧疚。
在母亲的九周年忌日,我写下这篇文章,也算是给自己招魂。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