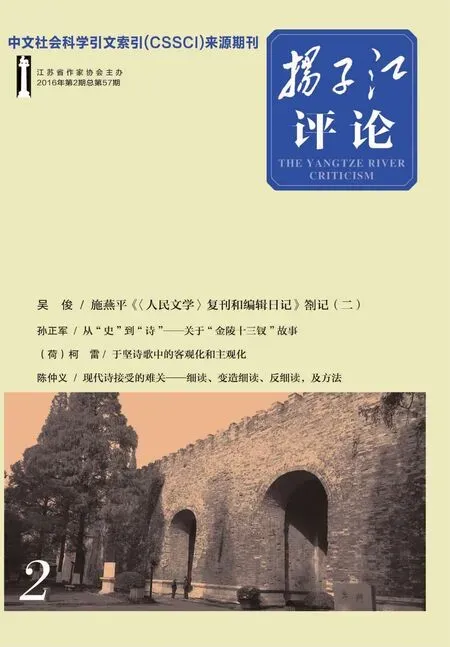从“史”到“诗”——关于“金陵十三钗”故事
2016-12-07孙正军
孙正军
从“史”到“诗”——关于“金陵十三钗”故事
孙正军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约35万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遭到杀害,8万名妇女被日军强奸,其行为残忍至极。“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屠犹”一样,同为“二战”史上的两场浩劫。在欧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如雅斯贝尔斯、汉娜·阿伦特、特奥多·阿多诺、齐格蒙特·鲍曼等,围绕“纳粹屠犹”开展了持续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产生了《奥斯维辛的爱情》《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朗读者》等一批关于“纳粹屠犹”的文艺作品。进而,“欧洲的‘屠犹’逐渐上升到‘二战’历史叙述的中心位置,即‘屠犹’已经形成为一个世界性话语。而与‘犹太大屠杀’一样惨烈的‘南京大屠杀’却在历史的记忆中被遗忘”。①近年来,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与影视创作逐渐升温。
2011年12月,根据严歌苓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在国内上映,一时引起轰动。电影以“姨妈书娟”的视角切入“南京大屠杀”,将“窑姐”们舍身拯救一群年幼无辜唱诗班女学生的故事,演绎成一群风尘女子的生死绝唱。其实,“金陵十三钗”故事是一个由“史”到“诗”演变的结果。
1
在电影与小说《金陵十三钗》产生重大反响之后,严歌苓在谈及小说的创作缘起时,多次提及“金陵十三钗”故事源自《魏特琳日记》。当严歌苓被问及《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女学生、军官以及神父等角色是否根据历史人物“糅合”而成时,她的回答是:“有一点影子的可能就是魏特琳在日记中所提到的她曾经历过的那件事情。魏特琳女士是金陵女子学院的教务长,当时日本兵来到学校说要带走100 多个女孩子,她当时实在没有办法就说,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专门干这种职业的?如果有,就不要让日本人伤害那些良家女孩了。最后,当时避难的20 多个风尘女子站出来了,使那些女学生们没有遭到噩运。我觉得这个挺震撼的,也就把它写进我的小说里了。”②
若仅仅根据严歌苓的表述,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就是出自《魏特琳日记》。但是,在详查《魏特琳日记》之后,我们发现了问题。日记中并无妓女为了拯救唱诗班女童,代替女童赴难的故事。遍查《魏特琳日记》,所能找到的与“金陵十三钗”故事最为相似的记载是1937年12月24日的内容:“12月24日,星期五。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③
将严歌苓口中与笔下的“金陵十三钗”故事,与《魏特琳日记》的记载进行比对,可知二者出入较大。妓女为了拯救唱诗班女童,自愿代女童赴难是严歌苓“金陵十三钗”故事的核心。而《魏特琳日记》中既无唱诗班女童,也无妓女自愿代女童赴难的记载。说“金陵十三钗”的故事源自《魏特琳日记》显然有点勉强。
2011年12月,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之后,随即有媒体报道“《金陵十三钗》很像韩三平的《避难》”④。电影《避难》是由韩三平与周力联合导演,1988年上映的一部影片。二者都有神父收留妓女与伤兵、日军逼要女童、妓女代女童赴难的故事,甚至有人认为“两部电影在故事上的相似度达70%以上”⑤。
两部影片缘何如此相似?原来,小说《金陵十三钗》的作者严歌苓是《避难》的编剧之一,当年参与了《避难》剧本的创作。而《金陵十三钗》可视为严歌苓多年后对《避难》核心故事的再创作,这就不难理解《金陵十三钗》与《避难》如此相似了。
那么,《避难》中妓女赴难拯救女童的故事是否来自《魏特琳日记》?《魏特琳日记》的发掘史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20世纪80年代中期,《魏特琳日记》的原稿才被发现,“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莉( Martha Lund Smalley )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极高的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学者研究使用。1999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从斯茉莉女士处获得魏特琳日记英文原稿的复印件,并立即组织人员对日记进行了整理翻译。”⑥2000年10月,《魏特琳日记》中文译本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说,直到1988年电影《避难》上映时,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还未能向研究者提供《魏特琳日记》的缩微胶卷。可见,《避难》中妓女代女童赴难的故事出自《魏特琳日记》之说更是无从谈起。
严歌苓说“金陵十三钗”故事出自《魏特琳日记》,在事实上造成了对这一故事源头及其发展演变的遮蔽。
2
现在可知,歌女(妓女)舍身拯救女童的故事,最早出自埃德加·斯诺对“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南京传教士书信的记载。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朋友,是当年第一个采访苏区的西方记者。在访问陕北苏区之后,1937年斯诺出版了震动世界的名作《红星照耀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向全世界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报道。斯诺一生著书十一本,此外还有大量的报刊文章。“他一半以上的著述向世人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⑦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1981年,斯诺第二任夫人洛易斯·惠勒根据斯诺生前的著作、书信、笔记等资料,摘录汇编《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斯诺自1928年来到中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段时间内最主要事件的记载与论述。1982年2月,在斯诺逝世十周年之际,中国学术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
《斯诺眼中的中国》第十二章《入侵中国》之《南京的浩劫》一节中,以文字加图片的形式对日本侵略者的“南京大屠杀”罪行进行了记载。其中有段文字就是歌女拯救女童的故事:
美国和英国教会学校的女孩子被抓了出来,送进军中妓院,随后就音信全无了。有一天我从这个地区的一个传教士写的信里,读到一个不寻常的爱国举动。一群歌女来到教会学校与她们的善良的姊妹们一起避难。这位传教士问她们说,有没有人同意去服侍日本人,免得非职业性的女孩子们也受牵连、遭殃。这些歌女同大家一样都憎恨敌人,但是她们全都站了起来。毫无疑问,不管过去她们的德性有什么亏缺,现在的行为是一种补救,而她们中间有些人为此牺牲了生命。据我所知,她们死后并没有得到追认,甚至也没有获得勋章。⑧
通过文中“免得非职业性的女孩子们也受牵连、遭殃”,以及“不管过去她们的德性有什么亏缺,现在的行为是一种补救”的表述,可知文中的歌女实为妓女。将此记载与《魏特琳日记》的内容进行对比,非常明显,《南京的浩劫》中的记载与《避难》《金陵十三钗》中妓女代女童赴难的故事更加相似。《南京的浩劫》才是“金陵十三钗”故事的源头。
《斯诺眼中的中国》是洛易斯·惠勒对斯诺生前著作的摘编,其内容主要来自斯诺生前出版的十一本著作,但《斯诺眼中的中国》未能标明每篇文章的详细出处。1982年之前,大陆仅以《西行漫记》为名,翻译出版了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由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其时“南京大屠杀”还未发生。1984 年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斯诺文集》,收集了斯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中也未见《南京的浩劫》的内容。“从苏区返回北平后,斯诺开始在英美报刊上连续发表他的苏区访问记,引发广泛关注。”⑨作为国际著名记者,斯诺作品的首次发表、出版多在大陆之外。《南京的浩劫》中妓女舍身拯救女童的故事,极有可能在斯诺生前即已发表或出版,其与西方读者见面的时间,远早于1982年《斯诺眼中的中国》在大陆的翻译出版。
斯诺是享誉世界的战地记者,“他的作品文字优美,论理透彻,引人入胜,堪称世界报告文学巨著”⑩。他的文风严谨,史料丰富,并亲身经历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其作品为“非虚构写作”,“史”的特性明显。“斯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史学家。”⑪对于《拉贝日记》与《魏特琳日记》,有论者曾经指出,“从拉贝到魏特林,他们以第三者的眼光,客观记录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景和事件。他们的日记,无疑也是这场人类灾难最有力的证词,使全世界真正确认了这场大屠杀的存在。”⑫抑或这是严歌苓一再强调“金陵十三钗”故事出自《魏特琳日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对于研究日本侵华史,斯诺的作品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一样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斯诺《南京的浩劫》的记载实为“金陵十三钗”故事“史”的源头,“诗”的出处。
3
第一次将歌女舍身拯救女童由“史”的故事演绎为“诗”的作品的是巴蜀作家李贵。李贵根据斯诺《南京的浩劫》的记载创作了长篇小说《金陵歌女》。电影《避难》正是根据《金陵歌女》改编拍摄而成。
1982年2月,《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在大陆翻译出版,歌女为了拯救女童从容赴难的历史故事呈现在国人面前。同年6月,日本发生了篡改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 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⑬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受到了中、朝、韩等亚洲受害国的强烈反对。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们,在歌女拯救女童故事与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的双重影响之下,1984年6月至1986年11月,李贵创作了《金陵歌女》,将斯诺笔下的历史故事演绎成一部长篇小说。1988年2月《金陵歌女》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目前,学界对《金陵歌女》的研究少之又少,这里笔者对小说内容稍作详述: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奸杀抢掠,无恶不作。战乱之中,娱乐场所安乐厅的阿玉、杜秋娘等十二位歌女,逃到圣保罗教堂避难。歌女们的不幸处境,得到了传教士贝尔登的怜悯。贝尔登将歌女们安排在唱诗班女童的宿舍。圣保罗教堂作为上帝殿堂的宁静与纯洁之所,一夜之间就被搅乱。歌女们在圣保罗教堂酗酒、抽烟、打闹。一名女童被歌女们从楼上扔出的酒瓶砸伤,致双方矛盾激化。歌女们的胡作非为使教堂的秩序无法正常维持,贝尔登同情歌女的做法受到了教堂其他人员的指责。通过交往,女童与歌女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得到化解。与此同时是汉奸魏德迈追捕歌女的行为。为了对日军表示友善,汉奸魏德迈与雷孟臣决定举办一个“日中亲善”圣诞舞会,对侵华日军进行慰问。侵华日军师团长谷寿夫点名要阿玉参加圣诞舞会。于是,开始了一场追捕歌女的行动。阿玉在家仇国恨面前誓死不供日本人玩乐。到处搜捕歌女的汉奸通过歌女们典当出去的衣物首饰得知歌女们就隐藏在圣保罗教堂。汉奸来到圣保罗教堂逼迫阿玉参加圣诞舞会。关键时刻,唱诗班女童们巧施一技,用阿玉的衣物首饰坠湖,佯装阿玉投湖自尽,帮助阿玉暂时脱离虎口。为了帮助歌女们逃离汉奸的魔掌,贝尔登设法将歌女们运往杭州的一个“工合组织”。圣诞节前,日军要求圣保罗教堂送十名少女至日本随军服务团。卡洛德院长为了保住自己的教绩,升任教区大教主,便决定把唱诗班的女孩子们献给日军。就在卡洛德即将把女童们交给日本人时,奇迹出现,歌女们抢在女童之前走向日本军车,为了保护唱诗班女童,歌女们放弃了触手可及的自由生活,并未前往杭州,而是代女童们奔向一个没有光的世界。
看过《金陵歌女》的故事梗概,就可知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与此颇有几分相似。
可以十分肯定《金陵歌女》中歌女代女童赴难的故事源自斯诺《南京的浩劫》。《金陵歌女》虚构那位给斯诺写信告诉他歌女们英勇事迹的传教士正是小说中的贝尔登。贝尔登自始至终经历了整个故事,并与阿玉有过一段懵懂的感情。正是《EDGARSNOW’S CHINA》(《斯诺眼中的中国》的英文版本)一书的出版引起贝尔登故地重访的愿望。他“要为那些带着误解和偏见、唾沫和冷眼、屈辱和愤懑而去的伟大灵魂送上一点安慰”⑭。
《金陵歌女》小说正文前有四张插页。第一张插页上用醒目的黑体字印着“献给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们”。第二张插页上引用了斯诺《南京的浩劫》中的一段文字:“毫无疑问,不管过去她们的德性有什么亏缺,现在的行为是一种补救,而她们中间有些人为此牺牲了生命。据我所知,她们死后并没有得到追认,甚至也没有获得勋章。”第三张插页至第四张插页分别绘有小说主要人物阿玉(歌女)、魏德迈(汉奸)、贝尔登(传教士)的形象。第四张插页的背面是小说的内容提要,对歌女与汉奸的行为进行了对比,并强调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作者李贵不仅在小说之中引用了斯诺对歌女评价的文字,而且还采用了《南京的浩劫》对侵华日军种种罪行的记载。
很明显,这是一部有意为歌女立传的小说。歌女的身份虽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但是她们善良纯洁的天性并未泯灭,国难当头,她们同样怀有一腔爱国热忱与一颗闪光的灵魂。汉奸的卖国求荣丑行与歌女的英勇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借剧中人物之口道出“我是记下一段历史,记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桩事情,记下一群卑贱的人的高尚人格,记下她们的爱国行为。”⑮
20世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为数不多,《金陵歌女》为其中之一,本应得到重视。但《金陵歌女》生不逢时,与当时的社会语境与文学思潮并不合拍,于是出版之后便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之中,未能进入人们阅读与研究的视野。至今,也未能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到一篇专题研究《金陵歌女》的论文。倒是根据《金陵歌女》改编拍摄的电影《避难》还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4
1988年上映的《避难》由李克威、李贵、严歌苓编剧。李贵的《金陵歌女》创作于1984年6月至1986年11月。从韩三平“1987年与周力搭档导演《避难》”⑯可知,在《金陵歌女》已经完稿还未出版之际,《避难》的编剧与拍摄工作就已开始。这也正是小说《金陵歌女》与电影《避难》同在1988年面世的原因。
电影《避难》故事:南方某城市被日军攻陷,战乱之中,名妓杨柳风、胡翠华和戏子小彩月来到天主教堂避难。她们把教堂的秩序搅得乱七八糟。霍尔登主教想请魏兰孙把妓女与唱诗班的少女一同带出教堂。四位伤兵来到教堂避难。日本军官服部中佐率部下强行闯入教堂,杀害了中国伤兵,发现教堂内有女学生,并以要为死去的日本军人唱安魂曲为由,逼霍尔登主教交出唱诗班女童。为了不让唱诗班女童遭受日军的糟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胡翠花和小彩月跟随杨柳风迎着日军的刺刀走了过去,为主教营救女童的计划争取了时间。三个中国女人被日军带上了汽车,随日军而去。其中一人怀揣手榴弹。途中她们引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电影以日军战报发布服部中佐在“执行公务”的途中,遭遇“车祸”全体阵亡的消息结束。
《避难》对《金陵歌女》的故事情节进行了改编。歌女避难教堂,与女童发生冲突,代女童赴难的故事予以保留。删除汉奸追捕妓女的那条线,新增四位伤兵来到教堂避难,以及日军搜捕伤兵的情节。故事的冲突更加集中。更为重要的是,严歌苓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书娟与玉墨的故事模型在电影《避难》中出现。《避难》中的婷婷相当于《金陵十三钗》中的书娟,名妓杨柳风相当于玉墨。且女孩婷婷对杨柳风的仇恨,正如书娟对玉墨的仇恨一样,其原因都是女孩的父亲与名妓有段艳情,导致女孩与父母骨肉分离。故事也是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突显了民族大义前,妓女的英勇行为。由此可见,“金陵十三钗”的故事架构发展至《避难》已经基本定型。严歌苓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的故事模型是对《避难》的丰富与发展。《避难》是《金陵十三钗》故事发展的关键一环,在《金陵十三钗》故事的创作链上,李贵与严歌苓正是通过《避难》进行了有效链接与传递。
5
严歌苓将《金陵十三钗》的创作归结为自己出国之后爱国情感的抒发。她在一篇关于《金陵十三钗》的创作谈中说道,“它是一篇我长久以来认为非写不可的作品”⑰。
严歌苓因参与电影《避难》的编剧而接触了“妓女舍身赴难”的故事。多年来,这一故事一直烙在严歌苓的心头。1989年,严歌苓赴美留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居住在美国。出国之后所处的语境,难免会让她受到“纳粹屠犹”研究与创作效应的影响。1997年,严歌苓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大会。在参观一个屠杀刑场时,她的内心受到触动,“感到非得为这个历史大悲剧写一个作品”⑱。经过漫长时间的发酵、酝酿,近20年之后,恰当的语境与契机诱发严歌苓对这一故事进行再次书写,将其精心打磨成为一篇五万字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发表在2005年第6期的《小说月报·原创版》上。“在严歌苓的书写中,这一群被历史放逐的‘无字’的女人们在小说中重新复活,为历史的暴力和民族的耻辱‘作证’,以被历史‘铭记’的方式,在女性身体和民族国家之间架起一座‘涉渡之舟’。”⑲
《金陵十三钗》中篇问世之后,反响巨大,在参与电影《金陵十三钗》编剧的同时,作者意犹未尽,又创作了《金陵十三钗》的长篇,并将其发表于2011年第4期的《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严歌苓说,“《金陵十三钗》成了我的‘一鱼五吃’,中篇、长篇、英文中篇、电影剧本,加上现在还有一个劝不住的投资人邀我写电视剧,整整‘五吃’。五年的剧本打磨,我没有从始至终,但这‘五吃’差不多让我把《金陵十三钗》的条条肌理、道道骨缝都吮了一遍”。⑳
我们先看中篇,再看长篇,后析电影。
如上所述,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沿用并发展了电影《避难》的故事架构。故事的发生地同样限定在天主教堂。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星条旗并不是法力无边的守护神,十字架下,也不是战争遗忘的死角,死亡与恐怖同样蔓延到天主教堂。二者故事中均有神父、妓女、军人、女学生等人物形象,只是人数与姓名不同而已。人物之间的关系、情节发展的脉络和救赎主题的呈现,二者极为相似。
《金陵十三钗》让“姨妈书娟”置身那场战争,缩短了历史的距离感。以“姨妈书娟”的眼光进行小说的叙写,增强了作品对大屠杀历史表现的现场感与真实感。这比李贵《金陵歌女》的第三者视角更能抓住读者的内心。严歌苓采用了她一贯使用的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细节描写,用先抑后扬的手法,首先渲染了妓女与伤兵在战争困境下的醉生梦死与放浪形骸的情景。醉生梦死之间,妓女与伤兵产生了朦胧的感情。最后伤兵为了不让他人受到牵连,死在日军刀枪之下。妓女则在日军向教堂逼要唱诗班女童之际,舍身赴难,拯救了女童。“十三钗”的行为是对“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千古骂名的颠覆,其形象实现了巨大逆转。
严歌苓创作《金陵十三钗》可视为对《金陵歌女》跨越时空的一次对话。“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 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体之间、占领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 似乎可以画上一个等号。”㉑严歌苓认为“大屠杀”中的“Rape”“是以践踏一国国耻, 霸占、亵渎一国最隐秘最脆弱的私处, 以彻底伤害一国人的心灵来实现最终的得逞和征服, 来实施残杀的。”㉒“他们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㉓与《金陵歌女》相比,《金陵十三钗》将其焦点更多地聚集在日军“大强奸”的罪行之上。“窑姐”们不停地念叨与女童们为之恐惧的正是日军的“大强奸”行为。
《金陵歌女》中的圣保罗教堂虽为歌女们提供了庇护,但圣保罗教堂的卡洛德院长是一位利用战争进行渔利的庸俗势利之徒。在接到日军司令部要求教堂送出十名少女至日本随军服务团之后,为了升任教区大主教,便决定向日军献出唱诗班的女童。而《金陵十三钗》则竭力塑造了英格曼神父的正面形象,他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不但收容了逃难的妓女,而且冒着危险为伤兵提供了庇护,在日军冲进教堂搜查时,他誓死保卫难民的生命,并在与日军的对峙中受到伤害。在日军逼着交出唱诗班女童时,他要陪护孩子们一起到日军军中,保护女童的安全。这说明从《金陵歌女》到《金陵十三钗》,作者对教堂与神父的情感立场发生了转变。
《金陵歌女》中的阿玉们本可远离虎口,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当她们知道卡洛德院长要将唱诗班的女童交给日本随军妓院时,在家仇国恨面前,她们自行组织起来,代替唱诗班女童赴日本人的征召,并伺机与敌同归于尽。阿玉们的行为更多地体现的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圣保罗教堂不能保护未成年女童时,族人的自救行为。“《金陵歌女》比美籍华人作家的相关小说更强调民族的自决和承担,强调民族的抗争和文化的自信。”㉔《金陵十三钗》妓女们在紧急关头决定李代桃僵、舍身饲虎的行为暗合基督教“原罪与救赎”的要义。正如玉墨所说,她们活着“就是给人祸害,也祸害别人”。她们要做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颠覆那个千古的骂名。玉墨们的行为既是对唱诗班女童的拯救,又完成了自我救赎。同为赴难故事,意蕴略有不同。
如果说,电影的编剧是一种集体创作,更多的是在体现导演的意图,那么将中篇小说改写成长篇小说,就完全是作者自己意愿的表达。与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容量更大,信息更多。作者将中篇小说扩展成为长篇小说,能将作者在中篇小说中未能表达的思想在长篇小说中进行充分地表达。与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对书娟与玉墨的关系进行了微调,玉墨不再是书娟父亲的情人,书娟对玉墨的仇恨不再那么强烈与刻骨。长篇小说以抗战胜利后“姨妈书娟”在日本战犯审判大会现场寻找赵玉墨的“引子”开始,并在结尾交代了“金陵十三钗”的最终命运。
对“南京大屠杀”战争场面与战时生活物资匮乏的描写,是长篇《金陵十三钗》增加的重要内容。作者着力再现大屠杀之后南京街头横尸遍野的惨景与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意在增加小说“史”的成分。
但问题是,严歌苓并不擅长描写宏大历史场景,她的长处是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以小人物折射大历史。所以当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的长篇中试图对战后场面进行描写时,就缺乏那种宏大叙事应有的效果。长篇《金陵十三钗》并无长篇小说应有的架构,只是在中篇基础上进行了内容的填充,也未取得长篇小说那种回肠荡气的效果。撑大了的中篇,反而失去了中篇的韵味。相比之下,中篇《金陵十三钗》更加玲珑剔透,更有艺术成就。
6
电影《金陵十三钗》是在中篇小说的基础上进行编剧的。电影采用英雄化叙事与好莱坞式的讲述,对小说情节进行了较大的改编,但“从小说到电影,妓女舍身救女学生的情节基本没有变化,这是故事的核心精华所在。”㉕与小说中的中国军队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弃城而逃、束手就擒不同,电影开始时增加了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抵抗而进行的激烈的巷战。也正是李教官一人战多敌,才让女学生们免遭日军的集体强奸。虽然中国军人最终都以身殉国,但毕竟进行了顽强抵抗,并让日军受到重创。“电影中的李教官形象成为中国军人在正面战场上殊死抗日的集中代表,所有观众都会为之感动。”㉖电影中仅重伤员王浦生一人与“窑姐”们躲在教堂地窖里避难,删去小说中伤兵与妓女醉生梦死的场景。影片中军人的形象不再让人感到颓废沮丧。
小说中保卫女童、妓女、伤兵的英格曼神父,在电影开始前,因日军对教堂的一次轰炸而身亡。救助教堂内难民的责任落在了殡葬化妆师约翰身上。日本军人的残忍行为激发约翰摆脱人性中自私、懦弱的一面,完成了从酒鬼、色鬼、财迷到英雄的转变。他冒死承担起拯救女童的任务。小说中玉墨与伤兵的感情戏转变为玉墨与约翰的感情戏,好莱坞风格明显。
日本军人来到教堂索要唱诗班女童,女童们不愿被糟蹋,登上教堂塔顶,准备跳楼自尽。为了让女童们免受日本人的糟蹋,玉墨们决定代女童去日本军营受难。赴难前的一首《秦淮景》成了青楼女子的生死绝唱。影片中的男童陈乔治为了保护女学生,自愿男扮女装,走向虎口。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荒淫无道、喋血残酷,影片中从力不敌众的中国军人,到摆脱自私与懦弱的约翰神父,以及要改变骂名的玉墨们,再到男扮女装的男童陈乔治,他们的人性都得到了升华。电影《金陵十三钗》成为一首绚丽悲壮的诗篇,再现了小人物的人性光辉。
7
行文至此,“金陵十三钗”故事的源头与演变已经十分清晰。当年,斯诺从一位传教士的来信中得知一群歌女为了拯救唱诗班女童而英勇赴难,他将这一故事记载下来,成为《南京的浩劫》中的重要内容,这正是“金陵十三钗”故事“史”的源头与“诗”的出处。
1982年2月,《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在大陆翻译出版,歌女舍身拯救女童的故事与国人见面。1988年,李贵据此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陵歌女》出版,这是“金陵十三钗”由“史”到“诗”的第一次演绎。同年,根据《金陵歌女》改编拍摄的电影《避难》上映。严歌苓参与了电影《避难》的编剧工作,使“十三钗”故事的创作得到了有效链接。《避难》是“金陵十三钗”故事发展的关键环节,故事中神父、妓女、女童、伤兵等人物形象的设置,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情节发展的脉络,在《避难》中已经基本定型。经过近20年的酝酿与发酵,在恰当的语境之下,身处异国他乡的严歌苓,以一位女作家特有的敏感与细腻的笔触,对“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再次进行书写,并获得了巨大反响。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又将这一故事演绎成为一群青楼女子的生死绝唱。
“就文学而言,如何在大量真实史料的基础上,重新书写这种血腥的大屠杀过程,并使其获得丰厚的审美意蕴,仍是对作家叙事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一种考验。”㉗“金陵十三钗”的故事经由众人之手,由“史”的叙述转变为“诗”的结构,情节得到了丰富,意蕴得到了深化,风尘女子的苦难与耻辱升华为一种圣洁的正义,小人物的人性熠熠生辉,故事则完成了由“史”到“诗”的嬗变。
【注释】
① 王达敏:《世界因为她的离去而损失良多——读张纯如〈南京大屠杀〉》,《批评的窄门》,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② 陈相乐:《“对张艺谋的不满只是传闻”——〈金陵十三钗〉原著作者、编剧严歌苓专访》,《华夏时报》2011年12月19日。
③ [美]明尼·魏特琳:《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158页。
④⑤ 陈玲莉:《网友报料〈金陵十三钗〉很像韩三平的〈避难〉》,《成都商报》2011年12月16日。
⑥ 张连红:《在南京的日日夜夜——〈魏特琳日记〉评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⑦ 陈力君:《论斯诺的红色中国镜像》,《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6期。
⑧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王恩光等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⑨ 李杨:《“记录历史”与“创造历史”》,《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⑩⑪ 《斯诺文集出版前言》,《斯诺文集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5页。
⑫㉗ 洪治纲:《集体记忆的重构与现代性的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⑬ 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⑭⑮ 李贵:《金陵歌女》,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56页。
⑯ 蔡卫、游飞:《从照明工到中国电影旗舰的掌舵人》,《中国电影》2010年第1期。
⑰⑱㉒ 严歌苓:《悲惨而绚烂的牺牲》,《当代》 (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
⑲ 吴雪丽:《严歌苓:历史重述与性别乌托邦》,《南开学报》2012 年第4 期。
⑳ 严歌苓:《五写十三钗》,《金陵十三钗——我们一起走过》,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9页。
㉑ 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读书》1999年第3期,第21页。
㉓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 (长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㉔ 李永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㉕㉖ 侯克明:《女性主义背景的英雄主义叙事》,《电影批评》2012年第1期。
作者简介※安徽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