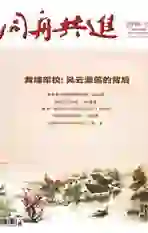毛公鼎,国之重器的辗转路
2016-12-07贺越明
贺越明
与大盂鼎和大克鼎相比,无论辗转经历还是归公结局,都以毛公鼎较为曲折和复杂,可谓命运多舛,还留下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纷争和悬疑。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镇馆之宝:毛公鼎、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因展厅面积所限,博物院通常每个季度换一次展品。即便如此,要让所藏60余万件文物逐一亮相展览,至少需花30年时日。纵使其它文物展品常换,上述三件珍宝却一直展示而不曾换过,故被公认为台湾“故宫三宝”。就青铜器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并称“海内青铜器三宝”。
毛公鼎是距今2800多年前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因刻器者为毛公而得名。此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下有三足鼎立,上有两耳高耸,花纹简洁,外形古朴。鼎身虽仅30.75厘米高,却铭刻着32行、497个篆书文字,是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鼎铭字迹清晰工整,篆文字字笔力遒劲,全篇一气呵成。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故而,铭文是研究西周史的珍贵文献,也是中国“造字时代”的经典作品。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价值无双的瑰宝重器。
与大盂鼎和大克鼎相比,无论辗转经历还是归公结局,都以毛公鼎较为曲折和复杂,可谓命运多舛,还留下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纷争和悬疑。尽管之前已有许多文字记述和考证,甚至还有影像记录和解说,其间有同有异,大同小异,有些情节颇为精彩甚至近似演义,但关键之处亦即它最后是如何从私藏变为公器的,似乎长期未有定论,直到现今仍有从头梳理和详加考释的余地和必要。
村民卖给收货郎
有关毛公鼎的出土经过及其发掘者,一向存在着几种版本和不同的说法。据陕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馆研究员贺世明考证,毛公鼎于1843年在陕西岐山县庄白村出土,发掘者系董家村村民陈春生。历史上,这一带被称作周原,是周人兴起的地方和灭商之前的都城。在西周灭亡的时候,周朝贵族纷纷逃亡,许多笨重的青铜器来不及带走,仓皇之际就埋入了地下。所以,这地方出土青铜器并不奇怪。由于陈春生并不识宝,把这件鼎器当作旧铜器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货郎,而货郎又将之转卖给西安北大街一家旧货站。当旧货站欲把包括毛公鼎在内的一堆破铜烂铁销毁重铸时,被路经的一位古董商发现,便以约白银20两的价钱买下了宝鼎。
这位古董商名叫苏亿年,是京城琉璃厂古玩铺永和斋的二掌柜,常在家乡陕西这一文物古玩出土大省搜寻货源,其兄苏兆年则是坐镇店铺专管销售的大掌柜。苏氏兄弟深知此鼎绝非一般青铜器,转卖出去必定能赚大钱,只是要寻一位慧眼识宝且有财力的主顾。于是苏亿年致书陈寿卿,详述宝鼎的形状、文字、花纹、色泽及来历。陈见函即回复,让苏赶快送进京师。
陈寿卿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者,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进士之身被朝廷任为翰林院编修。他对金石收藏考释极为钟情,不惜耗巨资在家乡山东潍县建造著名的“万印楼”,专门存放多年收藏的近万枚秦汉古印玺和万余件其它古物珍玩。他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被公认为19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他曾从苏氏兄弟手中购藏过几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也是出土于陕西岐山的天王簋。几次交易后,约定如若苏氏兄弟新得青铜器,必先送他过目;只有他无意购藏,才能售与他人。故此,苏亿年携带这件青铜宝鼎进京,邀陈到“永和斋”鉴赏并商购藏事宜。陈仔细看后颇为惊喜,深感此宝罕见。后来陈决定购藏,至于是以多少银两购藏,则众说纷纭,据传为1000两银。据说陈寿卿有言:“宝物无价,不能以金钱比价。”
陈寿卿购入毛公鼎后,没有置于京城府邸,而是送回山东老家秘藏,并嘱家人严守秘密,不得外传。由于铭文拓片鲜为人见,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否真实存在,且称即便有也是伪作之器。连陈的老友吴云也写信质疑:“究竟世间有此鼎否,窃愿悉其踪迹,祈示知。”另一老友吴大澂也发疑问:“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陈寿卿对此不直接答复,但撰有《毛公鼎释文》略作介绍,并将毛公鼎铭文拓印后,赠给少数同好作考辨和研究之用。光绪十年(1884),年逾古稀的陈寿卿给后代留下遗嘱: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念经信佛,希望后人能够安然平淡地做学问,并要保护毛公鼎,不使其从陈家散失。他病逝后,生前所收藏品由三个儿子朋分,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等古物。他遵照父嘱,谨言慎行,对家藏毛公鼎之事守口如瓶。但陈厚滋去世后,其次子陈陔违背祖训,开设钱庄和药铺,还经不住利诱,痛失了这件祖传宝物。
陈陔执掌家业后,结识了同邑同姓的陈芙珩,并泄露了家藏毛公鼎之秘。而此人背后是时任直隶总督端方,端方对毛公鼎始有觊觎之心。当毛公鼎转由陈陔收藏时,时任左都御史的陈子久看出端方的念头,唆使其子陈芙珩接近陈陔,游说他将毛公鼎卖给端方。起初,陈陔对端方出资万两白银购买之议并未心动,后来陈芙珩转告,除了万两白银,端方还可让他到湖北省银元局任职,终于使他动心。于是,在得到端方一纸委任书凭证后,陈陔不顾家人反对,在宣统二年(1910)将毛公鼎售予端方。从此,他满心期待到湖北省就任,但久等正式任命而不得,径直前往该局查问才发现,端方所拟的那纸文书凭证上的印鉴竟是一枚闲章。这时,陈陔才明白端方所许只是诱饵。
险落外人之手
第二年,端方被清廷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领兵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行至资州地区时被起义士兵所杀。其后人染上清朝宗室贵族子弟的纨绔习气,除了吃喝嫖赌外无一能事,生活日渐窘迫,到后来不得不靠变卖或典当家中藏品为继。到民国九、十年间,以3万两白银作价,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设的华俄道盛银行。典押到期后,主人无力赎还,英国记者辛普森表示愿出资5万美金购买,并委托端方的结拜兄弟、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项,但端家嫌钱太少而不肯割让。此事传出后,舆论哗然,文化界人士竭力呼吁不能让这件国宝流失,不然将愧对祖先和后人。北洋时期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叶恭绰闻知后忧心如焚,决意设法将宝鼎留在国内。他先出面劝说几位实业家购买未果,后来干脆变卖收藏的其它文物,与郑洪年、冯恕合资购藏,后由郑、冯二位出让给叶。
叶恭绰,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而喜爱书画,清末入仕任职邮传部,北洋时期历任几届政府的交通部长,财力深厚,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著名的词学家、书画家和收藏家。他买下毛公鼎后,一直将之藏在天津寓所,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日寇全面侵华后,华北顷刻沦陷,他携毛公鼎至上海的懿园寓所珍藏。不料,仅仅4个月后,日军又占领了上海,他只得避走香港。不久后院起火,他那居沪的姨太太潘氏伙同情夫图谋霸占财产,并威胁如他不应允的话,就将家藏毛公鼎的秘密报告日本人。为确保毛公鼎不被日本人掠夺,叶恭绰假意答应潘氏要求,同时电告时在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侄子叶公超,让他前往上海设法护宝。叶恭绰嘱咐他:“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1939年春夏之交,叶公超不辱使命,抵上海后即把毛公鼎转移秘藏他处。潘氏见如意算盘落空,便向日本宪兵队告密,使叶公超未及返昆即遭逮捕羁押。在牢里,他屡经利诱威逼,以至严刑拷打7次,均守口如瓶,拒不吐露毛公鼎下落。叶恭绰在香港惊悉侄儿身陷囹圄,急忙筹措资金营救。叶公超自己也在设法脱身,他在妹妹前往探监时,嘱托家人托人仿造一只青铜器以应付日本人。稍后,日军宪兵队收到叶家交来的赝品,加上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以重金保释,就将关押约50天的叶公超释放。一年后,叶公超摆脱监视,把毛公鼎偷运香港,完好无损地交到叶恭绰手中。
1941年12月,香港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沦陷。在当地避难的叶恭绰不仅因为与毛公鼎有着不解之缘,还由于拒绝出任伪交通部长替日本人做事,其行动受到日军的严密监视。最后,他托一位德籍友人,成功地将毛公鼎辗转携至上海。因他坚持不肯出任伪职,回沪后继续称病足不出户,坐吃山空,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终于陷入等米下锅的窘境。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把毛公鼎押给银行,后由巨商陈咏仁以黄金300两赎出。但叶恭绰向陈咏仁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一旦抗战胜利,要将这件国宝交给政府。其时,日军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陈咏仁表示愿意接受,因而成为毛公鼎的新主人。
陈咏仁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在江苏无锡开设铁工厂。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他开始惑于私利,罔顾民族大义,以名下的江南公司与日本军部做生意,用五金材料加工产品,制造机械,直接为日军军需服务,发了不小的“国难财”,在上海市区购置了豪华的花园别墅,也耗资搜集古董珍玩。到日本宣布投降时,社会上响起严厉惩处汉奸的呼声,这位富商开始恐慌。他想到了对叶恭绰的承诺,以为将毛公鼎献给政府或许可以赎罪,便通过叶公绰等著名人士联名致函政府表示愿捐国宝。信发出不久,便为新闻记者所悉,争相要求采访。还有人闻讯登门告贷,所求不遂怀恨在心,转而宣扬他过去与日军交易而有资敌之罪。陈咏仁一看情势不妙,担忧被当作“经济汉奸”处置,等不及政府来取宝鼎,就携眷悄悄弃家出走,逃到海外以避风头。果然过不多久,就有人上门查抄了陈宅。
私藏终变公器
一时间,毛公鼎的主人不见了。那么,价值连城的毛公鼎去了哪里呢?早前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抗战胜利后,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1984年10月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刊有《戴笠劫夺毛公鼎记忆》一文,作者沙孟海称他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机要秘书,受部长朱家骅之命拟文向蒋介石告状,蒋即下谕勒令戴笠交出这件国宝,云云。
曾任军统局总务处长的沈醉,在回忆录的叙述有所不同。戴笠令沈醉到上海查找失落的文物,特别提到“这次到上海务必找到一件国宝级文物——毛公鼎”。陈咏仁住宅在上海杜美路,他逃跑后,军统接收了其房产作为上海办事处。沈醉查找毛公鼎并不顺利,最后将上海所有古董商传讯到办事处。办公室内陈设有一组太师桌椅,桌下设置一个焚纸炉。他坐在八仙桌旁,对古董商说:“我这次到上海就是要找到毛公鼎,如果你们其中有人知情不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些古董商面面相觑,摇头低叹。此时,一个商人眼睛直视,大声惊呼:“呜呼,呜呼!罪孽,罪孽!”随着他的惊叫,所有人也发出了惊叫,都冲向八仙桌,沈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商人异口同声:“毛公鼎就在你脚下!”众人搬出毛公鼎,除去纸灰,清晰看到鼎内的铭文。沈醉大喜过望,只待向戴笠邀功受赏。谁知,3月17日却传来戴笠飞机失事一命呜呼的噩耗。但这段回忆有舛误,军统上海办事处所在的杜美路70号不是陈咏仁住宅,而是帮会大老杜月笙的房产,以其与戴笠的私交借给军统局使用。而且,所有古董商同时发现毛公鼎而惊呼的情形,显然有过度渲染的戏剧色彩。
关于毛公鼎被无意中发现的经过,另有一种说法。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星岛晚报》刊文《毛公鼎充字纸篓》称:当国民政府接到陈咏仁所具献奉毛公鼎的私函后,派了一位大员依址前往陈家宅,只见大门紧闭,封条交叉,阒无一人。原来,已被军统局派人查封了,询之经办人员,却谁也不知有什么毛公鼎、蒋公鼎。这位大员不得已,径赴杜美路的军统上海办事处查问,仍然查不出下落。因回去交不了差,他懊丧极了,坐在一张椅子上信笔乱涂,涂完把字纸揉成一团,随手向墙角字纸篓里一抛。突然,他如有所触地发现这纸篓不是藤制的、木制的,而是一具废铁似的圆炉。他立刻查问:“这是什么东西?哪儿来的?”军统人员漫不经心地回答:“这个又旧又重的铁家伙,是在陈咏仁家里抄来的。因为没有什么用处,暂时放在这里,权充字纸篓派用场,等收废铜烂铁的人来,让他收买去。”这位大员听了,不待他再说完大叫起来:“这不要是毛公鼎呀!”他俯身下去,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下,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是毛公鼎是什么?便立刻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哀江南》第七集,振华出版社1963年版)作者是名叫“振声”的老报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一、第十绥靖区少将参议兼驻沪通讯处主任,与军方及军统关系较深,所述不会全是道听途说。
也曾供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徐伯璞,晚年撰有《毛公鼎归国有亲历记》(1993年11月20日,《文汇读书周报》),其中说道:抗战胜利后,风闻毛公鼎在上海有了消息,遂引起学术界的极端关注。当时主管文博事业的徐伯璞经多方查询,得知毛公鼎已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于是几经奔走,终于取得宝鼎,置于教育部,并最终让其由中央博物院专人领去。该文所述颇具细节,但犹有存疑之处。
查阅上海档案馆馆藏有关毛公鼎的档案卷宗,其中有民国35年(1946)6月,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琇、副局长李熙谋签具上报市政府的《上海市教育局关于接受毛公鼎情形报告》。从这一报告可知,至迟在1946年4月19日之前,已知毛公鼎在军统局上海办事处,行政院即命上海市教育局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接受及保管;上海市教育局经接洽得知,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已将毛公鼎送去南京的局本部,且已向蒋介石报告;6月16日再接军统局函告,该鼎已送呈蒋介石。档案所录的此中经过,与徐伯璞的回忆文字有不小出入。
综合归纳以上各种说法,至少可以说明:抗战胜利后,毛公鼎由军统人员查抄陈咏仁的财产时所获,后在无意中获悉竟系国宝;陈咏仁既已函告政府有意捐献,叶公绰又以北洋遗老而与闻此事,亦为社会广知,戴笠即便想私藏也有心无胆,其生前没有见到毛公鼎,据为己有未成事实;兼管文物的教育部门认真追寻,而军统局既知此鼎价值,为表功直接上报并呈送蒋介石也顺理成章。无论逻辑上还是时间上,不存在军统局部下把毛公鼎送给戴笠私藏的运作空间。
毛公鼎从1843年出土到1946年归政府收藏,经过了100多年漫长纷繁的曲折历程,其间不乏国内外见利忘义、寡廉鲜耻之徒,但在几位爱国人士的保护下,最终完好无损地成为我们的国家财产。它先由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存保管,并在该院建筑初步完工后,和其它珍贵文物一起辟室展示,供民众参观。1948年11月,蒋介石展开退守台湾的部署,下令运走黄金和古董。12月22日,“中鼎”号军舰满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712箱文物珍宝从下关码头起航,4天后抵达台湾基隆港。毛公鼎也在其中,从此离开了大陆,后来存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这一历史因缘,它和其它从大陆运台的文物一样,名义上可算作国民党的“党产”,实际上都是整个国家的文化财富,是泱泱中华大地物华天宝的象征。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