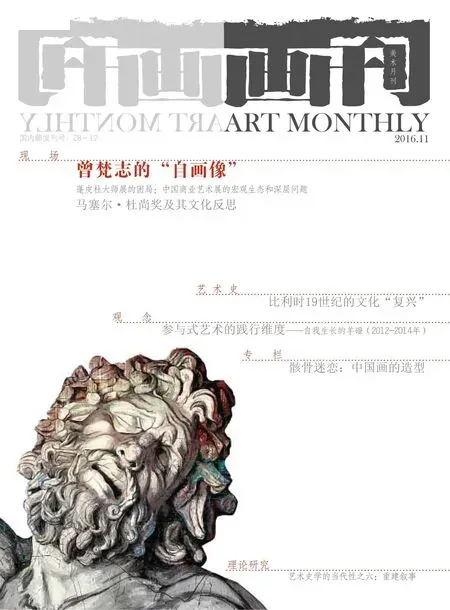马塞尔·杜尚奖及其文化反思
2016-12-06何宇红
何宇红
马塞尔·杜尚奖及其文化反思
何宇红
欧洲从来都不是一个缺少文化反思之地,这已成为这块土地的传统。尽管总有人会说,它那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是,骆驼还在,思想的明灯黯淡了,但火烬尚存。近大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大洋彼岸的金融垄断或侵吞,还是地球另一端新崛起的新型经济体,都没有真正动摇过欧洲作为一个思考者和行动者所应该具有的姿态。2016年10月18日晚间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第三画廊空间里正在举行的年度马塞尔·杜尚奖(Le Prix Marcel Duchamp)的获奖者联展开幕酒会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直以来大家都没有放弃的努力。当现代艺术在欧洲走过了黄金时代之后转向北美大陆,巴黎也挥别其辉煌而一时成为艺术的重创之地一蹶不振。特别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法国的艺术市场更是到了天寒地冻的境地,正是在这个时刻,吉勒·弗弛(Gille Fuchs),曾经作为欧洲奢侈品牌尼娜·荷齐(Nina Ricci)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也即后来马塞尔·杜尚奖的创始人,在1994年逆行而上地成立了他的“法国国际艺术传媒协会”(简称L'ADIAF),用意除了谴责当时在国际重要的美术馆、博物馆、博览会等等都严重缺少法国艺术家作品的收藏者,还有对于本土专业艺术机构之外普遍存在的对于艺术的无知状态的拯救;吉勒认为这些都同样严重波及和影响到了法国收藏家们的认知度以及他们的购买力。而事实上这个领域不仅没有消减,而且它完全跟英美地区一样是存在并且活跃着的。法国人在国际艺术舞台上这么长时间的缺席是一件不可忽视的非理性的消极现象。吉勒聚集了200多名艺术品收藏家和当代艺术的爱好者们,积极重建法国艺术家在本土及海外的影响和价值认可。而他在2000年倡导成立的马塞尔·杜尚奖则是法国国际艺术传媒协会诸多项目中最成功的案例;因为这个奖项是由收藏家们所设立的一个奖项,所以它迫使他们必须对自己所介入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这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其他收藏家和艺术家的一种重要的承诺。评选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全部来自协会成员,都是活跃和知名于当今世界艺术领域的重要人物,并且每年更换评委会名单。为保证这个奖项的公正,杜尚奖的评委们必须有一半来自法国境域之外;另外,参赛艺术家有权选择自己的推介人(或机构),以便与评审委员会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

展览现场
对于获奖艺术家来说,最大的福利不仅仅是那3.5万欧元的奖金,而是从此所对他敞开的一个可以大幅度延伸展示的舞台。先前组委会会将被提名的艺术家的作品推介到法国之外的欧洲博览会,像邻国的德国科隆艺术博览会和莫斯科艺术博览会,获奖者还可在蓬皮杜得到一个为时不短的展期,但是提名者只在那些博览会展出四天。近年来L’ADIAF跟本土的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菲亚克(FIAC)建立了合作,FIAC将会每年为杜尚奖的提名者和获奖者在主展场专门设立一个展示空间。今年的情况更加令人惊喜,与往届不同的是,杜尚奖提名者联展第一次从大皇宫转换到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展期也由原来的四天转变为近四个月,为此蓬皮杜艺术中心还特地提供了一个600平方米的新空间—3号展厅。这标志着杜尚奖提名者联展从一个短期展览转变为具有三个多月展期的常设展,这种转变使杜尚奖在当代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变得不言而喻。
讲到法国当代艺术的马塞尔·杜尚奖,当然不得不提到当今世界的其他几大艺术奖项,其中特别和理所当然要被提到的首推欧洲邻国英国的"透纳奖";人们经常将杜尚奖与之相提并论,认为是欧洲当代艺术两个具有同等分量和级别的奖项。其实从时间上来说,透纳奖比杜尚奖早了整整15年,算是行业内的老大哥。然而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的透纳奖现如今因其“挑衅风格”常年不变而更受抨击,被认为“惊世骇俗”,已经不再成为它的内容而堕落为落入俗套的形式。比如今年最为众所周知的就是其竖立在泰特美术馆门口的那个让人既津津乐道又嗤之以鼻的装置作品《大屁股》。更早前还有让人一头雾水的翠西·艾敏(Tracey Emin)凌乱肮脏的《我的床》以及达米恩·赫尔斯特(Damien Hirst)镶满钻石的骷髅《为了上帝的爱》。然而无论再怎么去谴责被无限质疑的“不恶俗就不死”的透纳奖,也无法抹去泰特美术馆自从成立以来为它所颁发奖项的那些艺术家们已经成为当今艺术界赫赫有名、身价千万的人物。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否能够被一直延续下去?或者说,还能坚持多久?
可能因为透纳奖设立得比较早,没有过多的当代艺术奖项先例的经验可寻,而因此走过很多弯路——包括成为笑柄、引起示威游行,甚至有一年被迫停办等等。现如今,日趋成熟的透纳奖已经将它的评委权力交给了观众,举行公众投票制(仍有疑议),也因此成为英国每年家喻户晓的当代艺术评选盛事。所以如果说当初透纳奖的初衷是以它的反讽、诡异、奇特来大大地冲击人们的艺术审美习惯和观念,挑战社会和民众的底线,从而拓开了人们对于艺术的想象力的话,那么杜尚奖则是更多地从人文科学研究的角度来推介和鼓励艺术风格的创新,挖掘历史、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向人们提供更多的思维空间,激活当代艺术的多维思考。吉勒认为,不同于英国特定的人文历史背景、思辨习惯和价值取向,法国历来拥有属于自己的人文传统,只不过有一段时间我们忽略了它,我们所设立的这个奖项就是要唤醒人们的文化反思精神,保存和延续法国文化的宝贵特质。同时,21世纪当代艺术的阅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了解艺术家创作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工作的媒介及表达意图,以及他们超越本色的写真承载着的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而我们的起源知识完全赋予了我们可以阅读的特有的照明和阅读图表。视觉艺术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但也有可能使我们眼瞎;我们走得貌似顺畅,其实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其他路可走。我们要教会的是必须先潜水,学会深呼吸,寻找另一条路径;当然,这些都绝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

左·展览现场

右·2016年杜尚奖提名艺术家巴尔德莱米·图果作品《克服病毒》局部 陶瓷 2016年

2016年杜尚奖获得者卡戴赫·阿提亚作品《记忆的反射》局部三 混合材料 2016年
万事开头难,然而吉勒们说到做到;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各艺术大奖都纷纷不遗余力地根据自身以及全球范围的人文环境和艺术生态来调整其评审标准,可以看出当代艺术已由一种抽象的表达演化为一种思维的渗透,渐渐地成为一种人类精神的书写和表达。近几年来杜尚奖评审团更青睐于当代艺术中的跨界研究,比如去年的获奖者梅立克·奥哈尼安(Melik Ohanian)就是因为在表现科学、天体物理学和视觉艺术的关系所作出的深入研究和努力而获得杜尚奖。今年的四位提名者更是有三位分别结合了医学、人种学等领域与当代艺术的关系,以独特的语言来诠释人类意识的各种状态。特别是获奖艺术家卡戴赫·阿提亚(Kader·Attia)所展示的一件混合了雕塑、现成品和电影的装置作品《记忆的反射》(Reflecting on Memory),为观众构建了一个思路缜密而清晰的可供分析的空间,其中影像作品是整个作品叙事的联结者和纽带,与那些亟待被找寻也最终被找到的现成品和雕塑共同构成了一种诗意的循环尝试。影像作品穿插了对于外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和精神分析者的访谈,主要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截肢,讲述那些缺失的肢体永远和他们身体(母体)呈现出绑缚的状态,尽管从生理学和物理学上看,它们已经是两个不相连的个体,但又永远似乎总被一条隐形之链捆绑着。艺术家通过镜子的倒影来完成这种效果,由于人身体的对称性,那些缺失的部分又通过镜子的反射重新回归。这种肢体向母体回归的本能,折射出人类的另一种本能,即对欲望的模仿。这是法国哲学家海奈·吉哈(René Girard)非常著名的观点,人的欲望向来不是天生的和个体的,它是通过模仿得来的。肢体的回归是一种欲望,镜像是模仿,当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人的欲望便得到满足,呈现一种看似完满的状态。这也传达了艺术家近几年来一直集中表现的概念——修复。关于自然的修复,关于人类本身的修复。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将各种元素分布在黑暗的展场里,包括那个展区入口处缺失半块的大饼,观众的迷失所带来的缺失感和“创伤”是呈现作品主题的先决条件,然后是寻找,这样由缺失引向修复也因此变得更加顺理成章。
“修复”所带来的思考是多元化的,有物象的也有心灵深处的。影像作品中个体的创伤其实是一种群体的创伤,那些装置作品中的物质性的缺失也隐喻着一种非物质的症结。人类对于这种“修复”欲望的复制赋予了艺术作品非凡的意义,更赋予了人类演化的意义。近年来当代艺术的其他奖项也都多多少少地围绕着这种人文思想的反思并以此为基准来选拔和奖励他们的艺术家,像去年伦敦弗瑞兹艺术博览会(Frieze Art Fair)将艺术奖项颁给了从事电影工作的年轻艺术家瑞查儿·罗斯(Rachel Rose),她在伦敦摄政公园以照明和声音的独特设计来模拟居住在里面的动物的声音和视觉感知频率,以提醒作为公共空间-公园的公平分享和体验;这也是对地球当今环境的一种修复设想。而与杜尚奖同岁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Art Basel)的奖项之一——“巴鲁瓦斯(Baloise)当代艺术奖”今年的获得者、年轻艺术家玛丽·里德·凯利(Mary Reid Kelley)则以她的电影《这是内脏》(This is Offal),围绕女性自杀的敏感话题,以荒谬剧院的传统表现手法和她丰富的文字,探讨了死亡、生命和人体器官在身体和外界之间的反作用。电影发生在一个太平间,女人的尸体被放在桌子上,对话在女人的鬼魂和她自己的器官、身体各部位之间展开。陪审团的决定来自于艺术家在技术上的创新使用,以及其解决社会责任问题的深刻和有趣的实验性探讨,将人类对于信仰的集体幻觉作了巧妙的揭穿,犀利地反映了"修复在死亡之后"的无奈。

左·2016年杜尚奖获得者卡戴赫·阿提亚作品《记忆的反射》局部二 混合材料 2016年

右·2016年杜尚奖获得者卡戴赫·阿提亚作品《记忆的反射》局部四 混合材料 2016年

2016年杜尚奖获得者卡戴赫·阿提亚作品《记忆的反射》 影像装置 2016年
一直以来,当代艺术博览会一方面办得红红火火、此起彼伏,一方面又吃尽闲言碎语、备受质疑,有人说那是收藏家们的一场游戏,甚至是亵渎艺术和审美。然而现当代艺术最终还是没有绕得过艺术博物会,无论你如何“阳春白雪”,或高举各种大旗,一切均已铁板钉钉。祸及池鱼,艺术奖项也被人看作是操纵这场游戏的几张王牌之一。其实就算是事实,那又怎样?任何事情都有规则,只不过是换了种说法:谁都迟早要坐到这张桌子上。你可以不按常理出牌,却不可以不遵守游戏规则,否则你就得出局!马塞尔·杜尚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方面保持了其奖项的独立性,同时它又与菲亚克当代艺术博览会和蓬皮杜艺术中心强强联手,互相地注入和提升是一种势在必得,也是一种大势所趋。有目共睹,共赢的结果总是建立在良性的体制和生态之上,否则再喧嚣华丽也终将被淘汰。综观欧洲大大小小的艺术奖项,存活率达到10年以上的除了组织者出色的管理策划和公关营销能力,最关键的还是在学术上遵循一条无比鲜活的线路。无论是巴塞尔当代艺术博览会、伦敦弗瑞兹艺术博览会,还是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卡塞尔艺术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等,所有奖项都具有某种共性,这些相似点不仅体现在对于当代艺术的多重表现性所作出的积极解读和跟进,对于鼓励和接纳年轻艺术家、域外艺术家创作的风险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能够真正地以人为本,通过艺术所生发的文化反思。这其中甚至包括世界最老牌、当今历史最悠久的瑞士艺术大奖,这个设立于19世纪的奖项除了在20年前将原来的瑞士联邦艺术大赛改名为瑞士当代艺术大奖,而且还将竞赛和活动时间调整到了与巴塞尔当代艺术博览会同步,以秉承其100多年之前设立此奖的宗旨:“以鼓励年轻艺术家,提高并保障瑞士艺术的质量。”

2016年杜尚奖提名艺术家巴尔德莱米·图果作品《克服病毒》 混合装置 2016年
跨界、修复、反思和接纳,当代艺术都不缺这些词。实践者们似乎总在寻找坐标,但更多的其实是在提供思考和提出问题。大数据本来是用来帮助我们更方便快捷地到达目的地;然而按图索骥似乎并没有如愿以偿,出现的却是更多的不安、焦虑、困惑、战争和死亡。艺术家利用当代各种新媒体和表现手法试图从艺术中寻找答案,杜尚奖组织者们推波助澜。这是一种良好的趋势,预示着当代艺术正在成为一种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构建一个绿色的有氧空间,抑或是一条指引迷失者回归的路径。
娴熟于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70后获奖者卡戴赫·阿提亚曾经在非洲刚果待过很多年,在那段漫长而寂寞的时间里,他做过很多绘画、摄影和雕塑的工作。有一天一个朋友送了他一份礼物,那是一块用棕榈树的植物纤维编织成的挂毯,上面绣有好几块非常漂亮的法国殖民时代风格的布片。卡戴赫在好多年之后的某一天才突然明白,那块织物的装饰设计不只是出于美学考虑而是更关乎伦理。因为他发现每一块缝制在棕榈织物上的欧洲布片下都藏着一个洞,表面的装饰行为实际上掩盖着的是一种修补。这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一件事却让艺术家感到无比震惊:一个人将修补和改变事物的美学合二为一的时候,他的意图是什么?这仅仅是一个隐藏行为吗?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东方和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犹如站在一个思想穿梭的星形广场,如何去理解西方世界在整个20世纪所忽视的东西,那些非西方语言体系的文化。卡戴赫在西方的人种学博物馆做研究时曾经发现了成千上百被修补过的藏品被锁在黑暗的储藏室里,从未见过天日。虽然西方近现代艺术深受非洲传统艺术的影响,但在西方中心的思维掌控下,这些非洲工艺品并不被真正理解。诸如此类的思考大量地反映在卡戴赫色彩浓烈、意义深远的作品中,他是各大艺术博览会的常客,是杜尚奖们最为青睐的佼佼者,也由此窥见艺术似乎总在与政治逆向而行,同时也见证了西方学者在面对各种异议甚至带有极大批判性的文化现象时所给予的包容力。在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布局下,杜尚奖们所给予的应该不仅仅是一个被叫做"修复"或"记忆反射"的作品的肯定和奖赏,更是对于被湮没了的渐行渐远人类思想明灯的呼唤,是他们对关乎有益于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极具前瞻性的态度。(摄影:吴智龙 庹颖)
注:
展览名称:2016年杜尚奖提名艺术家及获奖者联展
展览时间:2016年10月12日-2017年1月30日
展览地点: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