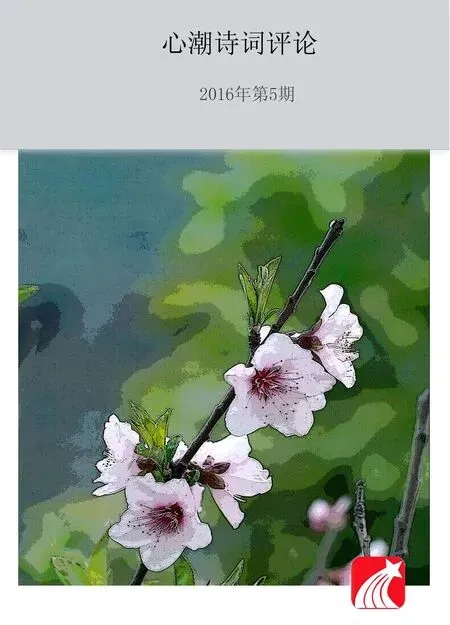论“绀弩体”与古典诗歌之关系
——从“谐趣”说起
2016-12-06涂谢权
涂谢权
论“绀弩体”与古典诗歌之关系
——从“谐趣”说起
涂谢权
幽默诙谐是聂绀弩旧体诗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在幽默诙谐背后,聂绀弩抒发的是传统文人失意的情感,体现了其严肃认真的作诗态度。其诗歌具有寓庄于谐、似谐实庄的内在特质,是在特殊社会环境下对旧体诗“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回归。从诗歌演进史来看,“绀弩体”亦可视为旧体诗在新时期的发展与延续。
聂绀弩的旧体诗以其鲜明的特色与独具的艺术魅力而获得人们的广泛称赞,在其朋辈之中即有以“聂体”或“绀弩体”视之者①按,聂绀弩在1977年1月5日致舒芜信中说:“但兄谓所谓‘聂体’者,真使我大吃一惊,不知所谓‘朋辈’果是何人。”聂绀弩逝世后,舒芜在1986年4月21日所写《记聂绀弩谈诗遗札》中对这些朋辈作了解释:“我打算回答他说,所谓‘朋辈’即是陈迩冬、黄苗子、张铁弦这几位老朋友。”详见《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 374页;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又,同时代文人荒芜《纸壁斋集》中也有题为《读绀弩同志〈北荒草〉中〈推磨〉,因忆五九年除夕前夜,野外脱大豆事,戏效绀弩体》的诗,可见“绀弩体”或“聂体”,在当时就已在朋辈中形成共识。。何谓“绀弩体”?林书认为是“聂绀弩所创造的以幽默‘甚至诙谐’为风格特点的旧体诗”②林书:《说“绀弩体”》,引自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页。。施蛰存也说:“聂绀弩旧体诗的更大的特点是它的谐趣,一种诙谐的趣味。”③施蛰存:《“管城三寸尚能雄”》,《读书》,1983年第1期。而程千帆也称其诗为“滑稽”。由此可见,幽默诙谐是“绀弩体”的突出特点之一。然而细读《散宜生诗》,不难发现其诗虽称“打油”,却是以严肃的态度写成,在诙谐、滑稽的风味中却隐藏着深沉、庄严的情感。正如胡乔木在《散宜生诗·序》中说的那样,聂诗“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是“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④详见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因此,“寓庄于谐”才是“绀弩体”的真正精神内核,而诗歌中“庄”的特质的存在,是其人生精神的真实流露,是作为诗人的聂绀弩向“诗言志”传统的回归。而所谓旧体诗的革新,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诗人在当代社会特殊语境下传承古典诗歌的一种自觉。
一、谐趣:“绀弩体”的表层意蕴
诚如高旅在《散宜生诗·序》中所说:“不闻‘生活为文学艺术之源泉’乎?诗人以刑狱流放,颇历坎坷,岂非‘这也是生活’(鲁迅语)?”①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聂绀弩的一生虽然谈不上波澜壮阔,但绝对可以说是坎坷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确实是聂绀弩诗歌创作的源泉与动力,也使得他的旧体诗有着深广的题材与内容。他在1977年2月2日给舒芜的信中说:“我所经历的远比汉公(笔者按:指吴兆骞)经历的深广得多,但一点也未觉得像梅公(笔者按:指吴梅村)所说的那样,倒是觉得到处都是生活、天地、社会,山繁水复,柳暗花明(这是说主导的一面,其他暂略),以及歌不尽颂不完的东西。”②聂绀弩:《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381页。按,本文中所有聂绀弩书信皆引自此,下不出注。后来又在《散宜生诗后记》中说:“我的诗如果真有什么特色,我以为首先在写了劳动,同时代写劳动的诗人当不会少,但我未多见,且不管它。古人也有写劳动的,就知道的若干篇章说,他们是在劳动旁边看劳动,在较高的地位同情他们的辛苦。我却是自己劳动,和别人一齐劳动,也看别人劳动。”他正是从日常的生活劳作中发现了诗意,如锄草、挑水、推磨、放牛、牧马、搓草绳、刨冻菜,甚而至于污秽不堪的积肥清厕、往复单调的伐木锯木等活动,都经过他的一番提炼而写入诗中。
聂诗题材往往琐碎不堪,但作者却故意郑重其事,琐碎之“小”与郑重之“大”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其诗歌谐趣的第一要素。如《受表扬》:
超额百分之二百,乍听疑是说他人。
支书竖拇夸豪迈,连长拍肩慰苦辛。
梁颢老登龙虎榜,孔丘难化溺沮身。
寥寥数语休轻视,何处荣名比更真。
好友舒芜曾问聂绀弩因何而受表扬,他回答说是奉命拾麦穗超额完成了任务。舒芜指出:“拾麦穗而有任务指标,本来是很可笑的。这样的表扬,也很可笑的。”③参见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引舒芜读诗笔记,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然而就是这样可笑的事情,聂绀弩却一本正经地以生动的语言予以刻画:“竖拇”与“拍肩”两个动作,支书、连长神情毕现;一个“疑”字则写出了表扬的出人意表与诗人受宠若惊的心理,以至于他有了像梁颢年老中状元那样的激动与喜悦,并强调表扬虽为“寥寥数语”却不可轻视。诗人当时写作此诗时的真实心理暂且不论,但从诗中将这种微不足道的表扬提升至超越了世界上的所有荣名来看,这种举轻若重、故作庄语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滑稽的行为。而这在聂诗中则属常态,挑水他可以是挑着乾坤和日月:“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挑水》)或者是“龙虎风云一担挑”(《柬周婆》)。烧开水他能想到项羽火烧阿房宫:“如何一炬阿房火,无预今朝冷灶炊。”(《地里烧开水》)清厕所虽极其污秽恶心,“香臭稠稀一把瓢”,然而在他看来,此与汉代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毫无二致;知识分子已然沦落到掏粪积肥的地步,他却将自己和万枚子比作承受“天将大任”的英雄曹操与刘备,手抓粪土在其诗中也变成了“手散黄金”(《清厕同枚子》二首),等等。
聂绀弩还善于提取生活中极富谐趣的细节进行详尽的刻画,通过放大事物差异与对立来构造诙谐滑稽的图景。如《女乘务员》描写在列车上叫卖各种报刊的女乘务员,诵读毛主席诗词、人民日报时是何其慷慨激昂理直气壮:“主席诗词歌婉转,人民日报诵铿锵。”然而却不过是文化低下、外貌鄙陋的黄毛丫头:“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表里不一的反差,令人忍俊不禁。又如《拾穗同祖光》(其一)写吴祖光与自己同拾麦穗,吴如王羲之,“俯仰雍容”;自己则如身长九尺四寸的曹交,“屈伸艰拙”。作者将这种强烈的反差置于同一视域中予以展示,诗歌的谐谑意味不言自明。而尾联“才因拾得抬起身,忽见身边又一条”两句,将自己稍得伸展却又不得不再次弯腰捡拾麦穗的懊恼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此诗的谐谑意味推向极致。《马逸》叙斑白老者追赶脱缰羸马,马之迅疾与老人之孱弱使得这场追逐毫无意义:“赛跑浑如兔与龟。”追赶者亦因此而灰心丧气,甚至连最寻常叱马的“谔”“嘉”之声也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无谔无嘉无话喊”的细节描写突出了老人追赶不及的窘迫神态。《怀张惟》中“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两句,批判者的热烈与张惟的漠不关心跃然纸上,一冷一热的对比也颇具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在具体事件和情感表达上,诗人往往以极度的夸张和奇妙的比喻来展示,如在聂氏眼里,草绳两股竟然如胶似漆,如同男女之间“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搓草绳》)。他的诗做到了如程千帆先生所云,将“奇思妙想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滑稽亦自伟》),从而颇具戏剧性效果。
此外,绀弩体的这种谐趣还表现在诗中普遍存在的用语新奇上。这主要表现在作者紧密结合现实社会大量使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语词。如钟敬文奉命参加“四清”运动,他即以《钟三往四清》为题而赋诗:“出问题时有毛选,得欢欣处且秧歌。投身阶级斗争里,见汝诗材大马驮。”其中“四清”“毛选”“秧歌”“阶级斗争”均为当时的常用政治术语,这种政治术语的使用,使得他的诗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类似的术语在其诗中广泛存在,如“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挽毕高士》),“花岗岩”即是当时流行话语“花岗岩脑袋”的省略,以此来表现毕高士至死“顽冥不化”的精神态度。大跃进后,他与萧军重逢,即以当时两人所经历的“大跃进”入诗:“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萧军枉过》)其他如“毛泽东思想都学,输君把卷定忘疲”(《赠迈进》)、“你我平生何所信,列宁主义马恩斯”(《赠五禾》)等。除了政治术语外,聂诗还不避俚俗,广泛采用口语俚语入诗,诗作也因此而增添了诙谐气息,如《赠董冰如高启洁夫妇武昌》中“门对珞珈山不远,人携辩证法同居。国风译好诗情重,血压防高菜味殊”四句,珞珈山乃武汉地名,辩证法为哲学名词,血压是医学术语,都是以常用语词入诗,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体现了董冰如、高启洁夫妇二人在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生活、工作的真实状态。《周婆来探后回京》中“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二句,“九头鸟”即出自民间谚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脚猫”也是由来已久的民间俗语。难登大雅的骂人词汇,偶尔也被聂氏引用入诗,如《有赠四首》其二“儿童涂壁书忘八,车马争途骂别三”,《钟三四清归》“红心大干管他妈”等。而《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掣肘偕行一笑哈”句中的“哈”字,《马逸》“无谔无嘉无话喊”句中的“谔”“嘉”二字,皆纯以拟声词入诗。为了语句的新奇,聂氏甚至敢于打破汉诗常规,故意将一些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引用入诗,如“书买《五百〇四峰》”(《赠雪峰》)、“嵩衡泰华皆0等,庭户轩窗且Q豪”(《九日戏柬迩冬》)、“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 K字楼”(《岁尾年头有以诗见惠者赋谢》)等。这种将政治学术术语、地理名词、口语俗语甚至是拉丁字母入诗的做法,将传统诗歌“诗庄”的特质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消解,也使得其诗歌具备了一些嘲谑的意味。
二、庄严:“绀弩体”的本质特征
谐趣的存在,使得聂诗带有了一丝“打油”的意味,秦似甚至当面称其诗为“打油”①聂绀弩:《散宜生诗后记》,参见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聂绀弩本人亦多次宣称其诗为“打油”,如他在1980年2月17日给邹荻帆、邵燕祥信中说:“我诗乃打油也,野狐禅也,不必重视。”1981年11月给杨玉清的信中说:“程千帆教授见赠中有云:‘滑稽亦自伟’;你曾说我‘奇才硕学’。所谓滑稽者,打油也。奇才者,不正之才也。”1982年2月9日给何满子的信中说:“关于此道,我但知打油,不知其他。”尽管如此,聂氏的旧体诗却并不能简单地以“打油”而视之,其诙谐幽默的表象下隐藏着真诚严肃的情感。正如程千帆在《滑稽亦自伟》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诗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则使人感到振奋。这是一位驾着生命之舟同死亡和冤屈在大风大浪中搏斗了几十年的八十老人的心灵记录。他的创作态度是真诚的,严肃的,而决非开玩笑即以文为戏的。”②程千帆:《滑稽亦自伟》,见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页。
这种“真诚、严肃的态度”,首先在于聂诗是自我“心灵的记录”,充溢着诙谐气味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严肃的情感表达。传统的文人失意情感是其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如《自遣》:
偶从完达赤松游,得道归来鸟鼠秋。
我马既黄千里足,春风不绿老人头。
他人饮酒李公醉,此地无银阿二偷。
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
据舒芜读书笔记,此诗作于聂绀弩从完达山归来之日,③详参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首联即是承此而来。“赤松”二字,语意双关,表面上描写诗人像张良一样追随仙人赤松子学道归来,实际上却暗示着自己在完达山砍伐红(赤)松的辛苦劳动,沉重中却不乏幽默。尤其是“他人饮酒李公醉,此地无银阿二偷”,直接用民谣入诗,虽写自己遭受冤枉、被人陷害,却又十分俏皮,然而这种俏皮与幽默更多地是为了表达自己被放逐的无奈。尾联描写自己余生研究《聊斋》《水浒》《红楼梦》等文学遗产,看似洒脱悠闲,实则是文人失意的悲愤,笑中带泪,与辛弃疾“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即事用雷父韵》:
虽邻柳巷岂花街,不为借书死不来。
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
江山间气因诗见,今古才人带酒杯。
便是斯情何易说,偶因尊句一诙谐。
柳巷花街,旧为青楼妓院之别称,亦是文人雅士流连之所,此为诗人居所。意指居处虽邻近花街柳巷,颇富诱惑力,而友人黄苗子(雷父)却非借书而不来,“死不来”对黄苗子嗜书如命的性格刻画入木三分,嘲谑意味十足又不乏尊重,且在嘲谑之中隐含着自己对友人到来的期待与来后的欣喜,这种嘲谑,是热讽而非冷嘲。颔联两句,“无鸟事”纯以口语入诗,俗之又俗,却生动地刻画了自己及友人之间“枯对半天”的百无聊赖,为下文凑齐四人“打桥牌”消磨时光作了很好的铺垫。诗以调笑、戏谑的口吻写出,轻松而幽默,然而看似轻松的笔调下,却饱含着诗人的深沉隐痛:纵有诗才,亦毫无用处,只能消磨于小小的酒杯之中。这一失意的情感,在其诗中比比皆是,如《马号》:“曾闻买骨来多士,行见挥鞭上九霄。嗟我老无千里足,唾壶完好未轻敲。”表面上在咏叹老马无用,实则是写诗人自我的闲置,抒发的是“那种‘受了伤’无法发挥作用的心情”,这种心情“通过诙谐语调说出,反显得含蓄深沉”。①林千典:《如此新声世所稀》,转引自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在聂诗中,也有不少隐晦曲折地反映当时政治的作品,讥刺、批判成为这类诗歌的重要主题。如《伐木赠李锦波》“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其中“高材”与“矮树”的生存状态,不正是当时知识分子与宵小的真实写照么?“胆齐落”三字表面是在写树,何尝不是当时文人的心理缩影?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如《伐木赠尊棋》“斧锯何关天下计,乾坤须有出群材”两句,林千典在1992年6月17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愚以为按句的表层意思可以认为是流水对,一问一答。即要问斧锯与天下大计有何关系哩?因为天地间(搞建设)需要(依仗斧锯采伐)超出一般的大材。至于深层的含意是另一回事。按现在的解释恐有公然写‘违碍’诗之嫌。”②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又《放牛》其二“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舒芜在 1993年给侯井天的信中说:“‘一鞭在手’、‘万众归心’,都是在说我这个老牛倌如今居然也一鞭在手,万众归心了。都是通过貌似自嘲,而有所讽刺……形式上的主语是‘我’,实际上这个‘我’另有所指,这样理解就没有‘不至于口吐这样的狂言’的问题。”③同上书,第39-40页。《没字碑》一诗,则是以武则天无字碑为引子,来批判江青欲“东施效颦”,仿照武则天“称孤道寡”的野心,并预言其必然落个“骑虎难下终须下”的结局,明确指出江青所踏上的是一条“君问归期未有期”的不归路。诗歌的批判矛头,直指当时权焰张天、炙手可热的“文革旗手”,极尽讽刺之能事,诗歌大胆热烈,作者的凛然正气、卓越胆识,于此可见一斑。其好友万枚子对此深表折服:“诗揭江青丑态,当时敢写反诗者,三草一人而已!”④转引自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其他如“吾民易有观音土,太后难无万寿山”(《颐和园》)、“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钓台》),则让人触目惊心。类似的诗句,聂氏诗集中比比皆是。这种政治的解读看似荒诞,但也并非全无根据,在聂绀弩的人生中,就曾多次发生过。“文革”中聂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诗“成为他‘现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状”,而“解诗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⑤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4期,第18页。。聂绀弩出狱后,在1977元旦给舒芜信中说:“兄谓我为无杂感为大误,并谓以杂感入诗开前贤未到之境,云云,未免过高。杂感实有之,不但今日有,即十年前也有,所以我认我所经历为罪有应得,平反为非分。至于以杂感入诗,目前尚未臻此。”而这种解读方式在聂绀弩看来当然不啻于“破案或揭发”⑥详见聂绀弩1982年10月25日写给舒芜的信,《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418页。,于其自身不利且十分致命。因此,在胡乔木批示要为《散宜生诗》再版作注时,聂绀弩极力反对,反对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注释从简,只注典故。他自认为其所经历“罪有应得”,以及反对为自己诗歌作注的行为,从另一方面也证明其诗歌确实存在着政治隐喻的成分。
文人失意的情感表达与政治隐喻的存在,使得聂绀弩的诗歌在诙谐幽默的表象下具有了严肃的情感特质。聂诗谐中有庄、似谐实庄的倾向,正是基于这种严肃情感特质的表达,从而也表明他的诗实际上是对古典诗歌“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继承。
而事实上,聂绀弩确实是在以“真诚、严肃的态度”作诗。受钟敬文的影响①在谈及这点时,他说:“我有两个值得一提的老师,陈迩冬和钟静闻。迩冬乐于奖掖后进,诗格宽,隐恶扬善,尽说好不说坏。假如八句诗,没有一句他会说不好的,只好从他未称赞或未太称赞的地方去领悟它如何不好。静闻比较严肃或严格,一三五不论不行,孤平孤仄不行,还有忘记了的什么不行。他六十岁时,我费了很大劲做了一首七古,相当长,全以入声为韵,说他在东南西北如何为人师以及为我师……写好了,很高兴地送到他的家里去,他看来看去,一句话未说,一个字未提,一直到我告辞(不,一直到现在,二十来年了)。但我更尊敬他,喜欢他,因为他丝毫不苟。”很显然,钟敬文那种对格律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影响到了聂绀弩。详见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他作诗能遵循旧体诗的格律,常常“口念诗歌检平仄”(《自遣用家天见怀韵》)。一旦发现诗不合律,即使诗句再好他也不用。如《代周婆答》第一首第五句,1977年4月致舒芜信中作“逍遥北海忘天泽”,他曾欲将此句改为“装潢小说干县令”,然而因为“县”字为仄声,用在此处不合律,所以将此改为“钦迟北阙巍华表”。他说:“拙作第一首下四句改为‘钦迟北阙巍华表’②按,“表”字非韵脚,而律诗第四句当为平声韵,因此信中“第四句”误,实为第五句。又,侯井天《聂绀弩旧诗全编》收录此诗第五句作“轻睃华盖摹唐俟”,而非此处所言“钦迟北阙巍华表”,则聂绀弩此后又有改动了。聂作诗态度之认真,于此可见一斑。,……‘钦迟’句曾改为‘装潢小说干天象’,从装饰小说以干县令来,可惜‘县’字仄,如为州长,定会用之,因‘大风吹楼’正谓小说也。”③见《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398页。又《颐和园》诗末两句原作“我来已是群游日,绝顶朝朝任跻攀”④见1961年12月28日聂绀弩给高旅信附录,《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然而高旅认为“跻”为平声,不合律。尽管聂绀弩认为“‘跻’多读平,我用作仄,虽字典亦有仄读”,但对此还是“心常耿耿”,于是改为“此园落尽千关锁,今义和团血尚斑”⑤详见1962年3月8日给高旅的信件,《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为了追求诗意的合理,聂绀弩亦经常锤炼诗句。如《柬慎之谢寄罐头》⑥按,此诗附于1961年9月26日聂绀弩给高旅的信中,详见《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散宜生诗》《旧体诗全编》及《聂绀弩诗全编》皆未收录。颈联上句原作“青山细语含羞草”,聂绀弩将其改为“燕山细语含羞草”,因为“青山自有含羞草,这东西暖和地方很多,南洋遍地皆是。燕山我还不知在何处、有无此山,更不谈见过含羞草没有,想来应该没有。但诗意原不在此,改后一南一北,意思更醒”。⑦详见《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事实上为了诗意而对原作进行修改的情况非常普遍,如1964年5月聂绀弩曾写下五首凭吊萧红的《红墓》寄给高旅,5月9日专门去信将前诗予以改动:“由办事处先手送诗五首,想均收到。今又改动。第一首‘翁’改‘弩’,‘一天’改‘南来’。第二首‘饥寒’改‘流亡’,‘千载’改‘天下’。第三首‘趋’改‘而’,‘祖国’改‘去日’,‘三鼓’改‘千里’,‘昨夜’改‘在眼’,‘不堪’改‘如何’。第四首‘千’改‘终’,‘头’改‘前’。第五首首句改‘霓雌不碍以文雄’,‘猛忆先驱’改‘隽语长思,’‘编’改‘同’,‘谁’改‘宁’,‘难云’改‘当尤’。改后似较佳,尊意云何?”⑧同上书,第280页。
严肃的情感与严肃的作诗态度,说明聂绀弩的旧体诗歌绝不可以打油视之。事实上,在诸多方家眼里,聂绀弩的旧体诗与打油诗还是存在着不同的。施蛰存曾指出:“聂绀弩旧体诗的更大特点是它的谐趣,一种诙谐的趣味。……谐趣不是戏谑,戏谑就成为打油诗;谐趣也不同于西洋的幽默,幽默要有一点讽刺。”(《管城三寸尚能雄》)虞愚评价聂绀弩诗说:“七六年七七年间,很多人都学‘聂绀弩体’,但大都失之油滑,未成正果,都学成了打油诗。惟有绀弩的诗,火候分寸恰到好处,巧妙地掌握了打油与诗的临界点,能在刚到临界点时,一下子拉回来,送上诗轨,而成为极富诗味的诗。”①转引自周健强《聂绀弩谈〈三草〉》,见《聂绀弩诗全编》附录,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页。聂绀弩自己亦云:“有时悲从中来,不知何故,所谓‘泪倩封神三眼流’(拙句)者,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散宜生诗自序》)都说明聂绀弩的旧体诗超越了一般的滑稽与打油,标志着“绀弩体”向旧体诗“诗庄”传统的回归。
三、“阿Q气”与旧诗的抒情机制:“绀弩体”的生成动因
如前所述,“绀弩体”诙谐是表象,庄严为本真,是在以故作轻松的姿态写深挚沉痛的情感,抒发的是知识分子兼诗人固有的传统情怀。那么,聂绀弩为何要以旧体诗的形式创作幽默诙谐的作品来抒发庄严的情感呢?
不可否认,诗歌幽默诙谐的特质源自作者性格中的诙谐因子。聂氏谐谑、乐观的性格一直存在,即使在其人生最困顿的时候依然如此。如《北荒草·往事》诗下作者自序云“饶河某晚会,约定我讲一笑话,后因领导不同意,遂罢”,即是明证。施蛰存认为:“一个人对待反映各种时代现实的世态人情,持过于认真的态度,或无动于衷的态度,都不会有谐趣。只有极为关心,而又处之泰然的人,才可能有谐趣。”(《管城三寸尚能雄》)聂绀弩正是这种对现实的世态人情极为关心且处之泰然的人,他甚至自己将此总结为“阿Q气”。如《散宜生诗·后记》自叙曰:
我有很多的低级趣味,写文章本是从报屁股上的滑稽小品开始的,至今结习未净。胡乔木同志的序说我对生活有诙谐感。程千帆教授赠我的诗说“滑稽亦自喜”,施蛰存(北山)先生评我的诗,把人家说是什么气魄、胸襟之类的句子,指为诙谐。诙谐、滑稽就是打油,秦似教授当面说我打油(我早已写信给高旅说我好打油又怕打油)。都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但他们没说我还有阿Q气,我也只在《九日戏柬迩冬》中明提过一下。在所谓“文革”中,狱中同号包于轨君说:他不喜鲁迅,因为他反对阿Q气。人没有阿Q气怎能生活?他年已七十,在“缧绁之中”,甚至还“非其罪也”,阿Q气就成为他的救心丹。我在《赠徐迈进》中,头一句就是“丘家有几女孩儿”,早已抒发这种阿Q气。次联“自己班房何所惧,浑身胖病早当医。”虽是迈进常说的话,也是由我的阿Q气采用的。瞧!挑起一担水,自谓挑起“一担乾坤”(《挑水》);挑土和泥,自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脱坯》),何等阿Q气,岂只是诙谐、滑稽、打油而已哉!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
所谓“阿Q气”是指鲁迅《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就是卑微的人生中自我嘲讽、自我超脱。从消极角度而言是一种自我的精神麻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却又是某种达观的生活态度。聂绀弩所言“阿Q气”,显然是指后者。应该指出的是,“阿Q气”其实是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之一,尤其是没落文人在面对艰难困苦时,在被压抑被奴役的状态下自我慰藉的重要手段。古往今来的文人皆是如此,杜甫“老大”之后还“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柳永黜落之后的“奉旨填词”、关汉卿自封为“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的放浪形骸等等,又何尝不是“阿Q气”!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阿Q气”更成为被打倒的知识分子的救心良药,用包于轨的话说就是“人没有阿Q气怎能活”。知识分子群体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阿Q气”,聂绀弩所提到包于轨、徐迈进是如此;王希坚也曾“牛棚一夕似三秋,穷极无聊学阿 Q”①王希坚:《喜读〈散宜生诗〉》,转引自罗孚《聂绀弩诗全编》附录,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页。;朱正“自告奋勇”为《散宜生诗》作注,也是因为自己“还有一些阿Q精神,并不认为自己吃了多少亏”,与聂绀弩有会心之处;而丁玲也自认为“我们都是阿Q”,等等。“阿Q气”的存在,是文人对现实的不满,也可以视为一种抗争——不过是无力的抗争而已。
聂绀弩诗歌的诙谐也正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他在1961年11月7日给高旅信中谈及作诗缘由时说:“五、六年来,诸事颠倒,感情思想拘滞抑塞,旁皇不知所之。自谴自挖,为之太过,不免矫饰,致形之于诗。然非此际遇,我亦无意为诗。”在1961年11月21日给高旅信中又说:“我的诗,是我有一部分时间,想了解一点我国古典诗的内容和方法的副产品。……再,这几年来,感情上也不可能完全正常,不免要发抒发抒,不管如何发抒都好。”这种“不正常”的情感,在其个人而言,是在于时代给其身心带来的磨难和困苦。高旅就曾批评他诗歌“专在‘凄苦’、‘小事’上兜圈子”,而聂绀弩认为此话“自然一语破的”,并说“但没有这,我还要写什么呢?”②详见聂绀弩1962年1月3日给高旅的信,《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然而在那种文化高压下,凄苦的情感是无法直接言说的,正因为如此,在其自我情感抒发的时候必须采用不正常的手段和方法,诙谐成为其最好的表达方式,正如他在《即事用雷父韵》中所说的那样:“便是斯情何易说,偶因尊句一诙谐。”
除了时代政治及性格特征外,“绀弩体”的形成还源自于诗人对旧体诗的再认识。聂绀弩之所以选择旧体诗来创作,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对于文体的逐步认识过程。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聂氏后期以旧体诗名世,但最初却是主张新文学、反对旧体诗的。好友彭燕郊在《千古文章未尽才》一文中曾记载20世纪30年代后期聂绀弩与茅盾文学主张之间的一次冲突:“茅公力主新诗必须向古代诗歌,以及民歌甚至民间曲艺学习,这自然正确,但茅公的主张,却偏重在形式的学习上。对茅公我们当然是非常尊敬的,这一回却真是不敢苟同。记得绀弩说过:那些形式多半已经死去了,要让它们起死回生很难,也没有必要,等等。……另一件事是胡风脱险到桂林时,拿出他的两三首旧体诗给绀弩看,也给宋云彬看了,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好。绀弩说:‘想不到他怎么也写旧诗?’意思是最好不写。”③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页。聂绀弩自己也承认其开始是“拥护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根本不做旧诗。”但自经历动荡之后,他对旧体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认为只有旧诗才是诗:“大概因为越在文坛之外,越是只认为旧诗是诗,其中有传统、习惯甚至与民族形式、旧瓶新酒之类有关。”④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谈及自己作诗经历时,聂绀弩在《赠钟敬文》一诗中说:“昔作新诗今旧诗,两回驴背受君知。问新诗好旧诗好,笑此一时彼一时。”“笑此一时彼一时”、只认为旧诗才是诗,都说明聂绀弩从思想观念上已全然接受了旧体诗,认可了旧体诗的存在价值,完成了从新诗向旧诗的观念转型。
那么,作者如何开始创作旧体诗的呢?聂绀弩自己曾说,一方面是因为“几十年前,学过一点旧诗的格律,如对仗、声韵之类的”,有着一定的旧诗基础;另一方面是“领导要做诗”,于是“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想起做旧诗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①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对此,舒芜有着详尽的解释:“聂文好用‘某种’字样,也许是杂文家的小小的狡狯,但是看到这里的‘某种情感’,我却不禁微笑地想:这里可是瞒不过我,我可知道这指的什么。五十年代他曾同我谈过:‘旧诗真做不得,一做,什么倒楣的情感都来了。’从一九五七年起,‘二十余年来’他所有的不正是‘倒楣的感情’么?”②舒芜:《一份白卷——关于聂绀弩的〈北荒草〉》,转引自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很显然,聂绀弩所要表达的“某种感情”乃是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是文人在面临政治高压下实实在在存在却又无法言说的一种特殊情感,聂绀弩称之为“倒楣”。他认为情感的宣泄,旧体诗是最好的渠道:“我觉得诗这种文学形式,应比较别种形式和作者本人的感情之类的关系要密切些。”(1977年2月 2日致舒芜信)③《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换言之,聂氏的倒楣情感正是旧体诗所擅长表达和抒发的。旧体诗以其特有的抒情机制与聂氏“不完全正常的感情”契合而成为其情感抒发的首选:“我觉得旧诗可爱的地方也正如此,若即若离,可解不可解,说能完全道出作者心情,却距离很远;说简直不能道出,气氛情调却基本上相近。有时心里想说的话,凑不成一句;有时由于格调声韵之类的要求,却自来一两句连自己也想不到的好句。这都比散文和白话诗更迷人。说是这么说,我自己现在还没真达到这种境界。”(1961年10月21致高旅信)④《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很显然,旧体诗歌独特的语言句式及其对含蓄蕴藉的审美追求,容易形成诗意层面的多样性,而这一种诗性的语言也使诗歌在接受层面带来了多种可能,古人所谓“诗无达诂”即是指此。但与此同时,旧体诗的这一抒情特征也使得诗人情感的隐晦表达成为一种可能。聂绀弩旧体诗歌创作的奥妙,也正在于此。
由此可见,聂绀弩旧体诗创作完成了由“奉命文学或遵命文学”向抒情文学的转变。他的旧体诗,是古典诗歌“言志”和“缘情”传统的回归。换言之,特殊的时代产生了特殊的情感,从而需要特殊的文学创作方式。聂氏旧体诗的创作,根基于其自身的人生经历与旧体诗特殊的抒情机制,是二者紧密契合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聂氏的旧体诗创作,是其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同时也是旧体诗文体的一种“自觉”。
四 “打油”:古典诗在新时期的演进
如前所述,聂绀弩之所以转向旧诗,是因为经历动荡之后,对旧诗有着重新的评估和认同。尽管他开始大量写作旧诗是因为政治原因,①在1981年11月给杨玉清信中,他说:“我是失学的小学生……近六十时,在北大荒劳动,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按,指当时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说要人人做诗,我也只好硬做,乃塞责交差,非自愿也。”见《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 139页。《散宜生诗自序》也说:“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〇农场第五队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全体震惊和骚嚷。……这回领导要做诗,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想起做旧诗来了。”引自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且出于交差塞责:“那时感情上的卑屈是主要的东西,但在创作心情上,则有凑成便算之意。”(1961年12月28日致高旅信)②《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然而自北大荒回京之后,便“一不做二不休,弄假成真,从玩票到下海(其实又何尝下海),年已六十,倒真学起做诗来了”。(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他在1962年1月3日给高旅的信中说:“品格与传且不谈,既然作诗,就该作得像诗一点,好一点,不要游戏三昧。……这要求完全应该,朋友就是如此作法。我对别人也曾表示过这种意见。那么,好吧,就来认真地学学作诗。”作诗,已然成为其人生后期的庄严事业。
既然聂绀弩在严肃作诗,那么如何来看待他诗歌中的“打油”呢?打油诗,古已有之。胡适《白话文学史》就曾指出:“白话诗有种种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民歌,这是不用细说的。一切儿歌,民歌,都是白话的。第二个来源是打油诗,就是文人用诙谐的口吻互相嘲戏的诗。如我们在上编说的,应璩的谐诗,左思的《娇女》,程晓的《嘲热客》,陶潜的《责子》《挽歌》,都是这一类。王褒的《僮约》也是这一类。嘲戏总是脱口而出,最自然,最没有做作的;故嘲戏的诗都是极自然的白话诗。”③胡适:《白话文学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虽然胡适的观点并不一定严密,甚而至于误将王褒俗赋《僮约》误归为打油诗,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旧体诗中是存在打油(或者是文人互相嘲戏的诗)的传统,而且源远流长。现代文坛上,文人以旧体诗打油者亦比比皆是,如鲁迅先生作《南京民谣》:“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④鲁迅:《鲁迅散文诗歌精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就将国民党内汪精卫等人争权夺利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其《教授杂咏》亦是如此,一如其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受志明和尚《牛山四十屁》的启示,周作人曾作《五十自寿诗》,自称“牛山体”,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皆有和诗,由此而形成了“打油诗”热潮。事实上,聂绀弩的诗歌打油,也是对这一旧诗传统的主动继承。他曾将自己的部分诗歌编集成册,命名为《马山集》,其《序诗》之序言中即明言此举曾受到了《牛山四十屁》的影响:“古有《牛山四十屁》。此册亦近四十首,题咏投赠,于人于物,颇伤于马,其有牛者,盖偶然矣。故题曰马山,以马怀沙云。”⑤转引自王存诚《“我诗非马亦非牛”——聂绀弩〈马山集〉评析》,《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3期。
应该承认的是,“绀弩体”很大程度上是借打油来创新,是旧体诗歌在新时期的演进。对于诗歌打油,聂绀弩有着清醒的认识,如1962年3月15日致高旅信说:
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力亦在此。截然界线殊难划,且如完全不可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油可打。以尔我两人论,我较怕打油,恐全滑也。君诗本涩,打油反好。故你认为打油者,我反认为标准。又,我认为涩者,并非意思难懂,而在字句别扭,亦即未照格式锻炼。
诗歌打油与否,聂绀弩认为并不在作诗方法本身,而在于作者诗风的倾向,需要因人而异。作诗艰涩者,当打油,如高旅;作诗圆滑者,则不可打油,如聂氏本人。这也说明聂绀弩对自己的诗歌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诗歌的利弊所在。如1961年11月7日致高旅信中说:“但迩来亦有一病,因学诗不免看了些前人集子,有熟语滥调危险,当力矫之。”如何矫正自己诗歌“熟语滥调”呢?在1962年11月28日给高旅的信中,聂氏亦认为:“我诗圆熟,自亦有觉,此为危境。初时惟恐不圆熟,近则惟恐圆熟,最怕像柳亚子,近于滑矣。现尚不知何以矫之,俗语新语似尚不足以办此也。”①《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一言以蔽之,为了免于诗歌近于熟滑,聂绀弩采取了“打油”的方式。所谓的打油,乃是故意。由此可见,所谓用以打油的“俗语新语”,其实是为了矫正诗歌因打油而出现的“圆熟”弊病。
聂绀弩的创作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诗中很多看似打油的诗句其实都是绝对、妙对,且能让人耳目一新。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钟三四清归》)二句,上句引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的成句,何其典雅!下联则以时语国骂来对之,又何其俚俗!雅俗之间,妙趣横生。王希坚评论说:“这一联不但‘青眼’对‘红心’、‘高歌’对‘大干’极为贴切,‘吾子’对‘他妈’更令人忍俊不禁,为之喷饭。”②王希坚:《喜读〈散宜生诗〉》,转引自罗孚《聂绀弩诗全编》附录,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页。然而这联妙对亦是经过修改锤炼而成的,据冯英子《不胜天地古今情》记载,此句原作“红心大干老专家”。则“管他妈”三字乃是后来修改而成,一改而“真点铁成金也”(罗孚语)③转引自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又如《清厕同枚子》中间两联“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无论平仄与对仗都极为工稳,尤其是以“苍蝇盛夏”对“白雪阳春”更是令人叫绝。其他如“旨酒能尝斯醉矣,佳鱼信美况馋乎”(《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难寻布底棉鞋了,尚着条花睡裤乎”(《除夜怀查九》)、“红烧肉带三分瘦,黄豆芽烹半碗油”(《中秋寄高旅》)等都是如此。类似的例子,在《散宜生诗》中不胜枚举,此不赘述。这种看似打油、实则工稳的绝对、妙对的存在,说明“绀弩体”实现了打油与旧诗的完美融合,也使得旧诗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换言之,“绀弩体”的打油倾向对旧体诗而言,并非是革命,而是一种改良。正如聂绀弩自己所说,他的作品是旧体诗的“变体,独特,别裁”。④详见聂绀弩1981年9月30日给高旅的信,《聂绀弩序跋书信》,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综上所述,作为新时期文人,聂绀弩早期“从‘五四’运动受到启蒙教育,后来成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老战士”(舒芜语),秉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但到了晚年,尤其是经历了人生磨难后,旧诗成为其情感的寄托,诗人也完成了由新文化向旧传统的回归。彭燕郊称聂氏旧体诗有现代意识,舒芜说他“毕生忠于‘五四’的战斗传统,捍卫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展了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⑤舒芜:《一份白卷——关于聂绀弩的〈北荒草〉》,转引自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都是不确切的。聂绀弩自己曾说“感恩赠答千首诗,语涩心艰辨者稀”“老想题诗天下遍,微嫌得句解人稀”,也当是有感而发的吧!
(作者系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
责任编辑:姚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