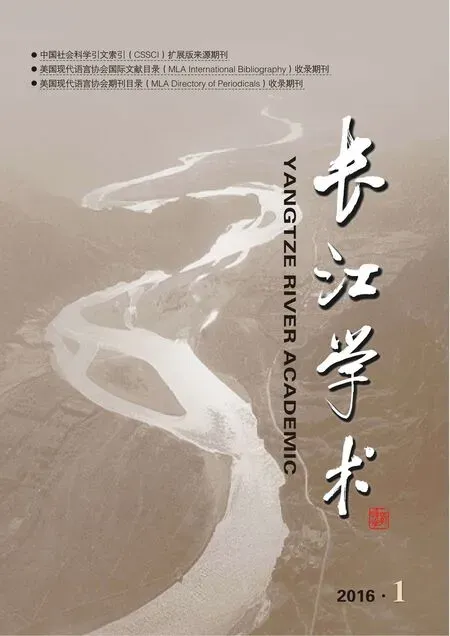论当代小说的反讽结构
2016-12-05晓苏
晓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论当代小说的反讽结构
晓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反讽结构被作家广泛运用。与其他结构形态相比,反讽结构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框架设置。本文认为,反讽结构的小说经常运用的框架有三个,分别为时空框架、因果框架和正反框架。同时,本文还分析了反讽结构小说所呈现出的独特的美学意味。
当代小说反讽结构常用框架美学意味
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反讽的源头可能要追溯到苏格拉底的那些对话性著作。作为戏剧中的一种语言技巧,反讽主要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佯装,二是反语。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反讽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它已经跨越了戏剧体裁,逐步延伸到了诗歌和小说等各种文体。与此同时,反讽的艺术功能也不断得到了提升,尤其是进入小说之后,它的作用便不再只是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扩展到了环境、时空、情节、人物和主题等各个方面。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小说的发展,反讽在文本中已由局部性修辞渐渐演变为整体性修辞,直接参与了小说的环境设置、时空安排、情节组合、人物塑造与主题传达等每一个环节的结构性建设,并且形成了一种小说的重要结构类型,即反讽结构。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属于反讽结构的小说可以说不胜枚举。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由于文化氛围的不断改善,反讽结构这一小说类型便愈发受到小说家的青睐,因此涌现出了一大批反讽小说经典。
在反讽小说中,反讽不再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已经被作家提升为一种既参与谋篇布局又参与表情达意的结构策略。如果说作为语言的反讽,它的作用主要还是微观的、局部的、外在的和传统的,那么作为结构的反讽,它的作用已变为宏观的、整体的、内在的和现代的,用学者浦安迪的话说,它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方法。”①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对于当代反讽小说,学术界已有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这里,笔者将重点研究一下反讽小说的结构框架以及这些框架带给文本的特殊美学意味。
一、反讽结构的常用框架
从结构的形态来讲,与诗歌的线型结构、散文的点式结构和戏剧的面状结构不同,小说更像是一种框架结构。框架具有立体性、复合性和层次性三个特点,既涉及形式又涉及内容,既涉及情节又涉及人物,既涉及语境又涉及情境。可以说,一部反讽小说的反讽性首先是由文本的反讽性框架决定的。也就是说,作家必须首先设置出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构框架,小说的反讽性才有可能传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讽框架的设置便是反讽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作家智性和才情的体现。通过解读大量的反讽小说,笔者发现,作家们经常使用的反讽框架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时空框架
时间和空间是小说的两个最基本的叙事元素,也是小说结构的经纬。如果说小说是一只鸟,那时间和空间就好比它的两翼,失去了时间和空间,小说就飞不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时间和空间就没有小说。在小说中,时间和空间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它们却有着天然的孪生性,彼此依托,互为凭借,相辅相成。学者曹文轩说:“因为小说在形式上属于时间艺术,因此空间问题反而在这里变得更加引人注意了: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究竟如何看待空间,又如何处理空间?空间问题就成了小说家的一门大学问。”实际上,除了时间对空间的处理,空间也在同时处理着时间,它们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小说的结构框架。
一般小说的时空仅仅只是个背景性概念,而反讽小说的时空必须具有反讽性,即对荒谬、矛盾、错误、无聊、可笑的对象进行审视、批判、嘲笑、揶揄和反思。只有这样,时空才能构成一种反讽性的结构框架。
铁凝的《春风夜》是一篇异常辛辣而深刻的反讽小说,它的反讽性主要来自作者对时空框架的绝妙设置。夫妻俩久别重逢,激动不已,可是俞小荷正要兴冲冲地进入春风旅馆的房间时,服务员却因为她没带身份证把她拦下了。平时,旅馆对身份证检查不严,只要出钱,即使两个野鸳鸯没有身份证也可以开房寻欢。但眼下却不行,全国“两会”正在北京隆重召开,警察每天半夜都来查房,合法夫妻没带身份证也不能同床共枕。无可奈何,这对农民夫妻近在咫尺却无法共度春宵。两口子怀憾告别的时候,俞小荷意识到了丈夫的性苦闷,于是多给了他一百块钱,含泪让他去找个小姐。
从上述细节中,我们不难发现时间和空间在这篇小说中的重要性。时间是春天,正值全国“两会”期间。俞小荷当保姆的空间是首都北京,约会的空间是郊区的春风旅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夫妻才相聚不能相欢,导致了妻子出钱让丈夫去找小姐的悲喜剧。假如时间不是春天,不是“两会”时期,假如空间不在北京,也不在效区的春风旅馆,那这篇小说的反讽性便不复存在。当然,一般意义上的时空是不能构成反讽框架的。换句话说,反讽性的时空必须拥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假设把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都改换一下,将俞小荷和丈夫约会的时间换成秋天,将“两会”换成运动会之类,再把俞小荷当保姆的地点改成上海或者广州,把夫妻约会的旅馆改为秋风旅馆。这样一改,小说在情理和逻辑上仍是成立的,但它的反讽性就消失殆尽了。
在《春风夜》中,铁凝别具匠心地设置了两种时间,一是自然性时间,一是社会性时间。俞小荷和丈夫约会的时间是春夜,这个自然性时间给人一种温馨和浪漫的感觉,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诸如春风拂面、春心荡漾和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类的美妙联想。同时,他们的这次约会又恰逢全国“两会”召开,这个社会性时间更有深意。众所周知,“两会”历来都是关注“三农”的。按说,俞小荷和丈夫的这次约会不仅时值春夜,而且还喜逢“两会”,真可谓碰到了大好时光。然而,这对农民夫妇哪曾料到,正是由于“两会”,他们合法的夫妻生活也过不成。作家通过设置春夜和“两会”这两个意味深长的时间,让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顿时获得了反讽意味。在空间的设置上,铁凝也是非常智慧的。她把俞小荷当保姆的地方选在了首都北京,把夫妻俩约会的地方取名为春风旅馆,这样一来,空间就有了某种特定的暗喻之义。在这个作品中,除了“北京”和“春风旅馆”这两个颇有深意的空间外,还有两个空间也别有意味,一个是“顺义”,一个是“方庄”,它们都处于北京市区之外。小说中这样写道:“他的车今天一早到顺义,因为大车不能进北京市区,卸了货,车就停在了顺义,他再搭别人的车到方庄。”开大车的都是底层劳动者,他们却不能进入首都北京,只能把卡车停在郊区顺义,人也只能待在郊外方庄。稍加分析,读者便可体会出这几个空间的反讽意味。
苏童的《神女峰》也属于典型的反讽结构,并且设置了一个经典的时空框架。一对无比相爱的恋人为了让爱情永恒,他们从南京坐船逆江而上,曹文轩:《小说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铁凝:《春风夜》,《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的荒诞性。荒诞性既是反讽的对象所在,又是反讽的魅力之源。余华的小说几乎都是反讽之作,作为一个公认的现代性作家,荒诞便是余华创作的永恒主题。他说:“我觉得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充满了荒诞,从压抑禁欲到纵欲乱性,从政治癫狂到经济混乱,从无视经济到经济至上,从人性遏制到伦理颠覆。”①余华:《我的文学道路》,《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正是由于这些荒诞的现实,余华才写出了像《河边的错误》这样充满了反讽意味的杰作。从结构上来看,《河边的错误》也是设置了一个因果悖论性框架。故事的起因是幺四婆婆在河边被杀,警察马哲负责侦察此案和捉拿凶手。经过一波三折,马哲终于发现了凶手。可是,凶手却是个疯子,他不仅不能接受法律的制裁,反而还逍遥法外又连续杀人。马哲忍无可忍,就开枪打死了疯子。一个负责捉拿凶手的警察,结果自己成了杀人的凶手。至此,反讽的意味就这样出现了。更具反讽意味的是,为了逃脱法律的惩罚,迫于妻子和局长的哀求,马哲极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是疯子,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小说结尾写道:“‘让我去精神病医院?’马哲心想,随后他不禁哧哧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响,不一会儿他哈哈大笑了。他边笑边断断续续地说:‘真有意思啊!’”②余华:《河边的错误》,《钟山》1988年第1期。在这篇小说中,余华设置了两层因果关系,第一层是,警察为了捉拿凶手,结果自己成了凶手;第二层是,属于正常人的马哲开枪打死了属于不正常人的疯子,而法律认为不正常的人杀人是正常的,正常人杀人是不正常的,结果正常人马哲无可奈何只好变成了疯子。由于多重因果悖论的出现,这篇小说的荒诞性便不断增强,反讽的意味也随之更加强烈。
第三、正反框架
在反讽结构的小说中,除了时空框架和因果框架之外,我们还能经常看到一种由正反两种特性的因素的对比与互衬而构成的框架,即正反框架。学者李建军在研究反讽修辞策略时,总结归纳了反讽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是非直陈式修辞性介入,二是轻松自信的超脱感和距离感,三是两极对立因计划经武汉去三峡朝拜象征着天长地久爱情的神女峰,结果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他们的爱情就分崩离析,女主人公只走到武汉便跟人私奔了。特具反讽意味的是,当轮船经过神女峰时,男主人公哭笑不得地骂了一句:“操,这就是神女峰?”在这篇小说中,短暂的时间对天长地久的爱情构成了反讽,神女峰这一象征着永恒爱情的空间与武汉这一暗喻了物质和商业的空间也形成了反讽。倘若把这对恋人出游的时间拉长到十天半月,把他们的目的地改为武汉的黄鹤楼,再把女主人公改在九江下船私奔,时间和空间这样一变,故事的逻辑性虽说不受伤害,但小说的反讽性将荡然无存。
第二、因果框架
原因和结果是小说的另一对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不仅是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可以充当结构的有力支撑,并且能够形成一种因果型框架。在那些传统或正统的小说中,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一般都比较符合正常的逻辑,而在反讽性小说中,作家们却有意破坏了因果之间惯常的逻辑性,刻意制造出因果关系的种种悖论,以此对荒谬和矛盾的事物表示嘲弄、挖苦、讥笑和怀疑。
因果关系的悖论有多种情形,有的表现为动机与结局的错位,如薛荣《网络诗人咚咚锵》中的那个纪福良,他本来是为了搜集咚咚锵的女友陈芳芳在外出轨开房的证据,结果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自己的老婆也红杏出墙,也在外面开房了;有的表现为现象和实质的矛盾,如谌容《减去十岁》中的季文耀、张明明、郑镇海和林素芬这群人,听到每人将减去十岁的小道消息后,表面上说是要夺回十年浩劫浪费的大好光阴,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有的表现为出发点与目的地的背反,如手指《去张城》中的主人公,出行的目的是要去张城看望从前的女友小艳,没想到糊里糊涂把车坐反了,最后到的地方竟是张镇,与出发时预设的目的地相隔十万八千里。
因果关系的悖论实际上就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素的相互对比。他所说的两极对立因素的相互对比,实际上指的就是结构上的正反框架。他说:“把两极对立性因素的对照,作为营造结构性反讽的原则和手段,即通过对悖反性因素——悲与喜、顺与逆、雅与俗、严肃与荒诞——的对照性组织,以获得一种反讽效果。”①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需要指出的是,在反讽性小说中,作者并没有对正反两种因素持褒贬态度,他只是客观而冷静地展示两种因素之间的尴尬、滑稽与矛盾,对相互对立的两种因素不作任何评价和判断。正是因为作者的克制与谨慎,反讽结构才与一般性的讽刺形成了区别,显示出了比讽刺更为深刻的批判力量。
薛荣的《扫盲班》是一篇意味深长的反讽小说,它的正反两极是由悲剧和喜剧两种因素构成的。父亲在城市工作,母亲在农村劳作,因为长期分居,父亲对母亲产生了信任危机。母亲留着齐耳的短发,腰身细细的,颇有几分姿色。她每天夜晚去小学上扫盲班,父亲便怀疑她是打着学文化的幌子出去找相好,于是派女儿跟踪母亲。父亲临走前嘱咐女儿:“接下来扫盲班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你每天晚上跟着妈妈明白吗?你别让她知道,更不能说是我叫你跟着的,你要看妈妈有没有跟鬼在一起,有的话就写信给我。”②薛荣:《扫盲班》,《芳草》2007年第5期。女儿接受任务之后非常尽心,连续几晚都跟踪母亲,并发现她和右派老师陆子刚十分亲密,有一天晚上,母亲埋头写字的时候,陆子刚还走到母亲身边手把手教她抄写,女儿这时急了,立即冲上前让陆子刚走开。这件事让母亲很恼火,她从此再不让女儿跟着她。上述情节是小说的前半部分内容,显然充满了喜剧性。然而,情节的后半部分却走向了喜剧的反面。由于母亲不让儿女跟她去扫盲班,女儿就只好一个人无聊地呆在家里。随后的一个黑夜,一个叫大庆的小流氓突然找到女儿,将她骗到了一条船上,还让她脱光了衣服。懵里懵懂的女儿被大庆平放在船舱里,然后她感到两腿之间一阵钻心的痛。到此,由喜剧性跟踪引起的荒唐故事彻底步入了悲剧的深渊。在这篇小说中,母亲的喜剧和女儿的悲剧形成了一种正反框架,二者相互对比,相互反衬。有意思的是,作者对母亲的喜剧没表现出丝毫的责怪,对女儿的悲剧也没表现出应有的同情。正是由于作者不站在悲喜两极的任何一边,小说才产生了超越二元对立的总体性反讽效果。
徐晓鹤的《达哥》也设置了一个正反框架,构成此篇正反的两极分别是雅和俗。小说以知青达哥为叙事主线,展示了一代年轻人精神空虚、价值混乱、生活堕落的一段青春岁月。作品描写的全是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招摇撞骗、调戏妇女这类俗不可耐的俗人俗事,可是文本中却又处处充斥着春天、诗歌、哲学这些极为高雅的因素。比如小说一开头就写道:“诗人说,春天到了。我一看,春天果然到了。怪不得棉袄穿起来好热。石粒妹子没有睬他。这使我很高兴。既然春天到了,我决定还是去屙屎。”③徐晓鹤:《达哥》,《收获》1987年第4期。春天、诗人、屙屎,这几个关键词一下子就搭起了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雅俗框架。上山屙屎的时候,诗人首先说了一句风景这边独好,接下来两个人就谈到了落汤鸡、猪油和黄黄妹子的奶子。后来达哥打破了德宝的脑壳被抓起来,诗人去囚室看他时还给他带了一本《古代诗歌一百首》。夏天来了,达哥已经读了好几本哲学书。他因为害怕那种海带的气味,就不跟石粒妹子做爱了。达哥很想看到黄黄妹子的奶子,可几次都没看到。有天晚上,达哥跟狗卵讲起了哲学,说哲学如何如何重要,讲完之后,狗卵就去偷了一只鸡。往回走的路上,狗卵提出脱光衣裤走路,于是两个人就赤条条地走在大路上。有一次拦一辆车去贵州玩,达哥还买了一本《资本论》。最后达哥杀了人,又和诗人逃到了春天屙屎的那个山上。在徐晓鹤的笔下,雅和俗既对立又统一,它们相互对照,相互映衬,相互反讽。事实上,徐晓鹤在这里对雅和俗都进行了消解,在他看来,世界是荒诞的,既无所谓雅也无所谓俗,俗便是雅,雅便是俗。
正反框架有很多组织形态,除了悲与喜、雅与俗等两极对比之外,还可以有强大与弱小、勇敢与怯懦、崇高与卑微、严肃与滑稽、真实与虚假、忠诚与背叛等多种对比,这些对立的因素都能用来设置反讽性框架。
二、反讽结构的美学意味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一旦设置了反讽的结构框架,那它就具有了反讽的文体特征,进而形成一种反讽小说形态。反讽小说与一般的讽刺小说不同,尽管二者都以荒唐和矛盾的事物为表现对象,进而对它进行嘲弄、揶揄和怀疑,但一般的讽刺小说在主题传达上都十分鲜明,即作者的倾向性比较明确,赞成什么或批判什么,提倡什么或反对什么,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读者都容易看出来。而反讽小说则显得含蓄、内敛、暧昧,作者往往是有意将倾向性隐藏起来了。正因为这样,反讽小说从美学上超越了一般的讽刺小说,拥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如果说一般讽刺小说属于言语反讽,那么拥有了反讽结构的反讽小说则变成了情境反讽。学者南帆说:“言语反讽让人们站到反讽者的立场上,而情境反讽则让人们站到观察者的立场上。言语反讽具有讽刺性,情境反讽往往更具纯粹的喜剧性、悲剧性和哲理性。言语反讽的意义可以归纳在修辞、风格、叙述和讽刺形式等名目之下,情景反讽更易于引出历史和思想。”①南帆:《反讽:结构和语境》,《小说评论》1995年第5期。在南帆看来,情境反讽显然比言语反讽更有审美意味,因为情境反讽不再只是作品中偶然出现的几个反语之类的局部性反讽,而是支撑整个作品的一种反讽性框架,属于总体性反讽。下面,笔者将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试图对总体性反讽小说的美学意味作一些分析与归纳。
第一、戏剧意味
反讽小说的审美意味,首先来自反讽结构的戏剧性。戏剧性指的是由文本中种种对立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冲突而产生的紧张感、生动性与诱惑力,它是小说可读性的主要来源。
矛盾性是戏剧性的显著特点,也是戏剧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讽小说基本上都是以矛盾的事物为表现对象的,所以与一般的小说相比,反讽小说显然更有戏剧性。如铁凝的《春风夜》便是一个矛盾交织的文本,其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俞小荷与久别的丈夫相见却不能相欢,这对核心矛盾又带来了一系列的衍生矛盾,有情感与欲望的矛盾,有需要与法规的矛盾,有百姓与官方的矛盾,有生活与体制的矛盾,等等。这一连串的矛盾便构成了一系列的戏剧性冲突。同时,作者又熟练地运用了对比、夸张和调侃等戏剧手段,从而有效地强化了文本的戏剧性。比如将俞小荷做梦与她多给丈夫一百元钱这两个细节进行对比,就很有戏剧效果。再比如,作者用夸张的手法写旅馆服务员对夫妻约会的种种干扰,就很有小品的味道。还比如关于夫妻俩分床躺着看电视的那一段调侃式描写,也具有浓郁的戏剧色彩。
戏剧性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话性,即通过对话把那些冲突的本质表现出来。同时,对话还能制造一种舞台表演的效果,从而增强小说的戏剧性。如韩东的《反标》,写的是极左年代一个调查反标事件的荒唐故事。故事发生在一所学校,有人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了一则反标,反标就是反动话,反动话就是反过来说:打倒好人,坏人万岁。负责调查反标事件的是林老师,她说反标是不能复述的,重复也是一种反动。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林老师发现了新的情况,于是与学生卫东发生了以下对话。林老师问:“你真的看见反标啦?”卫东说:“嗯。”林老师问:“怎么写的?”卫东说:“我不说。”林老师说:“没关系,为了工作的需要嘛。你只说一次,就我们两个人,不会告诉第三个人的。”卫东说:“我不说。”林老师愣了一下说:“那你写下来。”卫东说:“我不写。”林老师说:“你写下来我看一眼就撕掉。”卫东说:“不干。”林老师说:“那你说怎么办?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你说看见了反标,反标到底写的是什么?”卫东这时反过来问:“林老师你见过那条反标吗?”林老师说:“我当然见过。”卫东说:“林老师你说写的是什么,如果说对了我就点头。”林老师紧张地问:“你想干什么?”卫东说:“要不然你写下来,看完后我们就撕掉。”以上对话十分精彩,林老师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由自己亲自设计的逻辑怪圈。面对谨慎而机智的卫东,林老师最后变得恼羞成怒、蛮横无理。“‘我看反标就是你写的。’林老师放下杯子,站起来,手里的铝勺指着卫东。‘别在我这儿花言巧语,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没见过反标。’”①韩东:《反标》,《收获》1992年第1期。在上述对话中,严肃与滑稽、政治与游戏、本质与饶舌、忠诚与狡猾等两极因素形成尖锐的对照,既嘲弄了那个扭曲的时代,又讥笑了那些变态的人,让文本充满了辛辣的反讽意味。
除了矛盾性和对话性,场景性也是戏剧性的基本特点之一。如苏童的《神女峰》便是由一个一个的场景连结起来的,而且场景与场景还形成某种对比。比如老崔第一次对描月提到武汉时,描月不无鄙夷地说,武汉有什么意思?我小姨妈就住在武汉,说夏天热死人,冬天冻死人,又没什么好玩的。在这个场景中,描月还没对老崔动心,所以有话直说,毫无遮拦。可是,当老崔握着描月的手再次提到武汉并要求她到武汉逛逛时,描月却久久说不出话,只是凝视着老崔那只手,过了好久才说:“我小姨妈就在武汉,她一直写信让我去玩呢。”作品中还几次写道了喝酒的场景、斗嘴的场景和劝架的场景,这些场景分开着看生动俏皮,对比起来看则更是绝妙,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潜藏着作者不露声色的反讽。
第二、滑稽意味
滑稽是一种审美范畴。与一般的审美范畴不同,它是以某种丑的因素作为审美对象的,实际上是一种审丑活动。它通过对某种丑的因素的集中与放大来引人发笑,从而达到审美的目的。由于不同类型的滑稽在性质上有所差异,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情感态度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可以是痛恨和鄙夷,可以是同情和惋惜,还可以是赞赏和钦佩。滑稽性的近义词有喜剧性、搞笑性、诙谐性和幽默性等。
在反讽结构的小说中,滑稽是一种常见的审美形态。反过来说,滑稽性是反讽小说的美学意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凸显审美对象的滑稽性,作家们常常运用的手法有戏仿和夸张等。
戏仿一词来自西方,最早的意思是指对已有文本的搞笑式模仿。作家刘恪说:“戏仿的希腊词根意为重复曲,可见它必然含有模仿之意,带有借用一个文本或一个作家的个人语言的技巧与风格,目的为创造一种幽默讽刺的效果。”②刘恪:《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戏仿有多种类型,可以是对已有文本的戏仿,如格非的《半夜鸡叫》明显戏仿了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毕飞宇的《武松打虎》明显戏仿了施耐庵的《水浒传》,也可以是对历史的戏仿,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还可以是对现实的戏仿,如王蒙的《冬天的话题》。但是,不管哪一种戏仿,戏仿的对象都必须要有丑的因素,即它的不和谐性或不合理性。比如王蒙的《冬天的话题》,它所戏仿的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毫无实用价值的形式主义。王蒙极富创意地假设了一个沐浴学家朱慎独教授,他是研究洗澡的,为了听起来有学术性,他把关于洗澡的学问称为沐浴学。朱慎独是国内外罕见的一位沐浴学权威。他费时十五年,写下了多卷本《沐浴学发凡》,“内容包括人体与沐浴、沐浴与循环系统、沐浴与消化系统、沐浴与呼吸系统、沐浴与皮肤、沐浴与毛发、沐浴与骨骼、沐浴与心理卫生、沐浴与青春期卫生、沐浴与更年期卫生、沐浴与家庭、沐浴与国家、工矿沐浴、战时沐浴、沐浴与水、沐浴与肥皂、浴盆学、浴衣学、搓背学、按摩学、沐浴方法论、水温学、浴巾学、沐浴的副作用、沐浴与政治、沐浴的历史观、沐浴与反沐浴、沐浴与非沐浴、沐浴的量度、沐浴成果的检验、沐浴学拾遗、沐浴学拾遗续(一)——续(七)等章,堪称洋洋大观,走在了世界前列。”③王蒙:《冬天的话题》,《小说家》1985年第2期。接下来朱慎独又有了崇拜者余秋萍,还有了反对者赵小强。整整一个冬天,关于沐浴学中洗澡的时间问题的争论便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这是一篇绝妙的戏仿小说,不仅整个文本戏仿了现实生活,而且《沐浴学发凡》也戏仿了那些空洞无物、华而不实、虚张声势的各类著作,充满了滑稽性,让读者读起来忍俊不禁。
夸张可以说是反讽的主打技巧。刘恪说:“反讽不可不夸张,只有夸张,滑稽形象才能失调。所有的不协调只有在夸张中才能感到比例失调。”①刘恪:《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杨争光的《万天斗》是一篇被评论界忽略的反讽小说精品,它通过夸张刻画了万天斗这么一个滑稽性人物。作品写了与万天斗有关的三个生活片断。第一个片断写胡太平夫妇一大早跑到万天斗门口大吵大骂,说万天斗踩断了他们家的一棵玉米苗,而万天斗却矢口否认。胡太平夫妇却不依不饶,女人还朝万天斗脸上吐了一口痰。这个片断显然有些夸张,即使万天斗踩了玉米苗,他们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吐痰的细节更是带有夸张色彩:“胡太平的婆姨从背后闪出来,嘴巴裂成喇叭花那样子,朝着万天斗。啐——万天斗听见了这么一声。万天斗看见了一团什么东西从那个小窟窿里飞出来,粘在他的脸上。他知道那是一种脏东西。”杨争光有意用夸张放大了人性中的仇恨因素。第二个片断写村长将万天斗和胡太平夫妇带到村委会,本意是为了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但是,村长还未来得及发挥作用,坛子的几句笑话已让他们的矛盾烟消云散。坛子当时正在村委会和几个人聊天,他说:“婆姨一生娃,不管有人没人,蹲下一扯,奶奶就嘟嘟一下从那里吊出来,往娃嘴里一塞,让娃娃拱,猪就是那么拱,真不值钱,和猪一模一样。姑娘,你们谁见过姑娘的奶奶,你敢把姑娘的奶奶捏捏?你不要命了。”万天斗和胡太平夫妇一听坛子的话就如醉如痴,似乎都忘了刚才发生的事。村长也忘了,他也被坛子的笑话迷住了。这个片断显然也是夸张,通过夸张凸显了人物精神世界的空虚、无聊和卑琐。第三个片断写万天斗忽然想起了马跟,马跟这之前买他羊时少给了他一块钱。万天斗一直怀恨在心,决定去找马跟了却这事。万天斗去找马跟时,马跟正好睡着了。他即兴从墙上取下一把剃刀,在马跟的屁股上划了两下,“他听见刀子划进肉里的声音,有点发涩。然后,他听见马跟叫了一声。”②杨争光:《万天斗》,《收获》1989年第4期。万天斗用剃刀划马跟屁股的这个细节已经夸张得近乎荒诞了,但是读者却看到了真实而可怕的人性中的另一面。如果把这三个片断连接起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的行动不太合乎因果逻辑,原因小,结果大,即因果失调。人物的滑稽性便从这失调的因果框架中油然而生,让小说充满了黑色幽默式的反讽意味。
第三、现代意味
现代指现代性,它是与传统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方法论。现代性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前者萌芽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盛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虽然有阶段性的不同,前者侧重启蒙,后者侧重解构,但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现代性。现代性反实用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保守主义,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颠覆性,二是破坏性,三是创新性。
现代性也有阶段性的不同,分为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如果说前现代性的核心是建立一种现代文明新秩序的话,那后现代性就是要怀疑、推翻、打破已有秩序。前现代性重在建构,后现代性重在解构。学者周宪把前现代性称为启蒙的现代性,把后现代性称为审美的现代性,他说:“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以数学或几何学为原型的社会规划,那么,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则是对这种逻辑和规则的反抗;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秩序的追求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就是对混乱的渴求与冲动;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对理性主义、合理化和官僚化等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正是对此倾向的反动,它更加关注感性和欲望,主张一种审美——表现理性;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当作一种对绝对完美的追索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则是一种在创新和变化中对相对性和暂时性的赞美。”①周宪:《现代性的张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如果用周宪的观点来看,反讽结构的小说显然追求的是审美的现代性。它对传统的秩序持一种怀疑主义态度,进而对它进行了冷嘲热讽。如韩东的《反标》,作者虽然借叙述者之口告诉我们反标写的是反动话,内容是:打倒好人,坏人万岁!但读者丝毫看不出作者对写反标者的谴责与痛恨,相反倒是对负责调查此案的林老师给予了无情的戏弄与嘲笑。林老师说:“在我们班,而不是别的班里发现了一条反标。内容就不重复了。重复反标也是一种反动,是替阶级敌人进行宣传。我们今天抄的这段毛主席语录里包括了反标中的所有字句以及标点符号。毛主席语录本身是革命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林老师讲话的内容、表情和语气都是严肃的、庄重的、深沉的,但字里行间却潜伏着作者的辛辣反讽,让读者感到滑稽可笑,从而让读者在这种可笑中对林老师的一本正经产生怀疑。为了查出写反标的人,林老师命令学生们用左右两手分别写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把语录收起来之后,林老师左边放着一叠,右边放着一叠。小说写道:“她发现左边的一叠是右手写的,右边的一叠是左手写的。她把两叠抄写的位置进行了调换。后来又觉得没有必要。学生和她对面而坐,他们的左边就是她的右边,他们的右边就是她的左边。把两叠抄写再次调换。过后再次觉得没有必要。”②韩东:《反标》,《收获》1992年第1期。韩东运用他冰霜般的冷幽默,对林老师这一卫道士形象进行了不露声色却如刀刮骨的挖苦、揶揄和讥讽,表现了作者对极左政治和政治高压的怀疑与不满,进而彰显出一种审美的现代性。
On the Ironical Struc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Novels
Xiao S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In contemporary novels,ironical structure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many writers.Compared with other structural forms,irony has its major characteristic in the framing of structure.This paper argues that ironical novels have often used three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the framework,including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cause-effect structure,and the positivenegative structure.Meanwhile,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ironicalstructure within which the novel’s unique aesthetics is fully demonstrated.
Contemporary Novels;Irony Structure;Framework;Aesthetics
责任编辑:於可训
晓苏(1962—),男,湖北保康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间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