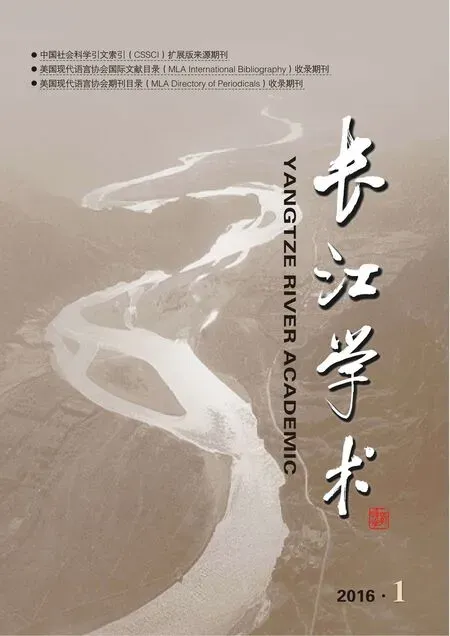刘永济的曲学研究
2016-12-05陈文新
陈文新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刘永济的曲学研究
陈文新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刘永济的古典戏剧研究,和同时代的王国维、吴梅一样,始终以曲学为中心,体现了鲜明的“民国范式”。其《宋代歌舞剧曲录要》聚焦于歌词,而对歌词的考察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歌词的唱法;歌词是否能够表现完整的故事;歌词是叙事体还是代言体,展现了完整而典型的戏曲史视野。《元人散曲选》是刘永济散曲研究的主要成果,其特点是从“风会”入手,在与诗词的对比中,准确揭示了散曲的文类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具有显而易见的文学史意义。
刘永济曲学宋代歌舞剧曲元散曲
刘永济对曲学的留意始于1932年就聘武汉大学教授之时。他为《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撰写的“学程内容”有云:“《戏曲》:本学程(一)从史的方面讲体制的变迁,及各代重要作家和作品等等。(二)从声律方面讲戏曲的格律。(研究问题和课外读物与词同)”①徐正榜、李中华、罗立乾:《刘永济先生年谱》,刘永济:《诵帚词集云巢诗存(附年谱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8页。其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宋代歌舞剧曲录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后收入中华书局2010年版《刘永济集》;《元人散曲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后收入中华书局2010年版《刘永济集》;《戏曲志》,已列入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刘敦纲负责整理,尚未出版。
一、刘永济曲学研究的范式
说到刘永济曲学研究的造诣与成就,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其研究范式或路径选择有何特点?
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留意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范式演变的状况。1978年春,中山大学董每勘教授写了一篇讨论戏曲研究范式的论文,题为《说“歌”“舞”“剧”》。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戏剧,称为“戏曲”是不尽恰当的。“原因是构成戏剧的东西,‘舞’是主要的,‘歌’是次要的,所以我不多说‘歌’,便于明确主次之分。过去的曲论家们对‘戏曲’的认识错误就都由颠倒了这种区分而来,他们不知道‘戏曲’是‘戏’,只知道它是‘曲’,尽在词曲的声律和辞藻上面兜圈儿,结果取消了‘戏’。曲论家非剧论家,而是纯粹的词曲家,压根儿不懂得‘戏’。”②董每戡:《说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2页。董每戡所说的“戏”,核心是行动,是有矛盾冲突的行动,所以,“戏剧没有矛盾冲突的行动便不成为戏剧。”③董每戡:《说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董每戡对于戏剧冲突的强调,从其研究理路来看,其实是把研究话剧的方式用于研究中国古典戏曲。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颇为盛行,那个年代关于中国古典戏曲的人物分析和情节分析的论文和著作中,“戏剧冲突”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1994年10月,比董每戡晚一辈、也是中山大学教授的黄天骥,为其朋友李修生的《元杂剧史》作序,就那个年代流行的戏曲研究范式提出了批评意见:
近几年,学术界对古代戏剧的研究,似乎处在“卡壳”的阶段。有些论著,不能说写得不深不细,但始终在几十年耕筑的框架上徘徊,学术水平没有新的进展。究其原因,我想,很可能是由于研究者没有摆脱苏欧戏剧观念的约束,依然以苏欧的话剧理论,作为分析评价中国戏曲的依据。例如,在剖析戏曲作品时,往往只着意于捕捉戏剧矛盾,抓住人物性格的冲突,审视矛盾的契机。这样做,自然是必要的,但却不能解决中国戏曲评论的全部问题。因为我国的古代戏曲,既是“戏”,也是“曲”。所谓“曲”,实即诗。在剧作中,“曲”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加上戏曲作家,往往就是诗人,当他们安排关目,表现人物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诗歌创作特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而诗歌创作,最重“意境”,注重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景物相融合,从而诱导读者产生联想,参与创造,体验形象之外的涵义。以我看,戏曲作家特别是杂剧剧作家,有不少人致力于意境的追求。因此,王国维、吴梅在评价戏曲时,都曾把意境作为重要的标尺。当然,有意境的剧作,未必有尖锐的戏剧冲突,戏剧性、舞台性或会稍逊,但是,如果一味以苏欧话剧的标准来衡量,死扣现实主义之类的概念,从而否定或者贬低这些戏曲作品的价值,那就不符实际了。①李修生:《元杂剧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首2—3页。
读了黄天骥的这一段批评,我们有一种仿佛重游故地的感觉。在董每戡之前,如王国维,如吴梅,如刘永济,他们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以曲学为中心,并不重视戏剧冲突,也因此受到了董每戡的非议;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古代戏曲的研究中,戏剧冲突的分析泛滥成灾,中国古代戏曲的民族特色遭到漠视,也因此受到了黄天骥的非议。汪曾祺在1989年第8期《人民文学》发表的《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一文,曾这样强调戏曲的民族特色:“中国戏曲,不很重视冲突。有一个时期,有一种说法,戏剧就是冲突,没有冲突不成其为戏剧。中国戏曲,从正出看,当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各场并不都有冲突。《牡丹亭·游园》只是写了杜丽娘的一脉春情,什么冲突也没有。《长生殿·闻铃·哭像》也只是唐明皇一个人在抒发感情。《琵琶记·吃糠》只是赵五娘因为糠和米的分离联想到她和蔡伯喈的遭际,痛哭了一场。《描容》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抒情诗,赵五娘并没有和什么人冲突。这些著名的折子,在西方的古典戏剧家看来,是很难构成一场戏的。”②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9页。汪曾祺和黄天骥所针对的,乃是同一种研究范式。
范式是美国哲学家T.S.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代表了一种共同的理念、共同关注的问题、共同遵守的操作规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学术史的演进常常表现为范式的更替和“革命”。具体到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从强调“曲”,到强调“戏”,再到今日的“戏”“曲”兼重,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范式演进,其脉络是极为清晰的。以这样一个学术史背景作为立论依据,可以说,无论是以曲学为中心,还是以戏剧冲突为中心,或者说,无论是以戏曲词章为中心,还是以舞台艺术为中心,都有其部分的合理性,只是不能以自己的学术立场抹杀对方。
厘清了上述事实,就可以对刘永济的路径选择加以确认了:他的古代戏曲研究,和同时代的王国维、吴梅一样,始终是以曲学为中心的,体现了鲜明的“民国范式”。考察其建树,务必留意和尊重这一事实。
二、刘永济的宋代歌舞剧曲研究
《宋代歌舞剧曲录要》是一部作品选集,选录对象是宋代的歌舞剧曲。宋代的歌舞剧,包括大曲、舞曲、曲破、法曲、鼓子词、转踏、赚词、诸宫调等。这些歌舞剧,通常有歌,有舞,也有歌词。刘永济的关注重心是歌词,而他对歌词的关注,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这些歌词的唱法;这些歌词是否能够表现完整的故事;这些歌词是叙事体还是代言体。其研究展现了完整而典型的戏曲史视野。
何以要研究宋代歌舞剧曲的唱法?因为这才能找出元杂剧唱法的源头,才能确认宋代歌舞剧曲在戏曲史上的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在“戏曲音乐·戏曲音乐史”的目录中列入了鼓子词、大曲、唱赚、转踏、诸宫调等,而在“中国曲艺发展简史”的目录中也列入了唱赚、转踏、诸宫调、鼓子词,仅大曲没有列入。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戏曲曲艺》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目录第6—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这两份目录表明,唱赚、转踏、诸宫调、鼓子词在严格的意义上属于曲艺,但其音乐直接影响了元杂剧等成熟戏曲样式,从音乐的角度看,这些宋代歌舞剧名目,是曲艺,也是戏曲。吴梅曾著有《元剧略说》一文,开头便道:“我讲这个题目,须要晓得宋词、元曲的分别究竟在那里。原来这曲子的起源,并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是从宋朝的大曲变成来的。宋朝大曲,现在留传下来的,不过七八套,都是文人墨客弄笔头的把戏。内中名目,倒也不少。什么叫做【水调歌】咧,【道宫薄媚】咧,【逍遥乐】咧,我们但把曾慥编的《乐府雅词》一看,便都知道了。但是他的唱法段落,完全与唱词的法子不同,差不多要费几十倍的辛苦。宋人的词,唱完一首就算了事。他却是联串了许许多多,至少的一套,也要有八九只,而且还要带唱带舞,所以觉得非常麻烦。《宋史·乐志》里头说:‘春秋圣节,三大宴,小儿队,女弟子队,各进杂剧对舞’,就是这种顽意儿。但宫里的杂剧曲词,民间是不会晓得的,所以没有传下来,现在就将曾慥编的几套,细细推究起来,知道就是元剧的根由来历。何以见得呢?这种大曲虽是全用词牌凑拢来的,但是却有许多名目。一套里头,有散序,有入破,有虚催,有实催,有衮拍,有歇拍,比较现在戏剧,什么慢板、倒板、二六等名色,也算得是一样的。元剧里面,每出曲子,一定有八九只,多的也许有十七八只,唱起来先慢后快,还有锣鼓按定拍子,竟是同大曲一鼻孔出气的。我就决定元剧是宋朝的大曲变成的。”②吴梅:《元剧略说》,原载《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号》,参见吕薇芬选编:《名家解读元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刘永济对宋代歌舞剧曲唱法的研究,重心是阐释一系列专业术语,如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杀衮等,宗旨则是揭示其戏曲史意义。而就具体的阐释而言,刘永济虽然大量参考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但有些地方,例如关于“中序”、“排遍”、“叠遍”等术语之间的关系,确比王国维说得更加明晰一些。
刘永济之所以关注宋代歌舞剧的歌词是否能够表现完整的故事,原因在于,表演故事是戏曲的特点所在,如周贻白所说:中国戏剧“能形成一项独立艺术部门,追本溯源,应当是以表演故事为主,逐渐地以他项艺术来丰富其表演形式,然后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的综合性的艺术”③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戏曲是综合艺术,需要音乐、舞蹈和故事表演的高度融合,而骨干是表演故事。刘永济之所以关注歌词是叙事体还是代言体,原因在于,戏曲的特点是演故事而不是讲故事。“表演的意思,是把一个故事的全部情节或部分情节,由演员们装扮剧中人物,用歌唱或说白,以及表情动作,根据规定的情境表演出来。”④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刘永济《文学论》第二章曾将表演分为两类:“一、表演实际者,作者以语言或文字将此实际之情节直达于人,人得因之以知其是非善恶、原因结果,故为学识之事。演说及信札属此。二、表演想象者,作者自身或他人将其想象中之情节扮演以直达于人。人观其情节,即生感应而自觉其善恶是非与因果关系,故为感化之事。戏剧属此。”⑤刘永济:《文学论默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页。所谓表演想象中的情节,即代言是也。由上述两个关注点可见,刘永济的戏曲研究,虽以歌词为中心,但他是在戏曲视野下关注歌词,而不是把歌词视为孤立的韵文作品。
从戏曲需要完整的故事以及戏曲需要表演故事这样两个角度,刘永济在《总论》中系统考察了宋代歌舞剧曲,对不同作品在戏曲史上的贡献作出了清晰的定位。“唐代大曲皆类聚诗人描写闺情、友谊及边怨的诗作成全曲,彼此不相连贯,宋歌舞剧曲除鼓子词分咏景物,调笑转踏分咏美人故事及名胜古迹者外,如董颖的《道宫薄媚》十遍咏吴越事,曾布的《水调歌头》七遍咏冯燕事,史浩的《剑舞》咏鸿门宴及公孙大娘舞剑器事,已具戏剧的雏形。而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十二首以元微之《会真记》崔张故事为题材,则更与后世爱情悲剧相近,故毛奇龄《西河词话》视为戏剧之祖。杨万里《归去来兮引》,隐括陶潜《归去来辞》,以数曲代一人之言,变旁述体为代言体,尤与后世戏剧的体裁相似,故王国维谓为元人套数杂剧之祖。此等剧曲则较之唐人更为进步了。盖宋代剧曲既上承唐代大曲之后,又下开金、元杂剧之先,实古今戏剧发展的枢纽也。”①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25页。这一段结论内涵丰富,不宜草草读过。
刘永济何以断言董颖的《道宫薄媚》、曾布的《水调歌头》、史浩的《剑舞》“已具戏剧的雏形”?尤其是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更被誉为“戏剧之祖”,其缘由何在?答案是:这几个大曲作品都表演了完整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更是表演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悲剧爱情故事。对于完整故事的重视,启发刘永济注意到了宋代歌舞剧曲中两种不同的“咏故事”的方式:“鼓子词皆用一曲连续歌之,以咏故事。其方式有二:一为横排式,一为直叙式。横排式者,并列同性质的故事,以同一词调歌咏之。直叙式者,直述一事的首尾,亦以一调反复歌咏。此式适宜于敷衍故事,较之横排式者,有显著的进步。”②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22页。所谓“有显著的进步”,是从“敷衍故事”的角度作出的评判;而之所以重视“敷衍故事”,在于这是戏曲的标志之一。“唱曲子,本是种表演艺术,因此敦煌曲词中便有演说故事的。如《凤归云》二首,不但完全代言,且用语体,极合舞台对白之用。这类词,当时或配合到歌舞戏、参军戏、俗讲中,以供演唱。其他《十二时》等,大概也是兼有演唱的。宋·赵德麟《蝶恋花》咏崔莺莺故事,亦属此类唱故事的词,只是无说白罢了。这种演唱故事的曲子,到金朝时发展出诸宫调。也就是从前只用一个宫调一个曲子,反复地唱故事,后来则用好几个曲调组合成套,间以说白,便成了一种剧曲,可以演说故事。”“也就是说,曲子有一路是朝组曲并演说故事发展的,在元代,这就成为了剧曲。那些仍维持单曲且不演说故事的就叫散曲小令,套取的叫套数。”③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下),台北:里仁书局2010年版,第210—211页。“敷衍故事”是剧曲之为剧曲而非散曲的一项重要标志。
刘永济对杨万里《归去来兮引》的推重,在于它不仅敷衍了故事,而且改“旁述体为代言体”,其敷衍故事的方式“尤与后世戏剧的体裁相似”。刘永济的这一说明,仍着眼于戏曲的历史发展,显示了一个戏曲史家的眼界。当然最早发现这一事实的并不是刘永济,而是王国维。《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在杨万里《归去来兮引》原文之下对此有一段说明:
王国维《戏曲考原》曰:“此曲不著何宫调,前后凡四调,每调三叠,而十二叠通用一韵,其体于大曲为近。虽前此如东坡《哨遍》檃栝《归去来辞》者,亦用代言体,然以数曲代一人之言,实自此始。要之曾、董大曲,开董解元之先,此曲则为元人套数杂剧之祖。”王易《词曲史》云:“以今考之,则其第一、第四、第七、第十调为《朝中措》,其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调为《一丛花》,其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与谱载无名氏之平韵《望远行》较近,然俱不用换头,且纯为代言体。诚斋生于绍兴初,卒于开禧二年,则此曲之作,殆与董解元《西厢》同时。然则元人杂剧,固参合宋金两邦歌曲体裁以成一种新体。”①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3页。
由此看来,王国维是现代关注杨万里《归去来兮引》以代言体叙事的第一人,而王易、刘永济又先后对这一事实给予了关注。不无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学者们提到变叙事体为代言体,通常仍只注意到诸宫调。如吴组缃、沈天佑《宋元文学史稿》:“在宋代歌舞戏如大曲、曲破中所述情节虽用的是叙述体,但其中已有歌、有舞、有念白表现。特别是诸宫调的出现,已十分接近于戏曲的形式。当然,作为戏曲题材,必须由叙事体转为代言体。而在《西厢记诸宫调》的散文中已开始出现了某种代言体的倾向,因此,诸宫调这种说唱文学对促使元杂剧艺术的成熟,关系尤为明显。”②吴组缃、沈天佑:《宋元文学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曲破”,原文误作“曲波”。如果我们注意到宋代的歌舞剧曲已开由叙事体转为代言体的先例,戏曲史研究的视野也许会更加开阔一些。
三、刘永济的散曲研究
《元人散曲选》是刘永济散曲研究的主要成果。他为《元人散曲选》所写的《序论》,1936年刊发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5卷第2期,集中表达了其关于散曲的理论思考,尤有分量。其特点是时时注意与诗词的对比。
文体本质上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中国古代文论对于辨体的兴趣,并非建立在琐碎的技术性的评价的基础上,相反,它总是从大处着眼,力求宏观地揭示出每一文体的属性。因此,假如我们缺少感性的辨体能力或理性的辨体指导,对古代各种文体“一视同仁”,那是会闹出笑话的。就中国古代的文体而言,不仅诗与文在审美品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如果在现代的文体分类框架下讨论古代诗、文,不难发现,古代诗、文内部的各种体裁类型之间,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我们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一类,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将诗(古诗、近体诗)、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之外。如果我们套用现代的散文标准来阐释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小品文,或套用现代的诗歌标准来阐释诗(古诗、近体诗)、词、散曲,如果不犯信口雌黄的错误,至少也会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很难说到点子上。刘永济对诗、词、曲的辨体考察,其学术意义在于,有助于读者对研究对象做准确把握,有助于在文化转型时代较为亲切地理解古人。
刘永济注意到:与唐宋诗词相比,元代的散曲尤为适宜于敷衍故事,杂剧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散曲的兴盛。“试以元人散曲之用,较唐宋人诗词之用,其显有进境者,莫如咏事。约举之有两端焉。诗中虽有长篇记事之作,词中虽有联章分咏之体,(如大曲董颖之《薄媚》、曾布之《水调歌头》、赵令畤之《商调蝶恋花》以及无名氏、郑仅、秦观等之转踏。)惟以字句整饬,措辞雅洁之故,未能生动自然。一也。赋家虽以铺布为体,然铺布之类有二:一曰横铺,二曰直布。横铺者,平列枚举,无时间之联贯者也;直布者,原始要终,具一事之端末者也。诗词之用赋,每多取横铺之法,而散曲则习用直布之体。二也。(横铺之式,亦有存于杂剧套曲中者,凡曲中分写春夏秋冬之景,或平列渔樵耕读之事者是。)惟其如此,故于扮演故事尤宜,剧曲之作,乃缘之而始盛。然则,欲工为剧曲者,当以小令为始事。小令既工,而后求联调成套,联调成套既精熟,而后讲联套成剧。斯二者,形制虽殊,而小大同贯;品质无二,而先后异功。学者于此,可以悟散曲与剧曲相关之切矣。”③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0—151页。元代的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读了刘永济关于元杂剧之兴盛得益于散曲之兴盛的分析,对元曲这一术语的内在合理性可以获得较为深切的理解。
散曲的兴起,与宋金时期北方胡曲的传入以及词的衰亡密切相关。在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人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还保存有其时流行的若干少数民族乐曲曲牌,如[阿纳忽]、[胡十八]、[唐兀儿]等。与此同时,一些民间俚曲在北方的一些地区流行开来。元人燕南芝庵指出:“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指汴梁)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①〔元〕燕南芝庵:《唱论》,见〔元〕杨朝英(随庵)辑:《乐府新阳春白雪前后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63册集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在这种背景下,词因为与音乐脱离而无法适应新的音乐形式,一种与新曲相结合的新的文学形式——散曲遂应运而生。从现存的散曲来看,它与诗词相比,在形式上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句式更加灵活,更接近口语。诗歌虽然也有杂言,词也被称为长短句,但散曲每句字数可任意变化,而且还能使用衬字,因此句式更加灵活多变。如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尾曲[黄钟煞]首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②关汉卿著,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03页。,按格律此句应为十一字句,加上“蒸不烂”等四个作衬的短语,就变成了二十三字,大大丰富了其表现力。第二,散曲的韵律,用的是北方音韵系统。与诗只押平声韵不同,散曲可平仄通押,且不避重韵。第三,散曲的对仗形式更加丰富。根据《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等的说法,有扇面对、重叠对、救尾对、合璧对(两句对)、鼎足对(三句对)、联珠对、隔句对等不同的对仗形式。多种对偶形式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散曲的表现力,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散文化的倾向。所有这些,都增强了散曲的叙事功能。刘永济由此切入,说明散曲与诗词的重要区别,是极有学术眼光的。
与许多学者一样,刘永济考察散曲与诗词之别,颇为关注相互之间的风格差异。“其为之也,有与词家大异者。兹就元人散曲观之,约有四端。一曰豪辣。豪辣者,气高而情烈,其言也,喷薄銛锐,鞭辟入里之谓也。二曰宏肆。宏肆者,挥斥八极,横放杰出,绝无顾借之谓也。此二者,盖有得夫阳刚之美者。三曰鲜丽。鲜丽者,生香真色,如出水芙蓉、浣纱西子,天然去雕饰之谓也。四曰流利。流利者,圆转自如,若明珠走盘,弹丸脱手之谓也。此二者,盖有得夫阴柔之美者。夫阳刚、阴柔者,文学之通性,今独以之论元人散曲者,惟散曲作者为能造其极、为能尽其用也。”③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9页。其《评介元曲家睢景臣〈高祖还乡〉套曲》一文,就此作了更加简要的说明:“古典文学中,元曲是生面别开的。在它以前的各体文学都是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的。在元曲便哀而伤,乐而淫,怨而怒了。以前的文学要含蓄,元曲却贵于痛快。”④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2页。刘永济的这种比较分析,可与任讷《词曲通义》的说法相互映发:“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弛、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词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⑤任中敏:《词曲通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9页。比照两位前辈学者的论述,真可用“英雄所见略同”来加以形容了。我们常说:词以婉约为正宗,而豪放为别体;散曲以豪放为正宗,而婉约为别体。所谓正宗、别体之分,强调的正是词、曲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差异,在解读词、曲时就不免说外行话。当然,这并不是说元散曲中没有含蓄蕴藉之作,只是,“其有风流蕴藉,含蓄不尽者,要亦不能出词家之牢笼,遂亦不能称曲家之独造。”⑥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1页。
元散曲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刘永济总结了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其一,受北方“土风”的影响。“盖南人之赋情也,或含思凄婉,或悱恻伤情,务极缠绵婉转之致。北人伉直,不习为此,故虽别情闺思之作,时挟深裘大马之风。不知者或讥其拙,实乃‘乐歌土风’,自然之理。北曲因此,别饶风味。求之于古,则北朝乐府,与之仿佛。”①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0页。其二,“文体穷变之势使然。”②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2页。盖含蓄蕴藉,本为中国古典诗词所长,“后来者无以易之。惟其如此,故曲乃别启土宇,与之争霸,终乃并吞八方,囊括千古焉,岂非文家之奇观哉!”③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1—142页。其三,时代的影响。“盖汴、洛本汉、唐文物最盛之邦,北宋之初,犹能继轨前代,增华囊时。一旦宗社迁移,沦为异域,北方人士,已失去此文化之中枢。及金、元相继入主,中原人士,望霓旌之无日,伤汉仪之难睹,又自深其摧痛冤结之情。而元之初盛,挟其金戈铁马之势,蹂躏中原,几不知声名文物之足贵。昔时丰镐,今化胡沙,血气之伦,尤增哀愤。于是沉霾厄塞,与日俱深。加以异种枭雄,猜忌汉人。情既炽烈,法亦严酷。于是才人志士,既慑其威力,复沉抑下僚,乃入于放浪纵逸之途,而悲歌慷慨之情,遂一发之酒边花外征歌选色之中。故写怀,则崇五柳而笑三闾;言志,则美严陵而悲子胥。其放浪纵逸之极,或甘沉湎,或思高蹈。饮酒则必如刘伶之荷锸,轻世则必如许由之挂瓢。又或凤帐鸳衾,极男女暱亵之致;爇香剪发,穷彼此相思之情。传神写态,必寸肌寸容而尽妍;绘影摹声,无一言一动之或讳。铸词则雅言与俚语齐观;用事则经史偕小说同量。举凡囊时文家所禁避、所畏忌者,无不可尽言之。”④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2—143页。在文学史研究中,刘永济以提倡关注“风会”著称:“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派别近私,风会则公也。言派别,则主于一二人,易生门户之争;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盖风会之成,常因缘此三事,故其变也,亦非一二人偶尔所能为。自来论者未能通明,故多偏主,或依时序为分别,或以地域为区划,或据作家为权衡。”⑤刘永济:《词论宋词声律探源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5页。西方学者中,丹纳的《艺术哲学》关注艺术的总体生存环境,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潮流》关注一个时代的总体风尚,其实也是一种“风会”研究。刘永济对元散曲兴盛原因的说明,则是其“风会说”的具体实践:他不是将作家、文体和时代等因素割裂开来加以考察,而是着眼于由这些因素所共同促成的“风会”,其分析因而极具文学史意义。刘永济“风会”说的理论价值可与丹纳、勃兰兑斯的建树相提并论,而其具体实践也具有显著的示范意义。
元代散曲家的作品,刘永济《元人散曲选》选入最多的几位,前期有马致远(小令十七,套数四)、关汉卿(小令十五,套数二)等,后期有乔吉(小令三十七,套数三)、张可久(小令三十,套数一)等,大体与各自的文学史地位相称。刘永济很少就某一具体的散曲作品写成文章,唯一的一篇是《评介元曲家睢景臣【高祖还乡】套曲》,原刊《长江文艺》1954年6期。这是关于睢景臣《高祖还乡》套曲最早的专题文章,也是迄今最权威的文章之一。在这篇六千字左右的文章中,刘永济就套曲的体制特点、睢景臣的生平、《高祖还乡》的题材、这个套曲的八支曲子等一一作了具体分析,精彩之处甚多。例如对《高祖还乡》尾曲的分析:
尾曲全用滑稽笔调来结束全套,是曲家最本色当行的手法。这位乡友居然向皇帝讨债,已经够滑稽了,还说“差拨内旋拨还”,“税粮中私准除”都可以,并且说出“谁肯把你揪捽住”,你又何必“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更是出奇了。总之全曲把皇帝的排场逐步增强,到了三煞曲,是达到最高度,忽然,奇峰突起,这位尊严的皇帝却原来是连他的“根脚”都熟悉的人,于是倾筐倒箧般把他的无赖行径都说出来。于是所谓皇帝也者,就毫不足奇了。这种写法是作者艺术性的高度表现。他是把外表尊严的神圣的一面,和内在平凡的丑陋的一面,两两相形的写法,突出地显示,使读者自然感到惊奇。他之能压倒同时的作家也就在此。……我想通过这一套曲,顺便谈谈元代曲家的共同思想,就是把帝王卿相,富贵功名,看成一钱不值,或用嘲弄的口吻,或用轻蔑的语调,或用叹息的神情,使得那些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都成为可怜可厌的东西。①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1页。
刘永济的评介,其特点是,既具有行家的专业深度,又具有良好的艺术感觉。这篇评介文章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为多种重要曲学文献所收录,原因在此。
Liou Yeong-jih’s Researches on Operas
Chen Wenx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As Wang Gwo-wei and Wu Mei,Liou Yeong-jih’s researches on Classic Drama always focused on Opera Study, which take on distinctive academic features of that age.focuses on lyrics,and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aspects:the way the lyrics were sung;what a complete story the lyrics implied or shown;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lyrics,all those three aspects reflectes a complete and distinctive vision of Drama Historywith the comparison with Shi and Ci,he accurately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the birth of SanQu’s appearance and what are its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which are significant to literary history.
Liou Yeong-jih;Opera Study; is Liou Yeong-jih’s main achievement in SanQu research,and characterized in his notice ofSanQu in Yuan Dynasty
责任编辑:陈水云
陈文新(1957—),男,湖北公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研究。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资助项目“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11—27410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