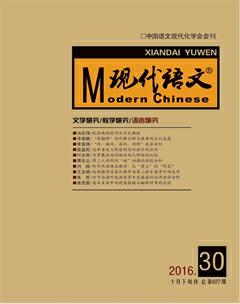北村:盛名之下的无力写作
——以《我和上帝有个约》为例
2016-12-03李颖颖
○李颖颖
北村:盛名之下的无力写作
——以《我和上帝有个约》为例
○李颖颖
摘 要:从先锋写作到基督教作家身份转变,北村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作家,并因其对人类灵魂中罪行进行审视和叩问的神性写作而享有盛名。然而因其理念先行和宗教先行等观念,其作品中出现了说教意味浓重、结构和人物设置模式化等弊病,笔者试图以《我和上帝有个约》为例分析其种种弊病对于作品文学性和艺术魅力的损害,以及盛名之下文本所呈现出的无力写作的状态。
关键词:精神审视 说教性 模式化 无力写作
从先锋文学创作的崭露头角再到基督教作家的身份转变,北村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然而这种重要性和意义并不在于北村的作品拥有多么精湛的叙事技巧或是深刻的表现力,而是源于其小说对于时代的观照以及对于人性的洞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呼唤能表现中国当下的文学叙事,精神的匮乏早已成为人人皆知的表症,知识分子在价值意义混乱的年代或丧失坚守、混迹文坛,或寄希望于时代转型、文学转型,或顺服于某种文学机制,而北村的深刻性正在于在中国历来缺乏罪感意识的传统之下,透过种种精神匮乏的表症,深入人们的内心,洞察人性中的罪性,并呼吁“良知的写作”和“良心的立场”。北村转型后的写作一直贯穿“罪与救赎”的主题,他一方面呈现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罪行和人性中种种的罪性,一方面积极地寻求着罪的救赎之路,《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等作品大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通过“罪—忏悔—救赎”的叙事模式,在真实的生活中探寻人的精神向度,揭示出人类灵魂中的罪性,并在神性救赎之下进行理想主义人格的塑造,从而奠定了北村在新时期文学书写中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
北村曾在小说中说过:“人有两种罪,一种是罪行,具体的罪行;一种是罪性,是内心的想法”,罪行大多是从社会角度出发所描述的种种社会问题,而罪性则是突破这一角度之后向着人的精神和灵魂开进的维度,《我和上帝有个约》以新闻纪录片式的叙述模式还原了血腥、残酷的杀人场面以及各个赤裸裸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展现出时代的罪与恶,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主人公陈步森以及其同伴种种的罪性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原因,而是进一步揭露出这一外在原因背后的人性深处的罪,并在小说中追问罪与爱、自义与公义等精神命题,因而才有了陈步森杀人之后精神的痛苦挣扎和深刻忏悔,主人公的忏悔是其灵魂深处罪感意识的觉醒,这与认错不同。中国历来缺乏忏悔的文化传统,因而中国人常常善于道德层面的认错却不善于灵魂层面的忏悔,认错是向外的,是对于他人承认自己错误的一种行为,忏悔则是向内的,是对自我灵魂的叩问和审视。《我和上帝有个约》中作者以一种介入现实的姿态,通过一个杀人案件将社会中一系列热点和每个人的罪性或罪感引出,从而拷问人性的罪恶和灵魂的变异。
然而文学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并从什么层面来介入现实、言说当下?关于这一点,有“中国《罪与罚》”之称的《我和上帝有个约》却在盛名之下呈现出一种无力写作之感。尽管北村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之前其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不会影响到他之后的创作,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前就想着如何把小说改编为电视剧是不恰当的,但是其作品中呈现出的新闻报道式叙述、影视化倾向仍然影响到了作者对于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的重构。在信息时代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已经看多了甚至习惯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罪恶,在对这些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事件进行文学化的重构时,如何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与激荡从而传达出作者所想要表达的理想价值是一项重要的叙事技巧,虽然前文中已经提到北村的小说并不以精湛技巧取胜,然而新闻式的重复报道和导演般全知全能的视角已然造成了小说盛名之下的无效叙事,甚至影响了文本的价值意义以及文学表现力。
阅读北村,读者常感于他的急切,作者在各个作品中常常急切地想要表达他的信仰,因而字里行间便带有一种匆忙之感,说教意味浓重。作者像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导演,为了凸显他的思想,小说中的人物便如同一个个提线木偶按照他的一言一行严格地进行表演,文中的牧师苏云起便是作者传教布道的代言人,他的每一次出场和发言都是作者内心的呼喊和对其信仰的诠释:面对现实的种种打击,背负种种罪名的人物在《圣经》的感召下信仰基督教便得到救赎,否则便在精神的折磨中疯癫或者死亡。从全文来看,关于“陈步森是否真心悔过、能否获得原谅和救赎”这一问题,作者安排苏云起与陈三木进行几次辩驳,并借他们之口探讨了基督教中“自义与公义、罪与爱”等种种精神问题:在陈步森被判死刑之后,一些基督徒对于上帝之爱产生了怀疑,“上帝既然让他的事路人皆知,就一定会主宰这件事,不让他经历死刑,而是好好地活在地上,为的是作更大更好的见证,可是现在结果却相反,一个洗净了罪污的人却死了……”[1],此时作者借苏云起之口阐述了上帝的爱与公义这一二元悖论,“信仰和正义是合一的……陈步森灵魂得救是一次他和上帝之间的救赎事件,就是个人和上帝之间有一个关系,但社会和上帝之间也有一个关系,在后一种关系中,法律是最重要的线索,即使法律可能不完善,仍需要遵守,救赎是使陈步森得永生,不是救赎他曾经的恶言恶行,他必须对自己的恶言恶行负责任”。尽管这段话很好地诠释出了上帝的爱与公义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急切地宣扬“信得永生”的信仰,文中陈步森在接受上帝之后形象被圣化,小说的整体倾向由挖掘人性中的罪性转变为宣扬陈步森有信仰之后的忏悔并为其争取原谅和减刑,其基调已然和基督教中的律法观出现偏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曾写到基督徒索尼娅在得知主人公杀人犯下罪行之后的反应是让他走到广场中心跪下,向人们认罪,接受惩罚,与陀式对比,北村小说中所宣扬的基督教精神有未体会深刻而出现偏离之嫌,北村在小说中所宣扬的信仰是被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浸染过的,尽管有大段大段基督教布道式的说教,但其核心又似乎是中国传统的“杀人偿命以及法理不外乎人情”,因而文本叙事呈现出暧昧不清的状态,宗教情结的过度渗透使得小说中宗教的诉求高于文学的本身,削弱文本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增加了小说说教的功利色彩。
正如北村所说“我对这些作品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为了强调其坚守的宗教美学,作者不惜牺牲小说的艺术价值,结构模式化、说教意味浓重。此外作者还在文中创造了一批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人物形象,《我和上帝有个约》中以苏云起、周玲为代表的基督徒大多是圣洁美好,内心平静喜乐的模样,而以陈步森、土炮为代表的人物则是充满了暴戾之气。在文中二元对立还表现为同为背负罪行的罪犯,虽然都在现实法律层面收到了应有的惩罚,因陈步森信基督而得到安息,土炮等人不信而得不到精神上的救赎。北村小说的另一大缺陷还在于对人物形象的模式化,无论是《愤怒》《陈先和》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等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性格、爱好等都有着惊人的相似,陈步森、孔丘、李百义、陈明达等主人公大都外表斯文但性格敏感执拗甚至偏激,他们都有不同于其他犯罪人物的爱好,比如诗歌。他们都经历过残酷现实的摧残和蹂躏,被逼入绝境之后犯下罪行,经过心灵的折磨和煎熬,最后皈依基督教得到救赎。这些主人公在皈依之前具有偏激的执念和以暴制暴的戾气,在信仰之后却急速转变为一副虔诚的忏悔者形象,人物被过度圣化,情节发展缺乏逻辑转折突兀,文本呈现出明显的断裂,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南帆曾说:“重要作家往往在他们的时代更为醒目。这些作家未必拥有大师的精湛和成熟,他们的意义首先体现为——劈面与这个时代一批最为重要的问题相遇。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牵动这一批问题,使之得到一个环绕的核心,或者有机会浮出地表。换言之,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谈论一个时代”[2]。北村的价值来源于此,并因此而赢得盛名,从《施洗的河》到《我和上帝有个约》,北村在其转型后的众多作品中展现了一个作家深深的现实焦虑以及介入现实的激情。面对种种的问题北村选择的是以宗教为解决之道,呼吁人们说出真话,深入灵魂,直视自我心灵中的罪性,然而其理念先行和宗教美学的坚持使得小说呈现出强烈的说教色彩,结构和人物设置也出现模式化脸谱化等弊病,其文学审美和艺术魅力大打折扣,同时其思想性和精神挖掘的深度也呈现出一种无力状态。北村的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我们在惊喜于作家对于生命的关怀和信仰坚守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作品呈现出的种种硬伤,一个伟大的作家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思想性,更要有文学性和审美性,只有这样的文学才可显示出对于思想的魅力和文学的价值。
注释:
[1]北村:《我和上帝有个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
[2]南帆:《先锋的皈依——论北村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李颖颖 江苏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