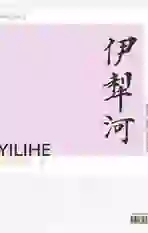时光的陷阱
2016-11-30田鑫
田鑫
稻草人
它站在田里,潦草、破败,身上的旧衣服和草帽已经遮不住它的伪装。一条腿近乎优雅地站立着,双臂伸直,想要把过往的风抱住,其实它连自己都抱不住,只能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稻草人。它像是早就知道我要回来一样,一直等在那里。我出现之后,它却只能远远地望着,没办法给我一个像样的迎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就在我们相遇的那一瞬间,它却把我带回到了过去。
刚开始的时候,稻草人是被隐喻的。村庄里有人得了怪病,久治不愈又找不出病因,通灵者就会抓一把草,照着这个人的样子扎一个小人,然后在患病的相应位置扎针。这个方法很灵验,我就曾见过卧病的人在扎了小人之后又重新回到田里干活。
不过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如果有人背地里照着谁的模样扎个小人藏起来诅咒的话,被诅咒者就会中邪,严重的甚至会因此丢了性命。说是这么说,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是被诅咒而死的。倒是有了这个说法之后,很多人对这小小的稻草人敬而远之。直到鸟雀来捣乱,这稻草人才有了新的用途。
村庄里的鸟雀野惯了,想吃啥就吃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人起早贪黑种下的糜子,还不等收割就被鸟雀吃掉了一大半。地少人多粮食薄的年月,填饱人肚子的粮食怎么能让鸟雀偷吃。于是,人们就开始收拾捣乱的鸟雀。
跟鸟雀讲道理是不可能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驱赶。我曾经跟着父亲守在糜子地里,看到有馋嘴的鸟雀落下来,就大声喊,用土坷垃扔。很多人都这么干,闲的时候,地垄上就会守着一堆人,鸟雀们看着乌压压的人,远远地躲起来。人散去了,鸟雀就又重新聚拢过来。
是稻草人解决了这个麻烦。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扎一个稻草人,让它穿着旧衣服戴着破帽子,然后替人站在糜子地里,鸟雀飞过来的时候,看见有人站着就乖乖躲起来。
我穿过的一件宽大的深色外衣,就曾被穿在那个站在我家地里的稻草人身上。夜里,我就梦见我站在麦田里,单腿站立,双臂伸直,不吃饭不睡觉不走动。我从糜子还是嫩芽站到糜子三月怀胎,等待收割,纹丝不动。
有一些耐不住性子的糜子,没有任何征兆就掉在了地上,我为此着急。鸟雀们偏偏在这时候成群地飞过来了,它们专找那些秆上有很多糜子的,两只爪子死死攥住,小脑袋不停地晃动。
看着它们这么肆无忌惮地吃糜子,我想大喊一声,嘴里却发不出声来,胳膊也使不上劲,不管怎么用力都没办法让那些讨厌的鸟雀知道我在吓唬它们。一着急,我就想起用尿来冲它们的主意。我朝着鸟雀最多的地方浇过去,它们“哗啦”一下子就不见了,可那些尿却并没有落在糜子上,全浇到了土炕上,梦就这样被尿惊醒了。
小时候喜欢吃甜食,如果闹到一块糖,我会先忍着不吃,而是一直把玩它。忍不住撕开糖纸,就舔一舔,再舔一舔。放进嘴里后,不搅动舌头,也不咀嚼牙齿,让它混在津液里慢慢融化,吃完还要舔了手指头和糖纸。
这样的机会一年只有少有的几次,甜菜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我对糖的巨大渴望。可惜在我的父亲眼里,甜菜却并不能算作粮食,家里仅有的几亩地里,麦子糜子玉米土豆挤得满满当当,甜菜自然是没有位置的。为了让家里能多出一些地来,父亲闲了就经常扛着铁锹去地垄上开荒,他垦荒的时候,有一种恨不得把整个村庄都变成自家地的野心,而我一心只想着吃甜菜。
在这里,我要坦白一件藏在心里许久的事。等不到父亲在自家地里种甜菜的那段时间,我曾趁着中午山上没人,一个人去别人家的地里挖甜菜。此前,我在山上转了好几天,才盯上那块夹在糜子和玉米之间的甜菜地。
五月的糜子和玉米都长得不高,一个人大中午钻到甜菜地里很容易暴露,但是为了吃到甜菜,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我猫着腰,从玉米地的地垄上慢慢挪到甜菜地里,以几棵稍微高点的玉米当掩护,蹲下去,拨拉起甜菜宽大的叶片后就是一顿挖。你不知道,我紧张到竟然忘了拿铲子,一手提着叶子,一手卖力地挖。
挖到就剩半截,有个声音喊了一声。坏了,肯定是被发现了,我怔在那里,一动不动,其实是不知道该动还是该不动。想着把那还剩半截的甜菜埋起来,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可是手却不听使唤,我也只能定定地蹲着,等那个声音靠近了再说。
可是,被我挖出来的土都要晒干了,甜菜的叶子眼看着蔫了,那个声音却一直没有走过来。我慢慢地把头拧向玉米地,那里没人;再把头拧向糜子地,妈呀!原来喊了一声的那个人在糜子地里。
我不敢再看了,可是奇怪的是,我明明就在他眼皮子底下,那个人就是不过来,也不吭声。做贼心虚,我就这样白白在甜菜地里蹲了大半个中午,当我看清楚那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穿了衣服戴着草帽的稻草人时,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一下子就瘪了,瘫在地上,手里还攥着甜菜宽大的叶子。后来才发现,那一声原来是放羊的人喊的。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嚷着让父亲种甜菜,见到放羊的人也躲得远远的,更别说稻草人。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想起这些事,但是说来也巧,我再一次回到村庄的时候,竟然是一个稻草人迎接了我。
就在我被稻草人带回过去而沉迷其中时,还是一个放羊人将我喊了回来。他赶着一群羊往山上走,看见我走下来,远远地就扔出一句话来:“回来了?”我回过神来,连声应着:“回来了,回来了!”
羊群走远,地上只留下一串羊粪疙瘩。我继续想稻草人,没在意就踩到了羊粪上去。哦!对啊,不在意的事情多了去了。比如现在,谁会在意一个稻草人在寒风里有着这样的心情。或许鸟雀会吧?也只有那些已经识破了稻草人伎俩的鸟雀,还会回到稻草人身边,就像八哥站在豢养者肩上一样。不过,鸟雀会将屎拉在稻草人身上,而八哥可能不会。
捉迷藏
有些人藏起来,你永远就找不到了。
我们说好的,你背过身去,从三开始倒数喊到一再转过来。那时候,你身后只有土墙、树和房屋,我们像被收回去一样,无影无踪。你朝东走去,东面是一排树,那里最容易藏人,可是树叶背后却没有人,树的背后还是树,没有你要找的人。你撤回来,到西边去,西面是一堵墙,你本来一眼就能看清楚,偏偏要走过去,似乎觉得我们应该隐身于土墙之内。我们怎么能在墙上呢,只有人死了照片才会挂在墙上。你死死地盯着墙,好像我们真的躲在墙缝里,突然就会草一样弹出来。然后你去了南边,那里的草垛里肯定藏着人。草从一开始就和人分不开,要不人死了为什么要落草之后才能入土为安。你半个身子钻进草垛里,两只手在里面乱摸,然后索性把整个人都塞了进去。在草垛的身体里,除了一只热乎乎的鸡蛋,你什么也没找到。拿着鸡蛋身上沾着草,你就去了北边,到一堵连着一堵的院墙跟前,这里住着村子里的所有人,你想着我们肯定也在那里。你挨家挨户敲门,喊着我们的名字,没有一个人答应,大人们都在山上干活,牲畜们在圈里打着盹,你手里的那个鸡蛋还热乎乎的,就是没人回应你,这个世界上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你回到原地,不喊,不叫,也不打算找我们。盘腿坐着,捉摸起手里的那颗鸡蛋来。你把它举起来,这小小的坚硬的壳里,有一块红红的东西,有些混沌,你盯着它的时候,那颗鸡蛋正好挡住了太阳,鸡蛋就成了太阳,壳泛着淡淡的光。你看得眼睛都疼了,起身,钻到草垛里不出来。
我们实在沉不住气了,就从屋子里出来,开始找你。我们去了树下,去了墙根,去了那些院子里。我们也去了草垛,但是我们却没有钻进去,有一只鸡在那里,我们就想着那里肯定不会躲着一个人。我们找不到你,就回到游戏开始的地方等你。
我们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捉一次迷藏。在沟里放牛的时候,我们就藏在牛的身后,藏在拾粪的背篓里,藏在长长的水草中间。在山上抓兔子的时候,我们就藏在山洞里,藏在玉米地里,藏在立起来的麦垛中间。找我们的人总能像捡麦穗的人一样一一把我们揪出来。但是我们就是乐此不疲,把藏起来和被找到当成一件大事。一直到水草、牛背、麦垛再也藏不住我们了,我们才把捉迷藏这档子事忘在脑后。
不过,我们学会了藏起别的东西。比如,醒来的时候床上的“地图”要先用被子遮住,等到没人的时候再拿出来晒干;收到女孩子回复的纸条要偷偷躲到没人的地方看。不过,我们始终没学会藏起来的秘籍,晒干的地图总是会留下痕迹,读过纸条的脸上始终有一坨是红红的。我们还是乐此不疲,仿佛藏起来是一件要用一生来干的事,同时还要时刻提防被人抓住。
藏起来有时候也会成为一件很危险的事。就像你的父亲,被人藏在水里一个晚上之后,再被找到时,就成了一个永远也回不来的人。他被捞水草一样捞上来,剥光了被泡得发胀的衣服。他赤裸裸晒在太阳底下,平日里被衣服藏起来的事物全部暴露在众人面前。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又一圈,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你却看不见任何东西,眼泪把太阳都晃得有些眩晕。村子里的人帮着你们母子将你的父亲藏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为了让你远远的就能看见他,人们给他培了高高的土堆。
再后来,你就失踪了。这么多年,我以为你是把自己藏起来了,忘了提醒我们去找,也忘了回去的路。从此,我们再也找不到你。是啊,捉过每次的人,只要不想让人找到就会永远都找不到。可是我不死心,我去你家找你,门上却落着锁。我去我们曾经藏过的地方,却一无所获。
这么多年了,我都快把找你这件事给忘掉了,你却出现了。那天在集市上,我远远地看见一个像你的人走了过来,你慢慢靠近,我竟然有些不知所措。我喊了一声你的名字,你停下来,一抬头就认出了我。我抓住你的手,生怕你再藏起来。
我一直想问你这些年把自己藏在了哪里?可是却没有张开嘴。我不知道说什么,你也不知道回答我什么,我们就拉着手站在人群里。可能是很久不捉迷藏了,我们忘记了藏起来之前要先喊三二一,分开时说出嘴的却是再见。
时光的陷阱
一条坝把村庄分成上沟和下沟。上沟是一汪水,人绕着水居住。下沟是看不到头的沟壑,草木躲在那里。上沟放水的时候,下沟就有一条小溪,水不深,在水草之上流着。运气好的话,能抓到鱼。我们挽起裤腿,猫着腰,眼睛死死盯着水草,发现有动静,就猛一下子把手伸出去,手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一般掌心里会有一条两指宽的鱼。
每次下雨或者坝上放水,去下沟摸鱼就成了我们的乐趣。水不深,可要抓住滑溜溜的小鱼儿却并不容易。得有陷阱,我们在水草平坦的地方挖一个坑,在坑的边上设计一个半圆形的槽,就算是陷阱。陷阱里的水明显比周边的水深,它们只会往水深的地方游,如果鱼儿不小心游到槽里,想退回去就难了。一个下午,陷阱里会捉半筐子鱼。
夏天摸鱼,冬天的时候,我们用陷阱抓麻雀。雪落下来的时候,就开始筹划着去哪设置陷阱。一定要在一个开阔的地方,最好有树或者半截墙,人就可以躲在后面,手里拉着一根绳子,绳子一头绑在半截木棍上,棍子支着一个筛子,筛子下面扔一些玉米和小麦。雪盖住村庄,筛子下面的玉米和小麦就成了唯一的粮食,也是最好的陷阱,饥不择食的麻雀看到它就激动不已。
我们屏住呼吸等着,有时候,一天都等不来一只,运气好了,不一会就会有一群麻雀飞来。它们躲在筛子附近,小脑袋转来转去,或者飞起来不靠近原地落下。反复几次,确定没有危险,就开始靠近筛子。第一只麻雀钻了进去,第二只,第三只……许是饿了太久,这些小家伙们刚钻进筛子里,小嘴就不停叨着地。急性子的伙伴就要下手,被摁回去了,大家齐刷刷盯着筛子,要等至少一半以上的麻雀进去。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狡猾的小家伙总不会傻到一股脑全部钻进去。看地面上的玉米和小麦吃得差不多了,猛的把绳子拉回来,棍子离开了筛子,几只麻雀就这样被装进了陷阱,飞走的几只,落在不远处的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们哪能听得懂它们说什么,麻溜地包围了筛子,手伸进去掏出陷阱里的小麻雀。
有时候,陷阱还会用在小伙伴身上。把牛赶到下沟,牛闷头吃草,我们就分成两队,一队攻一队守,各自占山为王开始战斗。守是最不保险的,老是被一锅端,得想办法阻止进攻,就开始在攻击的线路上挖陷阱。一般陷阱会挖在草比较茂盛的地方,草皮铲下来,在原地挖一个能把一只脚埋进去的坑,然后用棍子把草皮轻轻支住,然后埋伏在附近,就等着对方冲上来。只要一脚踩空,这个倒霉蛋就被“活捉”。我们乐此不疲地埋伏、挖坑、活捉,以至于下沟里到处都有我们挖的陷阱,后来还把牛也陷了进去,一只前蹄踩空之后,硕大的身子随之倾倒,一头牛因此失去了一条腿,最终失去了整个生命。
鱼抓住后上游还会下来另外一些,麻雀抓住后树上还会飞下来一些,草地上挖出来的坑过不了多久就又被新长出来的草皮遮盖,牛死了再也回不来。把它陷进去的陷阱一点责任都没有一样,待在原地,我们突然开始憎恶陷阱,憎恶曾经挖出来的水槽和支起来的筛子,这些陷阱,把我们带到下沟,带到半截土墙背后,我们躲在水里躲在墙背后的时候,陷阱也躲在某一个地方盯着我们。
我们抓住过那么多鱼,抓住过那么多的麻雀,总觉得没有什么是我们所抓不住的,但是偏偏却抓不住给我们布下陷阱的时光。当我们沉迷于用陷阱抓小鱼儿和麻雀的时候,它已经把陷阱挖好,就等着我们一步一步靠近。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排列整齐,朝它布下的陷阱走去,一个一个掉进去,却迟迟不见有人来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