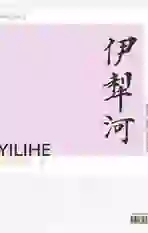1968年的死亡
2016-11-30南子
南子
1968年夏天,小镇上有了好多可看的热闹,街上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杂牌的革命群众,他们烧书,破四旧,给人剪阴阳头。那些年轻的革命小将们被集合起来了。很多人还没长胡子,大多是少年,脸颊还红扑扑的,脸上闪烁着急切的光芒,他们大多没满十七岁,而这场政治动乱却要求他们在未来很短的时期内去解决哲学家、道德家们困扰一生的问题。
那就是,在这场政治斗争的考验中,酝酿出他们对生命的激情,从中提取人性的恶之花。
现在,他们已将火热的夏季留在了身体里,取而代之的是狂热和愤怒。他们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想象,花在对人的刑罚上。
那一年,我们镇子上就死了两个人,一个是镇医院的院长廖志雄,他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斗争的对象——走资派。他的工资停了不说,那些革命小将们那些革命群众还要将他的手反拷着往死里打,后来他人不人鬼不鬼的回到家中。一日,因为家事和儿子发生争执。儿子说他当了“反革命”,把一家人害惨了。他自己因为父亲的事受牵连,没了学上。他悲愤交集,一下子倒地身亡。
有一天,我看见他的家人抬着棺材从他家门口出来,他的17岁的儿子低头抹着眼泪跟在后面。
还有一个人,就是小镇上的女教师韩雪。
韩雪是我小镇小学的音乐老师。在小学一年级的整整一年里,她教我们音乐课。
除了教课,她业余时间还抓校文艺队的活动。那些年,各单位的文艺队很受重视,一个单位或者说学校是否轰轰烈烈引人注目,至少有一半要靠能唱会跳的文艺人才,有了文艺人才,才能搞起文艺活动,然后是各种会演,评比,运气好的,会被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选走。
也许是在春天,也许是在操场上,也许内心还有秘密的欢乐,也许还多了一点为已逝的年代的一点点感动,我至今还能看见,韩雪轻盈地走在小镇学校的操场上。
清晨,一阵刚刚下过的春雨把空气洗得绵软湿润。清新的泥土味混合着草木复苏的清香气息,覆盖了教室、操场、宿舍、杏树、屋顶、玻璃窗,安静而祥和。
一切,美好得令人心疼。
19岁的音乐教师韩雪走出了教室,走在了课间10分钟的操场上。那架用了已有些年的手风琴斜挎在她的肩上,韩雪刚刚给孩子们上完了一堂音乐课,但音乐声似乎还没有停止,肩上那架手风琴似乎还有丝丝缕缕的旋律逸出。韩雪就这样踏着想像中的节拍,轻盈地走在了自己19岁的操场上。
这时,镇小学操场上已是沸腾一片,那一群群的孩子7岁或者9岁,男孩子们在操场上相互追逐、嬉闹;女孩子们则抓紧有限的课间十分钟时间跳皮筋,摇大绳,丢沙包。
韩雪轻盈地走着。那些奔跑着的孩子触碰不到她。清晨十二点钟的阳光触碰不到她。她在行走时,她的身体的每一个弯度,每一处亮泽,每一个暗处都显示出一种令人惊叹的完美。
晨风中,韩雪的裙角随微风轻轻扬起,那洗得褪色泛白的藏蓝色的确良连衣裙表明她来自一个与现在相距遥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她的体香随着肢体的走动时隐时现。当她走在长长的走廊里,昏暗的走廊里光线明暗交替,一截有光,一截没光,所以,她一会出现在光线里,一会儿出现在阴暗中,就是在阴暗中,她的身体也像是带着光,是那种柔和的黄光,这种光很容易让人想起某种夜行的动物。
我尾随着她,看她边走边微笑着,不时地抿了抿嘴,似乎想起了什么,灿烂的笑容中有一丝羞涩。
就在这样的一个微雨过后的早晨,阳光把整个操场都落满了。葱茏的树影倾泻在地。持续的微风中,有雨珠儿从新鲜的树叶上滑落在地的声响,有麻雀在操场上觅食时发出的焦急的咕咕声,还有从很远的草场传来的咩咩的羊叫声。
一个春日的清晨似乎都与这样美好的事物相关。韩雪轻盈地走着,一会儿孩子们把她的身影悄悄遮住,一会儿又将她悄悄显露。
那时我多么敏感!敬畏一切美好的事物。当我在人群中看到了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同一个人,一个是现在的我,一个是将来的我。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听说她的男朋友是学校体育老师,面色瘦削,黝黑,身材健美,会打一手好篮球,走路喜欢吹口哨。
但是,在学校里,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他俩同在一起的画面。她和他在一起是怎样的?这个画面曾经让6岁的我感到很好奇。
又是一个夏夜将尽的时候,小镇灯火稀落,窗外,榆树的叶子在随风哗哗响。而我那时,正在床上做着并不踏实的梦,不久,天就亮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一个美丽的生命正在消亡。过长的日光在慢慢毁去她的外形,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混合着树叶分泌的气味散发了出来,最后,终于引来了好事者。榆树上的鸟雀在拼命鸣叫,发疯似地。还有她宿舍门口的一小片晚饭花,一到黄昏就发疯似地开,一到白天太阳出来突然就枯萎坠落了。它们就像那些不幸的人,一个个与他们熟悉的小镇永远分离。
姐姐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她回到家,眼睛也没看谁,说是又死人了。
没等我说话,她说:“就是你总是念经一样念叨的韩雪,她死掉了,红小兵两天没见她,到家里来揪她,才知道她死了,尸斑都出来了,臭死了。据说是她早就准备好的,她的对象也没去现场,他什么玩意儿。”
我惊呆了。
她的对象——在我那个年龄,“对象”是一个不怀好意的词。像一个暧昧不清的影子,悬挂在我们的头顶,扰乱我们的视线和心情。
我曾偷窥过她的生活。
仍然是一个夏天的正午。午睡的气息覆盖了整个小镇的槐树、沙枣树、街道、屋顶、工厂、学校操场、玻璃窗,而我手上捏着一只布沙包,像一只无所事事而又警觉的猫一样来到了学校教师的宿舍区。那是两排泥平房。
正午的阳光闪闪发亮,我的额头闪闪发亮。
我绕到了韩雪宿舍后面的两棵槐树之间。我曾经在这片区域的垃圾堆里捡到过一毛钱的纸币和一个钢笔帽。此刻的正午没有一个人,两棵树之间拉着一条细铁丝,美丽而清洁的衣服带着年轻女教师的芬芳从容飘荡,有风吹过来,有变化的阵风,不仅脸颊和头发对它们有感觉,就连未曾关紧的窗户也会对它有感觉。
然后,我闻到了炒菜的香气。是什么香气呢?我趴在窗口边偷偷闻,却猛然听到有男人说话的声音,还有锅底与铁铲嚓拉嚓拉的声音伴随着油香味勾引着我的嗅觉,
他说:“小葱。”
他说:“姜末。”
他说:“蒜。”
我很着急,拼命地嗅着这股热气腾腾的香气。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沸水顶着锅盖噗噗响,炖鱼的香气混合着生姜和酒的气味,热烈而高亢,人的口水是挡不住的,我感到此时自己口腔里的涎水正奔涌而出,向着窗户里的炖鱼奔跑——
那时,还是幼年的我,心里可能就意识到了世界上有两种恋爱,一种是有好吃好玩的,就像韩雪和体育老师,另一种不吃不喝也不玩,如果写情书,总是要写到革命理想,若是谈人生,就要说人活着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样的恋爱像谁的呢?我父母的?好像也不完全是。
我妈整天给吃水煮土豆,喂得我饱饱的,满腹满肚,饱到了骨头里,连毛孔都喂饱了,但是,为什么我每天还是老觉得饿呢?觉得馋呢?
有那么一个时期,我的身体在白昼和黑夜展开了两个部分,白天,我对饥饿的抗拒显得正直勇敢,可黑夜一来临,我的意志就不堪一击了。好像我的肚子里藏了一粒火种,遇见风,呼啦啦地烧了起来。口水从胃里蹿出,凶猛,带着能量,像针似的,把我的胃扎得生疼,这种疼在身体里翻滚着,不像是水,倒像是煤油,把胃烧得更难受了,这让我时常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撕成了两半,如同一对敌人一样怒目相视。
比如,一到夜里入睡前,缺少油水的我,眼前老是晃动着有花生颗粒的花生糖,百花牌奶糖,葱油饼干,一年才能吃到一次的五仁月饼,苹果,南瓜瓜子,一小碗黄色透明的糖稀,到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的白米饭,烧猪肉,白面馒头,还有子虚乌有的炖土鸡,油煎带鱼,韭菜鸡蛋菜合子,胡萝卜羊肉包子,传说中的土豆烧牛肉,萝卜丝炒猪肉——
这些听说过的名字在黑夜里带着五颜六色潮湿和温暖的各种香气扑向此刻意志薄弱的我,令我四肢无力,脑袋昏沉。
可是,我却从未吃到过,一直愧对我的涎水。
猛然,墙边木桌上一帧翻扣着的相框吸引住了我的视线。我小心翼翼地翻开看。像片是韩雪的。韩雪坐在高高的山坡上,她的身后是连绵的群山,猛烈的山风吹乱了她额前的头发。
阳光下,韩雪的笑容无邪无畏,是那样的灿烂而彻底。
相片上,韩雪的身后还有一个男人模糊的身影。他紧紧地靠着韩雪。他就是我所在小学的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在屋子里有时候会没有说话声,发出另一些暧昧不清的声音。空气中颤动着新鲜青涩的汁液的芬芳,再到后面,含混不清的低语像一种非人类的声响弥漫在韩雪的屋子里。
我心里阴暗地想他们是不是在亲嘴,搂抱,这种猜测就像是一块密不透风的铁板,堵在了我的面前。
我父亲出事之后,敏感脆弱的我开始有着明显的不安。即使在路边上看到一男一女亲密地说话或走动,我都会突然慌乱起来。我看到周围的同学无忧无虑的神态时,我对他们的羡慕其实是充满了对他们父母的羡慕。我觉得这些同学的父母绝对不会有不干净的举止,我只认为我的家庭,只有我的父亲才会有这样的丑事。
风依然阵阵吹过,撞在窗玻璃上发出蓬蓬的响声,有人喊接电话的声音骤然响起,惊心动魄。我吓得转身就逃跑了,像个可恶的小偷。
我6岁整整一年里,我的南疆小镇与国内其它的大城市一样红光闪烁,口号和歌声此起彼伏,大字报一层层铺满我们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年月,那时候,经常会有人从高处跳下,从烟囱顶,从某一处高而险峻的山头,他们纵身跳下,气流呼啸而过,把那些红色的噪音留在了身后,而另一种红色从生命的深处流淌出。在加速度中啪地一声,整个的世界都完结了。但也有人采取了另一种死亡的方式,这些奇特的人们当中有一个就是韩雪。
听说韩雪的死是在同一年盛夏的某个正午。那一年,南疆小镇的街道上,似乎每一颗小石子都冒着热气,像正在爆炒着的黄豆,发着光,饱含石英的特质。街道上没有声音,最热的时候总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街道总是令人怀疑。
有一天,奎依巴格砖厂职工宿舍那一排低矮的平房前面聚集了好些人,他们不停地在韩雪的屋子里出出进进,凝重的神情使周围的气氛变得诡秘。
我那时年幼,无法猜测韩雪在死亡的前夕进行过怎样激烈的内心挣扎。从大人们零碎的言语中得知,她是自杀。
这期间,韩雪多次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殴打和侮辱。有学生用很钝的剪子给她剪“阴阳头”,把她的头皮撕下了一大片。最后一次,她被严重打伤,刚回家不久,打手们又到家里来揪她。韩雪听到砸门声,她不敢开门,恐惧和耻辱已经让她彻底崩溃了。
导致韩雪自杀的起因是这样的。
1968年的“十一”来临前的中午,韩雪刚和体育老师在宿舍做了一小锅高粱粥,一小盘滴了几滴香油的腌萝卜条,心情超好的体育老师自告奋勇地又干炒了一小碗黄豆,他大手大脚地将铁锅里的黄豆铲得四处飞溅,要知道一个男人大手大脚的时候是很性感的。可惜那时候没有“性感”这个词。他们在一起吃了这顿简单的充满了爱意的午饭。又吃了很多颗金黄疏松的炒黄豆。
吃罢饭,他俩一起到镇机关大礼堂彩排节目。
各单位在镇机关大礼堂彩排节目。大礼堂前一天刚清扫过,清洁的水泥地散发出好闻的尘土味道。当人们步入礼堂,领袖的巨幅画像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人们的笑容都被领袖制服上那一层含蓄而又华美的鸽灰颜色照亮了。
在这样一种气氛的感召下,人们纷纷以同样的姿势站成几排,右手举着红宝书贴举在左胸,放在自己的心脏位置。然后,像通了电一样,全身开始慢慢发亮,口中喃喃作声,开始念诵毛主席语录,稍一会儿,在人们念下一章节的时候有一小段间隙,大概是很短的两、三分钟,整个礼堂像骤然间沉入海底的船舱般寂静,所有的灰尘、呼吸及昆虫们都在此刻停驻了。
就在这时,站在队伍第三排的韩雪没忍住中午吃到肚子里颗颗炒黄豆的翻滚,不小心放了一个屁。的确是一个响屁,还绝对不是一个臭屁,放就放了,一个吃五谷杂粮的人,谁还没个屁放?
小时候,我听我家隔壁老伯说,你们女人最厉害的是忍屎、憋尿、夹屁这三招。忍屎,憋尿,夹屁这几个词读快一点,连起来读,一扫而过,简直就是一句咒语。不过,男人似乎比女人呢更爱放屁,放响屁。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难以节制。若是某个男的体恤某个女的,会不会主动承担这个屁?
四周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韩雪微微呲着嘴,有点尴尬害羞却忍不住想笑,她想蒙混过去,因为这个屁根本不值一提,当她抬起头,却猛然发现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前排的人纷纷回头来,朝着身后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像要找出这个罪魁祸首。
终于,离韩雪最近的一个妇女带着怨恨和怀疑的眼神看着体育老师,准备指认他。
此时的他,不知道有多夸张,他突然用一只手狠狠地扇着鼻子,不见得这个屁有多难闻,另一只手却牢牢指向自己身旁的韩雪——他丝毫没有犹豫,就向所有人揭发了她,出卖了自己的心上人。
这个美丽的女孩一下子捂着脸哭了,这个口口声声说喜欢自己的人,却在关键时候不肯替她窝藏一个屁。
这件事使她一下子羞辱难当,信心顿毁。
会还没开完,韩雪就被人绑走了,罪名是她蓄谋已久,恶意污辱伟大领袖。而这个体育老师也乘机与韩雪撇清了关系。
如今,这个在当年和韩雪谈恋爱的体育老师已儿女成群。
灵魂飞离了肉体,仍能在大地上行走吗?在正午提早到来的宁静里,另一个虚拟的我在想,如果我能够证明,那么我已经在证明了。用睡眠,用这颗不再跳动的心脏。
那一刻,我看见了韩雪在笑。
她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在人间。
在无数个她和她们之间。
我最后一次见到韩雪是一个炎热无比的中午,正在午睡的我被窗外一阵一阵的敲锣声惊醒,出门一看,一群人正从我家门口经过,是一群红卫兵学生,都是些孩子,他们的脸既苍老又邪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敲着铜锣,在人群中稍前的是一个熟悉的女子,她低着头,头被剃成了阴阳头,脖子上挂了一个很沉的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韩雪是破鞋。韩雪是反革命分子”,这行字被恶狠狠地打了两个红叉叉。
一个脏兮兮的小孩看见站在家门口的我:“斗人了,快来看斗破鞋。”
他见我在瞪他,就改口了:“快来看斗反革命分子。”
这邪恶、下流的称谓从一个看似不懂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像收音机上的一个开关,一下子把周围的声音给拧小了,彻底吸走了。
我站在原地,眼巴巴地看着韩雪被一群人挟持着,羞愤令她的嘴角有些歪斜,人好像突然消瘦了一圈,身体像是打摆子似的被人推搡着,摇晃着往前走,进行着游街批斗的闹剧,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
敲锣声渐渐远去了。
韩雪是怎么结束她的生命的?这是我长存的一个疑点,我不敢问姐姐和母亲,也不愿去问别人,我希望她是吃安眠药离开这个世界。我想她穿上自己喜爱的衣服,洗干净头发,把心爱的手风琴放到窗台上,然后一页一页撕下乐谱并投入火中。平静地看着它们带着暗花的字迹变浅,变灰,像灰色的蝴蝶一样在空中飘飞和消失。
我相信,韩雪在掂量死亡的时候只选择了睡眠,而不放心把生命交给刀、绳索、以及飞驰而来的汽车,因为她知道,她在借助这些工具结束生命的时候,她的灵魂也将会终止于这一动作上了。
还好,这样年轻女人死去的肉体我只是在想像中见过她,梦见过她,但真正的年轻女人死去的肉体我还从未见过。我现在、过去和将来都不想见到她。这世界上有一个韩雪就够了。
从那以后,在我经常陷入回忆的夜里,我从睡梦中被惊醒过,房间里是死一样的静寂。从窗外另一个不知名的角落里传来树叶窸窣的声音,一道惨白的月光照到我的床前,好似鬼魅在黑夜里游走时留下的印痕。我的额头有一层细细的汗珠,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似乎梦到了我的一个亲人的死亡,她死之前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而我恰好从她身边走过,看到她被几个面色凝重的大人潦草匆忙地裹在旧毛毯里准备送上卡车,从毯子里耷拉下来的腿赤裸着,泛着一种奇异的青白色的光。
别害怕。
黑夜里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梦”。
我重新躺下,而白天的疲倦战胜了恐惧,我沉沉地睡去。
我知道在这个死一样的夜里,黎明也在不屈不挠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