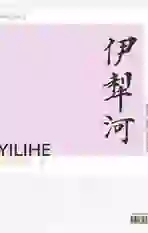菩提
2016-11-30郭从远
郭从远
我的故乡在两江汇合之城。这座城不仅在江边,还在山上。她有两江之秀美,又有群山之巍峨。那街是一层一层的,那路是弯弯曲曲的,那坡是长长的石梯坎上下连接的,好多楼是悬在石崖上的,不少树是从山上石崖中生长出来的。一座座的城门,一个个的码头,一声声的川江号子,一串串从两江深处飞出的浪花,还有多得数不清的山洞隧道,还有身处闹市中心却又夹在层楼之间的灰矮小屋,住在这里的人们出门就是坡,上下都是坎。
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那已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了。我有个女同学就住在这夹在层楼间的灰矮小屋里。我为什么特别记得她?很多同学的家我都不知在哪里,唯独她的家我不止一次去过。十七八岁的我,已朦朦胧胧地有所追求了,那种暗恋的滋味又甜蜜又苦涩,常常像有一只小兔在我怀里蹦腾,弄得我上课思想开小差,总想偷偷摸摸给她递纸条,放学后也总是像个贼似地跟在她后面。不时还用我那颇有点特色的男中音骚扰她一下。我把一首苏联的名曲《小路》改了词在她后面唱: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到你的小巷
我想同你并肩走下去
一直走到天放亮
这时,她总会回过头来,朝我嘿嘿一笑,吼道:“你快去找别人走去吧,和你走到天边边我才高兴哩!”说罢轻盈地飞下一级级石梯坎,转眼间就没了踪影。
我为什么这样喜欢她?我也说不清。人的感情就是怪,连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莫明其妙地就暗暗爱上了,爱得死去活来,全不管那个姑娘是不是爱你。以至于给自己惹下了一场大祸。那时刚刚“反右”不久,兴无灭资的教育搞得同大炼钢铁一样热火朝天。在我们不大的校园里,一个挨一个,建了少说也有十七八个小高炉。我们班上建了五个小高炉,一个组一个,在全校是最多的。我们把能偷能捡能从家里拿来的破铜烂铁全填进了小高炉的肚皮里,把能砍能挖能掏到手的木头煤炭全扔进了小高炉的火膛中,烧啊烧,烧得没日没夜,只要不上课我们就高兴,管它炼出的是不是钢。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听见我熟悉的歌声,是她和一个女同学在旁边的小高炉前轻声哼唱: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还听见她轻言细语地跟那个女同学说:“哎呀,你说他有多烦人嘛,跟在我后面唱,把这首歌的词改成什么什么,说要跟我走到我的小巷,还要一直走到天亮。哎呀呀,要多烦人有多烦人哟。”“人家恐怕真的爱上你了哩。哈哈哈——”“哎呀,你真没羞,资产阶级——哈哈——”两人扭抱到一起笑个不停。
我当时也说不出有多激动。我虽然不知道她真心怎样想,但我还是想入非非陶醉了,竟忘了给小高炉里添煤,以致小高炉降温,炉中的铁没成钢成了一堆废铁疙瘩。这可闯下了大祸。全班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批判。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夏云同学在总结时说了一席话几乎让我晕过去。他看看我,又看看她,十分严厉地说道:“你不好好炼钢,不好好兴无灭资,不好好改造思想,同你那个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反而把苏联的革命歌曲改成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吓得我们无辜的女同学有家不敢回。你不过就是看她漂亮嘛!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你必须好好改造世界观。否则,你将自绝于人民。”我哪能服他,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你敢说你会爱一个丑八怪?”“你,你简直顽固不化。”幸亏我们的班长、我的同桌罗林出来救了我。“好了,好了,夏云同学上纲是高了点,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不是阶级敌人。可你把好端端一炉钢烧没了,怎么说?还不好好检讨,保证以后干活认真一点。”谢天谢地,我总算没有挨处分,好好检讨了一下就算过关了,但从此我对她再也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了。可人这个东西就是怪,明明知道她不爱我,明明为她自己吃了一次亏,可心里还就是放她不下。要不是她出身红考到了北京上大学,而我出身黑被分到了西北边疆,后面接踵而来的一个个风暴又让我自顾不暇,终在边疆娶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她的影子在我心中渐渐变淡,我可能还会“小路”“小路”地走下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我们都老了。我退休后回到了故乡。旧地重游,又勾出无限往事。自然又想起了她。她姓向,名小美。她的人和她的名字名符其实。现在想来,当初我们班的夏团支书批判我的话一点没错。我就是看上了她的美。一个远没成熟的高中生莫明其妙地“爱”上了一个姑娘,不看她的美看什么呢?我又不是她肚子里的蛔虫,我哪晓得她心是美也不美?如今想来真是能笑破肚皮。年轻人的爱常常是盲目的。奇怪的是我回到故乡后还总想再见见她,却又一次也没遇着,就连我们班搞同学会她也从不参加。我问好友罗林,不想罗林哈哈笑起来,美美把我嘲笑了一顿。你还有那爱美之心呀?莫非你还想重温旧梦?天呀,我哪有旧梦可温?人家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不过就是同学一场嘛,只想见见,见见。那好,我告诉你一个地方,你哪天吃完晚饭去,她准在。不过有言在先,要是你碰了钉子可别怪我哈。哪能呢!我还是有点信心的。
那天天很热,闷得连气都透不过来,好像所有人的热汗都凝聚在一起了,把天地之间的空气搞得黏黏糊糊的。我按照罗林说的来到市区峨岭公园。虽说在市区,却是在山上。下车后上天桥,下了天桥就爬坡上坎。好在四周全是树木、鲜花和草坪,林荫道曲曲弯弯通向山顶,那里是公园最高处,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平坝,茶馆里三五一伙的人不少,喝茶摆龙门阵,下棋打麻将斗地主。酒吧里多是年轻人聚在一起喝啤酒饮料吃烧烤。登两江楼可眺望长江嘉陵江,观万家灯火,赏山城美景。我却没有一点心思停留。我沿着平坝往西走,树丛中,常有影影绰绰的情侣相互依偎、拥抱,促膝谈心。走了不远我就听见了熟悉的久违的歌声。我的心一颤,像一根刺扎了一样,血直往头上涌。我说不清我当时想了些什么,只觉得一股强劲的风暴把我拉进了漫长的时间隧道,把我拉回到青年时代。可是,当我走近唱歌的人群我看到的又分明是一群老人,头发全白的花白的染黑的,脸上的皱纹或深或浅,但他们唱得都那么投入,那么忘乎所以。还有一支小乐队伴奏,手风琴、小提琴、二胡、扬琴,听起来虽不那么协调,但很认真。唱着唱着他们就跳开了,据说是怀旧舞,却颇有气势,像是进军,像是呐喊,勇往直前,势不可挡。当然也有柔和的,又充满了痴情、迷恋和满腔忠诚。跳着跳着又有人跳开了交际舞。前后两种舞蹈完全不搭边,真是无奇不有啊。这时我看见一个头发花白却精神抖擞的老男人走到一个老太太身边请她跳交际舞,那老太太对他摆摆手,独自朝一棵黄桷树下走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我看见了我熟悉的那副神情,我断定是她,向小美。一冲动,我差点大声喊出她的名字。但我没有喊,我默默地悄悄地走到她的身边,离她半步远,跟她一起观赏嘉陵江的夜色。
你说这江美吗?她问我。
当然。
你说那条船要是开到大海要走多长时间?
不知道。
你想毕业后离开这里吗?
想。做梦都想。
我也是。
哎,真是太好了。
我们的理想肯定会实现。
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高中毕业前我们班到峨岭公园野游时,我和她就在这里有过的谈话。时间早把这段谈话冲走了,却在今天又在这里被我打捞回来。
我轻轻哼一声想引起她的注意,不想她毫无反应。我小心地向她身边挪动了一点,没想到她马上朝那边挪了挪。我不甘心,又朝她身边挪动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十分冷淡地把头扭到一边。难道她真不认识我了?还是她故意不想理我?我偏要好好试她一试。
你说这江美吗?
没有回答。
你说那条船要是开到大海要走多长时间?
还是没有回答。
你还记得我吗?
先生,你是问我吗?还是哪个地方病了喜欢自言自语?
你,你,向小美,我是你的高中同学陆一山啊。
我真想抓住她的双手,掰过她的脑袋让她好好认认我。可是没想到她说她不是向小美,说我认错了人,然后礼貌地向我点点头一阵风似地去了,去得那么快,就像没来过一样。我傻傻地看着她身穿白色连衣裙的瘦削的身影,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回家路上我轻声哼着那首《小路》,忧伤难言。
哈哈哈,罗林听完我的讲述,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你笑,你笑个屁!我冲他吼道。他好不容易才止住笑,擦擦眼泪对我说,你可不就是哪个地方有点病啊?都给你说了好多好多次了,她不愿意再见班上的任何一个人,你还硬要去碰钉子。唉——,我长叹一口气,喃喃说道,我不就是想解开我心中的一个谜嘛。多少年了,我就是想不通,她怎么会嫁给夏云?我给她唱《小路》改歌词的事,夏云怎么会知道?高中毕业前我问过她几次她都不说。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你还总往心上放啊,你还想不想多活几年?你想她当时那么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夏云就是积极靠拢组织嘛。你别忘了她可是我们班最早入团的,后来还当上了组织委员。可夏云他批判我追向小美是资产阶级,他为什么要追。罗林又笑开了。你都几十岁的人了,什么风风雨雨都过来了,还把这点事放不下?那当然不是,我只是从不解变成了好奇。而且我听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她居然又检举揭发了自己的丈夫夏云。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呀。那我告诉你吧,在你追向小美的时候夏云早就给她写过好几封情书了。为这事,班主任曲老师还专门批评过他,没少让我给他做工作,不准他早恋。当然他们还是从地上转入地下,又在大学变成公开,你以为她的《小路》是给你唱的呀?那是她和夏云的恋爱主打曲。至于后来嘛——,罗林慢腾腾地给我讲了好多好多。
要说夏云嘛,品质其实并不坏,个头虽说不高,可四方脸也还白白净净。他老爹是个老干部,地下党的,在市里当局长,他这个红五类大学一毕业回到家乡不出一年就得到了提拔,当了个小科长。没想到小科长没当多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他和他的老爹都靠边站了。夏云脾气本来暴烈,从来都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这一下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心里一百个想不通,总说是牛鬼蛇神翻天,让他们造反是“阳谋”,让这些右派分子跳,然后秋后算账,一网打尽。他把这话悄悄说给小美听,小美不吱一声。她已经把名字改成了向向青。意思是向旗手江青学习。还参加了市里一个最大的造反组织。两人观点水火不容。“文革”前,即使夏云当了科长,在家里也处处听小美摆布,工资全部上交,不管谁对谁错都是他夏云的错,特别是小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后,他更是把小美捧上了天,每天晚上不管再晚都要给小美洗脚擦背,犯了“错误”被小美罚跪搓板的事也是有过的。但在外面,在大事上,小美都是听他的。这下好,他一下成了走资派,小美也突然变成了陌路人,一天跟他说不上三句话,天天跑到外面去革命,连儿子都不管。夏云目睹小美的变化,心如刀绞。好在还有好多比他大许多的走资派,有些批斗会还轮不上他,群众组织又都不让他参加,他无事可做就在家带娃娃,有时就在日记上大发一通牢骚。也不知他哪根神经犯了病,居然把揭他的、批他的、斗他的人的名单记了个全,把他们说过的话干过的事也一字不落地记下来。当然,这个日记本他藏得很好,连小美也不知道。
有一天,小美从外面回到家,带了一份造反派办的小报,随手放在桌上去了洗脸间。久已不知窗外事的夏云拿起小报翻看,看着看着勃然大怒。原来在第二版上全版登的是他老爹的“三反”罪行。一气之下,他把报纸撕了个几大块,并高声喊道:“今后你不准把这些破玩意带回家!”小美忙从洗脸间出来,一看报纸被撕破,急忙拿起一看,大哭起来,奔到夏云面前双手不停地捶打他,你闯下大祸了,闯下大祸了。他还有点发懵,细细一看,冷汗淋漓,跌坐在地上。原来第一版上登的是伟大领袖的相片。他撕破了这张相片。小美哭着哭着朝外面跑去。夏云忙把报纸夹进他的日记本里藏起来。又害怕事情真的闹大,自己肯定会被打成反革命,便抱起儿子往奶奶家走去。
夏云拿不准小美会不会去揭发自己,这年头对谁都不能太信。其实小美去了罗林家里,她对罗林哭诉了一切,要罗林帮他们想个万全之策。罗林要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到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把报纸烧掉。
当小美回到家时,门口站满了红卫兵。房里也被他们抄了个底朝天。红卫兵并不知道报纸的事情,而是来抄夏云老爹窝藏在儿子家的罪证,不料想却抄出了那个日记本和报纸。
夏云把儿子交给奶奶回来的路上就被抓走了。第二天挂着黑牌游街,黑牌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夏云,在他的名字上还打了个大红八叉。不久被逮捕,关进了一个连亲人都不知道的监狱。小美心中急,外表还得装得没事一样。不光这样,还写了不知多少大字报,痛骂现行反革命夏云,揭发他的滔天罪行,哪怕都是些空话那也得写。就这样还不能得到造反组织的信任,一些人要求开除她,一些人要求批斗她。造反派头头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跟夏云真正划清界线。真正?怎样才算真正?她也许被急傻了,批傻了,或者是她怎样也不会想到事情会严重到这样的地步。头头要求她用实际行动跟夏云划清界线。什么实际行动?你是真的不知还是装疯卖傻啊?你不跟他夏云离婚,还甘愿当一个反革命家属,你能说是跟他划清界线了吗?她差点晕过去。离婚,儿子怎么办?她又找到罗林。罗林在房里走来走去也拿不定主意。她见罗林半天不吭声,呜呜哭起来,边哭边喃喃道,我是可怜我的儿子啊,这么小就没有爸爸了。罗林突然冲她说道,可你的儿子从此就是反革命的儿子了。这句话突见奇效让她不哭了。她匆匆忙忙离开了罗林家。
不久她向组织交上了同夏云离婚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她万万没想到夏云会自杀,会在监狱里用裤腰带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更没有想到的是,从此她也没有能再见到她的儿子,“文革”结束了好多好多年,夏家人都一直躲着她,拒不和她相见。她更没有想到的是,从夏云自杀的消息传开后,骂她的话也不胫而走,说什么的都有,“文革”结束后,更是公开指责她出卖了自己的丈夫,搞得她八面不是人。她见了熟人就躲。
唉——,罗林长长叹息一声,说:“这人世间的事还真让人说不清楚。我这个不信命的人,有时也不能不怀疑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在捉弄人的命运。”“你算是了解她的,你为何不站出来给她澄清事实?”我真有点埋怨我这个好友了。他委屈地看着我,“我说得还少吗?可她自己又把自己孤立起来,连同学会都不愿意参加。其实大家对她还是很理解的,听到那些流言也未必全都相信,有些人即使信也不会当面说出来呀,第一次同学会她去了,跟她说话的人是不多,可能就是怕她多心呀。那以后她就谁都不愿意见了。有一次我去通知她参加同学会,听她在家里轻声哼《小路》,我说你还没有忘记这首歌呀。她说,没想到一辈子过得这么快,转眼间我们都老了。想想这辈子除了这些歌我们还有什么可回忆的可怀念的?不过你的嗓子还是那么甜,好听。你以为我真的是在唱吗?她苦笑着问我。那你为何不去同学会跟老同学聊聊天,也可放松一下心情啊”。她摇摇头说,都是空的,空的,就想一个人安静些。
我彻底打消了再去找她的念头,就从罗林那里听听她“文革”之后的命运吧——
自夏云自杀后,她孤零零过了好几年,儿子找不见,找见了也见不着。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那头头的老婆在文革中因观点不同跟他离了婚。可能是二婚的缘故吧,向小美对对方的要求并不高,在一起说说话,排遣寂寞就行。谁知那头头却不甘寂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主动请命到单位下面的一个公司当了老总。这样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风言风语就传进了耳朵。她并不相信。什么小秘、二奶的,可能都是那些害红眼病的人瞎扯。虽说他们婚后工资都是各自为政,但他也经常给她买回不少贵重物品,让她感到一丝暖意。一天,她独自上街闲逛,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她下意识地闪在一边,她看见自己的老公挽着一个二十来岁的漂亮女人上了他的小车。她叫来一辆的士,让司机跟在后面。她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小车进了一个豪华别墅小区。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小区门口的保安,刚进去那辆车不是这里的吧?怎么不是,他们住进来快半年了。女的天天在,男的经常来。她差点晕过去。她强忍住心中的怒火,打的回到家,打算等他回来算总账。可是她没有想到她这个第二任丈夫再没有回来。他刚回到公司就被纪委的人带走了。后来因贪污受贿被判了八年。这一回是她主动提出跟他离了婚。流言蜚语却总是不肯放过她。有说她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同伙的,也有说她帮助他窝藏了几百万脏款的,还有更加不堪入耳的话,说是她第二任丈夫在外包二奶同她是一笔交易,给了她好多好多钱等等,不一而足。都是捕风捉影,全都查无实据。可她心力交瘁几乎崩溃了。她要求提前病退,得到批准。从此,一个人不知依靠着什么打发日子。常去的地方就是峨岭公园,常做的事就是怀旧,唱怀旧的歌,跳怀旧的舞。她把“文革”时期的歌能唱得一字不落哩,还像小孩子一样跳着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远飞的大雁》,学着牧民的姿态唱《站在草原望北京》《草原赞歌》,学着红卫兵的模样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世界是你们的》,学着样板戏的做派唱《红灯记》《沙家浜》。
苏联歌曲呢?那首《小路》呢?
也唱呀。有一次我去峨岭公园听他们那帮老头老太太唱,把我乐的。我本来是想硬拉她参加同学会。因为那次同学会是我们班想捐助母校的贫困学生。可看她那如痴如醉的样子,我又悄悄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找过她,让她独自自由自在吧。
听罗林讲完,我久久无语。
没想到半年后的一天,罗林打来电话,口气中充满焦虑。“你快跟我去一趟医院,附一院。她,她病了,病得很重,心梗。”“是小美吗?”“就是,就是她,你快点。”她是独女,父母亲都已过世,她这一病谁照顾她?
我同罗林匆匆忙忙赶到医院,赶到内科重症病房外,被挡在门口,一个先生朝我们走来。
你们是向小美的同学吧?谁是罗林?
我,我就是罗林。
我是向小美的律师,她生前委托我处理她的后事。
她,她——?
她要我通知你一声,转告同学们,别再想起她,谈论她,她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说罢,律师便跟我们握握手走了,我们愣愣地站在那里。等到反应过来,去追那律师,他早已走远。
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年。这一年来我和罗林不厌其烦地打听小美的墓地。特别是罗林,跑遍了所有的律师事务所,终于打听到了那位律师的线索,原来他就是向小美的儿子,在北京工作。罗林给他打去了电话。
在小美去世二周年的那天,我们在市里的所有同学到她墓地上向她献上了我们的哀思。她的墓地在公墓最后最边缘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墓碑上她的名字右侧刻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墓碑左下侧刻着“儿夏小云敬立”。
在我们默哀时,罗林的手机响了。
是夏小云从北京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