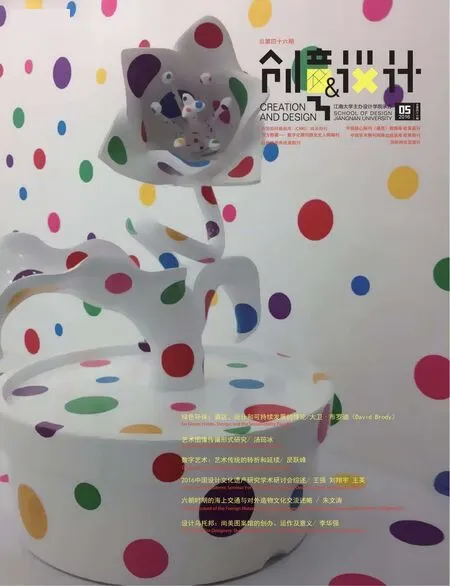六朝时期的海上交通与对外造物文化交流述略1
2016-11-29朱文涛江南大学产品创意与设计文化研究中心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文/朱文涛(江南大学 产品创意与设计文化研究中心;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六朝时期的海上交通与对外造物文化交流述略1
文/朱文涛(江南大学 产品创意与设计文化研究中心;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DOl编码:10.3969/J.lSSN.1674-4187.2016.05.007
二世纪末至六世纪是中国对外物质交流的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北方政权的中外交流主要通过西行陆路,而南方六朝的对外往来则是建立于东南海路的通畅。相对陆路,海上运输费用要比使用陆上商队便宜的多。海上交通自东汉末及三国时期就逐渐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重要位置发展起来。这一海上交通线从广州地区出海南下沿马来半岛到南海各地,经印度洋、波斯湾接上西方海上航线延伸至北非或罗马,或是从东部出海到朝鲜半岛南部再抵日本列岛。六朝时期海上交通线的开拓沟通了南部中国与海外诸地物质文化的多方面交流。本文试图对六朝时期的海路对外交流做综合评述。其一是梳理并考订几条海上通道的具体线路,建立六朝时期中国海上物质交流与贸易的总路线图;其二是通过六朝对外物质交流的几个典例,如法显航海、舶来玻璃、南朝窖藏银器、武宁王陵葬器物等,试图以点带面寻找中外造物文化海路交流的成因线索与相互影响。
一、法显航海表明南线海路商贸畅通
伴随南方政权的海上经营与佛教传播,六朝时期的南海航线日益通畅和重要。当时对海上贸易关系最主要的见证与亲历者首推东晋游方僧人法显,他所撰的《佛国记》中记载了他从天竺取经后自南亚半岛横渡印度洋返回中国的航海经历。它是我国现存有关海外交通的最早的详细记录,也是研究中国与这些地区海上贸易和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
天竺印度离中国本土泛海迢迢,根据《佛国记》记载,法显航海返国总共历经了三次中转,实为当时印度洋和南海之间的三段主要航线:
第一段法显从印度多摩梨谛国(Tāmralipti)出发,此国位于恒河入海口,是今印度东北部孟加拉邦的德姆卢格(Tamluk),搭乘商船昼夜十四日,到达狮子国(Simhaladvipa),今斯里兰卡。
第二段法显从狮子国搭商船,本欲东渡孟加拉湾,但经过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ands),数遇大风偏离航道,行九十日至耶婆提(Yavadvipa),此国位于现在印尼地区,可能为今天爪哇、苏门答腊之地。
第三段法显从耶婆提搭乘一开航广州商船回国,遇风暴,数月后漂至晋地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崂山登陆,自彭城南下回建康。(见图示一)
法显返国海路是当时南海丝路的基本航线,其西端终点还可以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延伸,跨过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王仲荦引阿拉伯人《古行纪》记载:“中国的商船,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六朝时期,向西的波斯湾航线可能尚未固定化,但从法显航海可见中国与印度及南海诸国贸易交通线之贯通。而且从《佛国记》中细节记载可印证南海商贸交通的种种繁盛表现。

图示一 法显海路回国路线图
其一,南海商船数量多规模大。法显三段航线中搭乘均是往来“商人大舶”,他从狮子国搭乘的商船“上可有二百余人”,从耶婆提国搭乘去广州的商船“上亦二百许人”。可知当时南海丝路中两百余人大型商船十分常见,人员规模如此,推知其所载货物可数十吨,船舶载重百吨左右,这已经相当于十五世纪欧洲航海船的规模。
其二,贸易航线已十分成熟,体现在商人对海港位置和航线路程判断的清晰。法显从狮子岛出发的商船本欲东渡孟加拉湾,应是绕马六甲海峡达南海,是最佳路径。如不遇大风,法显所乘海船每次航行方向都为正确。法显在去广州的商船上,“赍五十日粮”,且“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可见,商人对南海航行路线、路程和时间十分熟稔。
其三,远洋航海的经验和技术完备。法显从多摩梨谛到狮子国路程约为1200海里,花费十四日,平均每日顺风可行85海里,航行速度已是极快。当时航海商贾已深知需“得好信风”,后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五个月仍是为等候季风。法显狮子国出发的商船“后系一小船,海行艰崄,以备大船毁坏”,这小船真在之后的航行中遇风暴而用到,可见当时已有相当丰富的航行经验。
以上三点保障了南海丝路贸易的兴盛,并传播大量物质文化产品。法显在狮子国看见商人以中国“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一座高大的青玉佛像,有了思归之念。狮子国是海上丝路的重要中转之地,西可至波斯湾,北可达印度,东南可下南海。这说明当时中国生产的商品已经可通过海上航线网络大量销运到世界各国。
由于北方陆路的日益险阻使得南海丝路更为通畅,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东南亚都通过海路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官方外交,官方交往不仅是民间海路贸易的保证,更是民间频繁交往的明证和缩影。南海丝路在政治和商业的共同经营和开发下,其成为外来设计不断传播影响的重要通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佛教造物的输入。佛教文化的沟通是南海南亚国家与中国往来的基础,狮子国就遣书致宋帝、梁帝,直言两国应“共弘正法”“共弘三宝”,“以度难化。”而当时许多佛教造物如佛像、宝塔、舍利、菩提叶、佛器、佛经等也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人们对这些造物产生极大兴趣和作为模仿和创作的范本。狮子国赠送的玉制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晋、宋两代都保存在瓦官寺中,与顾恺之维摩画像、戴逵的佛像并称为三绝。张僧繇按南海传入的图本绘饰寺塔壁画,扶南国的“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这不仅对六朝造物的形态、主题与工艺技术有很大影响,也带来了艺术表现及观念的新内容,如“凹凸笔法”的使用和似于印度“六支”的“六法”理论的提出。
第二、稀有材质物品和工艺的输入。南海丝路的繁荣,各色商贾在重利驱动下,“商货所资,或出交部,将“山琛水宝”“千名万品”的货物“泛海陵波,因风远至”输入中土。其中有象牙玳瑁、珊瑚海珠、香料、火珠、古贝等自然材质,也有像金刚指环、摩勒金杯、琉璃唾壶、火布等金银、玉、琉璃、石棉及皮毛等各色工艺品。这些物品有些为南海南亚诸国的珍异方物,有些也可能是从波斯大秦转道流传而来的商品。而中国的主要传播和外销的物品是丝绢和陶瓷,1975年中国考古人员在西沙群岛北礁打捞到南朝的六耳罐、陶杯等物,无疑是当时运销海外时留下的,中国钢和铸铁也有可能通过海路传播,南朝曾以兜盔铠杖回赠南海各国。
法显所见证的南海丝路贯通建立起跨文化贸易的大流通,虽其具体规模和细节无法深入可考,但其对六朝造物面貌实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图示二 六朝与罗马之间贸易路线图
二、六朝至大秦萨珊之间西线海路与物质交流
六朝的海上丝路经东南亚、南亚一直向西延伸,六朝史料中多有出现的大秦,是海上交通能达之最西地域。“大秦”在《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宋书》《梁书》《魏书》等文献中确指是在西方的“海西之西国”,但具体地域不定,远近难分,不同学者由此提出不同见解,以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为代表的罗马帝国本土说、德国学者夏德为代表的罗马东部说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埃及说三种见解影响较大。三者观点虽有分歧,但都指向西方帝国之罗马,争议在于是罗马本土还是其相关属地。张星烺之观点颇为适当:《后汉书》之大秦,似指罗马帝国全部而言,《魏书》之大秦,似乃专指叙利亚,国都为安都城。因而,“大秦”多指罗马或罗马所辖东方行省地域则应无异议。
自两汉始,中国与大秦已通过陆路和海路建立联系。东汉末年,西域割据,陆道有所阻隔,对外的海道交通逐渐频繁,六朝关于大秦的记载更多来自海道。当时罗马商人都从海道经天竺、扶南、日南、交趾至中国进行商贸交易。黄武三年(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论由海路到交趾,最终达三国吴都,并与孙权谈论大秦的“方土谣俗”,居七八年后返国。大秦商人从何线路来华?文献并无记述。但从同期诸多史料中,我们可以大致廓清这一水上通道。三世纪中叶,孙权遣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并与天竺使者会晤,获知扶南到天竺的具体路途:“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朱应和康泰也了解自天竺西行到大秦海路的行程:“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径西行,极大秦也。 枝扈黎大江口就是恒河口,也就是法显海路回国的起点多摩梨谛地区,渡过恒河向西就能到达波斯与罗马在近东的交界,韩振华先生认为此处“大秦”为两河流域的报答,今天的巴格达。此地南延即为波斯湾。从恒河口也可以沿南亚海岸线南行到达斯里兰卡,然后再向西进阿拉伯海到达波斯湾。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就开始重视从波斯湾到印度西北海岸的海路贸易。中国商船可能沿同一路线越过印度西行到波斯湾沿岸与罗马或波斯商人贸易。这也正符合《梁书》中所载:“天竺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三国志》引《魏略》又载:“大秦……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载海西,遇风利时三月到,风迟或一二岁。”安谷城故址在两河流域下游,是安息与罗马的国界,也是波斯湾附近重要商埠。上述材料透露从波斯湾至叙利亚进入罗马疆界的主要通道。另一条海上通道能抵罗马疆域的是沿红海进入北非。罗马人的商船就能从红海口岸在四十天时间内径直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巴巴里贡(Barbaricon)巴里加扎(Barygaza)等地。中国《魏略》中提到从“乌迟散”到“乌丹”路线很有可能就是由北非埃及亚历山大港到红海口亚丁湾地区,乌迟散被普遍认为是亚历山大利亚城。张星烺先生对此作注解:古代东方等国货物由此道西往者甚多。三世纪中叶,吴国万震《南洲异物志》中有“加陈国”,普拉加什认为此处指古代居住埃塞俄比亚的库施民族,虽未确证,但极可能中国帆船已自南亚向西到达红海口沿岸 。(图示二)
创意与设计 | 设计史与传统造物Design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Creation 051

图1 南京象山王氏墓出土两只罗马玻璃杯 南京博物馆藏

图2 四世纪罗马杯 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藏
大秦与六朝通过直接或间接路线和渠道保持着大量物质文化交流。大秦一直被认为“其地多珍奇异物”。《三国志》注引《魏略》中更为详细记录七八十种名目繁多的物品。主要有以下几类:金银铜等贵金属;玛瑙明珠等宝石珍物;各色玻璃器;氍毹等多种羊毛或羊毛亚麻混织物以及各类草木香料。有些来自进贡,但大量皆来自贸易,其中有附会或误传,但玻璃、银器等大多确凿传自西方。晋人殷巨还为大秦众宝物中的火浣布(石棉布)作《奇布赋及序》。晋人郭义恭 《广志》、《后汉书》《魏略》等文献中还谈到一种“苏合”香料来自大秦。孙机认为“苏合”等外来树脂类香料的逐渐使用也使中国熏炉造型发生了炉身加深等种种相应演变。
六朝出土的大量玻璃器是当时西方海路进口的重要证据。玻璃制品在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很多名称,最通常的称谓是琉璃,相近的有璆琳、流离、瑠璃、壁琉璃等。玻璃一词在晋六朝时出现,即为颇璃、颇黎、颇梨等同音词。古代琉璃和玻璃几无差别,就其有众多同音名词来看,不难推断出两者都是音译外来词。关于名词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说认为玻璃琉璃出自梵文,玻璃是梵文spahtika的译音,意为石英,琉璃即壁琉璃是梵文Vatidnrya的译音。另一说认为琉璃源自西域的巴利文Veluriyam。另有一说认为古罗马人称玻璃物质为careuleum,这可能是壁琉璃、玻璃的母音。多种说法实无矛盾,可能是同一词源由西向东不同时期不同渠道辗转音译传入。与其名词一样,玻璃之物最早也出自西方,西方玻璃是以天然纯碱为助熔剂的钠钙玻璃,质地坚硬耐高温低寒易加工塑形,其与中国本土以铅为助熔剂生产的玻璃有着本质的差别。迄今为止,六朝时期的进口玻璃器皿不断发现,这些玻璃标本经过成分分析鉴定为外来的钠钙玻璃,而且圜底造型、磨花纹饰等特征都不属于中国传统器型和工艺。南京象山王氏墓出土的两只玻璃杯(图1)为厚壁、直口、圜底筒状,其造型与东地中海三、四世纪的罗马产品十分类似,其在口沿上、腹部和底部都磨有椭圆形纹饰,这是罗马工匠创制的磨花技法。其成分经过测试主要为硅、钠、钙,钾、镁和铁含量较低,并有二氧化锰做脱色剂,这与德国科隆四世纪出土的罗马玻璃成分相同,是典型罗马玻璃。(图2)出土罗马玻璃器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南京地区附近,之外还有湖北和广东。这些墓葬有几个特点:其一多为皇室陵墓和高门士族等大中型墓葬。因而六朝都城南京附近出土最多,而另一出土地湖北鄂州为古武昌所在,曾做过孙吴的都城和陪都。其二出土玻璃器多为器皿,但数量都较少,每一墓葬至多一至两件,因而多非日常器。其三大多为东晋时期的墓葬,而且以东晋早期墓为主,南朝墓仅见一座江苏句容的刘宋时期的墓。由以上三点大致可以得出一些推论:中国古代玻璃制品不如西方发达,因此将舶来品玻璃器视为珍宝极为推崇,只有皇室贵族才有资格拥有,文献中也有相关印证,《晋书》《世说新语》就有贵族宴饮时使用玻璃碗、玻璃钟等稀有器皿的记载。六朝出土多件罗马玻璃也印证史书上谈及大秦国出产十种琉璃,食具皆用水精等种种描述所知不虚。东晋之后,舶来玻璃器皿出土较少却与文献中大量记载外番进献玻璃器的记载相抵触,其原因可能是南朝时期东西方交流日趋密切,玻璃容器较于此前已经比较常见,亦或流向佛寺作为高级贡品,南方一些地方也出现吸收外来玻璃技术上的自行创制,玻璃在上层逐渐丧失昔日夸富的功能而有普及之势。虽尚无定论,但由此也看出进口玻璃器在南朝之后正逐渐扩大影响。
中国产品也对外输出,丝绸是罗马大秦在海上商贸中欲得之大宗。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把丝绸等奢侈品贸易与罗马经济衰落联系起来。虽是一家观点,缺乏确证,由此也可能看出东方丝绸对罗马社会影响甚大。四世纪罗马史学家马切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称:“以往在我国只有贵族才能穿丝绸衣服,现在各阶层的人都穿了,连搬运夫和公差也不例外”。中国之丝大多不由中国商人直接与罗马人交易,而由波斯、南亚、阿拉伯等商人转手,因而罗马人虽大量进口中国丝,很早就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但对原产情况却不明了,四世纪左右亚威安努斯(Rufus Festus Avienus)马切里努斯等人史书中对丝的来源仍有许多谬误。直到六世纪查士丁尼时代,曾久居中国的外国人才将中国养蚕制丝的具体方法传播到东罗马拜占庭。之后对蚕丝的加工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项重要收益。中国对罗马帝国出口的物品也不只是丝,还有衣料、皮货和铁器。

图3 广东遂溪县遂城镇边湾村出土的鎏金盅、波斯萨珊王朝银碗、萨珊王朝银币,遂溪县博物馆收藏

图4 五到七世纪萨珊波斯地区切面玻璃碗

图5 句容刘宋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

图6 日本正倉院藏波斯白琉璃碗
六朝与大秦虽然海路迢迢,但东西段辗转相连已建立起较为通畅的商贸路线,中亚及西亚波斯既是中西货品的中转交易之地,当地物质文化也直接流传各地。海上丝路入口一条是到广州后沿珠江支流北上到英德、曲江,另一条则从锡兰过琼州海峡到雷州半岛达遂溪,这两地都出土了以卑路斯时代为主的萨珊银币。1984年在广东遂溪边湾村出土一个盖陶罐,里面窖藏一批南朝金银器,其中有银币、银碗1件、鎏金盅、银盒、金环、戒指、银手镯等共计一百多件,(图3)是六朝发现的最大数量出土的一批海外银器,埋葬时间为南朝后期,来源地主要鉴定为波斯萨珊和粟特,这是中国南方与西海通航贸易的最有力的物证。在雷州港另一地松竹镇六朝墓中也出土有银项链、金银戒指等首饰,其中一部分也是由海外贸易而来。《隋书·食货志》在叙及南朝晚期情况时说“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其中可能也包含萨珊银币。夏鼐先生也认为是南朝墓葬中发现的萨珊银币是符合当时中国与波斯交往贸易的历史情况的。遂溪窖藏出土的银币还另有特征就是皆被钻有孔,也说明当时萨珊银币除有作通货的可能,更确证的功能是作为宝物收藏,穿孔作随身佩戴之银饰。
六朝域外玻璃器除罗马来源之外,还有萨珊地区的玻璃。萨珊玻璃在数量和分布上已经超过主要在南京一地发现的罗马玻璃。萨珊玻璃工艺兴起于三世纪,晚于罗马玻璃,并受其工艺技术的影响,但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萨珊玻璃更加透明,而且以凹凸球面磨花装饰于器皿外壁,模拟萨珊金银器的捶揲工艺和流行的联珠纹(图4)。鄂城西晋墓出土的玻璃碗残器和句容刘宋墓出土的玻璃碗完整器(图5)在成分、器型和磨花工艺上几乎完全一致,两者时间相差百余年,可见这类萨珊玻璃器有着固定的输入来源长时间一直源源不断的进口。萨珊与中国又有着更直接的商贸关系,所以比罗马玻璃流传更为广泛。
中国北方北朝也出土一些罗马萨珊玻璃器,但不同于南方进口玻璃,北方萨珊玻璃碗腹部有乳突状的装饰,不见于南方萨珊玻璃,不是同一来源和产地,而且六朝南方进口玻璃器在孙吴时期就出现,比之北方更早。由此我们也可进一证实南方地区的玻璃并非通过北方陆路贸易输入而是通过海路输入。南方玻璃器除了在都城附近发现,另一集中地就是在广州附近,广州在东汉以后就逐渐成为南方海路的出海口,进口玻璃器就是经海路至广州然后转输内地。玻璃是易碎物品,路上运输困难,而海上丝路则有着重要作用。南方进口玻璃器出土地也为六朝与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提供更多确凿物证。
南方中国绵延万里的海上丝路也因当时各种势力争斗和格局复杂动荡而时续时断兴衰更替,物质文化也在一定程度印证这一史实。三世纪初波斯萨珊崛起替代安息成为罗马与中国之间重要阻隔,控制海陆通道。三世纪末,萨珊多次败给罗马,罗马一度控制了海上通道,这使得大秦与东吴西晋频有接触。大秦使者分别于太康二年和五年两次通过海路到广州进行官方交往。这一事件在罗马史中印证,罗马征服叙利亚、埃及和波斯都在武帝太康年间,罗马人攻陷泰西封控制波斯湾头等出海要道,与东方之交通得以畅通。这也是罗马玻璃器在六朝初期频频出土的原因。之后,五世纪中亚游牧民族嚈哒人开始崛起,萨珊王伊斯提泽德二世和卑路斯一世执政时期曾被其打败,嚈哒人不仅逼迫萨珊纳贡称臣,而且完全控制了西域丝路。卑路斯王之继任者于是重新开拓海路而与中国南方发生了直接联系,文献就记载梁中大通二年萨珊朝遣使者向梁武帝献佛牙,之后又有两次进贡,可见南方出土的萨珊银币主要是在卑路斯(公元459-484年)或与其相近的时期制造并非偶然。在嚈哒人五世纪中期崛起的复杂背景下,粟特人也可能像萨珊一样利用海上航路与中国南方建立贸易联系。虽然南朝窖藏银器传入原因和细节尚无史料可考证,但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出现祆教图案,还出土较多的萨珊玻璃器都可以作为南朝与西亚中亚物质交流传播之佐证。此外,南方中国外交内政也影响海路的兴衰。如东晋时期,交州与林邑国(现越南南部)常有战事动乱,而日南交趾是中西海上交通的必经之道,显然会影响这一线路往来通畅。南朝初期与林邑关系逐渐缓和,加上佛教兴盛,中西海道商贸交往日益频繁。阿拉伯古代旅行家马苏弟也在《黄金原和宝石矿》中谈及:五世纪上半叶,幼发拉底河及上游常常能见到印度和中国的船舶停靠在岸边。而后,梁初又出现一小高潮,《梁书》载“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南朝中后期中西海路交通开始不断衰退,一方面与南方政权经历诸如侯景之乱等动荡日益衰败相关,另一方面,西罗马帝国于五世纪下叶灭亡,进入西罗马的红海航道不再重要,东罗马与萨珊波斯达成和平协议,重新开始原先有所阻隔的陆路通道,东罗马人与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建立贸易关系,而不再重视充满风险和不便的海上交通线。五世纪中下叶,中原地区与拜占庭频有交往,而南方政权与大秦的海上交通则由此而衰落。

图7 五代(梁)萧绎 作 职贡图 (摹本) 绢本设色 南京博物院藏

图示三 六朝与日本韩国之间物质文化传播路线图
三、六朝与朝鲜百济的东线海路与造物文化输出
六朝时期,朝鲜半岛三国鼎立,北部的高句丽、东南的新罗和西南的百济三国成割据对抗之势。此三国都遣使与六朝通贡交往,而其中百济与六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百济与南方政权建立联系根据中国正史的记载始于东晋咸安二年(公元372年),而根据日本奈良发现的百济铸造的“七支刀”上的铭文使用了中国纪年“泰和四年”(公元369年),说明百济和中国建立关系还要早于史书记载。自此之后,根据韩昇先生计算百济向南朝共派遣使者33次,刘宋到陈平均6-8年就遣使一次,可见其交往之频繁。
朝鲜半岛与南朝建立密切关系背后有着多种地缘政治和文化因素的推动,这也形成南朝对海东各国特别是对百济的物质文化的直接影响。四世纪开始海东各国竞相争雄,意图通过朝贡交往得到东亚封贡体制的共主—中国政权的册封和支持,以宣示其正统和实力。高句丽实力强大并接受北朝册封,南朝欲以高句丽牵制北朝也与其交往并册封其官职,高句丽旧地发现的东寿墓中的墨书铭记的内容和似于东晋的彩绘壁画即是明证。高句丽与中国的交好对百济形成严重威胁,也阻断百济往北朝的通路,于是百济通过海路不断加强与南方政权的联系,“每岁遣史奉表,献方物”。(图示三)《宋书》记载了从东晋开始百济受到的册封从镇东将军不断升至征东大将军,百济逐渐占有南朝与东亚国家关系秩序中的最高地位。南京博物院所藏的《职供图》经考证原图为南朝,图中所画东亚职贡使者皆以百济为首,(图7)这正与当时东亚秩序相印证。
政治外交直接促进了百济对南方汉文化的认同和交流。百济“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行用南朝历法,表明百济奉南朝为正朔。百济对南朝文化的吸收是全方面的:其一是官方的上流社会的知识文化的输入。《南史》就有记载百济从南朝求得《涅槃》、《毛诗》、《易林》、《式古》等经义典籍。受儒学政治文化的影响,百济也形成自己的“冠带文化”。其二是物质技术的引入。南朝的技术、军器和工匠对外国属于禁断之列,不得外出,百济却有特殊礼遇,不但博士工匠画师不断引进到百济,南朝还将腰弩等军器以及高度控制的寝陵工匠赐予百济,可见南朝与百济关系之密切。1971年,韩国公州郡宋山里发掘的武宁王(501-523年)墓是南朝深刻影响百济最有力的证明。武宁王墓是一座有长甬道“凸”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墓前有斜坡墓道和排水沟设施,墓室侧壁和后壁上有火焰形壁龛,龛下装饰有直棱假窗。(图8)武宁王墓的这些形制构造与建康地区的燕子矶梁墓、对门山墓等南朝大中墓葬惊人相似,从规模和等级上又低于梁宗室王墓,表明其恪遵南朝墓葬的身份规格,所以王志高先生称其为典型的“建康模式”。不仅形制近似,武宁王陵墓砖所用的砖为六瓣或八瓣莲花模印纹和钱纹砖与同时期的梁墓用砖极为相似,且公州出土的刻有“梁官瓦师”铭文砖更确认墓砖应是由南朝工匠烧制。武陵王墓砖砌的方式为四顺一丁三顺一丁,这也相同于南京南朝大墓的筑造。东晋南朝的墓室的建造均严格保密,外人无从知晓,朝贡的百济使者也绝无参观墓室的可能,因而许多学者进一步认为武陵王墓可能本身就是由南朝派遣的官方工匠所建造,或是由中国官方工匠指导下由众多百济工匠建造完成。武宁王陵在甬道处还有一石兽,身上有卷云图案,头上有树枝状铁质独角,杨泓认为这是南朝墓葬中的镇墓兽陶穷奇。(图9)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其似于南朝帝王神道石兽,是帝王威仪的象征物。而不管哪一看法都对石兽的南朝因素并无怀疑。
054
创意与设计 总第四十六期 | 2016.05

图8 武宁王墓墓室侧壁和后壁上的火焰形壁龛和六瓣莲花模印花纹砖

图9 武宁王陵在甬道处石兽

图10 武宁王陵的宜子孙兽带纹镜
墓葬中出土文物有九十余种,两千余件,其中许多为南朝器物,更进一步印证武宁王墓与南朝之关系。墓中随葬一串九十余枚的铁五铢钱置放在甬道中,经鉴定来自萧梁时期。梁武帝尽罢铜钱而更铸铁钱在普通四年(523年),也就是武宁王去世当年。这串铁钱即始铸不久之物,在武宁王去世之际由萧梁政权所赐予,在普通六年(526年)武宁王入葬时带入墓室玄宫。此钱置于墓志一面,此墓志上刻的汉文“百济斯麻王以前件钱,讼土王……”确证此钱是用于买地券,这是源自中国汉魏流行的道教文化的葬俗。这也说明百济全盘接受了南朝的丧葬思想和方术。
武宁王陵中出土三枚铜镜:方格规矩兽带纹镜、芝草兽带纹镜、宜子孙兽带纹镜,均十分精美,被确认为韩国国家级文化财。(图10)(图14)规矩镜流行于两汉,根据纹饰和铭文判断这枚规矩镜应是东汉后期的中国产物,而且此镜由传统的平缘演化为斜坡内收,外缘凸起的形状,这正是浙江会稽郡所造的画像镜的主要特征,可见此镜来自中国南方无疑。另两枚兽带纹镜也是汉镜,在镜背內区分别装饰有七个小乳丁,乳丁间装饰线雕异兽,这种形制又定名为“七子镜”流行于东汉晚期。在梁简文帝《望月》诗中就有“形同七子镜”之句。墓葬中还出土一些铜器如铜盏、铜匙、铜托银盏等均是中国南朝制品,其中一个铜熨斗在东晋象山7号墓葬中也发现一件,斗部口沿内斜,柄部上平下圆,两者在细节都十分相似。出土的铜匙和句容春城元嘉十六年墓的样例接近,出土的圈足碗、平盘以及罐等则和江都大桥镇窖藏出土器物类似。根据成分分析,这类铜器是铜与锡二元合金并使用锻造或轱辘工艺的响铜器,响铜技术不同于传统中国青铜技术,应是由西方传入的新技术,而且它不是经由亚洲内陆,是随佛教文化东传经由南海线路传入中国。
墓葬中还有一把镀金龙凤环首刀,据韩国学者研究此环首刀是标示等级地位的御刀。(图11)环首刀流行于两汉六朝,河北邓县南朝墓中就有手持环刀出行的画像砖,(图12)两晋墓中也发现过环首刀实物。六朝时刀环装饰日益华美,发展为仪具之一,《唐六典》中有“仪刀”条记下注“晋、宋以来谓之御刀,后魏曰长刀,皆施龙凤环”。武宁王墓出土的环首刀与中国文化也应该有很深渊源,也不排除直接来源东晋南朝的可能。
武宁王陵一共出土了九件瓷器:青瓷罐两件,黑釉盘口壶一件,瓷盏六件,都是来自中国南朝是中国和日韩学者一致定论,但其产地和输入背景则仍在讨论。韩日学者普遍认为青瓷六耳罐是在越窑烧制,黑釉壶是德清窑所制,与之前百济早期出土的六朝瓷器一样大都为长江下游的产品,如忠清南道天安市郊外龙院出土的黑釉鸡首壶、江原道原城郡富论面法泉里出土的青瓷羊等,而中国学者韦正做了仔细比较认为除青釉盘口壶外,其他瓷器都与长江下游产品有很大不同,而更接近江西地区的产品。瓷盏和六耳罐的泛黄色的釉色与洪州窑的特征接近,而且这些瓷器在洪州地区也不算精品。不是政治中心的江西地区或长江中游的一般产品如何流入百济地区值得我们深入考察,但从中揭示了武宁王的百济熊津时期与中国南朝的关系不仅仅在政治上,而在各种途径上的交流都有着之前未有的广度。全罗南道扶安竹幕洞祭祀遗址出土了中国南朝的青瓷,这一遗址还挖掘出百济时期祭祀的礼仪建筑“水城堂”,当时在竹幕洞海岸应是一座国际性港口,中国和日本的商船停留在此港进行贸易,这是各国商人为了祈求航海安全而进行的祭祀活动的场所,这一遗址见证了百济时期在民间商业活动上兴盛的海外贸易,也佐证了武宁王墓各种物品在中国南方的不同来源,以及中国物质文化对日本进行传播的路径。
创意与设计 | 设计史与传统造物Design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Creation 055

图11 武宁王墓出土的镀金龙凤环首刀砖

图12 邓县南朝墓中就有手持环刀出行的画像砖

图13 日本古坟时代画文带同向式神兽镜 九州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 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图14 武宁王陵出土方格规矩七子銅鏡
四、六朝与日本的东线海路与设计文化流传
日本自弥生时期就通过海路和中国南方吴越地区有着联系,在佐贺县吉野遗址出土的高床仓库和木制农机具就被安志敏等考古学家认为是从江南传入的,江南的土墩墓可能就是吉野里坟丘墓的始祖。三世纪时,日本群岛以今奈良为中心形成大和政权,同时兴起建造规模庞大的古坟,被称为古坟时代,时间跨度从三世纪中期到七世纪,上承弥生文化下启飞鸟文化,是日本古代史中第一个文化繁荣期,也正好与六朝时期相重合。古坟时代之初大致于孙吴时期,《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吴书》就记载亶洲人直接渡海到东吴的会稽通商,会稽人遇风漂流至亶洲。许多学者推测亶洲就是日本列岛。这说明中日之间通过海路有着大量民间交往。
文献记载大都语焉不详,且有争议,而在日本出土了更为直接考古证据,古坟时代早期有一项来自三国魏晋的南方造物及其技术最为引入注意:铜镜及制镜技术。日本各地古坟出土了数量众多铜镜,日本并没有较长久的青铜铸镜技术发展史,这些铜镜只可能与有着数千年铸镜技术的中国相关。中国南方铜料充足,经济发展迅速,自东汉后期就转为制镜重心,也出现了新流行的南方镜式,如神兽镜、画像镜和佛像夔纹镜。日本出土的铜镜也主要是这几种基本样式,经过王仲殊等学者经过型制、图纹和铭文的详细比对,确认为是“舶来品”的中国吴镜。日本出土铜镜中还常见大量的三角缘神兽镜,(图13)但在中国少见遗物可寻,这一问题得到了中日学者广泛探讨。一说为“魏镜说”,一说为“吴镜说”,王仲殊先生提出此类镜非魏镜和吴镜,而是东渡的江南吴地工匠在日本铸制。铜镜专家董亚巍进一步佐证此说,并认为工匠东渡传统延续到六朝晚期。他认为中国铜镜生产有了制模和铸造的行业分工和市场,东渡的吴地工匠主要掌握铸镜技术,一部分将中国做好镜模到日本去翻铸,另一部分是铸镜工匠自己塑型或采用当地人的塑型,然后在日本铸造。这也能够解释日本有些三角缘神兽镜中如何会加入“笠松形”等日本独特纹样。此说现在得到学界更多的承认,但最近洛阳等地又发现了多枚三角缘神兽镜,这为“魏镜说”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看来中日之间的早期交往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仍值得进一步讨论。暂不管这些铜镜之来源产地,这一时期日本为何罗致或制造大量“汉式”铜镜?我们可试做一些合理推论:日本这些铜镜的镜钮常常制作不佳,这说明其并非用于悬挂实用,而是仪礼所用。铜镜从形制到技术以及其中的道教内容都源自中国,对日本而言,不仅是舶来物,而且是一种正统信仰和政治威权的象征。大和政权统治者以铜镜作为葬礼或其他重要事件的特定恩赐,成为一种强化政治权威、密切君臣关系的一种手段,百济武宁王墓的铜镜也可作为佐证。(图14)大和政权初创之时大量的政治需要使得铜镜需求大增,真正的“舶来品”不够用,以至于招募大陆高水平工匠东渡制镜。这说明中国南方之铜镜不仅仅作为一种器物在日本流传,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象征参与到日本政权构建统一的进程之中。

图15 子持壺須恵器 奈良国立博物館藏

图16 孙吴时期的青瓷五联罐

图17 奈良县生驹郡藤木古坟金铜制马具
经历了中日官方交往记载的“空白期”四世纪之后,五世纪初,大和政权完成统一进入倭五王统治时期,并与当时的东晋政权建立外交,这一状况与当时的东亚政治格局息息相关,也使得中国南方物质文化也在日本岛进一步传播。大和国统一后向朝鲜半岛扩张,与高句丽发生战争但失利,因而改变战略:通过加入东亚朝贡体系,利用中国威望实现其强化政权和势力扩张意图。敌国高句丽一直加以阻难,直到东晋安帝义熙九年才与东晋建立朝贡关系,之后与东晋和刘宋交往朝贡共十二次之多。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倭国越海向中国遣使必须得到百济的引导和协助,百济受高句丽威胁而与日本结盟,成为中日两国交通的中介。刘宋之后,倭国由于不满自己在中国东亚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在朝鲜半岛势力的衰退,从而停止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但仍源源不断间接从百济吸收大量中国物质文化。《日本书纪》也有相关记载:倭王武时期从百济引进“陶部”“鞍部”“画部”“锦部”等各种工匠。杨泓曾举武宁王墓中出土的“七子镜”一例(图14):百济从中国输入七子镜,又向日本输出七子镜。管窥一斑说明中朝日之间的物质传播的基本轨迹。

图示四 公元二到六世纪六朝的海外海上交通与物质文化交流
日本制陶技术在五世纪有很大的发展,不同于以往野地烧陶的方法,而是在山地倾斜面挖掘洞穴井成有倾斜角的长条窑身,前有火膛后接烟道,采用还原焰高温烧制出胎质坚硬的陶器,称为“须惠器”(图15)。这种新制陶技术是在来自朝鲜半岛南部百济土器、伽耶土器基础上形成的,一度还被命名为“朝鲜土器”。古坟时代的须惠器制品在风格上与朝鲜半岛陶器也基本相同,应是由日本文献中所载来自百济的“陶部”工匠所制。而这一技术和风格的根源无疑是在中国六朝的南方地区(图16)。烧制须惠器的“登窑”与江南地区普遍使用的龙窑相似。须惠器中有许多“子持壶”与江南地区六朝初期的典型器“五联罐”十分相似。宿白先生还指出须惠器中的长颈壶、提瓶等器物也与江南硬陶有种种相似之处。许多学者认为硬陶技术的兴起在于发达社会分工下产生为提高政治威望的消耗性生产,日本的须惠器也并非实用器而是担当礼器功能。不难想象,倭王执政初期从百济引入源自中国的制陶术也参与其新统一政权和社会的不断巩固和强化。
南朝流传到日本的器物各类品种皆有。爱媛县松山市出土东晋青瓷四系罐,大阪黄金塚发现东晋元帝时“沈郎五铢”钱。在奈良橿原市五世纪下叶的新泽千冢古坟还发现一件罗马的玻璃盘,另有一件波斯萨珊的玻璃碗,类似器物在日本正仓院还藏有几件,其成分造型与上文谈及的湖北鄂州出土的玻璃碗十分相似,也是从南朝转道传到日本。上文谈到的南朝的响铜器在日本古坟时代也有发现,收藏于大阪久保惣纪念美术馆,之后的正仓院也有大量传世的佐波里(响铜)器,响铜技术的源头在中西亚地区,也是经过中国南方再流传到日本。
日本为学习中国的“衣冠之治”,还直接向南朝要求传艺。据《日本书纪》记载当时日本多次向南朝求得织工和缝衣工。这些匠工东渡使得日本服装出现较大变化。日本引入技术之后都进行了本土化的仿制生产以及改造。如日本奈良县生驹郡藤木古坟出土的两套一式的金属马具,金铜制一套为源自中国南方文化的舶来品(图17),铜铁制一套则为本土仿造。杨泓先生研究日本甲胄认为古坟时代的日本甲胄发生两次明显变化都和中国对其影响有着密切关系,但日本并没有简单模仿中国甲胄,而是进行了适合日本具体条件和技术传统的改进和创造,形成日本特点的“短甲”“挂甲”。日本马具甲胄发展应该又与日本形成统一国家后急需发展武备进行政治扩张有着内在关联。
古坟时代,日本对六朝先进物质文化积极吸收常常是间接的,以朝鲜百济为中介跳板,但却深远的促进日本统一政权和自身文化的构建。日本在南朝末期又与中国当时陈朝恢复通贡,逐渐开启了之后日本与隋唐进一步全面而直接的物质文化交流。
058
创意与设计 总第四十六期 | 2016.05
结论
六朝时期,北方的中外陆路交通常常受阻,而南方社会商业与都会开始兴起,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这为开拓与经营海上丝路提供了内在动因和条件保障。公元2至6世纪,中国南方社会频繁的海路贸易和政治影响扩张联接了多边的对外物质文化交流,建立起了西达大秦罗马东至日本岛的完整海上通道,初步形成波斯湾地区,南印度洋区域,东南亚海域,以及东亚海域四个主要海洋贸易区。以中国南方政权为东西方的重要中转,西方及西亚的罗马帝国、萨珊帝国,南亚的笈多帝国、东南亚各国、以及东亚的百济国、大和国之间建立了顺畅的物质文化交流,并有着具体的实物出土作为证据,中国的丝绸在亚洲西端的叙利亚巴尔米拉地区被发现,在东南亚的中爪哇查帕拉发现有六朝青瓷器,在东端的日本出土了多件萨珊玻璃器。通过海路建立起相互联系的世界化格局,对中国、东亚、南海甚至西方都产生极深远的影响。(见图示四)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条:
第一、通过海上丝路,六朝在东亚南海区域的朝贡体系进一步巩固,世界各地大量物品以通贡及贸易的方式通过海路抵至南方各国都会。其中佛教物质文化的输入和各种材质工艺的流行对六朝设计在文化内容和物质技术方面的变化起有关键作用,且泽被深远。
第二、通过海路辗转,六朝南方和西方大秦萨珊之间的交流也日益紧密,六朝各地出土的西来物品大大增加。但中西方间的交流受当时复杂的亚欧政治格局影响较大,众多舶来品的具体传播路径仍有缺环,尚待进一步研究。正因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传播不易,双方都非常重视获取外来物品,中国丝织物等成为重要的商品流转于西方各地。中国上层社会对西方物品的追崇导致逐步学习、仿制和本土化生产,并影响其他造物。
第三、中国南方还通过海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输出大量六朝造物,而且是工匠、技术、工艺等全面输入并伴有深入的民间往来。六朝造物作为外来强势权力文化象征引入百济和大和,甚至参与到这些国家在这一时期文化构建与政权强化进程之中,是隋唐时期与东亚文化交流高峰之前的先奏序曲。
(责任编辑:姥海永)
参开文献:
[1] 张嫦艳,颜浩:魏晋南北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对外贸易的发展[J]沧桑 2008(05)
[2] (东晋)法显,章巽注:法显传校注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1
[3] (东晋)法显,章巽注:法显传校注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0
[4](唐)姚思廉:梁书·列传四十八·诸夷[M]中华书局 1973:783
[5](唐)李延寿:南史·列传六十八·夷貊传上[M]中华书局 1975:1964
[6](清末)陈作霖:南朝佛寺志[M] 台北明文书局1980:246
[7](唐)李延寿:南史·列传六十八·夷貊传上[M]中华书局 1975:1952
[8](南朝)沈约:宋书·列传五十七·夷蛮[M] 中华书局,1974:2395
[9]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M] 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43
[10] 张绪山:近百余年来黎靬、大秦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5(03)
[1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 中华书局2003:27
[12]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 中华书局2003:49
[13](唐)姚思廉:梁书·列传四十八·诸夷[M] 中华书局,1973: 795中有述:交趾为今越南北部,日南为今越南中部,扶南为今越南南部、柬埔寨及老挝南部
[14](唐)姚思廉:梁书·列传四十八·诸夷[M] 中华书局, 1973: 795
[15](北魏)郦道元,陈桥驿等译注:水经注:黄河之水[M],台湾古籍出版社2002:36引康泰《扶南传》中谈及迦那调洲,现为缅甸南部的丹老群岛,枝扈黎大江为恒河
[16] 韩振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C],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1991
[17](英)赫德逊,王遵重 译 :欧洲与中国[M] 中华书局 1995:46-47
[18]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 中华书局2003:41
[19] 张绪山: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探索[J] 史学月刊2001第1期,转引尔道西斯:前拜占庭时期希腊人在印度洋的活动(M.Kordosis,Hoi elliniki parousia stin Indico kata tin proto-byzantini epoxi,Istorikogeographica),历史地理[M](03)255-256
[20]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中华书局2003:41
[21] 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中西间海上交通的盛衰[J]民族史研究 2004(01)
[22](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布帛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1518中录入《晋殷巨奇布赋及序》
[23]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图说(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415
[24] 罗宗真:六朝考古[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17
[25](美)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來文明[M] 吴玉贵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51
[26] Nicholson,paul T..Egyptian Faience and Glass Buckinghamshire:shire Publications Ltd,p16
[27] 安佳瑶:中国早期玻璃器皿[J] 考古学报1984(04)
[28] 安佳瑶:中国早期玻璃器皿[J] 考古学报1984(04)
[29] 安佳瑶:中国早期玻璃器皿[J] 考古学报1984(04)
[30] 董俊卿:雷家坪遗址出土六朝玻璃珠的相关研究[J] 江汉考古 2007(03)
[31] 王志高:六朝墓葬出土玻璃容器漫谈—兼论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玻璃容器的来源[C]“六朝历史文化与镇江地域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0
[32] 转引自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3:59
[33](英)裕尔 撰,(法)考迪埃 修订,张绪山 译: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M] 中华书局2008 :202-205
[34] 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J]考古 1986(03)
[35]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 考古学报 1974(01)
[36] 干福熹: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玻璃[J] 自然杂志 28(5)
[37]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 中华书局2003:45
[38](唐)李延寿:南史·列传六十八·夷貊传上[M]中华书局 1975:1951
[39] 转引自邓端本: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M]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08)
[40](唐)房玄龄等:晋书·帝纪第九·简文帝纪[M]中华书局 1974: 32
[41] 韩昇: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C] 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论文集:2004
[42] 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J] 考古1959(01)
[43](唐)李延寿:南史·列传六十八·夷貊传上[M]中华书局 1975:1951
[44] 韩昇: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C] 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论文集 2004 年
[45] 宋应有:百济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影响[C] 韩国学论文集2011
[4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外臣部·卷999[M] 中华书局1960:“南齐武帝永明六年,宕昌王使求军仪及杂伎书,诏报曰:知须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秘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
[47] 王志高: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考察[J] 东亚考古论坛 2005(04)
[48] 王仲殊:东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海东诸国的关系[J] 考古 1989(11)
[49] 王志高: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考察[J] 东亚考古论坛 2005(04)
[50] 邵磊:百济武宁王陵随葬萧梁铁五铢钱考察[J]中国钱币 2009(03)
[51] 徐萍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J] 考古1984(06)
[52] 杨泓: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J]1984(06)
[53] 贺云翔 等:三至六世纪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南朝铜器的科技考古研究[J]南方文物2013(01)
[54](韩)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6 (02)
[55] 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12
[56](韩)赵康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6(02)
[57] 安志敏: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J] 考古1990(04)
[58] 戴禾,张英莉:中国古代生产技术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J] 历史研究,1984(05)
[59] 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吴镜[J] 考古 1989(02)
[60] 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J] 考古1984(05)
[61] 董亚巍:浅谈鄂州出土铜镜与日本神兽镜的关系[J] 中国历史文物;2003(04)
[62] 杨金平:徐州地区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兼论洛阳发现、日本爱知县东之宫古坟出土的同类镜[J] 文博 2010(02)
[63] 韩国河:日本发现三角缘神兽镜源流述论[J]考古与文物 2002(04)
[64] 杨泓: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J] 考古 1984 年(0 6)
[65] 郭富纯:论朝鲜制陶技术对日本陶瓷文化的影响[J] 收藏家2009(11)
[66] 宿白:南方海外交通的遗物[Z]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讲义1974
[67] 顾幼静:硬陶文化的比较研究[J] 东方博物2009(02)
[68] 王志高:六朝墓葬出土玻璃容器漫谈—兼论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玻璃容器的来源[C] 六朝历史文化与镇江地域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0
[69] 蔡丰明:中国东海沿岸地区文化在东亚各国的流布与影响[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4(05)
[70] 童斌:日本出土反映古代中、朝、日文化交流的超一流马具[J] 国外社会科学1986(04)
[71] 杨泓: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J] 考古1985(01)
A Brief Account of the Foreign Material Cultural Exchanges via the Maritime Routes in the Period ofSix Dynasties
伴随六朝南方政权的海上经营以及佛教传播,几条海上交通路线日益重要并且通畅:南线海路从广州地区出海南下沿马来半岛到南海各地;由南向西形成西线,经印度洋、波斯湾接上西方海上航线延伸至北非或罗马;另一分路为东线,从东部出海到朝鲜半岛南部再抵日本列岛。这一时期海上交通线的开拓沟通了南部中国与海外诸国物质文化的多方面交流。本文结合物质史料对六朝的几线海路进行考订,建立起三至六世纪以中国南方政权为中心,东西文明区域之间海上物质文化交流的总路线图,并对六朝海上交通的成因以及对中国、东亚甚至西方所产生造物文化影响进行综合评述。
The southern China developed the material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overseas countries by sea in many fields in the period of Six Dynasties.This article is to systematically comb and collate several maritime routes during that tim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 general map will be formed,it shows that the material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by sea centered around China during the 3rd to the 6th century.It also comments on the causes of the maritime routes and the influences on the material culture in China, in East Asia,even in the west.
六朝;海路;造物;交流
Six Dynasties;maritime route;material culture;cultural exchanges
朱文涛,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在读博士后,研究方向:设计史与设计理论。
1本文系江南大学产品创意与设计文化研究中心(江苏省高校哲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专项研究资助项目、2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六朝设计史”(项目号:11BH067)、江苏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设计价值观研究”(项目号:11YSC0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