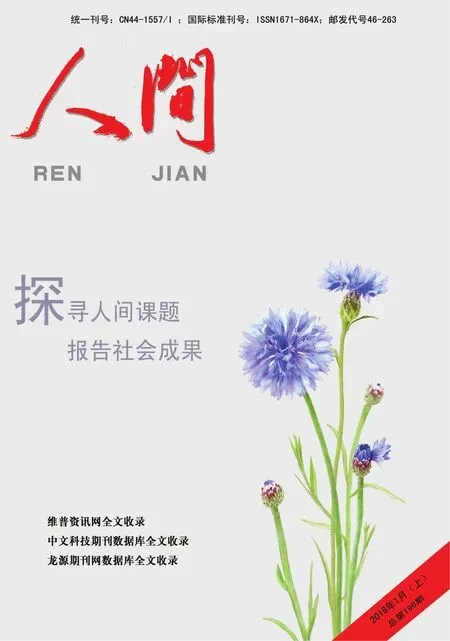论张衡《归田赋》的隐逸思想
2016-11-28刘佳
刘佳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论张衡《归田赋》的隐逸思想
刘佳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张衡的抒情小赋《归田赋》在汉代赋作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人处在东汉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其思想的转变在赋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归田赋》对人生失意情感的抒发,对逍遥之境的追求与向往,成为张衡晚年人生的深切表达。《归田赋》可以看作张衡对“逍遥”思想理解和追求的一个总结。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是汉赋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关键词:张衡;归田赋;逍遥;隐逸
赋的创作,到了东汉,模拟前人创作的痕迹明显,如张衡的名赋《二京赋》。即使是抒情赋的创作,也很难逃脱屈原、贾谊等的感伤情绪,但张衡的抒情小赋《归田赋》,却能独立于众赋之外,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摆脱了赋作陈陈相因的弊病,又将自己的个性和理想融于这篇小赋之中,实为后世赋的典范。
一、张衡《归田赋》的创作背景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崔瑗在《河间相张平子碑》中赞张衡曰:“君天姿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环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然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
张衡游历三辅之地,入帝京,进太学深造,习经学,受到一批儒学大师的指点,并结交了后来成为终生挚友的崔瑗。他一方面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很忧国忧民,关心国家的政治命运,然而张衡却遭到宦官的怀疑与排斥,在尽职与生存之间,张衡陷入了矛盾与苦闷之中,最终选择了屈势以求生的悲哀之路。《后汉书》记有:“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目共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状,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①。张衡于永和初年被任为河间相,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②。第二年(即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张衡在凄凉的心境中卒于尚书任上。
东汉中后期,政权的败坏越来越严重,士人政治思想与现实社会开始产生激烈冲突,他们对大一统的怀疑、对政权的失望造成了士人阶层的反抗心态和隐逸心态的产生,加上士人被外戚、宦官的戕害,他们对政权的失望可想而知。礼乐崩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思想成为士人的选择,如张衡、蔡邕、仲长统等人的老庄隐逸心态。他们的思想体现在作品上就是从铺张扬厉的大赋转为自我抒情的小赋,此种心态与赋作观念的转变尤以张衡为代表。
二、张衡《归田赋》中的隐逸思想
张衡的抒情赋的创作,以《思玄赋》与《归田赋》为代表,《思玄赋》属于长篇骚体赋类,但在抒情意义上有开风气之先和赋史研究价值的赋作,无疑是他的《归田赋》。该赋作于张衡去世的前一年,作者见朝政日非,遂生弃官归隐之思。《归田赋》云:“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张衡在都邑洛阳生活了四十余年,期间,他在天文、历算、史学特别是地动仪的制造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而他的官职不过是郎中、太史令、侍中等微职,所以“无明略以佐时”句就非常有意味,并且古人常将“河清”与圣人治国联系在一起,张衡的“俟河清乎未期”可见他对当时政治的绝望。
继而张衡油然而生摆脱世俗尘网的想法。赋云:“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鯋鰡”。“逍遥”语出庄子《逍遥游》,《逍遥游》所阐释的人生是远离尘世的功名利禄,摆脱人情束缚的人生,进而使自己的精神达到畅游无阻的境界。张衡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他的青年时期,他的早年之作《七辩》,就表现出对道家隐逸境界的向往。从“祖述列仙,背世绝俗”③的主人公“无为先生”以及依卫子劝其求神仙之美,先生乃欣然从之,从将飞未举的描述来看,张衡已于道家非常向往。
后来张衡在《与崔瑗书》中,表明自己“批读《太玄经》,知子云特极阴阳之数也……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④的乐趣。并且张衡一生好史,有很浓重的史学精神,而史学精神和道家精神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密切联系。老子本身也做过史官,况且史官要掌握历史的来龙去脉,对社会的观察和领悟也透彻。张衡的“朝隐”就与此有很大关系,他本人“虽才高于世,而无矫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结交俗人”。可见史学对他本人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后来他作的《应间》赋也表明了这种思想,赋云:“子忧朱泙漫之无所用,吾恨轮扁之无所教也。子睹木雕独飞,愍我垂翅故栖;吾感去蛙附鸱,悲尔先笑而后号也”⑤,文中多处用《庄子》的寓言,其心灵处在儒、道之间,张衡更是倾向于道家思想,《归田赋》就是张衡“隐逸”思想的具体体现。
张衡在《归田赋》中提到道的“逍遥”,首先有逃离尘世的心态,对世俗的纷争,他已无意于仕进,特别注重自我精神和人格的自由。如晚年所作《思玄赋》,他在《思玄赋序》中说道:“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状,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张衡晚年追求的是“逍遥”的田园式的生活,所以他想逃脱世俗的羁绊和政治斗争,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达到逍遥境界。
其次,张衡笔下的自然是充满了幻想式的自然图景,无论是百草还是百兽,都是作者的情感的寄托,这种田园生活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逍遥”的生活是以自我的精神完善为基础,没有《庄子》中阐发的极度抽象的“逍遥”,也不同于后来的田园派的真实的“逍遥”。最后作者极游至乐之后,收其放逸之心,归驾蓬庐。赋云:“于时曜灵俄景,系以忘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戒,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归田赋》云:“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张衡所谓“逍遥”最终落于“娱情”,这里的“娱情”的深层内涵即为感老子的遗戒,回驾蓬庐,终须有所归。
三、张衡的儒道人生
许结在《张衡评传》中提到“玄儒”一词,东汉中叶士人的玄
儒人生观,是从儒经思潮中脱颖而出的高蹈情怀和玄远意识的表现,其内涵是突破汉代儒学体系对人心灵的约制,建构一种新型的人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中往往有一种隐逸情结,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无非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儒家的仕进之志和出世的佛道共同构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然而儒家的出世之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状况。知识分子选择隐逸出世,其原因归结起来就是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之间的矛盾。在逃离社会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山水作为与社会政治的对立面,投身山水自然的行为实为某种象征,标志了自我人生价值的取向。
张衡《归田赋》中描写的归田隐逸的思想倾向正是对其《思玄赋》中表现的超越意识的“具体实践”。《思玄赋》中的主人公经历了一番天上人间的逍遥:“朝吾行于旸谷兮,从伯禹乎稽山。嘉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指长沙以邪径兮,存重华乎南邻……愁蔚蔚以幕远栖,越卬州而愉敖。跻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⑥,最后意识到想要寻找没有污秽的世界是非常虚渺的,寻找精神上的超越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归田赋》表达了作者在心超尘埃的精神状态下,做出了辞尘世之后的轻松愉悦的心态,其《归田赋》抛却了汉大赋描写景物的模式,如司马相如《子虚赋》提到云梦泽,首先就是全景的总览:“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⑦,又写其山、水、土、石等等,尽量将云梦泽周围事物尽揽其中。《归田赋》对景物进行了选择,在整个自然风景中切割下符合自己需要的部分,作者以春天为季节时间,然后写和暖的天气,花草繁茂,鸟语声声等等,景物清晰明朗,脱去了以前同类作品的繁缛艰深,在主客观的和谐交流中折射出较自觉的自然审美意识,也与张衡“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的心境契合。
张衡的《思玄赋》和《归田赋》代表了其对社会政治的疏离,从关注社会到关注人生,关注自我,抒发个人的情绪和感悟。《归田赋》描写的山川也由某种功利性的存在转为社会政治的对立存在,张衡所享受的不再是疆域的辽阔带来的愉悦,而是学习道家的“山林之乐”。张衡把玄思、志向、情感与自然景物联系起来,开拓了文学史上的审美领域,开启了六朝山水田园文学及玄言诗的源头。
注解:
①范晔.后汉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563.
②范晔.后汉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566.
③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490
④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P339.
⑤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488.
⑥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P208.
⑦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47
参考文献:
[1]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许结.张衡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范晔.后汉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王渭清.张衡诗文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M]中华书局,2005.
[7]郑明璋.汉赋文化学[M]齐鲁书社,2009.
[8]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9]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刘佳(1988-),汉族,男,工作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