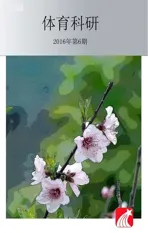体育的仪式治疗功能
——中国高密度举办体育赛事的文化学价值
2016-11-28路云亭
路云亭
体育的仪式治疗功能
——中国高密度举办体育赛事的文化学价值
路云亭
现代大型体育赛事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形态,它是一种与现代社会完全兼容的超体育的文化形态。为了塑造出更为理想的国家和城市形象,大型体育赛事在中国已经演化为一种国家仪式,它在精神方面的价值可能要高于其提高民众的身体健康水准的价值。中国高密度地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也是对中国节日数量不足的补充,对民众来说具有“超身体”的仪式治疗作用。
大型体育赛事;国家仪式;中国元素;节日;价值
大型体育赛事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形态,中国人为了振兴民族体育,也在挖掘、整理并设计属于自己的体育赛事,如中央电视台5套播出的《脚斗士》《武林大会》之类,但这些所谓的体育赛事无一成为国际主流赛事,甚至未曾经受起国内观众的初级筛选便早早就失去了收视率,沦为一种文化附庸或已全然淡出了民众的视线。在如此境遇下,中国人不得已又将相对成熟的来自异域的国际体育赛事看得如同己出,并对其进行了适度的改造,国际赛事的民族化改造再度变成一种潮流。体育是赛事,更是一种普泛的人类仪式,但中国人很顺利地将其改造成了一种民族仪式,甚至将其看成一种民族团结的象征体,体育赛事存在的合理性在中国也得到了更大的阐释空间。
1 大型体育赛事具有“超身体”的仪式治疗作用
无法否认,自从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之后,体育逐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热点性主流事件,但女排的登顶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体育人口在增加,也很难说中国就此成为体育大国。在吃饱饭尚有困难的时代,中国体育仅仅是一种观看类体育而非参与式体育,大量的中国观众观看体育赛事未必一定要在其中寻找娱乐的元素,很可能还在于寻找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虚拟出来的强大的自我化的能力。要获得这样的能力必须有一种先决的条件,那便是将体育的身体性元素抽离出去,将一种胜利模式灌注其中,让获得胜利的实体充当一种精神载体,而这种精神的载体在教化世界里是一种神圣价值观,而在世俗的世界里很可能仅是一种娱乐的对象,或是心理博弈或情感赌博的器具。法器的神圣性和世俗性在这里再度得到展示。
体育的另一种说法是竞技,而竞技和博弈乃至赌博的关系十分紧密。从终极的立场考量,竞技就是一场博弈,它和世俗生活中的赌博尚无法完全脱离干系,即便世俗生活中的赌博也花样繁多,赌钱仅是最低端的一种,而赌感情则属于最高端的一类。大量观看体育赛事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将自我的尊严一同押到虚拟的博弈场上去。新时期以来,不少中国人在观看体育赛事时也一度押上自己的倾向性,并因此而获得了一种漫长的兴奋感。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一种信息传输的非对称环境中度过了一段对体育的本质近乎异化性理解的岁月。无可否认,当年的女排夺冠给中国人送来了很大的解脱感、幸福感和充满了快意恩仇的爽煞之感,然而,它同样是一种刚在中国发端的异化类体育项目。从仪式学的角度看,当年的女排更近似媒体创造出来的神话。胡志毅在解读神话转移的原理时曾认为:“现代人类学的大师弗雷泽在考察了现存的原始部落以后指出,神话的发生与巫术仪式密切相关。神话用形象语言所讲述的事件往往要实际表演出来。在历史演进之中,仪式演出消亡了,而神话故事却流传下来。因此,我们须从活的神话中推演出已死的仪式。”[1]自从当年的女排之后,中国的诸多体育项目已经逐渐和国际主流体育文化脱轨。换言之,新时期的中国体育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非身体化的体育,或者说具有强烈的超体育特性,它和仪式化的体育更为接近。2016年中国女排在里约重获奥运金牌,演绎的是同样的文化性、传播性与社会性主题,郎平也再度成为里约奥运会期间最受国人欢迎的人。中国人再度温习了一遍久违的胜利仪式。所谓胜利仪式就是绝对战胜所有对手的一种仪式。换言之,胜利仪式的内涵就是不折不扣的金牌主义。
仪式有其固定的文化功能。“仪式帮助了个人或集体完成他们生命过程中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换,并记录人生的重大变化,提高了个人或集体的状态或地位并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2]如果说1981年的女排夺冠是一种由偶然性的体育事件缔造出来的国家仪式的话,那么,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女排夺冠就是一种固有仪式的回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早已被淡忘的仪式的复活形态。英国人类学家马丁·艾斯林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一种不可孤立的动物,势必形成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从而深切地依赖这些集体体验。因为一个社会团体的一致性就其定义而言,是由一系列共同的风俗、信仰、观念,由共同的语言、神话、法律和行为准则构成的。但首先是,这个团体(和其中的每个个人)必须能体验到它自己的一致性:仪式就是一个原始部落以及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用以体验这种一致性的手段之一。”[3]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群体中,而群体中的人的仪式具有不可或缺性,即便已经缺失的仪式也必将在特别的时间内得到复活,否则人类的社会性就不复存在,人类也将无法存在下去。具体到每个个体而言,仪式品质的高低会影响到当事者的常态化生活质量。仪式学家曾经将仪式看做是一种精神治疗手段。“人们缺席了婚礼或葬礼这样的仪式,同时也就丧失了在生命过程中安全渡过转变或成功处理生活危机的机会。心理治疗就成为这些缺失仪式的现代的替代品。当人们被现有的身份或人际关系所困扰时,咨询师可以协助来访者构建一个治疗仪式处理未解决的危机,获得遗失的身份与地位,摆脱曾经的自己或困境,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获得生命的继续前进。”[2]在此意义上考量,仪式是超时代的,任何一种固有的仪式都会在特别的时代以特别的方式展现出属于自己的新的生命形态。中国人还在回忆旧有的仪式,并且一如既往地将其视作一种抽象的精神。中国媒体屡屡声明的“女排精神”就是一种体育仪式化、仪式宗教化、宗教宣传化的代表。
现代奥运会一向具备业余主义的内在感召力。顾拜旦于1894年1月15日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曾说:“许多国家的业余运动员,为了抵御侵犯他们尊贵地位的金钱和职业化的精神,拟订了充满妥协和矛盾的复杂规则;而且常常受重视的是它们的条文而不是它们的精神实质。改革不可避免,但在进行改革之前,必须开展讨论。摆在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的问题都是有关业余规则中的这些妥协和矛盾。”[4]奥运会的业余主义始终是一种主流。鉴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中国人最看重的体育赛事一直是奥运会。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尚无法抵达奥运会的殿堂,正因如此,许多中国人更加渴望看到奥运会的神秘面纱。无以否认,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生机盎然且充满了期待感的时代,体育作为一种具备启蒙价值的先锋类的文化产物,早已在一种安静的状态下化为一种公共话语。许多中国人在了解体育之前,仅仅知道奥运会及其坚守的业余主义宗旨。受到固有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人反对西方式的职业竞技体育,因此而更加爱戴强调业余理念的奥运主义。这里寄寓着一种简单的逻辑,因为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体育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热衷于体育,为的是得到一种开放的国际视野,寻找更为充足的民族自信力,并借以建构一种更为豪迈而健康的国家形象。以奥运会为典范的体育赛事与国家意志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密。顾拜旦于1936年7月曾发表致柏林奥运会火炬传递者的祝词《高举火炬前进》,文章记载:“历史的统治和斗争将继续下去,但是知识将一点一点地取代危险的愚昧无知;相互理解将减轻不经思考的仇恨。这样,我曾为之劳动了半个世纪的大厦将得以巩固。”[4]顾拜旦未曾预见到希特勒对奥运会的利用。顾拜旦一贯坚持“奥运本位”的理想,将任何国家举办奥运会都看成是一种对奥运会精神的传播行为。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开启了另外一种国家与奥运会的链接模式,这种模式体现出3个方面的特质。其一,它彰显出一种秉持帝国思维的国民对奥运会的真实的认知状态。其二,柏林奥运会将巨大的体育赛事和巨大的政治图谋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景观。其三,柏林奥运会还开拓出国家仪式和体育仪式混同的先河,并推演出一种奥运会和政治高度汇合的新的奥运形态。当德日系体育日渐衰落之时,苏联一度成为该项体育法系的代言体,随着苏联的解体,所有东方主义的捍卫者都集体性地在世界上失去了声音。体育与国家的紧密连接关系开始松动。与此同时,英美体育法系再度崛起,预示着体育要在另一种单极化的模式内发展。体育脱离了政治,必然要寻找到另一种出路,并在一种貌似公正、独立、公开的立场上展示出其和平、柔性、优美的一面。
中国力量的崛起再度颠覆了国际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非常性关系。中国人一度极为认可奥运会的卓绝价值,主要原因在于奥运会可以很好地锻造出中国的国家形象。为此,中国申办或举办奥运会的热情极高。北京奥运会举办后,少部分兴奋过度的中国人一度丧失了对那届奥运会的常态的判断力,人们可以轻易地在报刊上看到歌颂北京奥运会的文章。“当然本届奥运会依然是我所看过的历届奥运会中最……成功的一届,无论是举办城市的城市建设、道路交通,无论是运动员的表现、志愿者的服务,无论是火炬传递、赛事组织,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方方面面,可圈可点的太多太多。但是我们必须沉淀激动的心情,平和、公正地审视此次奥运的全过程,要理智地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要接受中国还只能称为金牌大户,而不是体育强国。因为‘体育强国’这不光体现在取得金牌的数量、项目这一层次,而是中国人对于奥运精神的理解,什么时候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奥林匹克’,那时的中国才是当之无愧的体育强国。”[5]这篇文章有意无意地使用了“最成功的一届”的字眼,完全忽略了国际上对任何一届奥运会评价的中性化的用词惯例。最高级语汇的使用体现出使用者对文化统治力的追求意向,其原始的欲念内潜藏着一种对于国际顶级仪式的热恋与攫取之欲念,它几乎全盘展示出东方大国的一种蛮横而强直的大国思维,唯有具备大国思维的人才更愿意在公共媒体使用极限性用语。连清川在阐释帝国文化时曾说:“在《巨人》一书中,弗格森即提出,美国是否帝国,历来有强烈的争论。但是就他个人而言,确乎承认帝国有其合理性,而美国‘称帝’,也的确有着对于世界秩序建设的良性作用。那么他所提出的,不过是优化这个帝同制度的方案而已,从而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地维护世界的‘自由帝国’。”[6]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官方媒体看来,美国就等同于“美帝”,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常识,并会像传播常识一样传播这样的论点。然而,美国并非人们想象或感知到的形象、模样或形态。“不过,这是学界的一相情愿而已。在美国的政治廓阈之中,从来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所谓美国建设‘自由帝国’的思维。”[6]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帝国思维以及帝国实体,三者有十分明确的边界。如果仅仅在语言游戏的层面审读,并不会产生特别的后果,而如果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则极易造成一种想象的乱象。
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同样一直秉承“不称霸”的固有承诺,这个口号在20世纪后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都遭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嘲讽,因为当年的中国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一个由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群充斥全国的国度会有称霸世界的可能。但在21世纪的中国,这样的称霸与非称霸的选项却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对周边个别侵占中国海洋权益的国家有一定的震慑力,那也是基于一种“蚁象效应”。所谓“蚁象效应”,指的是有一种大国和小国的特殊关系。大象在行走,一不小心踩着了一百万只蚂蚁,蚂蚁抗议,但大象并不知道它给蚂蚁带来的灾难。这便构成了一种“蚁象效应”。中国人举办奥运会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所谓的“蚁象效应”,极端化的外域人士很自然地感受到那里有可能寄寓着一种隐形的“帝国”思维。其实,这种效应永远存在,因为在蚂蚁眼中,大象永远是帝国主义,而蚂蚁永远是受害者。而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蚂蚁集群可能利用繁殖的优势反制大象,而大象的生存一直比蚂蚁还要艰难万分,许多品种的大象一度抵达灭绝之险境。
就在人们谈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上升之时,旨在寻求和平的冷静型学者更为关注体育所营造出来的非霸权的内蕴。人们始终未能忽略体育的建设性功能,而几乎完全剥离了其国家霸权的精神符号。“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健康越来越关注,体育也由此由‘观赏性产品’慢慢向‘消费性产品’转变。”[7]从直观的角度看,中国长期以来贯彻执行的体育大国或体育强国的战略更接近东方主义的超级大国思维领域,而全民健身战略更接近游戏体育的本体。两种体育思想孰优孰劣?尚难做出判断。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战略设想都包含有国家治疗的意义。美国的Carmichael认为:“游戏治疗并非仅仅是在游戏室里使用玩具作为沟通手段的简单方式,而是包括诸如绘画、音乐、舞蹈、戏剧、运动、诗歌、讲故事等其他多种表现方式。尽管游戏治疗的主流仍然是游戏室以及象征性玩具的选择,但游戏心理治疗师已经将言语以及非言语的沟通媒介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扩展。”[8]由此可知,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设想具有一种国家对民众的精神抚慰功能。在此意义上考量,大众体育的思想价值要远远低于具有国民精神治疗意味的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战略设想统摄下的体育类型的思想价值。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部分学者依然停留在体育与身体健康的浅近层面,无法认识到体育的高端性价值。“有人说,北京奥运会的最大社会遗产,是群众对全民健身这一现代文明理念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理性,自觉健身的意识大大提高。体育健身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的观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回应。”[7]此论显然无法抵达体育的本体,是一种对体育的内涵所做出的极端功利主义性质的阐释,更是一种短视性、浅观性、浮泛化的体育认知。在国民精神治疗的大旗下,任何身体性的体育内蕴都显得失去了意义。由此可见,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策略主要的社会功能是治疗中国人的“东亚病夫”自卑症,而大众体育主要是提高民众的身体素质,前者属于心理治疗范畴,后者属于身体改良范畴,本无所谓孰优孰劣之别。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东亚病夫”自卑症是否依然存在?摘除此心理疾病是否需要一个强大而鲜明的国家仪式?回答此问题依然充满了艰难感。
2 高密度的体育赛事源自民众对过往群体集会的简单记忆
完全可以认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所具有的意义仍然被人低估了,北京奥运会是一场空前绝后、巨大无比、超越任何体育形态的国家治疗仪式。从表面上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仅仅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强的视觉冲击,而无涉心理治疗的范畴,其实,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如果仅仅是一种体育赛事,中国人不会花费亿万元的资本去参加一场如此规模的豪赌。毫无疑问,那场赛事远远超越了体育的范畴,而进入到了中国的国家乃至国际级超大型仪式的行列中。当然,体育毕竟是体育,北京奥运会首先让更多的中国人终于获得了近距离地欣赏、体味、把玩来自欧洲文明发祥地的奥运会的赛事的机会,中国人可以借此对奥运会的成套的文化和文明形态有了直观的了解。
中国自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30年间,一度热衷于开展各种群众运动,那种活动一直为所谓的“热火朝天”“大干快上”“多快好省”等术语及其意义体系所支撑,带有快意恩仇、一决千里、一举拿下等粗豪型战斗意志。刚猛的行为做派不仅成为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惯性,还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智囊集团的思维习惯,余风所及,就连最需要安详恬静、温和静好的中国的教育界也遭到了群众运动的影响,陈平原对此不无感慨:“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知道,校园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在制定发展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15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的要求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地急转弯,非常伤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10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一个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的实验必须小心翼翼,特别忌惮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换形’,而不应该是‘日新月异’。”[9]中国利用举国体制争取回来的体育赛事也和开展大型社会活动或运动的文化运营模式完全接轨。
展示或再现一下这段历史会让人回味无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时代,大型的群众运动一时间销声匿迹,但是,很多中国人的思维惯性仍在群众活动的画面上滞留。由于教育、文化、生理惯性等因素所致,人们的心理和生理习惯还残留着对大型群众运动的依赖性,尤其对独特的超大型化的聚会模式格外留恋。于是,大型体育赛事就成为弥补群众运动的必然选项。中国人对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热情主要源自这里。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谋划举办大众大型体育赛事了。只是当年中国的财力与物力、外交和内政都存在一些困难,一时无力搞出太多的体育赛事。到了21世纪,中国政府的财力、物力以及中国人的过剩精力都达到了一个新值,于是,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就从原先的设想变成了行动,从原来的幻想变成了现实。中国人为此冲动异常,大有“冲决一切阻碍誓死举办成功”的气概。
需要澄清一个问题。体育是否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或群众运动?或者说体育本身是否称得上是一种群众运动?这是一个难以给大众带来圆满回应的难题。从21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后,中国的确掀起了一个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高潮。广州于2010年为大众奉献上一出开闭幕式堪称异常壮观的亚运会,它让中国人再度感受到一种盛世欢乐的极限时光。2011年,深圳举办了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同年江西的南昌还举办了中国的第7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众多的大型体育赛事让中国人获得了节日般享受的同时,也让很多中国人自然联想到一种大运动时代的特殊的群众聚会的浩大境界,那里一度寄寓着“团结一致”“举国同心”“众志成城”“莺歌燕舞”之类的共同意志和狂欢镜像。巴赫金曾说:“狂欢节不妨说是一种功用,而不是一种实体。他不把任何东西看成绝对的,却主张一切都具有快乐的相对性。”[10]现代学者还将充满狂欢格调的群体盛会释读为一种盛世情怀,理由是人们也可以借此享受真正的节日般的快乐,更可以释放掉一些由全社会的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压力。仅从直观的角度看,各种各样的大型体育赛事的确是一种视听盛宴,其中不乏声、光、电、气之美,欢歌动天之景,更有如仙如幻的艺术镜像,它让中国人感受到一种大国国民的潇洒品格,而当年的群众运动也曾经在一种纯美学的范畴中寄寓着同样的审美元素。
中国的节日有其固有的东方性,体育赛事可以成为替代社会运动的暴走式、刚烈式、强猛式聚会形式,同时也不乏喜悦、吉祥、以及团圆的含义。新时期的体育赛事有其独特的价值,中国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和群众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体育赛事是一种自发的聚会形态,更是一种充满喜庆元素的非定期性节日,还是一种足以让国民感受到强大国家所特有的身体性和精神性双重满足的仪式。它超越了既有群众运动的国家主导、群众被动接受的结构,重构了中国节日学、仪式学和庆典学的深刻内蕴。不得不说,1949年是一个具有时代隐喻的时间节点。中国人在1949年以前的聚会方式大多集中在大自然的季节轮回、皇家内部的生活节律以及新政府的构建时日之类的仪式节点,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则是一个全面瓦解传统节日的时代,当年已经开启了以社会运动代替传统节日的先河,它使得节日皈依到一种单一的社会指向层面。
无以否认,中国在迈进现代社会之前面临诸多的难题。首先,何为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否需要高强度的节日效应?这里需要将新中国的体育的来龙去脉做出梳理。
中国的体育体制源于苏联,它呈现出一种典型化的举国体制的模样。颜下里曾梳理过苏联体育的前世今生:“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创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人类几千年来体育平权理想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充分满足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体育需要的长远和根本目标的确立标志着苏维埃体育开创了人类体育史的新纪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早期苏联体育虽然只能以军事训练为重心,但是,却从未脱离无产阶级体育的长远和根本目标。正是这一目标决定了高水平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都作为体育的有机构成而受到同等重视。但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随着二者地位逐渐变化,一种由超常态的高水平竞技体育与严重萎缩的大众体育所构成的畸形的体育行业结构在苏联逐渐形成。”[11]苏联体育并未突出其节日性,反倒一直在强化其中的国家主义内涵。其实,现代奥运会除却其节日性外,还有强烈的政治寓意。顾拜旦曾说:“伟大的德国爱国者路德维希·扬和瑞典人林分别在本国试图传播他们的体育宗旨。但是,路德维希·扬的一个观点是想建立一支能够使德国统一的军事力量,而林的目标则是通过科学文化的体育运动来增强体质。”[4]由此可见,体育和军事权威的象征意义有关联,而且至今为止仍未见消减之迹象。21世纪最初的十余年内,以体育赛事为核心的聚会方式则是一种和国际性节日接轨的庆典形态。任何节日都具有多维性,节日可以给举办者带来劳顿感,还可以给接受者带来享乐。即将迈进现代社会门槛的中国民众面临的是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乃至过劳死的威胁,而非举办节日过多所带来的空虚感。繁多的节日一度是一种国家虚伪繁华乃至过度享乐的标志,但是,工业时代的身体释放行为已经无法使人堕落,因为工业化是以将人的身体彻底纳入机器时代为目的的,举办节日只能拯救身体,而无法使之失去既有的价值。质言之,体育赛事只能是工业化时代的一种拯救性力量而非毁灭性力量。中国申办或举办为数众多的体育赛事有其独特的国情动因。体育进入中国后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在各种势力的鼓惑下,中国人也因为体育而改变了一些业已沿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
就体育赛事与休闲的关系而言,中国的赛事举办者和休闲者其实一直有一种共同利益,两者属于同一共同体中的互相依赖性元素,赛事举办者设计并建设一种休闲程序,而接受者则通过消费而获得休闲类享受。换言之,体育赛事的举办者举办一场赛事须付出劳动,而休闲者则可以借此体味到一种高品质的休闲生活。因此,对一些挣扎于困顿生活线上的劳动者而言,大型体育赛事无疑是一种值得体味的视听盛宴,更是一种优质的休息手段。中国的劳动者是国家的基础国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然在各自的领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且属于法定意义的纳税人,他们所能够享受的文化产品都是通过货币交换获得的,许多休闲活动经过了商业操作,具有现时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民众无须向一些提供休闲服务的机构额外地致谢。
客观而论,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举办的体育赛事相对密集,面对如此的景象,人们更需要探究其中的必然性。通常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都屈指可数,因此,许多国家在法定节假日之外还有许多补充性的节假日。中国自2010年以来陆续将原先的除夕、端午、清明、中秋等传统假日归入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序列,借以强化节日中的中国元素。然而,传统节日虽然有更多的民族认同感,却因为有过一段备受冷落与歧视的经历而丧失了其必要的神圣性。中国仍旧有大量的神圣性节日的空缺。在巴赫金认为:“节庆活动(任何节庆活动)都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节庆活动永远具有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世界观内涵。”[12]抛开传统节日的固有价值不谈,一个繁荣之国一定是节庆种类繁多的国家,中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节庆日多样化的国家。胡志毅在解读文革广场活动时曾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样板戏,是意识形态发展到极致时期的戏剧。如果说建国十七年的戏剧是一种‘国家的仪式’,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戏剧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它是政治运动发展到顶端的产物。广场上的狂欢是一种节日的体现,它与样板戏构成了大剧场与小剧场的关系。对于中国的政治而言,必须通过戏剧的神话与仪式,强化革命的历史,这不仅使革命合法化,而且使革命神圣化。样板戏是节日和狂欢中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剧场国家。”[13]在许多人的眼中,繁多的节庆日是盛世的标志,而所有关于盛世的描述都会在终极的意义上演化为一种仪式。在书写盛世场景方面,大型体育盛会几乎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即便是狂欢,也无以脱离其中的政治寓意。巴赫金曾说:“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10]盛世书写往往带有强烈的大众性、表演性和公开性,它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进步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在盛世书写者的视野里,大型体育赛会在中国并不显多,而只是显得过少,甚至可以说还少得可怜。中国的盛世书写首先应当考虑到政治符号或行政元素,但中国古代成就盛世仪式的主流项目主要是戏曲而非其他。诺斯罗普·弗拉亥指出:“神话在提供情况方面占有中心地位:它给宗教仪式以原型的意义,给神的传谕以原型的叙述。因而神话就成了原型,虽然我们为了方便,在讲到叙述的时候才说神话,在讲到意义的时候说原型。”[14]神话思维对帝制时期的任何人都有强劲的感染力。康乾盛世时的乾隆皇帝是一位戏曲爱好者,乾隆皇帝终其一生多次借助戏曲显示皇威与国威。表面上看,乾隆皇帝一直在褒扬戏曲的艺术功用,其实他仅仅是利用戏曲做了一种教化事宜。英国文学理论家里维斯说:“伟大的戏剧有时不仅是供人娱乐的。我想称它为一种典礼或仪式,即用一种郑重的方式展示某种深刻的涵义结构,演员和观众都参加进去。因此,一出伟大的戏剧,你越熟悉它,你的收获也越丰富。”[15]帝制时期的帝王很难将戏曲看做是一种艺术,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仪式或宗教形态。英国戏剧理论家墨雷曾说:“希腊悲剧是从古代宗教仪式中脱生来的,甚至在较晚的悲剧家欧里庇德斯的《酒神的伴侣》中依然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酒神祭仪的结构。”[1]新中国开国元勋中不乏戏曲爱好者,其对戏曲的理解同样无法脱离仪式的轨道。戏曲一向具备展示国家强大的仪式化功能。帝制时期的戏曲并非新中国的原始创造型文化类别,而天然地带有本土性、农耕性、封建性之类的符号元素,它在超结构的内涵上和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略有抵牾,戏曲在日后一直在改造与维护的两难选择中徘徊,其演进或生存的焦点便在于仪式的内涵、结构以及其形态的改变方面。
新中国的体育体制源自苏联,中国人宁可将体育的存在价值解释为一种苏联体育模式,也无以将古老的戏曲作为新中国的国家仪式。中国人对体育的迷恋也就此成为一种对苏联体育的再解读过程。“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国际工人体育运动对这种畸形体育结构的出现产生了最初的影响。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体育国际’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纽泽恩体育国际’长期进行的路线斗争迫使苏联体育不得不用体育成绩来证明路线的正确。高水平竞技体育开始被赋予了较多的政治含义。”[11]在苏联模式的干预下,中国人的体育理论家无法忽略苏联式体育模式的巨大影响力。熊斗寅曾呼吁要“拥有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彻底改善体育队伍的人才结构”[16]。他进而认为:“体育事业是一项科技性很强的事业,从事体育工作要求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才。体育人才应包括运动人才、科教人才和管理人才。为适应未来体育的发展,体育工作需要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16]体育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类别,它既具有游戏内涵,也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寓意,更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仪式。放眼当今世界,能将体育的游戏内涵和意识形态寓意融合得较好的国家则是现时代的中国。中国人将体育推向新高度的方法无非是将体育赛事做出仪式化、节日化和庆典化处置,而赛事的节日化与节日的赛事化规划可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找到根据,其中包括古罗马帝国种类繁多的节庆日名录。
3 国家仪式的缺失成为中国的盛世书写者建构体育仪式的动因
行政意志统摄下的节日与仪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真实风貌,这可以在古罗马帝国的行政形态中找到依据。英国学者纳撒尼尔·哈里斯在《古罗马生活》中记载,罗马帝国经历过王政、共和和帝制3个时期,罗马帝国时期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层,其一是由国王、官员、教士、骑士和自由民组成的贵族与平民阶层,其二则是奴隶阶层。以现代奥运会为范式的体育继承的是古希腊的竞技原则,但也融合了罗马贵族与平民的竞技传统。顾拜旦曾对奥运会和骑士制度的关系做出过论述:“在许多人心目中,中世纪是禁欲主义潮流占优势的历史时期。这种观点用以看待封建社会之前的历史时期,较之看待封建时期更为真实些。无论如何,在封建社会的中心,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界限明确的奥林匹克再生物——骑士制度。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宣布这种亲属关系。乍看起来,确实表面上不相似。骑士们自己就更少意识到这种关系了,他们没有任何主见。奥林匹亚不是为他们而存在。然而,只要我仔细研究一下骑士们的行为举止并探讨一下他们的动机,他们对体育的热情马上就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立刻看到这就像涨满了水的河流一样充沛。后来教会出现了,通过奇怪的相反方向的努力,把骑士制度已经打倒的东西又恢复起来。诸位会说,那是一种不同的精神。”[4]现代中国很少有人首肯罗马人奢侈的生活方式。以古希腊奥运会为原点的现代奥运会在中国传播得极为迅猛,其中就和中国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纳态度有关。从本质上而言,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更近似中国的商朝人。周文王打起了尚德的旗帜很快就推翻了商王朝,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一种非尚力国家的序列,因此,中国人眼中的罗马帝国就如同一种彼岸世界,人们永远也看不清其本真的面目,也无法阐释其存在的合理性,更无以接纳并发扬其中的尚武精神、狂欢思想以及肉欲主义的理想。
罗马帝国的兴亡也和帝国的民众过度参与娱乐活动有关。“各种娱乐活动的蓬勃发展是在共和末期,尤其是王政统治时期,娱乐活动成为古罗马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17]罗马人作为强大帝国的国民,其最大的爱好便是在节日中找到简单而纯净的快乐,即一种为荷尔蒙主义主导的感官快乐。罗马人的这一爱好的确和商纣王崇尚的酒池肉林之类的生活方式略有相似处,它再度推演出一种享乐的合理性和堕落性的两重意向。当然,人们还是看到了罗马帝国的败政和民众过度娱乐之间的因果关系。“古罗马政权从民众迷恋娱乐活动中直接得到启示,把民众沉迷娱乐活动视为不文明的表现。”[17]然而,罗马人理性的享乐主义和中国商代东方式的非理性的暴虐主义有所不同,罗马人的节日往往具有全民性的狂欢元素。罗马帝国的娱乐更具有人类本真意志的真实性。“在罗马王政暗无天日的统治时期,任何政治决策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著名的座右铭:‘要面包也要娱乐。’”[17]和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帝国一样,罗马帝国的节日也和民众的休憩需求有关。“古罗马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有圣日和俗日之分。按古罗马日历上的标法,一年被分为吉日和凶日。吉日能给人们带来好运,办事会成功,而到了凶日,人们的活动减少,避凶远祸。此外,还有专门的神日,这些日子也被列为凶日,一切活动都必须停止。这样一来,节日天数有增无减。共和时期,有固定日期的节日约120天,像农业节这样无固定日期的节日就占了四十几天。一个节日持续几天,这在当时很常见。在节日期间,人们可以参加许许多多的娱乐活动。”[17]质言之,罗马帝国的节日娱乐活动是一种全民性、日常性和普泛性的节庆活动。“王政统治时期:节日天数又有所增加。4世纪初,节庆日超过了175天。日历是节日表,也是工作和娱乐的时间表。节日与节日之间具有周期性,一个节日过后,又有一个节日来临,形成一个像工作般严肃而重要的习惯性节日。”[17]罗马帝国每年的运动会只有8天,其后又增加到16天。相比较而言,罗马帝国的节日的种类更为丰富,其宗教性节日更多,随季节而呈均态分布。“3月15日是岁序女神安娜·珀壬娜节,每到这时候,人们都兴高采烈做着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6月13日是封斋节前礼拜日,古罗马有庆祝活动。13日、14日、15日3天,人们带上面具,装扮成妇女,吹着笛子跑遍全城。”[18]罗马帝国的宗教节日和世俗节日很早就有分别,但宗教节日的地位要高于世俗节日。“有宗教节,世俗节就暂停举行,当世俗节举行期间,宗教节并不受影响,该庆祝人们照样庆祝。宗教节有利于人们重温文明世界建立之初的难忘时刻,缅怀文明世界的创立英雄的丰功伟绩。牧神节后不久,就是纪念罗慕路斯祭日的基利努斯神节。由此可见,大凡宗教节,其情况大同小异,基本都一样。”[18]罗马帝国还有其他有辅助性作用的节庆日,其中的农神节、女神节、圣像节都很有影响力。“农神节是农神的理想化形象,因而只能持续一天。俄普斯女神被看成众神之母瑞亚·库柏勒,因而也被人们同两天后举行的农神节混为一谈。人们认为俄普斯是农神萨图尔努斯的妻子,于是就将农神节延长了两天。俄普斯女神是掌管收获的女农神,人们在庆祝农神节的同时,还要庆祝圣像节。圣像节因人们供奉农神的金、银、泥圣像而得名。所谓的圣像,实际上是商贩在战神广场上兜售的农神圣像的仿制品。”[18]罗马帝国最具有狂欢意义的则是每年12月26日至29日举行的小丑节。“古罗马的小丑节是所有节日中最精彩的节日,小丑节的前身其实就是古罗马的‘自由12月节’。小丑节的庆祝日分别是12月26日、27日、28日,通常在教堂进行。其间,人不分地位高低,一律平等。弥撒一开始,神父被唱诗童赶下主祭席,另选一个临时神父,被选中的一般是小丑的头儿。礼仪常常就被小丑搞乱了,弥撒变成了闹剧,有人咒骂,有人甚至把毛驴赶进教堂,给毛驴戴上主教的教冠。”[18]在小丑节期间,罗马人的贵贱等级秩序临时性消失。小丑节最大的特点是颠覆,它催生出一种贫贱者最高贵、高贵者最贫贱的娱乐效果。神甫在通常情况下会当选为小丑,庄严的弥撒立即成为一场闹剧。“小丑节的意义比较单一,纯粹属于平民的一种发泄式狂欢。教会视小丑节是娱乐活动,是一年的安全阀,是人们发泄心中不满的机会,是人们嘲弄神圣而非嘲弄新时代新道德的坚定信念。”[18]罗马帝国的节日与庆典文明对后世欧洲和世界其他受到欧洲文化浸润的国度都有深远的影响。农神节是日后新年的原型。原先的室外化、大型化庆典逐渐演变为室内化、小型化的宴会及化妆舞会。原汁原味的罗马帝国的小丑节已不复存在,但也并未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它已然演化成当今风行欧美的狂欢游行活动,并成为欧美国家狂欢节的原型。
中国从未有过狂欢化的节日。在讲求面子、喜欢热闹、好大喜功方面,中国和罗马帝国有相似之处,但在狂欢无度、感官至上、彻底纵欲的理念方面,中国人和罗马人差异巨大。中国一直属于一种行为有所节制的东方国家。然而,在特殊年代集体意志的鼓惑下,中国人无法抵挡大型化仪式的真实诱惑。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人在大国情怀与意志、体面与排场需求的刺激下,无法释怀节庆时光的巨大传播效应,中国人一定要在独特的时空中追寻到一种令人心仪的空间和时间,并借以构建一种大型化的仪式,且在这样的空间中展示出自己的生活方式。现代学者好以“好大喜功”4个字来形容中国的汉唐伟业、乾嘉盛世,其实,这也是对人类伟大帝国共性的一种简单性的描述。世界上任何一种节日都有传承性。在节庆至上、仪式先行理念的统摄下,现代中国同样需要更为宏大的国家仪式,借以消解掉中国人百年来的屈辱史。现代体育学者对北京奥运会的评价就带有仪式至上主义的意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到今天,很好地完成了民族和历史赋予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体育自身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以‘无与伦比’谢幕,这在一定意义上把中国的体育推到了时代发展的前沿,因此,中国的体育没有回头路,只能前进。这次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看到了成为体育强国的可能,因此建设体育强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之举。”[19]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体育赛事密集举办的现象,并不存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其他各地方部门沟通不畅的问题,中国各大城市出现的体育赛事密举办现象有其积极的文化动因。依照儒家文化的理念,任何的大型庆典性活动都属于喜庆之事,而在儒家文化圈内的任何喜事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更具有不折不扣的文化统治力。中国人在过大年的时候仍然保留不让人随便说不吉利话的传统,体现出中华文化中固有的禁忌原则。在此意义上审视,各种对中国举办大量体育赛事的言论都有不吉利之意味。中国的确是一个经历过百年屈辱的民族,在一种除旧布新的喜庆时节,不应当有更多的非难性语汇的存在。
顾拜旦曾经认可过奥运会的节庆价值:“休战的思想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又一基本特点。休战与节奏密切相关。奥运会的庆祝活动必须准确地按照天体运行的节奏举行。因为奥运会是庆祝4年一度的人类春潮佳节的组成部分,纪念人类一代又一代不断的繁衍,所以必须严格地按照这种节奏进行。今天,像古时候一样,意外的情况可能会阻止我们召开4年一度的奥运会。但是,各届奥运会的顺序都决不会改变。”[4]中国也一样,2008年之后掀起的举办体育赛事的浪潮之所以引起人们争议,完全在于民众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态度不同所致。这些赛事看似劳神费力、劳民伤财,却已经是中国国家仪式或民族仪式的组成部分,寄寓着一种经历了百余年内外战争后民众释放情怀的需求,它显然还是一种由诸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欠账作用催生出来的文化现象。人人皆知战争创伤的严重性,却很少有人认为作为体育的仪式或作为仪式的体育可以有效地治疗战争创伤。中国在百余年的时间内并未做过几次带有巨大而彻底的欢乐寓意的国家性庆典,如今的中国在具备了足够的财力、物力的前提下,移植、引进或补办一些国家仪式不仅毫无过错,还适逢其时。在此意味上考量,那些对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持否定态度的人一定也是对中国百年的屈辱史缺乏清晰记忆的人士,更是一群对仪式功能缺乏理解的人,还是一些对仪式的治疗价值不太了解的人。
其实,反对中国高密度地举办体育赛事的人同样隐含有一种否定中国的举国体制的意向。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已在中国延续数十年,在数十年内一直发挥着一种十足的正能量,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了负面典型、非议目标,且大有变成全民公敌之势?原因在于举国体制是一种治疗仪式的主体单位,而当代国人对仪式的治疗作用一向意识模糊。“在一些文化中人们从超自然的层面理解健康和不适,认为疾病是由超自然的神、祖先的灵魂、鬼或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巫师或巫婆所引起,所以人们通常采用宗教或巫术仪式来治疗不适与疾病。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人与天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和谐,医疗的方式是通过仪式恢复人与宇宙的秩序与和谐。在人类处理与自己及自然的关系时存在一个人力所不能及的领域,仪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工具或手段。”[20]仪式治疗的作用一向具有及时性、当下性和瞬间性效应。经过多次仪式性治疗,现代中国人的东亚病夫自卑症已然接近痊愈,而用于治疗的主导性器具即为各类大型体育赛事,其中以北京奥运会最具代表性。“通过延续与继承计划经济时期所建立的体育管理体制,依靠国家意志的强力主导,在强大资源的有效保障下,‘赶超型’或称非均衡的奥运战略在局部范围获得了巨大成功。其结果是北京奥运以几乎完美的姿态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崭新形象。成绩是巨大的,问题也不容忽视。”[21]由此可见,中国人真正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节点很可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如果找不到更为适合的时间节点,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成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唯一的符号。意识形态意志再度压倒非意识形态意志的现象在中国仍然具有正确性。中国依然是世界级的大国,而大国之威无法摆脱典型而盛大的仪式而别有存在之可能性。
4 结语
在现有社会体制统摄下,中国的大型赛事都和国家的各级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存的大国体育和强国体育策略都是中国的国家仪式构建的思想与政策基石。质言之,中国体育的现行政策是中国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过程的产物,举国体制是一种针对全民的高效、强力、极端性的心理治疗手段。恰是在这种高压式、仿制性精神治疗的作用下,中国人的竞技能力自卑症、技能力匮乏症逐渐得到了治疗,东亚病夫污名也得到了彻底的洗涤,而治疗之手段则是包括北京奥运会在内的一系列大型化的体育赛事。换言之,中国举办或申办的大型体育赛事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还是一种大型仪式,而大量输入的仪式治疗程序使得中国人获得了更为稳定、恬然与平稳的心境。在此层面上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大型体育赛事的仪式治疗价值。中国人理应对那种加量化的仪式治疗程序报有一种感恩与理解之情,也不应遗忘作为中国式仪式治疗的主体机构。在合理利用体育赛事作为治疗仪式的层面上考量,我们国家的各级行政部门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2,421.
[2]Van Gennep.The rites of passage[M].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1965:3,3.
[3][英]马丁·艾斯林.戏剧剖析[M].罗婉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9.
[4][法]顾拜旦,詹汝琮,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M].邢奇志等,译.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2-3,158,64,120,152.
[5]王磊.中国还不是体育强国[J].中关村,2008(61):31-32.
[6]连清川.不合时宜的阅读者[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92,92.
[7]王镜宇,汪涌,岳东兴.从体育大国冲向体育强国[J].新闻天地, 2009(10):12.
[8][美]Karla D.Carmichael.游戏治疗入门[M].王瑾,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
[9]陈平原.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J].探索与争鸣,2014(9):13.
[10][俄]巴赫金,白春仁.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78-179,175.
[11]颜下里.从竞技体育强国走向注重大众体育的俄罗斯[J].体育文化导刊,2012(10):14.
[12][俄]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90:13.
[13]胡志毅.国家的仪式:中国革命戏剧的文化透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7.
[14][美]弗拉亥.文学的若干原型[M]//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44.
[15][英]里维斯(F.R.Leavis).莎士比亚与宗教仪式[M]//郑士生主编.莎士比亚全集(下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876.
[16]熊斗寅.世界体育强国浅析[J].四川体育科学学报,1985(4):4.
[17][法]让-诺埃尔·罗伯特.古罗马人的欢娱[M].王长明,田禾,李变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4,54,54,54,54-55.
[18][英]纳撒尼尔·哈里斯.古罗马生活[M].卢佩媛,赵国柱,冯秀云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7:154,154,155,157,157.
[19]张晓义.新时期建设体育强国的认识基础[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5):12.
[20]王敬群,张志涛,井凯,马骥.仪式与心理治疗[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1):119.
[21]黄玉珍.关于体育强国若干问题的思考[J].体育科技,2010(3): 2.
(责任编辑:陈建萍)
Ritual Therapeutic Function of Sports: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High Density Sport Events in China
LU Yunt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The Center for Sports,Media and Culture,Shanghai200438,China)
Modern major sport event belongs to alien culture,which is a super-sport cultural form compatible with modern society.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ideal image of the nation and the city,major sport event in China has been evolved to a national ritual.Its spiritual value might be higher than that of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fitness of the people.The high density sport events held in China are also a supplement to the insufficient galas and festivals in China.To the people,the events have a"super body"ritual therapeutic function.
major sport event;national ritual;Chinese element;festival;value
G80-05
A
1006-1207(2016)06-0017-07
2016-09-25
路云亭,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体育传播。E-mail:luyunting666@sina.com。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200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