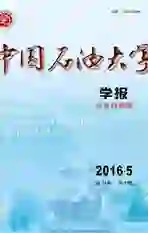北魏中期贪污之风盛行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
2016-11-26袁宝龙
摘要:北魏中期,贵族官吏群体中贪污之风盛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北魏从游牧部落向国家形态进化的过程中,许多旧有的历史传统被保留下来,对于公私财产观的概念模糊,成为北魏中期官员贪污普遍化的历史因素,并与俸禄制度和礼法工具的缺失共同构成贪风盛行的内在原因。而贵族官员阶层严重的贪污现象,在客观上坚定了北魏孝文帝实施变法的决心,促进了北魏的法制化进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北魏政权的崩溃灭亡。
关键词:北魏;贪污;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K23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5005205
北魏中期,贵族官员群体中贪污之风盛行一时:太武帝时期,公孙轨在上党,“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载物而南”[1]784。明元帝时期,“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1]713。实际上,贪污现象普遍而广泛地存在于北魏中期贵族阶层的群体内部。史称北魏“爵而无禄,故吏多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残贱。不贵礼义,故士无风节。货赂大行,故俗尚倾夺”[1]3063。总体来说,北魏中期王公贵族与地方官吏之中均多贪官,且其贪污取财的手段趋于多样化。[2]有关北魏贪风大盛的原因及其影响,值得人们思考。
一、北魏中期贪污之风大行的历史原因
(一)历史传统所致
首先,北魏长期保留了游牧时期的原始财产观,这是贪污盛行的重要原因。关于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唐长孺先生认为,拓跋部落的国家形成起源于猗卢时期,完成于太武帝时期。[3]值得注意的是,王公官吏贪污之风的盛行以及最高统治者致力于治贪的尝试也基本从此时开始见诸史籍。
两者间的因果逻辑如下:在拓跋部落完成封建国家的构建之际,必然会保留许多源自游牧部落时期的旧有习俗,其中也包括对于财产公私属性的认知判别标准。而根据游牧部落的历史传统,公私财产并无明确的定义差别。什翼犍时期,“时国中少缯帛,代人许谦盗绢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谓燕凤曰:‘吾不忍视谦之面,卿勿泄言,谦或惭而自杀,为财辱士,非也”[1]16。这段记载,固然表现了什翼犍宽厚的人君气度,同时也反映时人对公私财产的产权归属并无明确的概念。这种观念在北魏国家完成封建化进程后仍有所保留。道武帝时期,代人庾和辰“事难之间,收敛畜产,富拟国君。刘显谋逆,太祖外幸,和辰奉献明太后归太祖,又得其资用。以和辰为内侍长。和辰分别公私旧畜,颇不会旨,太祖由是恨之”[1]684。从现代视角来看,“分别公私旧畜”本是人之常情,道武帝却引以为恨事,可见时人对于财产公私属性的认知之模糊,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官吏贪污的可能性。至太武帝时,刘洁“既居势要,擅作威福……拔城破国者,聚敛财货,与洁分之。籍其家产,财盈巨万。世祖追忿,言则切齿”[1]689。最高统治者已经留意到臣下贪污恶行之严重,不过此时已经成为难以根除的顽疾。
其次,北朝政权统治者以政策的宽松来保持军将的斗志,这是贪污风气盛行与历史传统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内在联系。拓跋鲜卑以文化弱势者的身份完成了对中原文明区域的征服,最大的资本无疑是鲜卑民族世代传承的骁勇之风。因此,在文化差距几无可能于短期内消弭的情况下,胡族统治者必然要不惜代价保证武力的强势地位。由此原因,鲜卑军将的贪污秽举几乎具备了半合法甚至合法身份。北齐时期,名臣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天下浊乱,习俗已久……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高欢纵容贪污之风,就是为了实现对属下军将的拉拢收买。杜弼称“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为内贼,请诛之,高欢不为作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矟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栗汗流。高祖然后喻之曰:‘……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4]347348。这基本上代表了北朝统治者对属下贪污的普遍看法。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激励武人为国征战的斗志而有意放松了臣纲监管,使贪污行为趋于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使贪污之风进一步恶化。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10月第32卷第5期袁宝龙:北魏中期贪污之风盛行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二)俸禄制度的缺失
北魏平城时代的发展过程异常错综复杂,但是北魏皇权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却作为一条永恒不变的主线贯穿其中。[5]平城时代是北魏政权从游牧民族到国家形态嬗变的重要时期,不过这种转变并非自然的文化演进,而是拓跋鲜卑在整体南迁后,与中原先进文化经过深度接触后的被动转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形态,在经济结构以及制度建构上都会有所缺失,进而在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衍生出种种难以克服的顽疾。回归到本文的主题,北魏直到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始“置官班禄,行之尚矣”[1]153。也就是说,北魏至此始正式确立了官员班禄之制,此前官员薪俸机制并未制度化,而制度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并加剧了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
百官班禄之前,北魏并未在官员的经济收入方面形成一套有章可循的规章制度,这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构成有一定关系。东汉之时,“(匈奴)南北单于相攻,匈奴损耗,而鲜卑遂盛”[6]。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日渐强盛,“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狩猎为业”[1]1,其经济模式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经济体制。此后,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其经济结构始渐由狩猎模式向农耕经济转变。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1]20。这是北魏农耕时代的起点,进入平城时代后,农业经济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直到北魏基本完成封建化进程后,游牧时期形成的通过掠夺来积累财富的古老传统依然被保留,缴获的战利品成为国家的公共财产,统治者时常以之班赏群下。如登国六年,“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1]2849。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北魏远征杨难当,诸将商议,“以大众远出,不有所掠,则无以充军实,赏将士”[1]413。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赏赐亦是当时贵族官员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直到孝文帝“置官班禄”之前,贵族及官员阶层的合法收入主要依靠朝廷的赏赐。由于身份尊卑以及官位高低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个体所获赏赐的差异较大,获赏较少且洁身自好者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文成帝时名臣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家中“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魏书》称:“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1]1076而此种情况,绝非孤例。时人崔宽,以“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1]625,这便是俸禄制度缺失的时代背景下,官吏群体的不同生存状态。推行俸禄制之后,情况大为改观:“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于是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兆庶无侵削之烦,百辟备礼容之美……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1]11981199其中或有夸张之处,但是官员薪俸机制的规范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官吏贪污的普遍化。也就是说,官员薪俸制度的规范与否与贪污风气的盛衰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三)法制及礼制建设的缺失
早期北魏的法制思想表现出浓重的部落时代特征:“后魏初,置四部大人,坐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刑名之制。”[7]182原始法制意识和思想在猗卢时期有所发展:“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威严伏物,皆此类也。”[1]9不过,法制建设仍极其粗犷,并未形成固定的法律条文和系统的法制思想体系。随着北魏封建化进程的深化,北魏的法制思想渐臻成熟。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令王德修订律令,“(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1]2873。至太武帝时,“始命崔浩定刑名,于汉、魏以来律,除髡钳五岁四岁刑,增二岁刑,大辟有、腰斩、殊死、弃市四等,凡三百九十条,门房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条,五刑二百三十一条。始置枷拘罪人。文成时,又增律条章。至孝文时,定律凡八百三十三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7]182。可以说,经过多次修订,北魏的法制体系不断完善。不过,此时北魏法律的主要使命仍是巩固统治。从史籍记载中可知,北魏法律的修订往往与农民起义等政治事件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北魏法制思想的完善以现实需求为首要的发展动力,相比之下,对于官员贪污抑制的现实需求远不及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强烈。
此外,礼制建设的缺失亦加剧了贪污现象的恶化。可以说,法律工具的失效,使制止贪污的客观工具失去效力;礼制建设的缺失,则使王公贵族的主观防线形同虚设。《礼记·礼运》载:“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又称:“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表明了礼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秦汉时期,人们对礼的社会功能认知尚属初级阶段,认为其教化功能要远远深刻于对国家治理的功能;直到魏晋时期,礼在国家层面的积极作用始被凸显,而五礼作为国家制度也是萌生于魏晋之间。[8]魏晋之际,中原长期战乱,如前燕、后赵、前秦等民族政权虽然有过礼制建设的萌芽,但随即因政权短祚而告消散。
北魏礼制发展程度与国家形态的进化阶段相比,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无法对贵族阶层形成一种强大的感召力。简言之,北魏前期的法制思想及制度过于粗放简陋,礼制建设的迟滞又使礼法结合的设想无从实现,北魏的贵族官员群体因此失去了精神理念层面上的引导与束缚,也就无从谈起对品性与操守的重视。这一点在孝文帝之前已经引起了当时士人阶层的注意。天兴三年(400年),道武帝下诏:“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义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1]3738文成帝和平六年(465年),刁雍曾上表称:“臣闻有国有家者,莫不礼乐为先……是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易俗移风,莫善于乐……臣闻乐由礼,所以象德。礼由乐,所以防淫。”[1]869870明确提到了礼有“易俗移风”以及“防淫”之效,不过北魏礼制建设直至太和年间才真正开始,法礼之间的有机结合亦始于此时。与此相应的,是贪污风气在孝文帝执政时期的大为收敛。
二、北魏贪污之风盛行造成的影响
(一)贪污之风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孝文帝改革的决心
自道武帝开始,北魏历代诸君均表示过对贪污之举的强烈谴责,并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览察黜陟之”[1]33。三年,复命“分命诸官循行州郡,观民风俗,察举不法”[1]36。太武帝于始光四年(427年)亲自巡行中山,“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1]73。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年)诏曰:“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营家业,王赋不充,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自今诸迁代者,仰列在职殿最,案制治罪。克举者加之爵宠,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贯,刑赏不差。主者明为条制,以为常楷。”[1]117118凡此种种,皆表明了历代魏帝治理贪污的意愿与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集中整顿吏治的前后,多有大规模的赏赐行为发生,这可以理解为国君恩威并施、以赏养廉之意。可是这种赏赐的随机性很强,覆盖的范围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群体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也就无法有效地制止贪污行为。直到孝文帝时期,官俸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官吏群体的经济状态始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官俸改革作为孝文帝大规模改革的先声,也引领了此后的改革风潮。
太和八年,班百官俸禄制,国库的支出因此骤增,北魏国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①如何增加国库收入以保证俸禄制度的正常运转,成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孝文帝于班禄次年颁行“均田制”,他在诏书中说道:“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畜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1]156均田制的重大意义,自不须赘述,从孝文帝此诏可知,使国家财政逐渐脱离窘境当为实行此制最重要亦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北魏政府通过均田制,使闲置人口与荒废的土地结合起来,从而构成国库重要稳定的经济来源,进一步改进完善了国家的经济结构。
均田制实行之后,“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廓者,不可校数”[9]。我们自不能断言,寻求支持俸禄制的经济来源是孝文帝实行均田制的主要原因,但无庸置疑,使国家财政问题得到缓解,通过止贪养廉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皆是实行均田制的有利因素。而国家富足,又使孝文帝的进一步改革具备了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
综而言之,为了使俸禄制成为北魏国家的长效机制,从而使反贪计划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持,孝文帝必然要努力拓宽国家的财政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贪污之风的盛行在某种意义上坚定了孝文帝改革的决心。
(二)贪污之风盛行,加快了北朝的法制礼制化进程,并促进了考课制度的衍生
前文已述,北魏初期的法制建设太过粗放,并未形成一套完备严谨的法律体系。至什翼犍时,始对死刑及赎偿之法做出粗略的区分,号称:“法令明白,百姓晏然。”[1]2873法律条文真正的完备是在道武帝以后,自天兴元年(398年)王德修订律令开始,太武帝、文成帝诸朝均对法律有过不同程度的增删调整。随着北魏统治者消除贪污风气的意愿越发强烈,法律的力量也愈为统治者所倚重,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的法制化进程。
孝文帝锐意整顿吏治,曾多次修订律令。如:太和元年九月,“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1]144;太和三年,“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1]2877,这一次修订历时两年,始告完成;太和十五年复“议改律令”[1]168,并于次年颁行新律。
针对贪污之风,孝文帝从监察和考课两个方面进行理念革新与制度构建。监察方面,孝文帝完善了御史台的监察职能。《御史令》明确规定:“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内。”[1]353而且重用李彪等耿直之臣,致使“天下改目,贪暴敛手”[1]1392。
此外,孝文帝改进了考课制度。延兴二年(472年)孝文帝下诏称:“《书》云:‘三载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顷者以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1]138可见此制实行的主要目的即是为禁绝“竞为聚敛”之事。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又把考课周期由“三载一考,三考黜陟幽明”改为三年一考绩,根据考绩结果即行劝赏黜陟。[1]175北魏的考课制度,与官员的实际经济利益密切结合,因触动官员的经济利益而促使其尽忠职守,这也与孝文帝的反贪思想相一致。[10]此外,孝文帝通过对礼教工具的引介,努力营造礼法结合的文化氛围,进而实现贵族官吏的自我约束。
太和七年,孝文帝下诏禁止同姓联姻,称“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1]153,表现出对礼教的重视。十一年,孝文帝诏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1]2878安定王元休去世,其侄元嵩“未及卒哭”而出行,孝文帝闻而震怒,诏称:“嵩不能克己复礼,企心典宪……有如父之痛,无犹子之情,捐心弃礼,何其太速。便可免官。”[1]486对元嵩的处理是典型的法礼结合的案例,这也可以映衬出北魏当时礼法结合下的社会环境。
监察制度与考课制度的完备,法礼结合文化氛围的形成,成为北魏政权国家形态不断完善的例证,贪污之风与其他因素共同构成了礼法工具诞生的动力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魏社会的法制化进程。
(三)贪污加速了北魏亡国
孝文帝之死成为北魏政权盛衰急转的标志性事件,朝中的贪污之风也随之卷土重来。孝文帝去世后,宗族元禧受遗诏辅佐新君,他“虽为宰辅之首,而从容推委,无所是非,而潜受贿赂……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绣绮,车乘鲜丽,尤远有简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货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1]537,其弟元祥“位望兼极,百僚惮之。而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1]561。贪污与奢侈之风并行,成为后孝文帝时代的北魏统治阶层的新特点。
宗族皇室放纵于上,寻常官吏自然效仿于下,奢靡腐化之风使北魏国家从孝文帝汉化所缔造的盛世迅速转向衰败。也就是说,贪污风气的强势反弹直接导致了北魏国家的动荡局面,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分裂、灭亡。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孝文帝去世后仅35年,北魏即分裂为东西二魏:西魏在长安另立江山;东魏则固守洛阳,成为旧北魏政权的实际继承者。东、西两魏之间的对抗持续多年,后转变为北齐与北周之间的抗衡,占据先天优势的东魏、北齐集团由强而弱,最终为对手所灭。两国之间的实力消长自然由多方面原因构成,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与西魏、北周君臣励精图治不同,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几乎全面继承了北魏时期的贪污与奢侈之风,从而导致了政权的崩溃。
东魏的开拓者高欢,“初,神武自晋阳东出,改尔朱氏贪政,使人入村,不敢饮社酒。及平京洛,货贿渐行”[4]1987。北齐“自正光已后,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洁者寡”[4]32 。北魏至北齐贪污之风一脉传承,致使具有先天优势的北齐在与北周的对峙中渐居下风,至后主时,北齐“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4]113114。相比之下,北周则是另外一番气象:“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苏)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11]382六条诏书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11]391北周武帝宇文邕,“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后宫嫔御,不过十余人。劳谦接下,自强不息”[11]107。北周灭北齐之后,继任的隋朝完成统一南北的大业,终结了长达169年之久的南北朝乱世。如果追根溯源,北魏末年的贪污之风无疑在客观上加速了北魏、东魏、北齐政权的瓦解速度,加快了北方乃至全国统一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南北政权重归一统也是北魏贪污之风盛行产生的客观后果之一。
三、结论
北魏中后期贪污之风盛行,是当时政局的一大特点。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正处于国家封建进程中的北魏政权依然保留了部落时代的诸多旧习,这成为北魏贪污之风的历史渊源;除此之外,薪俸制度的缺失成为官吏群体疯狂敛财的客观因素;而礼制与法制之间未能形成一种有机张力,又使贪污者洁身自律的主观性束缚形同虚设。这种充斥于国家上下的贪污风气,也成为改变北朝政治格局的重要推动力。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以及汉化改革的思想中均可窥见其止贪养廉的主观意愿,礼制建设与法制化进程也成为统治者大力治贪的衍生品,只不过孝文帝首创和推行的一系列止贪之策在其去世后陆续失效,贪污之风也随即强势反弹,北魏政权在这种盛衰急转之下逐渐走向灭亡。北魏的分裂和灭亡,以及此后整个南北朝政局的变换走向,均与北魏中期以降的贪污之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内在联系,由此也可以看到北魏贪风盛行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刻悠远。
注释:
① 迁都洛阳后,由于军费开支大,曾经下诏减百官俸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百官俸禄在国家支出所占的比重较大,这次减禄直至魏孝明帝时才恢复。魏末孝庄帝以后,因国用不足,也曾经发生过“百官绝禄”事件。
参考文献:
[1]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策[J].探索与争鸣,1991(3):3744.
[3]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33.
[4]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6]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835.
[7] 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8] 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J].中国史研究,2001(4):2752.
[9]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60161.
[10] 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09.
[11] 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