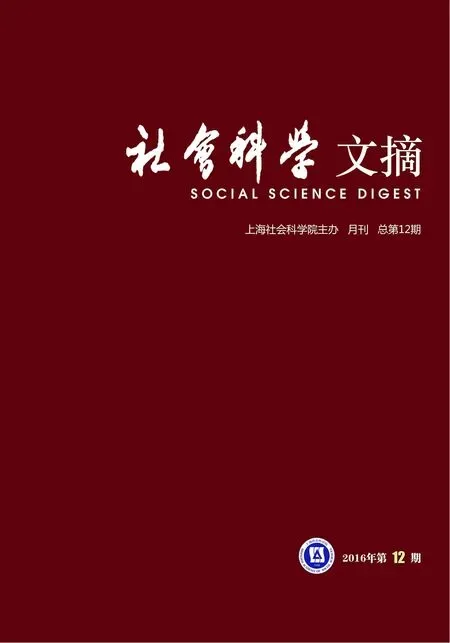时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2016-11-26张永清
文/张永清
时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文/张永清
本文关注和探究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所关涉的“内部”问题,而是其“外部”问题。原因在于,只有对“外部”问题进行彻底“清理”,才能对“内部”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剖析和论断,才能有效确定其理论指涉的边界与问题域。概言之,所谓的“外部”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第一,“何谓马克思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历史形态;第三,批评理论以往研究存在的整体性问题。下面我们就分别作扼要论述。
何谓马克思主义?
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一方面,一些理论流派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自己的“唯一性”,指责别的流派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形形色色乃至大相径庭的各种社会思潮都被“聚拢”在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下。究其实,各种主义之间始终在围绕着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坐标”“基石”等轴心问题展开讨论、争论,因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著作的不同解读,对这些著作在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实践及其效应的理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流派。基于此,我们拟从五个主要层面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第一个层面,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理论和学说,即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当西方学界作这样的限定和区分时,它内在地就隐含着两个核心理论问题:其一,如何看待马克思前后期的思想,或者如何看待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其二,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一个还是两个?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因而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以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的重新考察和审视。至此之后,这两个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持续关注和探讨的“显学”。
第二个层面,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即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总的说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探究上分工确有不同,理论贡献确有大小、主次之分,但“见解一致”,这一传统观点曾被广泛接受,从恩格斯本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列宁等都接受和秉持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间确有差异,但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主张采取一种类似于遮蔽、忽视甚至无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不一致的理论观点的做法,即一种“回避差异”“确保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思想之间确有本质性差异,不过,考虑到与恩格斯的多年友谊等因素,马克思“包容”甚至“容忍”了恩格斯的相关理论论述;第四种观点提出了更加“离经叛道”的新论断,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俩人其实是交替作为“第一小提琴手”出现的,真正说来,以往的相关研究不是“高估”而是“低估”了恩格斯的理论贡献。
第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梅林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主要是一种社会理论、经济理论但不是一种哲学。作为首席理论家的考茨基的相关论述就很有代表性:“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学说,而是一种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国际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尽相同。比如,拉法格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与此相反,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哲学特点的说明。
第四个层面,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又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彻底破产,俄国十月革命则标志着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它以革命的、实践的方式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之争。当然,“这一反《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语)也给西方社会关于马克思主义未来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众所周知,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的推广及运用。
第五个层面,马克思主义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而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时限、涵盖范围等问题要比上述四个层面的相关问题还要复杂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边界”等问题上,我们比较认同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狭之分与界定。原因在于,当我们审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形态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承担的主要是“描述性”而非“规范性”功能。当然,纯粹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任何描述都是以某种规范即理论立场为前提的。因此,作为描述性概念,它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多样化的思潮存在,同时又要揭示不同思潮体现出来的某种总体性。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其理论的总体性特征尤为突出: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将其放在理论探究的首要位置;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理论;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文化批判,注重对异化、物化与人的自由和解放关系的探讨;主张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为历史辩证法;注重对意识形态、实践等问题的深入研究等。
总的说来,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五个层面”就是我们“主动面对”的理论尝试。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每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只具“之一性”不具“唯一性”。反过来讲,如果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而非别的各种主义,那么除了各自的“之一性”外,它们还有无“同一性”或“最大公约数”?如果有,它们又由哪些“质的规定性”构成?总体看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公约数”或“质的规定性”。因此,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接受还是拒绝,肯定还是否定,继承还是发展,改良还是革命,围绕“最大公约数”展开的相关争论、研究及实践等就形成了形态各异、层面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历史形态
我们以“五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依据和参照系,将马克思主义批评划分为五个主要形态。
第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前史形态”,主要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8月28日之前的文学活动和批评实践。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文学青年”,首先从事的是文学及其相关活动,之后才转向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活动。此外,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哲学等其他领域,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犹如天空中的两颗行星,各自运行在自己的星际轨道上,两者之间并未“交汇”更谈不上“并轨”。还需要明确的是,尽管他们“前史时期”的批评理论与实践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又与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批评理论和实践有着不可分割、难以分割的复杂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初始形态”。与第一种“前史形态”比,“初始形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相关批评思想与实践的概括。换言之,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而言,如果“前史形态”的批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初始形态”的批评则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之所以不采用以往的理论表述:即将他们俩人的批评理论统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而使用“初始形态”这样的称谓,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从时限看,指的是1844年9月至1895年8月,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巴黎相见”到恩格斯去世这一历史时期;其二,以“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俩人“巴黎相见”之前与之后的文学活动及其批评思想;其三,在“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理论前提下,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文本、批评文体、批评观念等作具体剖析,重点关注两人之间的差异性、独特性;其四,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批评思想和批评实践看,尚不具备批评的整体性、系统性等理论特质;其五,在理论表述上,自觉地将其与后来被阐释者“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区别开来,这样做有助于厘清两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复杂关联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科学形态”,主要指的是以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卢森堡等为主要代表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种关于社会和经济的革命理论,因此十分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科学性”。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其整个理论工作中处于比较从属地位,相关批评也比较零散,尚不属于自觉的、系统化的理论构建,还处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探索阶段。此外,它的“科学性”还伴随着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的鲜明色彩。
第四,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政治形态”,主要指的是列宁主义的批评理论。列宁主义批评主要是一种介入性的政治批评或革命批评。客观而言,在某些历史时期,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者是“同一性”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也对批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列宁主义批评,列宁主义批评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我们看来,列宁主义批评是其时代和社会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第一次系统化、整体化的理论自觉、理论建构,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政治维度的丰富、发展和深化,它在充分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特别强调批评的社会性、党性、人民性、阶级性的有机统一。
第五,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化形态”,主要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的“哲学、文化转向”表明,文化已然居于其“总体性”理论的核心地位,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等构成其批评语汇中的“热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化批判观,其批判的范围涵盖从物化、异化到日常生活,从意识形态到审美意识形态,从技术理性到文化工业,从资本主义到集权社会等方方面面。概言之,对文学、艺术、审美等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批判性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卓越的理论贡献。
此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理应产生一个极其重要的第六批评形态,即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国形态。批评实践表明,一种相对成熟的批评形态的出现,都要经过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坦率讲,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第六批评形态目前尚未成形,还处在不断探索与持续发展的状态之中。
切实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
根据我们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研读与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上述五个主要形态中,对第一形态的研究最为薄弱,对第三形态的研究比较薄弱;相对而言,对第二、第四尤其是第五形态的研究要更充分些。换言之,研究存在着“冷热不均”现象。无可否认,研究的这种“冷热”变化与时代状况、社会现实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也与个人的研究旨趣密切相连。不过,当相关理论研究呈现出某些整体性缺失时,就需要认真对待,深入思考其中的症结所在。此外,从此前的粗略划分可以看出,后三种“形态”与后三个“层面”之间都基本吻合;然而,第一、第二“形态”与第一、第二“层面”之间却存在着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理论的认识,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总之,无论从思想史、批评史还是从理论创新、理论建构等任何一方面考虑,都需要切实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亟须加强对第一形态的研究。任何思想、观念的产生、发展都有自身的演变过程,过程本身的呈现其实就是问题的答案所在。因此,不能将第一形态与第二形态的思想关系人为割裂。无可否认,国内外学界对此也有所研究,但还不够充分、还不够深入。比如,对第一形态研究的薄弱就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三分法”和“四分法”中,马尔赫恩和伊格尔顿都没有把“前史形态”纳入其批评理论视野和批评范式中。这表明,在批评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对1844年8月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遮蔽”,“腰斩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个人思想发展的链条。由于未能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批评理论的“基点”或“起始点”,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前史形态”与“初始形态的”的关系,就不能完整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观念及其对后来批评形态的影响等。
第二,切实加强对第二形态的再研究。由于传统认识始终把第二形态视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核心”,并以此作为创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点”,因此对第二形态的相关研究确实十分具体、十分充分、十分深入。但是,我们认为,它依然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其一,只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之间的联系、共性,不关注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其二,只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理论与此后尤其是列宁主义之间的“同一性”,不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尤其存在着以后者“包容”甚至“取代”前者的研究倾向。比如,卢卡奇的相关批评就很有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对第二形态即“初始形态”的再研究必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上述两者之间的双重差异,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构建。
第三,在充分吸纳各种形态批评思想的基础上,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国形态”。我们以往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只满足于对前述几种形态及其问题的描述性研究,甚至把这些问题“知识化”,缺乏强烈的问题意识,即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最终落入为批评而批评的话语窠臼,批评理论的自觉和创新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思想的火花是在不断地碰撞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观念是在现实生活的沃土中孕育而成的。只有以我为主,立足当代现实,直面理论问题,才能对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作合理选择和有效吸纳,才能构建体现时代精神、满足现实需求的批评理论,这样的批评理论才会充满生命活力,才会具有真正的“中国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摘自《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