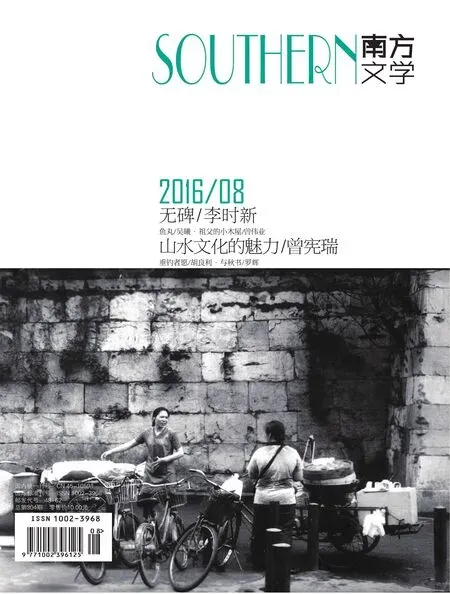墨酣漓水韵 气畅桂山奇
——戴延兴《水墨·五色气韵》漓江烟雨水墨画赏析
2016-11-26text黄继树
text_黄继树
墨酣漓水韵 气畅桂山奇
——戴延兴《水墨·五色气韵》漓江烟雨水墨画赏析
text_黄继树
桂林山水的精华,在桂林城至阳朔县城这百里漓江黄金水道上。而百里漓江的精华,又在漓江烟雨之中。
古代诗人抒写桂林山水的诗词,数以千计,更有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黄庭坚、范成大等名家之作。唐宋时丹青高手山水大师辈出,但今人何曾见过这些名画家描绘桂林山水的大作呢?难道是桂林山水在当时知名度不高,使这些名画家不屑一顾?当然不是,桂林虽偏处岭南,但唐宋时,随着文人墨客的诗文传唱,桂林山水早已名满中原,像杜甫、韩愈、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虽然终其一生未到过桂林,但他们写桂林山水的诗歌却影响深远,流传千古。难道是桂林地域遥远,交通不便,难以涉足?也不是。自从秦时开凿灵渠,湘漓沟通,从中原到桂林水路便捷,更无蜀道之忧。更令人十分困惑的是,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曾于熙宁七年(1074)到桂林任临桂县尉,他在桂林任职期间与桂林西山庆林寺的绍合和尚交好,两人常常流连于山水之间,米芾是著名的山水画家,他与儿子米友仁独创了一种以雨点形的浓淡墨交替渲染的画法,来表现江南烟雨中的景色,被称为“米点”,又称为“米氏云山”。但米芾除了在桂林伏波山还珠洞留下一幅书法和他的一幅自画像作品外,后人何曾见过米大师画的漓江烟雨作品?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古代的画家缺席桂林山水这个绝美的题材领域?直到最近看了戴延兴先生创作的《水墨·五色气韵》漓江烟雨水墨画系列作品,才恍然大悟。画桂林山水难,画漓江烟雨更难!这是不是古代画家们知难而退的一个原因呢?我们从古代诗人描写桂林山水的诗歌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间接的答案。
宋代著名的诗人、书法大家黄庭坚到桂林时,创作了一首《到桂州》的诗:“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李成,宋初著名画家,是当时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郭熙,宋代著名画家,熙宁年间(1068—1077)为御书院艺学(皇家书画院专职画家),师承李成,工山水寒林,善作巨幅壁画。黄庭坚被贬广西宜州,到桂时,见桂林山水奇绝,可惜宋代最有名的两位山水画家李成、郭熙都已经去世了,感叹再也没人能“奈何”得了桂林山水啦!
黄庭坚在诗中似乎还有未言明的一层意思:即使李成还在,郭熙未死,也对桂林山水无可奈何啊!明代诗人鲁铎到桂林,他深感桂林“夹岸青山映碧滩,滩清山好画应难”。鲁铎还有一首写阳朔白沙滩的诗,题为《白沙滩壁嶂奇绝,殆不可画次九龙韵》。“九龙”,不知何人,推想可能也是一位诗人、画家。“丹崖翠嶂映清流,天趣无穷到客舟。他日画图逢马夏,也应无足注双眸。”鲁铎在诗中叹道,面对阳朔白沙滩这般山水风光形成的天趣,便是此后见到南宋最擅长画山水的马远和夏珪这两位大画家的作品,也不愿再看了。
清代诗人顾嗣立有一首写漓江《画山》的诗:“画里看山山更闲,画山好手说荆关。淋漓如画真山在,又倩何人画画山。”面对淋漓酣畅泼墨如画的“画山”,诗人首先想起了画山的好手荆浩和关仝。荆浩,五代河内(今河南泌阳市)人,字浩然,隐于太行山之洪谷,因号洪谷子,善画,其山水之作可称唐、宋之冠;关仝,五代长安(今西安)人,画山水,初学荆浩,后有“青于蓝”之誉。诗人觉得“荆关”这样的大师画的仅仅是山水画,但是这如画的真山摆在这里,又是谁能画得下来的呢?
清代诗人阮元有一首《观漓江奇峰图卷》诗,其中两句:“荆关董巨多名笔,如此奇峰彼未曾。”“荆关”已前述,“董巨”则为董源与巨然,皆为五代时著名山水画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四人,被誉为“前之荆关,后之董巨”,为五代时四大山水画家。诗人阮元曾任两广总督,生平深通广晓,精研经籍,著述等身,可谓见多识广,但连他都未曾见过“荆关董巨”四大山水名家画过桂林山水。
清代诗人、书画家张维屏,有写象鼻山的诗句:“山形似象鼻,画手谁虎头?”“虎头”即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他的小名叫虎头,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这句诗的意思是谁来充当顾恺之,画出象鼻山的神韵来呢?
清代诗人张联桂作《望阳朔沿江诸山放歌》诗,有“西川王宰如再出,未知五日摹能工”之句。王宰,唐代蜀中(古称西川)人,多画蜀山,玲珑嵚空,巉岩巧峭。杜甫称其丹青绝伦。五日,谓王宰五日画一石,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诗人张联桂怀疑,即使像王宰这样五日画一石,十日画一水功力深厚的大画家,如果再生复出,也不知道能否把桂林山水描摹得下来?
从古代诗人抒写桂林山水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话桂林山水之难,甚至古代诗人认为桂林山水“应是天公醉时笔,重重粉墨尚纵横”([宋]邹浩)。清代诗人李守仁也认为漓江山水是出自“天公”的“淋漓大笔”,它把“万古丹青一洗空”,纵有才高八斗的丹青高手,也望而生畏,不敢再轻动画笔。
桂林山水的诗词作品,在桂林的历史长河中流淌了一千多年,直到近代才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桂林山水画。张大千、徐悲鸿、李可染、白雪石等名家都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桂林山水画。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桂林本土画家群体崛起,桂林山水画家之多,表现桂林山水的画作之多,更是一时之盛,但却鲜有独到创新给人以艺术震撼的力作。反正桂林山水你画得越像就越不像,你画得越美就越不美,因为现实中桂林山水就作为一个旷世绝伦的美景参照对象摆在那里,看你“奈此百嶂千峰何”。看来,画桂林山水要想取得新的突破,非得另辟蹊径不可了。这就是要从一般的桂林山水美学上升到桂林山水文化学的审美高度。
当我们站在桂林山水文化学的审美高度来审视戴延兴先生的《水墨·五色气韵》漓江烟雨水墨画作品时,顿时感到面目为之一新。画家用中国传统的水墨艺术手法,表现漓江烟雨,给人一种超尘脱俗之感。他笔下的山,悟得了桂山的神韵。桂林的山,挺——“四野皆平地,千峰直上天”([宋]陈藻);奇——“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清]袁枚);巧——“拔地复刺天,千山若羽簉”([明]俞安期),意即桂林的山排列整齐,若飞鸟的羽翅。看到戴延兴笔下的山,就使人想起古代诗人这些描绘桂林山峰的神美诗句。他所画的山,早已脱出桂山的形似而进入了一种神似。山无多余笔墨,没有画一棵树,一枝叶,一峭石,但你可以从那浸润的水墨中,似乎又看到巉岩危崖,奇树杂花,烟岚雾绕。
戴延兴笔下的山与水,结合得更为奇妙。他笔下的漓江,不着一墨,但你似乎又可以看到江水如镜,青峰倒影,雨带孤帆。看他画的山水,使人不禁吟出“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明]俞安期)的诗句,使你看到“青山簇簇水中生”、“船在青山顶上行”([清]袁枚)和“无数青山浮水出”([清]彭而述)的种种美景。这就是诗情画意的写照,使人们从他的画中体会到一种悠远而明晰的文化意蕴。
戴延兴的创新表现在他对桂林山水的构成上,他从大量的桂林山水的外形特征上提取共性,这种共性的提取是建立在他多年的大量素描创作积累的基础上,这些素描创作为他在构图上脱颖而出,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形态飘逸而形象上具有离立风骨的桂林山水画风格。这一点显得尤为可贵,如只重飘逸,则缺定力,给人过分虚无飘渺之感;如只重风骨,则作品显得拙硬,有失漓江烟雨之柔美。戴延兴创造的一幅幅漓江烟雨图,与他人不同之处正在此。他的画面上着墨非常简洁,有时简洁到惜墨如金的程度,但却常常让人一睹而惊奇,有一种“推蓬忽觉青山近,人与白云同一船”([清]张维屏)的身临其境之感。但是,他的画面上,却似乎只有玉笋般的一簇奇峰和扁舟一叶。烟在何处?雾在何处?雨在何处?水在何处?人在何处?一切都在虚无缥缈间。这就是飘逸,一种若有若无的美,给人以无限想象空间的美。
戴延兴作品的风骨,体现在他笔下的山。那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