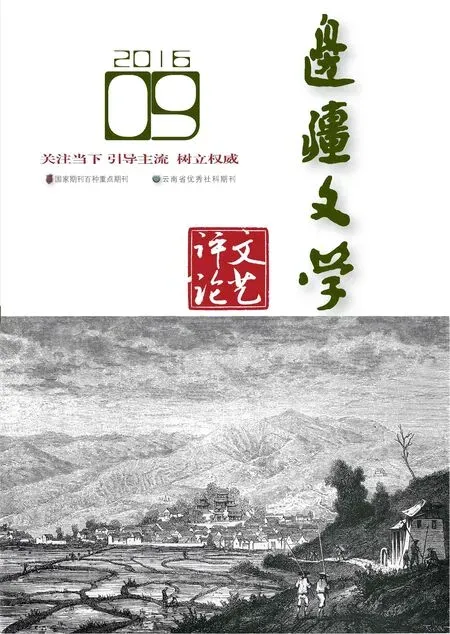戏曲的写意美
2016-11-26施培昌
◎施培昌
戏曲的写意美
◎施培昌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它植根于民族艺术土壤,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长期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迄今为止,她仍然是最能代表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艺术样式之一。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戏曲被边缘化,被陌生化,面临全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来自内部对优秀戏曲艺术的不尊重,甚至认为它是落后的艺术,要用西方的艺术方式来改造它。这些偏见直接造成对戏曲审美自觉和自信的迷失。针对这些审美误区,有必要对戏曲的审美作再学习、再认识。我在这里首先对戏曲写意美作探讨、发议论,只想求证于实践,其目的是进一步增强戏曲审美的自信和自觉。
“写意”是中国绘画的用语。什么是写意?例如,一幅画有梅花的水墨画,生机盎然,但认真一想,梅花的杆没有黑的,更没有黑花。为什么它给人真实感呢?齐白石大师在纸上画了几条鱼,并未画水,但它却给人以鱼在水中遨游的动感。这大概就是“写意”。在这里“写意”是与“写实”对应而言的。写意,是画家以写意的笔法,来描绘胸中的意象。
可以说中国戏曲是一种写意的舞台艺术,因为它从来就排斥纯客观地追求生活真实。但这绝不是说戏曲可以脱离生活。而是说不取外貌真实直取生活的本质内涵。艺术所表现的生活已经是经过艺术家改造过的生活,是在生活“实”的基础上融入了艺术家的“意”的结果。也就是说以“意”表现出客观对象的本质,而这一本质的展示过程中要渗透艺术家的情感因素。所以写意的实质是表达创造主体的意志和情怀。我们不妨以昆曲《牡丹亭》为例,看一看写意戏剧高在何处,妙在哪里。
昆曲《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中国戏曲中一部审美价值很高的经典,一部充满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的杰作。《牡丹亭》写的是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复生的故事,它演绎了杜丽娘如何从一位温顺恭谨,楚楚可人的千金小姐,变成一位缠绵悱恻,梦中去与陌生情人幽会的勇敢姑娘,又如何由一位在梦中与情人幽会的女孩、变成一位因相思而命赴黄泉的女鬼,成为女鬼后仍一往情深地去选择梦中所爱并勇敢地成就一段人鬼情,最后,终于得到自己所爱情人的帮助,还阳人间,实现了用生命换来人间爱情理想。这样一部美丽的戏剧作品。它不仅为今天的国人惊叹,也让当代西方人震撼。
这里我抄录一位名叫周泰的记者写的一篇纪实报道中的一段文字:“美国当地时间2006年9月29日晚,拥有1800个座位的洛杉矶加州大学若伊斯大剧院座无虚席。有些观众是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专程赶来的。青春版《牡丹亭》演到《寻梦》一场,全场观众都深深陶醉在女主角优雅缠绵的表演中。一位坐在轮椅上吊着点滴来剧院看戏的老师忘情地高喊着“I like this girl”,演出刚结束,观众们便迫不及待地涌向台前,希望近距离一睹“杜丽娘”的风姿,斯坦福戏剧系主任麦克,伦斯教授对记者说:“我看得目瞪口呆,世上怎么有这样好的艺术?真是太美了!”这就是中国戏剧艺术的魅力,这就是《牡丹亭》的审美价值。为什么400年前的作品,今天演来反响还如此强烈?因为它写了人、人性,写了人间真情,因而它就能与今人沟通。正是因为有了非写实形态,非生活形态的“写意”戏剧观,才催生出这部浪漫变形,奇情挚爱的好戏。
我们看到“写意”,它的文化渊源与中国艺术哲学、文化精神文脉相承。
王国维较早地认识到艺术创作的方法无非“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也。”(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先生这里的“造境”,即指不完全等同于生活,充盈着主观想象的艺术创作方法,“写境”,此处即为写实说法。
李泽厚说:“中国戏曲显示了中国艺术的理性精神……并不去逼真地创造幻觉真实,而更诉之于理解、想象的真实。”说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时,李希凡说道:“无论在内涵的形式,在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上,比较强调艺术家主体的心灵感受和生命意识的表达,整体地说,就是重表现、重精神、重写意(李希凡《中国艺术·序》。”在汤显祖看来:“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正是他的这种毫无牵绊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走向极端的想象力,才创造出这样一个最独特,最离奇,最抒情,也最美丽的作品。人变鬼、鬼变人未必是真的,但他们的“情”却是真的。“情到真时事亦真”(袁于令)。
对于中国戏曲来说,没有实,生不出虚来, 没有虚,不成其为艺术,即,“戏是生活的虚拟。”所谓写意之“意”不是单纯抽象的精神,它是高于生活的形神兼有的形象,这种写意形象,距离生活实际甚远,但它凝炼着生活中丰富的抽象特征。如以浆代船,为什么可以“代”呢?因为浆和船是有必然联系的,船和水又有必然联系,人们见浆思船,由船及水,所以浆就成了船和水的写意之物,而真船真水就成为观众联想中的形象。同样的道理,演员的划桨动作,可以使人联想,船行水上的景况,那么划船就成了戏曲表演中的“虚拟动作”。想象比直观往往还要感到丰富真实。凡以鞭代马、上楼下楼等皆属虚拟。在一台戏的演出过程中,演员既是虚拟的时间载体,又是虚拟的空间载体,二者通过虚拟动作统一起来。台上大量的虚拟动作可把天上地下、千军万马、游梦惊魂——展现,只要是生活中有的,没有不能表现的,全部仰仗于表演。在演员没有出场之前,舞台是一个抽象的空间,这空间由谁来填充完成?由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想象互为补充完成。当角色出场时,舞台才有具体的内容。演员的举手投足,舞姿亮相,就能点化景色万千,环境和情景全在演员身上。“看山如山在,看水如水流”。环境随演员的上下场或挪移而变动,人物下场了,环境也消失了。即“景”在演员身上。但这一切都借助观众想象,从演员的动作中想象出环境和情境来。“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这幅对联是对戏曲的虚拟性和能动性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戏曲写意美精练而生动的描述。
前苏联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5年4月,莫斯科有一次世界上顶级大师的聚会。为什么说他是顶级的呢?看看出场人物就知道了,有斯坦尼斯拉夫、丹钦科、梅耶荷德、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德国的戏剧家布来希特、英国戏剧评论家登·克雷……令人惊奇的是所有伟大的导演都到了,真是罕见!什么重大事件吸引他们云集莫斯科呢?这是由于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来到莫斯科演出并作演讲,第一次把中国京剧介绍到苏联。戏剧大师观看了梅兰芳的精彩演出后,在为他召开的研讨会上,对梅兰芳表演艺术一致称赞,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开放的舞台,凭借假定性的威力,表现了提鞭当马、日行千里、挥洒自如、姿态万千的表演艺术。”对中国戏剧来说:“三一律”樊篱,“第四堵墙”的障碍都不存在。要知道,当时在表演理论方面,有斯坦尼斯拉夫的体验派,有梅耶荷德的表现派,还有布来希特的间离派,他们的理论是互相对立的。但都一致赞扬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导演梅耶荷德说:“所有的戏剧都是假定性的,而梅兰芳的假定性是最具现代的,这是东方智慧。”可见中国戏曲所体现的“东方智慧”,集中体现于中国戏曲的写意观,虚拟化,在表现生活时获得更大自由,说明了这种独特的表演方法,足以在最简易的舞台,演绎任何题材故事的完整的表演体系。因而它是“最具现代的”。
戏剧的虚拟性,假定性得以成立是以观众的认同为条件的。比如戏曲的一桌二椅,其本身是简易的,但当一旦出现在具体的时空中,经演员的动作,就能想象出环境和情景来,或桌或椅,或床或井,或山头或渡桥,便有了确定的指向。虽然他们的外形实际上同它所代表的实物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形象上的直接联系,但是它们在戏剧情境中再现的意义却是明确的。戏曲的龙套也是如此,拿起刀枪就是兵士,拿起水旗就代表水,拿起云牌就表示云,只要他们参与到戏剧情境中去,具体所指就不模糊。但是这种虚拟性,假定性是需要观众的参予,需要他们在想象中同演员共同创造。
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戏曲作品在传统(一桌三椅)的基础上拓展了戏曲“写意”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意蕴。一些好的舞美设计,着力于外化人物的感受、感觉、感知,表现角色动作情绪与意义,挖掘剧作内涵,所营造的戏剧空间有着更深层次的写意性。
重庆京剧团创作演出的京剧《金锁记》,是根据女作家张爱玲的名作改编。剧中塑造了女主人公曹七巧的不幸人生,笔锋直指吃人的罪恶腐朽社会。导演是北京人艺,有先锋派之称的李六艺。想不到这位话剧导演却搞出了一台“回归戏曲本体”时尚新颖的戏。台上看不到相对具象的景物和固定的道具,看不到与戏有关的历史生活的真实图景,台上选择了月亮、门框、椅子等几个意向,在舞台上营造了一个空灵,流动而又意味深长的空间。
高低错落,随戏移动的“九道门”,自曹七巧嫁到婆家就穿过这一道道的门…… 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步步迈进了人生的终点。观众从门中看到了这个没落家庭的森严壁垒,有时候这门成了特写镜头,多人从门里窥视着曹七巧的一举一动,就像一种社会势力压迫着她的心灵。
一把太师椅放着一件男性的衣服,这是女主角骨痨病男人的符号。导演把这几件具象的东西,在片段式和场面的交替中,在推拉移动的时空中巧妙运用,景物写意的象征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效果。
著名话剧导演田沁鑫编剧导演的话剧《生死场》,可算是话剧现代化和民族性融合的典范。田沁鑫在她的《导演阐述》中写到:“…….要寻找整体视觉效果,我不追求形似,只要求传神,使象征成为主要手段。以朴拙、力度为原则,透视出写意观念的融合。加入戏曲时空表现的一些技巧,如可变性、流畅性、自由度等…….。”正是她对戏曲写意和戏曲舞台空灵的观念的追求和运用,才会把这部戏做得简洁、凝重、大气。在这个戏的呈现中,时空彻底打破,时序可以颠倒,空间可以重叠、交叉、闪回、梦幻等各种意识活动可以跳出跳进地自由展现。
戏曲讲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就是说用简约便捷的方式交待情节,扭结人物关系,凡是与戏剧冲突或人物性格关系不大的地方,就可以尽量省略,一笔带过,腾出时间,腾出篇幅、去揭示中心事件,叙述主要人物的精神生活和心理历程。重要关节须抓住不放。写深写透,有戏的地方要把戏做足做够,要浓墨重彩,层层渲染,有时要工笔描绘,精雕细刻,有时还得用特写直照人物心灵。
京剧《文昭关》是一出京剧老生重头戏,说的是决心除暴复仇的伍子胥在弃楚投吴途中,楚平王的缉拿,昭关的高山峻岭,使他陷入困境。幸遇隐士东皋公的同情,将他留宿后花园,一连数日,无计可施。这天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一夜之间头发都白了,东皋公一见大喜,当即让他乔装混出昭关。
在短短的三十分钟里仅以几次短暂的更鼓声表现了通宵达旦,从初更到五更鸡叫,使人确实仿佛度过了辗转反侧的漫漫长夜。更为奇妙的是那极为简练的胡须演变,一开始是黑胡须,唱了他的遭遇、心境后入帐。可心中有事睡不安,他又出帐,此时黑胡须变成了花白胡须,他又勉强让自己进帐睡觉,但情绪起伏更大,还是不能入睡,此时已五更鸡叫,当他再次出帐时,花白胡须竟然变成了全白的胡须。这就是简约,“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删繁就简,就是把无关重要的枝节去掉,裁去,把时间省下来,重点去揭示(通过唱)伍子胥这个人物的心路历程。这种奇妙的处理显示了中国戏曲无以伦比的写意艺术的优势。
写意,它不只是我国戏曲的美学原则而且是我国传统文学、绘画、音乐及戏曲所固有的美学财富。就中国戏曲而言,在写意艺术方法指导下产生的“虚拟性”、“程式性”的美学特征并不只是某个方面,而是贯彻在整个戏剧舞台的方方面面,使它的舞台呈现完全是中国风范、民族神韵。
可以说写意是中国戏曲的理论基础、艺术方法、创作法则。
(作者单位:昆明市官渡区文化馆)
责任编辑:胡耀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