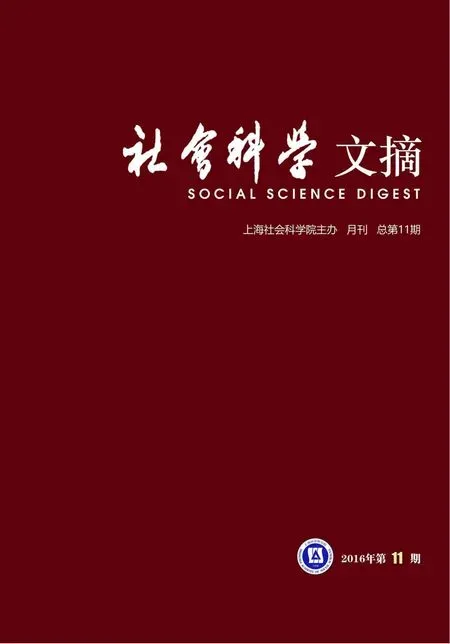从“无地彷徨”走向“话语重建”
——关于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
2016-11-26曹顺庆
文/曹顺庆
从“无地彷徨”走向“话语重建”
——关于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
文/曹顺庆
“旧体诗是否入史”之争暴露学界痼疾
学术论争有效展开的必要条件是论争双方所坚持的前提、所使用的概念是一致的。倘若论争的前提不清,难免出现郢书燕说的尴尬情况。“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很多讨论,即陷入类似的“泥潭”之中。
支持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往往列举其庞大的创评群体、斐然的艺术成就以及依旧葆有的文学活力等优长,指出旧体诗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而反对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则指斥旧体诗词僵死古板的形式、黯淡低迷的前景乃至对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冲击等,或坚决或迟疑地否认旧体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资格。两大阵营学者们,援引各类资料,“不亦乐乎”地申明立场、驳斥彼此。但是,不得不指出,在一片喧腾热闹之中,双方阵营都集体性地轻视或忽视了此命题中“史”这一字对于论争的重要性——对“史”统一的限定既是论争展开的必要前提,也是论争有效性的坚实保障。
由于在语言和形式上与“新诗”之间的显著差别,不论“现当代旧体诗词”以何种称谓(如,“现当代古体诗词”“现当代古典诗词”“20世纪旧体诗词”等)出现,论争双方并无过多分歧,其所指向的都是一个内涵与外延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然而,细究起来,这一研究对象行将进入或被摒弃而出的“现当代文学史”,在论争双方那里却并非是一码事:支持旧体诗词入史者多从时间范围层面来使用“现当代”——支持者甚至策略性地将其替换为时间意义更为明确的“20世纪”——这一限定词来修饰“文学史”;而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者则从文学性质层面来使用“现当代”——与“旧的”相对立之“新的”,或具有所谓的“现代性”的——限定“文学史”。由是,论争的双方正如在不同时空里缠斗的武者,虽相互朝对方挥着斧钺,却难直抵彼此要害。
正如年轻学者吕东亮指出的那样,“直观地看,旧体诗词能否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是一个名实之辩的问题”,即,论争焦点在实质上最终从“旧体诗词”落脚到了“文学史”上:支持入史者站在自己的立场指责目前的描述“现当代”时间范围内的“文学史”是“名不副实”的;而反对入史者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申明以描述“现代性”或“新的”文学为任务的“文学史”欲“名实相副”的话,势必将“旧的”诗词排除在外。这样看来,设若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现当代文学史”被更精确地分别命名为“现当代时期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现当代新文学史/现当代有‘现代性’的文学史”的话,论争双方围绕“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讨论似乎也可以就此而消歇了。
然而,论争的消歇不应是思考的终点而应成为其起点,在历次的论争中,学界的一些“痼疾”被或隐或显地暴露出来,亟待我们对其进行反思。
正视并自觉清理“唯科学主义”的痼疾
黄修己先生在论述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姻缘”时,就已隐隐意识到了“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前长时间里称‘中国新文学史’”的事实,然而他并未就此深入探讨。苗怀明在一篇直接回应黄先生的文章中则对这一“名称偷换”现象有着精辟分析:
有些研究者总是以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新、雅的态度,旧和俗的一方总是作为批判靶子的身份出现,被断章取义地丑化、妖魔化……将“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混用,就是这一思路最明显的体现,不管这种混用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种扬新、雅抑旧、俗之举基本上沿袭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思路。
上述引文揭露了一个令人警惕的问题:治史者有意或无意地将“新的”文学等同为现当代时期内唯一值得书写的文学形式,同时,又有意或无意地勾销了“旧的”文学的存在意义。有意的勾销难免受到文学之外因素的影响——毕竟黄、苗二位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及20世纪50年代是“新文学史”转变为“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时间节点,而无意的勾销因其隐蔽性和普遍性则会对学术研究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治史者的这类“无意勾销”正来源于其对“五四”以及新文化运动遗产的“令人遗憾”的继承。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在文章中他饱含激情地提倡“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决心与黑暗的旧世界分道扬镳。自此,严格讲求逻辑划分、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展开的科学观念或者科学主义成为“五四”文人反传统、建立新学术的“利器”,并“逐步演变成为统领社会意识的价值尺度和精神权威”,进而成为一种明显有别于古代话语体系的新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更为严重的是,当“科学主义”成为统摄社会文化的唯一“元语言”,当对科学的“有意识”使用演变成了对科学的“无意识”崇拜,“科学主义”就由此转换为“唯科学主义”。它对于文学史书写的负面影响不容被低估: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逻辑更像是进化论在文学领域的推演,即传统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与缺陷,最终“不可避免”地被“科学”“先进”的新文学与新文化所淘汰、取代——“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价值判断的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在这种倾向的导引下,文学的历史被视为是“不断‘进化’的链条,而组成这一链条的,则是一系列的断裂性阶段”,“不断划分阶段,不断把每个阶段宣布为‘新的起点’”的做法,实际上是“不断掩盖新的阶段与过去的关联”。以此为逻辑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当然无法尽可能地逼近历史,更无从谈起尊重和还原历史了。
在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及文化独有的生命力也被武断地进行了价值重估,往往被贴上“非科学性”“无体系性”之类的标签,这些错误印象的由来不在于中国文论不科学或没有体系性,而在于我们习惯拿着西方的、“唯科学主义”来审视中国传统的文学及文论,我们本有的文化系统当然会在这种审视和“被对象化”中产生严重的扭曲,甚至出现了中国人读不懂自己的传统文论的怪现象。另外,唯科学主义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异质性”。即,西方的科学主义作为“元语言”已然构成了我们当代言说的基本范型,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说”以及“说什么”,因为“无论我们将核心理念定位于何种‘异质内涵’,知识系统的逻辑演进都将沿分析性路数走完被先在理念所规定的逻辑域”,文化的“异质性”由此遭受到巨大破坏,这无疑对我们深入认识自身以及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了严重戕害。
当梳理“五四”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时,我们会发现,事实上质疑和反思的声音一直存在着。关于新旧诗词之争,反对者斥责新诗倡导者“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诗”是“矫枉过正”并不奇怪,即便是支持者阵营中也有很多人在新文化运动风潮过后纷纷“勒马回缰写旧诗”,态度与语气要比以前宽容不少,认为“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坦然承认当初带着“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语)”的自信对旧体诗词乃至旧文学、旧文化的“恶骂立攻”,只是在“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的时代背景下的权宜之计。这种清醒理性的反思精神正是“五四”新文化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以“五四”传统继承者自居的我们倘若忽视这一点,仍不去自觉地清理“唯科学主义”痼疾的话,那么,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仍然只能“令人遗憾”地继续遗憾下去了。
“现代性”之争引人深思
历次论争中诸位学者围绕着“现代性”一词进行反复言说、探讨的现象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学界的某种尴尬处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论争中,“旧体诗词入史”的反对者认为文学形式的现代性与内容的现代性同等重要,指出“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精神特征的现代性,而且是包括了文学语言、文体样式、文学思维等文学本体形式的现代性特征的”,依此定论“……旧的格律形式中的创作,仍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具有文学现代形式与审美品质意义的现代性诗歌”;而“旧体诗词入史”的支持者则认为“现代性与古典语言、古代文体形式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不应以排斥这些因素为前提才能得以确立”,相较于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形式,支持者们更重于文学内容,认为“主体精神的健全饱满,文本精神的充沛强大,能使一切诗体灿然生辉”,并且“恰恰是‘现代性’的引入为确立旧体诗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中的合法性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在上述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学者对于“入史”问题的态度是审慎的:吴晓东主张以“价值无涉”的方式,将旧体诗词、通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纳入到现代文学史当中,但是他随即指出“上述思路并不意味着企图简单化地超越或取代以往的文学史观”,毕竟“以‘现代性’作为核心取向的文学史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规范”。他希望“谨慎从事”,以“最终建立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学史观”。
耐人寻味的是,在历次论证过程中,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文章在使用“现代性”一词时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值得商榷的地方:反对“入史”者如王泽龙,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给了现代性众多定义”,另一方面却为了展开观点,对“现代性”给出了自己的新定义;支持“入史”者如陈友康,虽然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概念被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对现代性的理解却众说纷纭”,甚至有“随意增加或变更其内涵”现象的出现。然而在笔者看来,陈先生在文章中对现代性的理解远未到达充分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有人把语言形式的变革也看做现代性”的直接指责是否也是另一种的“随意增加或变更”呢?由此看来,中立者们审慎的态度并非仅是一种言说策略,这种态度本身即体现了其对“现代性”模糊的概念边界的警觉,亦即,“‘现代性’本身是否存在多种可能性以及是否存在无所不包的‘现代性’等问题,不失为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题目”。
相较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标准在文学史书写中的过分“泛滥”,现当代文学研究对“现代性”概念的引入诚然是一种巨大进步。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当“现代性”被十分广泛而又非常不严谨地使用——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内涵就已充满了矛盾和对抗,而中国的学者们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使它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意义赋予的过程——的时候,它便成为一个暧昧含混、充满歧义的概念,以至于失去了作为理论话语应具有的阐释的有效性,从而进一步导致许多文学研究的对话与论争无法真正进行下去的吊诡处境。“旧体诗词入史”问题中围绕“现代性”生发而出的许多讨论就是此处境中的冰山一角,因此,李仲凡呼吁“跳出‘现代性’的框框”“不再仅仅为它(注: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性做意气之争”是非常合理而明智的。
学界对“现代性”前后态度的剧烈转变引人深思:我们的理论话语体系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王富仁先生曾不无痛心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至今被当做外国文学的一个影子似的存在,不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我们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概念大都是在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换言之,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失语症”不只生发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它还散播至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蔓延成为一种“文化病态”: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这种学术上的“喑哑”“失语”,一方面使我们的文学阐释与本土鲜活的文学经验之间始终存有一层“隔膜”;另一方面它还牺牲了文学事实的丰富性,遮蔽了许多文学现象——现代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所遭遇的命运即是显例。
然而,指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正如质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一样,当我们意识到“失语”之后,我们的文艺理论、阐释话语应何去何从?
中国文论的重建与创新
关于“现代性”的诸多争端,李怡教授的观点最为透彻通达:“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卷入‘现代性话语’的混杂声响,而是重新检点我们的阐释立场,……如果是为了‘问题’本身的展开,‘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无关紧要的。”他甚至大胆设想,“在阐述20世纪中国文学世纪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可不可以摆脱对这一概念过分的依赖,以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解提炼出其他更恰切更丰富的语汇”。李怡教授这种以“问题”为导向、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十分可贵;同时,他的“以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解”提炼整合出“更恰切更丰富的语汇”的设想,也是笔者多年以来重点关注的一个命题。
1995年,我首次提出了“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与之紧密配合的另一个命题就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意图在指明学界固有症结的同时,尝试导引中国文论走出“无地彷徨”的泥淖,并由此开始逐步探讨中国文论的创新路径和话语重建的策略:重建和创新最先是从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的否定开始的,理由是,倘若作为文论话语重建最重要资源的古代文论被所谓“现代转化”的话,其实质仍只是“唯科学主义”更为隐蔽的归化行为罢了;紧接着“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文论中国化”作为重建与创新思路被明确地提出,意图“以中化西”,让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实现水乳交融的结合,以摆脱西方文论“化中国”的窘境,从而使中国文论话语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
除了学理层面的争鸣外,笔者还进行了许多实际的重建与创新工作,如,在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方面,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在教学工作中让学生直面经典,尝试在现实语境中去激活中国文论;又如,笔者近年来连续撰文呼吁在文学史中给予“无地彷徨”的现当代旧体诗词以适当的生存空间——本文亦包括在内,其初始动机何尝不是为了同样处于“无地彷徨”境遇的中国文论的重建与创新。
当然,在西方话语定于一尊的今天,欲实现上文所涉诸目标,无疑是障碍重重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笔者愿与诸位方家一道,以反思“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为起点,重新恢复起失去已久的文化自信,化合中西、自铸伟辞,以自身切实的研究实绩,去彰显民族精神、重塑民族传统,最终帮助中国文论走上一条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重建与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自《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