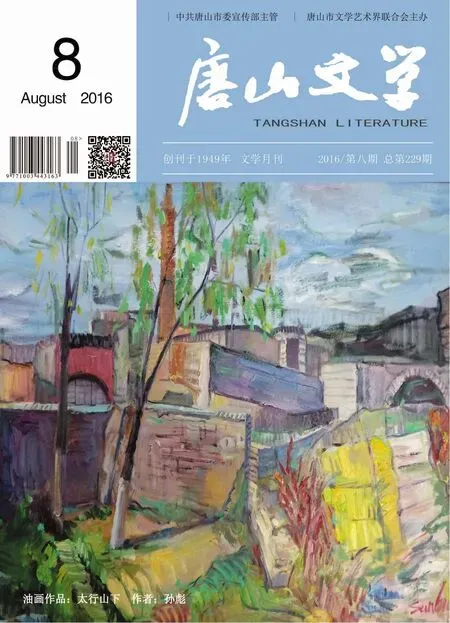试析白居易诗中的苏州水意象
2016-11-26聂佳旭
聂佳旭
试析白居易诗中的苏州水意象
聂佳旭
随着唐朝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入仕的官员比重越来越大,官员们普遍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另一方面,官员的任职并不一定是在自己的本乡本土,也可能是跨州越郡,宦游异乡。这些宦游之人往往敏感于自然转化、物候更新。而水作为苏州最大的自然特点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屡屡出现,构成了诗歌意象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水意象。所谓水环境意象,即指人对于水形成分布及所处空间的感受、认识和体验,是人的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相结合的产物,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唐代诗人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是地道的北方人。他在文学上主张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的文学手段,因此他的诗歌多为写实主义作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白居易在唐敬宗宝历元年五月到宝历二年九月担任苏州刺史,为官仅一年多,与苏州结下了深厚情谊。白居易在苏任职期间遍访名士,畅游山水,留下了很多作品传世,其中关于苏州的诗歌有一百三十多首,散文六首,如《吴中好风景二首》《白云泉》《正月三日闲行》等诗作都咏叹姑苏不同时节的怡人景致和水乡生活,苏州的水意象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充分展现。对此的研究已有不少,但针对诗歌中的苏州水意象研究甚少。笔者拟以白居易主政苏州期间创作的诗歌作品为主,将诗歌中的苏州水意象分不同层面来探讨。
一、水体的地理状况
苏州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西抱太湖,北依长江,气候温和湿润,是典型的水泽之国、鱼米之乡。唐代咏太湖诗歌中通过对“水”意象的描绘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图景与风情。太湖襟带吴越,有着庞大的河网系统。
太湖是白居易的诗作中出现的主要水意象之一,乐天往往引之入诗名,比如《泛太湖书事寄微之》《早发赴洞庭舟中作》《宿湖中》等等。《泛太湖书事寄微之》有“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的诗句,烟霭迷离的湖面上,几点轻舟从流飘荡,飘飘然像行驶在高空的云端。《宿湖中》中写道:“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浸月冷波千顷练,苞霜新橘万株金。”傍晚时水天相接,一碧万顷,树影、晚霞、秋霜、金橘等与太湖相伴的江南风物在诗人笔下增添了一层诗意浪漫的色彩。古体长诗《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在重阳日感慨年华逝去的同时,他更倾心于享受秋日太湖迤逦风光:“姑苏台榭倚苍霭,太湖山水含清光。”通过这一系列具体的意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时间段,描绘着水乡风光,可见诗人笔下太湖水面的开阔、水质的纯澈和周边环境的温润宜人。
河网密布是苏州地区的基本地貌,除了水流本身的分布,还从侧面体现在舟船与木桥上,这就构成了苏州城水陆双棋盘骨架。白居易在《登阊门闲望》写到“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是家家门前的小舟之况,而《小舫》记录自身驾舟水行的情景:“小舫一艘新造了,轻装梁柱庳安篷。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而伴着河网的密布的另一盛景就是木桥的纵横交错。在《正月三日闲行》中又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家家临水桥,出门皆用船是一派水乡的真实情景写照。白居易在宝历元年的重阳佳节,邀请众多名士郡斋宴集,醉后赋诗《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有言“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铜鱼今乃泽国节,刺史是古吴都王。”其中“桥相望”、“水道脉分”都可见河网之密、桥梁之多,甚至干脆用“泽国”两字代称。除了河湖之外,还有许多清泉在山涧之中。在灵岩山附近的天平山有一眼白云泉。白居易因此而作的《白云泉》是唐代著名绝句之一,即:“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诗中描绘了白云随风飘荡,卷舒自由,无牵无挂的形态;泉水涂涂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的清泉启迪了诗人超脱的境界。
这些河湖、山泉在白居易的笔下形成了一个个耀眼的光环,立体地展现了唐代苏州的水体分布情况。作为自然载体,它也为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诗情文韵萌生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二、水乡的物产经济
苏州在唐代属于江南东道,是“ 江南诸州,苏最为大”的东南雄郡。自古以来,江南地区就是物产丰盈的鱼米之乡。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概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时,江南已经是一片极具开发潜力的富饶地区。江南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经过两汉、六朝时期的不断开发,成了《宋书》中所描绘的“地广野丰,民勤本业”、 “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发展到至六朝时期,江南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改观,经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唐代则与杭州有“杭土丽且康,苏民富且庶”之称,江南已然成为一方富庶之地。
苏州的物产经济本身就极其的丰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江南水乡有着丰富的水中物产,这些物产在北方来客白居易眼中自是十分新奇。有些物产是北方没有的,有些物产北方虽然有但到底还有所差异,包括稻禾作物、白莲白藕、江南杨柳、苏州佳酿等等。在诗歌中,诗人往往流露出对水乡丰富物产的喜爱与赞美。
白居易在诗中也写到“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穗香。”这是描写江南暖湿气候下水稻作物适宜生长的自然生态状况。白莲白藕可算是吴地的主要特产了,很受白居易的喜爱。在《感白莲花》中有“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濆。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的诗句,表明了白莲不拘于杂花之色,高洁独立的品格。还有一首《种白莲》“吴中白藕洛中栽,莫恋江南花懒开。万里携归尔知否,红蕉朱槿不将来。”白居易在离开苏州的时候还特意移植了一些白莲到洛阳,每到莲花盛开,常请友人前来观赏。另一种颇受乐天青眼的便是苏州柳,他曾以《苏州柳》为题写一些诗篇。柳树本是南北方常见的绿化树木,苏州柳在白居易笔下却别有风情,似乎比北方的杨柳更加柔美多情。“金谷园中黄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絮扑白头条拂面,使君无计奈春何。”(《苏州柳》)在白居易离开苏州的多年以后,仍作诗怀念苏州的丰美物产。其中一首是《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齐云楼上事,已上十三年。”其中对于“竹筒粽”、“炙鹅鲜”以及苏州淳厚的夏至风俗可谓回忆绵长。
好水出佳酿。江南的清冽之水酿出了美味的吴酒,尤得白居易喜爱。他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曾写道,“日脚欲落备灯烛,风头渐高加酒浆”、“从事醒归应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须知菊酒登高会,从此多无二十场”,这些爱酒、饮酒、醉酒、醒酒的场景连串地出现在诗歌之中。离任之后,白居易对于吴酒更是时时在想、念念不忘。在《忆江南》的第三首中“江南好,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此后无论身在何处,白居易都会记起苏州的美酒佳酿和水乡特产。友人刘禹锡继任苏州刺史后,知道白喜爱吴酒,特地将新酿的酒寄给他,白非常高兴,赋诗曰 “惭愧故人怜寂寞,三千里外寄欢来”。可见白居易收到吴酒时那种意外的喜悦。还有《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也体现出多年后身在他方的诗人发觉,原本吴地家家都有的普通酒水也变得尤为珍贵而难求。
另外,白居易作为一郡之长,在保证朝廷赋税的同时,还要置办土贡。而贡品正是吴县西南五十里太湖中的柑橘。柑橘又是苏州物产的典型代表。《拣贡橘抒情》《宿湖中》《早发赴洞庭舟中作》《夜泛阳坞入明月湾即事寄崔湖州》等诗歌,既描写了苏州柑橘的样貌,也描写了柑橘所在之地的苏州山水之景。
自然的经济物产给白居易带来苏州独特的滋味,而白居易也为苏州的社会经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白居易在苏州绝没有盲目地嘻乐于山水而不为世用,游赏山水在他看来也不仅仅是为了一时的小我之乐,而往往在于发现山水之利后兼济天下。吴中名胜虎丘,白居易最爱游赏,但是每次都要先坐船一段而后步行于纵横的田埂艰难上山,州民游赏也总觉心神劳顿。因此刺史发动民工,清淤排涝,使河道畅通,从阊门直达虎丘山下的七里山塘便是由此而来。白居易命人利用河中挖起的泥土,顺势拓展河堤,加固垒石,又在堤岸植柳种竹,不仅解除了洪涝之忧,也可供车马往来驱驰。如此一来,无论从水路还是从陆路,去虎丘都是很简单的事。他在《武丘寺路》也讲出这一番盛景:“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頻”。其实,七里山塘泽被何止是一个时代的人呢?他在苏州太守期间做出了不少其他政绩,诸如修筑湖堤,考察水患的良好政绩,因此获得了苏州人民的爱戴。作为一名地方官,白居易在赏游山水的同时,始终坚守为民谋利的原则,以至于他离开苏州北上时,苏州老百姓纷纷悲啼,刘禹锡诗云:“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其中州民不舍之情可见一斑。
三、山水的审美意境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文人的作品与自然山水是分不开的,景与情与诗本是一个互相生发的过程。白居易一次在答友人诗中表达共鸣:“为忆娃宫与虎丘,玩君新作不能休。蜀笺写出篇篇好,吴调吟时句句愁。”说出了自己因苏州胜景“娃宫”、“虎丘”和“吴调”而文思泉涌,下笔难收。唐代的苏州地处远离中原政治统治中心的江南,在唐代虽然发展繁荣起来,但是政治地位还是不能与北方中原相提并论。因而较之北方,这一区域并没有太多的思想意识压制。高蹈独立姿态的文人异士时有涌现,白居易在此,也饱受熏陶。
最能体现白居易深受苏州山水精神洗礼的是太湖石。太湖石是白居易特别喜爱的吴地特产,离开苏州时还特意带走几块——“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这种心情在《莲石》诗篇则体现为“青石一两片,白莲三四枝。寄将东洛去,心与物相随”。白居易也写了许多关于太湖石的诗,在《双石》写道:“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诗文对太湖石的形态进行了细致描写与刻画,突出了怪、丑和无用的特点。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趣刺激了当时和后来的赏石文化。白居易更是以石为三友,为知己。他也是钦赞太湖石的天然工拙、自然造化、生命灵性,使诗人体会到一种古朴淡然的人生境界。
苏州的郡守文化更是促进了苏州的超脱意境,某种程度上给各种各样“因宦而游”与“为宦而游”的人提供了心灵的栖息地。在宝历元年之前,白居易尚未就苏州刺史任,他就已经久仰苏州及苏州刺史之名望,以之为尊位。在《吴郡诗石记》明白地记着他幼时对两州刺史职位的憧憬:“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稚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白居易卸任后感慨道:能在苏州这样的地方做刺史也是件幸事,毕竟这是自己多年来的梦想。由此可知,苏杭在白居易的心里不同于别处,不要说岭南荒蛮、巴楚凄凉之地,就是京畿赤县也难与此二州相比。同为外官,同为刺史,苏杭二州的刺史就显得更加清贵。
在短暂的苏州刺史经历后,白居易回到了北方,但他对苏州的美好回忆却是深久绵长的,甚至进入诗人梦中:“扬州驿里梦苏州,梦到花桥水阁头。”当同僚赴任苏州时,乐天总是以诗相赠,如《送刘郎中赴任苏州》:“仁风膏雨去随轮,胜境欢游到逐身。水驿路穿儿店月,花船棹入女湖春。宣城独咏窗中岫,柳恽单题汀上蘋。何似姑苏诗太守,吟诗相继有三人。”这三位吟诗的姑苏太守就是皆担任过苏州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他们访山水、咏物产、宴集唱和,增加了苏州本身的人文魅力。三位诗人将他们的政才、诗情都倾注在苏州这片土地上,姑苏给了他们一方诗意的栖居地,也因他们的吟咏而增添了许多文化色彩。
四、结语
苏州之水有它独特的客观意象与主观意象。宦游至此的白居易在饱览了吴越清丽秀美的自然景色,熟悉了与北方异样的社会物产。不仅丰富了自己诗文创作内容,也影响了其诗文创作风格。从水体的地理位置、水乡的物产经济到山水的审美趣味与超脱意境,在诗人白居易的笔下更为生动地体现出来。
在唐代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诗人像白居易一般,以平实的语言描写现实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也很少有哪一座城市像苏州一样拥有河湖之密、物产之丰、意境之美,泊船、白莲、吴酒、太湖石等等水乡意象无不影响着久经宦海的诗人。透过诗人的作品,后人可以看出唐代的水城苏州,也就更加理解诗人在作品中的意象含义。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200030
聂佳旭(1992—),男,江苏徐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史、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