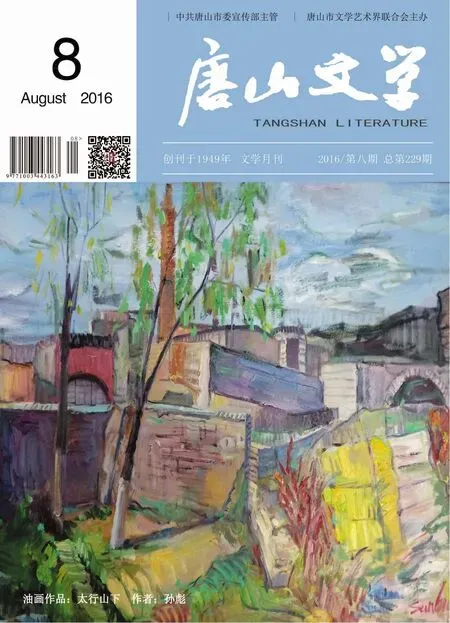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反思
——“学院派批评”为何成为一个贬义词
2016-11-26丁保花
丁保花
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反思
——“学院派批评”为何成为一个贬义词
丁保花
现今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大致分为三种: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学院批评。专业批评注重跟踪前沿文本,用简短而感性的文字评述文本,从众多文学作品中挑出精品,引导读者阅读。媒体批评注重热点事件,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结合的产物,发表在大众传媒上,从大众的角度考察文艺现象,批评话题可以是非专业的,参与对象也可以是非专业的。学院批评注重理论阐释,如同科学家研究基础理论,探寻文学规律,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这种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这三种批评都各有长处,可以说缺一不可,但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以贬义的口吻说起“学院派”,认为学院批评就是生搬硬套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将文章弄得云里雾里,让别人读不懂,脱离了文学现实。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认知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学院中学术体制的限制
当下高校中,其实并不缺乏优秀的文学批评人才,他们也能写出专业批评和媒体批评那样的好文章,但是大学的学术体制有其固定的规范,对批评文章也有模式和字数上的要求。一个老师要想评职称,要想申请各级社科类项目,就必须妥协于学术体制,去写那种厚实的有引有注的学术成果。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本来应该是相互平等、相互关联的三驾马车,但是当前的学术体制却重文学史、文学理论,认为这二者是厚重的学术成果,轻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批评无引无注,字数有限,是小学问。这种学术体制必然会导致学院批评文章的两个弊端。
第一是细读文本这个批评传统的断裂。在重理论的学术体制形成之前,批评家批评一个文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细读文本,重视文本的语言、情节、人物等,而不是为了合乎规范去引入大量理论和引注,空洞而脱离文本实际,本来不用理论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加了理论就有生搬硬套、故弄玄虚之感,让读者读不懂,不知道文章在讲什么。第二个弊端是批评文章文体的单一性,中国古代批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多种文体,如序跋、书信、随笔、论文、评点、语录、诗话、词话等。近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诸多文体,如梁启超的政论体、章太炎的逻辑体、鲁迅的杂文体、周作人的“美文”体、李健吾的随笔体、梁实秋的“教授”批评、思辨型的“胡风”文体以及茅盾基于“史论”笔法的作家论文体等等。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中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批评文体,丰富多样的文体使这些批评文章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采,能更好地表达批评者的理论和观点。无疑,以往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各种批评文体都是留给今人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批评者应该去研究和传承,注意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但是如今的批评工作者却普遍存在文体意识薄弱问题,这个问题又以学院派批评最为严重。因为学院派批评有严格的学术体制限制,批评文章有固定的模式和字数,所以学院派批评者有时候不得不采用单一的论文体写作,有论点、有论据、有理论等要求使得论文几乎成了一种“八股文”模式。特别是有的论文引用大量的理论和注述,几乎达到了借文本谈论理论的地步。这样的做法导致批评文章枯燥无味、晦涩难懂,读者读得不知所云,连批评者自己也不想再看第二遍。其实论文体是批评文体的主要方式,使用论文体进行批评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点,批评者运用论文体时,应该了解论文体的真正优点,即以理服人,恰当而娴熟地运用各种文学史常识和文学基础理论,同时批评者又能在文章中展示自己的风采,既有严谨的学理,又有独特的审美。读者在读到文章的理论时,只会觉得批评者用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酣畅淋漓,感受到一种理论之美、批评之美。但现在有的批评论文为了理论而写理论,故意制造阅读障碍,让读者读不懂,力图使批评文章高冷,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批评文章其实并没有运用到真正的论文体,他们运用的只是他们想象中的论文体,或者说是一种变形的论文体。这样的做法使得“论文体”“学院派批评”成了贬义词,实乃憾事。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批评者要重建文学批评文体意识,认识到批评文体的重要性,写出更多更好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在如今大众传媒普及,几乎全民阅读的时代,批评家更应该发挥自己独一无二的作用,指导作家写作,引导读者阅读,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
二、中国文学批评仍处在对外来思想、理论的吸收、模仿阶段
前文已经提到过,“学院派批评”注重阐述理论,是研究文学基础理论的主要群体。但是就如同中国产业界,更多的是引进技术,而缺乏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同样更多的是吸收、模仿外来思想、理论,而没有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这种尴尬的批评理论现状必然导致理论研究主力军“学院派”处在一种尴尬地位。中国文学批评使用的一些基本理论、概念、范畴、方法、现象描述、文学思潮概述基本上都借鉴于国外,而不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学经验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时,往往把这些现有的理论、概念等套在批评对象上,而不是从批评对象中提炼来源中国文学体验的新理论。事实上中国古代有自身的批评传统和批评精神,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文学批评著作可以说流传千古,而性灵、气韵、境界等文学范畴更是反映了中国文学之精髓,中国文化之根。但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批评体系却断裂了这种批评传统,更多地全盘引进外国批评理论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窘境,旧的批评传统没有传承,新的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又没有建立。一味地抄袭、模仿外国理论又会造成诸多弊端。首先是造成文学批评的逻辑矛盾、学理漏洞,外国的批评理论源于它的文化,有其绵延的批评史和独特的学理体系,尽管世界文学有共同的价值判断,但是也有差异、区别,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地方。由于民族性的差异,在借鉴外国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理解偏差的问题,更何况还存在语言的障碍,在翻译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意义偏移问题。而且中国的批评者在阅读外国理论时,往往只选取自己需要和感兴趣的一部分,这就很容易导致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理解有误。所以有时能看到一些批评者陈述的理论、范畴等逻辑相互矛盾,甚至一个批评者的批评文章中存在着前后矛盾、逻辑不通问题。借鉴来的理论就如后天移植的手臂,永远不可能像身体本身生长的手臂那样灵活自如、天然和谐。
一味抄袭、模仿外国理论导致的另一个弊端是中国理论研究的分散孤立。由于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在面对中国自身的文学经验时,文学批评就有手足无措之感,没有一个共同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批评家们只得各抒己见,得出一些分散而孤立的结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对“纯文学”进行定义时,有人认为是与大众文学相对的精英文学,有人认为是与俗文学相对的雅文学,有人认为是与商品利益相对的纯精神文学。对文学的多样化认识固然有其优点,但统一认识有时候也是必须的,两者都能促进文学批评的发展。但在当前的情况下,更多地是认识多样、研究分散,这样很容易造成研究者自说自话,做无用功。而且中国的理论研究群体之间也存在分散状态,在大学里,古代方向、现代方向、当代方向、中国方向、外国方向等等,各个学科之间界限清楚,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每个理论家在自己的领域里是一代大家,但对其他领域不熟悉,这导致各个学科和理论之间无法建立联系,不能共同讨论,不利于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批评群体里,专业批评、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三者也各有特点和领域,处于分散状态。这种分散状态不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文化价值引导,不能很好地发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作用。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各种文学充斥市场,良莠不齐。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必然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的价值引导。批评界分散的状态不利于应对当下多元的文化现象。
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呼声。中国文学想要表达真正的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世界文学想要看到真正的中国文学,发掘真正的中国之美。独立自主的道路注定是漫长而艰辛的,万里长路刚刚开始,中国文学批评仍然处在对外来思想、理论的吸收、模仿阶段,这种现状导致了诸多弊端,必然体现在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学院派身上,所以“学院派批评”成了一个贬义词,这种说法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不能独立自主的尴尬处境。就如同元素周期表之于化学,文学基础理论之于文学同样至关重要,就如高楼大厦底下的基石。我们可以看到,研究基础理论的重担沉沉地压在主力军“学院派”的身上,促使他们研究理论,一步步建立起理论体系的基石。“学院派批评”看似是贬义词,其背后又何尝不是一种沉重的责任和托付呢。我们期待“学院派批评”为自己正名,期待独立自主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期待真正的中国文学批评之声。作者简介:丁保花(1991—),女,湖北麻城人,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