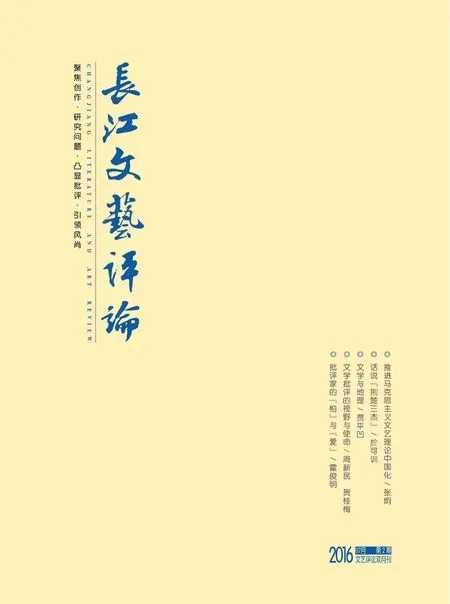“文学侠客”周明全
2016-11-25于京一
◎ 于京一
“文学侠客”周明全
◎ 于京一
一、敢为风气之先
我感觉周明全先在大学从事校报编辑工作,后转战媒体做编辑、记者,最后落脚出版社成出版人的职业经历,给他的文学研究生涯带来了难得的野性气质和理性谋略。作为记者和出版人,首先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捕捉能力,善于从庸常的琐屑和习见中发现症结或闪光点,这锤炼了他鞭辟入里、大开大阖的思维伸缩能力;其次要有分析问题、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与魄力,这需要以理性思考为根基、以深谋远虑为旨归,绝非眼前之功与感情用事可以应对。而兼具冲劲与谋略的周明全十分聪明又水到渠成地将自身优势运用到了文学研究和出版中。主要表现在:
第一,代际研究与出版。周明全的代际研究以“80后”批评家研究为切入点,在研究中发现问题、整理问题,迅速扩展至“70后”批评家研究和“未来批评家”研究。周明全所做的是一项在文学批评领域常常容易被忽视的工作,他关注的不是文本、作家或文学现象,而是对所有这些进行研究和批评的批评家们——说白了他关注的是大的文学场域,是关于文学的阐释和再生产。当然,这在现代文学领域早有温儒敏、许道明[1]等前辈学者做过筚路蓝缕的工作,但如此规模且代际分明的工作确属首次。由此,他把对狭义文学的研究引领到广义的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更加广袤复杂的园地。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采访并整理了对批评家们的访谈,获得了第一手鲜活的资料。出版专著《“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2],策划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二辑,集中推出了十一位青年评论家的集体亮相;自2014年开始,每年又推出一本《“80后”批评家年选》,以展示“80后”的最新和最高研究水准;2016年开始,他在《名作欣赏》主持“80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栏目,试图通过“80后”一代人的视野剖析目前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起“80后”一代人自己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
作为“80后”的一员,毫无疑问周明全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完成对自我一代思想的研究和身份的确证。但随着工作计划的相继开启,文学研究的魔力及其对相关问题的发现、发掘,早已引领周明全跨越了“80后”一代的藩篱,顺藤摸瓜地进入对“70后”“80后”和“未来批评家”的研究。2015年开始,他在《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主持“青年批评家”栏目,主要目的就是研究“70后”批评家的成长、研究方向以及对高校文科教育的理解和反思等,试图厘清这代人为何会被遮蔽以及他们的思想来源、今后的发展潜力等;并组织策划了《“7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涵括了八位最具实力的“70后”批评家的集子。2016年开始,又展开了对“未来批评家”的研究,在《名作欣赏》开设“未来批评家”栏目,主要推介那些优秀的、有潜力的在校文学硕士、博士。
总而言之,代际研究虽然充满歧义和争议,也为一些文坛及批评界大腕所批评,周明全自身也承认这项研究目前“非常仓促、问题很多”,但他的决心和信心看起来毫不动摇,“我做这个代际、出版这些书一个更深层次的想法是,我想做这些年轻人的精神成长史。我做这个访谈也好,综述也好,只是我在做这个大工程的一个前期材料准备吧。”[3]“做这些年轻人的精神成长史”,这是多么诚挚又恳切的肺腑之言,令人感动之余,我们是否深深地触摸到了周明全身上那种侠之大者的豪迈与气魄呢?!
第二,关于“中国小说”的倡议与研究。随着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热议再次沸反盈天。既有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水准的欢呼,也有武断地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蔑视。其实抛开这众口纷纭的一切,回到莫言的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一方面莫言确实用汉语为载体、以文学的方式重新塑造和呈现了中国现代以来的民族社会史和精神史,他以锐利而新颖的视角、结合自我的生命体验将现代中国的党派、群氓、运动、革命以及各种团体在历史斗争漩涡中的种种面相进行了极为详尽、夸张又真实的描画,令人怵目惊心、难以忘怀。另一方面莫言对小说这种文体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既有对现代西方各种流派纷呈的汲取,也有对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精髓的老实承继,他的写作已经开始自觉地试图将古今中外的艺术追求进行有机的糅合与互渗。我们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小说传统的优秀之处在传达现代以来我们民族的思想、情感、精神、命运等所呈现出的力量令人震惊——或者说中国小说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已经初露端倪,在莫言这里甚至可以说是初战告捷。
由此,周明全十分敏锐而适时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小说”的问题研究,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相继书写或发表了《可以无视,但不会淹没》[4],着力阐释“中国小说”这一概念;在《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5]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中国好小说”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品性:一是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二是中国故事、中国意境;三是中国风格、中国语言;在《谈中国小说创作的文学性》[6]中,周明全从故事、人物、语言、历史感、经典性、诗性美、拙朴美、浑然美等八个维度,探讨中国好小说的基本标准;2015年又撰写了《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我们这个时代的浅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的贫弱》等文章,一方面批评当下小说创作存在的浅陋直白等问题,一方面则进一步明确中国传统小说的独特性,他一再强调:中国小说的“散点聚焦”,远比欧洲的“核心聚焦”更有魅力,而且国外意识流小说和复调小说远不能相比。“中国小说”在叙述上是一种“流动体”,是日常生活的艺术再现,是和人的生活状态紧紧贴合在一起的,是一种生命的叙述模式。西方小说更重视讲故事,而中国古典小说则一直暗含有“文以载道”的文人情节。如此等等。
上述可见,周明全对“中国小说”的思考不可谓不周全,不可谓不深入。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小说’的重提,不仅是文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面对世界,在未来时代的一种精神姿态。”就现时代中国的全球性崛起和对软实力的提升及文化出口的期待而言,无论如何,对“中国小说”的重新讨论、定义和阐释都是刻不容缓的重要举措。现代以来,为了强国保种,我们不惜斩断传统、追慕西方,进行了百年的现代化艰难转型,这期间可谓喜忧参半、得失难分。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这百年绝不能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轻易抹除、扼杀或鄙弃,历史就是历史,没有这一百年的艰难探索就不会有现在的逐渐清明,尽管当下中华民族开始崛起,我们确实到了再次审视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的时刻,我们也确实应该重新接续传统的精华来破解西方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所产生的一系列困境,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传统文化优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换句话说,任何文明都具有某种时段性,在某一恰当的时段,某种适应它的文明才会相应崛起,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当下为了发扬国粹而完全抛弃西方的一切。落实到文学上,即当前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财富就可以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实中国传统历史上的先秦与唐宋文学皆是融汇新知的结晶,我们依然需要“拿来主义”,我们要以中国传统为根基,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以创新的眼界和姿态重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蓝图。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时刻警惕因对“民族强大”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幻梦而带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膨胀和“国家主义”至上。总而言之,当下重提“中国小说”的话题十分适时和必要,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谨防再次踏入历史极端的陷阱。
二、直抒胸臆批评不倦
周明全文学批评的侠义,还表现在他的豪爽与直率,豪气干云、直抒胸臆,从不避讳文坛的弊病和作家的身份地位,有时候甚至给人一种“偏执的深刻”之感。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浅写作》一文中,周明全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时代作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表面化写作,不仅没深入到生活的肌体里头,而且没有深入到文学的心脏深处。”文章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既剖示了“浅写作”的四个特征,又深挖出“浅写作”形成的五大根源。在直陈浅写作的种种乱象时,毫不客气地以当下著名作家的创作案例为靶心,分别批评了莫言语言的粗俗,指出了贾平凹创作速率的过快,抨击了阎连科的“王者心态”,甚至对张承志、路遥的文学思想表达了商榷,并就整个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先锋一代的模仿写作进行了大力挞伐,如此等等。周明全的观点是否能获得批评界和文学家们的一致认同暂且不论,至少他面对文坛和具体问题发声的真挚与恳切、他恨铁不成钢式的揪心与追问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
其实稍微用心就会发现,周明全的这些文章和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更非故弄玄虚,恰恰相反,完全是他个人性格与思想成长路程的真诚映现。恰如李德南在与周明全对话时所言:“读你的批评文章,我也觉得你不是想做纯粹知识方面的梳理,而是注重在文字中投入个人的生命热情,从中也可见你对社会人生的关怀。”[7]周明全确不是那种喜钻故纸堆的文学批评者,他的文字的力量之所以直击人心,关键在于他对当下现实人生、人世、人心与人性的直面与痛感。他的文章总是试图突破文字本身的拘囿和约束,而奔放到活生生的、毛茸茸的、有质感的、有喜有忧有死有生的人世间去;说到底,他最终的目的似乎不在文学本身,而在由文学为载体所承载的某种理想或者信仰,或是如他所喜言的“道”吧。也因此,他的所谓文学批评写作,大多是借文学之矛猛攻现实人生之盾,而文学在他手中也便成了随心所欲的“如意金箍棒”,很难中规中矩,而是天马行空,恣意驰骋。其实这与周明全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他曾自言:“三十多岁前的我,正是老村在文章中说的哪个样子,有太多无处宣泄的情绪压迫着自己,时常有种窒息的感觉。喝酒、打架、追女孩,可以说,那阵子我无恶不作。我的同事,小说家阿闻就时常说,我身上充满了匪气。”[8]也许正因为生命里已经拥有了如此丰富的压抑和痛苦,他又能秉持一种卑微、谦逊甚至忏悔的姿态,通过一己的思考将这些压抑与痛苦进行反刍、反思和追问(他曾不止一次地自言对虚度时光的懊悔和对读书的渴求),从而获得了一种可以不问对与错,但求态度真和诚的批评品质。正如他自己所言:“能直面自己灵魂的人,能自我揭短的人,在面对作家和作品时,自然就能客观地说出来自己的感受,不太容易受这样那样的影响。”[9]正因为他敢于敞开自我的胸怀,所以也就敢于与作家作品坦诚相待,无论如何,他都要将自我的感受和意见掏心掏肺地拱手托出。也由此,周明全特别强调他对理论性的批评划分毫无兴趣:“在我眼里,只有好的文学批评和差的文学批评之分。……评论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正常的人,这个要求似乎太低,但问题是,现在不少评论家就是鬼。”[10]他特别痛恨那些说着“鬼话”的丧失了道德底线的所谓文学批评家。
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使然,使得周明全对文学批评真挚品格的追求十分执着,批评不倦、追根问底,有时候甚至给人“严苛”之感。比如他对于“中国小说”的提出和阐述,先后大约集中书写了七八篇文章,从各个层面和角度进行阐释,目前仍在做进一步地探究和挖掘,已经引起了众多批评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关注。再如他对作家创作姿态的剖析,进一步展示了他对“真”的批评标准的推崇,在《入世与出世的写作——以阎连科和老村的写作为例浅析》中,他再次表达了对作家老村的认可和钦佩,当然他是对事不对人,他所认可和钦佩的是老村身上那种甘愿淡泊宁静、潜心用文学来呈现历史真实的忠诚和虔敬。他在文章中写道:“文学需要和现实对抗的精神,但同时也需要和现实的对话精神。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和现实对话,能对现实重建提出有价值的思考的作家。”[11]在他看来,众多以文学的方式对当下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对抗的作家,所完成的只是一种表象的模拟,所呈现的也只是一种肤浅的勇气,因此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阎连科的《四书》《日光流年》、贾平凹的《废都》等。他坦陈这些作品带给他的只是灰暗与放纵、苦难与颓败、压抑和变形,它们将现实的苦难进一步放大,放大到令人无可奈何、毛骨悚然进而麻木不仁或自我放逐的地步,然而文学于此的位置何在?文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文学仅仅是为了再次制造更大更多更令人恐慌的苦难和纵欲吗?显然,这样的文学已经缺失了最为宝贵的品质,那就是“面对当下社会的荒诞、甚至黑暗,作家要做的,不仅仅是和现实赛跑的问题,而是要创造。‘只有创造才能战胜黑暗’。”[12]也就是说,一名优秀的作家不仅要善于展示黑暗、引起警醒,而且必须要勇于探得光源、带来光亮,追求“至真”的大道——哪怕它遥不可及、模糊凌乱、甚至于荆棘丛生。人们需要的不仅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惧体验,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创造动力。由此可见,周明全赞赏的不是那种仅仅揭示苦难与矛盾表象的描摹型作家,而是能够以智慧之光穿透黑暗的重重幕帐、不断进取的思想型作家。
总而言之,周明全以真纯与虔敬的姿态直面文学和文学批评,由此他的坚守和追问才显得底气十足,即使他的批评研究中弥散着某种偏执的气质,那也会给人带来某种会心与可爱的感觉。更何况就我对他批评文章的阅读来看,尽管他的文章时有虎虎生气、野生泼辣,但他总能一语中的、切中肯綮、逻辑严密、剖析到位。比如他的《贾平凹何以抛弃性书写?——兼评贾平凹新作〈带灯〉》[13]一文,既别辟蹊径、点中要害,又高屋建瓴、以人带史,将个体之作家与历史、时代进行了勾连和打通,取得了很好的批评效果。文章先通过追溯揭示出“中国文学‘性书写’的历史脉络”,进而分析了贾平凹个人的性情与阅读对他这种书写的影响。然后剖析“贾平凹的性书写何以惹来非议”?认为他的书写过于直露变态、夸大其词,甚至沉溺其中故弄玄虚。既然惹来了非议,作家的压力肯定很大。所以紧接展开的是“贾平凹放弃性书写的动机初探”,一方面是作家主观的调整,另一方面是后工业化时代网络、影视及声光化电等多媒体冲击下文字载体的逐渐没落,逼使有上进心的作家必须转型,从商业化写作回归到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学本身,于是才出现了“带灯”这样以思想情感和生活细节而不是身体与性来取胜的女性人物形象。由此展开对小说《带灯》的解析,得出了“不夹杂性的带灯更人性化”,更值得尊敬和思考的结论。文章最后提出了“不再性书写后的贾平凹何去何从”的问题,从生命成熟和智慧渐开的层面,周明全认为“只要贾平凹不要功利,我想,放弃性书写后,他能更好地贴着土地书写,写出优秀的中国小说。”[14]整篇文章史论互助、纵横舒展、开阖有度、清晰明了,读后令人茅塞顿开、如沐春风。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发现,周明全的文学活动十分丰富多彩,绝非我这未曾谋面之友可以面面俱到、了然于胸。以上所言也只是我阅读其大作后的浅识陋见,挂一漏万甚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都是我应负的责任。总而言之,我认为当下文坛尤其是批评界特别需要像周明全这类“侠客型”的健将,期待明全兄大作不断、好文连连!
于京一: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1]如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周明全:《“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社,2015年版。
[3]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文学课堂之五:《“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讨论纪要”,《青年文学》,2015年第12期。
[4]周明全:《可以无视,但不会淹没》,《名作欣赏》,2012年第12期。
[5]周明全:《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
[6]周明全:《谈中国小说创作的文学性》,《上海文学》,2014年第12期。
[7][8][9][10]李德南、周明全:《开拓新路,正在崛起——对话“80后”批评家周明全》,《滇池》,2014年第9期。
[11][12]周明全:《入世与出世的写作——以阎连科和老村的写作为例浅析》,《名作欣赏》,2016年第1期。
[13][14]《贾平凹何以抛弃性书写?——兼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山花》,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