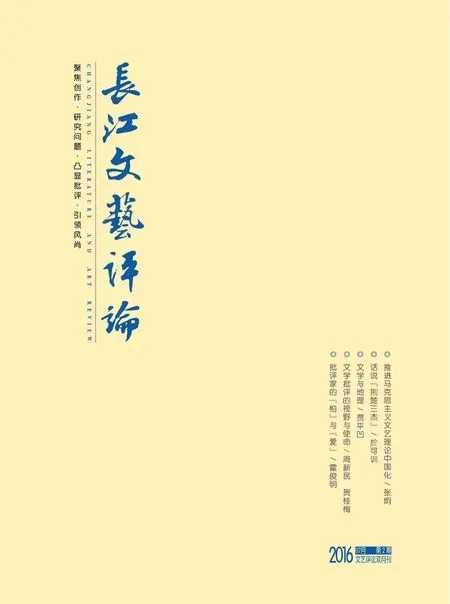批评家的“怕”与“爱”
——周明全的“批评”性格与精神面影
2016-11-25霍俊明
◎ 霍俊明
批评家的“怕”与“爱”
——周明全的“批评”性格与精神面影
◎ 霍俊明
点燃一根烟我蹒跚地向江水中走去
鱼啊虾啊早抛下澜沧江跑到沸腾的火锅架着木炭的铁网上去生活而冷落了江水
我站在齐腰深的水中
孤独恐惧像版纳九月天的阳光无所不包地向我袭来
远处时隐时现地传来一串串清脆的笑声
可我能感受到澜沧江的不安与愤怒因为我站在她体内能听到她的心跳
——周明全《澜沧江》
“周明全写诗。”我必须将这句话放在本篇文章的开端,在我看来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句话。这倒很像是古代章回小说和评书的开场诗,“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宇月,也难如钩也难圆。”正是因为周明全的诗人特质和精神内里,我第一次见到周明全的时候就立刻把他和一般意义上“批评家”面孔区别开来。
一
近几年我已经不怎么使用博客和观光别人的博客了,为了写这篇文章的需要我打开周明全的博客,一页一页翻下去,犹如拨转往日光阴的模糊指针。随着时间的不断倒退,在岁月的沙盘上一个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清晰的周明全面影凸显出来。时间的单行道使得一切都有了点萧索的况味和挽歌的底色。当年周明全的博客签名是“浪子周明全”“浪子明全”“浪子无尘”,我对此会心一笑——年轻就是资本,青春就是狂放,少年本是多情郎。我看到2008年周明全参加某活动时的一张照片。格子衬衣,牛仔裤,他的左右是两个傈僳族女孩——十足的美女。明全在画面里欢笑,他的手搭在两个女孩的肩上。实际上很多时候,一些人即使再年轻也不敢公开将手搭在女孩肩上。再一年前,2007年在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仍旧穿着格子衬衣和牛仔裤的周明全对着仿古建筑上影视美女明星的招贴画做出亲吻的动作。明全这么做了,因为他是透明的。很多人遮掩,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难以透明罢了。
那么,接下来还是说说周明全作为“评论家”的一面吧!在我看来,一个人成为所谓的评论家必然有其起点和某种渊源,像周明全这样近几年突然冲杀上文坛的更有其必然的动因。我想,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流浪”和“动荡”——可能更多来自于精神层面,实际上这在当下中国年轻人中多少成了普遍性的命运。我想到几年前的一个难眠之夜,一个年轻人在昆明发出的关于颓废和不安的自言自语——“这个冬天,我很颓废,不,准确地说是因为太幸福,幸福得颓废,幸福让我颓废。终于明白,这个世界,让一个男人颓废的事不单单是那些让人绝望的鸟事,幸福,幸福也会让一个男人颓废。这或许是这个光怪陆离社会的又一个奇观。”(《这个冬天,我很颓废》)我看到暗夜里闪烁的烟头,明灭的脸庞,以及铁皮屋顶上吹了一夜的寒彻秋风。
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必然有敬畏有挚爱,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他是一位举手的赞同者和热爱者,更多的时候又是自由独立人格的默守者。甚至一个优异的批评家必须敢于说“不”,敢于抛出冷眼,他可以对世事颟顸但是对于作家的人心不古必须敢于射出箭簇。这也许就是已经说得过多过烂的那句话吧——批评家的“怕”与“爱”。近日再翻旧书,陈丹青在谈论“大先生”鲁迅时有感于五四那个特殊的时代说过这样的话,“翻开五四那一两代人的影像,单模样摆在那里就是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们不能比的”。陈丹青的这话并非没有道理,文如其人,人面如心并非诳语(尽管也不尽然)。但是一个时代的风骨都是从一个个文人的面影、骨骼和文字建筑中合力完成的。我想,大抵如此。那么这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面影、面孔和精神范儿在哪里?其精神性格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是让人满意还是如此不堪?由此,我不由得想到了云南的几位诗人和朋友。而在青年一代做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当中,云南我想到的就是周明全。在闲聊甚至公开场合,我听到不少的人说周明全像高晓松。这种娱乐化的比附实际上我并不以为然。就像说中国的某某诗人是西方的某某诗人一样,总觉得缺少了底气和自信。实际上从个人交往上而言,在我的印象里,周明全从来都不会是另一个人或是某个面孔的翻版,他就是独特的自己。这种独特不仅来自于近年来他对“70后”尤其是“80后”青年批评家在出版和研究方面的大力推介,来自于他在系列学人和作家访谈中所呈现的精神世界的相互碰撞,而且还来自于他在与同时代人的切实交往中所建立起来的朋友甚至兄弟般的信任感。尤其是后者,在一个写作和批评从未如此浮躁、功利和短视的时代显得愈益重要。做人和为文都能够让我信任或折服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寥寥可数,周明全是其中的一个。朋友之间的交往甚至信任可能是无来由的,有的第一眼就建立起足够的信任。
出于好奇,我在互联网上搜到了周明全的出生地——云南曲靖的沾益。当年秦修五尺道,当年诸葛亮南征,当年的驼峰航线卸货点,而今这里是烟草基地、药用花卉基地。我和周明全都出生于中国的农村,这一点使得我们有共同的精神母体和血缘。想想,我和周明全还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我们在中学阶段都是报考过绘画专业的(我是中考,周明全是高考),专业分数很高但最终都并不如愿。如果我们当年都成了入流或不入流画家,就没今天文学上的什么事了。
有时想想,人生的偶然性会让人不寒而栗、浑身惊悸。
第一次见到周明全是在2014年昆明的冬天,如今转眼快两年过去了。那个夜晚我们在一个土菜馆喝了很多当地的土酒。实际上那晚我有些心事重重,本该不堪酒力,因为那时我的恩师陈超猝然离世没多久。但是那晚喝了很多酒,事后想想,有些可怕。居然当时是一杯杯(口杯)喝下去的,竟然少有的没醉(我确实没有酒量,但有点酒胆,有时候敢于乱中取胜)。我在酒桌上的挑剔也是朋友皆知的——只和好友至交喝酒,反之滴酒不沾坐山观虎斗。那晚,还在雷平阳的书房趁着喝酒后晕晕的状态胡乱涂鸦,现在想来只是平添惭愧不安罢了。
那一夜翠湖的秋风尽吹,那一刻我正在一点点认识这座高原上的写作者。那时我想到了周明全在一篇访谈中说过的一句话,“说实在的,我感到很遗憾,很少读云南作家的作品,和云南文坛也没有多少交际。说句得罪人的话,我个人觉得,云南是一个搞创作的好地方,但却不是一个搞文学批评的好地方。”
尽管这句话不一定周全和尽然,但是我喜欢这种真诚、直接,而包括很多青年评论家在内却早已经安于世故,学会了明哲保身、绕弯子和虚晃一枪。由此,我可以说周明全是值得信任的,这既与他的为人有关,又与他的做研究的出发点和态度有关。我在周明全这里看到了花束,也看到了夜晚闪着寒气的笔杆。
二
从代际的视角出发,周明全对青年批评家的推介是同代人中少见的,甚至有些独一无二。“时代”“代际”“同代人”在周明全这里并不是泛泛的甚至虚化无着的,而是直接建立于自己的批评话语和实际行动之中。
对于很多少年即谋得大名或一夜成名的那些作家而言,评论家的成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甚至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在文坛算是站稳了脚跟。而周明全对于“80后”作家和批评家成长速度的巨大反差更是感同身受,甚至不满于“80后”一代批评家的长期“缺席”状态。
评论家的成长缓慢不仅与个人能力和积淀有关(“诗有别才”“诗有别趣”同样适应于评论家),还与批评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有关。实际上从文学的产生之日起,文学批评就遭受到了反复的争议,甚至有人认为批评家就是寄生的一种动物,一种毫无创造性的应和者。包括布罗茨基也对文学评论的角色提出了善意的批评。确实,当我们看看当下的批评家的作为,再看看布罗茨基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诗歌批评家所作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的时候,对批评家类于“罗盘”角色的疑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看看当下吧!很多的评论者成了教书匠、掉书袋和西方文学辞典和老生常谈的术语、引文的贩卖者,有的则成了新媒体上频频露面实则短命夭折的快枪手,而真正能够通过批评将当下和历史以及个人勾连起来的批评者只能是少数中的少数。而近年来周明全对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推介(比如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80后”批评家年选),比如出版、访谈和个案研究,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出版、访谈和研究能够三者合一、相互支撑、彼此打开实则不易,而恰恰周明全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一代人的事儿也许只有深处其中的同代人才能完成。这是历史的惯性和时间法则使然。这让我想到的是2004年吴义勤说过的一句话,“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来了,但是对上一代人怀旧、挽留、痴情甚至有些怨艾的目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与奋斗视而不见。”如果视线再继续拉伸得远些,五四那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都是由五四那代人自己完成的,如果等到后来者进行历史尘沙的挑拣则简直有些痴人说梦罢了。早在1930年代初期,刘半农就道出了一代人迫近的历史沧桑感,而这种沧桑也仅仅是新诗发展短短十余年时间所造成的,十年前的新诗竟已成为“古董”了。这也不能不使“当代”书写历史的行为带有深深的焦虑感和迫切希望梳理历史的复杂心态,“这些稿子,都是我在民国六年至八年之间搜集起来的。当时不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了。那一个时期中的事,在我们身当其境的人看去似乎还近在眼前,在于年纪轻一点的人,有如民国二年出生,而现在在高中或大学初年级读书的,就不免有些渺茫。这也无怪他们,正如甲午戊戌,庚子诸大事故,都发生于我们出世以后的几年之中,我们现在回想,也不免有些渺茫。所以有一天,我看见陈衡哲女士,向她谈起要印这一部诗稿,她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1]所以,在“当代”语境中无论是史料整理还是历史叙述都带有不可避免的“见证者”身份。
从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写出影响甚巨的《代沟》之后,“代际”研究就从来没有被冷落过,尽管争议之声也并未中断。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代际概念和划分不是仅指生理年龄,同时也涉及文化特征和社会意识。那么就“80后”而言,这代批评家和前一代或前几代的批评家相比起来在批评方法和精神内质上有没有差异?如果有差异又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有时候代际有其过渡期和模糊性的一面,而代代之间的差异是否就是像文学史家指认的那样界限分明,一目了然?是否代代之间就更多的是一种“断裂”关系?每一代人在成长期是否都有精神的“父亲”?精神成人之后是否都有“另立门户”的“弑父”般的冲动?代际之间的关系远非黑白界限分明那样的简单,而是相当复杂,并且应该注意到即使是同一代之间也是有其差异性和不可消弭的个性的。在我看来英雄启蒙话语和精英意识以及更为广阔的介入能力在“80后”一代批评家那里有弱化的趋势(当然不是全部),而这成了包括周明全在内一部分批评家的焦虑。比如杨庆祥一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比如沉默的复数、小资梦应该惊醒、挫败感等等,我认为这些关键词在“80后”的批评中应该一定程度被强化。
周明全的《“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算是第一本整体性意义上的“80后”批评家的书,但是在社会学的命名上比“80后”的命名晚了十多年。还有一句更残酷的话令那些批评家们有无形的挫败感——乔治·斯坦纳说过“文学批评是短命的行业”。当然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我是比较早知道周明全《“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这本书的出版计划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卡夫卡。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上午世界大战爆发,下午去游泳。”这引起过巨大争议,因为这体现了作家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龃龉和矛盾。我觉得作为批评家除了书本、知识构成的精神生活,还应该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可惜,这么多年我们的批评自身并没有注意到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孰轻孰重。
如果批评家没有发现能力、命名能力、自省能力和挑战能力,批评家的“批评”就会变成软腻肉麻的互相吹捧。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批评缺少的正是真正意义上的争鸣和“批评”,更多的是自说自话,商榷、争论甚至争吵都罕有其声。与此同时,“说好话”的笑呵呵的批评家们挤满了会场、课堂和咖啡馆。这跟文学家批评能力和底线的丧失有关。而周明全正是从现场感和历史意识出发在整体意义上对“80后”一代批评家进行认定、梳理、辨析和研究,尤其是对一代人的现实处境、知识结构和成长路径的总结是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这是具有体温的文字,也具有一代人历史感和时间焦虑的精神症候。而对于同时代人的研究,很容易成为哥们兄弟似的“一叶障目”,很容易“好处说好”,却很难“坏处说坏”。也就是因为切实的人际交往以及某种一代人共同目的和方向的趋势,很难在同时代人身上一碗水端平,实则很难客观、公允。而就“当下”和“同代人”而言,更多的批评家很容易陷入“执于一端”的偏执和狭隘的泥淖之中,而周明全则是清醒的、自我反思与校正的,具有反省意识和自察能力,“肯定又盘诘,亲和又拆解”的立场因此显得格外重要。在这一点上,周明全提前做出了反思并且对“80后”一代人的批评处境、研究能写、批评态度以及不足之处都进行了有力的提请,“但是,作为‘80后’批评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甚至问题。比如,‘80后’批评家过早地‘老于世故’,一旦小有名气,就奔波在各种研讨会、新书发布会上,不注重自我的学习,丧失批评家独立的人格”[2],“从文体上讲,为数不少的‘80后’批评家们也还是按照传统的学院派要求在作文叙事,以致有点点未老先衰,手持檀板,一阙一段地唱着讨人欢心的谀辞”[3]。
关于一代人的研究,我在做“70后”先锋诗歌研究《尴尬的一代》那几年深有感受且有难以置喙的无力感,甚至因为评论了某人而忽略了他人而遭致同时代人的不满。但必须强调的是,同代人叙述同代人的不可替代性是毋庸讳言的。当年的马尔科姆·考利为同代人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文学流浪生涯》,而考利所做的正是为自己一代人的流浪生活和文学历史所刻写的带有真切现场感和原生态性质的历史见证。
多少年过去,一代人的回响仍在继续。
三
实际上关于同时代人的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文章已汗牛充栋,而我更对周明全的系列批评家个案访谈文章感兴趣。我几年前曾经说过,“一代人更是一个人”,个案研究的意义显然不容忽视。
周明全这些访谈主要集中于《名作欣赏》《滇池》《边疆文学》《创作与评论》《文学报》等,都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我看来,访谈是一种特殊的批评和研究文体,有细节、有温度、有故事、有看头,同时又有独特的切入视角,研究者和被访谈人之间直接的对话或者磋商更容易激起思想的火花。透过这些文字,我看到文本世界中的周明全敏锐而有锋芒,这一锋芒直指作家和评论家的问题和要害。平心而论,我喜欢周明全在访谈和研究文字中所建立起来的个人“性格”,而没有一般青年研究者的那种半生不熟的“知识化”和“假学院派”作风,而是直接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和问题意识以及整体的精神境遇出发。这种不落窠臼的研究方法多少与周明全的经历有关,他并没有像同时代评论家那样从学校本科、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一路的“规训”下来成为“职业批评家”“学院批评家”。他的报人和出版人经历以及他的其他文体的写作经历使得他的研究角度和出发点具有迥于他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意志,“我不太喜欢那些故作高深的文学评论,动不动就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一大堆主义,从头至尾都是巴赫金说,别林斯基说,唯独没有什么说。这样的文章,对文学史的研究梳理可能还有点价值,但对具体的文体,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4]从这一点上来说,十分难得。这使我想到了我的恩师陈超先生。尽管身处学院和高校之中,但是陈超对“掉书袋”和“填表教授”则是嗤之以鼻,而是在始终围绕着“当下”“噬心的时代主题”中以个人风格极其突出的话语方式将诗歌批评在文体学意义上提升到自觉的高度——“熟悉我诗学论文的朋友会注意到,我的诗学研究不是从理论中确证理论,我始终有着描述‘当下’的热情。我写作的个人方式,更多是介于诗人和批评家之间,类似于快乐的自由撰稿人,而非中规中矩的理论家。这种话语立场,使我写出了一种性质含混的文体。我的确更偏爱这种诗性随笔式的表述,如果它不致影响到论证力量的话。”
从精神隐喻和批评家的原型出发,我愿意指认周明全是“诗人批评家”。
1961年,艾略特将批评家分为四类,而他最为倾心的就是“诗人批评家”,“我们不妨说,他是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诗人。要归入这一类的批评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
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周明全在访谈中的对批评家和作家的“细读”能力和“还原”能力。关于批评家的“细读”能力我在此文中不想赘述,因为在我看来这关乎一个批评家的本职工作甚至良知和道义,反过来一个连基本的“细读”能力都没有的批评家是值得信赖的吗?或者说这样的人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批评者吗?与“细读”相应,周明全曾经在2015年用一年的时间集中阅读了百余部现当代的小说。这种阅读对于一个评论者的视野、整体感和问题意识的提升是必然的。
与此相应,我喜欢周明全访谈和批评文字中体现出来的机心、心得、敏识和渗透的感悟力。恰恰是这种特殊性的批评话语方式的难度形成了其日益凸显出来的重要性、有效性和独特的诗学禀赋。这使我想到的是当年的李健吾。他感悟式的批评方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算得上是绝对的“少数者”或者“异秉”。也就是说没有特殊的诗学禀赋、创作心得和“细读”能力以及澡雪性情的人这种方式不得为之,也不可能为之。
说说周明全的“还原”能力。
具而言之就是没有从庞大的文化体系和精英立场出发,而是将“批评家”还原为“人”。这种不刻意拔高、任意渲染、肆意美化的具有生命刻度的还原方式正是回到了文学和批评家的起点。这印证了近年来投身文学批评的周明全所倾慕的批评方式——“有难度的批评”“同情之理解”。当周明全公开宣称和指出当代作家的硬伤是“文学性的缺失”,对此我深为赞同——在一个比拼技术比拼故事“好看”的时代众多作家缺失的正是写作的诚意和文学性。实际上“文学性”在周明全这里并不是单纯指向了“美学”“技术”“修辞”,而是强化了写作者本应具有的那种写作的初衷、精神姿态和对文学本体性依据的尊重和创造。是的,这让我想到的是那句我们早已经烂熟于心的话——诗歌不是修辞练习,而是精神的淬炼和灵魂的一场大火。想想,现在的写作者是为什么在写作呢?当马尔克斯在晚年说出“活着是为了讲述”,那么当下的作家和诗人有哪个敢于说出——活着是为了讲述,讲述是为了活着?思想性和精神性的缺失最终关乎的正是“文学性”“人性”和写作者的本心,而就当下的具体写作情势来看这还直接指向了写作“现实”的难度以及写作自身的种种限囿,比如作家们急于表达这个时代的苦难、欲望和伦理化诉求,每个作家的道德感似乎都那么强烈而近乎前所未有。由此出发,我认同周明全的说法——“我认为,文学必须是对生活的严肃审慎的思考,同时又能飘逸轻盈地抽身于现实之外,而不是对生活作自然主义的再现”。与还原能力相应,从作家的个案研究我想到了老村的《骚土》。周明全近年就这篇“过去时”的小说本文进行了带有挖掘和还原的再次考察,有很多观点值得批评家们重视和检省,“前些日子,我读到作家老村的《痴人说梦》。这样一本能够将作家自己真实生命状态展现出来的作品,居然在众人的阅读中无声无息,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不仅要问,这是文学的问题还是读者的问题?我想是不是老村的真实与鲜活触碰到了某些作家的虚饰以至于虚伪的痛处?”(《让我们的文学鲜活起来》)。因为周明全的缘故,我曾与老村见过两次。我的观感不必多说,老村和周明全在我看来是互相视为知音的——“他对《骚土》的分析许多地方有我写作时不曾想到的地方。如果当时有他今天对我《骚土》的感受也许就不这样写《骚土》了。可能会写的更开阔一些。这篇评论无疑是我《骚土》出版以来,最有分量的一篇。周明全有南疆人的率性,朴实,爱喝酒,好玩,但很神,居然能看透《骚土》,真的神人一个。不久,文章被《名作欣赏》刊发。我不少文学批评界的朋友看了文章后,都很惊讶,都觉得明全将《骚土》被隐没多年的文本价值,给挖掘出来了。”(老村《潜伏于文学内核的文学探子》)
一个作家,终生能够遇到这样一个知音式的批评家应该足矣。
有了还原能力,一个批评家说话才会有底气,说出的话才真实可感、值得信赖。浅阅读、浅写作、浅批评,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但也许从未像当下这个新媒体和自媒体当道的时代这样刺眼而虐心。缺乏常识的批评家不在少数,缺乏诚信和人格的批评家又有多少呢?周明全在他的小说批评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是“中国小说”。是的,“小说”和“中国”共置呈现的时候,有那么多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批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让我们对批评家这一“行当”和“从业者”多少有些失望甚至不满。
连日来,暑热的北京在下雨,端午节当天的下午冰雹突至。冰雹砸在窗户和栏杆上竟然如节日的爆竹噼啪作响。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我们与身边的世界和自然之物离得过于遥远了。无论是生活中的人,还是作为一个写作者、评论者和阅读者过于依赖于新闻化和屏幕化的现实了。这成了他们唯一的现实。由此,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成名已久的作家或者已经谋得暴名的年轻作家已经集体堕入到这样的现实中去了。生活宽广但是又很具体细微,甚至会因人而异,而作为一个阅读者来说有时候文字如热锅烤蚁,有时候又被这个时代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弃之如草芥。心怀文字的人你见过,焦虑无着的人我们见得更多,但是对于怀着敬畏和爱护来看到这个时代文学的人也许并不多。至于一个评论家“怕”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到现在已经不必我再次说出。这让我想到周明全对房伟的那篇访谈,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房兄早年做过屠夫”,我不仅哑然失笑。我喜欢这种提问方式,最本质地回应了“人”“生活”“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我当年曾经在北方小镇的冷冻厂做过临时工,当时不会想到多年后自己会成为一个天天和诗歌、文学打交道的人。但是,话说回来,那个小镇,那段生活必然与我今天的命运不可分割,甚至每一分钟我都会在文字中滑向那段乡村岁月。这种切肤的体验必然会对与此相关的其他人的文本阅读有不一样的感受。
文学观和人生观,有时候恰恰就是从一个小镇、一个“屠夫”那里建立起来的。
文章就此打住吧!这个时代“短平快”的文字更惹人喜欢,那些端着手机的人早已经不耐烦了!
翠湖的西伯利亚海鸥今年还会再次飞来的。它们善于飞翔,有方向感,它们有巢穴,也有中途可供取暖的落脚地。
鸟犹如此,人却未必尽然。
霍俊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注释:
[1]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见鲍晶《刘半农资料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
[2]周明全:《绝境突围》,《创作与评论》,2015年4月号下半月刊。
[3]周明全:《脱“代”成“个”终有时》,《名作欣赏》,上旬刊第7期。
[4]李德南、周明全:《开拓新路,正在崛起——对话“80后”批评家周明全》,《滇池》,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