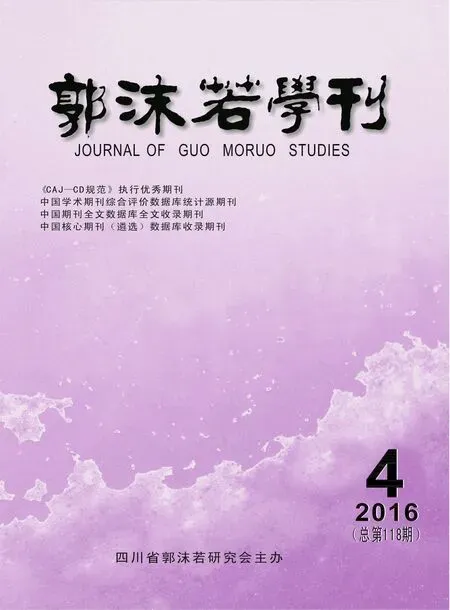艾芜的开创性、独特性与“标本”价值
2016-11-25张建锋
张建锋 杨 倩
(成都大学,四川 成都 610106)
艾芜的开创性、独特性与“标本”价值
张建锋杨 倩
(成都大学,四川成都610106)
艾芜开创了“中国流浪小说”的先河,是“行走文学”的先驱者。艾芜的文学创作是“主旋律”多样化的成功体现,题材的特异性、“另类”人性的书写、艺术的抒情性和“跨文化”的向度,构成艾芜的独特性。艾芜的文学创作从1930年代纵跨至1980年代,是我们认识滇缅边地、川西坝子社会历史变迁、时代特征的文学“标本”。在地域文学的版图中,艾芜的作品具有“标识”岷沱流域的价值。艾芜在“当代”的文学创作,是见证时代发展的文学“标本”,艾芜成为“跨代”作家中不可多得的“标本”作家,其创作是研究“跨代”作家“身份转型”的文学“标本”,具有特别的“标本”意义和价值。
艾芜;开创性;独特性;“标本”价值
《艾芜全集》于2014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联合推出,共19卷1000万字,是目前艾芜著述的最权威的文献集成,为人们研究艾芜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文本资源。笔者拟从开创性、独特性、“标本”价值等方面略论艾芜的文学地位和作品价值。
一、艾芜文学创作的开创性
艾芜是“吃‘五四’的奶长大的”,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无愧于时代的作家群体。艾芜的文学创作开始于1931年,《南行记》初版于1935年,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我们熟知,《文学丛刊》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影响广泛的、著名的大型文学丛书,第一集除了《南行记》外,还有鲁迅《故事新编》、茅盾《路》、巴金《神·鬼·人》、曹禺《雷雨》、沈从文《八骏图》、张天翼《团圆》、吴组缃《饭余集》、丽尼《黄昏之献》、鲁彦《鼠雀集》、卞之琳《鱼目集》、何谷天《分》、萧军《羊》、靳以《珠落集》、郑振铎《短剑集》和李健吾《以身作则》。《南行记》与这些作家的作品并列,体现出自身的文学地位和艺术价值。
《南行记》出版后颇受读者的欢迎,并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1936年3月周立波在《读书生活》发表《读〈南行记〉》说:“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照:灰色阴郁的人生和怡悦的自然诗意。在他的整个《南行记》的篇章里,这对照不绝的展露,而且是老不和谐的一种矛盾。这矛盾表现了在苦难时代苦难地带中,漂泊流浪的作者的心情:他热情的怀着希望,并希望着光明,却不能不经历着,目击到‘灰色和黯淡’的人生的凄苦。他爱自然,他更爱人生,也许是因为更爱人生,他才更爱自然,想借自然的花朵来装饰灰色阴暗的人生吧?”[1]385周立波看到了艾芜作品中“灰色人生”与“自然诗意”交织的艺术特质。1936年6月郭沫若在《光明》发表随笔《痈》,其中写到:“我读过《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人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2]38《6南行记》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肯定了艾芜的创作潜力。1937年6月20日黄照在《大公报》发表《〈南行记〉〈夜景〉》,高度评价到:“我觉得沈从文、吴组缃、蹇先艾、芦焚、艾芜、萧军这几个人大部分带有极浓厚地方色彩的作品,为文学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片天地同都市上的人十分生疏,然而却使他们畅快的呼吸到一种异常新鲜活泼的空气;这几个人之出现于文坛,在他们个人即或没有惊人的成就,无疑的将给予囹圄在都市的文学以很大的刺激和影响,至于给读者们身心的补益那是不消说了。”黄照把艾芜置于1930年代“地域色彩”浓厚的作家群体里,剖析了艾芜具有的高尔基一样的特色,“他把一种他所过目不论社会的自然的形象搬到了纸上重现,在重现过程中把握住原物的气色”。[3]391刘西渭(李健吾)在评芦焚的《里门拾记》时说“:沈从文先生的《湘行散记》,艾芜先生的《南行记》,把我们带进他们各自记忆里的传奇然而真实的世界。……读过《南行记》,我们爱那群野人,穷人,苦人”。[4]488-489黄照、刘西渭都捕捉到了《南行记》在题材、人物方面的开创性。《南行记》出版之前艾芜已出版了《山中牧歌》、《南国之夜》、《漂泊杂记》,待《南行记》、《夜景》问世之后,艾芜成为文学新星,由此奠定了艾芜在左翼文坛的地位,成为“左翼新人”,鲁迅甚至认为艾芜是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艾芜的《南行记》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鲁迅、郁达夫等人开创的抒情小说向前推进了一步,《南行记》等成为1930年代浪漫抒情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南行记》开创了“中国流浪小说”的先河,是可以与高尔基等人的“西方流浪汉小说”媲美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艾芜是“行走文学”的先驱者。
艾芜在写作过程中,虽然受到过高尔基的影响,但是,艾芜与高尔基还是各不相同的,不可简单地认为艾芜的小说是高尔基流浪汉小说的“翻版”,而忽视艾芜的开创性和独特性。艾芜与高尔基都钟情于流浪,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自转”,自成一格。艾芜与高尔基是情感共鸣,是精神相通,而不是艾芜围绕着高尔基“公转”,是高尔基的“反光”。艾芜与高尔基的文学道路都缘于流浪,这个起点的意义在于,他们从文化的边缘起步,注定了他们与中心、主流、正统异质的文学倾向。南行滇缅与漫游俄罗斯成为艾芜与高尔基文学创作的源泉,他们都以自身的流浪生活为素材,所写的事情当然不会件件属实,但那美丽的风景、奇异的人生和斑孄的世界,尤其是那真挚的感情和内在的思想,却都是真实的。这突出表现在带有自传色彩的“我”的形象上。高尔基笔下的“我”是一个漫游者,折射出高尔基的内心思想。高尔基以“讲故事的人”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并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形象,就是心中炽燃着爱火的“引路人”形象。《南行记》中的“我”的形象,用传统的话语概括就是一个“青年书生”,用“五四”的话语概括就是一个“新的智识者”。“我”的身上烙印着“五四”时代的痕迹,处于成长之中,青涩而可爱。这个“我”又不同于“五四”高潮中的“狂人”、“天狗”形象,鲁迅、郭沫若笔下的“我”是历史“青春期”的时代人物的典型,而艾芜笔下的“我”是走向社会、在时代中成长的青年典型。这种对比,恰好反映出艾芜作为“五四后”一代作家的特性,体现了艾芜对新文学的贡献。
二、艾芜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1930年代被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就文学而言,左翼文学与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等“杂语共生”,显示出那个时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艾芜在起步从事文学创作时,曾经有过“迟疑和犹豫”。他与沙汀一起写信向鲁迅求教小说创作的问题,鲁迅给予了热情的回复,这就是那封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艾芜、沙汀谈到了他们当时的创作特点和创作困惑,他们写到:“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同时,艾芜、沙汀还对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表示了他们的不同看法和他们自己的创作倾向:“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鲁迅在回信中充分肯定了艾芜、沙汀的小说创作对于目前时代的意义,并明确指出:“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同时鲁迅告诫艾芜、沙汀:“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5]366-369在得到了鲁迅的指点后,艾芜坚定了自己创作的信心,没有去跟流行的“普罗作家”的“风”,创作那种标语口号、贴标签式的“革命文学”,而是尊重写作特性、艺术规律,走自己的创作之路。艾芜和沙汀、周文、张天翼、萧红、萧军等一样,在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挖一口深井”,以特有的文学质地、文学风貌而引人注目,成为“左翼新人”。陈方竞在《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上)》中认为:“这批有‘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之称的青年作家最重要的作品的集体性出现,在左翼文学发展上是有标志意义的。”[6]45-46在我看来,艾芜等人的出现及其文学创作是“主旋律”多样化的成功体现,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都具有鉴镜意义。
艾芜的文学创作没有去写那个时代流行的知识青年苦闷、躁动的心灵,没有去写那个时代时髦的工人阶级激烈、愤激的“革命事件”、“暴动行为”,而是以自己亲历滇缅的南行生活为题材,“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来刻画,融入自己的感受、体验,融入南国边地风光、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融自然景物、故事、人物描写于一炉,半叙景物,半涉人事,在类乎游记性的抒情写景中,又不失去故事情节的兴味,把故事的魅力,抒情写景的感染力,人物性格塑造的形象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从而构成‘南行’小说独特的诗意和意境,开创了现代抒情小说的一种新类型。”[7]347题材的特异性、人物的传奇性、文化的异域性和艺术的抒情性,构成艾芜创作风格的独特性。
《南行记》缘于漂泊与流浪的经历,关注边缘状态和边缘人,挖掘边缘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并以此思考国民性问题。这是《南行记》的独特之处。《南行记》聚焦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边缘状态,即“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生活和人物。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人物活动的空间环境、人物的身份、活动的性质、事物、景物等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艾芜致力于挖掘、表现社会边缘人的“另类”人性。艾芜在社会边缘人身上“发现”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下、文明与野蛮、清醒与愚昧纠结在一起的两重品性和矛盾复杂性。这些与“普罗作家”笔下的“突变式的革命英雄”完全不同,显出了审美的独特性。
《南行记》对国民性的思考显示了“跨文化”的向度。艾芜在流浪过程中形成了随时随地研究人的习惯。通过与缅甸人的对比,艾芜感到中国人需要注入“年轻少壮的血液”。艾芜描写边缘人出没于荒山野岭,呈现最本真、最原始的生命状态,展现出未被“现代文明”所污染的原始的蛮性、野性、天真和快活等特性。他们大胆叛逆、反抗强权、倔强坚韧、野性不驯、蛮性十足,男不管“温柔敦厚”,女不讲“三从四德”,敢于反抗,不受约束,体现出“不安本份”的特性。这样的国民性格正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所缺乏的。艾芜以此完成了对国民性的反思。与鲁迅、沙汀、张天翼等作家相比,“另类”人性的书写与“跨文化”的向度,是艾芜源于自身经历而形成的创作视野。在反思国民性的作家行列中,艾芜具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体现出艾芜文学创作的个性特色、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三、艾芜文学创作的“标本”价值
艾芜是跨现代、当代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艾芜的文学作品折射着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是中国从现代走向当代的社会历程的真实记录。从《南行记》到《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从《丰饶的原野》到《春天的雾》,1930年代至1980年代的滇缅边地、川西坝子的社会面貌、风土民情像画卷一样徐徐展开,是一部形象化的社会史,是我们认识滇缅边地、川西坝子社会历史变迁、时代特征的文学“标本”。
艾芜是独具特色的川籍作家。《南行记》以“异域情调”为文坛关注,稍后艾芜转向描写岷沱流域的故乡,1937年1月即出版了《春天》,之后创作了《端阳节》、《落花时节》、《童年的故事》、《我的幼年时代》、《春天的雾》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描写艾芜故乡川西坝子的景物、人物和风情习俗的。艾芜与现代的川籍作家罗淑、当代的川籍作家周克芹一起,将岷沱流域的地域文化呈现出来,成为别样的文学风景。在地域文学的版图中,艾芜的作品具有“标识”岷沱流域的价值。
新中国建立以后,从国统区走过来的现代作家往往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创作要求,创作上面临困境,很多作家陷入创作危机,作品难产,甚至停产。扫描1949~1979年的文学创作,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跨代”的艺术大师们普遍沉寂,没有多少声音,处于“失语”状态。我们都知道,除少数作家如鲁迅、郁达夫、许地山、柔石、萧红、闻一多、朱湘等已经去世,张爱玲、林语堂、梁实秋等离开大陆之外,绝大多数的“跨代”作家都走进了新中国,生活在红旗下。但是,确实难以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找到他们的身影和存在。郭沫若、茅盾主要从事国务活动、文化管理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时,巴金年方45,曹禺虚岁40,都正值壮年,但巴金没有写出像《家》、《春》、《秋》、《憩园》、《第四病室》、《寒夜》那样的长篇小说,曹禺也没有重现《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的荣光;老舍虽然创作了《茶馆》,却在1966年投太平湖自杀身亡;沈从文彻底改行,放弃文学创作;叶圣陶、钱钟书、沙汀、张天翼、萧军、丁玲……也都没有声气!曾经我们都在问:为什么“现代”写得多,“当代”写得少?为什么“现代”写得好,“当代”写得差?艾芜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艾芜较快地完成了从“现代”到“当代”的“身份转型”。艾芜曾多次深入工厂、农村,并两次重走南行路,去体验前所未有的新生活,表现伟大的、建设新中国、新边疆的劳动人民,创作出《百炼成钢》、《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等作品,成为当代工业题材、边疆题材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南行记》系列小说,成为我们研究“跨代”作家“身份转型”的文学“标本”。
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艾芜“跨代”的“标本”价值。1930~1940年代20年艾芜共创作小说160篇左右,1950~1970年代30年艾芜只创作小说29篇,前者是后者的五倍多。在艺术质量上,《南行记续编》以及后来的《南行记新编》都没能超过《南行记》。艾芜自己说:“我初步研究一下,是解放后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没有弄清楚。一个政治运动来了,领导号召,我也乐于参加,想趁此改造自己,同时也想从运动中取得材料,从事新的创作。如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我参加了,并写了小说。但未完成,我又接到一个号召,要作家到朝鲜、到工厂、到农村,向工农兵学习,我又高高兴兴地参加了。于是未完成的土改小说,已写了五万多字,放到现在,仍然是残缺不全。”艾芜的反思其实代表了“跨代”作家的共同心声,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标本”意义。
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求作家们努力去适应新时代,表现新生活。“跨代”作家们熟悉的题材、生活、人物突然间丧失了“价值”,必须改变“写法”去塑造“新人”,必须重新摸索新的主题和人物观念,重新树立新的文学价值观。“跨代”作家们陡然之间成为“小学生”,要在“政治老师”的领导、引导下学习新的思想、树立新的观念、学会新的作文技法。艾芜曾经写到:“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对文艺工作者往往抱不信任的态度,总以为在旧社会生活过,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强调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一来,就非要下去学习不可。”这对作家的文学创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新的文学观念与“跨代”作家的创作风格、创作个性并不一致,往往处于游离状态。在题材定位上,新的文学观念要求描写“工农兵生活”,而“跨代”作家习惯于自由地描写花草虫鱼、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擅长于描写自己熟悉的某类题材、某类人物(比如沈从文的湘西、沙汀的川西北乡镇、老舍的市民、李劼人的四川嫂子等等),就算是描写过底层人物也并不符合特定的“工农兵”概念。在创作方法上,“跨代”作家普遍采用源于欧美、俄苏的批判现实主义,注重细致解剖现实生活,率真再现现实生活,基于人道、人性、正义、善、怜悯的批判现实生活。这样的创作方法被认为已经不适合反映新的生活,甚至被认为创作动机和艺术作用都存在不良因素。新的文学观念提倡的创作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等。“跨代”作家们在坚持创作时,只能摸索着向新的观念和规范靠近,尝试新的作文技法,努力成为一个“好学生”。艾芜曾经到工厂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创作出《百炼成钢》,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已经相当不错了,但还是受到批评、指责。小说中写了两个有缺点的工人,有人就说:“你应把三个工人都写成英雄人物、模范人物,而且彼此有矛盾,始终和衷共济,这才是我们新中国工人阶级应有的好现象。你写了两个有缺点的工人,损坏了新中国工人的面貌。”[8]303-305由此可见,“跨代”作家们适应新的文学价值观有多大的难度。艾芜在“当代”的文学创作,可谓是“戴着脚镣跳舞”。每一个舞步都折射出时代的印痕,都表现出一个忠实于生活、忠诚于创作的作家心灵的轨迹。尤其是“南行”系列小说,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更是能见证时代发展的文学“标本”。由此,艾芜成为“跨代”作家中不可多得的“标本”作家,具有“标本”的意义和价值。
艾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创性、独特性和“标本”价值,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和深入的探讨。我们相信,随着《艾芜全集》的出版,全方位的艾芜得以呈现,将推进艾芜研究,深化艾芜研究,艾芜研究将会有一个长足的进展。
(责任编辑:王锦厚)
[1]周立波.读《南行记》[A].毛文,黄莉如编.艾芜研究专集[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385.
[2]郭沫若.痈[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黄照《.南行记》《夜景》[A].毛文,黄莉如编.艾芜研究专集[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4]刘西渭.里门拾记[A].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陈方竞.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上)[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7]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8]艾芜.关于三十年文艺的一些感想[A].艾芜全集(第14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
中国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符:A1003-7225(2016)04-0012-04
2016-11-16
张建锋,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四川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杨倩,成都大学图书馆讲师,主要从事巴蜀作家作品及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