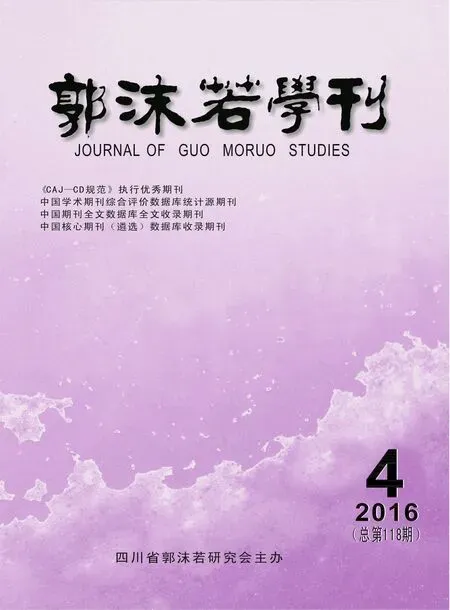革命时代的激情呐喊——郭沫若与贝歇尔比较研究
2016-12-23陈多智徐行言
陈多智 徐行言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革命时代的激情呐喊——郭沫若与贝歇尔比较研究
陈多智 徐行言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1756)
20世纪既是文学革命的世纪也是政治革命的百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郭沫若与德国表现主义诗人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均以笔为刃投身了这两场革命。个人命运与家国时势的息息相关,政治抱负与文学成就的微妙牵扯,个人品质与身后评价的互为表里,在郭沫若与贝歇尔身上展露无遗。而贝歇尔不论是人生经历、创作观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与风格均与郭沫若有较高的相似度。本文尝试主要从二者的身份转换、文艺观念、创作内容及技巧角度出发,探究郭沫若和贝歇尔的相似点。
郭沫若;贝歇尔;表现主义;政治诗歌
一、从反叛诗人到政治活动家
约翰内斯·R·贝歇尔(Johannes Robert Becher)是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诗人之一。库尔特·品图斯(Kurt Pintus)曾将贝歇尔的十四首诗作收录进德国表现主义文学的纲领性诗集《人类的曙光》(Menschheitsdämmerung①,1920)。然而数十年之后,他作为先锋诗人的历史似乎已被人淡忘,如今人们提起他,更多的联想是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民主德国首任文化部长以及民主德国国歌词作者的身份。贝歇尔文集的编者卡斯滕·甘塞尔(Carsten Gansel)曾评价道:“贝歇尔的出身、成长历程、秉性特质、主要经历及个人矛盾的总和也正是20世纪艺术、政治、人性道德所走过的歧途”②。20世纪交替着冲突、尝试和谬误以及“无止境的清洗、更新、崭新的与更优的选择”③,贝歇尔便脱胎于这种种的混乱。1891年他出生在一个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法院的高级公职人员,而紧张的父子关系和截然相左的价值观导致了贝歇尔与家庭的最终决裂。表现主义文学的一大主题即父与子的冲突亦是贝歇尔真实生活的写照。1913年起他开始亲近慕尼黑和柏林的艺术家团体,结识了魏德金德、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拉斯克-许勒等表现主义作家,他作品的表现主义风格也越发浓郁,其主题往往是“厌恶社会与反市侩”④。1916年贝歇尔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APD),但他亲近社会主义思想仅仅是缘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革命运动的纯粹情绪化”共感⑤。1923年,他“开始比较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1]2;1928年贝歇尔成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首任主席,同年加入“革命作家国际联合会”主席团。德国纳粹上台后,贝歇尔先后流亡巴黎、莫斯科,并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多次筹备旨在联合流亡作家的国际会议,但贝歇尔流亡莫斯科时期的经历使他招致了终身的争议。1958年10月贝歇尔逝世。德国统一之后,贝歇尔的政治家身份与作为所引起的争议渐渐盖过他诗人的声誉,德国国内的贝歇尔研究逐渐乏人问津。
20世纪20年代前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中国也正经历着革命浪潮的洗礼。生于1892年的郭沫若同样脱胎于旧式家庭背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处日本的郭沫若以笔为刃投身新文化运动,写出《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新诗,其代表诗集《女神》和贝歇尔的《没落与胜利》一样均致力于摆脱旧体诗歌的束缚,开创“新的形式”、“新的内容”,蕴含“新的知识”、“新的感觉”与“新的思想”,郭沫若更多次坦言对表现主义艺术风格的欣赏与共鸣。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后,郭沫若一跃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1921年6月郭沫若参与组建“创造社”。1923年起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革命高潮兴起与国际革命文学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转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他的创作随之开始了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郭沫若也和贝歇尔一样拥有复杂的政治经历,1926年7月他参加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8月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1928年2月因受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流亡日本。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回国投身抗战,先后就任国民政府的多个官方职务,同时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抗日救亡,逐步成为国统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先后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多个政府要职,并有惊无险地度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波涛,他身后却因种种原因广受争议。
综上,郭沫若与贝歇尔生前身后的经历犹如镜面成像,他们都成功完成了从激进的反叛诗人到政治活动家的转换,但后期围绕他们生活及政治经历的争议淹没了他们曾经凭借创作所赢得的文学成就。
二、表现论文艺观的认同
郭沫若受到德国表现主义思潮的影响早已是受到学界关注的不争的事实,其论文《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印象与表现》《生活的艺术》《文学的本质》等都直接体现出他对表现主义的“共感”和推崇。在《创造十年》中他直截了当地告白:“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破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2]77。在《印象与表现》一文中,郭沫若对表现主义的欣赏更加呼之欲出:
但是如像18世纪的罗曼派和最近出现的表现派(Expressionism),他们是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把自我的精神运用到客观的事物,而自由创造;表现派的作家……要主张积极的、主动的艺术。他们便奔的是表现的一条路。
艺术家总要先打破一切客观的束缚,在自己的内心中找寻出一个纯粹的自我来,再由这一点出发去……才能成个伟大的艺术家,要这样才能有真正的艺术出现。
艺术家的要求真不能在忠于自然上讲,只能在忠于自我上讲。艺术的精神决不是在模仿自然,艺术的要求也决不是仅仅求得一片自然的形似。艺术是自我的表现,是艺术家的一种内在冲动的不得不尔的表现[3]。
表现主义文学的特质,例如激情的呼号、人物类型化、背景虚化、重寓意而非情节、表现内在的自我以及重视“情感的沟通(emotionale Kommunikation)”⑥等特点,郭沫若不仅十分认同,也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创作和翻译当中,因此对于看重“自我的表现”与“忠于自我”的郭沫若来说,贴近表现主义这一重视社会功用的艺术潮流更多的是出于他内在的需要。且看他在《梅花树下醉歌——游日本太宰府》中的宣言: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我赞美你!
……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还有什么你?
还有什么我?
还有什么古人?
还有什么异邦的名所?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
破!破!破!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4]95-96
而贝歇尔同样提倡作家尽情地表达自我,因为作家的“思想感情差不多是同所写的情景紧密地联系着的”[5]5,不大胆地自我呈现就难以真正的表达,因为“有些感情,只有在艺术地体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很快地感觉得到”[5]8。虽然贝歇尔后期的创作回归了古典的诗节形式,其表达技巧和内涵仍然是现代的,充斥着表现主义泛神论的精神,而泛神论的色彩也突出体现在郭沫若的众多创作之中,二者诗作中共有的要求反抗、决裂、更新的呐喊更是跃然纸上,他们追求的从来不是纯粹的艺术的实现,而是个人与他所处时代的新生。
三、摧毁旧世界的强力呼号
《人类的曙光》初版刊行之际,编者库尔特·品图斯恰如其分地定义并肯定了一类“政治诗歌”:“……这种诗歌……的主题是它所控诉、诅咒、嘲讽和根除的同时代生存着的人的状况,它以可怕的爆发力寻找未来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艺术不能成为诗化的社评,而应该帮助人类去实现完善自身的理想”[6]22,而摧毁旧世界与呼唤新人类也正是郭沫若与贝歇尔共同的诗歌主题。
激情强力的呐喊呼号是表现主义文学创作的一大特征,这一点暗合了郭沫若自我扩张和直抒胸臆的需要,他就是要以铿锵的诗歌语言自由地表现自己,“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4]22。这类创作的代表有《女神》诗集中的《女神之再生》《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以《女神之再生》为例:
——雷霆住了声了!
——电火已经消灭了!
——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已经罢了!
——倦了的太阳呢?
——被胁迫到天外去了!
——天体终竟破了吗?
——那被驱逐在天外的黑暗不是都已逃回了吗?——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
——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他罢?
——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
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
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
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整首诗疑问句与感叹句交替叠现,语言铿锵有力,显示出一种昂扬奋进的风貌,与其说是诗,倒更像是一段情绪激昂的高歌,诗中一律以感叹号结尾的召唤感染力极强,更易激起读者的共鸣。不论古今中外,诗和歌从来不是割裂的存在。这一句句渐进式的激情呐喊在紧紧贴合时代脉搏的同时鼓舞意志激发热情,表现出作者的强烈意志,具体的内容及对客观现实的描绘降到了次位。
再看贝歇尔的诗歌作品,热烈的语调与饱满的激情也同样贯穿了他的创作,他的诗作大多篇幅较长,也许只有这样才足以抒发他充沛的情感。与《女神之再生》几乎完全相同的问答与标点的运用形式出现在诗作《怨与问》[6]211-214中。现摘录部分诗节为例:
黑夜中的猎场——!
为何为何总是总是一再地我在奔跑中碰撞并割断自己的
头——?!
为何你要阴险地撕断那条明亮的直线,我完美而稳健的
行踪——
……
痛苦地被鞭条和刺齿脱掉全身的叶毛?!
为何蓄意用雨水把我渴望的种子糟蹋?!
何时我能够最终解脱,
擦掉妓女们的污垢?!
何时能从我那徒劳击毁的不确定的音区中
终于跳跃出那唯一欢庆的世间音响,
你那赎出的和谐?!
实际上《怨与问》德语原文的节奏感与《女神之再生》更加相符。由于德语与中文构词及表达方式的极大差别,还原原文内容的诗歌翻译往往很难体现出德语本身的简洁与效率。例如“痛苦地被鞭条和刺齿脱掉全身的叶毛?!”一句有十六个汉字与相同数目的音节,而德语原文(Schmerzhaft mit Peitschen und Stachelkamm mich entlauben?!⑦)则仅有七个单词与十三个音节,相较中文译诗有更强的力度。尽管诗的力度有所缺失,但是译诗保留了原作完整的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女神之再生》与《怨与问》的形式几乎如出一辙。正如库尔特·品图斯所评论的:“这种诗歌的质量在于它的强度”。贝歇尔的这首《怨与问》有情感、有内容、有爆发力但又不失张力,是贝歇尔早期也是表现主义文学早期成熟的文学代表作。有趣的是这两首诗的内容恰好又是对郭贝二人泛神论精神的一个例证。《女神之再生》以中国古代的女娲创世神话为蓝本,而《怨与问》则明示或暗示了数十个《圣经》或欧洲异教传说中的典故或人物,两首诗满载着热忱的宗教式激情,仿佛要用一声声“何时……?为何……?”的质问砸碎高悬在世界上空的旧太阳,“欢迎新造的太阳”和它即将带来的新鲜的阳光和希望。
四、从启蒙的诗人到革命的号角
表现主义文学提倡艺术应发挥其社会功能。鲁比讷(Rubiner)曾为政治下过这样的定义:“政治是我们道德意图的出版物”。同时代的很多表现主义者都认为文学应该充当伦理宣传的喉舌,积极地参与到意识形态的政治讨论中去。艺术创作再也不是单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行动的目标。“文学创作需要的不是美,而是有用”⑧129-130。这一观点不仅符合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学观,也符合彼时彼刻时势的需要。而贝歇尔和郭沫若当仁不让的是德中两国政治诗人中的佼佼者。

贝歇尔的代表作《人啊,站起来》和郭沫若《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中的“澎湃的歌声”便是形式、内容、思想三重的相似。
内容上,两首诗均呼吁人的觉醒及崛起,具有鲜明的启蒙精神。前者在抨击资本主义坟墓般黑暗之后,更多地呼吁和平与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和解;后者则旨在唤醒中华大地上沉睡的人们,共同承担人类解放与世界和平两大使命。
到后期,二人的作品都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意识。贝歇尔很多后期的诗仅从题目便能看出与政治或是革命密切相关:《为人民而作的诗》、《工人、农民、战士》、《前进,红色战线!》等。现举《献给二十岁的人》[6]272一诗为例:
二十岁的人!……你们褶皱的大衣
拖过落日下的街道
兵营和商场。把战争拖向终点。
不久它将截住从避难所刮出的狂风,
将王宫宝殿在火海中埋葬!
诗人欢迎你们,拳头似炸弹的二十岁的人,
在你们披着铠甲的胸中,火山似新的马赛曲在摇荡!!
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更像一篇檄文,号召“二十岁的人”去革命、去反抗、去颠覆旧有的权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郭沫若的《上海的清晨》中:
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
面的是劳苦人的血汗和生命!
血惨惨的生命呀,血惨惨的生命
在富儿们的汽车轮下……滚,滚,滚,……
兄弟们哟,我相信:
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
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4]319-320
郭沫若是如此阐释文学和革命的关系:“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我始终承认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不两立的。”[7]37但这种革命文学过于强调文学的宣传和教化功能,忽略了文学的艺术性,一味粗暴地追求“力”的刚强和诗歌的煽动性与刺激性,往往会造成口号标语的堆砌。郭沫若自己也坦承:“只抱个死板的概念去从事创作,这好象用力打破鼓,只是生出一种怪聒人的空响罢了。并且人的感受力是有限的,人的神经纤维和脑细胞是容易疲倦的,刺激过烈的作品容易使人麻痹,反转不生感受作用。”[8]228
必须要承认的是,郭沫若和贝歇尔的诗歌最高成就都不是他们的“政治诗歌”。郭沫若自己也坦承,他主要的两本收录其革命诗歌的诗集《前茅》与《恢复》的艺术成就并不高。不过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二者的政治诗歌确实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用最浅显朴实的语言喊出最有力的口号,触动最广大的普罗大众,如果以此标准衡量,贝歇尔和郭沫若的革命诗歌无疑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五、充满破坏力的语言实验
贝歇尔的一首诗《准备》开头便是:“诗人忌讳闪耀的协调”⑧130。协调一向是古典文学的传统和倡导,无需进一步引证诗歌内容,诗人反叛传统文学理念的姿态便呼之欲出。
贝歇尔在德国诗坛成名,除了他惯于采用奇特的比喻和怪诞的形象[9]312,更在于他有意破坏德语的语法结构——“堆叠名词”、“省略冠词和定语”以及“不断地倒装句子”以期达到“专注于本质”的目的。这一写作方式在表现主义文学诸如戏剧、小说、散文等各类体裁中广泛运用,并进一步发展为一套“词的艺术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洛塔尔·施赖耶(Lothar Schreyer)在论文《表现主义诗歌》中对此进行了如下阐释:
‘这些树和这些花开花了(Die Bäume und die Blumen blühen.)’。省略这句话里的冠词,句子就变得更简短:‘树和花开花了(Bäume und Blumen blühen)’。词语用单数形式句子便显得更加凝炼:‘树和花开花了(Baum und Blume blüht)’。如果将这些词语从语法中解放出来,那么表达就会愈发简练:‘树开了花(Baum blüht Blume)’。而这句话最精炼的形式可被压缩到唯一的一个词:‘开花(Blüte)’⑧155-156。
让我们再来看贝歇尔诗作《衰败》[6]6中的几个诗节:
鲜花,飘飞的青草。
鸟儿,鸣啭歌喉。
……
鼓声。大号轰鸣。
雷电。张牙舞爪的火光。
钦贝尔乐器。打击的音响。
鼓声尖锐。似被击碎。——
这里仅用一系列名词、动词或名词性词组和意象的并置,便生动展现出从青草如茵的婉转歌唱到雷电交加的翻腾躁动变化历程。
郭沫若的很多作品也体现出了“词的艺术理论”的精髓,他在《新生》中写道:
紫萝兰的,
圆锥。
乳白色的,
雾帷。
黄黄地,
青青地,
……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4]157
贝歇尔对词的堆叠技巧的应用与郭沫若相比明显是更加成熟的。在追求精炼、简洁和力度的同时也兼顾了诗歌的内涵,呈现的画面直观、丰富、层次感分明,而《新生》则更像是一幅简笔画,尽管清晰明了,但略显单薄。
再如前文已例举的贝歇尔的《人啊,站起来》和郭沫若《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两首诗作在形式上都使用短语和短句,看似简单粗糙的堆叠和重复,赋予了诗歌一种急促如鼓点的韵律感和令人心潮翻涌的内在张力。原句(Mensch Mensch Mensch stehe auf stehe auf!!!)三个名词人(Mensch)与两个可分动词站起来或起来(stehe auf)的叠现打破了德语祈使句的语法结构,三个德语名词“人”的重复出现完全可以翻译成人们,而“站起身”、“起来”及“起”在中文的祈使句里并没有任何语义层面的区别,因此若以德语原诗为样本,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句式出现在了两首诗里。
结语
约翰内斯·R·贝歇尔是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中郭沫若的同龄人,其创作时间和作品风格与郭沫若十分贴近。《郭沫若全集》中提及的所有对他曾经产生过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德国作家或者诗人,例如尼采(Nitzsche)、魏德金德(Wedekind)、霍普特曼(Hauptmann)等,并未见提及贝歇尔之名,只能得出郭沫若受到德国文学的影响较深,是表现派同路人的结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郭沫若和贝歇尔之间存在影响的关系。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而言,我们只能惊叹类似的历史境况、个人处境、诗人性情、文学接受来源竟能隔着一片汪洋塑造出两位创作理念与风格如此相近的诗人。他们的人生彰显了文学与政治若即若离而又无比微妙的关系。“他是最伟大的诗人,人们这么说并写道。我始终赞同他是最伟大的,毫无疑问;即最伟大的活着便死去的诗人,没人倾听或阅读,但他活着并写着”⑨297。这是针对贝歇尔后期个人及作品最尖锐的批评。围绕郭沫若品格与气节的争议也遮蔽了他早期文学作品的锋芒,当文学创作成为了政治的左右臂,它独特的魅力是有所增益还是耗损,这也许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
(责任编辑:廖久明)
注释:
①德语单词Dämmerung包含两个截然相反的含义,既是曙光也是黄昏。此种取名方式是编者有意为之,详见文章第五节的分析。
②Nikolaus Brauns,Johannes R.Becher-Diskrepanz zwischen Lyrik und weltanschaulichem Engagement(约翰内斯·R·贝歇尔——诗歌创作与政治事业的分歧),München im Sommer 1994,S.1.
③Dr.Wolfgang Näser,Deutsch im 20.Jahrhundert-Becher,Johannes R(.1891-1958):Auferstanden aus Ruinen(20世纪德语-约翰内斯·R·贝歇尔:从废墟中再生),Marburg,2002,S1.
④Nikolaus Brauns,Johannes R.Becher-Diskrepanz zwischen Lyrik und weltanschaulichem Engagement(约翰内斯·R·贝歇尔——诗歌创作与政治事业的分歧),München im Sommer 1994,S.2.
⑤同上,第3页。
⑥Thomas Anz,Literatur des Expressionismu(s表现主义文学),Verlag J.B.Metzler 2002.S.162.
⑦Hrs.von Kurt Pinthus,Menschheitsdämmerung-Ein Dokument des Expressionismus,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2013.S.195.
⑧Thomas Anz,Literatur des Expressionismus,Verlag J.B.Metzler 2002.S.
⑨Eigenhändiger Lebenslauf Johannes R.Bechers von 1950,zit.nach Behrens S.297.
[1]贝希尔,黄贤俊译.贝希尔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郭沫若.印象与表现[J].上海《时事新报·文艺》第33期(1923-12-30).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德]约翰涅斯·贝希尔著,林枚生,善懿译.诗与生活[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6]库尔特·品图斯选编,姜爱红译.人类的曙光——德国表现主义经典诗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9]李伯杰等.德国文化史[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符:A1003-7225(2016)04-0048-05
2016-05-30
陈多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徐行言: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