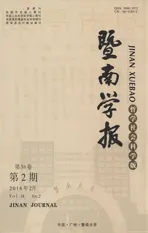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英文著述研究
2016-11-2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6
张 丽(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6)
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英文著述研究
张 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6)
[摘 要]华人移民新西兰迄今已有150年的悠久历史,自20世纪初年开始即有学者从华人海外移民的角度对此现象加以关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西兰华侨华人史得到了海外学术界的重视,涌现出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有关的英文著述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有综合性著作、专题史、口述史、社会调查报告、学术论文等多种形式,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淘金时代的华人史、排华立法和种族歧视、20世纪华人社会变迁以及新移民时代华人社会等几个方面,初步展示了新西兰华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关键词]新西兰华人;淘金华工;新移民
一、研究状况之历史回顾①相关研究可参见吴丹、张秋生的《大洋洲华侨华人研究综述》(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1期),但文中对新西兰华侨史研究的英文著述介绍甚少,只提到了冯吴碧伦的著作。
19世纪中叶以后,华人以史无前例之规模流布到世界各地,正式前往新西兰则始于1866年,首批有组织的华工于淘金热中到达该国南岛之奥塔哥省(Otago),由此开启了华人移居新西兰之漫长历程。华人移居新西兰这一现象,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后大凡探讨华人海外移民史的著述,对此都会有所提及。比如,坎贝尔的《中国苦力向英帝国国家的移民》、麦克尼尔的《海外华人》、潘琳的《炎黄子孙:华人移民史》,②P. C. Campbell,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P. S. King & Son,1923;H. F. MacNair,The Chinese Abroad,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5;Lynn Pan,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New York:Kodansha Globe,1994.等等。此类著述所涉及的主题以华人移民新西兰简况以及新西兰政府对华人移民的应激反应为主,即新西兰政府的移民限制以及华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关于小小的华人群体在新西兰生存和衍化的历史则鲜有触碰。19世纪40—50年代,有一些新西兰当地出版的小册子涉及华人。比如,马休斯的《新西兰华人少数民族》、曾经赴华传教的传教士麦沾恩所写的《新西兰的教堂与华人》和《我们身边的华人》。③A. Mattews,New Zealand’s Chinese Minority,publication unknown;G. H. McNeur,The Church and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Christchurch,1951;G. H. McNeur,The Chinese in Our Midst,Dunedin:PWMU,1951 -1952.
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开创性著述是1959年出版的《纽西兰华人同化之研究》。④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A Study in Assimilation,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59.此书的问世可视为新西兰华侨史研究之肇始。此后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研究大抵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研究成果中较为重要的著述有:
冯吴碧伦的《纽西兰华人同化之研究》,该书简述了华人移民新西兰的历史过程、排华立法的出台及其后续演变、最初两代华人移民的构成、华人社会组织、华人家庭制度以及华人的教育、职业状况,并概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利于新西兰华人同化的不同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书中的某些内容今日视之尤为珍贵,比如,作者对老华侨所做的口述访谈实录,对达尼丁(Dunedin)市华人中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总的来看,该书作为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参考。
19世纪70—80年代间较为重要的成果有高立夫的《纽西兰之华侨》和塞奇威克的《生存政治:新西兰华人社会史》。①Stuart. W. Greif,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Singapore:Asia Pacific Press,1974;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nterbury,1982.《纽西兰之华侨》简述了华人社会的历史,并将新西兰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美洲、澳洲华人移民的处境加以关联性的考察。本书的主要观察视角是新西兰华人同化的历史进程,作者于20世纪70年代初对多位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华人进行了采访和问卷调查,并据此评估了华人最终融入新西兰社会的程度。塞奇威克的著作对华人社会的历史有相当全面的呈现,尤其关注了华人社会内部组织结构的演变。该书在叙述华人社会每一阶段的发展衍化时,对于华人社团组织的变化以及华人表述自身利益诉求的群体性活动,都有精微之描述,这也是作者将其著作命名为“生存政治”的意蕴所在。
学术论文方面,《保持白新西兰》②P. S. O’Connor, “Keeping New Zealand White,1908 -1920”,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Vol. 2,No. 1,1968,pp. 41 -65.概述了排华立法的过程,尤其关注了1908—1920年间的种族歧视,此时正是郁积多时的“白新西兰政策”显化并作为政策公开表达的时期。另外,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新西兰各主要大学有若干以华人史研究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比如,《新西兰的移民限制》③F. A. Ponton,“Immigration Restriction in New Zealand:A Study of Policy from 1908 -1939”,Unpublised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Victoria,1946.首次尝试探讨新西兰政府与英国殖民地部的关系,同时考察了在此过程中海关署的运作;《新西兰的亚洲移民》④S. S. Rachagan,“Asian Immigration into New Zealand:A Survey of Attitudes and Legislation”,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Otago,1971.通过考察当地的传媒,检视了1865—1947年间政府活动在媒体上的反应,该项研究揭示了1946年以前报章上排华新闻报道的广泛程度,反映出限制移民政策在新西兰具有的社会基础。《惠灵顿的华人青年》⑤Lawrence Wong,“Chinese Youth in Wellington”,Unpublised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Victoria,1973;另外,其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还有V. H. H. Scurrah,“Asiatic Immigration into New Zealand 1870 -1920”,University of Auckland,1948;K. F. Lian,“A Study of I-dentity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Wellington”,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1980,等等,兹不赘述。指出,作者所观察到的惠灵顿华人青年尽管外表看上去已经西化,但实际上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虽然他们是新西兰公民,但更喜欢华人同伴。研究认为,这个群体是东西方两种背景的文化模式的综合体,作者希望解答的核心疑问是,为什么他们抵制完全的同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西兰的华侨华人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以及多样性方面获得较为重大的突破和进展。究其原因,除了华裔学者出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孜孜以求、终有成就以外,有两个外部因素不可忽视。其一,1987年新西兰政府实施新移民政策以后华人新移民大量涌入,这一现象引起当地社会和学术界对华人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更多关注,参与研究的学者明显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其二,2002年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就华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不公对待向华人社会公开道歉,其后则有新西兰华人人头税历史遗产信托基金会之设立,旨在资助华人历史研究并保护华人语言和文化,这些都对华人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综合性著述方面,伍德明的《华人历史之窗》①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Dunedin:Otago Heritage Books,Vol. I,1993;Vol. II,1995;Vol. III,1999.梳理了1865—1987年间新西兰华人社会的历史,并将伍氏家族几代人在新西兰的生活体验与感悟穿插其间,堪称改变人们对新西兰华人社会认知的鸿篇巨制。该书之重点在于淘金时代华人史,主要依据第一手的资料撰成,呈现了华人淘金者前往新西兰的历史背景、华工在奥塔哥省各金矿以及圆山矿区的工作与生活。该书还探讨了新西兰华人历史中的其他重大问题,如排华立法与措施、华人所遭受的不同表现形式的种族歧视、族群关系、华人社会同化、华人习俗中的陋习与恶习,等等。书中尚有15位知名华人的研究性传记,进一步拓展了观察的视野。
口述史方面,最为卓越的成果是叶宋曼瑛的多部华人口述历史以及基于口述访谈实录和档案资料所做的拓展研究,即《新西兰华裔妇女生平》、《龙在云乡》和《毛利裔华人》。②Manying Ip,Home away from Home,Lifestories of Chinese Women in New Zealand,Auckland:New Women’s Press,1990(中译本为《也是家乡》);Manying Ip,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The Making of Chinese New Zealanders,Auckland:Tandem Press,1996;Manying Ip,Being Maori-Chinese:Mixed Identities,Auckland: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2008.数部口述史通过对华人社会不同群体生活经历的实录,呈现出了鲜活的华人社会样貌。《新西兰华裔妇女生平》记录了数位华人女性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折射出华人社会的变化轨迹。该书在新西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曾入列当年新西兰十大畅销书排行榜。《龙在云乡》的优长在于揭示本地新西兰华人社会的形成过程,作者依据对20世纪50—60年代本地出生的华人的访问,勾画出华人社会的发展脉络,即如何从早年以单身的流动工人为主的小小族群,转变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庭社会,尤其关注了华人在中西两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华人家庭的代际关系、华人子女教育及婚恋等内容。除此之外,该书的拓展研究部分还探讨了种族关系以及1987年以后新移民涌入的影响。《毛利裔华人》记述了七个毛利裔华人家庭的故事,从侧面展示了新西兰的社会现实,并透视了新西兰华人移民与毛利人之间的关系。
专题史方面,戴渊的《中国认识新西兰的起源(1671—1911)》③William Tai Yuen,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 1674 -1911,Auckland: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2005.以中国如何知晓、了解新西兰为主题,对中国人认知新西兰的两个主要信息来源——知识和感知进行梳理,呈现了知识随时间而累积、感知随环境而变化的历史过程。其中涉及华人史的部分关注了华工早年在新西兰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政府驻新西兰外交机构的设立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布拉特肖的《金色前景:华人在新西兰西海岸》④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Shantytown:West Coast Historical & Mechanical Society Inc.,2009.专注于华人在南岛西海岸的历史,作者引用了当时的文图资料以及对华工后代的亲身采访,叙述了华人在西海岸的经历以及他们身为矿工、商人、厨工、菜农和传教士对西海岸历史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关于新西兰的排华立法,最为深入的专门研究是麦礼祖的《有关新西兰华人的法律及政策指南(1871—1996)》和《纽西兰人头税》⑤Nigel Murphy,A Guide to Laws and Polici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1871 -1996,Wellington: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Inc.,1997;Nigel Murphy,The Poll-tax in New Zealand:A Research Paper,Wellington: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Inc.,1996.,前者概述了新西兰有关华人及亚裔移民的政策和立法的演变过程,后者则对人头税的设立、存续和废除过程给予系统的展现。关于华人在新西兰从事专业种植的历史,有新西兰华农总会委托专家完成的两部著述,即《黄土子嗣》和《成功得自苦寒来》。⑥Lily Lee and Ruth Lam,Sons of the Soil:Chinese Market Gardeners in New Zealand,Pukekohe,N. Z.:Dominion Federation of New Zealand Chinese Commercial Growers Inc.,2012;Nigel Murphy,Success through Adversity:A History of the Dominion Federation of New Zealand Chinese Commercial Growers,Pukekohe,N. Z.:Dominion Federation of New Zealand Chinese Commercial Growers Inc.,2012.前者依据对新西兰各地百位以上华人菜农及其家庭的口述访谈撰成,保存了华人菜农在新西兰艰辛亦颇有成就的历史,后者则专注于纽西兰华侨农业总会会史。李海蓉的《虚拟唐人街——走进新西兰华人移民的媒体空间》①Phoebe H. Li,A Virtual Chinatown,The Diasporic Mediasphere of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Leiden:Brill Press,2013.简述了新西兰华文传媒的历史与现实,并对华文传媒在2005年新西兰大选中的表现加以个案的剖析。该书重点考察了华文传媒与华人移民间的关系,尤其是21世纪初年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社会生活及其诉求,提供了审视华人社会的新视角。《新西兰的华文平面媒体》以新西兰华文平面媒体,尤其是免费分发华文报纸为研究对象,观察华文媒体在华人保持文化认同、适应新环境过程中的作用。②David Lin,Chinese Print Media in New Zealand,Berlin:VDM Verlag,200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民熙对新西兰华人所做的调查访问及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有《纽西兰增城侨裔》,③Henry Chan(ed.),Zengcheng New Zealanders:A History for the 80thAnniversary of the Tung Jung Association of NZ Inc.,Wellington:Echo Point Press,2007.该书不仅概述了东增会馆80年的历史,而且追溯了诸多来自广东增城和东莞的华人在新西兰的生活轨迹,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近年来随着华人数量的增加,通过对华人移民所做的社会调查来分析新西兰的某些社会问题,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比如,亨德森的《新西兰华人技术移民的定居》④A. Henderson,The Settlements of Skilled Chinese Immigration in New Zealand:Issu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ocio-Economic Integration,Palmerston North:Massey University Press,2002.选取1997—1998年间定居于奥克兰的华人技术移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检视了新移民的英语熟练程度以及其他因素在其定居过程中的作用。韩裔学者Shee-Jeong Park的《亚裔新西兰人的政治参与》⑤Shee-Jeong Park,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Asian”New Zealanders,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Auckland,2006.则选择华人群体作为调查样本之一,考察了亚裔新西兰人的政治参与状况。这些调查分析为考察华人新移民的生活情状提供了实证资料。
论文方面,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论文见诸各种人文、历史、地理杂志以及多种论文集,数量相当之多。论文主题涉及华人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多个方面,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论题较具时效性,比如对新移民问题的诸多探究,甚至出现了互联网时代的民族主义与身份认同这样的切近现实的论题。比较重要的论文集有《新西兰的移民与国家认同》⑥S. W. Greif(ed.),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Zealand:One People,Two Peoples,Many Peoples?Palmerston North:The Dunmore Press,1995.、《演变的历史与身份认同:华人在新西兰》⑦Manying Ip(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Auckland: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2003.、《传媒与华人移民》⑧Wanning Sun(ed.),Medi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Community,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6.、《新西兰的毛利人与华人》⑨Manying Ip(ed.),The Dragon and the Taniwha:Maori & Chinese in New Zealand,Auckland: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2009.、《比较视野下的华人移民研究》⑩Suryadinata and Lee(ed.),Chinese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Singapore:Chinese Heritage Centre,2009.、《跨国移民与新华人》⑪⑪Manying Ip(ed.),Transmigration and the New Chinese: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11.,等等。
以下将依据主题分别叙述有关的主要研究成果。
二、淘金时代华人史
(一)华人在奥塔哥
华人到达奥塔哥之缘起。早年冯吴碧伦所做的研究,只简略提及19世纪50年代初即有华人漂流到新西兰,19世纪60年代奥塔哥发现金矿后才出现了真正的华人移民,首批前来的华工来自澳洲的维多利亚,时间是1866年。①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15.其后塞奇威克和伍德明的深入研究则厘清了华工前往新西兰的来龙去脉,两人均指出了华人应达尼丁商会邀请前来淘金的史实,但对于华人到达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塞奇威克称,1865年12月底,来自墨尔本的华商Ho Ah Mei率随从数人前来视察金矿场,并与达尼丁商会商讨了引进华工之事。该人回到澳洲后说服了12名身无分文的华工前来新西兰,这批人于1866年2月到达奥塔哥。②C.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 84.伍德明则认为,早在1842年即有华人到达新西兰的尼尔森(Nelson),而首批华工到达奥塔哥的时间则是1865年12月底。其时,由于数千名欧洲矿工离开奥塔哥,该省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有人遂提议邀请澳洲华工前来在矿区进行再作业,此议得到了达尼丁商会的认可。1865年奥塔哥省议会向华工保证,华工会受到与其他居民相同之保护。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华人踏上奥塔哥的土地。华人前来之时,当地社会就是否应引进华工有过许多争议,支持者、反对者均有之。③James P.,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pp. 123 -133.关于新西兰华工的来源地,最为准确的研究当属伍德明根据原始资料所做的梳理。伍德明指出,淘金时代的华工主要来自广东番禺县,尤其是“北番禺”地区。④根据当今之行政区划,所谓“北番禺”、“上番禺”(Upper Panyu)系指现广州市白云区。1896年的奥塔哥华人名单显示67%来自番禺、17%来自四邑,其他的来源地则有增城、香山(今中山)、花县。名单中仅有一位不是广东人,来自福建。在四邑人中,有超过八成来自台山。不过,新西兰各地移民之比例是变动的,1868年据说大多数淘金者为四邑人,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华人大量涌入后,番禺人可能成了大多数。⑤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pp. 11 -12.关于远赴新西兰所需之费用,一般研究均指出,移民们系采用“赊单制”(credit-ticket system)解决这个问题。叶宋曼瑛认为,所有前往新西兰的移民均依靠赊单制得以成行。在新西兰,宗亲会通常充当保人,亦有个别当地华商经常提供赞助并垫付旅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移民受到盘剥,从新西兰的情况看,赊单制似乎是真正地帮助乡亲的善举。不过,即使没有太重的剥削,大多数移民仍然需要四五年时间才能偿清利息、债务以及人头税。⑥Manying Ip,“Chinese New Zealanders:Old Settlers and New Immigrants”,in S. W. Greif(ed.),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Zealand,p. 165.
华人在奥塔哥地区的规模及分布。研究认为,首批华工到达后,华人数量增加迅速。1871年10月已经达到4159人。1871年以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地区华人数量开始减少,最终于1896—1901年间出现了转折点,其时仍以淘金为业的华人数量骤降,标志着淘金时代的终结。塞奇威克的研究表明,向新西兰输入华工是有组织的;伍德明也认为,先期抵达的华人中可能有代理人、商人和店主,他们在组织、协助华工输入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华工到达后很快进入内地,1869年已经遍布于奥塔哥省各金矿,甚至该省最遥远的内陆地区的瓦卡蒂普(Wakatipu)金矿也出现了华工的身影。⑦James Ng,“The Sojourner Experience: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in New Zealand,1865 -1901”,in Manying Ip(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15,1.
华工在奥塔哥矿区的工作及生活状况。研究认为,华工在矿区的作业以团队形式展开,小组中资金共用,主要是在欧洲人认为没有价值的废弃矿坑进行再作业,较之欧洲矿工,华工显然愿意从事劳动时间更长、报酬更低的工作。因此,他们的工作进展较为顺利。⑧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16.高立夫指出,与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一样,华人矿工很少独自工作,他们采取团队式生活和工作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如防范打家劫舍的欧洲人、维护家族团结,另外,采矿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重复置办设备和重复劳作。⑨S. W. Greif,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17.伍德明的研究则揭示了华工凭借其聪明才智在采金技术方面的贡献,比如徐肇开是采金船的开拓者,后来奥塔哥地区建造的采金船均以其船为范式。①James Ng,“The Sojourner Experience: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in New Zealand,1865 -1901”,pp. 19 -20.
华人向其他职业转移以及华人社会内部组织形态。塞奇威克的研究注意到,从一开始就有某些华人从事服务活动,比如菜园及其他商业,并在达尼丁开设有商号。除了从事服务业以及自己采矿,还有一些华人更愿意受雇于华、洋雇主赚取工资。②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p. 90 -92.另有学者指出,19世纪80年代华工逐渐离开矿区,前往新西兰的其他中心城市从事其他职业,尤其是专业种植。19世纪90年代中期,新西兰华人的聚居中心从奥塔哥首府达尼丁转为惠灵顿。在华人群体中,由于淘金者文化水平低下,他们与家乡的沟通必须仰仗有文化者,由此出现了三类地位较为独特之人,即代书人、商人或小店主、代理人和翻译。由于商人和店主是拥有最多资源的华人精英,华人遂依照家族和籍贯形成了以商人和店主为核心的群体。③James Ng,“The Sojourner Experience: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in New Zealand,1865 -1901”,pp. 10 -11.伍德明对徐肇开的深入研究还表明,19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西兰华商精英已经出现,并凭借其财力和地位,开始在本地华人社会事务中担负起领导责任。他们建立了覆盖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新西兰的华人商业网络,并与欧洲商人结成了实质性关系并参与新西兰事务。④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Choie Sew Hoy”,pp. 269 -289.
华工的归宿。由于资料的局限,这方面的研究系伍德明根据相关的人口统计数据以传教士亚历山大·唐的记载所做的推断。他认为,总的来看,大多数华人淘金者似有可能实现了在有生之年回国的目标,无论是否积下钱财。另外,大多数死者的遗骨似乎也被掘出由其他华工带回故土,由此大致可以解释缘何今日甚少在矿区发现华人墓地。⑤James Ng,“The Sojourner Experience: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in New Zealand,1865 -1901”,pp. 9 -10.
种族关系的演变。有关研究大多提及,早在华工到达新西兰以前,对华人的敌意即已存在。关于大批华工到达后种族关系的变化,冯吴碧伦的初步研究认为,华人到达奥塔哥以后,欧洲矿工感觉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对华人的敌意更加明显。⑥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16.伍德明的细致研究则揭示了其间的变化过程。他认为,双方最初的关系一度较为和缓,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前,奥塔哥与华人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⑦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 95.塞奇威克也认为,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相当和平,华人似乎已经能够继续存在而不遭到反对。⑧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 109.关于奥塔哥的种族关系所激起的全国性反应,多项研究均关注了1871年新西兰国会针对华人问题设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及其所做的调查结论。冯吴碧伦认为此乃有关新西兰亚裔移民的唯一真实、公正的调查。⑨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17.高立夫认为,1871年报告书使华人免受更具煽动性的指控,并宣布他们适合在新西兰居留。⑩S. W. Greif,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22.伍德明则认为,委员会以公平的听证会和明智的调查结论平息了欧洲人的担忧。⑪⑪James Ng,“The Sojourner Experience: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in New Zealand,1865 -1901”,p. 14.
关于奥塔哥矿区戒惧华人的原因,冯吴碧伦认为系由经济竞争、怀疑华人道德败坏以及有色人种是劣等民族的信条所引发。⑫⑫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17.伍德明则补充了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即奥塔哥矿区容量不大,到1871年底,华洋矿工总数为9000人,已达容纳之极限,华工的持续涌入引起了欧洲人的普遍忧虑。○13James Ng,“The Sojourner Experience: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in New Zealand,1865 -1901”,p. 14.关于奥塔哥省对华人的敌意愈益加深的原因,塞奇威克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华人群体内部的自给自足,但主要原因是采金的竞争加剧。除此而外,欧洲店主见及华人同行生意兴隆,则指控华人有另立的账户。①C.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 94.伍德明的研究特别关注了从地方到全国的排华浪潮日趋高涨的情形。他认为,1876年奥塔哥省议会取消之前,华工与欧洲矿工尚可共存,之后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其时新一代本地及国家领导人上台,取代省议会的某些县议会受到欧洲矿工的影响,对华人采取狭隘态度,1877—1879年间开始出现经济萧条,工会以及支持工会的自由党兴起,成人普选的开始,均构成了不利于华人的因素。②James Ng,“The Sojourner Experience: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in New Zealand,1865 -1901”,p. 21.伍德明还指出,19世纪70年代末期环太平洋地区普遍陷入贸易衰退,排华为共生现象,新西兰受到影响;从新西兰自身情况看,公共工程数量减少导致失业,国家负债严重,白人移民亦不能充分吸纳,这些都是促使对华人敌意增长的原因。③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p. 231.
(二)华人在西海岸
华人前往西海岸及其规模。新西兰南岛西海岸淘金热始于1864年,曾有大量华人在此淘金及从事其他职业。多年以来,华人在西海岸的活动几乎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之中,鲜为人知。近年来布拉特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关于华人前往西海岸的经过,早年的有关论述语焉不详,无法解释华人为何如此之晚才到达西海岸,只能推测可能是欧洲矿工反对所致,但没有根据。④Murray McCaskill,“The Goldrush Population of Westland”,in New Zealand Geographer,Vol. 12,No. 1,1956,p. 43.布拉特肖的著述澄清了有关的历史疑云。她指出,最早约从1866年起就有个别华人到达西海岸重镇霍基蒂卡(Hokitika),随后有华人途经西海岸前往奥塔哥。19世纪60年代末即有华工前往西海岸淘金,但因受到当地欧洲矿工的不良对待而折返。1871年起,许多华工认为奥塔哥金矿已达开采极限,遂再度开启西海岸探索之旅,并在许多地点站稳了脚跟。⑤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p. 17 -48.关于西海岸华人的规模,伍德明认为较多华人前往西海岸始于1871年,1891年达到峰值1609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广东番禹。布拉特肖的数字有所不同,她认为1880—1882年间华人数量增加一倍多,峰值为1739人,而19世纪90年代以后西海岸华人数量则持续下降。⑥James Ng,“The Sojourner Experience: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in New Zealand,1865 - 1901”,p. 14;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 239.布拉特肖的研究还关注了淘金时代终结以后留居于西海岸的华人,以及他们年华老去之后的凄凉晚景。⑦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p. 237 -238.
西海岸华人的职业分布。布拉特肖的研究证实,西海岸华工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与奥塔哥华工大致相同。从职业上看,西海岸华人大多数是矿工,尤其是在19世纪末期的全盛时代,但华人中商人、店主和手艺人亦不少。这些人随华工流动前往华人聚居地开设店铺,霍基蒂卡、里弗顿(Reefton)先后成为西海岸华人的重要商业中心。在华人数量足以维持生意的矿区,则有乡间小店开设。华人从事的其他职业还有厨工、寄宿店经营者、翻译、专业种植,等等。⑧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p. 51 -69.
西海岸的种族关系。有关研究注意到西海岸格外浓烈的排华气氛。关于华人与欧洲人关系的一般性考察,研究认为,华人在矿区通常不受欢迎,这种情绪在西海岸尤其明显。欧洲人对华人存有严重的偏见,没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华人近邻,因此任何交流都因不了解而蒙上阴影。与此同时,偏见不完全是单向的,希望尽快返乡的华人也并不尝试适应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⑨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 14.至于西海岸缘何以坚定排华而著称,有关论著分析了其中的特殊原因,比如,西海岸的很多欧洲矿工来自以排华而声名狼藉的澳洲金矿场;以反感华人著称的爱尔兰人在西海岸人口中所占比例甚高;西海岸人口中矿工所占比例远较奥塔哥等地为高,西海岸政客明显受到矿工利益的影响,后来成为新西兰总理的塞登(Richard Seddon)尤其将自己塑造为欧洲矿工的支持者①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 193.。
(三)华工在圆山矿区
就华人在新西兰南岛各地淘金的历史而言,华工在圆山矿区的工作与生活得到最为全面、细致的考察,这主要得益于传教士亚历山大·唐在矿区传教多年,保留了非常详细的记录。伍德明认为,圆山矿区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有三。其一,它是新西兰唯一一个由华人负责大部分最初开发工作的矿区,多年间矿区的华工人数超过欧洲人。其二,从世界范围看,圆山华人村是地球上最南端的华人村。其三,唐愿高的记录,可以有绝佳机会研究新西兰的华人社会。②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p. 9.塞奇威克和伍德明均依据唐愿高的有关记载,尽力还原了当年华工在矿区的样貌。伍德明对华工的生活和习俗、华工与欧洲人的关系、亚历山大·唐与华人的关系,都有精微之描述。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令人动容的是,唐愿高记录了许多事件,表明华工们渴望得到来自中国的消息,当中国在军事上几乎无能为力之际,他们依然对自己国家的强大抱有“自负”。尽管华工基本上都目不识丁,但依然坚守着对汉语的忠诚。伍德明认为,暂居时代支撑华工的这种自傲,是他们抵制基督教传教和异族通婚的原因。③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ntroduction”.
三、排华立法与种族歧视
(一)排华法案的确立及其演变
新西兰政府于1881年正式颁行排华法案,其后几经修订与调整,最终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渐次废除。研究华人海外移民史和新西兰华人史的学者对此问题均有所关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着眼于新西兰的排华政策与北美、澳洲等地排华浪潮的联动关系,后者则侧重于从新西兰内部的种族关系、经济及社会背景的角度加以剖析。
1.排华立法出台的背景及原因
关于新西兰排华法案与其他国家排华浪潮的联动关系,坎贝尔认为,新西兰排华运动的形成与澳大利亚相类似,尽管没有像澳大利亚那样对政治史产生同样巨大的影响。新西兰在排华法案出台过程中与澳洲亦步亦趋,北美、澳洲和新西兰在排华问题上明显存在着联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④P. C. Campbell,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P. S. King & Son,1971,pp. 79 -83.麦礼祖则指出,设立人头税的1881年华人移民法,系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855年的立法为范式,澳洲在排华立法方面起着带头作用,新西兰和加拿大的立法则以澳洲的有关立法为范本。⑤Nigel Murphy,The Poll-tax in New Zealand:A Research Paper,p. 13.
关于新西兰排华法案出台的远因和近因,一般研究均论及占统治地位之白人所抱持之“白新西兰”理念。有学者认为,从新西兰最初的移民历史看,新西兰人和英国移民之间不存在任何民族、法律或其他方面的差别,他们事实上是同样的人,新西兰并非一个新世界,而是新英国。⑥Malcolm Mckinnon,Immigrants and Citizens:New Zealanders and Asian Immigrat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Wellington: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1996.麦礼祖指出,最早明确提出“白新西兰”这个说法的是乔治·格雷(Sir G. Grey),这种观点在其后的数十年间并无大的改变,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⑦Nigel Murphy,“Joe Lum v. Attorney General: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in Manying Ip(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49.关于促成1881年排华立法正式确立的各种因素,伍德明认为,当初允许华人到金矿工作时,本来是期望他们会适时离开新西兰。1877—1878年经济衰退愈益显现,由于华人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来自西海岸的数名国会议员大力推动反对华人移民。①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 95.麦礼祖的看法大同小异,他认为,此为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其中主要有,西海岸矿工的排华运动组织得更为完善,且得到了许多国会议员的支持;1878年新西兰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澳洲排华煽动活动的剧烈爆发。②Nigel Murphy,The Poll-tax in New Zealand:A Research Paper,pp. 28 -29.
关于20世纪初叶排华浪潮的持续与排华法案的调整,有关研究注意到这一时期新西兰在华人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布劳利认为,尽管1919年的巴黎和会已经表明国际上对种族歧视性移民政策有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北美和澳洲都选择了继续巩固而不是破除其限制壁垒。从新西兰国内情况看,“一战”以后华人和印度移民数量明显增长,引起了劳工组织和退伍军人协会的不满,这些组织和个人的煽动激发了多起事件,最终导致1920年移民限制法修正案的出台。③Sean Brawley,The White Peril:Foreign Relations and Asian Immigration to Australasia and North America 1919 - 1978,Sydney:UNSW Press,1995,pp. 63 -64.叶宋曼瑛指出了新西兰社会排华情绪的普遍性和长期性,她认为,19世纪70年代的白人矿工、19世纪80年代的果菜园主、“一战”后的退伍军人、20世纪30年代的码头工人,无论在政治问题和社会见解上有何差异,在排华上都表现出一致性。④Manying Ip,Home away from Home,“Introduction”.麦礼祖则认为,20世纪初排华法案持续的原因,在于阻止华人移民的愿望与对本地出生华人的忧虑形成了汇合之势。对本地出生华人的担忧随着世纪之交华人女性数量的增长而出现,1925年新西兰政府决定将女性排除于移民配额之外,此举被视为阻止华人人口增长的另一种手段。⑤Nigel Murphy,“Joe Lum v. Attorney General: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p. 53.塞奇威克另有比较独特的见解,他指出,将持续不断的排华努力归于某几个人及其特有的倾向性,并不足以做出充分的解释。委员会和众议院辩论记录多达数百页,不能将此都归于某些个人行为,也不能只归咎于要求将华人逐出新西兰的公众。他认为,在新西兰的内政和对外关系——尤其是与英国的关系方面,华人问题肯定具有某种政治工具的作用。⑥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 170.
2.排华立法的内容及其演变
1881年新西兰排华立法及措施正式出台后,历经多次修正和调整,其间的变化过程相当复杂曲折,其中常被提及的限制移民办法有人头税、按照载货吨额规定附载华人之数量、入境英语测试、禁止入籍、再入境许可证制度、华人被排除在养老金法案之外、不允许获得永久居住权,等等。⑦Manying Ip,Home away from Home,Lifestories of Chinese Women in New Zealand,pp. 177 -180.有关研究对上述立法及措施多有梳理,并给予严厉的批评。叶宋曼瑛认为,这些立法和措施公开将华人挑出来,专门用以限制新西兰华人的数量。⑧Manying Ip,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p. 106.她还指出,华人移民新西兰的最初数十年间,始终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并成为多次官方排外努力的重点所在。⑨Manying Ip,“Chinese New Zealanders:Old Settlers and New Immigrants”,pp. 172 -175.
在各项排华立法和措施中,引起较多关注的是人头税和1920年法案。麦礼祖梳理了人头税的设立所引起的广泛争议以及政府的执意而行,他称,当时设立人头税的利弊引起很多争议,支持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人口构成并控制移民。反对者则分两派,一派赞同支持者的观点,唯不认为会有实效,达不到预期目标。另一派则认为人头税不公平、野蛮,违反国际法、条约以及人类和基督教的博爱原则。新西兰国会中也有许多人质疑用人头税阻止、限制华人移民的效力。然而,这些丝毫未能动摇政府的决心,人头税被视为防止“亚洲人入侵”的必不可少的壁垒,存在了63年,且从1881年设立之初的每人10镑提高到1896年法案所规定的每人100镑。⑩Nigel Murphy,The Poll-tax in New Zealand:A Research Paper,pp. 21 -29.
关于人头税对华人移民的影响,有关研究均注意到1896年法案出台后华人数量持续、稳定下降的状况。伍德明认为,10镑的人头税对华人移民未造成实际困难,而100镑的人头税则通常是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实施之时,这个数字意味着新西兰一般劳工的年平均工资,是华工约两三年的收入。伍德明还认为,人头税是后续新西兰华人基本上来自某些广东乡村和族群的主要原因,因为若没有新西兰的亲属提供经济援助,其他有意移民者几乎无法战胜人头税壁垒。①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p. 123 -124.麦礼祖则认为,人头税从10镑到100镑的大幅度提高对华人移民造成了巨大的打击。②Nigel Murphy,The Poll-tax in New Zealand:A Research Paper,p. 29.不过,高立夫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华人移民数量趋缓不是由于人头税,而是缺少一夜暴富的机会。③S. W. Greif,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26.
1944年人头税被正式废除,麦礼祖认为,有两个原因促成此举,一是工党政府于1935年上台,在新西兰,工党是华人真正的朋友;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37年以后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壮举,改变了新西兰公众的看法,新西兰华人从“黄祸”变成了“我们勇敢的盟友”。④Nigel Murphy,The Poll-tax in New Zealand:A Research Paper,p. 36.麦礼祖还认为,废除人头税和移民人数的吨额限制,表明新西兰取消了对华人移民的最后的歧视性立法,但是,公开法律的取消并不意味着歧视的终结,“白新西兰政策”依然持续。⑤Nigel Murphy,“The Legislative Response to Chinese Immigration to New Zealand,1881 -1944”,in Henry Chan(ed.),The Overseas Chinese in Australasia:History,Settlement and Interactions,Taipei and Canberra:Joint Publication of IGAS at NTU and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at ANU,2001,p. 88.
关于1920年法案,有关研究指出了其中的玄妙之处。塞奇威克认为,该法案将限制移民一事移出了公众和国会辩论的范畴,将政策的决定权交给了内阁,运用权交给了海关关长以及后来的移民大臣。⑥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 254.麦礼祖认为,该法案的特点在于其蓄意的模糊性,法案的解释和运用尺度主要落入海关官员之手,他们可以如其所愿解释、运用该法案。这种限制移民的办法被称为不动声色地保持白新西兰。⑦Nigel Murphy,“Joe Lum v. Attorney General: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p. 60.还有的学者认为,该法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满足了英国的要求,即自治领的移民政策要看似并无种族歧视。⑧Sean Brawley,The White Peril,p. 63.
3.华人对排华法案的反应
有关研究均提及华人曾经做出努力,谋求排华立法的修正。布劳利认为,新西兰华人并未驯顺地接受对自己的压制性移民法案。1881—1908年间,华人组织活动,抗议这些法案的不公平和侮辱性质,并谋求修改和废除。⑨Sean Brawley,The White Peril,pp. 31 -32.戴渊指出,排华立法出台后,华人多次向新西兰政府,甚至英国王室提出集体请愿,华人在请愿书中陈述种种理由,试图影响政府修正有关法案。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均毫无结果。新西兰华人还曾经与澳洲华人共同上书清政府总理衙门和张之洞,驳斥当地流行的对华人的贬斥之辞,并请求清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争取歧视性立法的撤销,总理衙门为此曾照会英国政府。⑩William Tai Yuen,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 1674 -1911,pp. 58,73 -75.塞奇威克认为,当地华人知道新西兰和英国的对外关系是唯一的薄弱之处,有可能由此入手使限制移民法案得到修正。华人围绕着排华法案而展开的请愿活动,促进了中国驻新西兰领事馆的设立。⑪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p. 171,586.麦礼祖指出,华人的这些集体抗议对新西兰政府通过排华法案没有产生任何影响,1909年以后,谋求修正排华法案之事交给了新任命的中国政府驻新西兰领事。⑫Nigel Murphy,The Poll-tax in New Zealand:A Research Paper,p. 32.
4.限制华人移民政策的松动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1939年以后新西兰政府限制华人移民的政策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有关研究对于政策的渐次微调及其背景,均有论述。
1939年开放华人入境。日军占领中国华南以后,新西兰政府于1939年允许当地华人妻儿前来团聚。叶宋曼瑛认为,此举系新西兰华人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但其出现不是由于立法的松动,而是由于战时的紧急情况。①Manying Ip,“Chinese Immigrants and Transnationals in New Zealand:A Fortress Opened”,in J. C. Ma and Carolyn Cartier(eds.),The Chinese Diaspora:Space,Place,Mobility and Identity,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ress,2003,p. 341.伍德明的研究则表明,内阁是在中国领事馆和新西兰华侨联合会的强烈要求之下做出此项决定的。华人移民的此项重大变化系由三个因素所导致,其一,新西兰华人终于有了强有力的、有代表性的组织,即中国领事馆、新西兰华侨联合会以及国民党,且三方合作得很好;其二,太平洋战争的风险日益增长,日本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其三,1935年选出了首届工党政府,在许多新西兰人仍然抱持种族优越观念之时,工党政府特别同情华人。②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 178.冯吴碧伦亦认为,工党执政标志着新西兰华人地位的重大改变,工党领袖做出努力践行其种族平等之理想,随后养老金法案、移民限制都有所变化。十年间,政治及民间领袖的立法演讲以及民意的表达都表明,华人与新西兰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极大改善。③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31 -33.
1947年华人获得居留权,1951年华人入籍禁令取消。研究认为,抗战胜利后,曾有新西兰华人返回广东,但由于当地经济不佳及内战临近,大多数人又重返新西兰。1947年,华人寻求到达尼丁天主教长老会的帮助,由该会向政府请求给予有关的1323名华人永久居留证,而不是强迫他们返回故乡。结果,1926年以来首次允许华人永久居留。④S. W. Greif,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45.塞奇威克认为,“二战”以后,新西兰政府面临着如何对待战时前来的华人难民问题,需要在接受和拒绝之间加以选择,新西兰两个政党对华人移民的传统立场不同,对华人继续移民的反应亦不同。欧裔新西兰人对华人的最大愿望是同化,不会容忍中华文化通过直接来自中国的家族移民和配偶而得到再生。塞奇威克还关注了在此过程中新西兰华侨总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⑤C.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p. 425 -426,431 -434.叶宋曼瑛认为,1947年新西兰政府通过了更加自由的定居条例,1939年以后以难民身份进入新西兰的妇孺以及这些妇女在新西兰生育的孩子被给予永久居留权。此举对新西兰华人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一个由完整家庭构成的真正的华人社会从此时起落地生根。⑥Manying Ip,“Locating Chinese New Zealanders:Comparing Contemporary‘Quality Migrants’with the‘Undesirable Aliens’of Yesteryears”,in Suryadinata and Lee(eds.),Chinese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pp. 53 -67.1951年,新西兰政府取消1908年开始的华人入籍禁令,允许华人申请加入新西兰国籍。有关的深入研究则披露了政府政策的另一面相。叶宋曼瑛指出,国内事务部的内部备忘录清楚地表明,新西兰希望严格限制华人居民的数量,华人被要求断绝与中国的联系,在法官面前宣誓效忠。⑦Manying Ip,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p. 145.
关于法律上歧视的最终消除,研究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西兰开始重视种族和谐及多元文化,政府不再坚持一贯的独尊英裔政策,百余年来法律上对华人的歧视已经消失。⑧Manying Ip,Home away from Home,“Introduction”.
(二)种族歧视
一般研究均认为,在排华情绪深厚的年代里,新西兰主流社会弥漫着对华人的轻蔑与排斥。关于蔑视华人的具体内容,高立夫考察加利福尼亚、澳洲和新西兰之情形后指出,对华人的共同指责有三个方面。其一,华人吝啬、消费低,有可能消耗当地的财富。当他们离开矿区进入其他劳动岗位时,会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其二,华人是不道德的,这证之于华人群体性别比例失衡,可以想见华人过着十足的放荡生活或接受异族通婚。其三,华人被认为是劣等民族的成员,最终会通过被迫的通婚,降低殖民地的欧洲属性。①S. W. Greif,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21 -22.叶宋曼瑛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的对华人的这些指斥在后来的数十年中反复出现,细节或有增减,而排华主题不变。②Manying Ip,Home away from Home,“Introduction”.伍德明认为,19—20世纪之交占新西兰人口优势地位的欧洲人对华人的主要偏见是,华人是劣等种族,不应允许他们在新西兰定居。③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p. 82.布劳利则认为,黄祸论是新西兰公共意识的一部分。④Sean Brawley,The White Peril,p. 16.除此之外,麦礼祖还专门考察了1890—1914年间新西兰的种族话语,探究白人对华人和毛利人的描述和歪曲如何被用以构建新西兰的国家认同。他指出,毛利人和华人均被排斥于构建国家认同之外,但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和理由。新西兰的国家认同以白新西兰为基础,华人及其他非白人种族被排除在外。不过,这种排斥对毛利人和华人是有所区别的。⑤Nigel Murphy,“‘Maoriland’and‘Yellow Peril’:Discourses of Maori and Chinese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Zealand’s National Identity 1890 -1914”,in Manying Ip(ed.),The Dragon and the Taniwha:Maori & Chinese in New Zealand.
与华人受到法律和社会排斥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主流社会对华人被同化以及本地出生华人的担忧与防范。麦礼祖认为,对本地出生华人的忧惧源于两个原因,一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减少新西兰华人数量的愿望背道而驰;二是本地出生华人会获得与新西兰白人同样的权力和特权。⑥Nigel Murphy,“Joe Lum v. Attorney General: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p. 55.伍德明则着重分析了亚历山德拉(Alexandra)所发生的种族对立事件,认为华人所遭受的人身暴力行为以及白新西兰政策,反映出早期欧洲人对华人有可能同化的担忧。⑦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3,“Introduction”;pp. 9 -23.叶宋曼瑛亦指出,许多新西兰华人经历过种族歧视,那些本地出生,不知道其他故乡的华人在其出生的土地上遭遇歧视,最初是难以理解的,往往是非常痛苦的。⑧Manying Ip,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p. 106.
四、20世纪华人社会变迁
(一)20世纪上半期的华人社会状况
20世纪上半期,新西兰华人社会出现了诸多变化,有关研究对此有所梳理。
关于华人的地域分布,伍德明指出,这一时期,与新西兰人口向北迁移的总体趋势相一致,华人从南岛逐渐向北岛迁移的情况非常明显,惠灵顿取代达尼丁,成为新西兰华人的社会及政治中心。⑨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p. 160 -163.
关于华人社会的人口及性别构成等指标,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引起较多关注。叶宋曼瑛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早期移民社会均存在性别比不平衡之共性,但新西兰的情况更为严重,且持续时间相当之长。究其原因,大抵是华人女性移民受到公开的歧视性立法的排斥以及选择性操控移民政策的结果。⑩Manying Ip and Liangui Liu,“Gendered Factors of Chinese Multi-locality Migration:The New Zealand Case”,Sites:New Series Vol. 5,No. 2,2008,pp. 31 -56.叶宋曼瑛的另一项研究认为,华人社会性别比严重失衡系由两方面原因造成,即新西兰政府的歧视性移民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使然。在新西兰政府将华人定位于不受欢迎的移民的大背景下,尽管有关的限制性法律系针对所有华人移民,但实际上使女性移民更加困难,档案记录也表明当局认为女性有生育能力,因而比男性移民更具有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当华人有能力负担人头税时,往往选择家族中的其他男性成员前来,而当地出生的女孩则通常被送回中国。①Manying Ip,“Redefining Chinese Female Migration:From Exclusion to Transnationalism”,in Lyndon Fraser and Katie Pickles(eds.),Shifting Centres,Women and Migration in New Zealand History,Dunedin:University of Otago Press,2002,p. 153.伍德明则尖锐指出,20世纪初年华人女性数量的增加引起新西兰各方的反应。1907年实施了华人移民阅读测试,1908年禁止华人入籍。立法者一方面宣称新西兰华人性别比失衡导致不道德,另一方面又想阻止华人女性进入。②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p. 263.
关于华人的职业及社会阶层变动。戴渊依据人口统计报告所做的研究认为,此一时期,与华人向北迁移同时发生的是华人职业结构的变化。191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在总计2567名华人中,菜农、矿工、洗衣工、果蔬店经营者分别占到人口总数的36. 7%、16. 2%、11%、10. 9%。此后数十年时间里,矿工人数进一步减少,最终菜农、水果商、洗衣工成为主要的职业群体。③William Tai Yuen,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 1674 -1911,p. 42.有学者于1973年所做的调查表明,奥克兰的大部分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职业是蔬果商、餐馆老板、进出口商、杂货商、超市业主,都是自雇式的。④M. L. Young,“The Auckland Chinese:A Community in Transition”,Unpublised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Auckland,1973,pp. 41 -59.华人从事种植业的情况得到较多的研究。高立夫认为,早期华人菜农基本上将其产品销售给内陆的华工,随着矿工人数的减少,他们开始将产品卖给商店,或自己在市集做流动摊贩。1900年,华人开始设立自己的永久性商店,并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欧洲顾客。此后,新西兰的果蔬业一直都是华人和印度人的生意。这样,专业种植和果蔬销售取代了采金。⑤S. W. Greif,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29.《黄土子嗣》的作者对菜农的调查表明,某些地区的菜农系家族中“拿起锄头”的第一代,他们通常别无选择,不得不努力工作,赚钱供给故乡的家人。⑥Lily Lee and Ruth Lam,Sons of the Soil:Chinese Market Gardeners in New Zealand,“Epilogue”.叶宋曼瑛指出,淘金时代结束后,华人向北迁移,进入正在发展中的城市,从事主流社会所不屑为之的卑贱工作,许多人成为洗衣工,华人还很快在蔬菜种植这个劳动力密集、英裔移民不感兴趣的行业立足。华人在种植业的成就引人注目。“二战”期间,华人种植的蔬菜成为盟军的生活必需品,这提高了华人的地位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很好收入保障的现成市场。⑦Manying Ip,“Chinese Immigrants and Transnationals in New Zealand:A Fortress Opened”,p. 347.
关于华人职业分布形成之原因,伍德明指出,最初的淘金者以及19世纪80—90年代、20世纪20年代之前来到新西兰的华人,英语若非全然不会也是极差,英语得不到提高,主要是移民聚居的自然倾向造成的,日益加剧的种族对立则使他们更加抱团,成为相对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少数族群,与欧洲人有着最少的联系。华人因缺少文化和语言技能在职业上受到限制,商人仍占据着华人职业群体之首的地位。⑧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p. 82,160.还有的学者对20世纪20—40年代的达尼丁华人社会加以个案的细致研究,分析了华人从事的主要职业,但得出了一个剑走偏锋的结论,认为欧洲人和华人疏离的主要原因在于华人移民试图定居并从事“自雇式”生意,达尼丁华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社会距离是经济环境问题而非社会或种族歧视问题。⑨Niti Pawakapan,“No Longer Migrants:Southern New Zealand Chinese in the 20th Century”,in Michael W. Charney(ed.),Chinese Migrants Abroad,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3,pp. 225 -226.
华人社团组织。冯吴碧伦对于这一时期的华人社团依据政治、宗教、家族性以及社会性团体加以分类,概述了各类社团组织的状况。她对政治团体的研究表明,国民党于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出现于新西兰,并得到许多华人的拥护,其发展的高峰在20世纪20年代末⑩原文有误,应为20世纪30年代——作者注。的抗战爆发之际,其时对党派利益的效忠让位于共同对敌的目标。冯吴碧伦还认为,新西兰华人——无论是华侨抑或新西兰公民,都不积极参与任何一国之政治。①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50 -65.
塞奇威克的研究关注华人社团的演变,对于这一时期华人社团或以维护本地华人利益的面目出现,或表现出与中国国内政治密切交集的现象有精细之刻画。他认为,19世纪末的华人社团主要是慈善性质的,如昌善堂,其主要活动是运送华工遗骨回乡。20世纪初年新西兰华人有三个主要的政治团体,康、梁的改良派于世纪之交即在华人中立足,孙中山的同盟会于1905—1906年间在新西兰积极展开活动,致公堂于1907年在此建立分会。20世纪20—30年代华人社团的变化更大,华人社会派系间的不和谐关系、故乡局势的恶化以及移民限制的加剧、持续排华活动的压力,迫使华人社会谋求社团组织的统一。这一时期出现了某些超越政治派系,更加关注个人基本需求的团体。尽管如此,华人社会内部派系犹存,且跟随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而联动,比如北伐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都对华人社团产生了影响,拥护国民党的社团明显居于领导地位。②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p. 142 -143,304 -314,588 -595.戴渊则指出,中国政府在新西兰设立领事对华人社会产生了影响,新西兰第一次通过中国领事听到了与主流舆论不同的华人声音,首任领事黄荣良出面为华人辩护,并进一步推动华人社团组织的建立。③William Tai Yuen,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 1674 -1911,pp. 82 -84.塞奇威克梳理了后来多位中国驻新西兰领事在华侨中所做的工作,如代表当地社会向新西兰政府请求允许华人妇孺暂时前来避难;推动华人社会的民族主义浪潮,促成了1935—1936年间纽西兰华侨总会的建立,等等。④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p. 388 -399.
麦礼祖专门研究了新西兰华侨农业总会的历史。研究指出,华农总会设立于1943年,其时大批美军驻扎于新西兰,为保障盟军战时蔬菜供给,新西兰总理提议设立全国性的华农组织,以便政府与之商谈蔬菜供给问题。延续至今的华农总会在保护华人菜农利益、争取政府和西农会(Diminion Council)承认华人种植者独特地位方面多有贡献。⑤Nigel Murphy,Success through Adversity:A History of the Dominion Federation of New Zealand Chinese Commercial Growers,p. 103.塞奇威克对新西兰华侨总会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活动——组织募捐和就华人难民入境问题与政府沟通——有详细之研究。⑥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p. 393 -399,401.
抗战及“二战”期间的华人社会。有关研究集中于华人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和华人社会本身的新面貌。塞奇威克和伍德明的研究认为,纯血统新西兰华人以征税和捐赠方式至少募集19万英镑,另外购买类似数额的中国战时公债。由于后来国民政府垮台,公债等同于额外捐赠。新西兰华人有一个共识,他们战时的人均募资额高于其他任何海外华人社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⑦C. P. 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p. 698;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 177.关于这一时期华人社会面貌的改观,有研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人立即加入新西兰各部队。对许多从军者而言,服役的时光使他们睁开眼睛面对一个事实,即自己比预想的更新西兰化。而对所有华人而言,战争使他们与欧洲、毛利盟友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尽管终将返回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华人与所在国社会彼此间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⑧S. W. Greif,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44.
华文报业。有关研究对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两个华文报业的繁荣时期有所关注。一般认为,华文报业的两个制约因素是华人数量少,新西兰与中国相隔遥远。叶宋曼瑛对此从另一个角度加以理解,认为华人社会规模虽小,但内部联系紧密,地理上的阻隔使得任何“本地”传媒都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影响力,正是这两个因素催生了20世纪上半期的华文报业繁荣的历史环境。“二战”期间以及战后一个时期华文传媒非常强大,充当了构建新西兰虚拟的统一华人社会的主要因素。其时,华人从暂居者转变为定居者,报纸起到了祖国与所在国两方面信息之源的作用,并得到社会上无可争议的支持。①Manying Ip,“Chinese Media in New Zealand”,in Wanning Sun(ed.),Medi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Community,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p. 178.另有学者指出,20世纪初期,新西兰华文报纸成为华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许多华人迁往市区谋生,令华文报纸易于分销,更重要的是,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华人成长起来,成了稳定的读者群。当时主要的华文报纸是《民生报》、《屋伦侨声》、《中国大事周刊》以及《侨农》,从中可以看出,华文报纸主要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新闻,尤其是报道中国最新的国内政治,这与当时的华人社会主要由矿工、菜农、菜贩和洗衣工构成有关,这个群体的梦想就是用新西兰辛苦赚得的积蓄返回中国安享晚年。另一方面,华人暂居者留驻于新西兰,必定要参与、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数十年间,洋人在华文报纸上刊登的商业广告很多,显露出华人社会渐进同化过程的点点迹象。②Phoebe H. Li,A Virtual Chinatown,p. 59.
(二)20世纪50—80年代之华人社会
华人社会地位的重大转变。一般研究均提及这一时期华人社会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整体提升,而最重要的上向社会流动阶梯则是教育。伍德明指出,由于获得免费教育的机会,20世纪30—50年代出生之华人成为大学毕业生,这一代人扩大了华人职业的基础,改善了华人的社会地位,为下一代华人树立了追随的榜样。其后,长久定居的华人家族的后代有了极高的大学就读率,约为新西兰平均水平的两三倍。年轻人大多进入专业领域而非商业领域,由此出现了本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专业人士家族。③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 204.叶宋曼瑛指出,调查显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华人家族中一般都有极为勤奋,且很有成就之子女。④Manying Ip,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p. 8.有关学者对华人菜农的研究表明,“二战”以后菜农家庭的孩子和年轻人利用了新西兰给他们提供的机会,许多人离开家庭菜园,从事其他职业,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入读大学,成为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与此同时,留守的年青一代则帮助父母经营生意,20世纪60—80年代是生意成功且颇有成就的时期。⑤Lily Lee and Ruth Lam,Sons of the Soil:Chinese Market Gardeners in New Zealand,“Prologue”.
华人社会的同化。一般研究均认为这一时期是新西兰华人融入当地社会最好的年代。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冯吴碧伦,她于20世纪50年代末所做的研究认为,当时的新西兰社会出现了某些有利于华人同化的因素,比如,限制移民立法的废除、允许华人入籍、不存在社会隔离、与主流社会的自由交往、经济机会以及通婚,等等。⑥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119 -126.20世纪70年代初高立夫所做的研究表明,华人具有较高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度。已经有超过七成的被访者无保留地视新西兰为家乡,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从未在社会上或经营中遭到歧视,这一点在49岁以下的受访者中尤为明显。有高达88%的受访者认为身为华人不妨碍其地位和职业的提升。他的最终结论是,问卷调查表明差不多所有40岁以下的华人有愿望及能力几近完全地同化。⑦S. W. Greif,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92 -94,161.伍德明认为,1951—1985年间新西兰华人经历了积极同化之过程,尽管程度有所差异,但是总体上看,长期定居之华人家庭基本上已被同化。⑧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 204.
另一方面,有些研究检视了华人社会同化过程中“华人性”丧失的问题。早年冯吴碧伦的研究对这一现象有所捕捉,她认为,第一代华工保留了相当完整的故乡风俗,到作者成长的20世纪40—50年代,故土风俗明显逝去。⑨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51.叶宋曼瑛的研究则挖掘了“华人性”消失的深层根源,她指出,华人的出现被视为历史的错误,危及新西兰的种族和文化纯洁,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都无可置疑地被认为是优越的,而对“华人性”则多作负面解释。妨碍构建华人社会认同的一大障碍在于新西兰是个遥远的国度,地理上的距离与政府的限制移民政策相结合,意味着新西兰华人与有助于培育其自我意识的中国社会和移民人口相隔绝。没有了更好的参照系,华人学会了透过欧洲人的眼睛自审,以欧洲人的标准自我衡量,华人价值观很快与一切次等、落后的事物联系在一起。①Manying Ip,“Chinese Immigrants and Transnationals in New Zealand:A Fortress Opened”,pp. 353 -354.有关研究均关注到“二战”以后出现的新西兰政府有意识地推行同化政策。塞奇威克披露1946年政府暗中破坏华侨联合会引进中文教师,因为担心这会影响到年青一代被英国文化同化的进程。叶宋曼瑛认为,绝对信服英国文化优越性的政府奉行同化政策,使华人像毛利人一样,丧失了太多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自豪感。②Charles P. Sedgwick,“Persistence,Change and Innovation: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the New Zealand Chinese 1866 -1976”,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Vol. 16,No. 2,1985,pp. 205 -229;Manying Ip,“Chinese Immigrants and Transnationals in New Zealand:A Fortress Opened”,p. 354.
主流社会的认可与“模范少数民族”。此一时期,华人社会得到了“模范少数民族”的称谓,以守法、勤劳、低调、温顺为特征。新西兰主流社会对华人社会态度的这一巨大转变,一般被视为华人社会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对此多有评价与分析。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所做的研究认为,华人从“不受欢迎的移民”成为得到高度肯定的“模范少数民族”,不同于新西兰其他少数族群,华人已被视为可接受度极高的群体。其时华人似乎未遭受歧视,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倾向于保持低调的公众形象,并不谋求与主流社会成员的密切关系,似乎也不再有淘金时代那样直接的工作竞争。③R. Chi-Ying Chung and Frank H. Walkey,“From Undesirable Immigrant to Model Minority:The Success Story of Chinese in New Zealand”,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Vol. 7,1988,pp. 308 -312.伍德明对此评价积极,认为华人被新西兰社会所接受一般被视为这一时代华人社会的最大成就。④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I,p. 204.不过,亦有学者对此评价似乎有所保留。叶宋曼瑛认为,到1986年,小小的华人社会看似已经稳定和同化了,主流社会几乎意识不到其存在:数量只占总人口的0. 6%,贴着“模范少数民族”的标签。然而,鲜有人深究华人付出什么代价得到认可,或自问历史上的排华情绪的幽灵是否真正烟消云散。⑤Manying Ip,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p. 145.叶宋曼瑛还认为,20世纪50—80年代,华人职业地位迅速提升,用来描述华人社会地位的普遍说法是,华人从菜农转变为成功的企业家,从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转变为受尊重的“公民”。当这种说法出现的时候,华人真正被视为新西兰的平等公民吗?实际上,华人始终处于被动之中,作为一个历史上受到诬蔑的少数民族,华人没有安全感。另外,当所谓的华人成功故事被用来描绘今日之华人社会时,华人为赢得主流社会承认所付出的代价常常被遗忘。他们在未来能否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取决于所有有思想的新西兰人的集体意志,而非只是政府的立法、短期的经济考量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⑥Manying Ip,“Still Floating:No Longer Sojourners,but Transnationals”,in James and Kember and Paul Clark(eds.),China and New Zealand:A Thriving Relationship Thirty Years on,Auckland: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2003,p. 38.还有的学者关注了新西兰华人应对种族歧视和社会排斥的种种策略,认为这些策略在历史上塑造了新西兰社会中一个驯顺的少数族群,并用以支撑平等主义和英才教育的神话。⑦Beven Yee,“Coping with Insecurity:Everyday Experiences of Chinese New Zealanders”,in Manying Ip(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215 -232.
(三)族群关系
华人与毛利人的关系是引起较多关注的课题,有关研究对于理解新西兰的种族关系并从另一视角观察华人社会很有助益。研究认为,华人与毛利人的密切关系始于早年间两个族群的交往。19世纪末20世纪初,毛利人与华人有着相同的被边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彼此之间是朋友、邻居和亲属。两个族群间的密切关系导致了华人男性与毛利女性之间的通婚成为较常见的现象。①Manying Ip,Being Maori-Chinese:Mixed Identities,“Preface”.还有研究认为,华人与毛利人都从事农耕,华人菜农和水果店主经常雇用毛利人做帮手,华人与毛利人通婚相当常见,尤其是在华人移民多为单身汉工人的年代。②Manying Ip,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pp. 108 -109.还有的研究指出了两个族群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认为,尽管华人和毛利人都受到歧视,但白人主流社会对待二者很不相同,毛利人是英国臣民,而华人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某些毛利人从主流社会学到了歧视的态度,并发泄其对华人的偏见。③Manying Ip,Being Maori-Chinese:Mixed Identities,“Preface”;Manying Ip,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p. 108.
关于华人与其他族群的通婚,伍德明认为,自华人现身于新西兰起,欧洲人就非常恐惧人种混杂现象的蔓延,异族通婚和混血后代的数字相当之小。在淘金时代,“异族通婚”一般指华人男性与欧洲女性的结合。1926年和1945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新西兰华人中混血儿的比例特别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异族通婚越来越多,人口统计中的混血后代数字可以反映这一趋势。④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 II,pp. 240,256,265.
五、新移民时代之华人社会
1987年新西兰政府推出新移民政策,开启了华人移民史的新时代。该项政策实施后,亚洲各国新移民短时间内大量涌入新西兰,这一现象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学术界对于亚裔、华人新移民的研究相当之多。由于新移民群体仍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任何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只能是相对准确的,其中何者可以成为历史的定论,尚有待于岁月的沉淀和时间的检验。
(一)新移民政策及其对华人移民的影响
研究认为,1987年法案应置于第四届工党政府全面撤销管制方案的背景下加以考量,政府大胆开启了经济结构调整之路,以刺激本地经济和吸引国际投资,全新的移民政策乃是整个社会改革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抵消之前持续10年之久的逆向移民的影响,1987年法案宣布移民选择以个人价值为标准,不因民族、国籍或种族而加以歧视,由此向“非传统”移民开放国门。华人移民新西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政府的移民政策,1987年法案对华人移民的意义不言而喻。⑤Manying Ip,“Chinese Immigrants and Transnationals in New Zealand:A Fortress Opened”,p. 342.
与华人移民有关联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是对《怀唐伊条约》以及毛利人对华人新移民态度的剖析。叶宋曼瑛考察了《怀唐伊条约》对新西兰华人的法律和政治地位的影响。她认为,1840年英国人与毛利酋长签订的这个条约,将新西兰主权交与英国王室,并确立了Pakeha⑥Pakeha今指新西兰白人,尤其是祖先是欧洲人的新西兰人——作者注。(此语用于非毛利人,当时指英国人)与毛利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于华裔和其他非英裔移民来说,麻烦在于不能确定“Pakeha”是否也包括他们。时至今日,如果深究新西兰华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否如其他居民一样得到充分之保障,情况则是含糊不明的⑦Manying Ip,“The Leg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Chinese New Zealanders:Implications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in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eds.),The Chinese Diaspora:Selected Essays,Vol. II,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8,p. 217.。关于毛利人对新移民的态度,研究认为,华人必须战胜的一个潜在障碍是重新获得本地毛利人的接纳。历史上毛利人与华人曾有密切联系,然而,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亚洲人”的涌入,毛利人的态度急剧转变,新一代的毛利人活动家认为,《怀唐伊条约》是一个只允许从欧洲、澳洲和英国向新西兰移民的协定,其祖先与英国王室缔约,作为毛利人的后代,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就移民问题与其磋商。⑧Ranginui Walker,“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Zealand”,in Stuart W. Greif(ed.),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Zealand,p. 285.
(二)华人移民的特性
新移民时代之华人社会表现出诸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无论是专门针对华人所做的研究,抑或将华人置于亚裔移民群体中所做的考察,对此均有所关注和探讨。有关研究多将新时代的华人社会置于历史的坐标系中,描摹其变化的轨迹。
关于华人移民来源地的多元化。研究认为,新移民政策实施以前,新西兰华人数量增长缓慢,系结合相对紧密、以粤语为日常语言的族群,其中大多数人可溯及与早期广东移民的关系,1996年的人口统计则显示华人移民来源地以中国台湾、大陆和香港地区为前三位,而且,新移民与新西兰原有之华人社会并无真正联系。①Anne Elsie. S. Ho and Ruth Farmer,“The Hong Kong Chinese in Auckland”,in Ronald Skeldon(ed.),Reluctant Exiles?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4,p. 221.
关于新移民的素质及移民动机。研究认为,由于新移民政策吸引高质量移民的选择性倾向,新移民大多数来自城市,是教育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士,具有可转换技能和商业经验,从新移民的动机看,香港移民多为寻求政治避风港,台湾移民则为谋求更好的子女教育和自身更为宽松的生活方式。②Manying Ip,“Chinese Immigrants and Transnationals in New Zealand:A Fortress Opened”,pp. 343 -345.还有的研究关注了促使台湾人移民海外的岛内因素,诸如始终存在的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担忧,以及支持国民党和民进党不同阵营之间所存在的内部社会政治紧张。③Lan-hung Nora Chiang,“Staying or Leaving:Taiwanese-Chinese Making Their Homes in New Zealand”,in Manying Ip(ed.),Transmigration and the New Chinese: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pp. 102 -138.
关于华人人口各种指标。有关研究均注意到新移民的到来对华人社会人口构成指标的影响,比如人口的年轻化、性别比的终致平衡,等等。其中女性移民与性别比的关系得到关注。研究认为,新移民政策实施后,华人女性移民数量大大超过男性,1991年华人人口性别比历史上首次达到平衡。1990年以后,许多女性新移民成为新西兰的留守妻子,与此同时,女性在家庭移民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由此改变了华人人口的性别构成关系④Manying Ip and Liangui Liu,“Gendered Factors of Chinese Multi-locality Migration:The New Zealand Case”,Sites:New Series Vol. 5,No. 2,2008,pp. 31 -56.。
关于新移民在当地社会的政治参与。早年间有学者特别关注了台湾移民的政治参与,认为新西兰的选举政策对各民族新移民极具包容性,在新西兰华人移民中台湾人无疑是最具政治意识的群体,他们的种种行为清楚地显示了政治参与的意愿。⑤Manying Ip,“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aiwanese Immigrants”,载汤熙勇编:《第四届世界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台北:2001年,第180页。另有研究认为,香港移民一般在政治上较为冷漠,可能是英国殖民地的经历使然。比较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移民群体,台湾人在新西兰政治中最为活跃,尤其是在1996年和1999年大选期间。⑥Manying Ip,“Asian New Zealanders:Emergent Political Leadership”,in Miller and M. Mintrom(ed.),Political Leadership in New Zealand,Auckland: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2006,pp. 153 -175.而最新的研究则表明,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移民的相对规模显著减小,其影响力亦在下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在主张新西兰华人移民的重大关切与利益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⑦Phoebe H. Li,A Virtual Chinatown,p. 166.
(三)新移民生存状态及回流现象
有关研究注意到华人新移民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回流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往往依据移民来源地、移民方式等对新移民群体做不同的划分,观察其生存状况。
关于商业移民以及新移民的就业状况。有学者指出,新西兰政府吸引亚裔人才的初衷是助推经济,然而,根据有关的调查和探访,华人商业移民的总体状况是严峻的,亚裔商业移民遭遇挫败的传闻比比皆是①Max Chapple,“The Work Ethic”,The Metro,Auckland,October 1992;Lloyd Jones,“Too Tough to Make Money in New Zealand,Say business Migrants”,New Zealand Herald,Sept. 26,1991,A5.。有学者认为,通过商业移民签证和积分制移居新西兰的华人新移民,大多很难让新西兰雇主承认其技能与专长,很少有人在新西兰开办新生意。②Anne Henderson,“Untapped Talents:The Emplo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Skilled Chinese in New Zealand”,in Manying Ip(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141 -161.针对台湾商业移民的研究则指出,新西兰华人商业移民面临着许多“自身障碍”,如语言和取得信用方面的困难,不熟悉法律规章,高税收以及严格的工业法律。台湾商业移民高流动性的原因之一是严峻的经济现实使他们明白,在台湾的市场更加有利可图。③Tim Beal,“Taiwanese Business Migration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in Manying Ip(ed.),Re-examin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in Australia-New Zealand,Canberra: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at ANU,2001,pp. 25 -44.叶宋曼瑛指出,新西兰人口数量少,进出口运费昂贵以及政府官僚机构缺乏灵活性,使得华人企业家的创业努力受到阻碍,在实际操作中,英语不娴熟以及不了解当地的规章制度,已经使许多创业计划受挫。面对长期失业或创业屡遭挫败,许多华人新移民自认为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回流”移民,穿梭于太平洋成为一种生存战略。④Manying Ip,“Chinese Immigrants and Transnationals in New Zealand:A Fortress Opened”,p. 352.还有的学者检视了新西兰政府的商业移民政策,并分析了其实施以后出乎意料的结果对新西兰社会和华人新移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认为,商业移民的试验令新西兰和华人新移民都非常不满意,华人新移民飞来飞去是一个不断地向更好的地方迁移的长期现象,未来的行为常态将是持续地流动。1998年新西兰政府承认商业活动和居住于新西兰无须紧密关联,这可能是对跨国移民的官方认可。研究还指出,新西兰华人新企业的特征是规模小,由暂住的、不成功的投资者和新手经营。很多人根本谈不上是大胆的跨国移民,实属不情愿的初次创业者,在故乡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商业经验。⑤Manying Ip,“Chinese Business Immigrants to New Zealand:Transnational or Failed Investors”,in Re-examin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in Australia-New Zealand. pp. 56 -88.关于华人新移民的总体就业状况,有学者依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观察居住时间长短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若将华人移民按照其居住于新西兰的时间划分为新移民(5年以下)、近期移民(5~14年)和久居移民(14年以上)三组,观察30~49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可以看到大部分新移民未在劳动力之列,其中台湾出生的华人新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比中国大陆、香港出生者低很多,在女性中尤其如此。近期移民的劳动参与率高于新移民,但仍大大低于久居移民和新西兰出生之华人。⑥Elsie Ho,“Contemporary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in David Ip et al.(eds.),Experiences of Transnatioal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06,pp. 41 -53.
关于香港移民的状况。Elsie Ho对香港移民进行了多年的追踪研究,表明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20世纪90年初的研究认为,抽样调查显示,奥克兰的香港移民中的工作人口相当不错地适应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职业范围广泛,但劳动参与率不高。⑦Elsie S. Ho and Ruth Farmer,“The Hong Kong Chinese in Auckland”,p. 229.Elsie Ho在10年后的研究则指出,2001年香港出生的华人移民占到新西兰华人总数的10%,但通过仔细分析可发现,香港移民的再移民或回流现象较为突出。尽管香港移民多具有中产阶级背景、良好的教育资质并长时间居住于新西兰,但大部分人并未加入劳动大军,处于失业状态。多年以来,经济前景的不佳以及对故乡的家庭的责任,已经使许多人放弃了在一个安静、和平的国家颐养天年的梦想。⑧Elsie Ho,“Reluctant Exiles or Roaming Transnationals?The Hong Kong Chinese in New Zealand”,in Manying Ip(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165 -181.
关于台湾移民的状况,有关研究亦揭示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大多数台湾移民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达新西兰,其公众形象一般为富裕、专业素质高以及成功的企业家。有学者依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颠覆了以上看法。有学者依据统计数据指出,在各少数族群中,台湾人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台湾人的个人中位数收入最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台湾人把新西兰幻想为“最后的乌托邦”,能够为他们提供生活的避风港和给予子女良好的教育机会。①Manying Ip,“Seeking the Last Utopia:The Taiwanese in New Zealand”,in Manying Ip(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 185.
关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状况,有关研究以2001年新西兰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指出了该群体的以下特征:增长迅速,2001年已经占到新西兰华人总数的35%;大多数属于技术移民类别;在新西兰华人中受教育程度最高;劳动力状况指标相当差,失业率在所有移民群体中居于倒数第二位。总的来看,近年来大陆移民群体显示出强烈的回流移民和再度跨国移民倾向。另外,对奥克兰地区100名大陆移民的访问表明,很多人继续维持着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可是很少有人会汇款回大陆;虽然该群体与华人社区联系甚为密切,却很少有人依靠其华人同胞获取在新西兰的首份工作。②Manying Ip,“Returnees and Transnationalism:Evolv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PRC)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No. 33,December,2006,pp. 61 -102.另有学者关注了大陆移民的故乡意识,有关研究对人口普查数据和移民统计加以数量分析,并对27个中国大陆移民家族进行了深度访问,据此认为这一群体具有“流动故乡”的意识。③Liangrn Sally Liu,“New Zealand Case:Study of PRC Transnational Migration:Returnees and Trans-Tasman Migrants”,in Manying Ip (ed.),Transmigration and the New Chinese: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pp. 57 -101.
关于新移民的流动性。新西兰华人新移民为了探家和做生意,成为穿梭于太平洋的空中飞人,是其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新西兰社会对新移民的这种跨国流动有所诟病,称之为“对新西兰不承担义务”。叶宋曼瑛指出,从新移民外迁的长期数据看,华人很少永久离开或离开一年以上,相应比例低于英国人。另一方面,若从短期流动的角度考察,亚洲新移民无疑是流动性最大的群体。④Manying Ip,“Chinese Immigrants and Transnationals in New Zealand:A Fortress Opened”,p. 351.华人移民的流动性引发人们将其与淘金时代的华人加以对比。叶宋曼瑛指出,新华人仍在流动,但他们不再是无权在新西兰居留的暂居者,他们大多数是新西兰公民或拥有永久居留权者,只是目前中国的就业市场和经济环境更具有吸引力,才使得新华人选择成为跨国公民。⑤Manying Ip,“Still Floating:No Longer Sojourners,but Transnationals”,in James and Kember and Paul Clark(eds.),China and New Zealand:A Thriving Relationship Thirty Years on,p. 44.另外需要指出的一个研究趋向是,华人新移民的流动性已经引起学术界关于移民研究的新思考。新西兰新移民政策实施20余年以后,华人新移民持续流动,显然不能或不肯在所在国或原籍国“永久地”安顿下来,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以往移民研究的传统概念是移民是定居的前奏,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华人新移民显然没有表现出定居的趋向,而是在新家和原籍国之间穿梭往来,也经常移往第三国。针对这一现象,近年来学术界有“循环式跨国移民”概念之提出。叶宋曼瑛依据对多代、多地华人移民的采访所获得的实证数据,提出当代的移民过程是循环式和持续性的。移民家庭根据家族成员在不同生活阶段的特定需要迁移和重新定位,华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极具灵活性和弹性。⑥Manying Ip,“Rethink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irculatory Transmigration:The New Zealand Case”,in Manying Ip(ed.),Transmigration and the New Chinese: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pp. 21 -56.
(四)新老华人社会之关系
有关研究集中于新老移民社会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和谐。有研究指出,新移民来源地呈多元化分布,而且各地的工业化和西化程度差异很大,新移民的不同群体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观念和行为,他们的到来给曾经是同质化的新西兰本地华人社会带来多样性。⑦Elsie S. Ho and Ruth Farmer,“The Hong Kong Chinese in Auckland”,p. 221.叶宋曼瑛的研究揭示了新老华人社会间的微妙关系。她认为,新移民表现出了与新西兰本地华人迥异的生活样貌,二者之间除了同一的种族渊源以外,共同之处不是很多,尤其是新移民的许多“非新西兰化”行为举止令老移民感到困扰。对已然同化的华裔新西兰人来说,说中文、信奉迥异之价值观、展现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华人大量出现,是令人困惑和不安的,而新移民的数量优势则意味着针对新移民的排外主义会把已经同化的华人移民卷入其中。针对新亚洲人的排外主义促使许多华人长期居民公开与新移民保持距离,许多人把种族主义的复活归咎于新移民。①Manying Ip,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pp. 126,143,8.David Pang对奥克兰某小学的入学资格加以个案的研究,表明新移民正在挑战新西兰华人传统的低调形象以维护自身的权益,他们的这些举动已经造成了与新西兰原华人社会的某些摩擦。②David Pang,“Education,Politics and Chinese New Zealand Identities:The Case of the 1995 Epsom Normal Primary School’s‘Residency Clause and English Test’”,in Manying Ip(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 237 -252.
(五)华文传媒
有关研究关注了新移民时代华文传媒的新特点。有学者指出,华文传媒的大量消费唯有在相当数量的人口懂中文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即华文传媒的命运与移民趋势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华人数量的增长,华文传媒大量涌现,形式多样,如报纸、周刊、杂志、电视、电台、网站等。另外,21世纪的华人社会因移民来源地的多元化而支离破碎,新西兰极其自由的公共传媒政策可以使少数民族传媒不受约束和控制地发展,已经引发了创办平面媒体的大潮,其质量则极不均衡。③Manying Ip,“Chinese Media in New Zealand”,p. 178 -179.
六、结 语
华人移居新西兰迄今已有150年的悠长岁月,在天遥地远的南太平洋,华人移民在历史风云的无常变幻中饱经族群和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留下无数悲喜交织的故事,有待探寻与书写。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新西兰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尚可从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推进。首先是历史资料的充分发掘。关于新西兰华人史,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存留,见诸当时的报纸、国会的辩论记录、新西兰政府有关部门的档案、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档案,等等,有待于更为深入和全面地发掘和利用。其次,加强研究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可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透过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加以综合考察,从而对新西兰华人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和面貌有更为全面而精准的呈现。在华人经济版图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拓展的今天,相关研究成果将会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以资借鉴。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经济·管理】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
[作者简介]张 丽(1963—),女,辽宁大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英关系史、香港史等方面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5 -10 -27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072(2016)02 -0053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