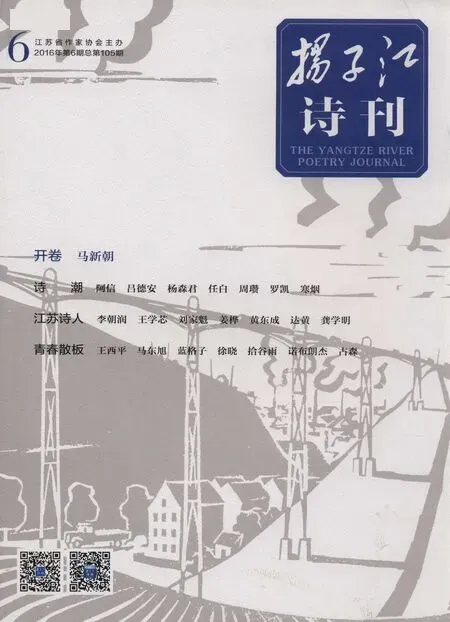北方居者(组章)
2016-11-25王西平
王西平
北方居者(组章)
王西平
王西平,1980生,现居宁夏银川。
从臃肿的自身里牵出一只花碗
所有的人,那是什么。
只有几句话,就各自隐入一段冰冷。
噢,男的,和摆弄弯管的钳子,你潮湿的下身,带着一根腐肉回到从前的果林。
你出门就遇见奇异的植物,遭遇锯齿般的表达,和盐味覆盖的自我。
你所看见的水,源头指向涤荡的谣言,以及被巴列霍的男孩捣碎的土豆泥。
你一生只负责启用小剂量的呼吸养花,喂金色的鸽子。和你的女人,携带一生的厨具,跃入美味的天空。
请相信,你就是那个用臂弯重建夏天的男人,就是女人孵化的“日常”。
因为,你懂得以麦子的方式和解,以麦子的方式炸裂。你的花篮里盛放着花花绿绿的“意外”。
你搬运十万座罗马围攻一段两个人的荤素史。你加冕于荆棘丛,起步于下沉的肉身。
然后,在自己的王国里,给每一种食物修建相册,为静脉间扑腾的油虾速写一勺淡水,为每一粒方糖安装棱角,为粗粮武装的甜甜甜甜圈谱写一首口唇诗。
“四块,汤圆。汤圆,四块。”你站在自己的舌尖上叫卖。
从臃肿的自身里牵出一只花碗。碗中扑腾着驴皮、生姜,和溺水而死的雏鸡。
更远处,那镜子遥远的内部——有人正不慌不忙地将一套餐椅拖拽而去。
夜色朦胧,你穿越马路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果腹之欲。
七日喵咪之春
字字废,词词弃,仿佛散架的鱼骨碎。
想到这一点,我时常奔涌起来,在纸上开凿一条唐渠,疯狂遐想,冲向了油墨堆砌的沙滩。
哦,这不是梦境,是现实。命里缺水的我,一生行走在荒原深处。那里的一生,只有七日。一二三……野花日日盛开,田野夜夜铺展。蓝色的小油伞,白色的芨芨草,我熟悉的绿植,第四日,第五日,他们越过黑色的土界,与杂草为伴,活着,然后死去。
是的,我,徒有一个忧郁的想法,诱发蓝色的裂口。
突然想到了灰色的土瓷,前几日家里的花瓶碎了,那瓷口,像一个星象的组合。
我说,一定是马尔克斯之花,一定是孤独滋长出的香蕉,一定是孪生猴子生出了艳丽的羽毛。
火苗在星盘上跳动,那里有异形虫,史努克,吃微光的少年郎。
还有一大群人(或者起立行走的生物)围着第六日欢愉,随叶子摆动。噗噗,生出新的甜翅。
飞翔吧,携仙侣告别蜂房,关于自然,我们拥抱,伏身沾染花粉。
恰好无风,日光静好,孩子们都来了,火猫点燃了喵咪之春。
是今日
窗外,一切都是“过往”,像电影一样奔跑,带着云雾氤氲。
然而停滞不前的,唯有停滞本身。
我扫了一眼:时光之雨打在叶子上,重音击在砖块上,一个人紧挨着另一个人,他们争吵,背靠背,又大步走进空洞洞的阳光。是今日。
一只鼹鼠钻进了地洞,我却不能。插上冥想的翅膀吧,鼹鼠的世界在夜里,像半截黝黑的烟筒一样出现。是今日。
更深处,一本半腐烂的漫画书,发出一种细微的声音:翻阅它。漫画的主人,曾经活着,和一只灰色的钟共享一枚时针。是今日。
猛然惊醒,扫了一眼,窗外,墓前,安放着果子,风轻轻吹打着馥郁的花篮。是今日。
哦,甜蜜之渡,饱满之渡,死死地,咬住金色之钩。对岸上演着胡商争相求购的故事,他们为了一颗象牙,为死亡封印。是今日。
是的,楝树花盛开。我和一顶鱼架撑起的衣帽走向弗罗斯特的鲍镇。那里有许多人,在诗行中追赶着硕大的蜗牛,它们遭受极限与速度,它们倒挂在地狱的树上咕咕发笑。是今日。
我无法将自己的轮廓,铸成硬币的两个凹面,无法让冰冷的银矿开口说话。是今日。
无数的人,死于哑然,失笑,死于胡乱翻转。一场告别终究是一场告别。还是今日。
北方居者
传说中的,关于鲸群的离去,源自于你,嘴唇轻碰的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海。
每个北方的居者,一出生,伴随着牛羊裹挟着白云,便是离去,或亦步亦趋,覆盖着青色的记忆。
也是优秀的牧人,摧毁了书中的圣地。通往那里的路,便是漫无目的的黑暗,不是梦,而是恶,我们孤独地漫游,没有停下来,因此,而失去了光泽。
人心是一面广阔的镜子,波澜不惊,却暗藏寂静。
而真正意义上的外在,呈现出一种宏大的诉说,一粒砂石的金斯博格式的嚎叫,一缕风的金色麦浪间的支离。
北方的居者,在狂野中伏地而走,像流水,注入荒原。白色,月亮,统统闪耀着静物的光芒,死亡的饲养员,他剩余的水果处女般滑润。可风景并未因此而点亮。
唯独那青蓝色的妖,一个接近男式女娲,站在戈壁的尽头,扬起枯叶。那么,阳光静美,照射在青稞上,酒水倒映着死寂的屋顶,飞鸟飞啊,生出了新的装置——振翅。
我们漫无目的地活着,仿佛一块无穷的大幕上,涌动着盲目的黑蛇,不在乎星星的闪亮,不在乎法力的无边。只有在玉门,吹笙人被裂口淫笑,音乐滋养着风格,或在高山上,站在距离外翻转,护送一头耕牛和它的家眷过河。
我们所祈求的田园,看上去气质正在塌陷,杂草丛生,灰鼠吐露着蒸汽……
这是北方,动物们用自己的脊梁搭建起了移动的山坡,花木和怪石,恋爱的鸟群,还有那未有人居的日子,看上去都消失了。
是的,北方居者,在封存的内部,有一颗被自然鞭挞的“人性”。
我们与紧闭的绽放结缘
阳光下,茁壮生长的酸菜,混合着日常的瓷味。
当鲜花有了水果筐,运送就是一件华丽的事件。
它们如此高傲,在中途,隐藏着半腐烂的讯息。
我们与携带的花期西行,轻松跃过高耸的云层。
这远比鸟更傻的告别啊,只是剧幕掀起的一角。
更大的轰鸣,来自一千零一夜的天空,和混乱的蛙式碧池。
汽车两侧,栗色之神翻卷着亚麻发辫,它说:“高速公路和鸟巢才是世界的两极。”哦,孩子,大人,和雨夹雪,统统隐入味道的国度。
我们透过历史,嗅到了迷雾的味道。我们一路向西,拥抱白杨叶的两面,热爱野色和野蛮的两面。
穿过一颗心的中央,我们将成为夜色孵化而来的怪兽。
呼喊着,伸出喉咙深处的黑手,撕扯着“康老子将冰蚕丝织物高价卖给波斯人”的故事。
我们和更多的人,只许穿着魔咒的戏服跳进乐园,我们需要花重金赎回绿霾,需要胭脂涂染下游的河域。
如今,在路上,我们以骨为箫,吹皱朵朵雏菊。
我们与紧闭的绽放结缘,给自己不留一丝罅隙。
裸露,但终将隐入叶片
两个人挤压出裸露,在伦理学院,出售肉乎乎的裸露,“那样真得很好吗?”
是的,他们在草丛里,翻滚,折断草茎流露出的嫩液,和白色的啤酒沫混合在一起。旁边是烤熟的黑鸭子在飞,蝴蝶开道,展翅,斑点渐渐在云烟中散开。
他们手持古铜色的面包刀,在复音节的花毯里沐浴,蚂蚁口含着睡眠之水,或吐露着黑色的槐蜜。
天地之间,他们自视为王,万物环绕着小小的城郭,这些日常的生活,不分昼夜地复制着通俗:隔着墙壁喊粗话,在静物的相册里捡拾鸡毛和蒜皮,像蜗牛背负着一万吨鼻炎胶囊穿越牛绒丛林,或像一群扁平的动物编织着闪电的树冠。
总之,爱,与不爱。他们携手在一只美丽的瓷国,搬运盐味重建一个完整的夏日,哦,品尝美食的倒影。
关于杯碗的学说,残羹冷炙的内涵,大腹便便的歌谣主义……
他们躺在大地的一角,仅有死亡占据了纸灰一撮,仿佛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一生”。
他们轻轻地吻啊,用湿软的舌尖一点一点地运输无援的“尽头”:那里,有牧牛的郎,有织布的女,有盲目的风,有斜桥,和错误的美。
他们是在挤压着裸露,在高大的立柜的中枢神经里,激起了玻璃之花。
他们祈求,焚香,用一切抽离的鞭,驱赶着牵牛花里幼小的牛。他们还牵出所有的词语,用冗长的祈使句抡起板斧,出走,劈开手掌,回到果中。
是的,他们裸露,但终将隐入叶片,像默片,展演着夏日里的热症,和厮守相爱的罪证。
没有终点,两个人或食无味
那样的表情,接近黄昏的冷杉,乡村,和飞鸟,遗留中的漆黑,快速退向云层。
我们鼓动着身体里的皮球,走向深夜,内心犹如红色的粉剂。一对悬浮的游魂。
一个,仿佛从一个字眼滴漏的另一个人。我们坚信这种孪生的理念,将诱引爱情跃入纸内,书写偶语。
“事实上,他只是我裙下的一只小猴”,清晨,走向街道,一起享用老板戏耍的特权,一起忍让店员推让的凄切。
没有终点,两个人或食无味。天使的阴影耷拉在畜栏上,星星茂密,肉铺林立,群兽汹涌而至。
我们共同举起赭色的酒杯,互道晚安。
法力消减在面包上,仿佛白脸的麦子,粉饰着一层黑雨。
亲爱的,“我的树在一个世纪之后将仍然被误会曲解”。
但它热力无数,在贫穷的山坳,低矮堪比茅草之林。一株与另一株,间隔着无数个未来,然而,田地便是粮食的中心。
透过冰凉中升降的土豆,和椭圆形的叶片,我们兀自寻向月亮的出口。
更远处,停泊着用心修筑的枯墓,前世的倒影映入其中。
云也退。
深山露水雕刻的记忆
葡萄的藤和枝肋,在霓虹之下,在玻璃杯反射的渍点上,变成酸甜的臂弯。
亲,饮下这一口,只是一个开端。我们或像孩子那样,在风暴转瞬即逝的折角里,熟睡,或潜入那紫色而又温润的液面。
我们不得不下沉到童年的状态,矮于花草。甩掉童话中的矜持,又像飞翔的泡泡那样,被强大的酒力快速托起。
哦,我们,在自己的饭袋里,掏出了臼齿的花冠。今后,你,我,我们,内心一定装满了成熟的果子,仿佛来自深山露水雕刻的记忆,枯烂的群星。
寄居的神啊,我们在小小的山坳里酿造时光,酿造一切白刃之上的光芒。浑身涂满油彩的神啊,仿佛十万只捆绑追踪的飞虫,夜里被绣花的法力扬起。
亲,饮下这一口,只是一个开端。我们携手钻进醉意朦胧软绵绵的纤维丛,我们穿越人群的黑色颗粒,我们被道路两边的木讷的植物分泌。
我没办法把一段楼梯,变成一段溪流,将人间的苦楚送往云巅;我没办法将一炷香火,插入你菩萨的泥身,晃动一批新鲜的窈窕山鬼。
我触摸到的潮湿,只是牵牛花中的芬芳。无计花间住的人儿,这是一个不相误的尘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