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城市,两类女人
——池莉新世纪小说初探
2016-11-25高国丽
◆ 高国丽
两种城市,两类女人
——池莉新世纪小说初探
◆ 高国丽
池莉从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已历35年而创作颇丰,其中经历了数次转变,变中有常,常中有变,逐渐形成了老练独到的个人风格。池莉一直以市民立场关注凡俗人生,她认同的“俗”不是恶俗,而是她多次解释的“有人有谷子”①,是真实的现实。80年代初期以《月儿好》为代表的系列作品虽粗疏稚嫩,且有模仿“文革”结束后复苏的主流人性论叙述的痕迹,但透着悠扬的灵气和诗意;自1987年《烦恼人生》以来,池莉开始用“新孩子”的“新眼睛”观察市民“神圣的烦恼人生”②,开凿市民庸常生活的“诗意”,与欲告别理想主义的社会转变不谋而合,很快在文坛引起轰动;90年代的中国社会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发生了剧烈变动,《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口红》等都市言情小说偏于传奇性,“在升腾和坠落之间”③演绎人生起伏;从《乌鸦之歌》、《水与火的缠绵》、《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到《所以》,池莉频繁地书写女性在家庭和历史中的命运或情感婚姻状况,似乎自觉地开始为她们这一代“新孩子”的生命经历命名。对于世俗生活,池莉不像之前那样单纯地表示认同,而开始透露出些许批判意味,并重新对她曾经“撕裂”的理想主义抱有一些期许。当然,35年来池莉创作的丰富性不能简单地用这几条线索涵盖,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她对市民生活的极大热情,和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持续关注。
汉味浸透的城市(武汉)一直是池莉写作的土壤。到了新世纪,池莉开始表现城市的历史和记忆的印记,侧重于书写家族历史中女性命运在城市中的变迁。细想来,池莉笔下的城市分裂成两种,或者说长着新/旧两张面孔:一个是现代化的都市性武汉,另一个是颇有乡土味的城镇性武汉。
当代中国关于城市形态的想象总体来讲分为两种: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摩登都市和以北京为代表的文化性乡土中国。赵园把北京的特点描述为“田园式的城市”,“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虽然“与乡村生活结构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④,这是跟现代化的大都市对立的、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一种城市形态。而陈思和以张爱玲的上海书写为例,把区别于“颓败”、“浮纨”的摩登都市的城市形态描述为“都市民间”,一种从底层发生的、与国家权利对抗的民间文化形态⑤。池莉在《生活秀》(2000)和《她的城》(2011)中描述的老城空间介于赵园和陈思和的描述之间,它不同于“田园式的城市”,也不以对抗性为特征,这些城镇性武汉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到现在还是破旧的充满商业气息的小商品市场,坚韧而顽强,却在历史变迁中被挤兑到城市褶皱里,是一个保存了乡土味的边缘存在,由商贩小摊、老房子、里分古巷、街坊邻里等构成。它曾是最早开始商业化和城镇化的地方,却在现代化进程中停滞了,被甩在了城市的尾巴上,但这里又滋生了最原始最朴素的市民伦理。这是一个共时的、静止的城;而《水与火的缠绵》(2002)和《所以》(2007)描绘的新城虽现代却不很摩登,是一般意义上的都市,由工厂、单位、公路、咖啡馆、公园、写字楼、公共汽车等风景构成,是历时的、线性的、流动的、承载着社会和历史变迁的现代化空间。
池莉的两座城市对应着两种女人:老城里典型的市民阶级女性和新城里的都市中产知识女性,她们与自己的城市分别形成一种对应和象征的关系。这两种城市空间和两种女人的背后是两种生活逻辑的对立,老城代表的是以几代居民知根知底的信任为纽带的街坊伦理,新城背后是洪水猛兽般发展主义的现代的逻辑;同时,在文本的构造中,池莉明显地把情感认同投向了行将消失却依然顽强的老城,通过让新城里的女人在老城里找到情感依托这一象征性表达,把老城塑造为具有治愈性的“藏污纳垢”的乌托邦。
一、两种城市空间和两类女人
老汉口本在民国时期就是武汉城市的起源地,在改革开放的小商品潮中重新苏醒,新武汉是八九十年代都市化进程的产物,这两种城处于一个并置的空间,却不是同一个武汉。一个是静止的精确的,一个是流动的模糊的,这两种城中住着两种女人,她们和两种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参差的律动。
1.两种城市
书写这两种城市空间,池莉用两种感知时间的方式来传达两种空间的特征和区别。正像《生活秀》中来双扬的生活方式,“白天要睡觉,晚上做生意”,一天从下午三点开始,吉庆街的沸腾从晚上开始,城市的每天是有规律的,重复的。《她的城》对老武汉的城市节奏表现得更明确:老武汉以早上/中午/晚上为感知时间的单位,每天像是同一天,只有流逝和重复,却没有真正的变迁。“这个城市没有早晨,一切从中午开始。”十二点过后,城市开始兴奋,然后蜜姐坐在店里,招呼着来来往往的客人,直到晚上八点打烊。以蜜姐擦鞋店为代表的老城在时间上只有早上、中午、晚上,“天天复天天,年年复年年”,这是抽空了时间的旧城,这里的时间只是轮回。同时,老城的空间也是定格的,水塔街的联保里是武汉最典型的里分,吉庆街是武汉最古老的街之一。这里的房子是建国以前就修筑的,时间让它们陈旧,却没有产生空间位置的变化,它们依然是稳定的,这样一种稳定的时间和空间在心理上给人一种安全的依托。
不同于老城用早上/中午/晚上来感知时间,新城总是用季节的轮回来推进时间和叙述:“秋天的长江”、“转眼就是深秋了”、“寒冬到了”、“这是一个疯狂的春天”、“春天又来了”、“这又是一个不正常的春天”,不断地指明情节发展的季节,或者用季节来带动情节发展。从春到冬,武汉四季很分明。季节的交替便是武汉这座城市独特的时间语言。武汉地形特殊,造成“冬抱冰夏握火”的气候特点,《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开始通过季节感受描述武汉的市民日常。正是这种明显的季节感受无意中开启了池莉以温度/季节感受时间流逝的写作方法。季节的轮回在流动中伴随的是城市的历史变化,同时,季节的交替不是圆形的从春到夏的轮回,而是线性的往前推进,这个过程和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这样一种时间带来的是流动感和对变化变迁的惶惑感。“无根的、被不断的扩张、重建与流动所构造着的都市,似乎以某种内在的想象性应和、抚慰着一个孤独的‘新孩子’。”⑥《水与火的缠绵》中存在着一种复杂的象征性书写。季节的春夏和秋冬,城市的复苏发展和矛盾焦虑,火与水之间分别存有一种模糊的对应关系。池莉以季节的轮换推动历史的变迁,在骚动的春天,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对应的事件是燕子、邝园、肖克等人去了广州和深圳,新的时代来临,芒芒进入“热恋期”,芒芒和高勇领取结婚证。而发生在秋冬时节的是:高勇的出现、二人相处出现问题、搞砸的生日、爱情幻想破灭、婚礼(魔咒)等。时间的顺序和发展的顺序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的一致性透露出一种发展的逻辑和秩序。
除了叙述时间带来的静止/流动的差异体验,两种城市还有精确/模糊的空间感受。亨利·詹姆斯的学生珀西·卢伯克在《小说技巧》中讨论过小说的“画面”和“戏剧性场面”的关系。卢伯克认为小说呈现给读者看的是轮番出现的画面和戏剧性场面,画面是叙述者在场描绘的,介入性强,而戏剧性场景是在聚焦灯下主人公自己表演的,叙述者隐退了⑦。老城的画面感很强,用大量细节和耐心的叙述打造了一种毛茸茸的精确质感,在叙述精彩的地方叙述人引退,人物和场景开始自己表演。呈现的是一种定格的抒情性的画面感,感觉大于故事,我们脑中总有一幅画面:蜜姐坐在联保里的擦鞋店柜台前,一口一口漫长地抽烟,打量着来往的人和不变的城,颇有抒情意味。而到了都市之城中,大量的“一笔带过性”的描述代替了“戏剧性场面”的呈现。池莉放弃了精致的描写,取而代之的是探讨两性关系的自白性的分析和议论,常常用概述性的语言扫过流逝的时间,很多故事在场面和跨度上没有展开,具体的描写和玩味少了,跟老城的描写相比,美感上显得不足。这不仅是因为后者处理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因而不太需要聚焦在某一个场景中,更是为了传递现代都市的模糊感,而不是老城的精确感。比较这两种描写方式,老城作为一个可能要消失,并且不会再生的空间,在叙述中被池莉带上了怀旧的意味。对她的注视和把玩有种把城市他者化的视角,把她当成了欲望的对象,所以要用倾注抒情性的画面感来呈现。池莉常常认同市民的价值取向,因此对这一古旧的商业化城市空间自然而然地倾注了一种审美关照。
2.两类女人
这两种城中住着两类女人,一种是曾芒芒、叶紫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另一种是来双扬、蜜姐代表的典型的城市市民女性。对于世纪之交女作家笔下用女性写城市的一批作品,贺桂梅将其指认为世纪之交怀旧视野中城市和女性的同构性书写,城市往往长着一张女性的面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之于北京胡同,王安忆《妹头》中的妹头之于上海弄堂,池莉《生活秀》中的来双扬之于武汉吉庆街⑧。其实来双扬与吉庆街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谈爱情》中“丈母娘”与“花楼街”的补充书写,而这组形象在《她的城》中借蜜姐和水塔街联保里进行进一步挖掘。如果来双扬作为城市的“主体”代表着吉庆街,她和城市是同构的,那么吉庆街的形象就是这个既能干又被欲望化的女人形象,同样,作为“人精”的蜜姐完全能胜任水塔街的代言人角色。可是到了现代之城,这里渗透着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如果去想象这样一个城市的话,我们的脑海里可能会浮现一个健壮的、西装革履的男性形象,他代表着一种前进的发展的面向,比如《生活秀》中的卓雄州或《她的城》中的骆良骥,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揭露的:野心和前进。但我们看到池莉还是把主人公写成了一类渺小的女性:《所以》中的主人公叶紫,就像“叶子”一样渺小而没有任何影响力,从小在家庭中不被重视,后来在三次婚姻中“拾取”了三次创伤和一次背叛。《水与火的缠绵》中的曾芒芒听起来就是“真茫茫”(迷茫)。所以,曾芒芒和叶紫这类女人和城市的关系不同于蜜姐、来双扬的主宰性,她们不仅不能对城市起到任何支配作用,反而被城市决定着。她们代表的就是人们对于现代这种城市逻辑的迷茫和无力感,在这样一种迷茫、渺小、无力的情绪上,曾芒芒和城市形成了一种象征关系,她们总是不能驾驭生活和城市,她们和城市的同一性更像是在性格上。《她的城》用自恋的口吻将这个城市的特点描述为“敞——的”:“这就是武汉大城市气派”,也就是推心置腹、毫无保留,这也是蜜姐的性格,而曾芒芒的城就像曾芒芒的性格一样,像是“水与火的缠绵”,水与火即是季节的表征,也象征现代之城既“火”一般发展又“水”一般迷茫的状态,就像既热烈又寡淡的曾芒芒。
这两类女性代表着城中女性的两个阶级,她们的差异本质上是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对立。对于这两种女人的解读可以从池莉使用的对“手”的修辞来分析。《水与火的缠绵》关于城市和女人的想象落在曾芒芒的婚恋故事中。写曾芒芒之所以选择高勇,始于“这只俊美的手”:
一只手出现了。曾芒芒首先看见的是一只手。高勇的手。这只手伸到她的面前,递给她一小块面包……它是修长的,健壮的,优美的,它肤色洁净,血管清晰,骨节有棱有角,他指甲椭圆又光滑,透出健康的粉红色……她感觉自己的血液改变了方向和流速,都朝这只俊美的手汇聚。⑨
这双手因其“坦白而丰富的表情”终于“说服”她选择了他。有意思的是,这次曾芒芒作为一个女性,竟然对男性投去了“看”的目光(一般都是男看女,女“被看”),她用欲望的眼神注视着这双手,一向比较“延宕”、缺少行动力的曾芒芒竟然在主动出击。而相反的是,在老城中,女性的手作为一种客体被这样注视着:
逢春在一旁已经把手套扯破了,脱下来了, 卷起来丢进了垃圾篓, 一双年轻的手被闷得潮湿苍白,青筋毕现,在她手背上画了水墨一般, 却也有一种惹人怜惜的好看。骆良骥一瞟一瞟的。⑩
“手”作为一种身体语言,承载着骆良骥“一瞟一瞟”的目光,池莉连来双扬都不放过:“来双扬就是一双手特别突出”,“用她皎美的手指夹着一支缓缓燃烧的烟”,“卓雄州最初就是被来双扬的手指吸引去的”。《所以》中也出现过叶紫为了“勾引”禹宏宽主动展示的手指。但蜜姐吸烟的两手指是黄的,不再是被看的对象,因为其实在《她的城》中池莉对蜜姐的形象做了一些男性化的处理。
以上呈现的池莉关于城市空间中“手”的修辞意涵丰厚,“手”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欲望对象,在两种叙述城市的文本中对于“手”的不同呈现,背后蕴含的是两种审美形态和婚恋标准。身为中产知识女性的曾芒芒,对爱情抱有一定的幻想,想寻找的是“橡树和木棉”般平等的爱情:“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红硕的花朵”。曾芒芒本来是一个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有追求有幻想的女青年,但生活使她在城市中丧失了自信。相反,市民女性怀揣的是一种实用主义价值观,这是一套“过日子”的生活伦理,所以她们理想的对象是有钱、懂得欣赏自己的美、体贴的成功男士,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本身把自己置于一个被看的位置上,她们要用自己的美貌去吸引理想的男性。知识女性保持的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所以关于她们的故事结构只能是一个期待——失望——破灭的悲剧性书写。而市民女性一开始就切实,安命,所以能处乱不惊,承受生活的一切不可承受之“轻”和“重”。这不仅代表两种婚恋标准,更是两套价值伦理和生活哲学。
3.两种城市风景
这两种城市空间拥有不同的城市风景。一种是固定的、陈旧的、有记忆的,另一种是行走的。老城的风景就是联保里的一切:水塔、商铺、里分、狭长的街巷、吊脚阁楼、小天井,尤其以巴掌大的蜜姐擦鞋店为核心。蜜姐擦鞋店位于最繁华的水塔街,但特别狭小,屋子一楼用蜡染的印花帘子隔开,里面供做饭和吃饭,外面当擦鞋店,二层是凌空搭起的一个吊脚楼,供婆婆居住。后门出来是长长的弄堂,联保里临街的房子“老朽破败”,路面“到处开裂,污水横流”。这个空间风景并不是一个诗意的完美存在,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藏污纳垢的市民生活的空间,对空间的过度利用给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狭窄和局促。这种空间描写传达了老街的命运:一方面她粘着城市记忆,顽强地、稳定地屹立在那里,永不会消失,一方面她已经被现代都市挤兑到狭小的空间里,似乎越来越“窄小”。
而新城里的风景主要是行走的:公共汽车和轮渡。武汉是江城,形成了“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的空间结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很多时候市民都要乘坐轮渡和公交车等公共运输工具。而公共汽车、轮渡形成了武汉独特的行走的城市风景,正切合了新城的流动性。池莉很注重以交通工具这种行走的风景来表现城市,《水与火的缠绵》中公交车、轮渡、飞机、火车等出现了数十次。曾芒芒生活中的大事都和公交车或轮渡有关:开始讨论个人问题、遇见高勇、结婚遭劫、分娩。在这里它们也不只是运输工具,以公交车为代表的运输工具就像是“都会的血液”,促成了城市快捷的流动性。这一城市风景处在一个行走的过程中,公交车代表的是拥挤、快速的城市特点和节奏,车上的人不会关注窗外的风景,却会关注车上的风景——陌生人。这是一个与陌生人交会的公共场所,其中大多数人是和自己相似的城市居民,也有一些施加性骚扰(破坏)的男人。这是一个可以公开观察别人和反观自己的场所,是城市缩微的一个断面,为人物的独白和思考提供了一个空间上的心理时间。池莉还特别描写了一些泼辣豪爽的女售票员形象,泼辣豪放刻薄的女售票员和拥挤慌张的公交车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公共汽车、轮渡是连接家庭和单位的一个缓冲地带,是一个人免于单位或婚姻家庭干扰的、可以独立思考的空间段和时间段,是一个难得的城市“真空”状态。这些公共空间往往以热闹的场面呈现这种都市生活的公共的一方面,人们既讨厌公车的拥挤肮脏,又离不开它的廉价快捷。以公交车、轮渡等为载体的公共空间表征了城中女人的精神状态,是都市女性心理的一面镜子。在这个空间里虽然吵吵嚷嚷,但这种吵嚷只能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公交车和城里的人一样准时准点地奔这奔那,支撑了城市的运转和现代化。如果说来双扬和蜜姐还能作为那个老城的主体性存在,融洽地代表那座城,那么曾芒芒和叶紫与城的关系,似乎有一种模糊的无力感,她们焦虑的精神状态和城市的紧张和高速之间形成一种象征关系。
二、街坊伦理与现代逻辑的张力
这两种城市空间塑造了两类女性,两类女性又反过来代表着两种城市空间。这两种城市空间承载的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而背后反映的是两套大相径庭的城市逻辑间的张力。以蜜姐为代表的老城象征着由几代城市居民传承下来的街坊伦理,和曾芒芒联系着的新城则象征着不断往前发展的现代逻辑。
1. 两种历史意涵:文化和发展
这两种城市往往会选择不同的叙述顺序进入历史。新世纪以前,池莉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按时间顺序来结构、推进情节的发展,但到了描写老城,池莉选择了插叙的手法从当下插入老城的历史和记忆,老城是一个静止的、永恒的城市空间,与新城相比较而存在,属于一种稳定的当下的空间。以插叙的方式进入老城的历史,先写老城永恒的、定格的当下日常状态,然后在人物关系的介绍或事件的发展中由人物讲出相关的城市历史,并把历史转换成了老街的文化积淀。从一个稳定的城市空间延伸出来的历史变化并不能对城市空间和人物性格造成什么影响,所以城里的人就算经历很大的变故,但当她看到“大街上的一切,都还在她眼睛里”的时候,就能处乱不惊,很快回归生活。蜜姐中年丧夫,也曾痛不欲生,但她之所以能很快回到做生意、带儿子、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因为对于城市,蜜姐是可以把控的。在这里,大历史是外在于蜜姐和来双扬的,历史在她们眼里被“自豪地”置换成了城市的历史,而城市的历史是她们的祖辈创建的,所以历史就是她们的家族史,是城市的文化积淀。换句话说,历史的意义在老城中被转化成了稳定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家族记忆。《她的城》呈现出来的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混杂的,她是一个新旧交接地带:
前五街道两边都是商铺!多卖内衣袜子……而中山大道那边!是近年崛起的商厦一幢又一幢!玻璃幕墙巨幅广告!光怪陆离!赶尽时尚。
“商铺”都是解放以前的老建筑,“商厦”是近些年崛起的新楼。而蜜姐的擦鞋店就出现在这样一个交叉地带。这里不全是老建筑,甚至还有酒吧,但酒吧也不是灯红酒绿的那种酒吧,而是洋人开的“窗明几净,音乐低回,歌手现唱,烛光花草,香氛氤氲” ,咖啡飘香的文化酒吧,代表一种缓慢悠闲的老城文化。蜜姐擦鞋店是作为这样一种城市空间的集中代表出现的,“店子小更合适立体地密集地充满各种文化因素”,有趣的是,大学生们常来这里拍照和玩自拍,因为它是历史积淀最浓的地方,把城市的历史书写成文化积淀,有一种为市民文化寻根的意味。在解放以前,蜜姐的祖父和丈夫宋江涛的祖父“开创了汉口这个城市和最先进的城市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老城的历史被转换成了积淀的城市文化和街坊间的伦理。
而在新城中,池莉选择顺叙来讲述历史和命运变迁,从1980年到1998年,从曾芒芒开始谈恋爱到准备离婚,从改革开放到抵抗洪灾,当代历史的发展、人物的故事和小说叙述的推进是三位一体的。在这里,城市的历史被置换成了现代这样一种线性的发展逻辑。在历史中完成的是流动的沧海桑田和社会巨变,这样一种变动、不稳定的历史之中,“文革”、被打倒、改革开放、市场化、失业潮、下海经商等使人的地位也容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邝园从昔日的锅炉工变成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并突然因病去世,高兰曾经是给毛主席表演过节目的富家女,后来却只能当一个卖汤圆的女工。这个城市是一系列历史变迁的产物。历史发展带来的不稳定和冲击,使得恒常的东西在瓦解。《水与火的缠绵》开头和结尾时间的选择颇能说明问题。故事始于反复点染的1980年5月的某一天,父母解除了“我”的禁忌:可以谈个人问题了。同时,与反复出现的汽车、飞机、轮船形成对照,这个城市开始醒来、复苏,走上现代化之路,发展经济了,这是一个春天。而结尾设定在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这种灾难本身蕴藏着对从1980年到1998年这个发展过程的反思,洪水造成轮渡停航、公交被淹、机场被淹,现代化带来的一切硕果都瘫痪了。《水与火的缠绵》开始于现代的发展,结束于对现代逻辑的反思。
2. 街坊伦理和现代逻辑之间
池莉把两种城市背后的意识形态阐释为两种逻辑间的对立。其背后街坊伦理和现代逻辑的张力是通过分别标出异项来实现的。以城/乡的格局标出了老城的城市性,以武汉/深圳(或广州)的关系格局标出了武汉的现代性。
池莉的写作一直以来都似乎渗透着一种城乡之间的等级判断。《生活秀》中把城乡关系书写成了来双扬和九妹的关系。九妹的母亲对生活的憧憬是“有钱,有城市户口,有饱暖的日子,有健康的后代”,而久久就算健康也不会娶九妹是因为九妹毕竟骨子里是乡下姑娘,来双扬那样的生活是乡下姑娘九妹的奋斗目标。《她的城》中写道,“乡下女孩进城!一是文眉!二是染黄发!三是穿吊带!四是说拜拜”,“到底是农村女人,进城十年八载也对皮鞋没个把握”,“几辈子的城市人与几辈子的农村人!终究有隔”,逢春之所以不同于别的擦鞋女,是因为她是地道的城市人。池莉赤裸裸地书写城乡间的等级差序,通过把乡村他者化来标出城市,这背后体现的是一套以老城空间为依托的市民的伦理和逻辑。老街虽是稳固的,但她作为一座商业化的城市,“是最早复苏的小商品市场”,所以宁静的表象下面也有逐利的商业逻辑。《她的城》一开始写逢春擦皮鞋,“十五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二十五分钟过去了”,逢春还在擦皮鞋,蜜姐不得不发怒了。一个恒常不变的空间里竟然也要这么争分夺秒,蜜姐的警句是“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本来是说在时间中稳定的东西才是可靠的,比如爱情,但蜜姐的意思是擦鞋工人对于时间要进行精确的算计,以更多地赚钱;而蜜姐把擦鞋改成“美容”和“养护”就是实行了“概念就是金钱”的商业逻辑。但“金钱逻辑”在“她的城”里并不是决定性的,它小于几辈人之间形成的以街坊伦理为表征的市民伦理。蜜姐就是这套自豪的、自足的街坊伦理的代表,这是一种“吃饭穿衣,饮食男女”的“过日子”的伦理,基于“城市居民之间那种因袭了几代人的无条件信赖”,是“对人情世故深谙和遵守”,“这就是城市居民骨子里头的生死盟约”,而蜜姐就是这种秩序的捍卫者。
因此蜜姐具有了“男性化特征”。在改革开放兴起的小商品潮中,这个老城“又把蜜姐塑造了一番,这回塑造的方向是革命样板戏里的阿庆嫂”,而阿庆嫂本来就是一个能干刚强却没有性别特色的女性。蜜姐是吸烟的,吸烟本来是一个偏男性化的动作,但在来双扬那里,吸烟变成了一种被别人的欲望所玩味的“风骚”,可蜜姐吸烟的时候“瘦溜的手指伸过去!摸来香烟与打火机!取出一支烟!叼在唇间!噗地点燃!凑近火苗!用力拔一口”,“伸”、“摸”、“取”、“叼”、“噗”、“拔”,完全是男人的动作,此外,蜜姐还当过“军人”,有“当兵的底子”,“总有女生男相气派”,说话也“嘹亮豪爽”。从来双扬到蜜姐,老城里的女人不再成为被欲望的对象,伴随的却是性别的男性化,其实蜜姐的男性化不是池莉处理女性问题的倒退,它恰恰有更丰富的意义。
首先,因为蜜姐是街坊伦理的捍卫者和执行人,与市民伦理不同的是,街坊伦理不仅来自市民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种无形的性别秩序。这一套伦理有底线和规矩。蜜姐的底线是“逢春不能在自己的店里出事”(红杏出墙),因为这样蜜姐一对不起逢春老公,二对不起“水塔街几代人交往过来的街坊”,三对不起阁楼上的婆婆。蜜姐做事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街坊间的影响。蜜姐和逢春表面上是老板和雇工的关系,实质上是以这一套街坊伦理为纽带的邻里关系,也正是如此,逢春作为昔日写字楼里的白领丽人才能拉下脸来擦鞋,这是一套大于金钱逻辑、大于一切的街坊伦理关系。
其次,蜜姐和逢春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暧昧性,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蜜姐形象有男性化之嫌了:
蜜姐冲上来!一把拽住逢春衣袖!逢春随之站了起来,蜜姐又打开擦鞋店大门!把逢春推了进去。进去一拉开关!忽地大亮刺刺的!两人都把眼睛一躲!蜜姐急急地又关掉了灯……反身坐在了楼梯上!抱住膝盖!说:“我的姑奶奶,这么晚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逢春动了动嘴巴!千言万语都堵在嗓子眼! 说不出来!只有眼泪先扑簌扑簌流下来了!她又要强烈抑制自己不要哭!于是肩头抽耸得厉害。
蜜姐说:“好吧好吧。我想起来了我忘记了给你钱。”
……逢春不接,哭腔哭调地说:“我又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要这个钱!这钱我不要!”
蜜姐和逢春之间的这段描写特别吻合言情小说中情侣间吵架的套路。蜜姐作为街坊伦理的代言人,本来和逢春之间是一种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但二者经历了颇有“言情”意味的一些发展以后,被处理成了闺蜜关系。池莉作为一个持市民立场的女作家,其性别观比较温和,自然不会在女性之间发展成一种同性爱叙述,尽管这样,池莉还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女性之间可以形成一种自我解放的联盟,来“一起协力对抗内心的痛苦与纠结,还有男人带来的种种麻烦和打击”。
不同于以城/乡的格局标出老城的城市性,在新城书写中池莉以武汉/深圳(或广州)的对照标出了都市的前进性,以突出这种都市空间代表的现代逻辑。深圳作为率先进入改革开放的城市,一直是武汉的榜样和先驱,是一个现代化的寓言。“去深圳”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用来应对90年代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下岗失业潮。深圳也是财富和现代化、进步的象征。《水与火的缠绵》中的燕子和《所以》中的妹妹叶爱红是这一批人的代表。深圳“是一个自由,一个解放,一个可能,一个悬念,一个心情,一根救命稻草”,其实武汉追随深圳的就是现代的前进的发展逻辑。以“深圳”的参照来表达现代都市之“变”,文中对这一逻辑的展现也体现在一些物件的升级中。比如从80年代的单位电话到90年代的家庭电话、手机,从自行车、公交车/轮渡到无人售票公交车、出租车和飞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城就是在这种发展的逻辑中形成的。深圳作为更现代的都市,一方面给武汉带来了发展和进步,主要是物质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破坏性的变化,主要是精神的焦虑。
在现代的发展的逻辑中,现代逻辑和婚姻的稳定性之间似乎形成一种背反式结构。池莉老是把现代逻辑的破坏性书写为男人发达了就要离婚或出轨这样一种模式,邝园的故事、肖克的故事,甚至丈夫高勇的故事都运作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下。他们抛弃已有的生活去深圳或广州闯荡,是为了改善妻儿的生活,但当他们真的有能力改善家人生活的时候,他们继续被一种现代的逻辑驱使:抛弃妻子,选择更好的妻子。这种现代逻辑打破了人们生活的稳定性。池莉把背后的原因书写为功利婚姻和物质婚姻的失败。《水与火的缠绵》中曾芒芒和高勇的婚姻属于双方按照自己开列的世俗标准“按图索骥”的功利婚姻。按池莉的话说:“就在我们打倒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同时,我们又以自由之名滋生了功利婚姻,就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又以经济之名滋生了物质婚姻。”池莉的女性主人公在婚姻的秩序里不断进行着“挫败”—“寻找”—“挫败”的循复探索,这使她的小说含有一丝宿命式的悲愁。因为在功利婚姻和物质婚姻结构之下,难有一个理想的男性婚姻对象。在新城中,一方面,发展的逻辑和婚姻的稳定形成一种背反式结构,把现代的破坏性书写为男人有钱就要抛弃妻子这样一种模式;另一方面,池莉也揭示了功利婚姻和物质婚姻的不稳定性。而在老城中,女性的婚姻角色颇为暧昧。贺桂梅写到,在女性和城市的同构书写中女性同时作为主体和客体,是被放逐于婚姻秩序之外的,从来双扬到蜜姐,虽然二者都是婚姻秩序之外的女性,但池莉通过赋予蜜姐一个男性化的形象(而不是一个被看的客体),使得蜜姐成为一个更具主体性的女性,她们作为城市的主人,都代表的是男性化的那套市民伦理或街坊伦理,但蜜姐最后和逢春形成了一个具有抵抗男权性质的同盟,这个同盟一定程度上战胜了蜜姐和老城代表的街坊伦理。
结语:烦恼地和乌托邦
在对这两种城市空间的想象中,池莉某种程度上安排了二者的交融。在对老城的书写中,池莉惯于安插一个外来者的视角,闯入这个稳定的城市空间。比如《生活秀》中的卓雄州和《她的城》里的骆良骥,他们都是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都来自那个现代的新城。一方面,他们给这种非主流的老城投去的是把玩的、欲望的眼神,老城是他们的消费对象;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被老城和城里的女人吸引,以至于卓雄州两年内每天去买来双扬的鸭颈,以至于骆良骥为擦一双皮鞋掏了两百多块,奇妙的是,卓雄州对来双扬的欲望竟然没有“性”能力实现,骆良骥也在逢春面前自卑、紧张起来。他们虽为成功人士,却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这是现代都市的双重意味:拥有金钱和发展,同时在光鲜表面之下存在很多问题。
对两种女人的并置性书写也有这种意涵。其实逢春也是一个外来者形象,她本来属于“汉口最豪华的新世界国贸写字楼”那个现代空间,蜜姐和逢春的关系是金钱伦理下的老板和雇工,更是街坊伦理下的邻里,还是市民女性和知识女性这两种女人的关系,池莉把两种女人并置于“她的城”里。蜜姐谙熟这座城及后面那套人情世故、街坊伦理,而逢春这个生瓜生蛋是“不懂的”,二者关系的呈现其实包含了池莉的基本价值取向,而这一格局是池莉早期写作中常出现的:在认同市民价值的同时,讽刺知识分子的劣性,表现在逢春这里是“小暧昧小情调小酸词”。更巧的是,这座老城治愈了逢春的焦虑:都市中产知识女性都有的婚恋、生活的焦虑。逢春最初是因为和老公赌气来擦鞋,在擦鞋的三个月里,逢春只看蜜姐这个人,就学到很多,很多问题得到了沉淀与分辨,逢春在蜜姐身上学到一种市民女性的智慧,治愈了她作为都市中产阶级女性的焦虑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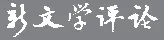
注释:
①池莉:《创作,从生命中来》,《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②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③於可训:《在升腾与坠落之间──漫论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④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⑤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⑥戴锦华:《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⑦珀西·卢伯克著,方士人译:《小说技巧》,《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9~82页、第102~103页。
⑧贺桂梅:《三个女人和三座城市》,《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249页。
⑨池莉:《水与火的缠绵》,华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⑩池莉:《她的城》,《中国作家》2011年第1期。
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