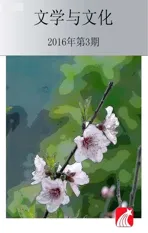论《红楼梦》对民国文学的多方沾溉
2016-11-25陈千里
陈千里
论《红楼梦》对民国文学的多方沾溉
陈千里
内容提要:《红楼梦》对三四十年代民国文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认清这一点,对于评价民国文学继承与新变的双重特性,当有所帮助。在雅文学方面,林语堂、张爱玲等人极为推崇《红楼梦》,有的作品甚至亦步亦趋地模仿。其他如巴金等人也明显地受到沾溉。在俗文学方面,不仅言情类作品如《金粉世家》等深受影响,而且武侠类也同样。如还珠楼主的《武当异人传》《云海争奇记》《蜀山剑侠传》等,就有大量脱胎于《红楼梦》的描写。
红楼梦影响民国文学雅文学俗文学
这里所谓“民国文学”,指的是上个世纪前中期的文学,重点是30年代前后的作家与作品。
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家可以说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域外文学的影响,如周氏兄弟,如胡适,如茅盾、老舍、曹禺、林语堂等。这一点早经研究者反复指出。而与此同时,本民族的文学、文化传统对他们的影响哺育,虽亦多有发明,但相比而言,研究的力度尚有所不足。即以《红楼梦》对当时文学的沾溉而论,可补充、深入研究的地方似仍多多。
一
唐德刚在《五十年代的尘埃》中以过来人的身份讲:“老实说,在笔者这辈‘五四’以后出生的‘作家’,它(《红楼梦》)对我们都是新旧文学习作的启蒙教材。”这当然是切实的肺腑之言。其实,不仅是他们这一辈,再长一辈的文人情况也差不多。究其原因,《红楼梦》自身的艺术魅力固然是根本,而当时社会上的“《红楼》热”也是很大的推动力。
1916年,《小说月报》刊登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提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其书一出,洛阳纸贵,四年多时间便印到了第六版。其立论之奇,有大出常理之外者,如指林黛玉为影射朱彝尊,贾宝玉与巧姐共同影射废太子胤礽,等等。但越奇特社会影响越大,这种情况古今一理。虽然此前关于《红楼梦》的“本事”已有多种说法,但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出来讲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何况,他还从方法论角度系统说明自己理论的“科学性”,更张大了如此解读《红楼梦》的声势。
1921年3月,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问世,开篇便以蔡元培的《索隐》作为立论的靶子。并以“笨伯”“笨谜”讥之①胡适原文是讲若依蔡说,《红楼梦》的作者简直就是一个设置“笨谜”的“笨伯”。但蔡元培在商榷文中直指胡“列拙著”“谓之大笨伯、笨谜”。。蔡亦撰文答辩。期间,顾颉刚也撰文加入论战,力挺胡适。而胡适在证明自己有关《红楼梦》的见解时,还通过各种媒介征求文献信息。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样做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这种种情况,都使得《红楼梦》成为当时一个社会文化热点,自然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到了1927年,胡适宣称得到了“甲戌本”,从而把他六年前的“大胆假设”完全、充分地证实了。又过几年,更“完备”的脂批抄本“庚辰本”出现,给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进一步提供了文献支持,也使得“《红楼》热”得以保持着社会关注的热度。
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这批文化人,对小说的看法深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不再以“稗官”“末技”视之。而《红楼梦》中含有的赞美青春爱情,追求个性解放,批评封建礼教,揭示宗法解体的思想内容,又与时代潮流相契合,因而更容易得到思想开明的文化人的青睐。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当属林语堂。他早年深受西洋文化熏陶,21岁才接触到《红楼梦》,而此后终其一生对其热情从无衰减。他两次立志把《红楼梦》译介到欧美。他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京华烟云》,其实就是作为英译《红楼梦》的替代物。对此,他本人毫不讳言。这,也可以看作是一时风气所致。
这一风气,体现到文学作品中,就是无论雅文学,还是俗文学,纷纷从《红楼梦》中汲取养分,“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大量作品或得其神,或仿其形,从而为这一文学活跃时期涂上了一笔浓厚的的民族色彩。
下面便就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稍作分析,而对于其中一向被忽略的作品则着墨略多一些。
二
雅文学方面,先来看林语堂。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对《红楼梦》的模仿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作品的前两卷是小说的主要部分,占了全书篇幅四分之三以上,其中大部分人物和情节都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影子。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写道:“(《京华烟云》)重要人物有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其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①林语堂:《给郁达夫的信——关于〈瞬息京华〉》,《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八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可见其模仿的程度以及其自觉性。
不仅人物的设置、类型大量模仿,就是一些具体的故事情节,场景的描写也近于“克隆”。兹举二例,其一“红玉似黛玉”,而红玉死于情感失落,死前尽焚诗稿与黛玉之死也颇为相似:
第二天,甜妹来见莫愁说:“三小姐,您应当过去和她好好儿谈一谈。昨儿晚上她晚饭后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儿,眼睛肿肿的。过了一会儿,少爷去看她,她不肯见。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理我。他俩一定又拌嘴了,因为她在床上躺了半点钟,她让我打开抽屉,把她的诗稿儿拿出来,然后叫我去拿铜脸盆,她把那诗稿儿扔在脸盆里,点了根火柴烧了。然后大哭起来,转过头去。三小姐,我跟她怎么说话呢?看见她,我就伤心。今天早晨她起得早,起来就咳嗽。我细看那痰里,有一块鲜血。我去叫她母亲,她母亲和她父亲一齐过来,去抓了一剂药。可是药有什么用处呢?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能告诉她父母。都是二少爷!年轻的男人那么不可靠……我恨他!”②林语堂:《京华烟云》(下),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506~507页。
据林语堂讲,他写到这里,自己被感动得不得了。不过,实在地讲,这段文字比起“黛玉焚稿”了,除了故事梗概相似外,艺术水平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其二经亚挨打一节:
她赶紧跑到院子里,用身子挡住孩子:“打死孩子以前,你先打死我!这么个小孩子,你打得那么重!”
老太太也来了,叫儿子住手:“你疯了?孩子若犯了错儿,有我还活着呢,你应当先告诉我。你不要为别人家的孩子打起我孙子来。”
父亲扔下藤子棍儿,转过身来毕恭毕敬的说:“妈,这孩子现在若不教训他,将来大了还得了?”
……撩起经亚的衣裳,看见他背上打了几条印子,又红又紫。曾夫人一见,心立刻软下来,不由得哭道:“我的儿!遭罪呀!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儿?”桂姐转过脸儿看她的小女儿爱莲,用力在她头上打了几下子,这是给曾夫人看的,因为经亚的挨打都是爱莲的话引起的。桂姐说:“都是你嚼舌根子!”①林语堂:《京华烟云》上,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63~64页。
熟悉《红楼梦》的人会惊讶于作者此时创造力的贫弱,因为整个故事就是“宝玉挨打”的缩写,甚至连小老婆的孩子多嘴多舌的细节也照搬不改,变化的只是文字简略的同时失去了原作的神采。当然,整体来看,《京华烟云》对《红楼梦》的模仿与借鉴,给林语堂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高标,使得作品的框架宏大,同时注重文化含量的丰富以及思想蕴含的超越性。
不仅是《京华烟云》一部书,严格地讲,林语堂的大部分小说和相当多的散文,都有取自《红楼梦》的成分。如他的几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框架,就是男主人公深陷情感纠葛之中,他的身边皆有两个女性,其一偏重于理想、精神境界,其一偏重于现实、生存境界。如同贾宝玉身边之林黛玉与薛宝钗。他对此有一套理论阐释:“宝钗和黛玉相对的典型,或者依个人的好恶,认为真伪之别,但却不是真伪二字可了。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守礼与放逸,本是生活的两方面,也就是儒、道二教要点不同所在。”于是,他就把这一来自《红楼梦》的钗、黛“双姝”在文本中造成的“二选一”困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情感张力空间,百分百地“平移”到了自己一系列作品中。如《京华烟云》中孔立夫身边的木兰与莫愁,《红牡丹》中梁孟嘉身边的牡丹与素馨,《赖柏英》中新洛身边的韩沁与赖柏英。
30年代的作家中,深受《红楼梦》影响者,林语堂之外当首数巴金了。但与林语堂完全相反的是,巴金在讲到自己创作历程时,总是大谈域外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卢骚、雨果、左拉、罗曼·罗兰、赫尔岑、屠格涅夫、、高尔基、狄更斯,以及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学习的对象几乎是遍及世界各国,谈起来如数家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几乎从不肯谈传统文学,偶而谈及也是负面:“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②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384页。——“线装书”竟然与“礼教监牢”相提并论。可是,作为读者,人们总是读着《家》而想到《红楼梦》,因为二者之间的血脉联系太明显了。
首先是两部作品的整体格局与主要矛盾。《红楼梦》的叙事格局是一个大家庭为主,适度辐射到社会上,也就是所谓四大家族,另外用虚笔带上朝政的蛛丝马迹,等等;而大家庭里,又把叙事焦点相对集中于几对青年男女身上,如宝、黛、钗是一组,宝玉与晴雯是一组,凤姐、贾琏是一组等。《家》的叙事格局也是这个样子,高家自是中心,周围虚写的有冯家,有学校、报馆等;位于焦点的也是三两对男女,觉新与梅、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等各为一组。而两个大家庭的主要矛盾在于父与子的冲突,冲突的实质都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小辈不肯认同老辈的人生道路而产生的“天恩祖德”与“不肖子孙”的矛盾。稍有不同的是,《红楼梦》表现的是贾政与贾宝玉之间的直接的冲突;《家》则有所变形。巴金把父权主要地移到了“祖父”身上。批判礼教,批判父权,以“祖父”当之,既便于写大家族,又有符号化的味道。
其次,两部作品另一个可比的、相似的地方是写大家族中被封建礼法压制的、摧残的青春与爱情。《家》中这方面的悲剧主要是觉新与觉慧,而二人所处情境都有《红楼梦》故事、人物的影子。觉新与梅的悲剧最为刻骨。梅的故事颇似林黛玉悲剧的意味。表兄表妹的关系不论,二人思想、性格相投也不论,只看梅表妹的形象,清高、消瘦、多愁善感,结核引起的咳嗽,等等。作为她的对照,则有丰满、“懂事”的瑞珏。这和林黛玉的形象——包括与丰满、“懂事”的薛宝钗的对比——何其相似。另一个悲剧是鸣凤。这个丫环的形象分明融合了鸳鸯、金钏和晴雯的要素。
另外,《家》与《红楼梦》在叙事态度上也颇为相似。这两部作品叙事态度的共同点在于,写家族的兴衰都有强烈的感情介入,也就是留恋与批评的混杂。表面上看,《红楼梦》似乎是留恋与批判兼有,而留恋多于批判;《家》则是批判远多于留恋——特别是作者自己所作的声明,几近于深恶痛绝。但是如果我们撇开那些略带夸张的批判性言词,深入到文本的具体描写之中,就会感受到《家》对于家庭日常生活描写中同样含有温情与留恋。如家宴的描写:
瑞珏等到众人的声音静下去以后,才慢慢辩解地说:“我为什么该罚酒?你们高兴吃酒,不如另外想一个吃酒的办法。我们还是行酒令罢。”
“好,我赞成,”觉新首先附和道。
“行什么令?”坐在瑞珏下边的琴问道。
“我房里有签。喊鸣凤把签筒拿来罢,”瑞珏这样提议。
“我想不必去拿签筒,就行个简单的令好了,”觉民表示他的意见。
“那么就行飞花令,”琴抢着说。
……
觉慧只得喝了一大口酒。他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他得意地对琴说:“现在该你吃酒了。——春风桃李花开日。”从觉慧数起,数到第五个果然是琴。于是琴默默地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说了一句“桃花乱落如红雨”,该坐在她下边的淑英吃酒。淑英说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又该下边的淑华吃酒。淑华想了想,说了一句“若待上林花似锦”,数下去,除开淑芬、觉群等三人不算,数过淑贞、觉英、觉慧,恰恰数到觉民。于是觉民吃了酒,说了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接着觉新吃了酒,说句“赏花归去马蹄香”,该瑞珏吃酒。瑞珏说:“去年花里逢君别,”又该淑英接下去,淑英吃了酒顺口说:“今日花开又一年。”这时轮到淑贞了。淑贞带羞地呷了一小口酒,勉强说了一句:“牧童遥指杏花村。”数下去又该瑞珏吃酒,瑞珏笑了笑,说了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该觉英吃酒。觉英端起杯子把里面的余酒吃光了,冲口说出一句“感时花溅泪”。
“不行!不行!五言诗不算数。另外说一句,”瑞珏不依地说。淑华在旁边附和着。但是觉英一定不肯重说。觉慧不耐烦地嚷起来:
“不要行这个酒令了。你们总喜欢拣些感伤的诗句来说,叫人听了不痛快。我说不如行急口令痛快得多。”
“好,我第一个赞成,我就做九纹龙史进,”觉英拍手说,他觉得这是解围的妙法。
急口令终于采用了。瑞珏被推举为令官,在各人认定了自己充当什么人以后,便由令官发问:“什么人会吃酒?”
“豹子头会吃酒,”琴接口道。
……
“母夜叉会吃酒,”瑞珏指着觉新正经地回答。
于是满座笑了起来。做母夜叉孙二娘的是觉新,他为了逗引弟妹们发笑,便拣了这个绰号,现在由他的妻子的口里说出来,更引人发笑了。……青年男女痛快地笑着,忘记一切地笑着,一直到散席的时候。①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98~100页。
这里为了节省篇幅,中间删去了将近一半。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看,这样铺排描写与推进故事无关的场面,实在有辞费之嫌。而作者之所以这样津津有味地写,不必讳言,作者对大家庭贵族式的生活还是持有欣赏、留恋态度的。熟悉《红楼梦》的读者,读到这里自然会产生会心之处,因为这一类的笔墨与《红楼梦》在笔法上、情调上,实在是太相似了。
民国时期作家受《红楼》孳乳而又坦然承认的,林语堂之外便是张爱玲了。张爱玲的文学一生与《红楼梦》关系至为密切。她的处女作就是《摩登红楼梦》,而最后的学术性著作则是《红楼梦魇》。她自己讲,《红楼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又讲:“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②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她的代表作《金锁记》,更是处处透露出背后的《红楼梦》的影像,而最直接、明显的是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金锁记》的故事框架与《红楼梦》中夏金桂的故事十分相近:夏金桂出身于专卖桂花的商人家庭,出嫁时已经败落③曹雪芹《红楼梦》一〇三回:“那夏家本是买卖人家,如今没了钱,哪顾什么脸面。儿子头里就走,她跟了一个破老婆子出了门,在街上啼啼哭哭的雇了一辆破车,便跑到薛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2页),因此经常通过干兄弟往娘家搬运钱物;夏金桂相貌俊俏而为人粗鄙,故与薛家以及贾府诸人格格不入,甚至公开吵闹;夏金桂因不甘“守活寡”而反复挑逗小叔子薛蝌,“天天抱怨:‘要是能够同二爷过一天,死了也是愿意的。’”薛蝌对她则是不即不离;夏金桂因情欲不得满足而移恨于香菱,几乎置香菱于死地;最后她死于自己的情欲之火——“金桂自焚身”。这里面,门户不当的婚姻,俊俏而粗鄙的媳妇同整个家庭的摩擦,因压抑的情欲产生仇恨,叔嫂之间的暧昧情事,以及欲火焚身的自戗,类似的情节要素都出现在《金锁记》中,并构成基本的故事框架。当然,《金锁记》绝非简单照抄,自有其带有根本性的超越;而且即使是对《红楼梦》,也不是抱定这一段来仿效,鸳鸯的故事、凤姐的故事,甚至秦可卿的故事等,作者也或多或少有所采撷。不过,曹七巧故事的基本框架,受到夏金桂故事的直接启发当可无疑——要知道,张爱玲八岁即读《红楼梦》,已到了熟极而流的程度,正如她所自诩的:“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④张爱玲:《红楼梦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页。所以在她要编织一个变态的情欲故事时,《红楼梦》中的类似故事也就“自会蹦出来”了。
其次看人物的刻画。人们谈到曹七巧的形象,往往认为受王熙凤形象影响而来。其实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夏金桂。王熙凤虽不文虽泼辣但言行总是“得体”。而夏金桂的泼辣则是粗鄙失态,在文化层面上与整个家庭格格不入,这恰是曹七巧作为家庭角色的基调。另外,夏金桂的叔嫂恋描写,心理上依违不定,行为上迹近变态,这也是曹七巧情感矛盾的主要特色。夏金桂之外,其他人物的影子也在曹七巧周围若隐若现,如曹七巧斥骂哥嫂一节:
七巧啐了一声道:“……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头一缩,死活我去。”①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而《红楼梦》四十六回鸳鸯骂哥嫂一节:
鸳鸯照他嫂子脸上下死劲啐了一口:“……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②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19页。
从语言结构到遣词造句,都是如出一辙。由于张爱玲对《红楼梦》熟极而流的把握,不自觉间就在自己的人物身上打上了《红楼》人物的印记——甚至于到了迹近“克隆”的地步。这一点,她倒真是可以和林语堂引为“同道”了。
三
《红楼梦》对民国文学的沾溉不仅仅表现在“雅文学”中,“俗文学”中的表现同样不可忽视。
这可以从影响力最大的两类“俗文学”——武侠与言情的作品中看出来。
武侠,似乎与《红楼梦》风马牛不相及。无论是故事题材,还是表现手法、文字风格,武侠应该更接近于《水浒传》,而远离于莺莺燕燕的《红楼梦》。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以民国武侠作者第一人的还珠楼主而论,他的作品题材总体来说可归结为“《封神演义》加《水浒传》”,但其中经常间杂小儿女情态之闲笔,而且模仿《红楼梦》之处颇多。如《武当异人传》中,林绿华与崔晴的描写,仿《红楼》之形者,模《红楼》之神者皆有。仿形的,如林绿华葬花一段:
(林绿华)忽想:“前晚香雪满地,梅花已是开残,每年此时,必有葬花之举……莫非因为他,连梅林都不去么?”念头一动,便信步走去。到了梅林,一夜未来,花落更多,满地芳华狼藉。花犹如此,人何以堪!便择一空地,照乃母昔年所传葬花之法,施为已毕……绿华自小爱花成癖,每见落红委地,便生怜惜,磨着乃母学来的禁法。……不由多挨了一会。忽然想起,“后山就在对面,莫被他看见,笑己卖弄,再误认作是存心想引他来,岂不冤枉?”想到这里,兴趣立减,慌不迭待要赶紧葬完了花回去,手指处喝一声:“疾!”那千千万万的梅花,立时海涛一般卷起,四方八面,分成无数急流花浪,二次又向坑中急泻而下。
此等寒芳冷艳,理宜幽赏,方不负它们清标独上,葬花韵事,添上你们男子便俗。一个半仙之体的侠女,竟和林黛玉一样的伤春、葬花!更妙的是,其姓名“林绿华”又隐隐与“林黛玉”相呼应,作者又让她口中讲出“添上男子便俗”的妙论——脱胎于《红楼梦》自是毫无疑义了。
至于林崔二人的情感世界,更是一派“红楼”笔墨。如写林绿华的小性与崔晴的痴情:
(林绿华)当时一赌气,便犯了小孩脾气。因是素日性情温和,心事不能明言;崔晴又一味体贴恭顺,实说不出此外有什过处,表面不好意思发作。勉强坐了一会,便推有事,老早回洞。崔晴留她不住,当晚回洞,已是恋恋不安。第二日黄昏前便去梅林相候,只说昨晚别早,没有畅谈,绿华必也早去,哪知人并未来。……心虽苦盼,还未在意。久候不至,心疑连日形迹亲密稍过,也许词色之间失了检点,引起疑虑,看在居停分上,不肯翻脸,人却就此疏远下去。再一回忆连日相对情景,越想越对,急得通体汗流,心凄不已。独个儿在林中自怨自艾,又悔恨,又相思,眼巴巴盼到天明,玉人终是不至。没奈何含恨回去,苦盼凝想,自不必说。
熟悉《红楼梦》的读者至此必会心一笑,因为这和林黛玉耍小性“辖制”贾宝玉之时,贾宝玉那种窘迫情态实在是太神似了。而还珠楼主就此直接出面发了一通议论,道是:
男女相爱,用情越专,处境越苦,猜疑也越多。哪怕日常缠绵,情若胶漆,稍有误会,便疑对方变心薄情。在别人眼里极寻常的一件事,而局中人却认为问题十分严重,仿佛要命神气。及至事情揭穿,或是双方对面,彼此相处无言,就此恨释冰消,无端神魂颠倒,白赔上许多精神眼泪,不知所为何来。可是冷热循环,愈演愈烈,每经过一次波折,情爱也必随以增进。①此处并以上两处引文,均见于还珠楼主:《边塞英雄谱·武当异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136~138页。如果把这段话从《武当异人传》里摘出来,直接贴到《红楼梦》的评点本中,人们很可能要叹为“量体定制”呢。
还珠楼主对于《红楼梦》所描写的“小性儿”林妹妹与“被辖制”的宝哥哥实在是印象太深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到自己的作品中。即使神魔色彩极重的《蜀山剑侠传》也为此提供了相当多的篇幅。例如:
大家忙了一阵,英琼将粥煮好,切了一盘腊味,又取了一大盘咸菜捧将出来。金蝉、若兰最爱吃那腊味,赞不绝口。朱文笑对金蝉道:“九华虽然清苦,辟邪村玉清大师颇预备许多荤素吃食,我不信这一趟莽苍山,会把你变成一个馋痨鬼。今天才到李师妹家中第二天,也不怕人家笑话。”说罢,抿着嘴,用两个指头在脸上刮。金蝉见朱文羞着笑他,便也反唇相讥道:“朱姊姊你还不是不住口地吃鹿肉,还说我呢。当心把神雕的粮食吃完,神雕不依吧。”朱文正要还言,英琼见二人斗口,忙道:“朱姊姊、金哥哥爱吃腊味,我还多着呢。即使吃完,只要叫我金眼师兄出去几趟,便能捉得好几个回来。我们都跟亲手足一样,谁还笑话不成?”朱文冷笑道:“我不过见他吃得野相,好意劝他几句,他反倒来说我。这类烟火食,我一年也难得吃上两回,因见李姊姊劝客情殷,又加上头一次吃鹿肉,觉得新鲜,才拿两片撕着就稀饭。谁似他狼吞虎咽的,这一大盘倒被他吃了一多半。为好劝他两句,还反说人吃不停嘴,吃你的吗?”金蝉见朱文娇嗔满面,便低下头只顾吃,不再言语。
灵云是一向看他二人拌嘴惯了的,也不去答理。见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便也取了筷子夹一片慢慢咀嚼,那一股熏腊之味竟是越吃越香。笑对金蝉道:“无怪你们争吃,果然这鹿肉很香。英琼妹子小小年纪,独处深山,居然布置得井井有条,什么饮食设备样样俱全。与若兰妹子一样,都是那么能干,叫人见了又可爱又可敬。要像这种殷勤待客,怕不宾至如归,把山洞都挤破了吗?”若兰见朱文、金蝉拌嘴,在旁边也不答言,只顾吃。这会听灵云赞她能干,便笑道:“姊姊怎么也夸奖起我来?我哪一点比得上诸位姊姊们?不过平日仗着先师疼爱,享享现成的罢了。”
这时朱文停箸不食,坐在那里干生气。金蝉不时用眼看着朱文,想说什么,又不好说出似的。英琼惦记着那只神雕,匆匆在后面取了两只鹿腿,出洞喂雕去了。芷仙怕他二人闹僵,看他二人神气,知道金蝉业已软化,容易打发,便劝朱文道:“姊姊不要生气,招呼凉了,不受吃。”还要往下说时,灵云忙拦道:“我们休要劝他们,他二人是这样惯了的。”朱文误会灵云偏袒金蝉,本想说两句,猛想起灵云患难中相待之德,不便出口,越发迁怒金蝉,假装看雕,立起身来,独自行出洞去。金蝉见朱文出洞,知她心中不快,讪讪地立起身来,也跟了出去……金蝉便向朱文赔话道:“你还跟我生气么?下次我再不和你强嘴了。”朱文站在那里,只是不理。金蝉仍是不住地说好话,定要朱文接他采的那枝梅花。朱文被他纠缠不过,正要伸手去接,若兰忍不住要笑出来,连忙忍住,高声说道:“天都不早了,你们还采梅花玩,大师姊她们叫回去开辟凝碧崖呢。”朱文见若兰忽然现身出来,不禁脸上一红,不再理会金蝉,回身便走。金蝉无法,只得同若兰跟在后面。
假如把这段文字中的人名完全隐去,可能不少读者会想到《红楼梦》大观园中,林黛玉和贾宝玉使性子斗口的情形。而金蝉也罢,朱文也罢,在《蜀山剑侠传》中可都是几世修行,神通广大,飞行绝迹的剑仙,作出林、贾一样的呕气斗嘴行为,似乎有些与身份不合。可见,《红楼梦》影响作者到了怎样的程度。
当然,这样写的效果,使得仙人们有了较多的“人味”,有别于纯粹的神魔作品,所以也未始不是妙笔。
类似的爱情描写、小儿女情态,还珠楼主的其他作品如《独手丐》《蜀山剑侠传》《云海争奇记》等书中也不乏其例。此外,还珠楼主还经常在小说的神魔、武侠故事间隙穿插一些家庭生活情景,甚至是贵族世家的生活。其趣味,甚至描写的具体情状,都隐隐现出《红楼梦》的影子。如描写虞家兄弟的居所:
魏、钱二人所居乃是五间一幢的精舍,当中一大敞厅,隔旁各有两间,一明一暗,俱是紫檀雕花隔断,满壁图画,陈列精雅。舍后一座小土山,两旁环植芭蕉,杂花夹径,红紫芳菲。舍前种着几株抱多粗的梧桐树,奇石三五,嶙峋矗列,溪水右来,到北汇成一他,与精舍正门相对。夏日荷花满开,碧梧高柳,鸟声吵吵,为园内纳凉消暑胜地。晓星住室在右侧假山侧面竹林以内,中间曲曲弯弯通着一条石子铺的小径,两下相去并不甚远。
小妹见虞家花园布置风景无一不佳,所备房舍自成一个院落,门外假山屏蔽,修竹成丛,门内只靠东北墙角一所房子,对面两株梧桐树粗均合抱,时正深秋,落叶飘萧,树下分列着石几瓷墩,想见夏日碧荫映窗、清风送凉幽静景象。西南面又是一座假山,山角一亭,可供登眺,通体苔薛鲜肥,杂花满生,山下玉兰数株,均在半抱以上。屋侧还种着七八株梅花树,也都丈许高下。①还珠楼主:《云海争奇记》,中国书店,1989年,第393、396页。
作者特意借书中人物之口,对此做出评论,特别是家居的雅俗分别,道是“不少富户人家”,“到处油漆得金碧辉煌、红颜绿色”,“朱红漆的家具和一些不论真假的古董字画,乱糟糟聚在一起,塞得满满”,结论是“书香世族的气象固与暴发之家不同”。这与《红楼梦》描写贾府的情调完全一致。类似的笔墨还出现在何异家居的描写中。何异是个退隐的江湖人物,而其居处一派清雅之气,足见作者的特殊趣味。
对于“书香世族”生活的向往,还表现在对其饮食起居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如写虞家的汤圆:
虞家肴点原极精美,虞妻因老人多爱吃甜的,添做一样珍珠汤元,江母吃完夸好。小妹见那小汤元比龙眼核还小,都一般大,颜色雪白,里面包着三两种细而香腴的甜馅,放在极清的紫色枣汤以内,端的色香味三绝,隽美无匹,便问:“怎么做的,这样灵巧好看?”虞妻道:“与普通汤水元一样做法,不过小些罢了。那馅子是用黑芝麻、瓜条、核桃仁、花生米、桂元肉分别磨碎,先用肥母鸡腹中板油加蜜生酿,这时取来和在一起,用石臼捣烂成泥,再加上自制花露拌匀,用模压成黄豆小粒,外皮是好糯米七成、香粳稻三成磨成了粉,再入小磨重磨,过一次过筛,加水揉匀备用。另有木模一副,共是三块:一块是底,上有一百零八个大半圆的小木槽;中间一边是百零八个和馅一般大的圆球,湿粉放在槽内,木球对槽一压,正好成了一个馅窝,把馅放在里面;上层一块,也有同样木槽,只是浅些,也放湿粉压过;两边一合,倒出来放在筛内,略加点干粉一滚,便颗颗均圆,大小如一了。汤用北方带来的好红枣,洗净蒸涨去皮,加冰糖冷水煮开,文火熬汤,去枣不要,再用细绢滤过,等汤元煮熟捞起,放入枣汤以内,就成功了。另外两种馅子,一是豆沙,一是莲泥,并不费事。后园花多,居家无事,任其开败可惜,每当花事,我便带着下人,在天明日出以前,择那含苞半开的采摘下来,去掉须蒂,和蜜装瓷封紧,有的是蒸,有的用隔水炖,制成元叶花留露,原坛封藏,用时取一半勺,便有极浓郁的香味了。②还珠楼主《云海争奇记》,第397页。
对此,作者同样是借书中人物之口来赞扬一番。有趣的是,赞扬时再次提出“世族”的话题:“可见得大家世族的起居饮食,绝非一般暴发户所能梦见呢。”这段“汤圆制作论”,似乎只有《红楼梦》四十一回的“茄鲞制作论”可与之相比。平心而论,《红楼梦》的论“茄鲞”与全书的“好就是了”的主题紧密相关,故似乎辞费而实为妙笔。还珠楼主在这里用五六百字细写汤圆制作,却实在没有必要。但是,他似乎还不满足,另一顿饭又铺陈了一番汤面的制作:
那汤面倒还不错,适才叫厨子再添一样。他说汤已隔夜吊好,只有这个快些。做面以前,先用鸡鸭隔锅吊汤,撇去浮油,再用顶上口蘑和瘦金腿腰峰布包吊浸在内,文火煨上些时,将渣弃去备用,借那火腿卤味,不用点盐。那面也与外间不一样,用鸡蛋清和,不加滴水,褂得极薄,切成分许宽、四寸长条,先放滚水内煮个半生,再放原汤煮熟,好使汤味浸入面里,汤仍是清的。吃时另备四个小碟,看是一碗清汤面,厨子却要费不少事。③还珠楼主《云海争奇记》,第464页。这种写法只能称之为“不吝辞费”了。看起来,还珠楼主一则是炫耀见闻,二则恐怕也有些与《红楼梦》争奇斗胜的潜在心理。
再来看看“言情”类。
民国言情小说第一人非张恨水莫属。茅盾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①《关于〈吕梁英雄传〉》,《中华论丛》第2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张恨水白话小说的处女作为《真假宝玉》,《红楼梦》的影响不言而喻。他的代表作《金粉世家》是现代文学中第一部正面书写家庭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书是张恨水为《世界日报》的副刊写的连载,由1927年2月14日到1932年5月22日,刊载了五年有余。
张恨水对古代文学有相当的修养,这使得他的小说写作很好地接续了传统,所以深受大众的欢迎。但也使其不陷入模仿的泥沼。《金粉世家》在大的框架以及人物、情节等方面都有对《红楼梦》模仿的痕迹。
《红楼梦》以宝、黛、钗的感情纠葛与贾府衰败两条线索相缠绕来结构全书,《金粉世家》亦步亦趋,在冷清秋感情经历的同时描写了金铨大家庭的盛衰。金铨是外交官出身的国务总理,他的家庭包括他的三个太太、四个儿子与四个女儿;故事开始时,子女中有四个已经结婚,仍然住在一起;随着故事进展,又有一个儿子结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包括了五个核心家庭的大家庭。大家庭中,有三个小家庭是多妻的;八个子女中,七个嫡出,一个庶出。可以说,中国封建大家庭的要素几乎齐备。而故事的演变与《红楼梦》也是大体相当,就是一面铺陈着贵族大家庭钟鸣鼎食的富贵气象,一面刻画着“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衰败趋势。这种情况前可以比《红楼梦》,后可以比《家》、《京华烟云》与《四世同堂》。在这个意义上,《金粉世家》可以看作是《红楼梦》与民国文学的衔接部。
人物形象方面,男主角金燕西则隐隐透出贾宝玉的某些气质。如他发现丫鬟小怜打碎太太的法国香水瓶时:
燕西便对老妈子道:“你去看看六小姐在家里没有?”老妈子答应着去了。小怜道:“你叫她去看六小姐作什么?”燕西笑道:“让她走了,我有一句话,要和你说。”小怜一顿脚,说道:“嘿!人家正在焦心,你还有工夫说笑话。”燕西笑道:“你自己先捣鬼,我还没说,你怎就知道我是说笑话呢?我告诉你吧,我那瓶香水,还没有动,我送给你,抵那瓶的缺,你看好不好?”小怜道:“好好!七爷明天有支使我的时候,一叫就到。”燕西道:“你总得谢谢我。”小怜合着巴掌,和燕西摇了两下,说道:“谢谢你。”燕西道:“我不要你这样谢,你送我一条手绢得了。”小怜道:“你还少了那个?我的手绢都是旧的。”燕西道:“旧的就好。你先把手绢拿来,一会儿你到我那里拿香水就是了。”小怜红着脸在插兜里掏出一条白绫手绢,交给燕西道:“你千万别对人说是我送给你的。”燕西道:“那自然,我哪有那样傻。”……燕西给了她香水之外,又给了她一条青湖绉手绢。小怜道:“我又没有和你要这个,你送给我做什么?我不要。”燕西道:“你为什么不要?你要说出一个缘故来,就让你不要。”小怜道:“我不要就不要,有什么缘故呢?”燕西就把手绢,乱塞她手上,非要她带去不可。小怜捏着手绢,就跑走了。②张恨水:《金粉世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70页。替丫鬟小怜担责一节,显然是《红楼梦》第六十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中,贾宝玉替五儿担责的翻版。而索、赠旧手帕的描写,也分明有贾宝玉赠林黛玉旧手帕的影子。
再如金燕西和诸纨绔结社作诗一段:
这其中的冯有量,是个少年大肉胖子,为了几个芍药花的典,搬不出来,急得头上的汗,象黄豆一般大,只管往下落……高声念道:“人人都爱牡丹花,芍药之花也不差。昨日公园看芍药,枝枝开得大如瓜。”这首诗念完,所有在座的人,都不觉哈哈大笑。冯有量他脸色也不曾变,站在大众堆里说道:“这麻韵里的字很不好押,诸位看如何?给我改正改正罢。”孟继祖极力地忍住笑,说道:“这一首诗,所以能引得皆大欢喜,就在于诗韵响亮。我再念第二首诗给诸位听。”于是又高声念道:“油油绿叶去扶持,白白红红万万枝,何物对他能譬得?美人脸上点胭脂。”①张恨水:《金粉世家》(上),第102~103页。
这里不妨拿《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的一节比较一下:
薛蟠道:“我可要说了:女儿悲——”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冯紫英笑道:“悲什么?快说来。”薛蟠登时急的眼睛铃铛一般,瞪了半日,才说道:“女儿悲——”又咳嗽了两声,说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薛蟠道:“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当忘八,他怎么不伤心呢?”众人笑的弯腰说道:“你说的很是,快说底下的。”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说道:“女儿愁——”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众人道:“怎么愁?”薛蟠道:“绣房撺出个大马猴。”众人呵呵笑道:“该罚,该罚!这句更不通,先还可恕。”说着便要筛酒。宝玉笑道:“押韵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么?”众人听说,方才罢了。②曹雪芹:《红楼梦》,第384页。
从场景,到趣味,以致细节的种种描写,如众人对粗俗鄙陋者的取笑,被取笑者的窘迫神态,甚至以“押韵”来解围,都是如出一辙。无怪乎有评论家称金燕西为“时装贾宝玉”,称《金粉世家》为“我们的民国《红楼梦》”。
当然,《金粉世家》的思想境界与《红楼梦》颇有不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心理,有“陶庵梦忆”似的留恋情结,但多了一份反思(虽然并不完全自觉)。而《金粉世家》铺陈渲染富贵生活的效果则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大众艳羡富贵心理的迎合。
总之,《红楼梦》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文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认清这一点,对于评价民国文学继承与新变的双重特性,当是有所帮助的。
(陈千里,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Chen Qianli
A Dream of Red Mansion has an overall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30s and 40s.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is in evalua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n elegant literature,Lin Yutang,Eileen Chang and others paid great tribute to A Dream of Red Mansion and imitated the classic inmany aspects.Other writers like Ba Jin have also been much influenced and benefited from the classic.In popular literature,both romances such as The Story of a Noble Family(Chinese pronunciation Jinfen Shijia)and chivalrous stories are enlightened by the classic.The descriptions in the works of Huangzhu Louzhu,such as An Extraordinary Person At Wudang Mountain,Competing On the Sea of Cloud,A Chivalrous Swordsman atMount Shu,aremuch similar to thos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Influence;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Elegant Literature;Popular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