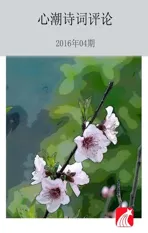探讨新田园诗的概念及其内质表现
2016-11-25吕克俭
吕克俭
探讨新田园诗的概念及其内质表现
吕克俭
新田园诗的概念,涵括两个要素:“田园诗”是前提,“新”是关键。也就是说,新田园诗,首先必须是“田园诗”,然后才是“新田园诗”。尽管“新”是这个概念的关键字眼,但不能盲目的为“新”而“新”,反忘了“田园诗”的概念与内质。就近些年所看到的某些新田园诗,存在着因为概念模糊以至作品似是而非的问题,存在着刻意求新求异以至作品空泛矫情的问题,存在着缺乏审美意识以至作品枯燥乏味的问题,存在着忽视传统承继以至作品浮浅粗糙的问题。从新田园诗创作所出现的问题来看,我们有必要界定新田园诗的概念,弄清新田园诗的内质。
一、概念的话题
概念,决定作品的类属;内质,决定作品的质量。那么,新田园诗的概念将如何界定呢?
我认为,新田园诗的“新”,不在其类属上,而在其内质上。理论上讲,新田园诗与传统田园诗的内涵是一致的,只是外延略有不同。因此,在概念表述上并不发生矛盾。也就是说,新田园诗应该是:以当代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为创作题材的诗歌。这里所说的“当代”,界定了新田园诗的时间范围;而“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又界定了新田园诗的内容范围。如果脱出此外延,则不属于新田园诗的范畴了。由此看来,当今田园环境内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当然也包括人物),都是新田园诗的创作题材,如果这些事物(这里只指人或物)脱离了田园这个大的环境,而进入到其他新的领域,那么这些事物就不再是新田园诗的创作题材了。这点是需要着重强调的。
譬如,有些诗人以农民工在外的打工生活作为诗歌的表现内容,并将这种诗歌当作新田园诗,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我们来看看《鹧鸪天·农民工》这首词:“背井离乡图个啥?薄微收入寄回家。肩扛煤气披朝露,手捧砖头沐晓霞。思父母,念妻娃。他乡背地泪花花。风中遥望回家路,天际苍茫挂月牙。”毋庸讳言,这是篇表现农民工在外艰辛生活的佳作。若以“新田园诗”的概念去考量这篇作品,就会发现:这篇作品“新”则“新”矣,但是所描述的内容既不是“田园风光”,又不是“田园生活”。也就是说,词作描写的并不在“新田园诗”的内涵范围之内。然而,作者与编者都将其视作“新田园诗”。我们再来看一首同样标题为《农民工》的绝句:“岁月沧桑岂等闲,富人总赚穷人钱。龙台仙境修多少,依旧柴门屋漏天。”同样写农民工的辛酸,依我判定这首诗就属于“新田园诗”。理由是:这首诗的结句向我们呈现了这位农民工在家乡的居住状况,尽管只有一句,但在极具震撼力的对比中,将读者的视线定格在“依旧柴门屋漏天”的现实的窘境中。这种窘迫的现实,恰恰是属于“这一个”的“田园现状”,这种田园现状的再现,也就决定了这首诗的类属。“农民工”打工生活,属于“三农”题材(当然也属于其他类别的题材),而“三农”题材的诗作,其实并不完全属于“新田园诗”。尽管农民工群体,曾经身处(或者将来依然身处)田园环境,也曾经是(或者将来依然是)田园诗词歌咏的对象,但是毕竟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农村(尽管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他们现在的生活已再不是田园生活。应该说,这时的农民工属于城市的特殊群体,而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了,或者说农民工已经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实质上的工人身份。以他们现在的城镇打工生活作为创作题材的诗歌,一般来讲就不再属于新田园诗的范畴了,而应该属于城市文学(或者称作“城市诗歌”)的范畴。
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是否属于新田园诗,取决于田园环境,而不是事物本身。事物所处的环境改变了,那么所创作的诗歌类属也就随之改变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那就是所吟咏的事物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脱离田园环境,而只是诗人将其从田园环境中独立并凸显出来,歌之咏之且别有寄托,这类诗是否属于新田园诗?有位词人以小龙虾为创作题材,写了首很是精彩的词作(遗憾的是,原词找不着了)。词的上片写小龙虾生长的环境、形态、习性,以及词人由此生发的联想;下片写小龙虾之美食诱人,使人念念不忘。有人却将这首词作归入“新田园诗”。很显然,这是篇咏物作品。尽管这个“物”,是田园中的“物”,但毕竟与“田园生活”“田园风光”都联系不上。
其实这类诗歌作品,只是诗人暂时的借助田园事物以纾情志、以骋胸怀。表面上是吟咏事物,实质上是借物遣兴、借物言志。尽管诗人所咏的“物”好像没有离开田园,但是这些“物”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已经将其从田园环境中“剥离”了出来,或者是抽象了出来,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符号载体赋予了这种“物”以特别的意义,而这“特别的意义” 似乎又与田园生活不搭界。因此,这类诗歌只能属于别有寄兴的“咏物诗”,实在很难将其归入到“新田园诗”里去。
二、内质的话题
我们接着讨论,新田园诗的“新”究竟体现在何处的问题。如前所述,其“新”应该体现在新田园诗的内质上。
那么,新田园诗的内质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其内质应该是:新的田园题材,新的田园情感,新的田园诗创作手法等等。这样说来,又有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与之对应的旧的田园题材、旧的田园情感、旧的田园诗创作手法是否就不属于新田园诗的内质了?这其实是新旧田园诗的内涵问题,二者在内涵上有重合部分(其实,新旧田园诗都类属于田园诗范畴)。
那么,这个二者的交集里到底是些什么?我想,应该是古典田园诗里至今仍然存在的田园题材、田园情感、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等。像这类交集中的东西,依然是我们新田园诗内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因为这类部分前人都写滥了而予以摒弃。整句歌词来说就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爹是爹来娘是娘。”谁能说这亘古不变的就不是新田园诗的题材?就非得要予以弃绝,然后再在其他地方钻牛角尖地寻出所谓的“新”字来不可?显然,这是违背常情常理的,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违背了创作规律。若是这样的话,为了所谓的表象上的“新”,而舍本求末地去创作所谓的“新田园诗”,则那些矫情的、粗俗的、虚伪的、肤浅的东西就汹涌出来了,充斥诗坛,必然使得我们的新田园诗越写越窄,越写越糟,越写越没有读者,越写越没有出路!这,才是我们真正须要警醒和摒弃的!
随手翻开诗词刊物的田园栏目,像“梦中笑醒农家汉,百姓欢呼党最亲”(《乡村掠影》)、“尧天舜日小康雨,酿熟香红甜万家”(《回乡偶成·柿子林》)、“信步康庄邀五柳,欢歌一曲颂尧天”(《雅园生态农庄》)、“农民歌盛世,岁岁是丰年”(《咸安梅家咀村》)、“常乐人间名利远,农家谁羡戴乌纱”(《农家》)、“如今更喜多新富,笑驾丰田游八方”(《农村秋日》)、“栉比高楼迎旭日,乡村富裕胜天堂”(《今日农村》)、“如今电脑非稀物,遍及寻常百姓家”(《重访山村》)……这些诗句过于浅俗、矫意,甚至夸饰,缺乏情感的真实性与思想的深刻性,不具视角的独特性与审美的独创性。因而,其田园诗的内质就显得虚泛而不醇厚,诗作也就空有其形了。
三、新与旧的话题
题材决定内容,题材新则内容新,题材“旧”而内容不一定旧,如果在旧题材中发掘出新意义,那么作品内容同样是新的。
内容新,不在题材,而在思想意识。正如秦牧在《拾贝·核心》中所说的:“在丰富的生活之中,靠什么来摄取题材提炼题材呢?靠思想!”可见思想才是决定作品内容新旧的关键因素。思想新,内容毫无疑问的新;思想旧,内容毋庸置疑的旧。
有人要说:古典田园诗里那些旧内容的东西,尽管在今天看来并不存在,但是特别有古意、古趣、古味,实在难以割舍!这纯属个人喜好,另当别论,只是你写的是“个别”而不是“一般”,或者说是“臆想”而不是“现实”,只是你创作的诗词不属于新田园诗词的范畴罢了。有人又要说:新农村新气象,不写“新”就是复古、泥古!这话初听起来,的确有几分道理,似乎非常切合新田园诗的求新理念。但是仔细想来,这种看法属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判断观,不“新”就是“旧”,不“今”就是“古”。显然,这种观念违反了认识论,否定了事物存在的多元性、复杂性。
新事物的产生,总是依附于旧事物的存在,新的登场并不意味着旧的退场,况且“新”并不能完全取代“旧”而独霸江湖、独领风骚,新与旧总是需要相生相伴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有时新的已经不再新了,甚至被更新的取代,而旧的依然顽强地存在着。我这样说,并不是抵牾新事物,更不是漠视新事物,而要说的是我们的诗人在面对新事物的同时,除了敏感度、热情度之外,更多的需要诗人们从新田园诗的内质上去敏锐的发现,睿智的思考,高度的提炼,新异的表现,而不是一窝蜂式的人云亦云。比如说:农村的农机使用,农民的手机使用,养殖业的机械化,日常生活现代化等等新方式、新现象、新风光,都是古典田园诗人见所未见、更是吟所未吟的田园题材。诗人首先歌之咏之,新人耳目;竞相歌之咏之,无可厚非;反复歌之咏之,则拾人牙慧。反复地、简单地歌咏新事物,又没有全新的视角去作全新的尝试,所以这类作品就实在是有点扰人耳目,流于热闹甚至戏说的浮浅。况且新事物、新方式、新现象在当今农村并不都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新的东西恰恰成了简单重复的“旧新闻”“旧题材”了。而实质上的的田园风光、田园生活,其主题基调、主体色调并没有多少改变。面对这些新鲜事物和陈旧事物,关键是我们的视角要新,切入要准,深入浅出,语言鲜活,手法新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所创作的诗歌同样是无须争辩的新田园诗。
由此说来,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犹如深蕴不语的宝藏,同样值得我们去发现、去思考、去发掘。这也可以看着是田园诗歌创作——浮华背后的返朴归真!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田园诗人的目光无论是聚焦到“三农”的“新”上(注意:不做表面文章),还是聚焦到新旧田园诗的交集上(注意:不泥古复古),只要是能关乎痛痒、运乎匠心,便是体现了新田园诗内质的“新意”,觅得了新田园诗创作的“真谛”,而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所咏事物的新旧。况且,亘古不变的所谓“旧”题材,恐怕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田园风光与田园生活的本质要义,因而也就成了田园诗歌的永恒主题。谁能说山野田畴、村舍鸡犬、渔樵稼穑就一定是旧事物、旧题材呢?其实,这些不变的事物是无所谓新与旧的,就看我们的诗人是否能从新的视角、新的侧面去发掘出新的东西,然后以诗的美学观念和诗的创作方法去作新的尝试与新的诠释。
从新事物中捕捉新的契合点,从所谓的旧事物中发掘新的闪光点,折射田园风光,透视生活本质,这才是我们新田园诗所要追求的东西,同时也是新田园诗人的创作使命。
四、文与质的话题
我曾在《摭谈当代田园诗的文质与真伪》一文中谈过:
“文质”关系,是个古老的话题,“文”是指事物的外部呈现,也就是“形象”,将形象诉诸文字,则又兼指修饰、文采;“质”是指事物的内在含蕴,也就是“本质”,将本质行之于文,则指具有的律义、情理。在诗歌创作中,“文”与“质”,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孔子说:“质胜文则野(粗俗),文胜质则史(虚浮)。文质彬彬(谐调适当),然后君子。”尽管这段话是论人的修养的,然而借以论诗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文质彬彬,然后佳作!……现今田园诗作的粗率,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质”的过分强调与体现,弱化和淡化了“文”的作用,使创作的田园诗显得质实而乏味,甚至流于口号式的直白抑或粗俗。……诗歌评论常说的“文质兼美”,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不管最终的这个“美”,是雅还是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与“质”,必然的交融互化!
可见,文质问题,关乎新田园诗的创作质量。
新田园诗的创作质量,取决于内质表现的新颖;而内质表现的新颖,又取决于审美角度的新颖。
审美角度,体现了诗人洞察生活、提炼生活、表现生活的睿智程度与创新能力。新田园诗人只有热爱田园、体验田园、感悟田园,才有可能出现生活的顿悟,才有可能出现创作的灵感,才有可能从全新的视角和侧面去表现田园,写出别开生面的、新鲜活泼的新田园诗词作品来。这里,使我们想到了那些经典的民间歌谣、古典诗词、自由体诗,他们在表现诗歌内质时的独特的视角、精当的选材、丰富的内蕴、以及新奇的手法等等,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创作启示。
当然,新田园诗词创作的成功与否,其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譬如说,你的作品题材新、角度新、手法新,然而如果作品的语言诗化欠缺或者语言风格相悖,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作品,可见语言同样的关系重大。无论是直接叙说还是婉曲描述,无论是采用雅言还是选择俗语,首先必须是“诗的语言”,然后才是语言风格的一致性,因为诗歌的内质,必须依靠诗化谐美的语言才得以最终的完美彰显,务必使得所创作的新田园诗“文质兼美”,这同样需要我们新田园诗人引以重视并且加以历练。
新田园诗的概念及其内质表现,是个理论色彩较浓的话题。由于本人的诗学素养不足,加之创作实践不够,又缺乏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所以本文呈现出“理性”多于“感性”,“理说”多于“例说”的现象。而且,“理说”不一定科学辩证,甚至失之偏颇;“例说”又未免以偏概全,不具有普遍性。只是希望我所阐述的观点不至于产生误解,同时也希望能给新田园诗的创作繁荣有所裨益。若是,幸甚至哉!
(作者系东坡赤壁诗社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江 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