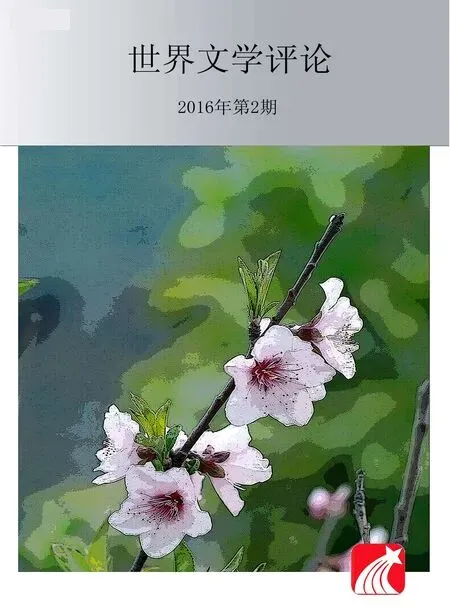《鼠疫》中的伦理选择
2016-11-25段亚鑫
段亚鑫
《鼠疫》中的伦理选择
段亚鑫
内容提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小说《鼠疫》描写了阿尔及利亚海滨城市阿赫兰遭受鼠疫了侵袭,居住在该城的居民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对危难,不同的人物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普通民众从对疾病的恐慌到变得麻木;医生里厄等人则组织防疫队、研制血清、开展救援;记者朗贝尔则千方百计想逃出去,但最终内心却发生了转变。本文采取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着重分析普通民众、医生里厄和记者朗贝尔这三类人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最终探究加缪在《鼠疫》中所要传达的伦理思想。
鼠疫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困境 伦理选择
长篇小说《鼠疫》①是法国当代哲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品,“一部被法兰西文学界奉为经典的长篇巨著,一部被译成28种语言,畅销1 000万册的作品。该作是全球畅销书中的传奇,半个世纪以来常销不衰,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其存在主义的荒诞哲理在《鼠疫》这部寓言式的小说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在小说中,作家描述了一座海滨城市阿赫兰被突如其来的鼠疫卷入了灾难之中,无数普普通通的人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其中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医生里厄、记者朗贝尔、神父帕纳鲁、罪犯柯塔尔、卫生防疫队长塔鲁等人在这场灾难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选择,这些迥然不同的倾向导致了每个人的不同命运。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评论界主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或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鼠疫》,更多关注现代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在面对大灾难时的困境和救赎等问题。本文试图采取新的视角,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方法,从《鼠疫》小说文本出发,探究小说中普通民众、记者朗贝尔和医生里厄这三类典型人物在面对伦理困境时,做出不同伦理选择的根源所在。
一、鼠疫肆虐下的伦理困境
在《鼠疫》的开篇,加缪笔下的阿赫兰城是一座普通的海滨城市,人民的生活平静而祥和,透过作家的描写甚至透露出一种平淡乏味的现代城市之感,“阿赫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一个毫无臆想的城市,即是说,它是个纯粹的现代城市。”(2)“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城市的市容和这里的生活面貌都很平庸。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大家也不难打发日子。”(3)这样平淡无奇的城市生活景象在现代世界中可谓比比皆是,因此阿赫兰也可以被看成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具有很强烈的象征色彩。由于城市缺乏活力,人民安于现状,所以当鼠疫灾难来临之时,整个城市陷入混乱与盲目之中也是必然之势。“事态严重到连朗斯道克情报资料局都在它播送的免费广播消息中宣称,仅在25日这一天中就收集并焚烧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死老鼠。这个数字使人们对眼下市内每天出现的情景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同时也加剧了大家的恐慌。在此之前,市民仅仅对那些让人憎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现那既不能确定规模也不能揭示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11)疾病的肆虐给民众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多的是心理上,除了由于无法预料而产生的恐慌和畏惧,我们也不应忽略鼠疫给人们造成的各种伦理困境。按照文学伦理学的观点,“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伦理困境往往是伦理悖论导致的,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伦理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伦理两难,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2]。在小说《鼠疫》中,伦理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对于小说主题与思想的表达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定居者——普通民众
对于小说中的普通民众而言,鼠疫给他们造成的伦理困境主要在于灾难对人类情感的割裂。鼠疫传染性极强,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防止更多人感染上这种疾病,首要的措施便是进行防疫性的隔离,这种隔离不仅仅是将病人与健康人隔离,从伦理的角度而言,也是将父母与儿女隔离、将热恋中的恋人隔离、将远在他乡的游子隔离……所以,当民众选择遵照医嘱进行隔离时,就必然会面对无法在情感上得到慰藉的两难处境,这是一种在理智与亲情之间的伦理选择。“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分离注定要延续下去,我们应当设法和时间修好。总之,从此以后,我们又回到坐牢的状态,迫不得已靠回忆往昔而生活。倘若我们当中有谁企图生活在对未来的向往中,他们很快放弃,起码会尽快放弃这种向往,因为他们正在体验想象力最终强加给相信它的人们的那种创伤。”(53)同样,仍然会有少数人坚持将个人情感放在首位,不顾及鼠疫带来的风险,“然而这一来,病人家属却关上了大门,宁愿与鼠疫病人亲密相守,而不愿与他分离,因为他们如今已知道分离是什么结局。于是只听得一片喊叫、命令、警察的干预,继而动用军队,这才把病人夺走”(66)。然而在大局面前,这样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也显得更加的无助和痛苦。
(二)抗争者——里厄医生
里厄医生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也是小说的实际叙述者。在灾难面前,因为自己特殊的医生身份,意味着里厄医生必然会在这场鼠疫当中肩负起比他人更多的义务与责任,因此,他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也显得更加的困惑与无助。“里厄大夫甚至在朋友面前确认有几个分散的病人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刚死于鼠疫时,他还不相信真有危险……里厄大夫在凭窗眺望这座尚未起变化的城市时,面对所谓的‘前景堪忧’,他几乎感觉不出在他心里已产生了轻微的沮丧之情。”(29)疫情刚刚爆发,里厄医生在目睹大量病症,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城市正在遭受鼠疫的侵害,他无法将一座现代城市与曾经在古代欧洲、亚洲杀死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鼠疫联系起来,“大夫不耐烦了。他这是在听任自己遐想,不应该这样。几个病例算不得瘟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行了”(29)。从伦理道德层面而言,里厄医生与生活在此处的人们所担忧的是一致的,这场鼠疫很可能夺去这座城市无数人的生命,特别是其中还可能有他的亲人与朋友,甚至包括他自己的性命。但从医生的职业立场出发,又必须抛开个人情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与鼠疫展开斗争,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却是必须要面对的,因此这样的一种伦理困境在里厄医生身上表现得是非常明显的。
(三)外来者——朗贝尔
相比于生长于阿赫兰的普通民众与里厄医生,偶然来此地采访的记者朗贝尔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被卷入这场鼠疫当中来的。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并不属于这座城市,没有义务同鼠疫作斗争,自然不必像其他人那样与这座城市共存亡,况且对妻子的思念让他无时无刻不想离开阿赫兰,“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所作的不顾一切而又千篇一律的长期努力,他们之所以拼命,是为了找回自己的幸福或防止鼠疫侵害自己。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将威胁着他们的监控企图拒之于门外”(103)。很显然,朗贝尔这一类人与普通民众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既相似又有差异:他们同样因为鼠疫而失去了自由行动的权利;同样与亲人远离;同样有面临感染恶疾,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但不同的是,外来者的伦理身份使朗贝尔在这座“死亡之城”找不到归宿,他不属于这里,因而也无需承受这种无妄之灾,他的伦理困境更集中体现在逃离与束缚之中。所以,朗贝尔最初选择的是不顾及这座城市的安危而使自己免于这场灾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花重金买通看守,准备逃出阿赫兰,如果从防治疫情大局出发,这样的伦理选择显然是自私的、利己的。
二、危机四伏中的伦理选择
在鼠疫的肆虐中,生活在阿赫兰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危难,“从那一刻起,可以说鼠疫已成了我们大家的事……就这样,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楚”(50)。但每个人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却又是有差异的。按照文学伦理学的观点,《鼠疫》中这种在相同灾难面前却表现出不同的伦理困境的现象,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小说人物他们不同的伦理身份。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3]在小说《鼠疫》中,普通民众、记者朗贝尔和医生里厄在便具有三种不同的伦理身份。首先,虽然加缪对普通民众的描述只是概括性的,但读者还是可以很直接地从小说中发现,作为处于危难中心的本地居民对鼠疫态度的变化。普通民众是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这群人象征着生活在本地的居民对待危机的选择。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者朗贝尔来自法国,只是因为工作才滞留在了阿赫兰,他认为自己与这场鼠疫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相对于当地的普通民众而言,他显然是一个外来者的形象,这两类人在对待鼠疫的问题上必然会产生伦理选择上的差异。与前两者都存在差异的是,里厄作为当地有名的医生,无可厚非地具有了在鼠疫中担当救死扶伤主角的“社会身份”,“由于社会身份指的是人在社会上拥有的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可或接受的身份,因此社会身份的性质是伦理的性质,社会身份也就是伦理身份”[4]。里厄医生对鼠疫的疫情判断、对患者的治疗以及组织防疫等工作都起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所以由于里厄医生的伦理身份,他在鼠疫中的选择是具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按照文学伦理学的理论观点,“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文学作品就是通过对人如何进行自我选择的描写,解决人的身份的问题”[5]。由此可见,小说《鼠疫》为读者呈现的不单单是不同人物,还有这些人物因为具有不同的伦理身份而做出的不同伦理选择这一种静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展现出了小说中人物的自主选择,并最终再次确认身份的过程。
(一)普通民众安于现状
在这场鼠疫中,普通群众作为一个整体,灾情的发展最与他们息息相关,在经历了对疫情的恐惧和因为隔离所带来的流放感之后,加缪笔下的群众又陷入了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鼠疫伊始时他们还能清楚忆起他们失去的人儿并思念再三……在鼠疫的第二阶段,他们连记忆力都失去了。并非因为他们忘记了亲人的面容,而是因为——这也一样——那已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面容,他们在体内已感觉不到亲人的存在。”(135)生活在阿赫兰的人在鼠疫中,似乎已经忘记了痛苦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而且“他们已进入了鼠疫时期的正常生活秩序,这种秩序越是不好不坏就越有效力。我们当中已不再有人满怀豪情,谁的感觉都同样平淡……头几个礼拜那种猛烈的激情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替代,把这种沮丧情绪看成逆来顺受可能犯错误,但它却真是一种临时性的认同”(136)。这样的情景,好像鼠疫从未发生过,此时的阿赫兰没有丝毫的波澜,一切又恢复了往日平淡乏味的状态。造成如此荒诞之景的原因正是普通民众的伦理身份,他们在灾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既受制于隔离政策而无法逃离城市,又由于缺乏与鼠疫进行斗争的专业医疗知识和足够的勇气,所以只能选择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言,“群体虽然有着各种狂乱的愿景,它却不能持久。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长远的打算或考虑”[6]。在灾难面前无所适从的阿赫兰居民正是一种“乌合之众”的象征,“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非常短暂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而很容易屈服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很快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隶”[7]。所以此时“我们的同胞已循规蹈矩,就像有人说的,他们已经适应了,因为他们别无他法”(136)。当然加缪对于这种选择显然是持一种忧虑和批判的态度,他认为“上述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136)。
(二)里厄医生奋力反抗
作为医生的里厄的伦理选择对于这个城市的兴亡是至关重要的,他如果也如普通民众一样对鼠疫采取一种默认和冷漠的态度,后果将不堪设想。诚然,在治疗鼠疫的瓶颈阶段,他也表现出了与他人一样的倦怠,“对其余的事,他并不抱很大的幻想,而且他的疲惫正在使他尚存的那些幻想逐渐消失。他明白,在他还看不到尽头的这段时间,他的职责已不再是治愈病人。他扮演的角色只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判死刑,这就是他的任务”(142)。但医生的伦理身份,让他即使对治疗鼠疫的过程感到麻木,也没有放弃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他们看来,加之于无辜者的痛楚实际上从来性质都一样,即是说,都是令人愤慨的耻辱”(160)。虽然疫情并没有因为里厄医生和其他同事的努力而立即有所改观,但他们仍旧不懈地努力着。并且在这场灾难面前,加缪并不是想将里厄医生这类人塑造为力挽狂澜的英雄,小说中同样表现出了他们的无助和疲倦,但最可贵的是,他们能正视自己的伦理身份,最终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认识了自我的职责。里厄医生的伦理选择也正如加缪哲学中“西西弗斯”一样,以自己的力量,不停地推动落下的巨石,“在清醒地认识到荒谬之后,最后投入到人类反抗的熊熊火焰之中”[8]。
(三)朗贝尔的重新抉择
相比于前两类人物,作为外来者的记者朗贝尔的伦理选择则表现得十分复杂,作为来自他乡的滞留者,阿赫兰对于朗贝尔而言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他也并不需要如里厄医生那样对鼠疫灾情做出自己的贡献,因而,在阿赫兰与和妻子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样的伦理选择并不违背他的伦理身份。加缪对于这种利己主义的选择并没有持批判的态度,反而认为“尽管表面上这种拒绝并没有别的方式奏效,但笔者认为那样做也确实有它的意义,而且这种方式即使有虚夸的一面,且矛盾百出,仍然显示了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种自豪感”(103)。在作家看来,每一个人的选择都应该是自由的。但是作家显然是想在朗贝尔这个人物身上赋予更多的伦理思考,朗贝尔在与里厄等人的接触中渐渐了解这场鼠疫的危害,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虽然在鼠疫中为了爱情逃离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过错,但这样的行为依旧会使他的良心受到煎熬,“朗贝尔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然还坚持过去的看法,然而,假设他真一走了之,他会感到羞愧。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那边的亲人”(155)。甚至他逐渐否定了自己外来者的身份,“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156)。通过朗贝尔这个人物伦理选择的转变,加缪使陷入伦理两难的人物在做出伦理选择时,选择了更为高尚的,也更符合他人利益的选项,这显然包含了作家强烈的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关怀,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文学之中的伦理选择问题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过程。
三、荒诞世界里的生存之道
在《鼠疫》的结尾中,突如其来的鼠疫并不是依靠着里厄医生和同伴们的努力而最终被消灭的,而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阿赫兰这座城市,人们因为鼠疫而产生的所有悲伤与苦痛仿佛都与这场灾害不在同一个维度之中,这样的构思,再次凸显出加缪作为存在主义文学大师所特有的对世界荒诞性的认知。小说中面对鼠疫逐渐变得麻木的人群,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加缪的另一外部代表作《局外人》中莫尔索的形象,同样的孤独、冷漠和无助。但作家在《鼠疫》中想要表达的显然与《局外人》有所不同,加缪曾这样说道:“《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诞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9]由此可见,作家想要借助“鼠疫”这样一个特定的伦理困境,发掘不同人物相同的选择,并最终认识到他们只有团结一致,才会有希望所在。
因此,里厄医生成为了加缪笔下塑造的第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物,他的伦理选择不是个人性质的,而是关乎于全城人命运的选择,他不再像默尔索那样离群索居,以自己独特又孤独的方式反抗这个世界的荒诞,而是采用集体主义的方式,积极应战鼠疫。再次,加缪塑造里厄医生这个人物,并不是要夸大他在与鼠疫做斗争中的英雄形象,而是宣扬在荒谬世界中,每个人只有正确把握自己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尽自己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就能够战胜困境。“不过,里厄也明白,这本编年史不可能是一本最后胜利的编年史,它无非显示了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了些什么,并指出今后如遇播撒恐怖的瘟神凭借它乐此不疲的武器再度逞威,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难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233)最后,里厄不仅在与鼠疫的斗争中勇于奉献,也在这场灾难中重新审视了人类,无论是对爱情、亲情还是友谊他都有了新的认识,这样的感悟自然也源于他积极、主动伦理选择下的内心收获。
记者朗贝尔伦理选择的转变也绝非作家为了情节的简单创作,而是包含了强烈的存在主义思想。正如萨特所言:“而存在主义者却说,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而不是通过某一特殊事例或者某一特殊行动就作为你整个承担责任。”[10]促使朗贝尔担负起责任,做出英雄般的选择也不是偶然,而是在鼠疫灾难面前,被里厄医生等人的坚持不懈、救死扶伤的态度所感染,从而重新审视自我后做出的改变。“尽管如此,如我曾经说的,我们是能判断的,因为人是参照别人进行选择的;而在参照别人时,人就选择了自己。首先,人能够判断——也许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一种逻辑判断——在有些事情上,人的选择是根据一种错误,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选择则是根据真实情况。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说他欺骗自己。因为我们曾经解释人类的处境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处境,没有借口也没有援助,所以任何人以自己的热情或者发明什么决定论学术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就是自我欺骗。人们可以提出反对说:‘可是为什么他不可以选择自我欺骗呢?’我的回答是,我没有资格在道德上对他进行判断,但是我断定他的自我欺骗是一种错误。谈到这里,人们没法不作(做)一项真伪的判断。自我欺骗显然是虚伪的,因为它掩盖了人有承担责任的完全自由。”[11]朗贝尔在满足“小我”与追求“大我”的抉择中认识到,放弃自我欺骗,追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获得内心安宁的道理,这样一种转变是更有价值的。
小说《鼠疫》显然传达出作家希望唤起更多的“局外人”参与到集体反抗荒诞世界的意图。正如加缪在给罗兰·巴特的信中谈到了关于《鼠疫》主题时所言:“我认为同《局外人》相比,《鼠疫》无可辩驳地代表了从独立反抗到对团体抗争的转变。如果说从《局外人》到《鼠疫》是一种进化的话,这种进化是朝着团结和参与方向的。”[12]从对小说《鼠疫》人物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的分析,我们同样不难看出在荒诞的世界,个人利益的安危是建立在他人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只有做出符合道德和正义的伦理选择,才能脱离困境,给这个世界点亮新的希望。
注解【Notes】
①[法]加缪著:《鼠疫》,刘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张茂军:《加缪,一个对抗荒诞的反抗者——加缪文学思想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4页。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
[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宇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7][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宇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8][法]加缪:《西西弗神话》,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9]张茂军:《加缪,一个对抗荒诞的反抗者——加缪文学思想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10][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11][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译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2]张茂军:《加缪,一个对抗荒诞的反抗者——加缪文学思想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The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the French writer Albert camus' novel The Plague described the coastal city of Algeria, Oran that suffered plague, the city residents were living with the threat of death. Different characters made different choices in the face of distress: the residents are from being panic disorder to becoming numb; Dr. Rieux organ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team,developed serum and carry out rescue work; Reporter Tarrou is trying to escape, but his heart has changed ultimately. By taking the method of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ethical choice of the residents, Dr. Rieux and the reporter Tarrout, and fi nally convey the ethics thought in The Plague.
The Plague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Ethical Predicament Ethical choice
Duan Yaxin is from Humanities Schoo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The research area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uropean Literature.
段亚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欧洲文学。
Title: The Ethical Selection in The Pla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