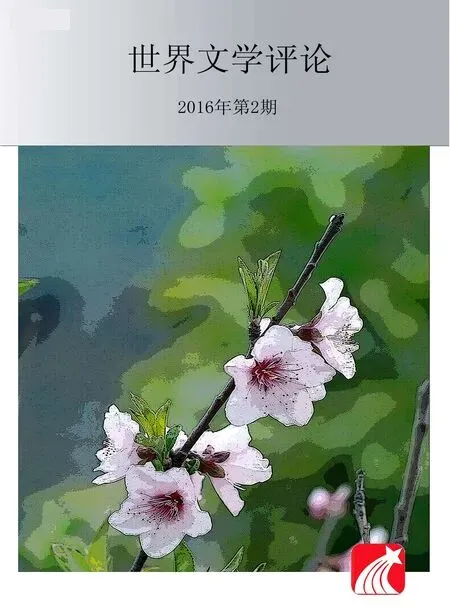门罗的“丑陋”现实主义和加拿大想象①
2016-11-25丁林棚
丁林棚
门罗的“丑陋”现实主义和加拿大想象①
丁林棚
内容提要:在门罗的小说中,作者将加拿大现实和苏格兰历史与个体叙事相糅杂,呈现出独特的时空交织体民族叙事。作者颠覆了宏大叙事和民族神话,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丑陋面,将焦点转向个人及家庭空间的民族文化象征意义,再现出加拿大想象。这种时空交织体使作者利用丑陋现实主义以平凡的叙事呈现加拿大苏格兰人的位移身份,构建加拿大人的想象社区。
日常生活 丑恶现实主义 民族性 门罗
在门罗的小说中,苏格兰记忆和加拿大现实交织成一种时空共同体,共同塑造了她的加拿大想象。她的作品没有神话式的宏大官方叙事,而是利用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展现民族想象,通过“丑陋”的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日常生活细节,绕过传奇、神话用个体视角对生活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进行观察,塑造苏格兰——加拿大身份想象。门罗小说中“处处可见耸人听闻的恶行,光怪陆离的犯罪,令人脸红的性幽默,大庭广众之下的杀人放血”[1]。她的作品充斥了丑恶和罪行。正是这些丑陋的现实给她一种强烈的地方归属感和民族想象,构建了基于现实主义的民族“想象共同体”[2]。本文旨在细读门罗的短篇小说,阐释其文化意义,分析“丑陋”现实主义手段再现苏格兰—加拿大民族想象的作用。
门罗的“丑恶”现实主义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就是用“哥特式”写作再现生活的恐惧和不安。这种“丑恶”现实主义描写不像英国小说《德古拉》那样描写吸血鬼或怪兽形象,也不像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心理畸变小说那样,而是刻意展现现实的“恐怖性”。例如,《荒野小站》背景设置在荒野,对生存造成危险,并影响到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状况。安妮作为一个孤儿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活,忍受着丈夫带来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痛楚。荒野生存使安妮疯癫,在丈夫黑伦死后失去理智。她的精神和肉体存活反映了加拿大早期移民拓荒生活的艰辛,表现出典型的加拿大哥特写作特征,突出了人与荒野的精神联系和冲突。小说中人物和背景都有据可查,如1898—1905年的英国驻加拿大总督明托伯爵等。部分情节甚至是作者对自己家族史的改造,如故事中的兄弟俩就是她的两个祖父。小说中描写了加拿大移民的精神隔绝,又对普通女性生活中的家庭暴力、疯癫、监禁等丑恶现象进行细致观察,站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体验生活的丑恶,展现了加拿大—苏格兰性的日常性。
实际上,这种“丑陋”现实主义所展现的是一种“平庸民族主义”[3]。民族想象并不总是一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宏观文化表述,它常常“植根于日常生活,存在于社会互动、习惯、常规和实际知识的普通细节之中”[4]。文化的意义往往“在普通行为中表达出来”[5]。门罗认为现实生活虽不起眼,但却是个人身份、民族想象的现实基础。随着安德森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提出,民族与身份不再被认为是“一切实践的根本或是隐藏在行为表面之下的本质”[6],而是和日常生活甚至是丑陋的现实有关。民族与国家正是来自现实、地方、个人,来源于看似随机事件序列,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因此,“官方”、“历史”和“正统”等民族性概念被后现代语境下的平庸现实主义所替代,转向琐碎而细微的现实。
在门罗的作品中,作者甚至借用丑陋的身体细节再现民族想象。身体描写成为门罗构建苏格兰性的重要媒介。威廉姆斯指出,身体是被生活书写的“体验的身体,是积极的、表达性的身体,是‘有意识’的体现,它不仅是文化和自我生存的基础,还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和各种机制的基础”[7]。“身体的坐卧行立”都使得它成为“文化和身份的表征的体现”[8]。例如,在《田中石》中,姨妈的双手“红得像剥了皮的兔子”[9]。原来,这是“为了保持地板和桌椅洁白,长期使用石蜡”而造成的。[10]但是叙事者却只记得“曾经见到过许多这样的双手”[11]。在此,这双丑陋的手是苏格兰长老教信仰的体现,折射出清教式生存状态下加拿大先驱的精神状态。[12]同样,在《我母亲的梦》中,阿里莎“像疯了一样连续两个晚上不停地清洁房屋”,她“感到一种需求,必须把每一个碟子、每一把锅、每一件装饰品都清洗干净,必须把每一张照片上的玻璃擦亮,拉开冰箱,擦洗它的后部,在垃圾桶里倒满漂白粉”[13]。这种丑陋的生活细节无疑体现出加拿大苏格兰人的民族性格,反映出他们“狭隘而顽强的原教旨主义的长老教信仰”[14]。可见,在北美土壤上生根发芽的是一种嫁接而变形的文化模式,它反映了早期加拿大移民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
门罗的丑陋现实主义还体现在对苏格兰历史的琐碎化描写上。尽管历史往往被神圣化用以强调民族的“本真性”,但门罗的本真性却没有光辉的形象。在《岩石城堡的景观》中,叙事者以个体视角呈现出日常生活背后的民族想象。正如盖尔纳所说,“一个人具有民族性就像他有一个鼻子和两只耳朵一样”[15]。例如,叙事者通过碎片、孤立的陈述,在修正故事的过程中展现了一个普通加拿大人对历史和民族记忆的探索。哈泽尔拿着笔记本到处寻访丈夫的踪迹,用自己的视角重构家族史和民族记忆。她甚至出现了历史颠倒和错误,如把1645年苏格兰菲利浦豪战争誓约派的胜利日记为1945年,并以为丈夫在“二战”中服役和菲利浦豪战争有关。宏大的民族战争在叙事者笔下被平庸化处理,凸显了日常生活的平凡,这种明显的错误也反映出加拿大历史和苏格兰历史的现实疏离。哈泽尔此时成为一个完全的异域人,“独自坐在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角落,不停地记录笔记以使自己不陷入惊慌”[16]。这种细节描写显然凸显了苏格兰—加拿大时空体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对加拿大苏格兰后裔的心理影响。
丑陋现实主义的描写以个体和偶然的视角重构了民族性。这种民族想象既不能摆脱苏格兰后裔的欧洲历史渊源,又同时表现出对这段历史的“遗忘”和“背离”。加拿大性就是在苏格兰民族记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矛盾体。在《毫无特色》中,叙事者眼中的苏格兰“毫无特色”[17],到处肮脏不堪,马路坑坑洼洼,无法通行。就连这里的居民也单调乏味,只知道种植“大麦、燕麦和土豆,从不尝试一下小麦、黑麦、萝卜和卷心菜”[18]。当民族寻根之旅和想象中的浪漫无法一致时,幻灭的苏格兰现实和想象中的民族性产生进一步错位。面对艾德里克河谷,叙事者感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需要回到远离自己生长的国土去寻找过去。尽管我对过去的知识积累了不少,但我仍然是个天真的北美人。过去和现在在此地纠缠在一起,共同创造了平庸而又令人不安的现实,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19]。
在门罗的小说中,宏大的神话和苏格兰传奇也在叙事者的亲历中一个个消解,这种神话的幻灭给民族想象抹上了一层丑陋和平庸的色彩。在《城堡岩石的景观》中,苏格兰历史和民族传说在叙事者的口中成为一条条孤立线索(如但丁《炼狱》中出现的哲学家迈克尔·司各特、苏格兰游击英雄威廉·华莱士以及被捕捉并杀死的魔法师梅林的故事),就像她的家族史和个人经历一样等待着核实验证。叙事者来到艾德里克教堂。这座建于1824年的教堂无论在“历史面貌还是庄重气氛方面”再次令她感到失望。她甚至感到,自己“非常显眼,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浑身感到寒冷”(6)。的确,民族(nation)有一种特别的模糊性,因为“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文化意义的建构体系,是对平庸生活的再现,而不是‘社会政体’的组织结构,它强调的是知识的不稳定性”[20]。门罗所描写的苏格兰—加拿大矛盾时空体反映出后殖民时代加拿大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平庸化是再现民族想象的一种文化表征手段。在对模糊性的探索中,作者构建出一个“居间”的场域,需要叙事者和作家从各方力量之间进行“协商”。的确,她小说中的角色常常需要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故事和传说中捋清脉络,通过否认和再确定重新组织现实。加拿大多元民族性就体现在被“嫁接”到加拿大本土的苏格兰记忆之上。
“混杂性”身份的描写甚至表现为地点的模糊、时间的混淆等。在《不同》中,叙事者发现必须对各种细节重新整合安排,甚至会把事实和幻想混淆。她的探寻常常在“不经意间偶然变得清晰”,却不能给她提供任何关于过去的主线,[21]因此必须在各种元素之间“协商”和探索。在《查德莱和弗莱明家族》中,祖父的身世成为诸位妯娌闲聊的构建品。她们的对话显然是对民族记忆“协商”过程的再现。几位姨妈“各有各的故事,说法不一”[22]。母亲认为祖父是个高材生,后来把钱财挥霍一空移民加拿大。伊莎贝尔却认为,他和一个女仆有染,被逼无奈逃到了加拿大。其他几位姨妈也各自各显展开猜测,有的甚至认为祖父“可能有法国血统”[23],并追溯到威廉王。祖父的形象在几位饶舌女人的闲聊中一遍遍被协商改变,完全失去了光辉的高大形象。这种丑陋现实主义的表征不但没有使一切明朗,反而加剧了叙事者家族身份想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门罗对加拿大苏格兰人的历史想象印证了巴巴所说的民族寓言的集体性,因为“个人故事和个体经历的讲述最终包含了集体性本身的复杂构建过程”[24]。门罗也认为,“即便在小声说话的狭窄空间中,仍然会有故事诞生。人们是带着各自的故事活动的”[25]。民族想象是个过程,其意义不断被创建和更改。民族“是一个模糊暧昧的叙事过程,它使文化处于一种最富生产力的状态之中”[26],在叙事的构建过程中不断被生产、组织、复制、拆分、重构。同样,《暴风雪》的叙事者也面临着通过个体叙事构建民族历史的困惑:“我想,当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怎么肯定我的确知道了呢?故事中我曾经利用了这些人们,不是所有人,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我随心所欲地引诱他们,改变他们,塑造他们,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27]
门罗善于通过对平庸和丑陋现实的关注再现民族想象,把苏格兰民族记忆和加拿大的现实空间存在结合在现实的个体表征上。民族的再现“是矛盾和不确定的,对历史性的民族志书写开放了其他个体叙事的可能性,允许了差异的存在”[28]。这种个体、随机和细节视角使作者借用后现代的边缘视角重新建构了关于民族的寓言,消解了官方叙事,展现民族想象的平庸和丑陋。詹明信指出,关于民族的“寓言精神在本质上是非连续的,充满了停顿和异质性,具有梦想的多重含义,而不是对符号的一种单一均质的再现”[29]。
总之,门罗将苏格兰和加拿大元素相交融,用矛盾的时空交织定义了加拿大的民族想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作者运用丑恶现实主义手法颠覆和解构了民族叙事的宏大。她的日常故事“与其说是一种线性叙事,不如说是记忆的油画,上面覆盖了一层层的修饰痕”[30]。透过这些修饰痕,我们可以看到门罗人生的家族史和苏格兰民族记忆,它呈现了加拿大苏格兰人的“位移身份”,以个体视角构建了加拿大人的民族想象。
注解【Notes】
①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为11BWW031)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Howells, coral Ann. Alice Munro: contemporary World Writers. Manchester UP, 1998, p. 58.
[2]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2006, p. 145.
[3] Billig, Michael.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1995, p. 37.
[4] Edensor, Tim.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Oxford: Oxford UP, 2002, p. 17.
[5]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1, p. 57.
[6] crang, Michael. cultural Geographies. London: Routledge,1998, p. 162.
[7] Williams, Simon J., & Gillian Bendelow. The Lived Body: Sociological Themes, Embodied Issues. London: Routledge,1998, p. 208.
[8] Edensor, Tim.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Oxford: Oxford UP, 2002, p. 72.
[9] Munro, Alice. Friend of My You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0, p. 25.
[10] Munro, Alice. Friend of My You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0, p. 25.
[11] Munro, Alice. Friend of My You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0, p. 25.
[12] Munro, Alice. Friend of My You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0, p. 25.
[13] Munro, Alice.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98, p. 212.
[14] Gittings, christopher E. "The Scottish Ancestor: A conversation with Alice Munro". Scotlands , 1994(2), p. 85.
[15]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nded. Oxford: Blackwell, 2006, p. 6.
[16] Munro, Alice. Friend of My You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0, p. 75.
[17] Munro, Alice. 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06, p. 3.
[18] Munro, Alice. 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06, p. 3.
[19] Munro, Alice. 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06, p. 7.
[20] Bhabha, Homi K.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Nation and Nar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1-2.
[21] Munro, Alice. Friend of My You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0, p. 23.
[22] Munro, Alice. Friend of My You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0, p. 14.
[23] Munro, Alice. Friend of My You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0, p. 14.
[24] Bhabha, Homi K.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 Homi K. Bhabha.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92.
[25] Munro, Alice.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p. 120.
[26] Bhabha, Homi K.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Nation and Nar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3.
[27] Munro, Alice.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p. 120.
[28] Bhabha, Homi K.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 Homi K. Bhabha.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300.
[29] Jameson, Frede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n, 1991, p. 73.
[30] Moore, Lorrie. "Introduction". Moons of Jupiter. Toronto: Penguin, 2006, p. 9.
In her short stories, Alice Munro weaves personal narratives with her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 Her stories deconstruct the sublime mythic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sordid" reality of quotidian life, representing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 through personal, marginal, and local depic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Munro's realistic portrayal of the familiar and quotidian landscape and offers a cultural reading of her construction of canadian nationness.
everyday life sordid realism nation Munro
Ding Linpeng is from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Peking University. Field of interest: Literature in English.
丁林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
Title: Munro's "Sordid" Realism and canadian Imag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