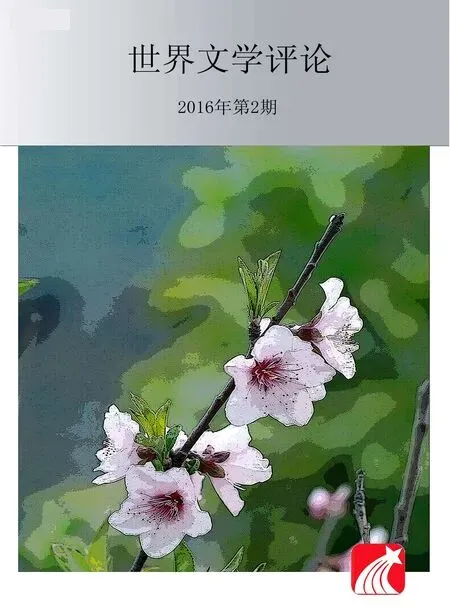王尔德《莎乐美》中唯美主义艺术与道德的冲突①
2016-11-25蒋润园徐雅恬
蒋润园 徐雅恬
王尔德《莎乐美》中唯美主义艺术与道德的冲突①
蒋润园 徐雅恬
内容提要:奥斯卡·王尔德(以下简称王尔德)是英国19世纪的作家、艺术家,其唯美主义理论成为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先驱,对后期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前人多从艺术至上、艺术无用论等唯美主义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倾向和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矛盾。主人公莎乐美作为基于唯美主义理论塑造的美学形象,身上包含的道德元素,构成了文中艺术与道德的多重矛盾。本文根据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论,从七层纱舞、月亮及死亡意象的角度,分析《莎乐美》一文中体现出来的王尔德关于艺术与道德无关的思想,以及文中蕴含的对这种想法的质疑及否定。
奥斯卡·王尔德 《莎乐美》 艺术 道德
Authors: Jiang Runyuan is from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fi led i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Xu Yatian is from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fi led i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初,王尔德的作品陆续被翻译引进国内,对于王尔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尔德的童话作品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对于王尔德文学理论的研究,如吴刚的《王尔德文艺理论研究》(2001)、张介明的《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2005)、吴其尧的《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2006)等,然而对于王尔德戏剧《莎乐美》的研究甚少。
国内对于《莎乐美》的研究主要集中角色分析,月亮意向分析以及基于王尔德唯美主义理论对《莎乐美》中的唯美性的分析。同时也有对《莎乐美》中存在的道德与艺术的矛盾进行的分析。从人物角度出发,刘茂生在《莎乐美从唯美主义到现实主义:莎乐美身上的道德特征》(2008)中提出,王尔德在创作莎乐美这一形象时,虽然坚称坚持唯美主义的艺术理论,但在她身上体现出的身份背景、伦理关系等让她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社会道德的印记。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王尔德的研究在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主要以传记的形式记录和探索了王尔德的生活,但是,对于王尔德的作品《莎乐美》的研究相比之下就数量和广度都有所不足。许多研究者将其与王尔德的艺术理论和文学道路联系起来,如艾尔曼(Richard Ellmann, 1918-1987)的研究认为,《莎乐美》是王尔德文学思想趋于成熟的体现。[1]一些研究者对莎乐美的形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Norbert Kohl认为,莎乐美是“致命的女性形象”(femme fetale)[2]。部分研究着重于《莎乐美》中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及其象征意义,有的认为先知约翰代表基督教的善恶观念,莎乐美代表感官体验主张,而希律王在亮着时间摇摆;有的结合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莎乐美代表了本我,希律王代表自我,约翰则代表超我。
二、《莎乐美》中艺术与道德的冲突
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的先驱,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与道德无关”等具有重要后世影响意义的唯美主义理论,这些理论随后都成为了唯美主义思想的奠基石。尤其是“艺术与道德无关理论”, 将艺术完全凌驾于道德之上来保证艺术的完全自由。
但是,在王尔德后期的剧作《莎乐美》中,这些理论仅仅得到了部分验证,仔细推敲,却会发现他在艺术和道德的冲突面前,已经做出了现实的判断。在这部作品里,王尔德体现出来的唯美主义观念是含混而矛盾的。(一)从七层纱舞看艺术与道德的冲突
七层纱舞是整部戏剧高潮的前奏,是莎乐美亲吻约翰头颅的序曲,通过这样一种唯美的艺术表达形式,体现出王尔德心目中艺术与道德的矛盾和冲突。
一方面,七层纱舞是王尔德借莎乐美之舞,对于艺术的至高追求的表达,莎乐美身上的罪与美,象征着现实中的艺术与道德。七层纱之舞,即在舞蹈的过程中层层揭去面纱。莎乐美的这一场舞蹈,是通向自己的欲望、通向自己的审美追求的道路。遆存磊在《莎乐美的七层纱之舞——解读王尔德的〈莎乐美〉》中提到,“莎乐美在宫廷中跳着七层纱之舞,妖异魅惑,充溢着欲望的气息;而究其本质,她的美,她的爱恨之切,又是纯洁无杂质的。莎乐美气质的矛盾,是于他人之眼的映射,在她自己却是天然谐和的,并无不适之处”[3]。莎乐美执着追求自己的爱与欲望,这种纯净的、单一的向往本身就是对于美和艺术的追求,无论母亲、父亲和他人如何阻拦。而这场七层纱之舞,就是她这种狂热的追求的过程。莎乐美的舞蹈模仿从天梯降到地狱时,一次次地脱去纱巾。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抛开自己作为公主的条条框框,抛开人世间的种种束缚,一方面是执着自身追求,从天梯降到地狱的放逐,另一方面又是为了爱情和美,从人世通向至真至美的升华。莎乐美作为一国的公主、父亲被处死、母亲被父兄夺走,平日里当然被重重束缚所包围,而七层纱舞之中,面纱一层一层褪去,正是象征了社会中的道德、教条一层层脱离开去,直到剩下本真的、纯净的莎乐美自身以及她心底深处的追求和爱情。约翰作为莎乐美的审美对象,也成为她压抑生活中的一个突破口,是莎乐美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不断增长。从这方面来看,也是王尔德寄希望于莎乐美,希望自己、也希望艺术脱离生活的囚禁、道德的束缚,从而达成“为艺术而艺术”的根本目标和“艺术与道德无关”的愿望,维护艺术本身的纯洁性和真实性。
另一方面,七层纱舞暗示着王尔德心中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以及其必不能共存的思想观点。莎乐美跳七层纱舞,是其摒弃道德追求艺术过程的见证。当希律王肯定地表明,只要莎乐美为之做舞,便会答应莎乐美的一切要求之后,莎乐美本来被传统道德观念牢牢束缚,万般拒绝,后来则处于对自身愿望和艺术的追求以及对爱情的向往,转变为愿意跳极尽魅惑的七层纱之舞。莎乐美要求侍从“给我把香油和那七层面纱拿来,并且要他们把我这脚上的鞋子脱下”。这一举动在希律王看来是“哦!你准备赤着脚跳舞。那好极了!那好极了。你的小脚儿一定会像白鸽一样。它们一定会像在树枝上舞蹈着的小白花儿一样”。可见莎乐美不仅选择了舞蹈,更是选择了用七层纱将舞蹈推进到极致妩媚的境界,又赤足而舞展现其纯洁、美好的一面。据艺术学家研究,七层纱舞起源于伊什塔尔(Ishtar)下到地狱的神话的一种东方舞蹈。七层面纱分别代表着太阳、月亮和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这七种神的可见载体,这象征了自然界和人类精神的最大能量。研究者认为,人们可以连续穿越七重天,而这七层面纱之舞,正象征着想象、理性、激情、极乐、天生的胆识、天赐的同情和天赋的认知。莎乐美的舞蹈妩媚妖娆,原文中认为,“在鲜血之上跳舞更是一个恶兆”(She must not dance on blood. It were an evil omen), 在自己的继父面前展现婀娜多姿在传统观念看来是不道德、淫秽的,但是为了追求极致的美,达成对约翰疯狂的追求,莎乐美摒弃了心中道德的观念,最终也落得死亡的结果。这表明,莎乐美虽然看似实现了其艺术追求,获得了约翰的头颅,但在希律王所代表的社会现实的压迫之下,最后还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意味着,王尔德虽然支持艺术与道德无关,但不可避免地为艺术追求的过程刻上了深深的道德烙印,并且暗示了这种审美追求最终的悲惨结局。莎乐美身上的罪恶与美的冲突,也是王尔德心中矛盾心理的体现。
(二)从“月亮”看艺术与道德的冲突
1.月亮在传统意义中的意向
月亮在文学作品中一直都是女性形象,在古希腊神话中月亮神阿尔忒尼斯(Artemis)是天父宙斯的女儿;在苏美神话体系中,月亮神伊南娜(Inanna)一直都是少女形象。在传统意义中,月亮历来被认为是女性象征符号。月亮的女性象征意味在《莎乐美》中得到了保留,并有了更丰富的发展,代表着全然不同的象征意味:在希罗底的侍者眼中月亮是死美人,在希律眼中是疯女人,在莎乐美眼中是纯洁的少女。不同人物对于月亮的看法差异体现了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也象征着他们相异的审美追求和道德判断。
2.月亮之于艺术
《莎乐美》中数次提及月亮。作为剧中人物共有的审美对象,月亮寄托了莎乐美对艺术的执着和对美的追求,也表达了王尔德的艺术理念和道德观念。
文章的开头希罗底的侍者不断重复“这月亮也像一个死美人似的,她走得很慢”,预示着故事的悲剧走向。在莎乐美血上做舞之后,希律王说“月亮变成血一样的红了”。红色在西方文化中是死亡的象征,影射莎乐美满足希律王的欲望跳七层纱舞,也就不可避免地刻上了罪恶与死亡的印记,作为艺术和美的代表,莎乐美已经无法逃脱传统道德的审判。最后,尽管“一团大黑云与月亮相遇,把它完全遮掉了”,但落幕之前“一道月光落在莎乐美身上把她用光明盖着”,表明莎乐美虽死,但对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的执着已经在莎乐美身上达成。
莎乐美亦是王尔德在“艺术与道德无关”理论指导下创作出的形象。希律王认为月亮好似一个醉妇、一个发了狂的女人,是莎乐美爱上约翰之后狂热的审美追求的映衬。莎乐美向约翰求爱不成继而跳七层纱舞来获得约翰的头颅。“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并不符合一般意义上以‘善’为基础的美学标准,她在浓墨重彩和曼妙舞姿的烘托下显得冷艳而残忍,亲吻头颅的动作更是令人感到变态及生畏。”[4]七层纱舞以及亲吻头颅这一系列有违于常理的动作体现出了莎乐美无视道德的美感。
借莎乐美和月亮,王尔德也在剧中阐述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借由希罗底之口,王尔德说,“月亮像一个月亮就是了”,这句话与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希罗底回应希律王“她像一个发了狂的女人,是不是”的答复,暗示了王尔德认为喝醉、发狂、裸体等等的词汇描述月亮都不足以对其进行道德判断,月亮只作为其本身而存在,亦是说艺术本身与道德无关。
3.月亮之于道德
从希律和莎乐美对月亮的其他解读中,也可以读出道德批判的印记。
希律在莎乐美中是淫邪、肉欲的代表,其眼中的月亮同样也有着淫乱,不道德的表征意义。希律对莎乐美有着执着的不伦的迷恋,然而妻子阻止他,莎乐美拒绝他,这种求而未得让他在欣赏月亮时也带上了对莎乐美的爱。他感叹:“她像一个狂女,一个到处找着情郎的狂女。她又裸着体。她全然是裸体的。她在霄汉之间脱得赤条条的。那些云想去遮盖她可是她不愿意。她好像一个喝醉了的女人偏来倒去地在云里穿过……我想她一定是找着情人……她不是像一个东偏西倒的醉妇吗?”[5]作为审美对象,月亮展现了审美者的内心世界。月亮在此处是欲望的象征,“找着情郎的狂女”,“全然是裸体”充分表达出了希律对莎乐美——他的继女的爱与迷恋,这是乱伦的不道德的爱,充满着淫邪和肉欲,渴望着感官上的满足。
从希律身上可以看出王尔德对希律代表的邪恶伪善的社会上层的批判。希律在王尔德笔下是无视道德的典范,弑兄夺位,崇尚金钱权利,又对继女有不伦的爱。“……王尔德所扮演的更像是一个路见不平就出手的游侠角色。他基本上是从非功利的艺术家的角度来审视和参与周围的纷争,既没有让自己的道德立场受到实际身份的和利益的拘囿,也没有害怕自己的言论前后不一致或观点矛盾而变得出言谨慎,噤若寒蝉,而是放任自己纵横恣肆地游走于各条道德论战的战线之间。”[6]王尔德宣称艺术与道德无关,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王尔德借由希律针砭时弊,讽刺了维多利亚时代丑恶的现实。
莎乐美在对月亮的称颂中,体现出来的则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美学标准。莎乐美眼中的月亮是纯洁的,“她又冷静又纯洁。她一定是一个闺女,她大有闺女的美质,不错,她是一个闺女。她从来没有把自己污辱过,她从来没有像其他仙女一样把自己的身子让男子轻薄过”[7]。莎乐美背负着父亲被杀,母亲嫁给叔父的痛苦,而后又被继父垂涎美色。生活在这种种束缚中的莎乐美苦闷但是无力反抗,只有纯洁如“处女”的月亮能让莎乐美惺惺相惜,她借月亮表达自己不愿被男子污辱轻薄,表达出对充满乱伦欲望的希律的强烈的谴责和排斥。莎乐美在见到约翰先知时,对约翰的描述中又提及了月亮,“我深信他和月亮一样纯洁。他好像一道月光……”[8]在莎乐美心中,月亮是纯洁的美的象征,约翰又有如月亮般纯洁,她对约翰的强烈追求正显示出了她对美的强烈追求。此处,王尔德借莎乐美表达己愿,虽然处在俗世的种种虚伪堕落的道德束缚之中,但是只有对纯洁的美的追求才是心中己愿。这两处对月亮的称颂,一方面表现出了莎乐美不愿被男子玷污,保持自身的高洁的愿景。另一方面,对约翰纯洁肉体的向往也体现其对于约翰象征的至高无上的道德的向往。
王尔德的文学理论中虽然称艺术与道德无关,但是此处,他还是将传统道德思想体现在了作品中。Joseph Donohue 在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中提到了Philip cohen的观点。Philip cohen认为,王尔德的作品中,反映出了莎乐美与约翰一系列的精神和道德危机,标志着希律头脑中艺术追求和道德判断的冲突,同时也是王尔德自身艺术与道德的冲突,既是他对于自身不道德行为的“掩饰”,也是一种“坦白”。[9]
(三)从“死亡”看艺术与道德的冲突
死亡历来也是王尔德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莎乐美》中同样也可以感受到大量直接或者间接的死亡讯息,如希罗底侍从眼中的月亮“像一个从坟墓里走出来的女人一样”,又如空中不时传来的预示着死亡的拍翼声。叙利亚少年在为莎乐美打开囚禁约翰的古井后自我了却了生命,约翰因莎乐美而被砍下了头颅,希律又因惧怕莎乐美的疯狂下令将其杀死。死亡贯串了这整部剧作。但在王尔德的笔下,死亡是具有美感的,死亡是由爱而生的,死亡有其道德意义。
1.唯美的死亡
王尔德在《莎乐美》描写了两个极美好的形象,莎乐美是白银做脚的小公主,美丽纯洁如月亮,让叙利亚少年和希律都为之倾倒。约翰是神圣的上帝的侍者,有如山地积雪般洁白的身体,有乌黑浓密的头发和朱红的嘴唇。两者都是世间最纯净美好的肉体。然而,这样的两个人都最终却都遭遇了死亡的结局。然而这些美好人物的毁灭却能给世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美是王尔德一贯的价值追求,他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创造美,展示美。死亡是人们一直都惧怕的,人们避免谈及死亡从而无法了解死亡的美学意义。然而王尔德由于自身的人生际遇,对死亡有了更深的理解。“王尔德通过其作品中塑造的美好人物最终迎来了死亡结局的悲剧故事,意在挖掘美的毁灭的价值意义,继而提升死亡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10]王尔德将死亡变成了展现美的一种手段。人的生命是脆弱而短暂的,莎乐美或者约翰终会以人的身份在世间消失,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形象却能在现实中永远流传下来。
但是此处也不乏艺术与道德的矛盾点。王尔德对于死亡的艺术态度是超然的,他将死亡作为自己的艺术创作素材,认为死亡仅仅是展现美的一种手段。然而,在约翰死后,希律说道:“我深信一定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11]死亡在此处不再是纯粹美的艺术的体现,相反,它有了道德判断意义。约翰先知,作为最崇高的道德的代表,他的死亡代表了对道德的蔑视。王尔德借希律之口,传达出了破坏道德将会受到惩罚的意愿,希律口中的不幸的事即无视道德将会受到的惩罚。由此可见,作为纯唯美意向的死亡在此处还是摆脱不了道德的影子。
2.道德的死亡
文中叙利亚少年爱上了莎乐美,在阻止其亲吻约翰无果后也选择了自杀。叙利亚少年的死亡象征着道德束缚的死亡。叙利亚少年不是可有可无的虚设。在这部戏剧中,他作为莎乐美的一部分,是莎乐美身上的道德标示和处女情结的具体化。“在莎乐美遇到先知之前,她清冷,自恋,是没受过欲望污染的处女;在听到先知的声音之后,莎乐美一再要求叙利亚人放出约翰,并要靠近看约翰肉体的纯净之美”[12],在叙利亚少年死后,莎乐美的欲望和对唯美主义的追求完全体现了出来。叙利亚少年的死亡是莎乐美充分追求欲望和无视社会道德的开端,象征着莎乐美自身的道德束缚的消失,体现了王尔德“艺术与道德无关”的美学理论。
但同时,叙利亚少年的死亡预示着莎乐美与约翰之间的爱的悲剧性结局,带有一定的道德批判性。叙利亚少年不断地告诫莎乐美:“请您莫停在此处,公主,我万请您莫停在此处。”[13]“不要望着这个人,不要望着他。”[14]然而莎乐美还是执意要亲约翰的嘴。最终叙利亚少年在哎的一声叹息中,自杀倒于莎乐美和约翰之间。莎乐美对约翰的追求可以说是对艺术与美的追求,但是这样的追求一旦超越了道德的界限,最终还是落入毁灭的结局,这预示了艺术至上的失败。王尔德认为艺术与道德无关,但是此处,对莎乐美进行了道德的判断,不免与其艺术理论产生了矛盾。
3.罪恶的死亡
莎乐美跳完美妙绝伦而又令人生畏的七层纱舞后壮烈地死去,她的死亡具有超越现实的美感。“那种毁灭自己又剥夺他人生存权利的死亡看起来残忍而恐怖,但是这种死亡却具有超越生活,超越现实的艺术之美。”[15]莎乐美的死亡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她疯狂地爱上了约翰,强烈地渴望能够触摸约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不惜将约翰的头砍下来亲吻他的嘴。莎乐美在做七层纱舞之后,获得了她一心追求的东西——约翰的嘴。她忘情地亲吻着他的嘴,就像是对待一个成熟的果子一样。莎乐美的死亡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显得恐怖而诡异,但正是这种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死亡强烈的展示出了一种超越现实,远离生活的纯粹的艺术之美。这也符合了王尔德“艺术与道德”无关的唯美主义理论。
但是王尔德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传统道德判断的影响。在她终于亲吻到约翰的嘴后,原本深爱着莎乐美的希律却对莎乐美产生了无尽的厌恶。在他眼里莎乐美变成了一个怪物,恐怖而诡异。他相信莎乐美犯下了罪恶,将要受到惩罚。这表明王尔德并没有把莎乐美置于完全抛弃道德,追求艺术至上的环境中,他还是考虑到了传统道德对人的制约作用。莎乐美最终还是为她残忍而恐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她无视传统道德的行为还是受到了惩罚。
结 语
《莎乐美》为王尔德创作的经典悲剧,在《莎乐美》中,王尔德通过特征鲜明的人物刻画,新奇大胆的情节设计以及狂热的感官描写,践行了他唯美主义的美学理论。但是,《莎乐美》也不仅仅是纯粹地在展现无关道德的艺术之美,崇尚“艺术无关道德”的唯美主义理论与文中对于现实道德影射之间的矛盾在《莎乐美》中得到了体现。七层纱舞唯美妩媚,是莎乐美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和对道德的公然挑衅;月亮寄托着莎乐美对于唯美的“纯洁的处女”的期盼,但也因为希律等人被强加上了道德色彩;死亡则作为艺术与道德斗争的结果,体现出王尔德心目中艺术生存环境之艰辛。剧中人物的所言所行,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也是王尔德唯美理论中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以及王尔德自身与当时社会舆论压力、道德压迫的斗争之体现。艺术的体现总是会打破道德的界限,而他们之间的联系与矛盾,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注解【Notes】
①本文为“华东理工大学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项目”(项目编号为WS1325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张文娟:《论〈莎乐美〉的唯美性》,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2] 张文娟:《论〈莎乐美〉的唯美性》,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3] [英]王尔德:《莎乐美》,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
[4] 秦黎:《莎乐美唯美主义形象道德特征的消解》,载《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117—120页。
[5] [英]王尔德:《莎乐美》,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6] 吴刚:《王尔德文艺理论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7] [英]王尔德:《莎乐美》,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8] [英]王尔德:《莎乐美》,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9]Donohue, Joseph.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6.
[10] 邱美玲:《论王尔德文学创作的死亡主题》,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页。
[11] [英]王尔德:《莎乐美》,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12] 孙宜学:《凋谢的百合——王尔德画像》,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13] [英]王尔德:《莎乐美》,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14] [英]王尔德:《莎乐美》,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15] 刘茂生、郑少敏:《王尔德作品的死亡叙事与道德隐喻》,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218页。
Oscar Wild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19thcentury aesthetic movement. His works and aesthetic theories exerted a great infl uence on later writers. Previous studies mostly focused on his aesthetic ideas including "Art for art's sake" and "Art is useless". Recent researches have noticed his aesthetic tendency and its confl ict with morality, which is fully embodied in his one-act play Salome. The main character, Salome, as an aesthetic image, cannot be wholly separated from the moral restrictions enforced on her, which constitutes the multiple confl icts between art and morality in the play.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explore the confl ict by analyzing the dancing of seven layers, the image of the moon and the meaning of death in the play, revealing Wilde's ambiguous attitude toward his aesthetic ideal and its moral consequence.
Oscar Wilde Salome art morality
蒋润园,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徐雅恬,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 confl ict between Aesthetics and Morality in Salome by Oscar Wil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