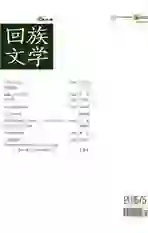黑三姑
2016-11-23川宇
川宇
黑三姑,不是别人,黑三姑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因为长得黑,我们就叫她黑三姑。后来,为了叫着顺当便索性叫她黑姑。
一个秋天的傍晚,我第一次见到了黑姑木海买。当时,她戴着黑盖头,穿着一身黑衣裳站在院子里,呆呆地看我,活像一截黑色的木头。她黑色的上衣是大襟样式,扣子是盘扣,从脖子方位一直扣到衣服的下摆。她的黑裤子很宽大,裤腿用一根细小的麻绳扎绑着。离地面最近的地方就是她的脚了。她的脚小小的,脚上穿着黑鞋、黑袜。她全身上下无一不是黑的,有点滑稽,也有点可笑。我顺着她的衣服往上看,看到的是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呆板,僵硬。她的眼睛不大,目光涣散,这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木讷、呆滞。她的眉毛又短又粗,鼻子塌陷着,嘴唇像冬天的树皮一样干裂。她看起来很丑,这是我初次见到黑姑时对她的印象。
我还记得黑姑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眼睛瞪得好大好大,很兴奋。我问她话,她也不说,只是一味地低着头,用她粗糙的手一个劲地揉搓着衣襟。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黑姑不是祥林嫂,却神似祥林嫂,我有点好奇。母亲说,黑姑是娃娃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白叶,小儿子叫黑叶,他们都在收破烂。黑姑的丈夫叫根柱,一个病身子,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根柱在的时候总是打骂黑姑,让黑姑挑水,劈柴,洗衣,做饭,下地,喂牲口。所有男人干的活,她都在干。十几年前,她要走几里路到山沟下去挑水,因为山沟下有一眼清澈的泉水。每到那眼泉边,她先是舀一马勺清清的水,一气喝下,然后再蹲着身子,把水舀到木桶里,用扁担挑着回家。一路上,还要经过几道坡,山坡陡峭,往往一担水到了家里就剩半担水了。为此她要多跑几趟。前几年十多家人合起来打了一眼井,她不用再到山沟下挑水了,可还是要上下一道坡。她们家还养了几头牛,她还要铡草喂它们,一天要喂好多次。
有一次她来我家与母亲闲聊时说,牲口比人金贵,她想做一头牛。
母亲笑着说她老糊涂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黑姑想做牛的话心里面酸酸的,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落感涌上了心头。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黑姑坐在桌旁,端着一碗米饭,母亲不停地往她的碗里夹菜,夹肉。黑姑吃得津津有味,不时还放下碗筷,拿起一块带骨的肉啃。她说,她喜欢啃骨头,那种味道别提有多香了。她啃着肉骨头,美滋滋的,就像在吃山珍海味。吃完饭,她还习惯性地舔了碗。我注视着她舔碗的动作,不禁哑然。她先是把碗边放在嘴边,再伸出舌头在碗里面旋转,几圈下来,碗里面残留的汤水便全部被吸进了她的嘴中。她有点像魔术师,被她舔过的碗就像刚清洗过一样,散发着一种幽幽的光。我看她时,她低垂着头,正用她柔软的舌头舔着她干裂的嘴唇。我看着她那卷动的舌头,不由得想到了一头拉不动犁的老母牛,一遍又一遍地舔食着牛槽里剩下的汤汤水水。
母亲说,黑姑家很穷,她刚结婚那会儿,炕上连一页席都没有,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还揭不开锅。现在生活好些了,但黑姑这些习性却保留了下来。
慢慢地,我与黑姑熟了,黑姑也不再躲闪着我,还会与我说一些高兴的事。晚上黑姑坐在母亲的炕头上,高兴地说她今天来我家的路上捡了二元六角钱。母亲问她是怎么捡的,她说她从家里出门,沿着河道走,捡了好多垃圾,有废纸,有铁丝,还有十几个塑料瓶子。到县城时,她在一家废品收购站将这些捡的垃圾卖了二元六角钱。她谋划着用这钱买一袋洗衣粉,回家洗她的脏衣服。我听着黑姑的话,觉得她怎么也不像这个时代的人。我那可爱的孩子,每天都要花十多块钱,还不知足,而黑姑捡到了二元六角钱的垃圾高兴得盘算个不停。我走出母亲屋子的时候,看到黑姑的脸上满是幸福的微笑。
那个夜晚,我彻夜未眠,眼前总是飘动着黑姑的影子。我躺着,有种窒息的感觉,总感到有一条舌头在我脸上舔来舔去,好像我就是一只吃饭的碗,而我的周围全是垃圾,围着我飞旋,不停地飞旋着,飞旋着。
第二天一大早,黑姑换了一身咖啡色的衣裳,整个人看起来素净多了。我知道这是母亲特意送给她的,母亲还送了她几包洗衣粉、几双袜子,还有一些吃的东西。黑姑要走了,我们送她到大门口。我望着黑姑远去的背影,感慨不已,她一生受苦受累,到头来还要忍受一切疾苦与磨难?黑姑走的时候是快乐的,满脸的笑。
天色渐晚,我不由得为黑姑担心,从我家到黑姑家要走十几里的路,不知她是否回到了家中?不知她是否还在回去的路上捡垃圾?
这以后,黑姑每隔几个月就来我家转转,母亲也总是做最好的饭菜给她吃,还给她买新衣新鞋。每次来,黑姑总说她解了馋。母亲笑着说,馋了,你就来吧。她点点头,怯怯地说,嗯。
这个春天过后,眼看就要到10月了,黑姑一直没有来我家,母亲有点着急,我也有点疑惑。大半年过去了,她为什么没有来我家?我们还真想她了。父亲打电话过去询问,才知黑姑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放下电话,父母就动身去看望黑姑了。他们也好多年没有去黑姑家了。等他们从黑姑家回来,我才知道了黑姑的病情。原来,黑姑的肚子里面长了一个肉疙瘩,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母亲说,黑姑仅仅是吃了几服中药,也没有到县城的大医院看病,她害怕花钱。现在黑姑稍微好些了,也能下炕来回走动,可那个肉疙瘩还长在肚子中。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沮丧。我猜,那病肯定好不了,要不母亲怎么会有那样的表情。于是,我萌发了去看黑姑的念头。
黑姑家在四河湾村,说是湾,其实不是湾,也没有四条河,只是一道山岭拐了个弯,一条河从山岭下穿越而过。黑姑就住在那道山岭上。我去的那一天,天气特别好,细碎的阳光照在脸上,暖融融的,像小孩子柔嫩的手一般抚摸着我的肌肤,让我倍感亲切。
一路上,我很少说话,只是一味地透过车窗看远处的山和节节后退的树。远处山上的树不多,零散地立在山坳里,山地里的麦子早已收割,只剩光秃秃的麦茬留在地里。一片又一片淡黄的颜色被一些绿色的玉米环绕着,山路两旁树上的叶子在柔柔的风中来回飘动。阳光则透过树叶倾泻而下,不时还有一两只鸟从树上飞起。多美的风景啊!经过朝阳村,经过马曲嘴村,经过牛头河村,不一会儿就到了四河湾村。
四河湾村总共有一百多户人,黑姑家住在一个山坡上。山坡上有两户人,一户是她的大儿子,另一户是她的二儿子。黑姑在大儿子家生活,有时也去小儿子家吃顿饭。我们到的时候,黑姑的大儿子碰巧到县城赶集去了,黑姑站在二儿子家的门外,脸上满是笑容。黑姑现在已能四处走动了,但很少吃饭,整个人看起来也清瘦了好多。那个疙瘩还长在她的肚子中,有时她会感到疼,可她就是不对人说。我们来了,她高兴地与我们寒暄,说她好多了,说她现在能吃下一大碗饭了。大姐脱去她那件洗得发白的黑上衣,为她穿上了新买的羊毛衫,她高兴得合不拢嘴。她穿着那件新羊毛衫在院子中来回走动,每走一步都要掀起衣襟看看,那眼神好像在看着自己的孙子一样,分外开心。
那天,我像个好奇的孩子,在她们家转悠着。从前院转到后院,从后院转到前院,再转出院子,转到碾麦场,转到草垛旁,转到菜园旁,最后转到了黑姑家的自留地。我顺着麦茬地走,脑子里却想象着黑姑是怎样一步步沿着河道捡垃圾,一直捡到了我家门口。想着想着,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觉到有一条毛毛虫爬上了脊背,全身上下有一种奇痒的感觉。我转过身,看到黑姑站在大门口望着我。黑姑的目光就是一条毛毛虫,让我无以安放。
我走到黑姑家的牛圈旁,听到一声牛叫从圈里传出。我隔着窗户看牛,牛也瞪着铜环般的眼睛看我。我们对视着,一句话也没说。我还能说些什么,我又能说些什么?我们喂养它,我们食用它,我们把它的骨头和汤喝进了肚子,还把它的皮穿在了身上或者脚上。我想,或许对于牛来说,它还是想做个人。我看着牛,黑姑曾经说她要做牛的那些话,好像就在耳边响起。
我们走时,黑姑站在门口相送,她的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微笑,没有一丝得病的迹象。大门外,大姐悄悄告诉我,黑姑得了癌症。黑姑知道她的病情,但就是在笑,一直在笑。她说,她离做牛的日子近了。
开春的某一天,黑姑在土炕上躺了整整三天,就笑着离开了这个世界。黑姑离开时,眼睛睁得很大,像她家的老母牛一样,看着窗外。送埋体的那天,我没有去。那天,我在另一个村欣赏着别人的笑脸,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心底莫名地难受、莫名地悲伤。这世界有人生,有人死,有人欢笑,有人悲伤……身边熟悉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终只剩我一人,最终的最终或许什么也不会剩下。
她到底做回牛了吗?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黑三姑,我的姑姑,一个名叫木海买的回族老人,她曾来过这个世上,像牛一样犁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