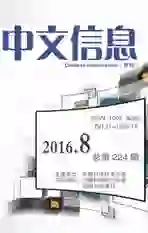从杜慎卿与“市井四奇”的形象中浅析吴敬梓的雅俗观
2016-11-22李雨薇
李雨薇
摘 要: 《儒林外史》作为文人小说的巅峰之作,在广泛展示精英政治的破产、道德沦丧与价值缺失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将自己的雅俗观暗藏在反讽的笔法中,在表现士林的众生百像的同时,通过文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口是心非与言行的背离,揭示其在道德文章掩盖下的利益运作以及在诗文歌酒之外的浅俗本性。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在市井这一边缘地带勾勒出四个奇人的肖像速写,展现了天真、纯洁、高尚的普通人形象,与前文中的“风流名士”形成鲜明对照。本文通过儒林名士杜慎卿与“市井四奇”的形象浅析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雅俗观。
关键词:《儒林外史》 杜慎卿 市井四奇 雅俗观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68-02
在古代,雅俗观是历代文人学士们品评文学艺术并进行定性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社会评价人物品行操守并进行人格分类的决定性语汇。总而言之,“雅”与“俗”是深藏中国知识分子心底的最为稳定的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而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在对人物群像的塑造中也体现了其关于雅俗的评判尺度。
一、杜慎卿:风流掩盖下的镀金俗人
“面若傅粉,眼若点漆,温恭尔雅,飘然有神仙之概”“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 陈美林:《陈批儒林外史》,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第362页。]公子而兼名士神态,杜慎卿一出场便给人以风流才子的印象,且是小说中少有能得到作者赞叹的人物。他议论诗的区区数语便将“名士”萧金铉“说的浑身透冷”,这其中固然有萧的诗作不足取的原因,然而也可以看出杜的才情;在吃食上,他也追求风流名士的清雅,桌上所摆的“只是江南鲥鱼、樱桃、笋下酒之物”,居家宴饮亦是不俗;在萧金铉提出要即席分韵作诗时,他笑道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觉得“‘雅的这样俗,还是清谈为妙”;甚至关于永乐、建文二帝的评价他也有惊人之语,足以使囿于正统之争者有所感触。
由此观之,杜慎卿比蘧公孙更具气度,比娄氏兄弟更有文采,甚至比其他所谓名士更像词人骚客,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风流公子似乎的确是个“大大的雅人”。然而这位雅人,在展现其外在的风流潇洒后,又没有表现出任何刚健昂扬的内在风骨支撑,这不禁又使得我们雅人名士的身份产生质疑。
在与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同游雨花台时,“杜慎卿在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矫揉造作,毫无欣赏山光水色的心胸,与后面相约去雨花台看落照的菜佣酒保形成鲜明的对比。莫愁湖盛会看似风雅,本质上也却又成为了杜慎卿沽名钓誉的平台。以上种种使我们认识到“风雅”不过是这位“名士”求名的手段。杜慎卿的所谓的“雅”只是一种浮在表面上的风雅,一种浸透了“六朝烟水气”顾影自怜。
除了刻意追求风雅之外,杜慎卿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也实在耐人寻味。《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曾有评语,即“‘功名富贵为全书第一着眼处”。这就连所谓的名士杜慎卿也难免牵涉其中。由于吴敬梓在塑造人物时主要运用了反讽的手法,并且,他也并没有以道德权威的形象对人物的行为做出评价,只是将人物言行全面呈现任由读者体会,这不仅使得小说中许多人物的言行具有前后矛盾的特点,也使得吴敬梓的雅俗观被深深地隐藏起来。对此,我们需要详细的分析杜慎卿的前后矛盾的言行来体会所谓“名士雅人”对于功名利禄的真实态度,进一步解析吴敬梓在杜慎卿这个人物身上投射的雅俗观。
杜慎卿口口声称自己“最厌的人,开口就是纱帽”,然而当郭铁笔送他图章时,道了许多仰慕的话,什么“尊府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 ,天下都散满了”、“管家们出去做的是九品杂职官”,什么“天长杜府老太太生位太老爷,是天下第一个才子,转眼就是一个状元”。杜慎卿一面说这些是 “恶谈” ,一面却又说“亏他访得的确”,表面上是斥责他人的语气,要通过言语上蔑视功名富贵来维护自己的名士风度,骨子里却是自鸣得意,显然为祖上历居高官而骄傲。除此之外,杜慎卿对待科举的态度也值得考量。虽然杜慎卿力求在精神领域保持其优越性,瞧不起醉心科举的狭隘俗夫,然而却也始终摇摆于科举道路与名士风流之间,所以他的行为始终摆脱不了市侩气。当鲍延玺向他借银寻求帮助时,他却说是因为“自己这一两年内要中,中了后要使用银子”中与不中 ,很难预料,必是“中”之前用了银子,才知“这一两年内要中”。中前要用银子 ,中后又要银子去谋求官职,可见其出仕求官的心切。
以上种种“名士言论”与“求名利之行为”形成了一种巧妙的“自然之讽”,在杜慎卿身上展示了《儒林外史》中普遍出现的文人“失真”的现象,即或者言行不一,口誦圣贤之言,却行为不端;或者一派名士风范与言行,却借此求名求利。深究此现象出现的原因,仍逃不过“功名富贵”四字。因此,杜慎卿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即使杜慎卿通过种种手段为自己套上名士的光环,用名士的言行来掩饰自己求利的目的,但在蛛丝马迹之间依旧流露出其内心沾染的世俗社会功名富贵的铜臭。尽管一派名士风范,其内心却缺乏对文人文化的真挚追求,空有名士之皮却无名士之骨,看似风雅,却实在称不上真正的名人雅士。杜慎卿本质上不过一个追求一己之利的禄音之士,是风流掩盖下的镀金俗人。
二、市井四奇:边鄙角落中的雅士
市井四奇出现于《儒林外史》的倒数第二回,该章节一开头便是一个对南京文人生活的纵览式描述:“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花坛酒舍,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
这表明儒林间的风气进一步堕落,在这种环境下,儒林中已经很难再出些品性高洁的名人雅士。于是,在这一回中,作者塑造了俗世四奇的形象,将他们放于市井俗世中,却又让他们分别精通琴棋书画这四门标志文人品味和修养的艺术。“俗”的身份与“雅”的艺术,似乎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却又和谐的出现在在俗世四奇身上,这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进行一个雅俗的定义,甚至模糊了我们对于吴敬梓雅俗观的认知。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深究一下吴敬梓安排此矛盾现象的原因,从另一个方面来探究吴敬梓的雅俗观。
为什么吴敬梓非要把这四个人物写成普通的市井小民而不是儒林中人?为什么一部题为《儒林外史》的小说偏偏结束于退出而不是回归文人世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恰恰正是因为他们市井之人的身份才使得他们对于文人文化的热爱格外真挚,他们操习一门艺术,或追求某种学问,是因为他们真正热爱,而不是像文人通常所做的那样,以此作为博取个人荣耀的一个晋身之阶或积累文化声名等名望资本的手段。换而言之,正是因为他们市井中的低贱行当和地位,使他们远离了社会升迁的晋升阶梯,也远离了精英世界,由此确保了他们追求文化艺术的真诚性。于是,比起杜慎卿等所谓名士所追求的表面形式的“雅”,他们热爱琴棋书画所表现的“雅”是一种更为不言自明的真诚的“雅”。
事实上,市井四奇之一的荆元与其朋友在关于“雅人”与“做雅人”一事上吴敬梓也暗藏了自己的雅俗观。
荆元的朋友曾经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想与?”荆元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
荆元的朋友认为他之所以迷恋诗歌、书法、音乐和书籍,是因为他想成为“雅人”。他们的结论很清楚,如果他不放弃裁缝这个上不了台面的行当,就是做梦也达不到这个目的。荆元的回答,直截了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小说在这里,再一次使用了“做”这个词。荆元的朋友用它来形容荆元对艺术和学问的痴迷时,暗示了一种算计和执意的努力,目的是为了改善个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但是荆元自己却表明,他的文化活动只是自娱自乐,没有任何外在功利性的目的。于是这种“自娱自乐”反而使其到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雅”,是吴敬梓所追求文化人格。
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吴敬梓在塑造俗世四奇的形象时并非要刻意突出他们“俗”的身份,其本质上还是要突出他们的“雅”,展现一种摆脱世俗利益的自觉的文化追求和高尚人格。但吴敬梓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一个“俗”的身份可以将“雅”与“雅”自身携带的声望利益割裂开来,保证文人所展示的对“雅”的追求与其内在修养是一致的。因此,市井四奇虽有着“俗”的身份,身处边鄙角落中,但却实在是一群雅人名士。
三、吴敬梓的雅俗观浅析
通过杜慎卿与市井四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吴敬梓雅俗观的评判标准是看人们对于文人文化的实践是否是真诚的、真挚的,归根结底为一个“真”字。之所以为本质为文人中“雅”的代表的市井四奇安排世俗的身份,是在其文化理想破灭,文人“失真”现象普遍出现的无奈之举。
而关于什么是“文人失真”,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这些以杜慎卿为这些文人代表的最大特点,即对于儒家伦理道德和文人文化理想的实践也是越不过“功名富贵”四字,并非是其内心真正的精神追求。儒学一旦蜕变为利益交换的工具,它在传递价值、弘扬美德和构建现实中所起的中介角色也就随之消失了,而儒学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因此这也可以理解为何“真”可以成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雅俗观的评判标准,为何俗人可以是雅,雅人可以为俗,因为“真”的背后是对儒学真挚的、真诚的实践,是一种儒家特有的人格理想,而这种人格理想正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和遗世独立的超然情怀。吴敬梓的雅俗观是把文雅和庸俗作为文化人格直接对立起来。这种雅俗观并不与人的身份等级和政治地位相联系,而是以人格为基础、以文化为准绳,形成的新的雅俗观,这体现出一种文化的自觉意识。
结语
虽然吴敬梓的雅俗观并没有摆脱儒学的范畴,但是他在以“儒家禮教”为雅俗标准的基础上却有了超越和改进,即是否对儒家礼教进行真挚的、真诚的实践。“真诚”成为吴敬梓雅俗观的另一重标准,如果仅仅将实践儒家礼教作为求名求利的手段,则也要被归为俗类。除此之外,他的雅俗观也突破了儒家传统的身份等级的限制,将四位市井之人放入“雅”的一方,醉心名利、矫揉造作的士子杜慎卿反倒被归为俗类,这体现其雅俗观的进步性。
参考文献
[1]陈美林:《陈批儒林外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
[2]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三联书店,2015年。
[3]顾鸣塘、陶哲诚:《〈儒林外史〉精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周先慎:《明清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5]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6]涂荣:《杜慎卿形象的生成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02期。
[7]涂荣:《<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创作心理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6年。